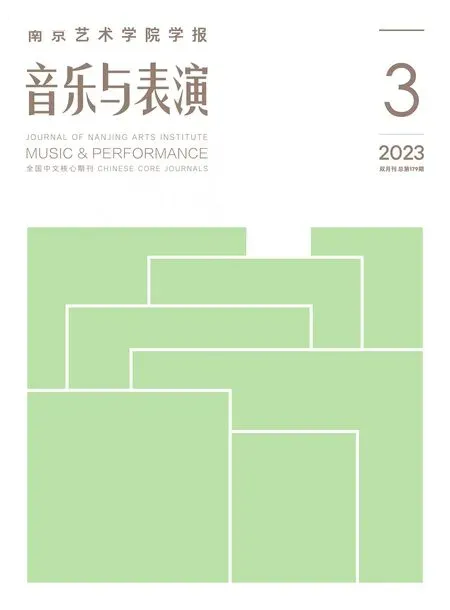21 世纪前后中国慢电影的美学特质及其沉思体验
2023-12-23孙力珍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孙力珍(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引 言
近十余年来,西方电影理论界有关“慢电影”(Slow Cinema)的研究方兴未艾,且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导演及其作品被纳入到这一研究视阈内①在《蔡明亮与缓慢电影》一书中,作者林松辉整理出当代电影中“惯常的嫌疑犯:经常出现在缓慢电影论述中的当代导演”,其中,侯孝贤先后三次在米歇尔・西蒙、弗拉纳根、阿德里安・马汀(A. Martin)论述慢电影的文章中被论及;而贾樟柯则两次分别在弗拉纳根、阿德里安・马汀有关慢电影的表述中出现。(详见林松辉.蔡明亮与缓慢电影[M].谭以诺,译.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18.)。这为我们探索中国电影的“慢美学”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参照。要指出的是,判断一部电影的叙事节奏、视听影像是快还是慢,这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判断的标准也存在着时代、地域、文化与个体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将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慢电影”指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电影?电影文本中的“慢美学”特质如何被创作主体呈现继而被观众感知?
2006 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于国内上映时和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撞车”,遭遇几乎无人“捧场”的窘境。无独有偶,2015 年侯孝贤推出武侠片《刺客聂隐娘》,再次挑战了观众视听体验的耐性。停留在武侠电影惩恶扬善叙事惯例中的观众,面对叙事情节与视觉影像如此之“慢”的武侠片,直呼“看不懂”,甚至出现中途退场现象。自《风柜来的人》(1983)以降,侯孝贤再也无意创作娱乐观众的电影作品。实际上,21 世纪前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拍摄缓慢电影的导演,如台湾地区的侯孝贤、蔡明亮;大陆的贾樟柯、毕赣、王小帅、胡波等。这些创作者所拍摄的影片,在形式上呈现出缓慢的影像风格。这种风格特征,以反类型手法区别于主流电影的经典叙述,展现出丰富的视听影像内涵;从内容上,这类影片展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等),反映时代迁卷,并在可见、可感、可思的影像当中,折射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情感意识与精神面貌,这也使得中国慢电影在国际影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慢电影、慢美学及其审美特征
从词源学角度来说,在2016 年版《新编现代汉语词典》中,“慢”被释义为“速度低,走路、做事等费的时间长(跟‘快’相对)”。[1]这使“慢”本身的含义往往被贬义为“落后、效率低”等代名词,致使诸多研究将“慢”放置在“快”的对立面,忽视了慢在其他美学层面的延伸含义。而“慢”在美学、思想等层面的延伸,也正是本文试图从思维模式跳脱这一“快/慢”二元对立的窠臼。
正如法国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慢》一书中,对“速度”展开思考,并从机械加速形式,深刻地反诘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2]实际上,昆德拉对“快”与“慢”的这一诘问,揭示了人们身处急遽发展的现代社会,丧失了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曾拥有的从容和悠闲。在这个意义上,“慢”具有以“审美现代性反思社会现代性”[3]94的含义。近年来,“慢”这一概念也相继在诸多领域出现,如1989 年法国倡导的“慢食运动”①1986 年,意大利人卡尔洛·佩特里尼提出“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其目的为“通过保护美味佳肴来维护人类不可剥夺的享受快乐的权利,同时抵制快餐文化、超级市场对生活的冲击。”受到慢食运动的启发,不少推广慢活观念的组织和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详见林松辉.蔡明亮与缓慢电影[M].谭以诺,译.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3。)以及不少国家兴起的“国际慢城”计划,甚至中外电视里也都出现了一些“慢综艺”的节目。这说明“慢”不再必然是落后、低效率的代名词,而是意味着人们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21 世纪前后,这一理念蔓延至电影领域。2003 年,法国电影评论家米歇尔·西蒙(Michel Ciment)提出了“慢电影”这一概念。之后,此概念就一直被广泛用于指代“以循序渐进的节奏、极简主义的场面调度、简洁晦涩的叙事为主要特征、坚持长镜头作为自我反思的修辞手段的影片”。[4]然而,此概念的提出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以《视与听》(Sight and Sound)杂志主编尼克·詹姆士(Nick James) 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这一类电影将不过是艺术电影导演为电影节和电影批评者特定生产的影片”[5],并以此指责慢电影以消极的态度抵抗好莱坞经典叙事电影模式。有别于尼克·詹姆士激进的言辞,英国华威大学的学者卡尔·斯库诺佛(Karl Schoonover)指出:“慢电影并非单纯对好莱坞经济学无意义的攻击,反而是向更大的系统说话,那系统将价值与时间、劳动和身体,以及生产力和文化生产的特定模式和类型紧密联系。”[6]
实质上,“慢电影”是在人类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甚至娱乐休闲时的行动节奏亦愈来愈快——的时代语境下被提出的概念,它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时间,尤其是对非戏剧化的日常生活步调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在昔日曾经拥有的从容和悠闲生活的缅怀。慢电影也并非一个有着严密逻辑内涵与外延的电影类型学概念,而是在现代语境下具备反叛精神和自我反省意识的一种艺术理念和价值追寻。在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侯孝贤所执导的《悲情城市》(1989)、《戏梦人生》(1993)、《海上花》(1998)、和《咖啡时光》(2004)等影片中,导演不断尝试“减缓来自命运转折点的个人创伤的速度,使我们在这些移动的纯粹时间中面对未知的绵延”。[7]蔡明亮导演的《洞》(1998)、《黑眼圈》(2006)、《脸》(2009)和《郊游》(2013)等影片,更是人们公认的“慢电影”代表性文本。而深受侯孝贤影响的大陆导演贾樟柯,从《小山回家》(1996)开始,亦倾向于建构“缓慢”的影像叙述。②面对他人质问:“为什么要用七分钟的长度……去表现农民工王小山的行走呢?”贾樟柯坦言:“当下人们的视听器官习惯了以秒为单位进行转换……这长长的七分钟,与其说是一次专注的凝视,更不如说是一次关于专注的测试。”参见贾樟柯.贾想I: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13。新锐导演如毕赣、李睿珺、胡波、杨超等人,同样采用了缓慢电影的形式,探讨关于时间、生命乃至情感的相关议题。上述导演的创作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慢电影”向观众提供一种另类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所彰显出的慢美学特征,可以从以下层面进行理解。
从全球文化语境出发,考察“慢”所具有的美学含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广义而言,美学是体现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但早在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中国当代美学开始从研究“美是什么”转而研究“审美”,这种“美学转型是由美学所面对的事实决定的”。[8]23美学离不开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不是认知活动,审美对象不能从审美活动中超越出来而存在。“正是这种审美事实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将研究的目光对准审美活动……而不再对‘美是什么’作形而上的追问。”[8]24
同样,本文对“慢美学”的理解,也是从审美活动的立场出发,考察“缓慢”的审美特征,表现为对当前现代化语境中文化所隐含的加速现象的一种反拨。具体而言,现代/后现代社会语境强调视觉媒介逐渐趋向碎片化、断裂感、浅表化。而“缓慢”的审美内涵,注重观看/阅读的完整性与持续性,拒绝当今短、平、快的视听文化侵扰,要求观众放慢观看与聆听的速度,深入感受影像或文本背后隐藏的文化意涵与持续的时间性,浸入沉思的可能性。
21 世纪前后中国慢电影的美学特征,并非仅仅是指出叙述与影像节奏的缓慢,而是“透过使用长镜头、延长的时间和等待的喻象语法来建立影片与观众的不同关系”[9]41。进一步而言,电影中的慢美学是由观众参与其中的审美活动构成,提倡新的时间经验模式、观看方式,以及在审美活动中形成新的观看主体。
由此,将“慢”作为电影的美学/审美观念,“并不像电影类型学那般建立几个标准来判断什么电影属于‘慢电影(Slow Cinema)’的范畴。而更重要的是拟定某些坐标,论述电影产生缓慢之感的机制及其对意义生成的价值”。[3]93一般而言,“慢”体现在电影的形式层面,创作者通过缓慢的美学策略,电影的叙述与视听风格可以呈现出令人感到无聊或是沉思的影像时刻。从电影的叙事与影像风格两大维度入手,可以进一步描述具有一定共性的、缓慢的创作机制。
在叙事层面,一些电影导演经常有意以戏剧冲突之“淡”,来营造或强化叙事节奏的“慢”,这不仅使得银幕角色跳脱了戏剧情境的约束,而且造成了一部分观众对叙事节奏的陌异体验。换言之,这颠覆了一部分观众业已固化甚至窄化的观影习惯及其对影片的接受模式,向他们提供了新颖、另类、迥然不同的审美体验。
在视听语言层面,长镜头内部的“无为时间(dead time)”①“dead time”一词源于玛丽安·多恩的《电影时间的浮现:现代性、偶然性与档案》一书。在本文的论述语境中,将其译为“无为时间”,用以表示在长镜头绵延之下的无事发生的时间,某种意义上浪费掉的、耗费却无结果的时间。(参见Mary Ann Doane. そ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 Modernity, Contingency, the Archiv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41. )成为衡量影像是否能够提供“慢感”体验的关键元素之一,它强调“无事发生”或“很少有事发生”的时间形态在长镜头中的完整呈现。这使得观众被迫直面非戏剧化情境下时间的本真状态,进而产生心理上的缓慢之感。当“慢感”体验生成且被感知时,观众得以进一步体悟慢美学视阈下银幕角色身体的“非生产性”特质。这不仅可以调动审美主体的沉思体验,而且能够激活审美关系中观众观看行为的主体意识。
二、“慢”中显形:叙事情节的迟延与缓慢镜语的生成
21 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一些主流/商业大片以大场面、快速剪辑、组织碎片时间等手段,形成模糊和表层的感知方式,造成了审美意蕴的浅薄。电影也由此被认为是与现代“加速时代”合谋的文化商品。在这种时代语境之下,国内一些慢电影的创作,以叙事情节的迟延和缓慢镜语的生成,形成了可见、可感与可思的影像时间与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时代状况乃至情感议题的深度感知与体验。
(一)叙事情节的迟延
叙事情节的迟延主要体现在淡化戏剧性、无事发生、陌异体验这几个方面。虽然“淡化戏剧性”并不必然导致电影产生缓慢之感,但是戏剧性的退场或者弱化,通常会使得大量的日常景观和无事发生的时刻在电影中显现。在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中,淡化戏剧性表现为情节的线性因果链消失了,影像常常表现为无事发生的日常琐碎。淡化戏剧性的做法并非仅仅意在营造某种氛围或诗意,而是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提供一种特殊的审美方式,以“缓慢的动作重新诠释主体与世界、距离与速度的关系”。[10]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存在着大量日常性的、没有紧密线性因果链的情境所组成的影像序列。影片《三峡好人》始于一个极为平常的乘船场景。在这个长达3 分钟的场景当中,缓慢的横移镜头扫过一群乘客,展现他们乘船时的无聊状态——静坐、打牌、聊天、看手相等。即使镜头“发现”了主角韩三明,也并没有表现激烈的冲突事件,而是伴随着韩三明的视线,切换至三峡的景观。这种开场段落既没有丰富的人物动作,也没有交代性的叙事“开端”。可以说,戏剧性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无事发生的时刻迫使观众搁置对戏剧冲突的期待,转而注视“日常化”的影像内容,不得不将注意力聚焦于影像本身。
这一方式在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中表现得更为极致。影片《海上花》的开头以一个长达8 分钟的镜头呈现中国清朝末年青楼里的酒桌文化。场景中既没有出现叙事动机,也没有交代主要角色——王老爷、沈小红和张蕙贞——之间的矛盾冲突,只剩下无事发生的日常时刻和人物的生活状态。侯孝贤在接受采访时声称:“Action(动作)不是我感兴趣的……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这个痕迹里头活动。我花非常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11]淡化戏剧性与无事发生的“反故事”形态,成为侯孝贤“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使得影像展示的比角色所陈述的以及情节所表达的要丰富得多。换言之,在这样的影片中,影像不再只是叙述故事及演绎情节的工具,而是重新赢得其在电影中的主体地位和核心价值,人物和情节等其他元素则退居次席。
叙事情节的迟延导致不同的叙事段落之间缺乏明晰的因果关系。这会阻滞某些观众的期待视野,致使他们无法进入自己习以为常的审美模式中,也会使一些观众产生陌异的(甚至是负面的)观影体验,获得一些另类、新颖、非主流、非传统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叙事情节的迟延可以阻止观众过度地沉浸到剧情当中,防止观众过于被剧情裹挟,使观众与剧情之间保持适度的间离,从而在观影过程中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智和思考。
(二)长镜头绵延下缓慢镜语的生成
安德烈·巴赞的场面调度理论强调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他之所以提倡纪实性美学,是旨在将生活的完整性和多义性尽可能如实地展现出来,以此达成人对客体世界的尽可能完整的感知。与之不同,慢美学视阈下的长镜头是“对巴赞以来的现实主义长镜头理论的一种‘逸出’或称‘逃逸’”[12]。如果说慢电影使一部分观众(尤其是习惯于主流娱乐片叙事节奏的观众)的审美期待受挫,那么,慢美学视阈下的长镜头则强化了观众直面“无为时间”的缓慢之感。长镜头绵延下的“无为时间”加剧了叙事情节的迟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另类的、反主流的审美场域的建构。
一般认为,长镜头经常作为营造影像慢感体验的方式之一。然而,镜头越“长”,电影就必然会越慢吗?实际上,很多影片的实践都表明:长镜头并非“慢”的代名词。以萨姆· 门德斯(Sam Mendes)执导的《1917》(2019)为例,整部影片由一个镜头拍成,但是该长镜头不仅承载了强烈的“事件”效果,而且把行动集中在连续的时间之内,充分利用时间张力结构中的戏剧性元素,营造紧张激烈的冲突。故而,镜头的长短本身并不意味着慢/快。为了避免落入“长”等于“慢”的思维定式,我们需要重返镜头内部,考察长镜头调度中“无为时间”的显现如何消解了时间的事件性价值,促成了影像的慢感体验。
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在《电影时间的浮现:现代性、偶然性与档案》(そ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 Modernity, Contingency, the Archive)一书中,阐述了时间的“事件性”价值。她认为:“为了生产意义,叙事电影在一个‘有事要发生’的意义上坚持事件概念,以证明它在确定的时段内成为摄影机关注对象的正当性。”[4]因此,电影的时间就此被“打包为时刻:时间被凝缩,变得非常有意义”[13]。然而,许多慢电影作品对时间的“事件性”通常毫无兴趣,相反,它们常常将“无为时间”纳入到视听体验当中,致使在接受场域内,慢电影客观上是要求观众在持续性的观看过程中,实现对银幕内信息充分而深入的感知,并且在此基础上调动自己的想象和联想,进入审美再创造的广阔天地。
《刺客聂隐娘》中,侯孝贤用三次长达数分钟的长镜头来模拟聂隐娘的视角,表现她藏匿于暗处,观察大寮政务及其日常生活。这种貌似无事发生的长镜头,实际上让观众充分看到和意识到聂隐娘的迟疑,并且感同身受地去想象聂隐娘内心的矛盾和纠结。换言之,侯孝贤导演不是刻意地表现女主角的内心状态,而是巧妙地诱导观众去想象和体悟女主角的内心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路边野餐》中,主人公陈升在简陋的发廊中,以第三人称的口吻缓缓道出自己与妻子的浪漫婚姻,后来因还债而锒铛入狱,以及其妻因病而亡的生命历程。在这一段落中,时间的流逝中弥漫着陈升对妻子的愧疚之情。发廊中看似无事发生的“自说自话”揭开了男主角内心世界的“冰山一角”,也开启了他在现在时态中自我救赎的可能。在此,虽然并没有任何戏剧性事件直接地或者直白地发生,但长时间“无事发生”的背后,片中角色的丰富情感,需要观众在持续性的观看和积极的想象(即审美再创造)中才有可能充分感知影像背后含藏的复杂情绪。与上述两部影片类似的是,在《清水里的刀子》一片中,导演亦摒弃了戏剧性的方式,采用极为缓慢的影像,表现中国西部的日常生活,通过缓慢的日常生活里所潜藏的生命力与西部恶劣环境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呈现出“生与死”的旷日持久的对抗。这种“对抗性”不仅凸显了生命/时间的缓慢流逝,而且使观众更深地感受到角色面临艰苦、单调生活的孤寂感。
从这一角度看,电影中的“缓慢”很大程度上是观众与电影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与视听影像的建构,在影片刻意回避和减少叙事行为的同时,致力于开启一个可以在影片内进行美学沉思与反省的时间和空间。
三、沉思体验:拒绝遗忘与主体意识的显现
在大部分主流叙事电影的制作中,“快速剪辑”迎合了速度文化的特征,“剪辑师剪得越频繁、越分裂,或者越粗暴,观众的反应就越积极、越激动,对电影时间的体验就越快”[14]。这种“快速”的影像体验鼓励观众遗忘过去甚至当下,进而一味追求感官上的快感——一种短时间的、生理上的本能反应。而21世纪前后“缓慢电影在各地出现,既回应社会领域中加速的现代生活,也重塑了人们感知回应叙事电影中对时间的处理方法”[9]6。这种回应在中国电影的慢影像实践中,通常以“慢感”体验拒绝遗忘过去,并使得记忆在现时影像中不断地生发与积淀,这增强了影像的蕴藉性。此外,在接受场域中,记忆生发与情绪累积也营造了内省式的视觉感知功能,激发审美主体的沉思体验,形成反思性的审美场域。
(一)拒绝遗忘:记忆的生发与情绪的绵延
中国慢电影影像实践的重要特征即“拒绝遗忘”。这种“拒绝”的姿态建立在长镜头内部持续性时空同一的基础上,并由证物的出现、抑或角色的日常对话所生发的记忆与情绪在持续性的时间与空间中弥散开来,使得过去记忆在当下现时影像中氤氲与积累。凭借记忆的生发“渗透个人情感、精神指向的审美经验”[15],以此补全现代个体缺失的精神向度,达到一种颇具蕴藉性与持续性的审美体验。
“拒绝遗忘”即拒绝忘记有关过去的记忆。如果说记忆的生发是“建立在对过去的各种指涉形式的基础上”[16],那么,中国电影的慢影像实践中,有关记忆的叙述主要是通过证物的发现、抑或经由日常言说对曾经某件事物的提及,引发个人/群体对过去的道德情义、家园、历史等的怀想。诸如贾樟柯的《小武》一片,影片约17 分01 秒处,主观长镜头随着满是怨气的小武逼近(曾经)好友靳小勇家门口,他并没有横冲直撞直接进去质问(为什么结婚不通知他),而是在门口徘徊片刻,并伸出手抚摸那块刻有(他们曾经)比试身高痕迹的墙壁。这一“痕迹”引发了小武对过去友谊的回忆。这一回忆并没有采用闪回镜头来表现,而是在长镜头持续时间内以小武的犹豫、抚摸(墙壁)、低头沉思的零碎动作来加以衬托、暗示。在上述具有“慢感”体验镜头当中,小武对兄弟情义的怀想、记忆,使得他在急遽发展的时代中,仍然保留了具有“情义担当”的主体,而非小勇在资本裹挟下极力抹除自己过去的历史。在慢电影美学视阈中,无论是从个体本身出发,还是从时代潮流发展进程出发,拒绝遗忘是“小武”在影片中叙事的逻辑起点。而在《三峡好人》中,当摩的小哥载着主人公韩三明到达“青石街5 号”后,面对韩三明的质疑,摩的小哥指着眼前汩汩流动的江水,操着一口四川口音无奈道:“这底下以前是我的家。”此时,曾经的“家园”与当下的“江水”形成鲜明对比,有关“家园”的记忆在这一时刻被提及,暗示了时代变革下人们被迫离散,但是有关家园的记忆却不曾消失。流动的江水此刻反而被赋予了“纪念碑”属性,其稳定性与个体拒绝遗忘的无效性(拒绝以往并不能改变现实)在两人身上呈现出一种背反的张力:作为个体的“人”的多重维度在须臾之间获得释放。
如果说贾樟柯电影通过这种含蓄、缓慢的动作、语言来表达对友谊、家园的记忆与留恋,那么,毕赣以角色的游荡、观察与极为日常的言说形成对往事的描写。如《路边野餐》42 分钟的长镜头中,导演以极为日常化的影像,将主人公陈升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心理状态凝缩在“荡麦”这一超现实空间中,实现了其对妻子情感上的弥补。这样的角色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如出一辙(如主角罗纮武在梦幻之镜中见到遗弃自己的母亲)。这种缓慢的视听影像中对记忆的回溯,成为个体弥补精神创伤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形成了“创伤—记忆回溯—释然”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创伤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分析层面的,而缓慢的记忆回溯和想象性情境建构为精神分析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主体在现在时态中的救赎,也就是解开心结的释然。
由此,“慢下来”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可见与可感”,而是使观众在当下体验过去的时间、空间,进而引发审美主体在接受过程中的沉思体验,重新认识本体、发现本体乃至重构本体,激发银幕中角色的现代主体意识的萌动。
(二)从无聊到沉思:现代主体意识的萌动
从《三峡好人》《刺客聂隐娘》《地球最后夜晚》遭受的市场冷遇可以看出,在接受场域中,一些观众以原始状态面对电影的“慢感”体验时,表现出强烈的无聊特质。海德格尔将“无聊”一词解释为“冗长的、单调的;既不刺激,也不兴奋”[17],“冗长的、单调的”描述的正是被展示对象的状态,而“既不刺激,也不兴奋”则描述了审美主体面对被展示对象时的心理感受。于是,“拒绝无聊”在此表明了审美主体与时间的关系。在这一层面上,慢电影美学所诉诸的缓慢之感,实际上造成了观众直面“时间”本身的可能。诸如侯孝贤电影以长镜头表现女性游荡姿态与主体意识的觉醒,贾樟柯电影不断诉诸时代痕迹的“静照”,甚至毕赣以极端的长镜头聚焦个体孤独的生命状态。进言之,“慢下来”的影像美学,以迫使观众直面时间乃至回溯记忆的方式,映射了“时间的集体性和反思性体验极端匮乏”[18]的现代社会。而缓慢的影像机制对现代性体验的捕捉与陈述,致力于唤醒被速度异化的人的主体意识,并将其从慢感体验中强制性析出,重塑了内省式的视觉感知功能。
埃米尔· 莱安(Emre Çağlayan)认为:“慢电影强调观察是一种参与模式,并渴望通过将屏幕持续时间与不间断的实际时间等同起来,使观众产生催眠抑或沉思效果。”[19]如果说“催眠”一词对应了慢美学中的“无聊”特性,那么,“沉思”则唤起了观众在观看行为中自主意识的维度。如《咖啡时光》(2003)中,长镜头下未婚先孕的阳子,因童年被母亲遗弃的遭遇,阳子拒绝踏进婚姻/两性殿堂,并坚持独自抚养即将出世的孩子。面对父母、朋友的质疑的目光,阳子亦采用沉默与坚决的态度予以回应。这种叙述方式不仅改变了接受者(观众)受(叙事)支配的状态,且银幕角色的日常行为迫使观众从叙事中抽身出来,主动参与到银幕角色的状态当中,并进入与银幕角色同等的境地。以王学博的处女作《清水里的刀子》(2016)为例,在面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时,导演为保证影片的意境与在地性,摒弃了戏剧性的方式,以极为缓慢且克制的影像,深入当地日常生活的循环,酝酿出“向死而生”的死亡哲学命题。这一命题亦不是由角色演绎出来,而是通过缓慢的日常生活所彰显的生命力与影片所描述的西部恶劣环境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表现出来,呈现出“生与死”的对抗。这种“对抗性”不仅凸显了生命/时间的缓慢流逝,而且使观众更深地感受到角色面临生死的孤寂感。这也表明了观众对于“慢”的感知,在于其体验到时间在电影中的绵延,而不是被叙事技巧、蒙太奇等压缩时间方式操控。
因此,慢电影及其美学视阈下现代主体意识的表征,一方面表现为银幕角色摆脱了叙事蒙太奇的支配,以拒绝遗忘的身体姿态游走于可见甚至可感的影像中,呈现出强烈的时空纵深感;另一方面,在接受场域中,观众因叙事情节的迟延,产生陌生化的观影体验,这使得观众以一种参与式的姿态浸入纯粹的影像感知当中,并形成自觉观看的意识。于此,慢电影及其美学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观者自主感知影像的活力,更新了其体察影像世界的方式。
结 语
慢美学对效率、速度、时间乃至人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关注与反思,为我们重新审视21世纪前后的中国艺术电影①除却本文所涉及的中国当代艺术电影中具备“慢”特质的电影导演之外,外国电影诸如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Béla Tarr)、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Nuri Blige Ceylan)、塞米·卡普拉诺格鲁(Semih Kaplanoglu)、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等,也经常作为慢电影的典范被援引和加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这个新的视角来探索中国当代艺术电影的审美意蕴和价值诉求,可为电影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提供另一种思辨的维度。德·卢卡指出,慢美学“在接受场域中培养了持续观察影像的方式,可能会使感知恢复活力,并更新观察世界的方式”。[4]确实,倘若把以好莱坞主流娱乐片为代表的美学称为“快美学”,那么,“快美学”主要是借助蒙太奇等手段,以人为组合的一大堆时间和空间的碎片搭建了一个精彩而虚假的世界。相比之下,慢美学恰恰致力于促使观众以一种安静的、从容淡定的、更加深入细致的方式去观察和感知这个真实的(尽管或许有些平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