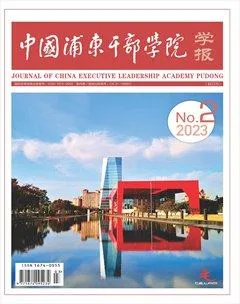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一元化领导的主要动因、举措和成效
2023-12-20魏德平
摘 要:中国共产党由于受“王明路线”影响,曾遭受重大损失,也影响中共党组织领导权威,诱发张国焘以军事实力为依靠挑战中共党的领导权威。延安时期,中共在面对全面抗战新局面时也曾出现中共党组织对军队、政权以及其他中共领导的组织和团体弱化和虚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共发展的亟待解决的严重制约因素。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将中共建设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核心的任务和使命,通过处理典型党军关系事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确保中共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实现。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决议和决定明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并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延安时期,中共加强一元化领导强化了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巩固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借助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也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形成。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毛泽东;张国焘
新中国成立前夕,时逢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文中总结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时强调:“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1480文章高度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关键性作用。中共之所以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这与其始终强调自我完善和发展,高度重视党建有密切联系。延安时期中共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中共加强党的建设的成功范例,值得深入探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一元化领导相关既有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郭为桂、胡俊祺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为主要文本,考察“党领导一切”的观念和体制发展历程,指出从建党时期到土地革命时期,观念层面的“党领导一切”主要指党领导一切群众斗争(群众运动),强调党对其他组织的绝对领导作用,同时初步建立了党领导军队和领导苏维埃政权的体制;全面抗战时期,观念层面的“党领导一切”主要指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并侧重于构建横向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一元化领导)。[2]高中华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融合在一起,开展“双拥”工作,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化解了党政军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之脉。[3]张冰强调,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围绕政党控制逻辑,探索推进了一元化政府领导体制创新,其中包括:以党委(而非以职能部门)为中心的“平面化”管理;以任务(而非以规则)为中心的层级指挥管理;基层面向的资源配置及政府运作方式等。这一模式创新,极大地增强了革命时期中共的竞争优势。[4]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领导地位方面,而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相关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本文以基本史料为基础,旨在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一元化领导的主要动因、举措和成效进行探究。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
一元化领导的主要动因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到“王明路线”影响,遭受重大损失,也影响中共党组织领导权威,诱发张国焘以军事实力为依靠挑战中共党的领导权威。延安时期,中共在面对全面抗战新局面时也曾出现中共党组织对军队、政权以及其他中共领导的组织和团体领导的弱化和虚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共发展壮大的亟待解决的严重制约因素。
延安时期中共强调一元化领导与恢复和加强中共党组织领导权威密切相关。土地革命后期,“王明路线”给党中央和全党造成严重损失。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5]86“王明路线”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所犯的“左”倾错误,不但对中国革命造成深重灾难,同时也动摇了中共党组织的领导权威。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会师后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和张国焘会合后,双方在中共政治路线、红军主力发展战略方向等关键问题方面逐渐发生尖锐分歧和争论。张国焘开始凭借其掌握的红四方面军优势军事力量向中共中央权威发起挑战。1935年8月沙窝会议期间,毛泽东曾批评张国焘:“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6]223-224双方由于都难以说服对方,最终公开分裂。[7]107-109随后,张国焘另立“中央”,公开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8]299张国焘在得到党内军中部分力量支持后,逐渐开始以正统“中央”自居。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组建的“中共中央”致电已经转战抵达陕北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因此,“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张国焘甚至提出:“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9]959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再次致电林育英:“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10]964张国焘挑战中共中央领导权威在当时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造成很大困难,也给毛泽东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斯诺向毛泽东提问:“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回答:“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11]213张国焘依恃军事力量优势对中共中央发起挑战使中共中央必须严肃考虑中共党组织和军队之间的关系问题。
延安时期中共也面临为应对新形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考验。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对革命事业的领导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对军队的领导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中共对军队的领导权有所削弱。1937年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在前线的军事领导人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明确提出部队政治工作存在问题:“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12]56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回忆:“平型关战斗结束以后,八路军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一带休整。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我到一一五师去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我即奉命离开总部,到一一五师师部和所属的两个团里跑了约半个月时间。其间我与师部首长和团营连的指战员进行了座谈,共同探讨我军在新的形势之下,如何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检查和座谈中,我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13]167在新形势下,中共还面临其他亟待解决的加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实际上是党政军民系统中党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的增强,上下级联系的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活动的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14]422-423甚至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也存在严重的“闹独立性”问题。任弼时在西北高干会上的讲话曾就陕甘宁边区“闹独立性”问题有过介绍:关于“闹独立性”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情形怎样呢?应当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特别在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中,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还存在着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比如,在军队方面,对于党的尊重是不够的,自以为与党是平列的,甚至觉得比党还要高一些、大一些,认为自己是中央的军队,就不把自己的工作时常提到西北局去讨论,对边区党的决议也没有认真去执行。在政府工作方面,前一个时期,有某些政府里面工作的同志对西北局的决定很不尊重,没有认真按照决定办事,如发票子、运盐等问题,到了后一个时期,又发生了政府工作中的党员干部对于党团也不大尊重的情况。在群众团体方面,曾经有一个时期,青年团体向西北局闹独立性,走到‘青年主义’‘第二党’的倾向”。[15]8-9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都向中共提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确立革命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延安时期,中共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和巩固由于受“王明路线”影响遭到严重削弱的中共中央领导权威,进而捍卫中共党组织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中共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也需要不断加强其在革命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这些都是事关中共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前途的重要且亟需解决的任务。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
一元化领导的主要举措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将中共建设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的任务和使命,通过处理典型党军关系事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确保中共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实现。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决定明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并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将中共建设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核心的任务和使命。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决议明确指出:“要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必须更深刻的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16]546紧随其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16]565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17]474上述决议、决定和中共主要领导人讲话都强调指出中共党组织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处理典型党军关系事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就是典型案例。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人员共56人。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张国焘进行了集中批判,都涉及张国焘违背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3月27日,朱德发言强调:“张国焘从鄂豫皖时期就犯原则性错误。他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不信任。……他要个人指挥党。……他思想里没有马列主义,有的只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所以才发展到放弃党的领导,想自己另造一个党。”[18]633-6343月30日,毛泽东发言指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19]667-668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说总负责)张闻天批判张国焘指出:“他是标本的‘实力派’,枪杆子高于一切。我们与他会合时,他一看我们只有这么多枪,于是乎一切吞并的手段和阴谋就都来了。后来发展到公开要书记当,要当总政委等。可见他是军权超过了一切。”[20]3073月31日,中共颁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违反党的领导问题进行总结定性。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17]121-122决定强调:“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17]123随后,中共中央将批判张国焘的相关决定和精神及时向党内军中作了传达和贯彻。[21]181中共中央通过批判张国焘凭借军事力量挑战中共党的领导权威,再次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申中共党组织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延安时期,中共还通过制度建设确保中共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实现。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五人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与批准。”“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组织党的委员会。”“各级党委会的任务是:(1)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2)依靠党的工作和组织的基础,保证上级每一任务的完成;(3)对于干部的审定和保证;(4)监察党的道德和党的纪律之执行。”[17]419-4201937年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在前线的军事领导人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12]56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表示同意:“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22]57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建设构建起了党组织对军事力量的绝对领导的体制机制。
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决定明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14]423“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交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报告上级党委。在遵照各组织上级的决议解决具体问题党委内部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责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见,亦必须执行同级党委的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有关机关。”[14]423-424决定进一步从制度上巩固和加强了中共党组织作为抗日根据地“一元化”核心力量的地位和权威。
中共中央还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西北高干会就是中共中央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关键性会议。“西北局高干会是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简称,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开始,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历时八十八天。西北中央局所属的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出席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的二百零九名领导干部到会旁听(当时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干部,是到延安来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因为会议延期召开,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一个区域性的会议,规格之高和时间之长,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空前的。”[23]396-397“这次会议时间较长,内容丰富,所解决的问题也很重要。因此,西北局高干会成为全党整风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主要事件。”[24]119“会议的议题,一是通过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二是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三是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25]596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军队重要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1942年11月2日,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西北高干会上发言指出:“党是最高的组织形式,是领导一切的,要领导政权、军队和民众团体。军队不能闹独立性,政权不能闹独立性,民众团体也不能闹独立性。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26]136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云在西北高干会上发言指出:“以前地委、县委只管党务,今后除管党务外,还要管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工作。就是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后,地方党委要管党政军民四方面工作,责任大大加重了。”[14]522-523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西北高干会上发言强调:“在三三制政权中,党一定要领导,一定要在政治上占优势。没有党员不行,党团一定要受党领导,党员一定要受党团领导,绝对不允许党员随随便便闹独立性。”[14]633会议结束前夕,代表中共中央指导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对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作了总结:“边区党各级的干部,必须忠诚地服从西北局的领导,为坚决执行西北局的每一个决定而奋斗。对于某些仍然继续闹独立性的同志,须严申党的纪律。西北局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西北的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的组织,只有爱戴西北局,坚决执行西北局的决定,才能表示他们真正是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真正是爱戴党的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5]24-25中共中央通过召开西北高干会向全党以及中共领导的政权、军队以及其他组织和团体郑重强调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总之,延安时期,中共通过制定政治目标、典型事件引导、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等方式方法,积极推进和加强中共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努力构建起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巩固和发展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延安时期,中共发展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理论和实践运用对中共自身以及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
一元化领导的主要成效
延安时期,中共加强一元化领导强化了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巩固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借助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也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形成。
延安时期,中共加强一元化领导强化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27]604他既强调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中共对军队实行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通过处理张国焘问题加强党对军队一元化领导取得显著成效。张国焘本人在受到中共中央批判后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公开表示接受中共中央对他的批评和批判。1937年4月6日,张国焘在《关于我的错误》检讨材料中表示:“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28]611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是中共党史上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事件。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先念在20世纪80年代对该事件作了高度评价:“党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方法和步骤是很正确的,也是非常成功的。……这些经验非常宝贵,对以后解决党内问题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29]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不仅向全党全军明确了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争论和分歧在政治上的是非曲直,而且维护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国革命中的权威和地位。参与延安时期批判张国焘问题的黄华回忆:“批判张国焘分裂中央,是我在党校学习期间的一件大事,大大提高了我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认识,对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和维护党的统一、严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的认识。”[30]301
中国共产党探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的问题曾发生过多次失误,有些还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些失误和错误不但给中国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也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但是,中共在汲取经验教训后,实现了自身更大的发展和超越。中共在实现实质性转变、发展和超越过程中,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5]73-74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巩固了中共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共的发展和壮大,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领导力。
延安时期,中共强化一元化领导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形成。列宁曾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31]23列宁的论述强调了领袖对群众、阶级和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很长一个时期正是由于没有形成这样“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才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大革命的失败与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集体的错误有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5]74土地革命的失败更与王明、博古等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推行“左”倾路线有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5]86“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5]76中国革命遭受的上述重大损失用事实教育了革命者: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要有成熟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后,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中共各项事业,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中国革命的曲折前进历程,尤其是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惨重损失与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革命取得的显著成就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毛泽东一系列观点和看法得到党内越来越多同志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认可和支持。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32]389陈云对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认识历程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经历过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这一过程始于遵义会议,巩固于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于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33]141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明确支持,无疑是助推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形成的关键一环,不过使得共产国际的这一支持产生更为持久深远影响的结构性因素,还在于此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历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在全党确立的过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5]73“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5]111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能坐镇延安,如臂使指般自如和顺畅地指导全国,与中共党组织高度一元化领导密切相关。因此,延安时期中共在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过程中,坚持和完善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加强一元化领导,成为思想统一、政治团结、组织巩固的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政党,保证了党组织本身的战斗性和感召力,是中共在艰苦的内外环境下不断壮大的重要内因。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环境中,中共以一元化领导建立和巩固了广泛根据地,保证了党组织在党政军民学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升了中国人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士气。中共加强一元化领导对其自身发展壮大,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受艰苦环境考验,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赢得国共角逐胜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战时期,中共全党团结一致,以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解放战争国共逐鹿华夏,决定中国未来命运之际,中共全党高度的统一性与党组织高度的战斗性和团结性,更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力量涣散形成鲜明对比。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一元化领导对中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当前加强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郭为桂,胡俊祺.“党领导一切”:观念和体制的变迁——基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的文本考察[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高中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双拥工作与一元化领导的强化[J].理论与改革,2017(4).
张冰.科层困境与国家建设的中国出路——以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为中心[J].广东社会科学,201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徐向前.徐向前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张国焘第二“中央”致彭德怀、毛泽东等电(1935年12月5日)[M]//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张国焘坚持要中共中央取消中央名义致林育英电(1936年1月20日)[M]//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意见(1937年10月19日)[M]//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卷[M].2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M].修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李聚奎.李聚奎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洛甫、毛泽东关于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的指示(1937年10月22日)[M]//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M].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下)[M].2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张国焘.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6日)[M]//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李先念同志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革命回忆录问题的谈话要点[J].中共党史研究,2009(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苏]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孙小帆]
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Wang Ming Line”, the CPC suffered severe losses, which also affected its organization leadership authority and induced Zhang Guotao to challenge its leadership authority based on military strength.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the CPC also faced the problems of weakening Party leadership of the military,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These problems gradually became serious constrai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proposed the task and mission of building the Party into the leading cor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emphasized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ver the military by handling typical incidents of Party-army relations, and established a sound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unified leadership of its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officially issued a resolution to emphasize its unified leadership and organized a special meeting to address the issue.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the CPC strengthened its leadership over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unified leadership and consolidated its core leadership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ith Mao Zedong at its core, realized the Party’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by promting the unified leadership.
Key Words: Yan’an Perio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ified leadership; Mao Zedong; Zhang Guo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