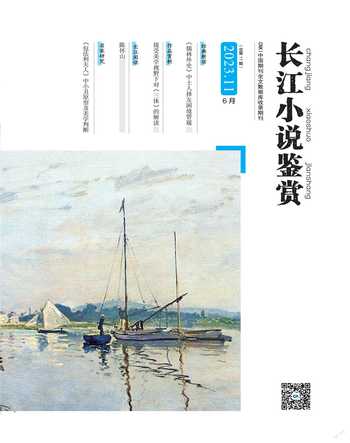苏童小说中的空间隐遁与心理互涉
2023-12-20马丹芳
[摘 要] 《妻妾成群》讲述了一个关于痛苦和恐惧的故事,颂莲从思想开放的文明世界走进了封建陈腐的旧式宅门,她在新文化与旧思想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将新未新、脱旧未旧,最后在精神的自我质问中决然崩溃。《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根据小说《妻妾成群》改编创作的电影,人性的对峙在张扬而又闭锁的空间中沉浮不定,女性的生存场域在生命镜像的对立中难以和谐,呈现了一种无序中的有序,最终在灯笼烛火的日渐燃烧中,曾经鲜艳的女性之火走向衰微暗淡。
[关键词] 《妻妾成群》 颂莲 《大红灯笼高高挂》 空间 心理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93-04
从《妻妾成群》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小说到电影的艺术转换,这种改编方式无可避免地会带来小说内在特质的撕裂和混乱,同时也输入了新鲜血液,在文学化和视觉化的流动中呈现了电影艺术的美学元素。小说的题目《妻妾成群》,似乎是对陈佐千生活状态的桃色描述,集众星捧月之势,具有内在意义的影射和暗示。电影的题目则将具有中国元素气息的“灯笼”置于题首,其鲜明的色彩具有冲击人心的力量,陈府妻妾最终难以成群,万艳化为同悲。
一、围城内外“阅悟”与“听说”的空间对峙
从雾雨氤氲的江南家苑,移植到封闭肃穆的深宅大院,这是从小说“阅悟”到电影“听说”的空间跳跃,在电影中可以直观地体会到环境带给人物的压迫之感,将小说隐藏在文本中的熏染效应烘托出来,由此带来了一种外在氛围的整体流转。故事的自然环境出现了一种收拢式变动——电影的陈府大院在中轴线位置正襟危坐,其“口字型”结构将院中的女人牢牢锁锢,四方视线拘囿在青墙灰瓦之中。在陈府牢牢矗立的围墙内外,不管是对小说文本的阅读体悟,还是对电影作品的视听观看,情节和人物的改动在小说和电影的比照中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对峙格局——相互对立、互相吸引,由此形成的人性对峙却极不平衡。从绿树花藤的江南府邸,走到封闭工整的北方大院,生命的浮华与萎靡毫不消退,甚至是愈演愈烈。
“小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电影基本上是一种视觉的艺术。电影既然不再以语言为唯一的和基本的元素,它也就必然要抛弃掉那些只有语言才能描述的特殊内容,而代之以电影所能提供的无穷尽的空间变化。”[1]在小说与电影的裂缝中,可以看到这个封建家庭始终流淌着紫红色的血液,整个陈家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大井,人们看似活着,实则沉溺不知。书中的颂莲不施脂粉,只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进行装饰,女学生外表的知性气质便迎面而来。对比之下,巩俐饰演的颂莲似乎一开始就在指认自己“遥远”的学生身份:一头利落的齐耳短发变成了两条粗实的麻花大辫。对颂莲外在形象的改编处理,使得她的学生气在影片中一开始就从外形上被模糊了,粗粗的麻花辫子消弭了齐耳短发隐寓的叛逆求新,也打散了颂莲的书香气息。这种改编是在迎合电影“听说”的表现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颂莲的个性特征,失去了“阅悟”文本的个性光辉。陈家太太们在陈府大院中相互倾轧,她们在各自分属的院落里安然度日,看似有序中实则潜藏着争宠的暗流涌动,无序才是陈家生活的本来面目。
有序的家庭伦理中潜藏着无序的狰狞面目,这种有序中的无序加速了颂莲人格的消泯,使其浮在怅惘之上,凄苦之下。对比小说中同样处于“中间”的颂莲——一半是新思想的沐浴洗涤,使她这样一个具有内倾性格的知识分子,勇敢探询井里的秘密,生发出“一眼就看见两个女人浮在井底里,一个像我,另一个还是像我”[2]的心灵质疑;另一半则是旧观念的作祟摇摆,使她甘愿沉溺在封建余孽的争宠风浪中。女学生和姨太太的双重身份也使颂莲陷入一种新旧矛盾中,中间人的姿态使她在陈家苟延残喘——思想不够新,不足以面对井底看到的穷途末路;同时观念又不够旧,无法消化井底命运所带来的恐惧。颂莲最后的反抗是以“疯”作为代价,但颂莲的癫狂并不是她自身的精神状态,而是陈佐千无情宣判的专断结果,他冠冕堂皇地成了诊断病根的“良医”,疯的并不是在井边喊着“我不跳井”的颂莲,疯的是陈佐千,是封建家长在井边的失态。
颂莲的眼睛就是镜头,陈府为“妻妾成群”的伟大构想提供了基本的物理空间,小说和电影之间的联动作用还体现在由此延展开来的心理空间——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命运随着电影的色彩点染得到了“有声有色”的传达。灯笼是带有中国元素的象征物品,它在陈家象征着太太们的荣辱兴衰。电影对故事情节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加入了挂灯、点灯、灭灯、封灯、捶脚和点菜等仪式化设计,“不仅表现出强烈的视听觉冲击,更暗喻女性完全被男权掌控的悲剧命运”[3]。电影中大红灯笼的高高挂起,将颂莲的女学生身份燃烧成灰烬,她和陈家其他太太都将荣辱兴衰寄托在灯笼的点灭之间,因而把女性命运推向了极不自由的境地——“井”边不从的清醒消失殆尽,毅然成为“灯”下听话的忠实奴仆。作为受宠象征的大红灯笼无论怎样闪耀,第二天都会随着陈佐千的离去而陨灭,仿佛这份恩宠从未来过,晦暗的黑色成为裹挟院落的主要色調。点灯和灭灯,将红与黑的意境氛围全盘托出,红色闪耀在每个沉寂的黑夜,肩负着幸福和残酷的双重使命,得宠的人希望点灯的红光可以永驻,失宠的人则希望灭灯的黑光快快挨过。电影运用了色彩蒙太奇手法,在心理空间中将冷暖对立的两种色调和盘托出——高调红色与低调灰色。“房屋内的每一个摆设都转换为虚化的镜头语言, 呈现出来的则是黑与红的争夺,就好像是命运与封建陋习之间的激烈搏杀。”[4]人物随着冷暖色调的强烈反差,呈现出不同的命运境遇,红色在灰色和白色的包围之下,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氛围感,“视觉收缩性强的灰色和视觉膨胀性强的红色、白色正好形成了一种压抑与抗争、焦渴与期待的矛盾”[5]。点灯的红光微弱地照耀着灰色的高墙深院,它在四方小院中短暂地跳跃,影射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对女性生命的无情漠视。“长明灯”将红与黑的对比推向极致,颂莲在雁儿的刺激下假装怀孕,陈佐千下令点亮四院的长明灯,此时的红色照亮了周遭的灰暗,但红灯笼本身就是恩赐的结果——这是灰色的妥协,而不是红色的胜利。后来得知真相的陈佐千一怒之下“封灯”,黑色外套就宛如治丧一般将红灯笼套住,也预示着这院的女人将过上灰暗无光的日子了。在这个阴冷幽深的大院中,还有一种复杂色调令人舒缓又窒息——白色。白色是颂莲前期喜欢穿着的颜色,她身上的颜色随着情节推动而不断变换,白衣黑裙和素色旗袍出现在影片的开头结尾,这样的白色代表着清冷寂寞的人物情感。小说没有过多渲染颂莲衣着的色彩,电影进一步将人物性格的内在流变投射到外在穿着的变动中,是一种直观且含蓄的表达。颂莲走过了红与黑的世界,在这个漆黑的陈家大院挥洒有限的生命,白色的雪花簌簌飘落,即使有色彩艳丽的旗袍包裹着她,也抵挡不住白雪的透骨冰凉,她彻底迷失在这个黑白世界里了。
二、跨越人性的藩篱——沉浮于对抗和屈从的心理漩涡
陈府大院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6]。在对抗和屈从的心理矛盾中,以颂莲为代表的女性迷失在家庭的漩涡里,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暗淡的人生选择。颂莲本该是带着栀子花香的“女学生”,而不是在“妻妾成群”中熏染造就的带刺玫瑰,颂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命运嬗变的姨太生活,这是她新思想下的旧选择,自此“新”便丧失殆尽。小说和电影的创作者设定了一些看似合理的选择——“颂莲们”苦于人性的藩篱,在对抗和屈从中做出生命选择。
颂莲的“绝望”来自不同的深渊,庭前花落各有不同。比较小说和电影中的颂莲,她们的所思并非所见。一个是向下看——对陈家花园的“死人井”展开了汲汲探寻,不满足于他人对枯井的简单描述,最终只得在井边挥洒生命的余晖;另一个则是向上看——对“死人屋”充满好奇,这是来自人性本能的好奇发问,因为死人屋是抬头便可瞧见的建筑物,它不苛求一双善于发现的独到慧眼,因而电影里的颂莲不具备发现问题、积极探索的学生思维。颂莲目睹了梅珊的被迫死亡,这种突然的生命流逝给自己的心灵造成了猛烈打击,她的生命也开始走向尾声。“死人井”要求用一种向下看的姿态注视生命,并保持不断的探索寻问,这不是普通人能到达的心灵高度;但“死人屋”只需颂莲轻轻抬头,就能体会到它的禁锢警示——谁也别想越过这条线,你能看到的已经是极限了。
井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象征着女性命运的极不自由,它被奉为封建伦理和专制礼教的化身和象征。电影中的陈佐千虽然只有一个朦胧的虚化背影,却对女性生存场域具有绝对统摄的权威力量。在一妻三妾的畸形家庭中,陈佐千式的夫妻生活逐渐走向“妻子属于丈夫,而丈夫只属于他自己”[7]的不平等关系,而四位太太的身心只能聚焦于陈佐千一个人。但与其他三房太太不同的是,颂莲曾将自己短暂地栖息在另一位男性身上。这是一个被简单化处理的男性角色——大少爷飞浦,他更像是一个被阉割处理的男人,极富深意。飞浦的男性气质弥散在封建的父性气息中,这个在父权制度下滋养生长的大少爷,却被传统力量反噬吞没,因而以性别缺陷、取向混乱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来。飞浦沐浴过新式教育的“五四”新风,对于颂莲而言,他是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及时的救赎也是彻底的毁灭。与飞浦明暗交错的情意往来,是颂莲走向精神决堤的重要一步。年轻温厚的飞浦吹箫而来,颂莲意识到原来两心相通远胜于肉体快感,她开始憧憬这个年轻的身体。与飞浦的交往,是颂莲在死水般生活里的苦中作乐,也是她逃离争宠风浪的温情港湾。然而,在飞浦身上发生的精神畸变,却将奄奄一息的颂莲推向了灵魂的深渊,这些潜在因素都掩藏在他的性格弱点和性别障碍中。首先,飞浦烙刻在骨子里的软弱畏缩是无法改变的,在与母亲争吵之后,他冷漠地忽视颂莲,胆怯地与母亲站在同一阵线。飞浦的屈服顺从渐渐地抽空二人的感情基础,直至消殒。另外,飞浦曾向女学生颂莲寻求情感认同,也敢直言自己“怕烦,怕女人,女人真是让人害怕”[2],却对颂莲说“你跟她们不一样。所以我喜欢去你那儿”[2],这是倾诉的表达还是情意的宣泄?飞浦和颂莲的理解发生了错位异化。颂莲将飞浦的话视作情感暗示,正像指缝之中的冬日暖阳,在这个阴冷黑暗的家中照亮了自己。而飞浦肯定的是对方的本质属性,但在颂莲那里却变成了“在我这儿你和她们不一样”,变成了一份感情的抒发。飞浦是陈家寄予厚望的新生力量,却以不同的叛逆方式对抗着家族使命,他的悲剧源于痛苦,而看得见的痛苦常常会酿成悲剧。此外,颂莲的另外一半还是梅珊,她们在悲戚痛苦的境遇中惺惺相惜,梅珊之死把颂莲推向了一个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她似乎带走了那个井边不从的颂莲。因此在深井失去了提供水源的基本职能之后,它还能以坚挺不屈的姿态傲立在陈家院落中,可以说是封建余孽的延伸与发展,它无穷无尽地吞噬着封建压迫下的魂灵。颂莲在妻妾环侍的紧张环境中,并没有感受到太多来自陈佐千的深情爱意,他的性欲望发泄在谁身上都一样,“像是在经历一种历史的循环, 北京来的女学生颂莲终于退回到古老形式的起点”[8],浊世里的鲜花难逃枯萎的宿命。这样的叙述和演说逃离了叙述者的情感温度,与陈思和所说的“小说所隐含的主体意识弱化及现实批判立场缺席的倾向”[9]正是一致的。雁儿的死使颂莲从受害者成了施暴者,梅珊的身亡带来了颂莲的魂灭,她再也无法为“女人”发声,最后只剩下井边的疯言疯语。
苏童在传统封建家庭的“旧瓶”中注入以颂莲为代表的“新酒”,其酒味醇厚悠长,飘出了妻妾成群的陈家深院,或许可以将这种叙事构思理解为苏童最初对“旧”世界的想象和书写冲动,或者“对旧时代一种古怪的激情”[10]。陈佐千承袭了三妻四妾的传统习惯,将妻妾妇女推向“第二性”的附属地位,亦主亦奴。历史是一条潜在的涌动河流,苏童流动式地将颂莲产生的一系列“幻觉”“想象”“梦魇”等通过“虚幻空间”不断延伸,以此展现了颂莲内心想说却不敢说的真实意念,成为颂莲一步步走向“死亡”之路,然后完成自我毁灭的凭证[11]。穿过历史的雾霭,陈家的女性在低矮的生存空间中紧张地呼吸,汲求安身立命的生命资源,簇拥而上的她们构成了陈佐千“帝王构想”的后备力量,有零碎破落之感,饮到最后便知《妻妾成群》的茶苦酒悲。
三、结语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陈佐千沉醉于营造妻妾成群的男性权威,四房太太在人性的相互倾轧中抢夺男权压迫下的生存空间,而第五位太太的加入证实了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人性悲剧。在小说中,我们可以体悟到语言文字之下的情绪牵动和人物情结;在电影中,则可以体会到人物行为与视听效果的联动反应,电影为小说提供了镜像效应——众芳身处污淖,怎能不染?以颂莲为代表的女性被禁锢在陈府的围墙内,往外看不到自由的生机,在内则是沉浮于对抗和屈从的漩涡中。物理空间的堆叠变化营造出心理空间的位移传递,浊世千红难逃藩篱,妻妾在小说和电影中都难以成群。
參考文献
[1] 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高俊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2] 苏童.妻妾成群[M].广州:花城出版社,2020.
[3] 刘虎.论小说电影改编的一种路径[D].南宁:南宁师范大学,2019.
[4] 李彦瑾.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色彩意境分析[J].电影文学,2013(22).
[5] 柯晓兰.电影改编:如何在“镣铐”中“舞蹈”——以《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妻妾成群》的改编为例[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8(1).
[6] 苏童.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M]//妻妾成群.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7] 福柯.性经验史(第3卷)[M].佘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8] 程光炜.我读《妻妾成群》——在苏童与《包法利夫人》译者对话中品味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18(2).
[9]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0] 张学昕.为何会有“描述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苏童《妻妾成群》重考[J].小说评论,2022(3).
[11] 张丽婷.《妻妾成群》中的心理空间探析[J].大众文艺,2020(9).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马丹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绍兴文理学院科研课题(Y202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