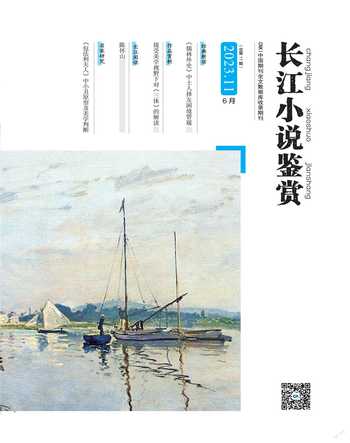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中的小丑原型及美学判断
2023-12-20秦中岳
[摘 要] 本文以小丑原型分析郝麦的人物形象,进而说明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寄寓的美学判断。福楼拜通过塑造郝麦这个“小丑”,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话语进行戏仿,从而质疑其有效性。福楼拜的美学判断是某种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
[关键词] 小丑原型 郝麦 美学判断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76-04
《包法利夫人》之后,警惕浪漫之幼稚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福楼拜之后的小说”成为现代小说的同义词[1]。但是,福楼拜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浪漫”的反思,更在于其对被卡林内斯库称为“市侩现代性”的批判。《包法利夫人》作为福楼拜美学判断的结晶,它的深刻性在于其对现代化或者说是启蒙话语展开的丰富而复杂的提问与质疑。福楼拜塑造的郝麦形象,无疑是被“进步”话语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现代小丑,而正是这位小丑,揭开了所谓“进步人士”的虚伪面纱。
一、美学判断与郝麦
福楼拜对市侩现代性进行了一种美学判断,这是一种审美现代性,它逆资本主义“进步”而起,并且反对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卡林内斯库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2]福楼拜身上的审美现代性与市侩现代性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他的美学判断上。所谓美学判断,传达的是一种对于生命和历史的洞见,它比伦理判断、政治判断等更为复杂微妙,也因此更真实准确。这是一种艺术真实,是福楼拜力图以艺术的方式抗争,揭开迷信“进步”外衣下平庸、媚俗的本质。美学判断借助于虚构,但它深入生命的底层,将感性、理性、想象力等融为一体,超越善、恶,以美、丑判断为指归。
诚然,《包法利夫人》讲述了一个庸俗的关于出轨的故事,但它凝结了福楼拜心中强烈的反叛激情,它无疑是福楼拜对“进步”话语所做的美学判断的结晶。小说一经出版,就遭到法国第二帝国法庭的起诉,认为它“败坏公众道德、败坏宗教道德”。然而,这种站在道德立场的指控是没有力量的,也辜负了福楼拜创作小说的良苦用心。
《包法利夫人》确实是“美的艺术”的经典,但绝非“为艺术而艺术”。换句话说,美学判断并不意味着为了美的形式而置道德、政治、宗教等于不顾,而是在审美经验的复杂性中发现庸常视角下被掩盖、被遮蔽、被忽略的真实。美同样是一种对生活和对社会更全面的思考。福楼拜自己也曾批评过那种唯美主义的倾向:“惟有思想是永恒而必要的。如今已不存在昔日那样的艺术家,那类艺术家的生命和精神都只是服从自己求美欲望的盲目工具。”[3]
若干年以后,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的道路就像与现代平行发展的一部历史”,它“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4]。昆德拉正是指出了以福楼拜为开端的现代小说思想内涵的现代性,它以美学判断表达了理性之外的困惑、质疑、批判。福楼拜对当时流行的“进步”话语嗤之以鼻,他认为,深藏于宗教、哲学、历史、理性中的“进步”思想过于肤浅和片面,而现代人的精神则愈加空虚。福楼拜就是要掀开这所谓“进步”的“皇帝的新衣”,暴露赤裸裸的真实。
这样的真相不仅显露在爱玛的悲剧中,诚然,爱玛的灵魂被“进步”话语中的时髦和浪漫荼毒,她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裹挟着大踏步迈向一种庸俗的现代性,“但作品里有的人则具有正确的时间感觉,因此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5],这个人就是郝麦。郝麦的法文名Homais与爱玛的法文名Emma发音极为相似,这或许是福楼拜故意为之。爱玛与郝麦构成一组对照,就在爱玛被所谓的浪漫书籍冲昏头脑,一步一步在婚外情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在欲望编织的高利贷陷阱中无法自拔的时候,郝麦则抓住每一个“进步”的机会。爱玛一家抵达永镇的第一天,郝麦就先行抵达金狮客店,他扬言必须跟上时代,后来又对周围人鼓吹:“全变啦!必须跟着世道走!”[6]而在结尾,爱玛被高利贷逼得服毒自尽,丈夫离世,女兒沦落到纱厂成为一名童工。这个被“进步”碾碎的破落家庭让人感到苍凉。而郝麦的运道却截然相反,他“正确”的时间感让他在“进步”的时代如鱼得水,他在小说最后得到了十字勋章:
自从包法利死了以来,一连有三个医生在永镇开业,但是经不起郝麦拼命排挤,没有一个站住了脚,他的主顾多得不得了。官方宽容他,舆论保护他。他新近得到十字勋章。[6]
但郝麦也不过是被“进步”话语愚弄的小丑,他所笃信的“科学”与“进步”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同样牵制着每一个人。正如童明所言:“科学、理性、知识、主体、进步,这些曾经(并仍然)激动人心的中心词,构成了启蒙话语,其展现的如幻如梦的前景,令自主者受之鼓舞而有所作为,而不可自主者则为之迷茫,反遭愚弄。”[1]郝麦究竟是“自主者”还是“不可自主者”?其实,这两者不过是一体两面。郝麦和爱玛一样,与其他人拥有相同的欲望,却以为那是他自己的欲望。虽然郝麦利用“进步”话语向上爬,并混得如鱼得水,但他也是被“进步”话语利用,成为“进步”脚下俯首称臣的庸众。所谓的现代文明、“进步”话语,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文化趣味、思想观念的集合,而它们又通过大众传媒手段持续渲染和洗脑,影响全社会。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现代性面前,傻非但没有消失,相反,却与进步并驾齐驱。”[4]
郝麦这个被蛊惑而不自知的、自以为跟上时代的小丑和傻子,对权威和时髦言听计从。他的话语不过是一遍又一遍重复已被奉上神坛的“进步”话语,而他的自我却只能保持长久的沉默。郝麦对科学无所不知的背后,恰恰是其对世界的一知半解,而这正是培育迷信的最佳场所。“现代的傻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对既成思想的不思考。”[4]在这种对“现代的傻”的描绘中,福楼拜展现出其对于“进步”深刻的美学判断。毫无疑问,郝麦是现代的小丑和傻子。
二、郝麦、小丑与戏拟
正如巴赫金所言:“骗子、小丑、傻瓜在自己周围形成了特殊的世界、特殊的时空体。”[7]郝麦的傻在于他对所谓“进步”话语来者不拒,他不假思索地“紧跟”时代潮流,生怕被时代抛弃,被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落下,他不断赶路,并且讨好、谄媚高高在上的权威。在郝麦的迷信里,蕴藏着巨大的反讽,其中最讽刺的莫过于郝麦看到一篇治疗跛脚的新方法的文章后,与爱玛合谋,鼓动包法利为客店的跛脚伙计伊玻立特实施外科手术。结果手术彻底失败,客店的伙计被截肢,郝麦作为所谓“进步”话语的代言人,讽刺地显示出被“进步”欺骗的一面。福楼拜让读者一同见证了一场关于现代、科学、进步沦为迷信的荒诞闹剧。
郝麦表面上对“进步”话语深信不疑,但他关于科学和进步的任何知识都来自报纸和宣传册。他这样的滑稽形象,如巴赫金所言:“这些人物的存在,本身便具有转义而不是直义:他们的外表、他们的所为所说,表现的不是直截了当的意思,而是转义,有时是相反的意思,不可照字面理解;他们是表里不一的。”[7]虽然“进步”话语成了一种迷信,然而,郝麦却打着进步、科学的幌子,获取了数不清的利益。在迷信“进步”话语方面,郝麦或许是一个小丑、一个傻子,但在利用“进步”发家致富方面,他尤为精明。郝麦理所应当地成了一个现代性的帮凶,与“进步”合谋。郝麦最后的胜利,象征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历史进程:启蒙话语、现代性的车轮滚滚而过,而在此过程中抓住了机会,就几乎意味着抓住了数不清的财富、地位、荣誉,郝麦正是如此。然而,被侮辱、被损害的,如可怜的客店小伙计,却永远被埋在历史的尘埃中。福楼拜的美学判断的深刻性在于他洞察到“进步”很难衡量社会变迁、历史发展的好与坏、善与恶,少数人的所谓的“进步”或许是用另一些无辜的人被剥削、被压迫换来的。
而郝麦作为一个被“进步”话语蒙骗的小丑和傻子,他口中所说的进步、科学、现代就自然地拥有一种滑稽感:
至于郝麦先生,凡足以纪念大人物、光荣事件或者高贵思想的,他都特别喜爱:他给四个孩子取名字,根据的就是这种原理。所以一个叫拿破仑,代表光荣;一个叫富兰克林,代表自由,一个叫伊尔玛,也许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让步;一个叫阿塔莉,却是对法兰西戏剧最不朽之作的敬礼。[6]
在郝麦给孩子们取的名字中,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反讽。这种戏拟,或如巴赫金所言:“(在戏拟中)作者借他人的话语说话,但在这个他人的话语中引入了一种语义的意向,与他者话语的原有意向针锋相对。第二种声音一旦在他者话语中安家落户,便与主人顶撞抵牾,并且强迫主人为完全相反的目的服务。话语成为两种声音争斗的竞技场。”[8]这样就解构了对启蒙和对“进步”话语的迷信。这种戏拟蕴含着福楼拜对启蒙与进步的警惕态度,在福楼拜看来,所谓启蒙、科学、进步已经很难用好与坏来衡量,必须对它们进行复杂的美学判断。同样,在这种对“进步”话语的戏拟中,福楼拜暴露出它的片面性、封闭性、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福楼拜用戏拟这种亦庄亦谐、戏谑调侃的手段,对所谓“进步”的桀骜不驯、自以为是进行了批判。
戏拟原是语言对语言的模拟,而在这种对“进步”话语的调侃中,将现实世界的真相和众声喧哗引入其中,同时又戳破“进步”的虚伪面纱,揭示出隐藏在“进步”下面的蝇营狗苟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郝麦的小丑形象也正如巴赫金所说:“在反对所有现存生活形式的虚礼、在反对违拗真正的人性方面,这些面具获得了特殊的意义。”[7]福楼拜也正是通过对郝麦的刻画、对“进步”话语的戏拟,表达了他对科学、进步、现代的复杂态度:“进步”话语所描述的美好世界未必是世界的真实,未必会给所有人带来幸福,未必会让人们走进真正的现代。而他也提醒人们,要警惕启蒙、进步、科学的讹诈和欺骗,最为重要的是要借助艺术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借助小说叙述复杂的美学判断。这样,人们才不会沦为郝麦那样的小丑和傻子。
三、怪诞丑角理论与启蒙话语
上文分析郝麦小丑原型时借用了巴赫金的“怪诞丑角理论”,这是其狂欢化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狂欢化诗学理论作为巴赫金穷尽一生思考和构建的理论体系之一,始终与他的对话思想联系在一起。对话思想是巴赫金一生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巴赫金对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生存方式总的看法与观点。在巴赫金看來,对话现象几乎无所不在,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人才能得到证明和完成,这是一种超越辩证法的观点。只有从对话思想出发,才能深刻地把握福楼拜在郝麦这个小丑和傻子形象中蕴藏的复杂的美学判断。
巴赫金以狂欢节为切入点,展开了他对丑角人物的认知与解读。而狂欢节作为一种众声喧哗的节日,人们可以推翻一切日常的拘束,平等而自由地交往,这就是对话的雏形,也是民间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对话的场所。而狂欢节上行为怪异的丑角,如骗子、傻瓜、小丑等,以一种特殊的地位和形象成为揭穿事实的“盗火者”,它们毫不留情又诙谐幽默地指出自己所在的日常世界的虚伪和欺骗。正如巴赫金所言:
人和行为之间、事件和其参与者之间的一切旧联系全都瓦解了。在人和他的外在地位(职位、尊严、阶层)之间暴露出严重的脱节。在骗子的周围,被人们郑重而又虚伪地占据的高位和尊称,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全都要变成面罩,变成化装舞会上的服饰,变成道具。处于开心的哄骗这一气氛中,所有这些尊称和高位莫不发生变化,失去分量;它们的情调会从根本上转变。[7]
无论小丑、骗子、傻瓜以何种形式揭露虚伪、洞察真相,他们必定要撕下在日常生活中常规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假面”。而在这撕下的过程中,必然充满了对话性,必然是两种话语的交锋与征战,所以不存在孤立的小丑、骗子、傻瓜。
福楼拜让郝麦戏拟的“进步”话语,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而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也与启蒙话语密切相关。对“进步”话语的迷信和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理性的迷信和崇拜。如果从后现代的角度观照启蒙运动,其实际上是一次利弊参半的历史运动:它推翻了中世纪以神学、宗教为特征的世界观,建立起科学和理性的新世界,其进步性有目共睹;然而,当理性、进步成为一种新的迷信,当启蒙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启蒙所产生的问题也不能被忽视。
从某种程度上说,自尼采以来,人们就开始打破对于理性的过度崇拜。尼采将欲望、生命意志等引入理性思维,为后现代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着力点。而阿多诺、利奥塔、福柯等理论家更是全面展开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但后现代主义并非要反对启蒙,这些哲学家反对的是对于启蒙的盲目崇拜,是启蒙的体系性暴力,他们想要继承启蒙运动的遗产,同时警惕被启蒙的旗帜遮蔽的另一种迷信。
福楼拜所处的时代,正是启蒙话语风靡的时刻,是所有人被“进步”话语裹挟着一往无前的时刻。但福楼拜凭借着文学家独有的美学判断,察觉到“进步”话语背后的盲从、迷信、虚伪和暴力。正如童明所说:
从文学阅读中可以体悟,美学判断除了非功利的特质,还将理性、想象、直观、欲念融为一体,形成更为成熟的判断,因而不同于以理性为唯一特征的体系现代性。没有20世纪之前现代经典文学的美学积累,我们未必能明辨现代体系的问题所在,也就没有直逼要害的眼力。[1]
四、结语
福楼拜笔下的郝麦,在小说最后得到了十字勋章,但永镇却从此暗无天日。郝麦这个小丑披着启蒙的外衣,把无耻变作光荣。他成为偽善的代言人,也是十九世纪被“进步”话语包装过的“人”。福楼拜塑造了郝麦这个满嘴都是“进步”的小丑,他意在与启蒙话语对话,他要质疑与抗辩。福楼拜的美学判断一针见血,他借郝麦之手,把“进步”话语的荒诞滑稽撕开。
福楼拜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在旧有的神学宗教体系被打倒之后,新的“进步”话语未必能给人带来其所许诺的幸福。郝麦身上具有强烈而又深藏不露的对话性——福楼拜借此与进步对话、与现代性对话。但与其说郝麦具有小丑、骗子、傻瓜的边缘性,不如说他想成为“进步”话语的弄潮儿。郝麦并不是巴赫金定义的无关痛痒的生活的参与者和窥伺者;相反,他伺机而动、无能甚至残忍,凭借他对“进步”话语的熟练掌握与运用,在所谓的新时代、新世道如鱼得水。郝麦这个现代小丑,近乎疯狂地从边缘向中心突进,他身后扬起铺天盖地的尘埃,这正是迷信“进步”话语的恶果。
参考文献
[1] 童明.现代性赋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 福楼拜.福楼拜小说全集(上中下)[M]. 李健吾,何友齐,王文融,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5] 范能维.《包法利夫人》与审美现代性[J].东吴学术,2019(5).
[6] 福楼拜.福楼拜文集(第一卷)[M].艾珉,编. 李健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7]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8]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秦中岳,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