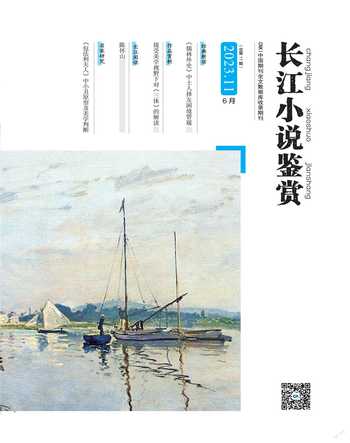论非虚构文学的跨文体特征
2023-12-20刘雅芳
[摘 要] 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学性概念,学界对非虚构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虽未达成统一的规定,但对其跨文体性的认识似乎已达成共识。萧相风创作的词典体小说《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从结构布局、语言、内容三个方面体现了其作为非虚构文学的跨文体特征:词典体小说兼具词典的框架特征和小说的叙事功能,满足非虚构文学展现真实生活的需要;散文体、诗歌体的渗入打破了语言的诸多限制;小说超出叙述故事,呈现出学术探讨的基本面貌,展现出学术化趋势。《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作为非虚构文学,打破了文体界限,勇于对传统文类进行实验性的探索和尝试,其文体的多样化表达使文本成为意义丰富的复合符号空间,打开了文学发展的新视野,同时为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 非虚构文学 跨文体 《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獻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85-04
一、研究背景
2010年之后,《人民文学》《钟山》等国内多家重要文学刊物对非虚构文学的提倡引发了一股讨论与创作非虚构文学的热潮。非虚构文学是满足人们对真实感、在场感的渴求而产生的一种打破原有文体界限的新文学,它提倡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的写作,重视作者“在场”的姿态,力图摒除文学中浮夸、虚假的一面。“非虚构”的概念之辩一直是学界热议的命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如王晖在《“非虚构”的内涵和意义》和《现实与历史:非虚构文学的独特叙述》中认为非虚构文学“更多的是指一个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1],而“田野调查、新闻真实、文献价值、跨文体呈现应该成为构建非虚构文学的基本内核”[2];丁晓原认为,“‘非虚构显然是一个包含了报告文学在内,但比报告文学内涵更多、外延更大的文类概念”[3]。另一些学者认为非虚构文学已然构成一种新的独立的文学类型,如张文东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理想和现实的可能性都在于:在尽可能模糊的文体界限中营造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以某种‘中间性的创新模式打破传统文学(小说)叙事的存在样态,使历史或事实在被最大限度还原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景观”[4];李云雷则认为非虚构文学是“新兴的文体和新的文学现象”[5],其以个人的体验为核心来表现世界。尽管学界尚未对“非虚构”的概念达成统一的认识,非虚构文学的边界不明确、含义含混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人们也可以从上述讨论中获得一个共性的认识,即“非虚构文学”确实具有跨文体性。
文体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是构成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所谓跨文体性,即指作家在创作某一作品时打破了单一的文体限制,渗透、共存了多种文体的特质,使文本变得更丰富多样,增强了文本的张力。需注意的是,跨文体不是不同文体的简单叠加拼凑,而是要融各种文体之长,以达到协调的效果。童庆炳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中认为文体“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6]。面向更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非虚构文学的跨文体性正是其质疑和挑战传统文类秩序的表征,也正因如此,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学性概念,它的生长和发展获得了更充分的自由和空间,也得以展现出更丰富多彩的面貌。正如《人民文学》专设“非虚构”栏目,打出旗帜将其引入文坛主流视野时解读道:“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概念划出界线,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7]非虚构文学跨越文体的规范和边界,其呈现出的各种文体互渗和共存的现象值得关注。本文将以萧相风的词典体非虚构小说《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为例,分析非虚构文学的跨文体性。
二、《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的跨文体特征
《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后简称为《词典》)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后以单行本出版。作者萧相风于2000年南下广东开启“南漂”生活,辗转在不同的工厂做过多份工作。他以词典为叙事结构,有意整理出与工厂生活密切相关的四十几个关键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融入多年来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解释和说明,形成一本“发现现实的还原之美”的非虚构词典体小说,因“从无可置疑的个人体验出发对这个时代工业生活做出了大规模表现和思考”而获得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词典》中,非虚构文学的跨文体特征在结构布局、语言、内容三个层面上有所展现。
1.结构布局:介于词典和小说之间
萧相风以词典的体式建构《词典》的外部框架。《词典》的内容核心是围绕工业生活而挑选出来的44个关键词。作为同一个场域下的要素,这些关键词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作者并未根据含义和相关性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而是严格按照词典的结构特点,将其按照二十六字母表A-Z的顺序组织。同时,作者使用“详见‘××词条”的方式,将各章节提及的内容索引到其他章节词条,通过这种指向性的提示将各关键词重新链接成网络,弥补按字母表排序所造成的零散的不足,强化了词典在绘制工业生活缩影上的实操性。这也为读者在阅读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便利多样的阅读方式和路径。书中的各章节以关键词为标题,正文则围绕其展开阐释,正如一般词典对词语的释义。当然,《词典》并非只是一本词典,其内部对章节词条的阐释保留了其作为小说的实质内容,即叙事。各章节词条中,作者围绕各章的关键词展开故事的叙述,尽管情节并不采用线性的叙事,人物和情节的发展也有断裂的情况,但各章内部都具备相对完整的故事内容,基本符合小说叙事的特质。
作者萧相风在跋文中写道:“假若我将现实作为目的地,那么从词语这个入口进入,就会发现现实的还原之美。假若我将词语作为目的地,从现实的入口进入词语,同样令人大为惊奇,历史与现在、现实与美学的距离仿佛裂开的彼岸,同时也让我意外地找到了距离产生之后的参照物……为了找到真理最小巧的人口,我选择了个人词典,用心存敬畏的态度,试图与大家的记忆找到相似的姿势。”[8]其主要使用了两个策略:其一是将现实的生活体验解构为词语,以词语作为故事的中心和主题,在叙事中重新建构并逐步还原接近真实的现实,实现小说“非虚构”的功能;其二是结合现实,观照作为符号的词语,透视词语所凝结的内涵及其历史变迁,在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下重新观照现实,获得词典对现实的注解和解说意义,进一步深入认识现实。词典体小说兼具词典百科全书式的严谨和小说闲谈式的个人化体验,既符合非虚构文学最大限度展现真实生活的诉求,同时也蕴含作者介入生活的思考和个人化的体验,展现了非虚构文学不同于传统虚构小说、社会百科全书的别样意义。
2.语言:散文体、诗歌体的渗入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何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风格和质量。在传统的文体规范认知中,一个特定文体的语言风格和特点应该符合该文体的性质并一以贯之,不能旁逸斜出。小说的主要功能为叙事,尽管不同作者的语言有其个性化的特征,但总体而言,小说的语言通常应该是简明形象、雅俗共赏的。非虚构文学打破了文体的界限,也打破了语言方面的诸多限制和壁垒,使文本的语言选择变得自由而丰富多样,展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
萧相风对《词典》有着明确的定位——这是一部个人词典:“我笔下的南方是一个小小的切片,是坚实具体的南方和情感虚拟的南方冲突构建下的个人词典。我反对它仅仅是社会史、血泪史或统计数据。”[8]因此,在《词典》中,他运用了个性化的语言,在常规的小说叙事语言之外,展现了散文体、诗歌体渗入和共存的独特风格。
散文的语言风格通常灵动而自然,运用在小说中更能展现出形象的生活情态和细腻丰富的情感。在《词典》中,萧相风常采用散文化的语言,茶余饭后式的闲谈,向读者阐释各个关键词。同时,他也充分发挥了散文化语言优美细腻的风格,比如“电子厂”一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荧光灯挂在低矮的流水线上,在夕照或月夜之时,远望那些荧光灯,它们是新的夕阳或明月,悬在那工业的屋檐下嘤嘤地叫着,哼着。黄昏时的蝙蝠从瓦片下飞起,也是轻轻地打开声音相似的电波。”[8]这句话运用了比喻、拟人、联想等修辞手法,作者将流水线的灯比喻成浪漫的夕阳、明月,并感知到电灯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将其描述为缠绵的嘤嘤声,将电波声联想成蝙蝠飞起的振翅声。这句话融入了作者的亲身体验和个人情感,将电子厂流水线的工作场景描绘得温柔宁静,颠覆了读者心中认为电子厂流水线工作枯燥无味的刻板印象,表露出作者细腻的心灵和生活化、感性的语言风格。再比如“老乡”一章中的描述:“老乡作为宗族文化的产物,它是从与血缘相连到与土地结盟的候鸟。在长途跋涉的迁徙里,可以相互呼唤,相互结伴并指引方向。从农村到城市,老乡是一个过渡的木船。”[8]作者将老乡比喻成候鸟和木船,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中相互陪伴,帮助彼此适应新的环境,形象地表达出城市底层中老乡关系的人情味。读者能从文字中感受到萧相风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力、轻盈浪漫的想象力和温柔细腻的情感感知力。
萧相风对诗歌也颇有兴趣,著有《中国现代诗歌普及十讲》,对诗歌的写作手法、表达方式等颇为熟悉。在《词典》中,他引入了自创的四首诗,用诗歌表达了对南方工业生活的切身感受,充满真挚的生活体验和蓬勃的生命气息。在“冲凉”一章中,他引入了自己作的诗作阐释:“记得两千年到东莞/第一个落脚点是黄江/老乡说,冲凉!/后来我才明白是洗澡//这个鸟地方/洗澡就洗澡/咋叫作冲凉//也对/一腔热血壮志,很快/就被彻底地冲凉//”[8]诗歌简明的语言不仅解释了“冲凉”在生活中的常见含义,还借“冲凉”的多义表达了在南方工业生活中屡遭挫折的无奈之情,抒发自身情感,丰富了叙事和抒情的语言表达形式,增强了文本的张力,读罢令人回味无穷。
3.内容:超出“故事”的学术化趋势
人们通常认为,小说最基本的功能是讲好一个故事,但非虚构文学与生俱来的对真实“现场”的关注、对作者“在场”深入思考的期待、对社会功用的重视预示了它不仅仅满足于讲好一个故事。非虚构文学展现出向学术化发展的趋势,故事似乎已不再是它的核心,非虚构文学的目光转向关注,甚至是讨论社会热点话题,其切入点专业而深入,在展开讲述时注重措辞的准确和符合事实,尽可能避免夸大或遮蔽。
《词典》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化趋势。首先体现在小说故事线的弱化和人物的模糊化上。《词典》的关键词按照字母表排序,切断了不同关键词之间语义上的关联,削弱了文本中叙事的连贯性和衔接性,故事零散分布在文本的各个角落,呈现出片段化的特点,只为阐释关键词服务,成为词语的注解。传统小说常以人物塑造为核心,而《词典》并非如此,其故事中的人物常没有具体的姓名,仅以小Q等化名或甚至以简单的“老乡”代称,人物面目模糊,缺乏立体的形象和鲜明的特征,只担当演绎故事桥段、注解词条的功能,在需要的时候草率登场,讲解完词条所需的故事内容后便匆匆离场。其次还体现在讨论话题的全面性和专业化上。《词典》作者从自身多年工厂工作经验出发,列举了44个关键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和工厂生产秩序直接相关的,如“ISO”(国际标准化组织)、“QC”(品控)等;一类是和打工日常生活相关的,如“集体宿舍”“食堂”等;一类是和整体社会生活相关的,如“流动人口证”“暂住证”等,较全面地涵盖了打工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其对词语的阐释十分專业和严谨,比如在“流水拉”一章中,作者详细介绍了“流水拉”的构造和使用方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拉长、助拉、物料员等岗位,近乎一本专业指导手册。此外,在“打工诗人”一章,作者对打工诗歌的艺术特征、命名及其面临的诗歌内部话语权纠纷等问题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讨论,批评了打工诗歌中对苦难直白、毫不克制的宣泄,以及在诗歌艺术上的自我限制和满足,并表达出对打工诗歌中存在的“诗歌为个人私利打工”现象,即对某些诗人以打工诗歌扬名和自我包装行为的批判,这些有深度的独特思考也呈现出学术探讨的基本面貌。
实际上,古代的“小说”本为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之意,与论说、议论并不互斥。直到近代,中国小说吸纳了西方文学理论,才将议论和小说截然分开。非虚构文学的学术化倾向似乎可以说是一种对中国小说传统的复归。余岱宗认为:“‘百科辞典式创作意识以及多种学科话语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影响,让现代小说的文体呈现出多角度多方位地吸纳各种学科知识的态势。现代小说文体不再以单一的叙事路径贯彻文本始终,而是不断延伸出种种话题,让小说创作的‘故事成为吸纳多学科话语的载体,而不是让多学科话语成为‘故事的附庸。”[9]非虚构文学的学术化倾向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不满足于讲故事的野心以及作者身份的多重性使它的文本获得了丰富的含义和意义。
三、结语
选择跨文体进行创作意味着要打破传统文类秩序,勇于对传统文类进行实验性的探索和尝试,这对创作者而言是考验和挑战。萧相风从个人的感受出发,自觉地进行跨文体创作,他的《词典》是应对这场挑战的一次有效尝试。《词典》体现出的跨文体特征印证了杜鲁门·卡波特所说的“非虚构作品是一种既通俗有趣又不失规范的形式,它允许使用文学所有的手段”[10]。这种跨文体特征分别体现在结构布局、语言以及内容上:词典体小说的跨文体体式既能分门别类地展现真实生活,又能包含作者介入文学现场的思考;散文体、诗歌体的渗入在小说中增强了文本的抒情功能,丰富了文本的个性化色彩;小说超出“故事”的学术化趋势则使文本成为吸纳多学科话语的载体,赋予文本更丰富的价值和意义。文体的多样化表达使小说成为意义丰富的复合符号空间,打开了文学发展的新视野,同时也带来创作手法的革新,为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 王晖.现实与历史:非虚构文学的独特叙述[J].当代作家评论,2017(1).
[2] 王晖.“非虚构”的内涵和意义[J].杉乡文学,2011(6).
[3] 丁晓原.报告文学,回到现实大地的行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〇一〇年纪实文学》序[J].当代作家评论,2011(1).
[4] 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J].文艺争鸣,2011(3).
[5] 李云雷.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J].文艺争鸣,2011(3).
[6]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7] 留言[J].人民文学,2010(2).
[8] 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9] 余岱宗.百科辞典式的创作意识与现代小说的文体变革[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10] 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M].仲大军,周友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責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刘雅芳,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