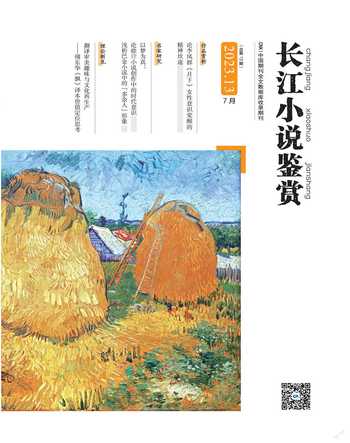狂欢化理论视域下的《红高粱家族》
2023-12-20王美银
[摘 要]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以其忧乐共生的情思、神奇瑰丽的想象、雅俗共赏的语言以及原初原欲的生命体验成为文坛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之一。莫言的诸多作品皆含有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因子,与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存在着契合。本文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框架,探究《红高粱家族》在叙事语言、叙事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狂欢化特质,并略述莫言狂欢化叙事产生的具体原因,从而揭示莫言狂欢化叙事的内驱力。
[关键词] 狂欢化 莫言 语言 《红高粱家族》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3-0070-04
以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为研究基础探索莫言的小说早有先例,但多以比较研究为主,如李贵苍、陈超君的《叙事的狂欢:莫言与格拉斯笔下的侏儒形象》,刘堃的《福克纳和莫言——狂欢化叙事的构建与阐释》。近年来,因狂欢化理论的深入传播,运用该理论研究莫言单部作品的论文也随之增多,如周琳琳的《论莫言〈檀香刑〉的狂欢化色彩》,以及周卫忠、宋丽娟的《莫言小说〈蛙〉的巴赫金诗学解读》。以上研究多从整体着眼,比较全面地把握了莫言作品中的狂欢化精神。
尽管前人对莫言作品中的狂欢化精神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读者对其作品阅读的深入,狂欢化理论在其作品中有了新的呈现方式与理解方式。因此,本文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其作品中的狂欢化特色做进一步的研究,使人们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在具体作品中的实際运用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一、狂欢化理论概述
1.狂欢化理论溯源
狂欢化理论与狂欢节息息相关,狂欢节的诸多特点是狂欢化理论的主要来源。中世纪的欧洲存在大量狂欢性质的庆典,古希腊、古罗马的木神节、酒神节等都是狂欢节的前身。狂欢节中没有任何的等级关系、限制以及禁令,人们不再以教会和王权作为官方话语,而是采取非官方的角度和立场。在狂欢节中,原有的社会身份消失,民众所体验到的是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平等和自由,解除了种种束缚,乌托邦的理想和现实暂时在狂欢节这个场所得到实现。因此狂欢节不仅仅是狭义上的节日,更代表了民间文化以传承的方式将即将消失的仪式通过狂欢节流传下来。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虽来源于狂欢节,但两者并非完全一样。狂欢化不仅仅是狂欢节活动中所有庆贺、演出、仪式的总和,还将与狂欢节类似的所有形式包括进去。狂欢化让狂欢节不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拥有了普遍的意义。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巨人传》时首次提出的,他以一本《拉伯雷和他的世界》拉开了研究拉伯雷的序幕,也拉开了对狂欢化理论的研究。
2.狂欢化理论的具体内涵
巴赫金在对狂欢节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总结出“狂欢式的外在和内在特点”,即狂欢化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狂欢式的外在特点包括四个方面:大众性、仪式性、平等性及娱乐性;而狂欢式的内在特点以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快乐的相对性及个体感受的双重性三个方面为突出特点。在三个特点之中,世界感受的狂欢化是最为重要的,它涵括两方面内容:颠覆与破除旧有的等级制,主张平等、自主的开放性对话精神;强调事与物的未完成性、变异性,反对其孤立自足的封闭性,这些内容也是诸多文学作品狂欢化理论的普遍表现方式[1]。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在文学中显著的特征是语言的张狂放纵,狂欢广场上的大众语言最贴合地表达着民间以及平民大众的思想诉求。这种语言让人们沉浸在狂欢的欢声笑语和平等自由中,消除了等级秩序,人与人之间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广场语言是粗俗的、冷嘲热讽的、夸张的,是根植于民间文化的诙谐。
二、叙事语言:随心、无修饰
狂欢化的语言以自由随性为特征,有时也体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它是狂欢外在的集中体现,其包括诸多形式:广场骂人、吆喝、起誓、粗口等。莫言的作品就从多方面表现了狂欢化的语言特征,在他的创作中,农民所运用的是符合他们身份的、随心且无形式约束的语言,粗话、脏话、咒骂等构成他们语言必不可少的部分。在《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的语言就极具代表性,他自称“老子”,且经常把“狗日的”“兔崽子”这些少见于传统小说中的粗鄙的话挂在嘴边,这些词汇语言原不应出现在以严肃规范为特征的书面语中,但因其与余占鳌所处的虚拟的“现实生活”非常契合,且此类叙事语言能够更直接地反映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以及人们内心的真实欲望,而被莫言大范围地应用于作品中,并构成其作品的一个语言特色。
同时,小说中描绘的肉体、生殖器、粪便等粗鄙形象颇为常见,它们也构成叙事语言的狂欢化特色。《红高粱家族》中屡次描写撒尿的场景,其中一次类似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降格”,即“我爷爷”往高粱酒的篓子里撒尿,却阴差阳错地酿成了上等的高粱酒。《红高粱家族》中还有多处提到了“乳房”、男性生殖器等肉体形象,枪弹射穿了奶奶高贵的乳房,暴露出淡红色的蜂窝状组织。
最后,对权威话语的戏拟是莫言小说狂欢化语言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戏拟是对社会语言的再度模仿或表现,进而达到一种嘲讽、蔑视、解构的目的[2]。《红高粱家族》中,九儿是一个小人物,她的种种行为只是为了个人的爱欲和幸福进行的抗争,一个小人物的落幕本可以用“死亡”来简要叙写,但莫言却用了“生的伟大”——在特定革命年代用来赞扬为国家和民族崇高利益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的词,这是对“死亡”的一种嘲讽,是对“生的伟大”的戏拟。
莫言的狂欢化语言用简洁、接地气的叙述方式展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其作品中那些粗鄙的叙事语言起到了支撑人物生活、行动空间的作用。在作品中,语言不再是经过雕琢后的精心安排,而是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随心之语,语言在小说的世界中尽情地狂欢。
三、叙事结构:复调结构
狂欢化的叙事结构在《红高粱家族》中具体指向文本中的复调结构。远古时代的狂欢节活动是最早的复调起源,而现实生活的复杂与多方面是莫言复调结构的主要来源。文学作品中的复调,多指作品的多声性,即作家与小说主人公是平等的,小说中有多个并列的声音在进行全面对话,《红高粱家族》从结构层表现出多声性,形成多个“声音”交融混杂的复调结构。
1.整体性结构的复调
《红高粱家族》从整体而言有三个既并列又彼此交融的声源,它们构成了小说最外层、最主要的复调叙事结构。小说的叙述者主要是“我”与“父亲”,以接受者的时空为起点,“我”代表着现在,“父亲”代表着过去,我们在两种不同的时空中并列存在,二者的声音在时空的交界处发生交融,“我”的声音服从于父亲的声音。同时,“我爷爷”虽然在小说中多存在于他人的叙述中,但在“父亲”处于儿童时期时,“我爷爷”的声音是故事最为权威的声音。由此,在叙述过程中就出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声源”,它们在不同的时空交错出现,但又统一于高密这一神奇的土地,这使文本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整体性复调结构。
2.多方面的综合复调
叙事手段中的复调多种多样,在小说中多采用的是叙事角度、内容以及叙事的时空排布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多方面综合性的复调结构。在《红高粱家族》中除了整体结构的复调性,莫言还设置了文本的多方面综合复调,即将时空的同时性复调结构与叙事角度的复调结构相结合。时空的复调性即前文中论述的“我、父亲、爷爷、奶奶”四人所处的三个既相连又相离的时空,而叙述角度的复调性则体现为一、三人称的不断交织以及隐含作者的不断登场。在文本中,三个不同时空有不同的行為主体,因而莫言设置了多个叙事角度,在“我”的时空中,“我”是第一人称叙述主体;在爷爷和奶奶的时空中,第三人称的叙述占主导地位。此外,小说中虽以“不动声色的叙述”为主,但在“我”和“爷爷奶奶”的时空中,作者多次现身发表自己的观点,隐身与现身在这两个时空中又形成了一种复调。部分学者曾指出,一部作品中多元素的相互组合可看作是一种叙事手段的复调结构,《红高粱家族》是一个容纳异样的声音、思考与对话的复调性文本。
四、人物形象:狂与痴
狂欢化的人物多指用狂欢式的眼神观察着现实生活,用相反的角度审视周边世界的特殊人群。他们往往以非理性的视角观察着常人难以窥视到的世界,碰触着其他人物不曾见识过的新领域[3]。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檀香刑》中的“傻子”赵小甲都是狂欢化的人物形象,他的诸多创作中还包括类似“精灵”或“怪人”的角色,这些特殊形象的塑造使得莫言的小说呈现出多种文化色彩交织的特色。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便将一批以“痴”和“狂”为突出特征的狂欢化人物带上文学舞台。
1.狂者:余占鳌与九儿
“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九儿”是《红高粱家族》中的狂者代表。余占鳌作为“狂者”,他的狂有两个突出方面,其一是对人伦秩序和礼教制度的蔑视。因为对九儿一见倾心,于是余占鳌不顾人伦纲常直接将回门的九儿掳进高粱地;为了让九儿能够及早地脱离苦海,余占鳌果断地杀掉了单家父子。他的许多行为或出于本心的喜恶,或出于突然的情欲,传统的人伦秩序与礼教制度对其并不构成约束作用。他“狂”的第二个方面主要表现为对当时权势的不屈服与反抗,面对各种政治势力的示好与拉拢,余占鳌一概拒绝,其凭借自己的才智与胆识建立起一支能与日本人周旋抗争的土匪队伍。他对向自己示好的政治势力是不屑的,他并不怕他们对他的打压,相反,他认为这种压迫反而更有助于其队伍的成长。
九儿作为当时的女性,与余占鳌不同,她的战场是向内的,她叛逆的对象是家庭。九儿的“狂”以对传统“三纲五常”的漠视和对父权、夫权的反叛为主要表现。首先,她蔑视传统的封建礼教,做出许多不为当时礼法所容的大胆荒唐的行为。她会用小脚掀开轿帘,只是为了去看轿夫宽阔的肩膀;当她发现是余占鳌将自己掳进高粱地时,没有惶恐,反而暗呼,被幸福冲得强烈震颤。其次,不似传统的温柔淑女与贤德妇人,九儿敢于反抗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与夫权。她嫁进单家非本人意愿,故而其不情不愿的情绪远高于所谓成亲的喜悦,为了表现自己的不满、愤怒,也为了为自己谋得一线自由,新婚之夜她手握剪刀。对父亲的所作所,她也是百般怨恨的,于是在当家后,用二十个包子决绝赶走自己的父亲。凡此种种,皆反映了九儿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反叛者的“狂”。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莫言设置狂者形象的用意,这类人物形象的存在对建立一种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狂者是世界的反抗者、破坏者和追求自身理想的坚定行动者,他们不同于那些屈从于传统道德伦理的庸常人物。狂者的人物形象源自民间诙谐文化中的怪诞人物形象,其外在的形象就是对常态化形象的颠覆,同时,狂者即余占鳌与九儿的观念与传统伦理道德中宣扬的观念格格不入,这使得二者在内在思想上也背离了传统的人物形象。通过写狂者内在与外在的奇特和他们的种种反常行为,来打破接受者心中预设的对过去世界不平等的认知,重构文本的潜在社会秩序,呼唤文本接受者的自由平等意识。
2.痴者:父亲
“父亲”是《红高粱家族》中“痴”者形象的突出代表。《红高粱家族》整体故事的展开背景是在父亲14岁多一点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都是父亲回忆式儿童视角的产物。儿童受伦理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不深,保留了最原初的天真状态,故而父亲作为儿童所看到的是事物既本真又混乱的状态。作为儿童的父亲很容易产生一种无知迷茫的“痴傻”状态,如他不理解九儿死后余占鳌的种种特殊行为,不明白“我爷爷”脸上两行泪水背后的真正情感含义;不理解九儿对“二奶奶”的种种恶毒咒骂。这诸多的“不理解”是父亲作为儿童对成人世界繁杂关系的不解,其只能看到事物与行为最表层的意义,这是莫言对父亲采用儿童视角所产生的必然命运。
3.人物的“脱冕”作用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仪式是“笑谑地给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而脱冕者就是那些小丑、骗子和傻瓜”,所谓“脱冕”便是对权威与规则的解构与消减。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通过构建痴者与狂者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另类怪异的行为提出对官方道德价值观的质疑。同时,因为这些狂欢化的人物,莫言的小说不再是单声部叙事的世界,而是多种声音混杂的多声部共鸣世界[4]。这样的文本世界里,叙述人不再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是被其他声音质疑的对象,而文本中所渗透的传统道德观也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文本的规则意识被削弱。
五、莫言狂欢化叙事产生之根源
矛盾多元的社会因素与历史因素是莫言狂欢化叙事产生的主要原因,莫言所处的创作现实环境正是一个矛盾的、多元的文化环境,其创作受到当时文艺界呈现出的新气象的影响。当时,我国文坛语言脱雅趋俗的审美倾向盛行,这使莫言摒弃了原本选择的优美典雅的语言,转而使用以俗为特征的文本语言,这也为其狂欢化语言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可能。同时,西方文学思潮中现代派的文学精神、个性的思维观念恰好与莫言反叛封建传统道德、颠覆传统的审美原则相契合。由是观之,莫言狂欢化叙事的形成既与个人选择息息相关,更多的则是时代影响的必然结果。
六、结语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一部极具特色的小说,其在魔幻现实主义之外,又流露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特色:用粗俗戏拟的狂欢化语言、复调式的狂欢化结构、痴与狂的狂欢化人物,使文本呈现出“狂欢化”特征。总体而言,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在《红高粱家族》中的凸显,不仅给读者解读文本提供可捕捉的线索,而且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时代性新理解做出了特别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亚.《红高粱家族》的“狂欢化”叙事[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3(1).
[2] 丁国兴,陈海权.神魔共舞的狂欢化叙事——《红高粱家族》中莫言的叙事特色[J].江西社会科学,2005(1).
[3] 李小歌.莫言小说中的狂欢化形象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9.
[4] 刘堃.福克纳和莫言:狂欢化叙事的构建与阐释[J].求索,2017(8).
[5] 牛镭.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叙事特色赏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13(4).
[6] 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 薛伟,周敏.嗜血的狂欢——解读《红高粱》的“狂欢化”[J].名作欣赏,2014(2).
[8] 杨宇.莫言小说狂欢化特色探究[D].兰州:西北大学,2010.
[9] 张力浠.巴赫金狂欢化理论视角下的《十日谈》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5.
[10] 周卫忠,蒋颖.巴赫金诗学的狂欢话语與莫言小说的民间话语[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9,40(1).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王美银,南华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