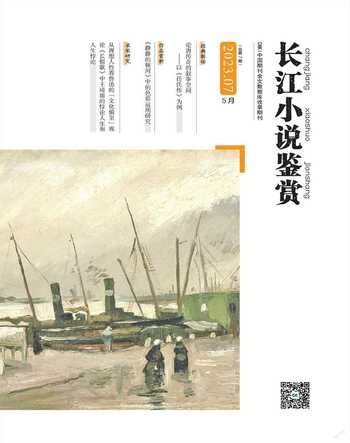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中的色彩运用研究
2023-12-20李玉竹
[摘 要]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是20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静静的顿河》是世界文坛上一部不朽的巨著。此座丰碑的造就,离不开肖洛霍夫在作品中对色彩的巧妙运用。本文从文学与色彩的关系入手,结合肖洛霍夫本人的美学原则,分析色彩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状态、表现状态流动、形成对比关系、构建各类环境、助力艺术手法发挥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 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 色彩研究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07-0054-04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是20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曾获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静静的顿河》是世界文坛上一部不朽的巨著,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安德斯·奥斯特林在授奖词中称其为大家展开了一幅绚丽多彩、气象万千的乌克兰风景画。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同乡、哥萨克老作家绥拉菲摩维奇也曾多次盛赞肖洛霍夫作品中色彩的非凡,早在为《顿河故事》写序时就曾评价肖洛霍夫的写作语言是一种富有色彩的语言,十分形象,就像草原上的鲜花一样,明亮鲜艳,生意盎然。随手翻开《静静的顿河》的书页,各种颜色跳跃其间,白纸黑字上支棱起斑斓的画卷。肖洛霍夫在作品《静静的顿河》中对色彩的巧妙运用,无疑是造就此座丰碑的重要原因之一。
曹继强在《试论色彩与文学》中谈到,文学和色彩之间本不存在着必然的关联,但是通过社会生活这个纽带,二者得以联系起来。一方面,文学反映着社会生活,另一方面,色彩是社会生活的呈现,具有丰富、生动、形象的特点,并且包含着特定的内容与情感。因此,色彩自然而然地融入文学所反映的圈层,参与文学形象的塑造,渗入文学语言的表达。曹继强借用马克思的话进一步说明“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他认为,色彩美拥有不容小觑的审美价值,是一种促成主观情感和客观存在和谐律动的重要的形式美。文学之所以可贵,就是因其形象性强于一般社会科学,丰富性高于其他艺术门类。色彩的形象性与丰富性则能够帮助提升文学的形象性与丰富性,益于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因此,有必要把色彩这一蕴藉着情感内容的形式美自觉地引入文学领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必然会给人以美的享受。如高尔基所说:“我所理解的‘美,是各种材料——也就是声调、色彩和语言的一种结合体,它赋予艺人的创作——制造品——以一种能影响情感和理智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就是一种力量,能唤起人对自己的创造才能感到惊奇、自豪和快乐。”色彩,也必然是组成文学作品之“美”不可或缺的材料。
與众多擅用色彩描写的作家不同,肖洛霍夫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美术知识,也不曾潜心研究绘画艺术,他在色彩上的出众表现与他的艺术造诣不甚相关,而是最直接地源自他的经历和他的所见所闻。他没有刻意地玩弄技巧去构造色彩世界,只是随性地书写,诗意地记录。当他睁开好奇的双眼打量这个世界时,亲爱的哥萨克的面貌就永远刻进他的心扉。当他蹒跚学步、咿呀学语时,他的足印就掠过了顿河的美景,顿河的方言亦擦过他的嘴唇。他在草原最为柔情的哺育下生长,就此缱绻一生。故乡的一切都与他息息相关,在他的作品中发出奇响。与此同时,他心目中的“真实”并不排除残酷丑陋的一面,当然也不排除在表现“社会斗争的苦难与悲剧”时,细节描写的逼真性和严酷性。肖洛霍夫有着极严格的“细节真实观”,他认为,即使是在细枝末节的刻画上,也要讲求真实,不能凭空想象杜撰,否则将失去读者的信任,读者会怀疑作家在大事上也有撒谎的可能。为此,他在为《浅蓝的原野》作的序中,写了关于“银白色羽茅草”的一段话,充分表现了他的美学原则:“在莫斯科,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莫普(即‘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文学晚会上,可以随便听到说,草原上的羽茅草(还不是一般的羽茅草,而是‘银白色羽茅草)有种特殊香味……实际上,羽茅草是种极其讨厌的淡黄色的草……没有一点香味。不能赶羊从那里经过,因为扎上羽茅草的刺,羊就会死。”由此足见肖洛霍夫的心细与严谨,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是其作品中的每一小处着色,都浸透着他的考量与斟酌。
一、色彩与人
《静静的顿河》以生长在顿河边的格里高利为男主人公,展示了在战争大背景下俄国特殊群体哥萨克人的苦难历程。肖洛霍夫用悲剧的手段,令一个个姿态各异的形象跃然纸上,每个人物都置身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构成形形色色的人物画廊。
作品中大量色彩被用来描述人,且反复出现,时常成为人物牢固的记忆点。色彩于文学十分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在读者还未完成整体信息的集合以形成总体印象前,作为刺激性信号先一步引导读者的感知,带给人直觉的愉悦。《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就经常利用色彩的这一特点来提高作品的表现力和吸引力。比如阿克西妮亚的黑眼睛:情意初生,面对格里高利时,她心头烦乱,不知所措,“她那黑眼睛角上忽然挂起了泪珠儿”,楚楚可怜;面对潘捷莱的质问责骂时,她用“一双黑眼睛火辣辣地盯着他”,出口的话更为泼辣;偶尔与司捷潘和谐相处时,她“忽闪着头巾下露出的黑眼睛”,言笑晏晏;终于与心爱的格里高利两人世界时,她总“把潮湿的黑眼睛移到格里高身上”,情意绵绵;格里高利独自一人思念阿克西妮亚时,首先回想到的也是阿克西妮亚“用火辣辣的黑眼睛又顽皮又多情地从下面盯着你”;谢尔盖一时没认出阿克西妮亚,对她的第一反应也是一个“胖乎乎的黑眼睛漂亮女人”;得知格里高利没死时,她“模糊的黑眼睛里没有眼泪,但是流露出很深的痛苦和默默祈祷的神情”;和格里高利一齐离开时,她“两只黑眼睛在白绒毛头巾下面亮闪闪的”,充满期盼……阿克西妮亚灵动的黑眼睛就这样从头到尾地眨呀眨,在所有事件里闪烁,涌动她纷杂的情绪,成为阿克西妮亚魅力形象的重要闪光点,直到她最终死去,眼睛变得昏暗,阿克西妮亚的黑眼睛没能再次出现,故事也走向尾声。又比如米佳的绿眼睛,几乎米佳的每一次出场,肖洛霍夫都会有意识地提到他的眼睛:米佳想引诱娜塔莉亚时,“忽闪着绿色的猫眼睛,像切口似的两个瞳仁在过道的黑暗中亮晶晶的”,充满危险的信号;面对妲利亚,他“眯缝着轻佻的绿眼睛对妲利亚瞟了一会”,诸多暗示;他人争论时,旁听的“米佳那像猫一样竖着的瞳仁亮闪闪的,使人看不出,他的一双绿眼睛在笑,还是气汹汹地冒火”,心思难测;全村人来到会场开会时,对大家均是衣着方面的描述,只单独点到了“绿眼睛的米佳”;自愿为他人执行死刑时,他也是“忽闪着眯得细细的绿眼睛”,尽显残忍……米佳最突出的就是这样一双猫一般的绿色眼睛。绿色眼睛通常被认为是带有一定邪恶意义的,早在古罗马时代,诗人马提亚尔就提出绿眼睛属于堕落邪恶之人,此后这一说法长盛不衰,相面学认为绿眼睛反映出恶劣的本性、虚伪狡诈的灵魂、放荡堕落的生活方式。米佳这一角色也正符合绿眼睛的象征。肖洛霍夫也常常多次利用颜色强调人物某一方面的特点,反复代称引用。比如在卷四第一章中,上尉的斑白头发比他的姓名出场更早,更多。我们先看见一个“用手撩了撩乱蓬蓬的斑白头发”的军官,看见这“斑白头发的军官”与人交谈,发生行动,方知这是“斑白头发的上尉梅尔库洛夫”。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在描述门把都像镀了金的莫霍夫家的女儿时,肖洛霍夫多次用到了粉色,显示其娇嫩。她的嘴唇是粉红色的,饱满的,脚指甲也是粉红色的,手掌也是粉红色的。在娜塔莉亚初见格里高利时,小说也描写过一次她粉红色的酒窝,那是属于少女初见心上人的娇羞。阿克西妮亚曾经病得厉害的婆婆,嘴唇就绝非粉红色,而是焦黄的。阿克西妮亚在司捷潘回来后又看见格里高利,心跳之下,嘴唇则是煞白的。格里高利尚且年轻,眼白是蓝蓝的,老去的潘捷莱,眼白则是黄黄的。阿克西妮亚想找德萝兹季哈治疗相思病时,想着格里高利,望着东方,那边是幸福的玫瑰色。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亚的事情暴露给司捷潘,阿克西妮亚惊慌失措时,他俩幽会的院子月色是昏黄的,篱笆外是不知为何物的黑糊糊的东西,屋里司捷潘军服的银条不亮了,阴影灰沉沉的,仿佛一切颜色都是消沉的、无光的。不同的颜色,显示了不同人物、不同时段的情状、心境。除了静态地显现某一刻人物的状态,颜色在流动之中也揭示了人物的状态变化。亲家米伦当在户外受了冻,褐色麻子就会变成灰色,当他看到娜塔莉亚出嫁又突然回娘家,发了急,麻子又变成灰白色。格里高利最初带着阿克西妮亚私奔出去讨生活,要向中尉解释自己还带着一个娘们时,“透过毛玻璃从阳台上射进来微弱的光线,变成了粉红色”,八卦起来的中尉的眉毛也被这亮光照成粉红色,暧昧之息尽显。绿眼睛的幼猫在成年后眼睛会逐渐变黄,而拥有猫一般绿眼睛的米佳,到了作品尾声,也变成了猫一般的黄眼睛,完成了他性格上的转变,他已然完全成为一个冰冷无情、决绝残酷的人。
二、色彩与境
颜色还能够形成对比关系。我们往往会将暖色调、亮色调与热烈、积极的情状联系起来,而将冷色调、暗色调与低沉、抑郁的情状相联系。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联想的过程,其实就是视觉经验与其他感觉经验搭建互通桥梁的过程。文学色彩心理也立足于此。肖洛霍夫对战斗状态下的着色总是暗沉而阴冷的,马刀闪着青色寒光,田野是灰色的背景,黑黑的新耕土地迎面飞来……顿河的冰透着青色,烟灰色刺刀蒙着水汽,一件件灰大衣晃来晃去……给本已紧张的气氛抹上更为严峻冷酷的色彩。而当格里高利在战争中回忆起童年,回忆起心中那最神圣隐秘、最柔软的地方时,看到的是蓝蓝的艳阳天,毛茸茸的綠树,金黄色的麦茬,是一切鲜亮活泼又轻快的颜色,何其温暖,何其美好。而生活在这片美好土地上的哥萨克人民都是黑黑的,他们有黑黑的脖子,黑黑的胳膊,黑黑的手掌,黑黑的胸膛……唯有一口白牙常常配合着爽朗的笑容。他们热爱劳动,淳朴自然。与此相对的,处于上流社会的军官们养尊处优,卡列金有着“白皙的手”,阿列克塞耶夫有着“白白的手”,波波夫有着“肉嘟嘟的白手”,有副官“优雅地扎煞着白嫩的手指头”,也有军事监督“那又白又嫩的手指头”被格里高利“那又黑又粗糙的手指头轻轻地碰了一下”,就“把手一缩,好像被扎了一下似的,并且在灰大衣腰上擦了擦,厌恶地皱起眉头,戴上手套”。格里高利却也表示“对于这些白脸白手的家伙,我一点也不心疼”。黑与白,在此刻形成一种对比,划出一道沟壑,即使能够一同作战,双方的内心也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
富丽的环境画卷的构成更是离不开色彩的渲染,这画卷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美丽的顿河河畔,一年四时,各有其景,各有其色。在肖洛霍夫的笔下,早晨,是淡灰色天空,风过黑云,晨雾如灰色无头蛇,万物沐浴于通红的朝霞,露珠为青草蒙上银色,留下过路人烟黄色的脚印。夜晚,树枝黑黑的轮廓印在深蓝色天空的画布上,星星如肥大的蓝黄色仙果挂在枝头一般,闪烁在树枝间。秋日,蓝天显得有几分暗淡,小山沟上掉落的苹果树叶子却鲜艳如红血,山岭后的地平线则成翠绿一片。冬日,白雪皑皑,银色雪粉飞舞,又经阳光照射放射出童话般霓虹的色彩,瓦蓝色的寒鸦在黑糊糊的烟囱旁取暖,受到惊吓,又立刻划过淡紫色的天空。明暗斑驳,动静结合,肖洛霍夫用他的一双光影魔术手,将一切呈现得如诗如梦。在这布满美丽自然风光的土地上,也有着盛大的人文节日盛景。“三一”节后,全村人就会一起出来割草,阳光透过灰羊羔皮一般的云片洒下,绿得透着墨光的草场上闪耀着艳丽的绣花围裙、五颜六色的花头巾,像七彩缤纷的霓虹。何须丹青,自有画意,有大的整体布局,有小的细枝末节,“三一”节日图跃然纸上,极显风情。这些画卷,既是写实,又是抒情,更是哲思。
三、色彩与技
色彩,助力于艺术技法的形成。如卷四十五章中,“那个尹古什人眯缝着眼睛,急躁地发表着意见,频频举起一只手来;他那上衣的袖口卷了起来,露出雪白的绸里子。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最后看了一眼,看见了这白得耀眼的绸里子,不知为什么他眼前出现了被旱风吹皱了的顿河水面,层层的碧波和海鸥那斜斜地耷拉下来、用尖儿划着浪尖的白色翅膀。”蒙太奇在法语里意为“剪接”,在俄国逐步发展成一套组合电影镜头的理论,当单个不同的镜头被拼接到一起时,会形成新的含义,这是它们独立呈现时所不具有的。在这个场景中,画面的转换、镜头的拼接通过“白”这一色彩成功做到了。又如最后一章中,“犹如是从恶梦中惊醒,他抬起头,望见头顶上黑沉沉的天空和一轮闪着黑色光芒的太阳。”这是《静静的顿河》中极为经典的一幕,历来为人所称道。太阳如何是黑色?在正常现实情况下,太阳无论如何也并不会变成黑色。这里的“黑色”,代表的是格里高利当时的心理状况。只因哀切,只因望绝。在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中,艺术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而存在的,艺术的目的就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石头就应该有石头的质感,所以他提出了“陌生化”的说法。此番描写,正是打破了常规的“自动化”阅读,打破了“完全确实”的情境,满足了读者“趋新”“好奇”的心理,产生了很强的“陌生化”效果。
四、结语
总而言之,肖洛霍夫对色彩的匠心运用为《静静的顿河》中的人物打造、感情宣泄、状态变化、环境建构、艺术效果等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窗口,为作品注入了更多缤纷的活力。不可否认,色彩作为一种载体能够表达各种情感、理念和信息,是文本构建中难以或缺的因素,色彩的合理运用能给文学本身增添无限的魅力。色彩经常且普遍地作为文学内容构成的一部分存在,参与人物、环境等的塑造描写,并因此而具备情感,有时甚至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它也是色彩心理积极活动的结果。应当说,文学色彩在增添文学的感受性上、在文学的美学表现上,其意义都是不能低估的。倘若文学有可能摆脱掉色彩心理的纠缠,人们就会发现,那些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不过是些难以消化的皮带和干巴巴的劈柴。一方面,色彩为自然现实充当表现者和摹写者;另一方面,它充分表现出作家的主体意识。所有的色彩事实都必须是创作主体所能够亲眼观察到和感觉到的具有主体自身独特意义的东西,从它开始被主体反映时便已经是“人化”的了。可以说,色彩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心理方式和表现。所以研究文学与色彩,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色彩运用,对于挖掘作品深意,更好理解作品,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M].力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2] 何云波.肖洛霍夫[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3] 孙美玲.肖洛霍夫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4] 黄浩.文学色彩学[M].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
[5] 芝兰斯基,费希尔.色彩概论[M].文沛,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6] 帕斯图罗.色彩列传:绿色[M].张文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7] 李建军.任何人都会在它的翅膀下感到温暖——论肖洛霍夫与《静静的顿河》[J].当代文坛,2018(4).
[8] 曹继强.试论色彩与文学[J].当代文坛,1986(3).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李玉竹,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