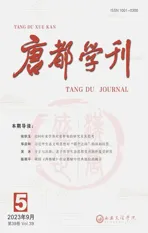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2023-12-20陈丽平
陈丽平
(辽宁大学 文学院,沈阳 110136)
京都赋是两汉大赋中最具代表性题材之一,以都城为赋作题材始于扬雄《蜀都赋》,之后杜笃创作了《论都赋》,在汉明帝时掀起都城赋创作的小高潮,班固、崔骃、傅毅均大致同时创作了都城赋,而班固《两都赋》是其中篇幅最长、影响最大的创新之作,大约五十年后,张衡模拟《两都赋》创作了《二京赋》。这两篇赋作因为题材、风格类似,赋作者又同属于东汉著名的大赋作家,所以这两篇作品常常被作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京都赋相提并论。这种习惯容易让读者忽视一个事实:在六朝的文化背景中,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在当时人的文学接受中,其文学审美与创作水平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张衡《二京赋》在赋学审美上被高度评价,而《两都赋》处于被忽视状态,其赋学地位是边缘化的,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这种审美差异化现象就更为突出。这种文学接受状态的原因何在?班固《两都赋》又是在何时、何种契机下使其在六朝时的京都赋接受中由边缘走向中心?以下将从赋学风尚、注释学、文化背景等方面入手来探究这些问题。
一、魏晋赋学风尚中重《二京》轻《两都》取向
汉初大赋受到纵横家言的影响,具有铺张扬厉的特点,赋家为了营造文章气势,形成了夸饰虚构、罗列名物、堆砌辞藻的风气。扬雄是改变汉赋风格的关键性人物,他从“讽谏”效果出发批评汉大赋“劝百讽一”,这使得汉赋在夸饰、虚构方面渐渐弱化,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就是这一风气转变过程中的作品。
魏晋时期兴起的赋学风尚,崇尚可信征实、广博。这种观念在曹丕《答卞兰教》中已经有所体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1]119曹丕强调赋的文体特点之一是以“事类”依附的特征,强调赋作者不应该夸大其词,对于所叙述对象当持实事求是原则。左思对于《三都赋》颇为自信,《三都赋序》详细说明了《三都赋》在征实、博物方面超迈前人,“匪本匪实,览者奚信?……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2]645左思以征实可信为标准评论赋家时,对汉代的赋作名家进行批评,认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赋作举例其“假称”,批评其文辞藻饰、内容虚而无征。因而,左思对于包括《两都赋》在内的大赋持批评态度,表现出重写实轻文辞倾向,左思在《三都赋序》中对于赋作的征实性做了说明:“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2]645之后,皇甫谧《三都赋序》中也强调了赋作征实的重要性,“其物土所出,可得批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案纪而验,岂诬也哉!”[2]74要求赋中所提及的物产、制度,都符合实际,不能有夸饰。
博物趣味是魏晋赋学的又一新变。班固《东都赋》在具体事物铺陈的丰富性方面逊色于张衡《二京赋》,这是魏晋之后人们重《二京赋》轻《两都赋》的又一原因。《二京赋》比《两都赋》更为详尽地描写了社会的人情习俗,详细描述长安的繁盛富丽,生动描写了鱼龙百戏等戏剧、杂技。文辞也更为富瞻弘丽。《三国志·国渊传》中,魏郡太守国渊认为:“《二京赋》,博物之书也。”[1]256国渊的评价,显示了对《二京赋》中对物产等事项描写的兴趣。萧子显《南齐书·乐志》载:“角抵、像形、杂伎,历代相承有也。其增损源起,事不可详,大略汉世张衡《西京赋》是其始也。”[3]说明萧子显也把张衡《二京赋》看作是博物之书。这体现了魏晋之后《二京赋》比《两都赋》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南朝时期赋学审美变化,还体现在对物象描摹细致。《文心雕龙·物色》指出:“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4]419刘勰概括的晋代以来的赋学审美,重视物色的细致描摹,讲究物态描写生动。《南史·张融传》提到顾恺之指出张融《海赋》缺乏对盐的描写,张融立即求笔添句,“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5]展现了当时注重细致描摹的赋学审美特征。
班固《两都赋》开创了把两个都城对照书写的体式,张衡《二京赋》在赋的结构上沿袭了这一体式。班固《两都赋》创作宗旨在于通过对都城的描写讽刺西汉、赞颂东汉,这样的创作宗旨使得他在西都与东都的描写上存在差异。《两都赋》对西都长安的描写,尽力表现长安宫室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奢,描写颇显夸张;东都的描写重点则在光武帝拨乱反正、汉明帝制度、典礼建设上,对畋猎、宫室的描写,就克制、简洁得多,宫室部分只叙述明堂、灵台、辟雍相关内容,就文辞与气势而言,与西都描写相比黯然失色。因而,曹道衡先生认为《两都赋》是存在缺憾的,“因为他所写长安富饶的情况多系目睹的景色及熟习的史事,所以不少片段写得有声有色;写到洛阳时,则未免把君主理想化,结果仍不免有空洞说教的成分。……写实的成分有所增加,夸饰过度以至离奇的神话内容,已不复存在。”[6]曹道衡认为东都的描写远远逊色于西都,西都铺张描写丰富而东都显得单薄。就两都叙述均衡、物象丰富生动、描写细致而言,张衡《二京赋》是更为成功的。张衡《二京赋》创作目的就在于讽刺东汉社会风气的过度奢侈,《后汉书·张衡列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7]张衡对于两都所代表的政体都有不满,有借描写都城批判政治的意图,有学者认为《二京赋》的完成,与张衡青年时期出武关、游三辅、观京师的生活经验有关,因而二京的描写比《两都赋》更为丰富、生动,在写实性上更为准确。张衡《二京赋》对于个别事例的描写浓墨重彩,如《西京赋》中对于“百戏”的描写,刻画生动、形容详尽,《东京赋》中对“大傩”的描写也令读者印象深刻。李善《西京赋》注中提及杨泉《物理论》盛赞“平子《二京》,文章卓然”。
因而,《两都赋》《二京赋》在六朝时期文学接受的不均衡状态,既受到魏晋时期新的赋学审美风尚影响,也是由其作品自身的艺术水平决定的。班固《两都赋》对西都、东都的文学描写艺术水平的不均衡,其艺术审美也与晋代以来新兴的赋学审美不吻合,导致了《两都赋》的边缘化。而张衡《二京赋》具有博物特征,描写富赡而且较为写实,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在魏晋以来不断被发掘,在六朝崇尚征实、博物的赋学追求下,《二京赋》在京都赋中的代表性以及经典作品的地位在西晋时期就确立起来了,而《两都赋》经典地位的确认要到梁代萧统的《文选》编撰之后才最后完成。
二、《二京赋》《三都赋》并称与《两都赋》的边缘化
左思《三都赋》问世后,文人们乐于将《二京》《三都》并称,而这种现象又转移至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在赋的注释学成果日益流行后,为《二京》《三都》注释非常流行,两篇作品均出现了多种注释本,而《两都赋》不仅少见于文人们的议论,并且在注释学领域也被边缘化了。
据《抱朴子·钧世》第三十记载:“《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
《世说新语·文学》中云:“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眦,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
《晋书·孙绰传》中绝重张衡、左思之赋,每云《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也。
左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左思《三都赋》问世后,晋宋之际的人们常常将《二京赋》《三都赋》并提,称颂其成就,以上葛洪、张华、孙绰以及庾亮的言论,均是将张衡《二京赋》与左思《三都赋》并提,并且,《隋志》著录《五都赋》说明魏晋时期对张衡《二京赋》的评价远远高于班固《两都赋》,班固《两都赋》确实未能成为那个时期人们心目中京都赋的经典。
《两都赋》被边缘化还表现在魏晋之后的注释学领域,此时,对赋注释的风气渐兴,在汉代以来众多赋作的注释成果陆续出现时,班固《两都赋》却始终未有注释之作。在现存文献中,东汉、魏、晋、宋、齐梁时期,集部文献的训诂、注释并不丰富,汉代以后的诸多单篇赋陆陆续续有人为其作注,比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班固《幽通赋》、张衡《二京赋》《思玄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左思《三都赋》、潘岳《籍田赋》《西征赋》《射雉赋》、谢灵运《山居赋》,都有东汉至齐梁时期的学者为其作注。其中,与《两都赋》题材、写作思路最为接近的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甚至有多家注释。《二京赋》的作注者有曹魏时期的薛综、晁矫、傅巽,两晋时期的李轨、綦毋邃;《三都赋》的注者有两晋时期的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等(1)《文选》李善注保存了一部分旧注,《文选集注》中也有这些旧注遗存,刘跃进著、徐华注《文选旧注辑存》对现存旧注做了新的整理。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赋注有“《二京赋音》二卷,李轨、綦毋邃撰;《齐都赋》二卷并音,左思撰。”“《杂赋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晁矫注《二京赋》一卷,傅巽注《二京赋》二卷,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赋》三卷,项氏注《幽通赋》,萧广济注木玄虚《海赋》一卷,徐爰注《射雉赋》一卷,亡。”“《洛神赋》一卷孙壑注。”“《二都赋音》一卷李轨撰。《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梁有《赋音》二卷,郭徵之撰;《杂赋图》十七卷。”。在这种背景下,班固《两都赋》却始终未出现注释作品。这种现象,说明班固《两都赋》在魏晋时期确实不被人们重视,因而也未能吸引学者为其作注。
刘宋之后,总集编撰之风渐盛,时人编撰专门赋体总集的热情很高。谢灵运撰《赋集》92卷,同时以《赋集》为名的总集还有多种,如宋新渝惠侯撰50卷;宋明帝撰40卷;后魏秘书丞崔浩撰《赋集》86卷,说明赋集编撰,受到刘宋皇族与门阀士族的重视。这个风气延续到了齐梁时期,梁武帝萧衍编撰了《历代赋》。《隋书·经籍志》中还出现了各类专题赋集,如《乐器赋》《伎艺赋》《杂都赋》等。《隋志》著录有“《五都赋》六卷,张衡及左思撰”[8]722,出现了将张衡、左思二赋合到一起的“单行本”,这反映了《二京赋》《三都赋》的流行,是当时人将二赋并称风气的反映,同时显示出《两都赋》的边缘化。
三、刘宋以来京都赋题材的突出与萧统赋学思想的渊源
编撰文集之风兴起于刘宋时期,门阀士族、皇族热衷于对文士的招揽,乐于树立“好文”的名声,宋新渝惠侯刘义宗“爱士乐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称之”。临川王刘义庆“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当时著名文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聚集于刘义庆处。宋明帝“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于华林园芳堂讲《周易》,常自临听”[9]113。他们与召集的文士编撰了丰富的书籍,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宋新渝惠侯、宋明帝、谢灵运都编撰过《赋集》,梁代萧衍《历代赋》、萧统《文选》的编撰,正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京都赋位于诸多赋题材类型之首,至少在刘宋初年的总集中已经定型,赋集编撰促进了赋作题材类别的分辨,曾编撰《赋集》的谢灵运较早提到“京都赋”。谢灵运《山居赋》序中,“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9]1161这里提到的前四种类型的赋作题材,很可能是他编撰《赋集》中的典型题材,把京都题材置于宫观、游猎之前,这与晋宋之际张衡《两京赋》、左思《三都赋》流行的趋势是符合的。
梁代《文选》与《文心雕龙》是对赋作总结最全面深入的,延续了赋作总结中按照题材分类的做法。《文心雕龙·诠赋》也提到了赋作的分类,“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对称[4]60,其中“京、殿、苑猎”对应的正是谢灵运的“京都、宫观、游猎”,谢灵运、刘勰所强调的“京都”在萧统《文选》中也排在第一位。《五都赋》的出现,说明了人们对京都题材中张衡、左思赋作的重视。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才得以正式形成,成为与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同样的经典。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萧统赋学观的独特,这与萧统储君身份有密切关系,强调文学政教意义,强调臣子对当朝皇权的颂扬自觉,也与萧衍、沈约对他的影响有关系。
梁武帝登基后为了在思想上加强统治,借助于对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倡导,设置五经博士,广开学校,修订礼乐制度,重孝道,萧衍的这种心理也体现在他登基前后文学风格的差异,“前期作品显示着一定程度的才华,而后期作品却是一堆令人生厌的说教。”[10]56萧衍的思想转变,在太子萧统的教育中也体现了出来,萧统在童年时期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遍读《五经》。萧衍在东宫的藏书与人才储备上可谓用心良苦,有计划让太子萧统成为儒家思想推广的助手。
萧统《文选》展现出的对儒家思想的强调、对皇权权威的维护,是其父萧衍教育理念的呈现。萧衍本人对赋集编撰也很有兴趣,《隋书·经籍志》著录了他编撰的两部赋总集,“《历代赋》十卷,梁武帝撰,……《围棋赋》一卷,梁武帝撰。”[8]722萧衍还命才学之士为赋集作注释,“十七年,……左卫率周舍奉敕注高祖所制《历代赋》,启兴嗣助焉。”[11]但是,萧衍《历代赋》是无法被萧统简单复制到《文选》赋类当中的,《历代赋》是通代的、追求作品多而全的总集类型,萧衍热衷通代集大成特征的学术总结工作,“令群臣编撰《通史》,三皇五帝一直到梁代,……编撰《全策》三十卷”[10]49-50,而《文选》编撰宗旨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2]2。萧统精选赋作涉及对精品赋作的认定、分类与排序等问题,需要与《文选》中诗、文等文学体裁编撰风格相一致,也就是说,《文选》儒家思想倾向与重教化、维护君威思想源于萧衍的影响,而体现的审美思想是萧统的个性特征呈现。
萧统赋学观念也受到其师沈约影响。沈约曾协助萧衍即位,被任命为太子少傅,沈约在赋学认识上对于萧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沈约撰写《宋书·谢灵运传论》,全文录入了谢灵运两篇长赋《撰征赋》《山居赋》,同时录有序和谢灵运自注,沈约突出强调了谢灵运诗歌影响力“名动京师”,却没有完整收录一首谢灵运的诗歌。沈约在该篇中也谈到他对汉代文学的看法,充分肯定了司马相如与班固著作的文学里程碑意义,“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9]1176魏晋以来,沈约是第一位对于班固赋学的转折意义做出积极评价的人,沈约对班固赋学史地位的重视直接影响到了萧统。
四、《两都赋》在萧统《文选》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相对于魏晋以来班固《两都赋》的边缘化,《文选》将《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奠定了《两都赋》作为两汉文章最重要代表作的基调。刘勰是最早明确肯定班固《两都赋》政治及道义价值的,“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4]433这就摆脱了左思、皇甫谧以“征实”评价赋作的标准,强调了大赋“体国”“义”的赋学标准,并以此赞美了班固《两都赋》,出现了对班固《两都赋》评价变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提出先秦两汉十家“辞赋之英杰”,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均入选十家。刘勰在“魏晋赋首”名单中,虽然将左思排除在外,其《才略》中评价左思,“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4]407,说明刘勰对京都赋成就是认可的,对于班固《两都赋》评价之高前所未有。范晔《后汉书》全文选录了《两都赋》,却只是提及了《二京赋》,没有收录文章,说明范晔对于《两都赋》比《二京赋》更为看重。
刘勰、范晔对班固《两都赋》的评价变高,而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的经典地位的确立,萧统《文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班固《两都赋》被排在张衡《二京赋》《南都赋》、左思《三都赋》之前,不是简单“以时代相次”的结果。萧统更多地出于对作品政治意义的考量,班固《两都赋序》既确立了臣子颂扬君主的基调,肯定大臣“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歌颂义务,又盛赞那些歌功颂德大赋的“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的价值,班固强调的臣子颂扬君主的义务与赋学理所应当的歌功颂德,正符合萧统《文选》编撰的皇家立场。郭英德先生总结了“文选”类总集文体顺序特点,其中提到“先源后流”“先公后私、先君主后臣下、先朝廷后地方”规律[12],这些原则是在《文选》及其之后产生的各类总集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来的,而萧统是这一文体排序规则的首倡者。
萧统《文选序》梳理赋体流变,强调了司马相如之后赋的快速发展,“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2]2,描述思路上着眼于题材的丰富多样。“邑居”“畋游”产生时间早,前者以张衡《西京赋》、司马相如《上林赋》为代表,后者以扬雄《长杨》《羽猎》为代表,分别对应赋正文中的第一类“京都”和第四类“畋猎”。《文选》赋类排序按照“先公后私、先君主后臣下原则”,前四类依次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均是与封建国家的政治、礼制密切相关的重大题材,这四类题材符合“先公后私”原则中的“公”。
从政教意义出发,“京都”放在首位既符合谢灵运、刘勰赋学分类的惯例,又符合萧统重视赋学突出君威的政治意义,班固《两都赋》主张臣子有歌颂皇家政绩的义务,认为臣子的职责之一是颂扬君主政绩。“郊祀”是与国家祭天地的礼制大典相关的,“耕籍”“畋猎”是反映皇族重要礼制活动的。就文学标准衡量,“京都”与“畋猎”两类艺术水平最高,因而选篇数量较多,“京都”选录了三位作家的八篇作品,“畋猎”选录了三位作家的五篇作品,而其余两类“郊祀”和“耕籍”各选录了一篇,但是在排序时,却把产生时间更早、艺术水平更高的“畋猎”类置于“郊祀”和“耕籍”之后。实际上魏晋以来文人赋学关注热点更多表现在“畋猎”,左思“作赋拟《子虚》”,扬雄《甘泉赋》、潘岳《籍田赋》作品题材偏冷僻,艺术性及产生时间上均不敌畋猎赋中司马相如等人赋作,然而,萧统优先考虑作品的政治意义,天子祭天仪式、皇帝对臣民农业上的籍田礼制,依照国事轻重,其意义要高于畋猎活动。 另外,畋猎带有娱乐性质,传统政治中多有批评。“畋猎”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就其政教标准而言,被扬雄批评“劝百讽一”“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对君主未有实际的影响力。因而,就赋作的政教意义,“京都”第一、“畋猎”排在“郊祀”“耕籍”之后,是萧统在综合衡量作品政治与艺术意义后的排名。
隋及唐代初期文选学初步形成,更加巩固了《两都赋》经典地位,陆续出现的《文选》各类注释专书,改变了《两都赋》未有注释的状况。“萧该有《文选音》, 曹宪、许淹皆有《文选音义》。而到了李善、公孙罗, 二者皆有《文选注》六十卷, 李善又有《文选辩惑》十卷, 公孙罗又有《文选音》十卷。”[13]除了这些文选学早期的注释类书籍,唐代中后期又出现了五臣注、《文选钞》《文选音决》等各类注释书籍,这结束了班固《两都赋》受到注释学冷落的状况,而拥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注释成果。
萧统作为储君,以编撰总集的方式、以赋类的选篇与排序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确立、引导与示范。与所选作品的口碑和艺术价值相比,萧统优先考虑的是作品题材政治文化上的教化意义,作家对皇权的态度是否具有示范性,在这些因素考量下,班固《两都赋》在萧统《文选》编撰中的经典地位得以突出,这一定位,摆脱了魏晋时期盛行的推崇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忽视班固《两都赋》的局面,把班固《两都赋》加入经典京都赋作的行列中来。萧统昭明太子的特殊身份与《文选》编选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之后兴起于隋唐时期的“文选学”,使得班固《两都赋》在《文选》中所确立的经典地位得以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