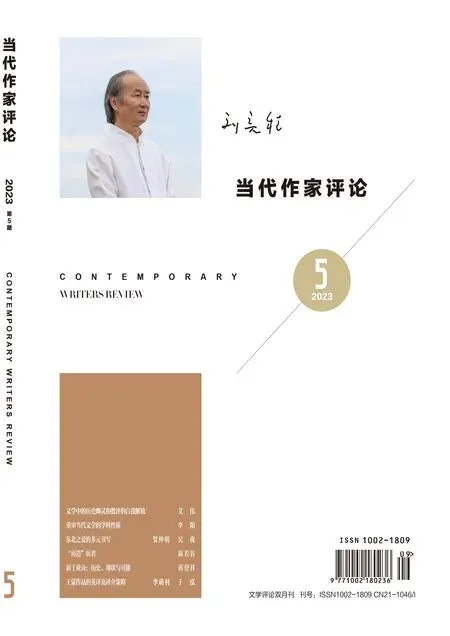城市之问与疫病之思
——论叶兆言“梅城”的意义建构
2023-12-19秦崇文刘久明
秦崇文 刘久明
城市叙事作为文学世界的重要命题,其伴随着城市转型和城市本身的发展变化而产生新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叙事由早期的“宏大叙事”向“传奇叙事”的反思现代性转向,让城市从叙事背景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叙事主角。以叶兆言的“梅城叙事”为契机,对这一历程进行爬梳,我们发现“梅城”成了对往昔的回放装置。“怪胎”“标本”“盆景”三位一体的“梅城”内核成为文学城市构镜中的叙事单位和可被解析的文化符号。作者将城市问题化,借“梅城瘟疫”对中国卫生现代性历程进行反思。传教士哈莫斯与“梅城”百姓之间的碰撞交流、共同抗疫过程成为中西医学、中西文化碰撞、磨合的缩影。在此意义上,“梅城抗疫”为近年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世界提供镜鉴,还为探究文学疾病叙事动力机制提供可能。作为叶兆言城市叙事的起点,“梅城”的意义建构为其实现“巴尔扎克式的野心”打开了新的诗学空间。他对“城市的本质”进行哲学追问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城市叙事提供了新视角。
一、城市叙事转型与“梅城”的诞生
叶兆言说:“我在小说中虚构一个城市的开始。这以前我的小说中有秦淮河这样的点,但这只是利用,只是到《花煞》时才突然决定虚构一个城市,它有了一种诞生的感觉……这以后的小说将多以这个城市——梅城为背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传统的继承,是一种巴尔扎克式的野心……建立王国的野心。”(1)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第22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梅城”被赋予了作者特殊的情感心理结构,叶兆言对自己的心理期待直接给予揭橥,其原型在新安江、兰江和富春江的交汇处。“梅城”成为源头活水,激发了作者“巴尔扎克式的野心”——极尽展现中国的社会风俗及整个社会的面貌。
若将新时期之后的城市叙事进行整体考察,不难发现,其中呈现出一种从“现代化叙事”到“世俗化叙事”再到“城市传奇构建”的演变趋势,出现了诸如朱文颖的《水姻缘》、铁凝的《哦,香雪》、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废都》、陆文夫的《围墙》、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王安忆的《长恨歌》、叶兆言的《花煞》等一系列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写实小说作品,从不同侧面书写了城市的“层累形象”。
其实,许多小说家都有自己的“一座城”,诸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卡夫卡的“城堡”、鲁迅的“S城”、沈从文的“凤凰城”、贾平凹的“废都”等。在《花煞》这部反映汉语小说文体变化的小说中,“梅城”作为叶兆言城市叙事的诞生之地,给予人们广阔的想象空间。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叶兆言将笔触转向南京,书写了另一个“梅城”。在《状元镜》《追月楼》《半边营》《十字铺》等“秦淮系列”作品中,作者将南京视为一种背景而存在,真实的南京被“虚化”,背离了历史主义的“城市叙事”,而“南京”是否成为宏大“历史叙事”并不是关注重点,叶兆言只想建构一个属于城市的“浪漫传奇”。在此意义上,“梅城传奇”成为对早期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拨、一种对历史心性的回应。
在以往的小说中,叶兆言通过塑造医生视角中的“非正常”人物,进而将社会医疗史、卫生现代性和百年文学之关系紧密联系起来。诸如《后羿》中具有神话色彩的智力发育不全的“羿”,《去影》中有性瘾症、偷窥狂的迟钦亭,《挽歌》中患癌症、肺结核的林黛、仲癸,《花影》中的植物人妤小姐、乃祥,《状元镜》中患性病的张二胡、沈三姐,《追月楼》中的搭背丁老先生,《半边营》中瘫痪的华太太,《夜来香》中患肺结核的蕙,《走进夜晚》中有性瘾症的马文,《走近赛珍珠》中癌症患者刘岳厚,《枣树的故事》中患尿血症的勇勇,《苏珊的微笑》中失眠的苏珊和瘫痪的张蔚芳,《玫瑰的岁月》中肺纤维化的臧丽花,《我们去找一盏灯》中“我”经常失眠还有抑郁症,《桃花源记》中的小芸小时候得过大脑炎导致一条腿有些跛。苏珊·桑塔格指出:“疾病并非隐喻……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5页,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在此意义上,苏珊关于隐喻的指涉为我们探究“梅城”的诗性空间提供文化层面上的深度思考。
从“梅城”开始,叶兆言将城市叙事的目光转向了城市本身,希望构建一个个“城市传奇”,让城市从叙事背景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叙事的主角,进而对“城市的本质”进行解答。城市是人类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后天形成的人文环境,符合人性发展是城市的本质基础,满足人类需要是城市本质的核心,环境则是城市本质的基本载体。城市的产生、发展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叶兆言突破以往对城市进行宏大叙事的桎梏,强化城市在现实关系中的对话张力,让“梅城”成为历史价值的当代链接。“梅城瘟疫”将卫生现代性“问题化”,构成“梅城”意义建构的重要内容。
叶兆言指出:“梅城是一座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别墅区仿佛是这座小城之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仿佛是人身上长在危险部位的一个肿瘤,惹不起碰不得。”(3)叶兆言:《花煞》,第308、2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类似医学语言增添了作家对“梅城”的反思力度,“梅城”的现代性历程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悲剧色彩。小说人物哈莫斯成为叶兆言的代言人,“由于靠想象写文章给哈莫斯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总是情不自禁地在《梅城的传奇》中,胡乱塞进一些他的私货”,(4)叶兆言:《花煞》,第308、2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这些“私货”正是叶兆言想深入探究的。他将作家创作的主体性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进行了融合,坚持所谓“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须怎样的手腕”。(5)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第3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在疾病叙事思想层面,一般情况是小说用疾病和死亡作为工具去揭示人物的心理发展,进而构建故事情节。与其他作品所描写“身体”之病不同的是,在“梅城”故事之中,叶兆言将目光投射到了历史的纵深之处,叙述视角从个体抗“病”转移到了宏大历史场面中的集体抗“疫”上来。
二、“怪胎”“标本”“盆景”:“梅城”的意义阐释之维
叶兆言说:“我虚构了一个叫梅城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中西文化大碰撞产生的结晶。它是一个泡在酒精瓶里的怪胎,是一个被钉子戳在墙上正逐渐风干的标本,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家辛苦培育出来的盆景。”(6)叶兆言:《花煞》,第357、309、311-312、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作者对历史发展的片段性与延续性做出象征性描绘,这里的“怪胎”“标本”“盆景”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三个维度:“怪胎”象征其杂糅性、丰富性、糟粕性;“标本”象征其价值与历史底蕴;而“盆景”则象征其可塑性、现代性和反思性。在此种意义上,“梅城”不仅仅是江南的一个城市,而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状态的缩影。为此,在医疗史研究中展开“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还可能推动中国这一问题研究取得突破。当然,这也拓展了“梅城”的意义阐释边界。
在小说《花煞》中,作者对“梅城”鼠疫进行了深描,其故事时间被定位在20世纪上半叶。起初,人们并不认为街上出现的死老鼠和人们发烧有着某种必然联系,“人们相信发高烧只是因为触怒了神灵,因此,每当鼠疫流行刚有预兆的时候,家家便在神龛上供上香,而且在每天天亮前,噼里啪啦地在房间大放爆竹。从发现街上的第一只死老鼠开始,直到城市里埋葬了死去的最后一位病人,这种仪式始终被大家顽固不化地执行着”。(7)叶兆言:《花煞》,第357、309、311-312、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这种由来已久的仪式反映了民众对疾病、对身体乃至对宇宙的认知。从生物学视角看,这种企图通过“传统仪式”达到治疗结果,无疑是无科学依据的迷信行为,也无法准确地衡量其具体的确实治疗作用。人们至多从“心理疗法”泛泛地解释它的存在。第二年,“顽固不化”的态度出现转变。鼠疫流行时间的快速性、范围的广泛性,引起人们对鼠疫的重新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社会对鼠疫的认知、预防及应对策略的改变。
关于如何抗击鼠疫,在光绪年间就有相关的医著中出现过抗疫之法,并涉及近现代卫生概念。清代嘉定人余伯陶在《鼠疫抉微》中指出:“避之之法,当无事时,庭堂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风黑湿处,切勿居住,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不可众人拥杂一处,反易致病。”(8)余伯陶:《鼠疫抉微》,第951页。《鼠疫抉微》为鼠疫专著,不分卷,刊于1910年。此段话结合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地气及郁蒸过程的顾忌以及西方对起居环境卫生的特别重视。小说中有类似的细节:“可以采取在家中隔离治疗的办法,但是重要的前提是一旦发现病人,就必须立刻报告……人们不再拒绝医疗队来把病人拖走……活着的人便变得越来越理智……无数的臭虫被消灭了,街道上墙角里积水的坑被填平,所有的粪坑都加了盖子……”(9)叶兆言:《花煞》,第357、309、311-312、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与西方工业化带来的城市水污染及环境污染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中国还处于“工业启蒙”时期,“卫生”概念更多指向了“日常生活”。
围绕鼠疫的对策、防疫措施及治疗方法,从哈莫斯在抗疫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看出,抗疫在中西文化认知层面上的差异。强制隔离的防疫措施难以让民众接受,早期中国的避疫思想和经验,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即本能的躲避与医学上对瘟疫传染的阐明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并且也有违“患难与共”的传统道德。当然,作家以一个外国人哈莫斯的经验表明,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在“抗疫”这个层面上,达成了“和解”——居家隔离,发现后立刻汇报,并将其经验进行推广:“很快,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搭起了男女浴室……任何人只要一发现有发烧的症状,便主动地送往隔离处,人死了立刻挖坑深埋……”(10)叶兆言:《花煞》,第357、309、311-312、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叶兆言对“梅城”鼠疫进行深描,揭示了鼠疫开始时间、发病时候的症状、人们面对鼠疫的各种心态、抗击鼠疫的一些具体措施、抗疫经验推广、抗疫结果等。“梅城”抗疫很大程度融合了世界各大瘟疫的文化历史语境,作者对其进行了在地化、整合化处理。从更宽泛意义上看,作者不仅以小说家身份书写鼠疫,同时以人类学家田野考察视角对此次鼠疫进行纪实,更以一位医者如何抗疫的视角看待此次抗疫行动。鼠疫的医学解释是:“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腺鼠疫是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身上附着的跳蚤等通过吸食人的血液,将鼠疫杆菌传入人的体内而引发的疾病。而肺鼠疫通过飞沫也能传染。”(11)〔日本〕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第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作者在小说中对鼠疫的具体描写符合医学意义上对鼠疫的概念界定。
显然,“梅城”抗疫经验与中国近代卫生制度的形成有着紧密联系。近代中国的卫生制度化是在对19世纪末广东和香港的腺鼠疫流行和20世纪初东北、山西的肺鼠疫流行的应对过程中,摸索着逐步展开的。在近代瘟疫中,政府在鼠疫的防治上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称道的举措,最终较好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进而促进了现代国家公共卫生和防疫机制的初步建立。当时,民众对西方人引以为傲的西医并不接受,对其疗效也不相信,而西医也似乎找不出中医医疗系统对抗鼠疫的优点。在应对“梅城”鼠疫的策略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持久对立与冲突。尽管如此,各方还是对此做出积极反应,在这次抗疫行动中达成一些抗疫共识,诸如接受哈莫斯的抗疫经验,医疗队允许进行一次送瘟神运动等等。在叶兆言的小说中,历史事件不仅仅作为一个叙事框架而存在,而且更作为反思的对象被抽取出来并给予人性思考。
小说《花煞》中,“梅城”的故事时间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达半个多世纪,“梅城”成为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投射,“梅城”的抗疫过程也成为中国卫生现代性进程的缩影,同时,这也构成了小说的隐性叙事线索。而故事的显性线索则以“梅城”教案引出洋人与华人、教民与百姓之间的矛盾,以官府缉捕斩首带头分子情节结束,并于结尾处铺陈了一个“留种”的情节,由此引出胡大少的两个遗腹子胡天、胡地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虔诚的浦鲁修教士,他以虔诚的信仰感动了胡天手下对洋人洋教恨之入骨的“匪徒”。小说中传教士哈莫斯的《梅城传奇》记录了关于中国某个城市的纪实故事,他还在中国遇到自己的爱情,逐渐被中华文明所征服,最后定居“梅城”,和胡天胡地打交道,和鼠疫奋战,最终成为一个“中国人”。这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其中旧家族、小官吏、市民、土匪以及外国传教士都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五线谱中的特色音符,叶兆言通过这些时代浪潮中一线人物的命运及切身感受,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小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困境。
哈莫斯作为一种符号化存在,在“梅城”抗疫过程中扮演了西医传教士的角色。在西医传教士的观念中,耶稣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神迹是通过对生物性疾病的治愈而显现出来。“西医”与“信教”这两种神迹同时出现在病人头脑中时,很容易发生混淆和裂变,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宗教与治病的同步性,病人常常混淆生物体和精神体所显示出来的真实作用,信教与信医之间即取决于直观表现而又无法判然二分,这时候病人往往会直面医疗效果而决定信教和不信教之间的取舍。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信仰表现出来的内在状态在性格上是一时,拥有特殊的所谓“无责任性”。二是医疗效果的明显性常常掩盖了其作为宗教神迹注脚的工具性作用,这时病人就会淡化对精神本质的认知兴趣而对药物疗效的效果性产生好感。
中国文学疫病叙事有着自己所遵循的系统,即人们逐步建立起了一种“身体化”的评价体系。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中,传统中医学成为“落后”“迷信”部分的隐喻符号。中西医之间的竞争与共存使得早期的中医处于不利位置,就算力挺中医的章太炎,也不留情地质疑传统医学的一些核心观念:“然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12)章太炎:《论中医剥复案与吴检斋书》(1926),《章太炎全集》第8册,第3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这也就不难理解鲁迅发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感慨。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土疆界被频繁侵害。“身体的病不只来自于肉体疾病,还来自于封建权力等对身体的压迫。”(13)王佳明:《中国新文学中沉重的身体能指》,《艺术广角》2023年第3期。“身体”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政客、现代知识精英、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知识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损而复原再造的历程,令民众痛楚地感受着被凌辱的命运,想象着自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污辱、歧视和践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号。民众容易把精神疾病用身体化的形式加以表述,对此,叶兆言说,之所以“摄取异域的营养”,则是为了“挖掘中国的魂灵”。在对卫生现代性进行钩沉时,叶兆言将目光投射在历史的区隔、片段性与延续性上,以反思历史的方式思考中国问题,回应了鲁迅所言:“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14)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怪胎”“标本”“盆景”三位一体的多元内核架构,其阐释边界指向“梅城”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三、“梅城叙事”中的卫生现代性反思
叶兆言的本科毕业论文《〈围城〉内外》,老师称其“老是在外面转,就是不进‘城’”,(15)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第56、22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这为文学创作带来反思——如何才能“入城”?这其中关乎文学的系列问题。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文学的最初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们通过语言实践获得自我确证与精神救赎,这也是文学疾病叙事的最基本动力。直到“梅城”出现,这个问题似乎才有了答案。作者花了很长时间来构思这部小说,“我在小说中虚构一个城市的开始……它给我以领土的归宿感。这以后的小说将多以这个城市——梅城为背景”。(16)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第56、22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梅城”给予作者一种“入城”的感觉,一种归属感。透过“梅城”历史长镜头来反思当下的文学疫病书写,不仅仅是对珍贵的文学历史底片的回望,也为文学疾病与现代性研究带来启示。
20世纪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发表,成为现代精神医学的诞生标志。经历过病痛的人们通常会用隐喻性的话语来向自己或他人形容和诉说自己的经历,成为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无意识”。在疾病体验和道德含义方面,作家似乎更为敏感,他们通常用戏剧性的意象来表达疾病的意义。他们用虚构和自传记叙病痛对身体的影响,洞察疾病体验的方式,这是其他更为平实的表现形式无法比拟的。从社会建构论来讲,疾病成为一种天谴、一种诅咒,乃至一种道德审判。
21世纪后,我们惊奇地发现,以前单纯的诊所治疗或医院治疗,如今已形成跨界之势,诸如艺术治疗、故事治疗、叙事治疗等等。以“治疗的文学”角度来看,作家的“弃医从文”或“亦医亦文”或“以文为医”或“疫病叙事”现象都成为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表征。“梅城”成为叶兆言疫病叙事的标志性宣言,“梅城”抗疫的人类学深描也预示着作者从身体疾病叙事向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创作倾向转变。在小说中,哈莫斯最后终于找到了有效控制百姓的“办法”,这更是一场中西文化碰撞之后的“和解”:
哈莫斯相信许多宗教仪式一定有它卫生上的根源,当鼠疫在这个绝望了的城市处于僵持徘徊阶段时,他说服了特别医疗小组允许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次游行被称为送瘟神运动……整个街道都充满了硫黄气味,哈莫斯相信,这些弥漫在空气中的烟雾起着杀菌消毒的作用。不过这还不够,哈莫斯让人把发了霉的含毒盐渍和硫黄合制成熏蒸菌类的烟雾剂,发放到各家,在供着神龛的房间,当作香点上,让刺鼻的烟雾一天到晚弥漫在房间里。(17)叶兆言:《花煞》,第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送瘟神运动”及每户家庭“供着神龛”似乎是一种迷信或是对死亡的恐惧,若要深入理解其中的原因,那么其中暗藏着传统医学所必须处理的课题。在传教士哈莫斯看来,中国人的疾病观是混乱而无序的,并没有建立起诸如基督教那样的道德秩序。因此,身体患病实际上暗示着一些风俗习惯的低下和丑陋,这些陋习影响着民众的生命状态,首先只有灵魂得到救赎,身体疾病才能真正得到治愈而重获新生。这种源于西方中世纪的理念认为:疾病“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疫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借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18)〔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第5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我们必须依赖医疗人类学或宗教研究提供的分析架构去认知迷信、宗教、仪式与医疗之间的微妙关系。“科学—迷信”的二元思维无疑会将这方面的研究空间严重地压缩。撇开迷信与科学的对立,我们观察仪式过程中的神衹、巫师、家属、邻居等,分析治疗场所、时间安排的意义、所用器具、符号、语言所指涉等。这些分析所透露的信息,正是用来了解身体疾病观的重要资料。在此意义上,我们得依赖医疗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然,从小说中透露出叶兆言相对保守主义的认知倾向。
“梅城”的“污染”与“防治”,从社会性、文化性层面传递出作者反思现代性的用力点。道格拉斯指出:“社会生活中的污染观念在两个层次上发生作用,一个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另一个是表达性的。”(19)〔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第3页,黄建波、刘博赟、卢忱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她将肮脏界定为失序,从而将洁净与肮脏提升到社会性、文化性层面进行探讨,并对詹姆斯·弗雷泽古今人类心性割裂的观点进行了清算,从而强化了人类心性一致的理念,为文化重建提供理论支持。从文化价值系统来看,“现代性”意味着两种核心价值的出现,第一是“工具理性”(指终极关怀与理性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成为社会行动(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第二是个人权利(正当性的最终根据)观念的兴起。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互相结合构成社会契约,最终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并与现代国家基础的现代认同一起,共同构成现代价值系统。(20)见金观涛:《历史的巨镜》,第9-1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花煞》所传递的现代国家文化价值理念,通过“梅城抗疫”表达了出来。
叶兆言在重读罗素的《中国问题》时指出:“在二十世纪,东方想摆脱西方的影响绝无可能,然而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服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问题的发现,和问题的解决,几乎同样重要。”(21)叶兆言:《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第20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很显然,作者想借“疫病”描写揭示中国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答案,也体现了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叶兆言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疫病”问题,在时间上则贯穿了整个文学发展史。将“梅城”抗疫纳入医学社会史、卫生现代性和文学系统中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其呈现出既传统又现代的艺术张力,“梅城”的意义阐释边界与作家的个人经验、家国命运和民族精神紧密相连,“梅城抗疫”为深入研究中国卫生现代性、文学疾病叙事的内在动力机制与精神向度提供可能。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梅城”事件,它是对人类难以摆脱的疫病纠缠的集体命运的叙事。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到1918的“世纪大瘟疫”,似乎都在对人类发出“警告”:如今,人类正面临全球危机。所谓“人”,其内涵包括两点:一是从“动物”进化的,二是从动物“进化”的。尽管现代性的文学观念呼吁“文学是人学”的崇高理念,但我们不能对文学本身的“人学”内涵加以阉割或选择性遗忘。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家园,对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叶兆言在小说中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失恋的哈莫斯也需要通过写作,医治自己心灵上所受的伤害”。(22)叶兆言:《花煞》,第304、281、283-2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由此,故事主人公哈莫斯与小说作者叶兆言构成一种互文关系,从侧面回答了“写小说永远是个流动的过程,这不可捉摸的过程溶化了小说家的生命状态”,(23)叶兆言:《〈枣树的故事〉序》,《叶兆言绝妙小品文》,第405页,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同时,这也暗示了文学的治疗功能和精神指向。
余 论
叶兆言以“梅城”为起点的城市叙事,在对宏大叙事进行反拨的同时,以一种“问题化”的方式将“城市的本质”纳入现代性系统进行考察,并以此对现代性及现代性本身进行深刻反思。其中,“巴尔扎克式的野心”为叶兆言的“王国”提供了一种目标导向。以“梅城”构建为起点,去探索一种属于自己的“城市性表述”,发掘城市之于人的本质意义。
在叶兆言看来,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就算哈莫斯用了不少小说家的笔调,《梅城的传奇》仍然不失为一本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书”,(24)叶兆言:《花煞》,第304、281、283-2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它出自一个最终对中国文化完全入了迷的西方人手里……西方的入侵,原意是想把古老的中国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可结果却是适得其反”。(25)叶兆言:《花煞》,第304、281、283-2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作者以海德格尔“问题的形式结构”与伽达默尔存在论诠释学去透视中国近代卫生现代性历程,背后潜藏着作家的文化阐释立场与获取自我本质特征的阐释学处境。
当然,叶兆言的“梅城叙事”也有其局限性,如对个体生命关注时,难免落入“宿命论”结局,使故事缺乏深刻性;小说有意识地借助史料(如人名、地名等)以期构成互文关系,这种制造的“真实感”和“历史感”往往对故事情节构成弱化;刻意追求中西文化相结合,往往出现文化裂缝,使得故事变得较为刻板和混乱;尽管注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但忽视了其他表述方式,使得人物形象塑造较为单调;小说文本插入了过多作家对事件的评述内容,没能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创造性阅读机会。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疫病必将与人类始终共存,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近代中国发生的从“瘟疫”到“传染病”的术语转换,是由知识界到国家层面的“传染病”概念的接受史,这是一个疫病认知科学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场知识的嬗变可以说也是疫病现代性的体现。从地方病到文明疾病模式的演进,“梅城”事件所折射出的作家反思现代性创作倾向,叶兆言的“梅城”不仅仅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物等物质意义的空间呈现,更是地理空间、社会文化空间和情感心性结构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结构性存在,“梅城”的意义不仅存在于作者的创作过程之中,而且存在于读者阅读、理解、阐释的思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