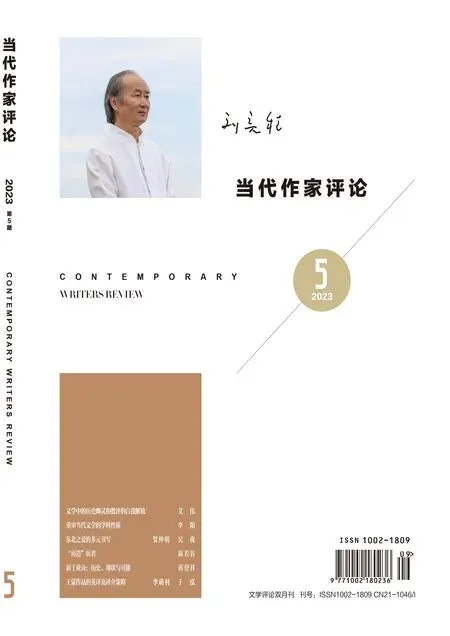刘亮程年谱(节选)
2023-12-19喻雪玲
喻雪玲
1974年,12岁
2月,随着母亲改嫁,刘亮程一家离开了生活12年之久的皇渠村的地窝子。伴随刘亮程整个童年的地窝子生活,留给其深刻印象。他在《老皇渠村的地窝子》中写道:
在老皇渠村的那几年,我们似乎生活在地底下。半夜很静时,地上的脚步声停息,能听见土里有一些东西在动。辨不清是树根在往前伸,还是虫子在地下说话。一只老鼠打洞,有一次打到地窝子里。那个洞在半墙上。我们一觉醒来,墙上多了拳头大一个窟窿。地上没土,我们知道是从外面挖进来的。也许老鼠在地下听到了我们的说话声,便朝这边挖掘过来,老鼠知道有人处便有粮食。或许老鼠想建一个粮仓,洞挖得更深更隐秘些,没想到和我们的地窝子打通了。
一到深夜地下的声音便窸窸窣窣,似有似无。尤其半夜里一个人突然觉醒,那些响动无声地压盖过来,像是自己脑子里的声音,又像在土里。那些挖洞的小虫子,小心翼翼,刨一阵土停下来听听动静。这块土地里许多动物在挖洞,小虫子会在地下很灵敏地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我们家是这块地下最大的虫子,我们的说话声、哭喊声、锅碗水桶的碰敲声,或许使许多挖向这里的洞穴改变了方向,也使一些总爱与人共居的小生命闻声找到了这里。(1)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23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书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后父的马车拉着刘亮程母亲和5个孩子,顺着玛纳斯河下游驶向太平渠村。太平渠村,即《一个人的村庄》中黄沙梁的原型。从皇渠村搬家到太平渠村的这段路,后来被刘亮程写进《两个村子》:
也是一个早春,来接我们的后父赶一辆大马车,装上我们一家人和全部家当,顺着玛纳斯河西岸向北走。在摇摇晃晃的马车上,我们一直看着河湾里父亲和奶奶的坟渐渐远去、消失,我们生活了许多个年头的皇渠村一点点地隐没在荒野尽头。一路上经过了三两个村子。有村子的地方河便出现一次,也那样绕一个弯,又不见了。
从半下午,到天黑,我们再没看见河,也没听见水声,以为远离了河。后父坐在前面只顾赶车,我们和他生得很,一句话不说。离开一个村子半天了,还看不见另一个村子。后父说前面不远就到了。我们已经不相信前面还会有村子,除了荒滩、荒滩尽头的沙漠,再啥都看不见。(2)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55-356、285、363、192、192、199页。
刘亮程一家开始了在太平渠村的生活。太平渠村整体呈镰刀形状,镰刀把这一块靠近玛纳斯河,一条路两边住着刘亮程后父家等一些老户。路在北边朝左边的沙沟沿撇过去,那里住着后来新搬来的河南人。关于此,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后来一些新来的人家在沙沟沿盖了一溜矮房子,村子的模样便变成一把镰刀状。”(3)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55-356、285、363、192、192、199页。刘亮程后父家的院子,是一个传统的院落。院子由篱笆墙围起来,共有三间房,里套外两间是住房,另有一间是库房。房前有菜地,屋边种着树。后父养着两只羊、一头牛,有一辆牛车,还有几只鸡、一条狗。刘亮程用文字记下这个院子:“那时家家户户有一个大院子,用土墙或篱笆围着。门前是菜地,屋后是树和圈棚,也都高高低低围拢着。”(4)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55-356、285、363、192、192、199页。
春天,刘亮程母亲跟着太平渠村的人一起挖渠、打坝,在大田干活。后父在马号喂马、赶车。每天黄昏收工回来,母亲忙着做晚饭,后父带着刘亮程以及大哥喂牛羊。关于后父,刘亮程写道:
后父早年曾在村里当过一阵小组长,我听有人来找后父帮忙时,还尊敬地叫他方组长,更多时候大家叫他方老二。(5)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55-356、285、363、192、192、199页。
一年后,我才能勉强地叫出父亲。父亲一生气就嘟嚷个不停。我们经常惹他生气。他说东,我们朝西。有一段时间我们故意和他对着干,他生了气跟母亲嘟囔,母亲因此也生气。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有过一段很不愉快的日子。后来我们渐渐长大懂事,父亲也渐渐地老了。(6)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55-356、285、363、192、192、199页。
9月,刘亮程开始在新胜大队上五年级,学校离家七公里。刘亮程家搬家到太平渠村(集体化时期叫新胜下二队),是新胜大队最远的一个村子。刘亮程每天吃完早饭,往书包装两片烤馍馍,连走带跑40多分钟到学校。路上,刘亮程与哥哥,后来与弟弟以及同村的十几个孩子每天一起上下学。上学途中要路过一个碱滩和坟地,路边长着浓密的芦苇、碱蒿,草丛中有很多早年留下的旧坟。关于这段上学之路,刘亮程在《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中写道:
再后来,我们家搬到太平渠村,属于新胜大队了,依旧在玛纳斯河边上,只是朝北迁徙了几十公里,更加荒凉了。我在那个学校跟着上五年级,大队离我们村七公里,同村的十几个孩子,每天早出晚归,步行上下学,路边也有坟,孤孤的,没在野蒿草中。有时独自路过,有意不去看,但总觉得那里有眼睛看过来,脊背生凉。(7)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4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本文所引该书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中午上完课,刘亮程从书包拿出两片馍馍当午饭。吃的时候,还都低着头,因为好多同学没有带馍馍。更多时候,中午还没到,馍馍已经吃完,整个下午都得饿着肚子。刘亮程手工缝制的书包里,还常装着火柴,假如路上能抓到鱼,就点堆柴火,用红柳枝穿上鱼烤着吃。实在饿得不行,就钻到旁边苞米地啃两个青苞谷。饥饿,在那时是常有的事情。童年的饥饿感,一直蔓延在刘亮程之后的创作中,他曾多次写到饥饿:
那些年月我们一直都没有积蓄下足够的粮食。贫穷太漫长了。(8)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55-356、285、363、192、192、199页。
许多年后的一个早春。午后,树还没长出叶子。我们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白面在一个月前就吃完了。苞谷面也余下不多,下午饭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坐好一会儿,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9)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217、205-206、243、12页。
有一年我们储备的冬粮不足,连麸皮都不敢喂牲口,留着缺粮时人调剂着吃。冬天蚂蚁出来过五次。每次母亲只抓一小撮麸皮撒在洞口。最后一次,母亲再舍不得把麸皮给蚂蚁吃。家里仅剩的半麻袋细粮被父亲扎死袋口,留作春天下地干活时吃。我们整日煮洋芋疙瘩充饥。那一次,蚂蚁从天亮出洞,有上百只,绕着墙根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到天快黑时,拖着几小片洋芋皮进洞去了。(10)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217、205-206、243、12页。
还以他者视角描写与饥饿相关的场景:
那年春天,整个荒野没冒一星点绿,风刮到村里突然停住。一户人家吃光粮食,面袋抖了三遍,灶上空沸的半锅水,浮着几片枯叶。七八个人,面朝东坐在院子,一口一口喝风和空气。不远的荒野中,一窝老鼠躲在阴深洞穴,分食最后的麦粒。它们终于熬过长冬,一个个皮包骨头。吃完最后几粒麦子,它们便要倾穴而出,遍野里寻找吃食。落到地上没埋住的草籽、没有落地的草籽、鸟吃剩的草籽,都是老鼠的食物。(11)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217、205-206、243、12页。
在2000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村庄》中,一篇文章的名字直接叫作《永远欠一顿饭》,他在其中谈道:
现在我还不知道那顿没吃饱的晚饭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多大影响。人是不可以敷衍自己的。尤其是吃饭,这顿没吃饱就是没吃饱,不可能下一顿多吃点就能补偿。没吃饱的这顿饭将作为一种欠缺空在一生里,命运迟早会抓住这个薄弱环节击败我。(12)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217、205-206、243、12页。
这些书写饥饿的文字说明,留存于刘亮程记忆中的饥饿感正如“没吃饱的这顿饭将作为一种欠缺空在一生里”,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精神诱因。
1975年,13岁
1月,冬闲,后父白天在马号做事,有时给村里赶大车,有时赶自家的牛车进沙漠拉柴。一到晚上,因后父会说书,家里就聚来很多人听他说《三国演义》《杨家将》《薛仁贵征西》。说书时,后父坐在自家土炕上,炕中间的小桌子上点一盏煤油灯。大人们坐在炕上,孩子们搬个土块坐在地上。刘亮程大哥说,自从他们搬到太平渠村,每年冬天都能听到后父说书。关于后父说书,刘亮程在《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中写道:
小时候,我的后父是个说书人。我们住的那个偏僻村庄,只有一个破广播,有时响有时不响,收音机也不是每家都有。我记得一到晚上,村里许多人就聚集到我们家,大人们坐在炕上,炕中间有个小炕桌,炕桌上放着茶碗、烟,我父亲坐在离油灯最近的地方,光只能把他的脸照亮,其他人围着他,我们小孩搬个土块或者小木凳坐在炕下面,听我父亲一个人讲,讲《三国演义》《杨家将》《薛仁贵征西》。我父亲不怎么识字,他所讲的那些书,全是听别的说书人说了之后自己记住的,在我印象中,我父亲从来没有把《三国演义》或《杨家将》讲完过,他讲不完,他学的就是半部《三国演义》。(13)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32页。
后父在家说书,大家听得入迷,母亲也边听边做手里的活。关于此,刘亮程后来写道:“他会说书,讲故事,在那些冬天的长夜里,母亲在油灯旁纳鞋底,我们围坐在昏暗处,听父亲说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14)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35、133、167、18、29页。
6月,给羊和猪割草成了刘亮程的事。几乎每个周六周日他都赶牛车去割草,有时带着三弟四弟。村里割草有规定,要等村庄北面老渠道附近的草长好,选日子统一收割,割草日子一般选在6月中旬。刘亮程会提前10天左右,去渠两边的深草处先割出一溜,就地晾晒。等村里通知可以割草,刘亮程赶着牛车过去直接拉干草回家。
有关割草的经验,后来在其文字中有所呈现:
我翻过沙梁,一头钻进密密麻麻的深草。草高过了头顶,我感到每一株草都能把我挡到一边,我只有一株草一株草地拨开它们。(15)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35、133、167、18、29页。
夜晚的田野虫声连片,各种各样的虫鸣交织在一起。“有一丈厚的虫声”。虫子多的年成父亲说这句话。“虫声薄得像一张纸。”虫子少的时候父亲又这样说。父亲能从连片的虫声中听出田野上有多少种虫子,哪种虫多了哪种少了。哪种虫一只不留地离开这片土地远远走了,再不回来。(16)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35、133、167、18、29页。
7月,“全县开展小麦万亩丰产运动”,(17)李德濂主编:《沙湾县志》,第36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中学生参与集体劳动。刘亮程所在的班级,由老师带队集体割麦子。收割麦子,是刘亮程早年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后来多次出现在他的创作当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诗歌时期,刘亮程就以“麦子”作为诗歌意象,创作出“生命是越摊越薄的麦垛/生命是一次解散/有人走过你的一生没有遇到你”(18)刘亮程:《晒晒黄沙梁的太阳》,第27页,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等诗句。
麦地太大。从一头几乎望不到另一头。割麦的人一人把一垄,不抬头地往前赶,一直割到天色渐晚,割到四周没有了镰声,抬起头,发现其他人早割完回去了,剩下他孤伶伶的一垄。他有点急了,弯下腰猛割几镰,又茫然地停住。地里没一个人。干没干完都没人管了。没人知道他没干完,也没人知道他干完了。(19)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35、133、167、18、29页。
这些文字生动呈现了少年刘亮程因力气不足常被落在后面的内心焦虑,记录下他有关收割麦子的深刻记忆。
冬天,放学回家,刘亮程常和邻居李庆贤结伴去套兔子。运气好的时候,刘亮程大清早可以背回来两三只兔子,一只兔子能卖八毛钱,可以用来补贴家用。更多时候,是空手而回。套兔子的经验,后来被刘亮程写进《野兔的路》中:
兔的路小心地绕过一些微小东西,一棵草、一截断木、一个土块就能让它弯曲。有时兔的路从挨得很近的两棵刺草间穿过,我只好绕过去。其实我无法看见野兔的生活,它们躲到这么远,就是害怕让人看见。一旦让人看见或许就没命了。或许我的到来已经惊跑了野兔。反正,一只野兔没碰到,却走到一片密麻麻的铃铛刺旁,打量了半天,根本无法过去。我蹲下身,看见野兔的路伸进刺丛,在那些刺条的根部绕来绕去不见了。(20)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35、133、167、18、29页。
1976年,14岁
4月,母亲除了上工干活挣工分,一化雪就开始在自家菜园栽种洋葱、大葱,撒萝卜种子。刘亮程记得,太平渠就他家种这些菜种子,村里人种菜时都到他家来买种子。刘亮程和几个兄弟帮忙挖菜园子、翻土、拾柴火、拔草、浇水等。母亲时常心疼他们岁数小,干的活太重。
7月,暑假中的一天,后父交代刘亮程给院子修一个院门。刘亮程带着弟弟妹妹挖土和泥,用现成的土块砌门墩,又从柴火堆中选用一些棍棒搭起门楼。他没有听从后父的嘱托去使用房顶上那几根粗直的大木料,最后修了一个不大的门,后父并不满意。关于这段修门的经历,刘亮程写道:
我十四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天早晨,父亲吩咐我修一个院门。他只告诉我木头在房顶上呢,让我拣好的用,便扛着锨头也不回地下地去了。
没想到修门这件事会这么早地落到我身上。那时的我,并不理解父亲的真正用意。父亲一直留着这个院门,并不是他没时间去修,也不是有意要偷懒。修门是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活儿,父亲把它留给了儿子,他要从儿子身上看到这个家族以后的兴衰和前景。
十四岁的我,怎么会领会这些呢?
我只觉得这活儿好玩。
我和了一堆泥,土块是现成的。动手砌门墩时,为院门的宽窄我还思量了一阵。那天家里好像只剩了我,门口的马路上也没有一个过路人。忽然感到我要独自完成一件事情,心里没底,却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忙的人。(21)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89-390、396页。
据刘亮程说,许多年后他回到太平渠村,这个门楼仍然在。那时他家房子的院墙已经倒塌,但他早年修的门楼还在,刘亮程在《修门》中写道:
它将成为一座荒野中的门。
进出的只有时间和风。(22)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389-390、396页。
9月,刘亮程升入初中二年级,尝试创作诗歌和童话,他的诗歌还被老师当作范文读给班里同学听。当时村里传读的几本没封皮的旧书传到刘亮程手中,他读后印象深刻,想着自己以后也要写一本从哪里翻开都可以阅读的书。多年后他才知道,其中一本没封皮的书原来叫《镜花缘》。关于这段读书经历,刘亮程在访谈中提到:
那时候我们村里还有几本内地逃荒来的人带来的古典小说,繁体字,我读到过一两本,都破得没头没尾。其中有一本,早没有了书名,只剩下书瓤子,我反复读了多遍,里面主人公的旅行奇遇让我萌生了写童话故事的冲动。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本书是《镜花缘》。(23)刘亮程、宋庄:《刘亮程谈枕边书》,《中华读书报》2020年9月2日。
冬天,后父叫刘亮程跟着村里人一起进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去拉柴。刘亮程半夜四点被叫醒起来吃饭,母亲早已为他装好热水和馍馍,他赶着牛车跟着村里人一起出发。牛车很慢,大概要走五六个小时,天快亮时才能走到沙漠里,到了砍柴的地方,整个人早已冻透。刘亮程先把牛车卸下,拴好牛,给牛喂些带来的草料。再就近拾一堆柴火点火取暖,取出冻硬的馍馍和铁皮军用水壶,将水壶直接扔在火中烧热,再找一根柴火棍,穿起馍馍在火上烤,就着热水吃点儿馍馍。然后开始砍梭梭柴,再一根一根扛到车上。因年少力气有限,刘亮程砍柴的速度慢。村里人装满一车,他才能装一半,装多也拉不动。他看同来拉柴的人装好车准备往回走时,就赶紧再拾一些,拿绳子固定住,跟着村里人往回走。
关于进沙漠拉柴的经历,刘亮程在《寒风吹彻》中有论述:
牛车一走出村子,寒冷便从四面八方拥围而来,把我从家里带出的那点温暖搜刮得一干二净,浑身上下只剩下寒冷。
那个夜晚并不比其他夜晚更冷。
只是我一个人赶着牛车进沙漠。以往牛车一出村,就会听到远远近近的雪路上其他牛车的走动声,赶车人隐约的吆喝声。只要紧赶一阵路,便会追上一辆或好几辆去拉柴的牛车,一长串,缓行在铅灰色的冬夜里。那种夜晚天再冷也不觉得。因为寒风在吹好几个人,同村的、邻村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好几架牛车在这条夜路上抵挡着寒冷。
因寒冬进沙漠拉柴,刘亮程的一个膝盖被冻坏。关于这条冻伤的腿,他写道:
天亮后,牛车终于到达有柴火的地方。我的一条腿却被冻僵了,失去了感觉。我试探着用另一条腿跳下车,拄着一根柴火棒活动了一阵,又点了一堆火烤了一会儿,勉强可以行走了,腿上的一块骨头却生疼起来,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一种疼,像一根根针刺在骨头上又狠命往骨髓里钻——这种疼感一直延续到以后所有的冬天以及夏季里阴冷的日子。(24)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112-113、343、346页。
自这年起,刘亮程开始独自进沙漠拉柴火。每周拉一车梭梭柴,家里的柴垛开始垒起来。
1977年,15岁
刘亮程就读初中三年级,学习成绩突出。
暑假,家里篱笆院墙坏了,后父说要打段土墙。后父帮忙栽好打墙用的梯子、绑好椽子,扔几锨土便去干活了,剩下的交给刘亮程兄弟几个。刘亮程带着三弟、四弟用一整个上午,打出一堵歪扭的土墙。刘亮程在《一截土墙》中写到这段打墙经历:
我们从早晨开始打那截墙。那一年四弟十一岁,三弟十三岁,我十五岁。没等我们再长大些那段篱笆墙便不行了。根部的枝条朽了,到处是豁口和洞。几根木桩也不稳,一刮风前俯后仰,呜呜叫。那天早晨篱笆朝里倾斜,昨天下午还好端端,可能夜里风刮的。我们没听见风刮响屋檐和树叶。可能一小股贼风,刮斜篱笆便跑了。父亲打量了一阵,过去蹬了一脚,整段篱笆齐齐倒了。靠近篱笆的几行菜也压倒了。我们以为父亲跟风生气,都不吭声地走过去,想把篱笆扶起来,再栽几个桩,加固加固。父亲说,算了,打段土墙吧。(25)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112-113、343、346页。
我提夯,三弟四弟上土。一堵新墙就在那个上午缓慢费力地向上升起。我们第一次打墙,但经常看大人们打墙,所以不用父亲教就知道怎样往上移椽子,怎样把椽头用绳绑住,再用一个木棍把绳绞紧别牢实。我们劲太小,砸两下夯就得抱着夯把喘三口气。我们担心自己劲小,夯不结实,所以每一处都多夯几次,结果这堵墙打得过于结实,以至多少年后其他院墙早倒塌了,这堵墙还好端端站着,墙体被一场一场的风刮磨得光光溜溜,像岩石一样。只是墙中间那个窟窿,比以前大多了,能钻过一条狗。(26)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112-113、343、346页。
这段土墙,是刘亮程打起的第一道墙。墙上的一个洞痕,令他记忆深刻。墙快打到顶时,一只小斧头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四弟在打好的墙上画了一个圈,刘亮程和三弟一锨一锨往里挖,果然看见一把小斧头躺在土墙里。这个挖出来的小洞,以后被风越吹越大。刘亮程说,风刮过墙洞的声音也留在他后来的文字中。
太平渠村没有种西瓜,暑假中的一天,刘亮程一个人赶牛车到十公里外的沙门子买西瓜。到了瓜地,看瓜老头问刘亮程是谁家的孩子。刘亮程说是刘彪的儿子。老头说,他知道刘亮程的父亲,说刘父吹拉弹唱样样都会,文化程度高,还专门给刘亮程切一个西瓜吃。关于先父的才能,刘亮程在创作中谈道:
先父是传统的旧人,写一手好毛笔字,会吹拉弹唱,能号脉开医方,能颞骨治病。在甘肃老家时,先父是县城关小学副校长,拿国家工资,1961年携家带口逃饥荒到新疆,落魄到新疆沙漠边一个村庄。(27)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175、42、43页。
是年,刘亮程的三弟方如果刚上初中,开始写作。自此,刘亮程家兄弟三人都写作。关于此,刘亮程写道:
许多年前,我还上初中,我大哥已毕业务农,我三弟也在上初中,比我低两级。在那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我们兄弟三人开始写小说,一人写一部,都是长篇。我弟弟如果为写小说放弃了一年多学业,我大哥也不安生种地,一心扑在小说上。我也几乎为此荒废了学业。我们兄弟三个想通过写作找一条离开农村的光明大路。
可是,我们都没有把那部小说写完。或许我们根本无法完成它。三弟写得稍长点,完成了好几万字,我和大哥只写了开头和中间的一些片断。我记得那时大哥的文字已相当凝练,描述故事的能力也非同一般。我们三人中,最有文才的是三弟,思路开阔,行文无拘无束。我最差,几乎写不成几个完整的句子,却天天想着要写成一本书。结果,多少年后我真的写出了一本书。
我的两个兄弟却早早地搁笔了。
我的文章中有几个精彩句子,是三弟如果扔弃的文字中摘抄的,我觉得扔掉可惜。我的一些想法可能受大哥的影响。记得谁说过,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同时代的作家共同完成的。而我的文字确确实实是我们一家人共同完成的。我们一家八口人,竟有三口投入到文学写作中。即使我们最终写不成半本书,我想我们的精神也能感动万千文字。(28)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414页。
1978年,16岁
11月,刘亮程在沙湾农镇中学读高中一个多月后,收到石河子地区农业机械化学校(以下简称“石河子农机校”)的录取通知书。据刘亮程石河子农机校的同班同学孙建祥介绍,因石河子农业机械化学校刚组建起来,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故1978级学生开学时间推迟至11月13日至15日,录取通知书也晚到一个多月。关于这段上学历程,刘亮程写道:“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石河子农机学校,学了三年农业机械”。(29)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175、42、43页。
刘亮程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是和另一个来自地方的同学学习说兵团普通话(河南腔),这对他并不困难。之前在沙湾,村里有一半人是河南人,他平常已听惯他们说话,但他一直都说新疆土话(地方话)。
在农机校,刘亮程继续读诗、写诗。学校图书阅览室订阅有《诗刊》等诗歌类杂志,刘亮程后来一直跟进阅读。关于阅读诗歌,他曾写道:
我在那样的环境中写诗。每周来一次的邮递员是我最期盼的,我订阅的诗歌杂志,总是晚两个月到。我在三月的料峭寒风里,收到一月出版的《诗刊》,再把自己一个星期前写的信,交给邮递员捎走。至少半个月后,信才会送达,回复过来,一定是两个月后,天气都由寒转暖了。(30)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175、42、43页。
12月,寒假回家,帮家中拉柴火。一天,村里来了一辆汽车收购柴火,收购人一眼看上刘亮程家高高码起的柴垛。母亲要把家里那堆柴火卖了,刘亮程开始不愿意,认为那一根根的柴火,都是自己和家人辛辛苦苦从沙漠拉回家取暖的。尤其是那棵足有碗口粗的活梭梭,又长又直。最后,这堆柴火换来一百多元。柴火和柴垛,常出现在刘亮程的创作中:
早些时候太阳总是一大早就直直照到我们家东墙上,照到柴火和牛圈棚上,照到树根底下的层层落叶上。那柴垛永远是干燥的,圈棚上的草从来没有因潮湿而捂烂一棵,即使柴垛底子也都干干爽爽,第一缕曙光贴着地面平射过来,正好照着最底下那层老柴火。(31)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187、430、431页。
柴垛是家力的象征。有一大垛柴火的人家,必定有一头壮牲口、一辆好车、一把快头、一根又粗又长的刹车绳。当然,还有几个能干的人,这些好东西凑巧对在一起了就能成大事、出大景象。(32)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187、430、431页。
现在,我们再不会烧这些柴火了,把它当没用的东西乱扔在院子,却又舍不得送人或扔掉。我们想,或许哪一天没有煤了,没有暖气了,还要靠它烧饭取暖。只是到了那时我们已不懂得怎样烧它。劈柴的那把斧头几经搬家已扔得不见,家里已没有可以烧柴火的炉子。即便这样我们也没扔掉那些柴火,再搬一次家还会带上。它是家的一部分。那个墙根就应该码着柴火,那个院角垛着草,中间停着车,柱子上拴着牛和驴。在我们心中一个完整的家院就应该是这样的。许多个冬天,那些柴火埋在深雪里,尽管从没人去动,但我们知道那堆雪中埋着柴火,我们在心里需要它,它让我们放心地度过一个个寒冬。(33)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第187、430、431页。
在刘亮程看来,家正是由柴火和柴垛这样具体又实在的生活事物构成。在此基础上,家成为人精神的家园,带给人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