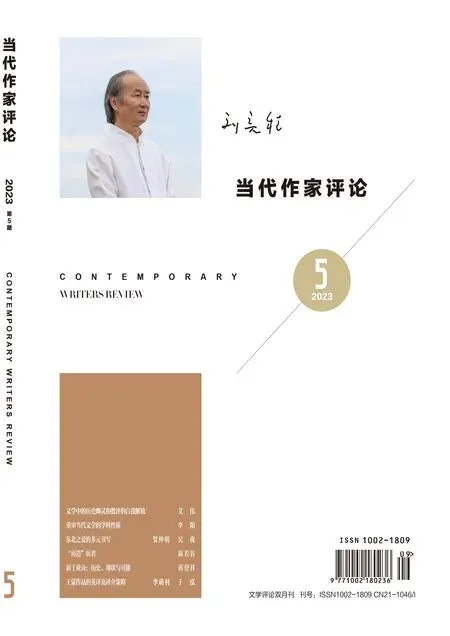王蒙作品的英译及译介策略
2023-12-19李萌羽
李萌羽 于 泓
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同时,王蒙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其作品被译为20余种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现有研究对王蒙作品的英译情况与译本的接受情况介绍较少,缺乏从翻译视角对译本质量的评价和对译者译介策略的探讨。本文将梳理王蒙作品的英译与接受情况,考察其作品译介面临的困境及译本采取的策略,并通过分析重要译者朱虹的译介实践,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在突破外译困境方面的出路。
一、王蒙作品的英译与译本的接受
王蒙作品的英译活动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纽约Praeger出版社和伦敦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社会主义国家作品集《苦果——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BitterHarvest:TheIntellectualRevoltbehindtheIronCurtain,1959),其中收入的唯一一篇中国作家的作品就是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见温奉桥、张波涛:《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第180页,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6。第二阶段为1980—1999年,《中国文学》于1980年第7期发表了《悠悠寸草心》等3篇王蒙小说,“熊猫丛书”于1983年推出王蒙小说集《蝴蝶及其他》(TheButterflyandOtherStories)。这些译本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锋,为英语世界读者打开了了解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扇窗,也激发了英语世界主动译介王蒙的热情。随着王蒙的创作进入“井喷期”,对其作品的英译日益活跃,国内译出和海外译入齐头并进。第二阶段出版、发表的英译作品共22部(篇),先后有20多位译者参与译介,有以戴乃迭(Gladys Young)、梅丹理(Denis Mair)、文棣(Wendy Larson)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译者,也有以朱虹为代表的中国译者。出版机构包括中国的出版社、英美商业性和学术性出版社。不同性质的出版机构与不同身份的译者组合,形成了多样的译介生产模式,共同构造了王蒙作品英译的多元图景。21世纪以降,为王蒙作品英译的第三阶段,共计出版译作11部,其中多数为中国译出,部分为上一阶段译本的再版,与王蒙充沛的创作力相比,王蒙作品的英译空间有待进一步开拓。
通过分析王蒙作品的英译历程,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
其一,译介体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译本多采用小说集形式。选材囊括了王蒙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蝴蝶》《夜的眼》等重要作品甚至拥有多个译本,王蒙十分倾心的微小说在梅丹理的《相见集》(TheStrainofMeeting:SelectedWorksofWangMengI,1989)中也得到了大量呈现。小说集的出版形式能够灵活捕捉并充分展现作家的创作风格与动向,较大限度满足读者对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渴求,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对王蒙形成虽不够深入但相对全面的了解。相较于译介成果丰硕的中短篇小说,其他体裁则鲜有译者涉足,收录在《雪球集》(Snowball:SelectedWorksofWangMengII,1989)中由Cathy Silber和Deirdre Huang合译的《活动变人形》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王蒙作品的英译长篇。众多长篇和其他体裁作品的译介空白亟待填补。
其二,译本注重呈现作家的文体创新。王蒙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东方意识流”手法,创作了一系列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意识流小说。这一时期涌现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选集多囊括了王蒙的意识流作品,以展现中国文坛焕然一新的气象。例如,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主编的选集《花与刺》(RosesandThorns,1984)便将《夜的眼》作为开篇之作,译者Donald A. Gibbs在译序中也特别谈到了小说对情节的摒弃、电影式的描写和内心独白等创新性叙事策略的运用;(2)Perry Link,Roses and Thorns: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1979-8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44.本文所引内容英译汉皆为笔者译,不另注。“熊猫丛书”推出的《蝴蝶及其他》收入了王蒙的意识流代表作《蝴蝶》,并以之作为题目;《1949—1989最佳中文小说》(BestChineseStories:1949—1989,1989)则收入了《风筝飘带》。此外,王蒙的部分创作谈也得到了译介,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创作主旨和文体创新。如王蒙写于1979年《关于“意识流”的通信》,经Michael S.Duke翻译,于1984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ModernChineseLiterature)上;《蝴蝶及其他》则收录了王蒙1980年的创作谈《我在寻找什么》,并将其作为选集的开篇。
其三,译材选择与时代需求关系密切。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中国渴望被世界了解,他国读者也对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充满好奇,因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尤为活跃。王蒙创作的深刻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剧变中的创伤、疑惧、反思、期待等复杂心理的作品,自然成了译介的热点。《蝴蝶及其他》的译序称,王蒙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中国当代文学从未呈现过的复杂性和深度,(3)Wang Meng,The Butterfly and Other Stories,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1983,p.7.该译本选取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理想信念受挫后的彷徨与反思,以及对中国社会的犀利洞察。《相见集》前言也指出,王蒙的作品“忠实、动人地反映了一代人猛烈的觉醒、跌跌撞撞的前行和理想的重唤”。(4)Wang Meng,The Strain of Meeting:Selected Works of Wang Meng I,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9,p.xii.王蒙远赴新疆的独特经历也受到了译者的关注,他对新疆充满温情的书写,揭开了中国广袤西部的神秘面纱,为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21世纪以来,中国在对外译介活动中更加注重文化“走出去”,对王蒙的外译越来越聚焦作家探讨中国文化思想的作品,如《中国人的思路》(TheChineseWayofThinking,2018)和《中国天机》(NewChina:AnInsider’sStory,2019)。近年来,英语世界对王蒙作品的译入有朱虹、刘海明合译的《王蒙自传》(WangMeng:ALife),2018年由Merwin Asia出版社出版。这部译作将作家于2006年至2008年分3卷出版的超千页自传压缩至350页,作家一生跌宕起伏的经历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成了译介重点。
通过考察海外学者对王蒙的研究情况和海外读者对译本的评价,可以看出王蒙作品译本在英语世界赢得了一定的关注,但受众囿于学者群体,大众读者的接受情况不够理想,与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在国内享有的声誉形成较大反差。英语世界对王蒙的研究是译本接受成效的重要体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与译介的热潮相伴相生,英美学者利用译本,对王蒙的创作手法和其作品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了视角新颖、方法多样的探索,反映出这一时期译本在学者群体中较好的接受成效。21世纪以来,译本在主流读书网站上的得分与评论情况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大众读者的态度。以美国最受欢迎的在线读书社区Goodreads为例,王蒙的条目下共列出40部作品,包括王蒙作品英译本、原作和其他语种译本,共计获得407次打分。其中,英译本的平均得分均在3分以上(满分为5分),有读者甚至给出满分,并有读者将其标记为“想读”。
作为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王蒙的创作彰显了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但就其作品英译情况而言,不仅远没有充分呈现其全貌,而且存在着一定的译介困境和挑战。该如何采取有效翻译策略改变现状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王蒙作品的译介困境与译介策略
王蒙作品的译介受制于作家自身的创作特质。王蒙的创作扎根本土,书写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动荡中的遭际,不为迎合大众的阅读趣味而刻意营造跌宕的情节,并且随着创作的深入,愈加注重对作品知识性、自由性、丰富性的追求。扎根本土的题材选择和不重故事营造的创作倾向对读者和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又要有较强的文学鉴赏能力。这些对王蒙的作品译介形成了挑战。王蒙鲜明的语言特色更为其作品的译介增添了难度。他的语言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特别是在90年代的“季节”系列长篇后,王蒙进入语言狂欢的创作状态,风格日益凸显。语言特色依附于源语思维与表达方式,无法在翻译中自然传递,读者能否在译文中得见作家文风,考验着译者文学再创作的功力,需要译者在持续、艰辛的探索中反复打磨译笔。然而,多数译者对王蒙的译介浅尝辄止,缺乏对王蒙的长期关注和对其语言特色的准确把握。译本中普遍存在的原作特质的减损,使读者低估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也难以就作家和作品形成深刻、统一的印象。
王蒙作品在进入英语世界时也面临着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普遍挑战。英美国家对翻译文学持明显的拒斥态度,翻译作品在图书出版总量中的占比较低且难以提升,这种拒斥与英语世界的文化心态有关。“当一种文化处在转型期,也就是当其正在扩张、需要更新或即将步入革命阶段时,会出现大量的翻译活动”,(5)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Blackwell Publishers,1993,p.10.而对于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文化来说,翻译的作用则不被强调,这使得中国文学的译入困难重重。最突出的挑战来自英语世界以读者为导向的出版文化。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曾提到,在美国,即使是知名作家,有时也需听从编辑基于对读者接受预判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甚至改变情节走向和故事结局。(6)见吴赟:《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白睿文访谈录》,《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常因陌生的社会语境和意识形态冲突使出版机构对读者能否接受心存疑虑,译作通常无法在不断适应读者口味的调整过程中完成。由于语言障碍和知识背景的缺乏,英语世界的读者大多需要依靠译者与出版机构对作品的择取。为引发阅读兴趣,译作常以跌宕的情节、新奇的故事为卖点,无形中破坏了原作的整体性与文学性,误导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英语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使得受众群体难以扩大。
译本能否突破作品特质与接受环境所形成的内外部双重困境,与译者采取的译介策略密不可分,其中,译材的择取和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方法是两个重要方面。王蒙的英译者在选材上侧重作家的文体创新,翻译上有“厚译”和“删减”两种倾向,使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以美国汉学家文棣翻译的《布礼——一部中国现代主义小说》(BolshevikSalute:AModernistChineseNovel,1989)为例,译者仅选取了中篇《布礼》,将其作为“首部英译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推介给读者。文棣采取了明显的“厚译”策略,为克服语言文化理解上的障碍,译者通过大量加入副文本,以文外加注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充实的背景信息,辅助读者领略作品全貌。文棣还结合自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为译本撰写了前言与后记,前言介绍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历程,着重阐述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布礼》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先驱之作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译文后附学术文章《中国知识分子与消极的自我界定》,进一步分析了《布礼》的现代主义技法、结构与主题,探讨了逻辑和情感作为支配人物对待世界的两种方式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语言在建构真实方面的可疑性。副文本的设置考虑到了不同类别读者的需求,前言和注释为大众读者提供了足够的背景知识,附文解读则是译者与同行学者或希望深入了解作品内涵的读者的对话。《布礼》译本忠实顺畅的风格和译介质量得到了肯定。王蒙亲自为译本作序,感谢文棣将这部“叙述内心体验历程的小说”译成英文,让读者“体验一下这独特的遭遇”。(7)Wang Meng,Bolshevik Salute:A Modernist Chinese Novel,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9,p.ix.汉学家傅静宜(Jeannette L.Faurot)盛赞文棣的翻译是“准确地反映了原作的风格与内容,对西方读者不熟悉的名字和术语进行了有益的注解,附文解读引人深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重要问题”。(8)Jeannette L. Faurot,Reviewed Work(s):Bolshevik Salute:A Modernist Chinese Novel by Wang Meng and Wendy Larso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Dec.,1991),p.178.
但《布礼》译本也受到了一些非议。《弗吉尼亚评论季刊》称《布礼》为一部“彻底的中国式小说”,认为其中陌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人物的观念习惯和直露的情感表达使读者深陷困惑,并特别指出将现代主义作为卖点并不成功,以西方现代主义的标准衡量,读者会认为这部作品乏味、浅显、缺乏创新性。(9)Hardy C. Wilcoxon,Jr.,The Ties that Bind,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Autumn 1991),p.761.《布礼》作为一部易与西方读者发生意识形态冲突的作品,无疑是个极具挑战的选题。译者以西方读者熟知的现代主义作为突破口,试图拉近读者与作品间的距离,但也特别在前言中说明小说所面临的两极分化的评价,既有人将其视为具有变革意义的现代主义实验之作,也有人将其视为只是时序错置的典型现实主义创作,提醒读者在阅读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但多数并不了解中国文学的读者会自然地动用以往的阅读经验,将作品视为对西方现代主义技法的模仿,难以将其置于中国当代文学环境中考察并体会其开拓性。评论中对译者的“厚译”风格也不乏贬抑。《科克斯书评》指出,文棣遵循了最糟糕的学术传统,通过大量注解,试图将小说拆解后重构,使读者难以真正体会王蒙在形式上的创新。(10)Kirkus Review,Bolshevik Salute,引自https://www.kirkusreviews.com/book-reviews/a/wang-meng-2/bolshevik-salute/。“厚译”注重作品的学术价值,拒绝删减、绕行,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作品的文化内容,为海外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却并非再现原作文学审美性的最佳途径,过于侧重内容,有时甚至亦步亦趋的翻译风格,难免造成文字的滞重和对原作形式的损耗,繁复的注解则会不断打乱读者的阅读节奏,加重理解负担,进而影响整体的阅读体验。
由戴乃迭等9位译者合译的《蝴蝶及其他》是另一类译介策略的代表。译本囊括了王蒙的成名作和重要的意识流中短篇,选材丰富且具有代表性,能够全面地向英语世界读者展现作家的创作风貌,较之于专注某一特定作品的译本来说更易吸引读者。译本采用了“删减”的翻译策略,为保证译文的整体表达效果,译者省略了原文中大量的修饰、铺陈、排比;删除了无益于直接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容,使故事更紧凑,脉络更清晰;对带有政治和地域元素的内容进行了删减或解释性翻译;对文化负载信息量大的段落进行了编译。有读者评价该译本为了解中国提供了“非常有趣且独特的视角”,并称赞王蒙的写作才华,特别是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能力要远超中国同时代作家。(11)Joseph L.Reid,Review on The Butterfly and Other Stories,引自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238277#CommunityReviews。由此可见,译本在选材和接受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初期,帮读者剔除了阅读障碍的译本,甚至是编译、节译本,往往收效更佳,作为较早走出国门的中国当代小说译本,《蝴蝶及其他》满足了短期内向英语世界宣传推介中国当代文学的需求。
然而,此种翻译策略终究是译者采取的权宜之计,不可避免地以损害原作叙事风格和文化旨趣为代价,使译文无法成为在文学审美价值上足以与原作匹敌的作品,使读者难以走近、理解王蒙。以该译本中最重要的《蝴蝶》为例,译者戴乃迭为突出小说的故事性,删除了她认为可有可无的内容,特别是人物较为发散的思考与回忆。例如,张思远在去往山村的途中突然想起过去视察时路遇灰兔的经历,从灰兔闯入车灯的光柱,在疾驰的车前惊慌奔命,到最终逃过一劫,小说对这一插入式回忆进行了细致描写。灰兔遇险时的仓皇和得救时的侥幸,亦如张思远在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中深刻体验过的惊惧与如释重负一般。灰兔的细节作为重要的隐喻,为中文读者津津乐道,而译本却将此段删去,虽然内容的衔接依然顺畅,却尽失原文在人物情感递进方面的巧思,使读者难以深入人物内心。对故事性的追求难免以忽视文学细节为代价,除有意的删减外,译文还存在几处明显的错译。译者对原作语言风格的处理也显得谨小慎微,考虑到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译文刻意淡化了原作充满情感起伏的语言特色。《蝴蝶及其他》的“删减”策略折损了原作可贵的审美特质,违背了王蒙“不要故事只要生活事件,不要情节只要情景”(12)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第71-7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的创作理念,也使译本丧失了丰富的选材所带来的优势。经过译者的简化和过滤,承载着作家探索与创新的8篇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只能是重复、刻板的印象,有读者认为该译本未能达到阅读期待,“故事乏味、千篇一律”。(13)Dan Dwgradio,Review on The Butterfly and Other Stories,引自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238277#CommunityReviews。
《布礼》与《蝴蝶及其他》作为现有译本普遍采取的两种译介策略的代表,无疑是推动王蒙作品走入英语世界的有益探索,但均存在明显不足,未能达到最为理想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译本选材能否真正激发读者兴趣,翻译实践能否在增与删、忠实与叛逆间达到良好的平衡,是译介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突破困境的译介策略探索
“厚译”与“删减”分别代表着文学翻译中由来已久的“异化”与“归化”倾向,前者力求贴近原文,保持译作的忠实、完整,而后者注重读者,以顺畅的阅读体验为首要标准。需特别注意的是,“异化”与“归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任何合格的翻译实际上都是两者的结合,是不断在原作和读者间寻求平衡的结果。“异化”与“归化”与其说是译者刻意奉行的翻译准则,不如说是译本在历经译者反复权衡后呈现出的整体倾向,而真正优秀的译本自然是合理、巧妙地平衡了两者的“融化”之作。虽然王蒙作品英译本的整体接受情况尚不理想,但我们可以从少数进入英美主流销售渠道并在读者间产生良好反响的译本中,找到趋近“融化”境界的成功之作,并探索译者在“融化”理念驱动下采取的有效译介策略,作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突破译介困境的可行方法。
朱虹是王蒙作品最重要的英文译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起,她以独到的视角和极富个性的译笔,将大量中国新时期小说译为英文,译本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朱虹对王蒙的译介历时30余年,是唯一一位持续关注王蒙创作的译者。她编译的《中国西部小说选》(TheChineseWestern:ShortFictionfromToday’sChina)收录了王蒙的短篇《买买提处长轶事》,1988年由美国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出版后,又于次年由英国Allison &Busby出版社使用《苦水泉——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SpringofBitterWaters:ShortFictionfromToday’sChina)为题再次出版,后经转译在雅加达出版印尼文版。1992年,朱虹在美国文学期刊《巴黎评论》发表王蒙《坚硬的稀粥》译作。1994年,纽约George Braziller出版社推出了由朱虹选编、多位中外译者合译的王蒙小说选集《坚硬的稀粥及其他》(TheStubbornPorridgeandOtherStories),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Kinkley)评价这部选集“编辑、翻译得非常好”。(14)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续)》,《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该选集在Goodreads上的得分在王蒙作品英译本中遥遥领先。同时,该选集为英语世界的王蒙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视角。《王蒙自传》是朱虹最满意的译作,历经多年打磨终于在2018年由Merwin Asia出版社出版。文棣评价这部译作“非常值得一读”,“编辑和翻译都很出色”。(15)Wendy Larson,Book Review,The China Journal (January 2020),p.201.
朱虹综合了多种类型译者的优势,既有本土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准确理解和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热情与责任感,又有近乎英文母语者的语感和对读者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的把握,还有学者型译者对文学问题的敏感和对作品的深入阐释。朱虹将“融化”理念充分融入译介的各个环节,她的译本得到了读者的青睐,拥有着持续的生命力,为我们研究以“融化”为导向的译介策略提供了优秀范本。
译材选择作为译介的第一步,是决定译本能否吸引读者的关键。朱虹善于从中西文化、历史、社会的交汇处选取切入点,挑选和组织译材。《中国西部小说选》所突出的“西部”和“西部小说”是中美两国都有的地理、历史和文学概念,朱虹在译序中指出“中国西部”与“美国西部”在迥然不同的时代环境下,显现出惊人的相似,两国的“西部小说”都记录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探讨了变迁背后的意义,并提到中国年轻一代西部作家对美国西部作家的借鉴。(16)Zhu Hong,The Chinese Western: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8,p.viii.读者对翻译文学的排斥很大程度上出于对陌生文化的排斥,朱虹借由英语读者熟知的“西部”概念,让读者带着中西比较的眼光,踏上一段富有探索和发现乐趣的阅读旅程。这部选集不仅向读者推介了王蒙等一批书写中国西部的当代作家,也实践了文学翻译推动文化间对话的最高理想。
朱虹的译材选择也离不开她对文学潮流的敏锐观察和精准把握。《坚硬的稀粥及其他》囊括了王蒙八九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意识流作品和先锋实验小说,向读者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坛求新求变的意愿和锐意探索的成果。朱虹以灵活生动的译文,再现了她所解读的王蒙笔下一个个“急于逃离过去,又不知前路在何方的人物”,认为他们是“集希望、欢喜、坚韧、反抗、沮丧、怀疑、焦虑与困惑的‘辩证的荒诞主义’”,(17)Wang Meng,The Stubborn Porridge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94,p.5.呼应了20世纪世界文坛的米兰·昆德拉热,使英语读者自然地联想到昆德拉在创作中反复探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状态“力脱思特”。文学潮流反映着特定时期作家的创作喜好和读者的阅读口味,朱虹对文学动态的捕捉和在译作中对文学潮流的呼应,既能及时满足读者的需要,又有助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融互鉴。
朱虹的译材选择也极具个性化,她依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对作家的译介潜力做出判断,选择与自身精神气质相通的作家和与自己译笔风格相契的作品。出生于1933年的朱虹与王蒙同为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与成长的一代,对王蒙作品有着格外深刻的体认。朱虹高度评价王蒙的个人品质,称王蒙“有智慧,有自嘲,有超越,很乐观,很坚强”“是个有个性的人”,也非常认可王蒙的创作才华,特别是他奥妙的语言,她坦言:“我写不出那样的小说,但可以做翻译,让外国人更多地了解他。”对作家的认同和对作品的欣赏让朱虹在翻译实践中以母语读者的姿态,借由译文与读者真诚分享“发现的喜悦”,(18)舒晋瑜:《朱虹:我吃亏在英文比中文好》,《中华读书报》2018年2月28日。这样的译文往往更富感情,更有温度。
“融化”的选材是助力朱虹译本走进读者视野的前提,真正决定其译本接受成效的是她在译文中营造出的“融化”效果。《坚硬的稀粥》是朱虹认为最难译的一篇小说,作品整体的讽喻基调,叙述人幽默、夸大的词句,众多的人物及其千变万化的立场、语气、情感,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无一不考验着译者“融化”的功力。但《坚硬的稀粥》也是朱虹最出色的译作之一,王蒙曾向她转述读者对此译文的评价,称朱虹翻译得“很有味儿”。(19)见穆雷:《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 ,《外国语言文学》2003年第1期。这句简单却有分量的褒奖足见译者不但讲好了原作的故事,更充分再现了其中蕴藉的审美特质。我们不妨以这篇译作为例,聚焦译文对作品语言风格的再塑,分析、归纳朱虹在翻译中用以实现“融化”效果的具体策略。
朱虹的译文处处展现着重构原作语言特色的巧思,“融”中式表达于英文语境,“化”中国文化于英文思维。《坚硬的稀粥》尽显王蒙的语言才华,小说中充满典型的“并置式语言”,即将众多意思相同或相悖的词语大量排列在句中,(20)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第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显现出独特的气势与韵味。朱虹对千变万化的词语进行了合理、适度的归化,她常能找到英文中意义相近的惯用表达,如“既喜且忧”(a mixed blessing)、“落后于时代”(living in a time capsule)、“脱缰野马”(a galloping fire)、“掏心窝子”(returned trust for trust)、“庸人自扰”(much ado about nothing),(21)以上英译文均出自Wang Meng,The Stubborn Porridge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94,p.8-38.使译文更流畅、精确,又不失原文的力度。在处理结构松散的语句时,朱虹会通过大幅调整语序,使译文的叙述重点更突出,更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为进一步方便读者理解,朱虹甚至会调整句子位置或重新划分段落。此外,朱虹还积极融会具有相似语言特色的英语作家的行文方式。例如,她借鉴了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纽约外传》中的笔调,“采用了不歇气的长句子和有失比例的大字眼儿去表达原文中的夸张、机巧和那股滑稽模仿的傻劲儿”,(22)见穆雷:《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 ,《外国语言文学》2003年第1期。将原文风格更自然地引入英文。
有研究认为朱译本的成功主要源自译者游刃有余的归化译法,但实际上,朱虹并非一味追求译文的地道、易读,尤其是对待带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时,她很少选择绕行。朱虹常不避异化色彩,对富于文化意趣的内容予以完整保留,如“假传圣旨”(fabricating the edict of the Emperor)、“滋阴壮阳”(nurturing the Yin and energizing the Yang)、“山珍海味”(a gourmet feast of all the delicacies extracted from seas and mountains)、“醍醐灌顶”(It was as if an enlightening fluid had been injected into our brains)。有时看似不必要地译出了词语中的意象,却以恰到好处的力道还原了作者在文字间刻意营造出的荒诞、戏谑之感。对中国当代社会特有的,特别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字眼儿,朱虹会在保证英文表意顺畅的前提下尽量沿用中文的表述方式。朱虹也很少删减或模糊处理读者无法直接领悟的文化内容或微妙细节,而是通过简短的脚注向读者说明原作中的社会现象、政治标语等的影射,或通过文内解释的方式进行化解。例如“‘四二一’综合症”(Four-Two-One Syndrome)、“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主义”(the fallacy that the moon over the U.S. is rounder than it is over China)等当时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译者在直译的基础上,将前者进一步解释为“four grandparents and two parents revolving around the single child”(祖父母和父母围着一个孩子转),将后者解释为“the blind worship of things foreign”(盲目崇拜国外事物),使读者既能接触到富有趣味的源语表达方式,又不以牺牲理解为代价。
关于如何平衡归化与异化两种倾向,翻译家叶子南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该归化且能归化时归化,该异化且能异化时异化,归化的程度因语境而异,异化的深浅随场合而定。”(23)叶子南:《回旋在语言与文化之间——谈翻译的两难境地》,《博览群书》2002年第10期。
朱虹的翻译实践正是对这段话的完美诠释。但她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充分平衡两者的基础上,进行了不逊于原作的大胆的语言试验,融自身创作才情于译文,以英文鲜明地塑造出一套王蒙的笔墨。朱虹的选词富于创造性,她认为王蒙的文字是自我指涉的,能够引人注意并派生意义。例如,她并未将小说题目中的“坚硬”译为“hard”,而是选择了富于人格化的“stubborn”,其中蕴含着的强硬、执拗、棘手等多重意味,与小说主题完美契合,奠定了译文讽喻性的基调。朱虹在遣词造句方面下足了功夫,有时为达到与原文同样强烈的讽喻效果,不惜在特定位置做加法。如老保姆徐姐操持家务数十年,全家敬重,地位特殊,堂妹指责妹夫轻视徐姐,称他在大家族中“还没徐姐要紧”。如果紧贴原文译作“You are no more important than Elder Sister Xu”,就表示徐姐与妹夫同属外姓,在大家族中地位都不高,这显然不符合说话人的原意,朱虹将此句译为“You are not worth Elder Sister Xu’s litter finger”(你连徐姐的小指头都不如),看似加入了不必要的成分,背离了原意,实际上却更忠实地还原了人物的语气和情感。
朱虹的翻译融中英两种语言特色于一炉,平衡了语言风格的忠实度、故事性、读者体验等方面的关系,既照顾了译语表达习惯与读者感受,又平衡了原作内容与风格的忠实度,充分保留与再现了作品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使译本实现了较为理想的“融化”效果,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了可资借鉴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