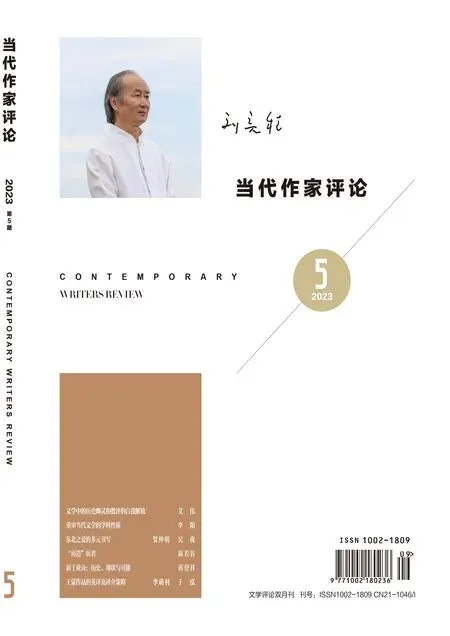主持人
2023-12-19郜元宝
郜元宝
主持人的话本期主持人语暂停对评论界同行评头论足,专心跟弋舟、艾伟过过招。两位作家都动真格的了,我必须全神贯注,才对得起他们的认真劲儿。
艾伟的新作《镜中》一度令我陷入迷惘。我感觉不好把握他这次大幅度的华丽转身。看过一些评论,包括艾伟本人的《后记》,以及他谈论《镜中》的短视频。去年底在北京某处散步,我们还坦诚地交换过意见,但这一切仍然无法消除《镜中》带给我的困惑。
直到读完这篇在《后记》基础上改写的创作谈《文学中的历史幽灵和批评的自我解放》,我才觉得或许可以走出迷惘与困惑,说一说艾伟过去的创作以及如今的转向所触及的当代小说“文史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了。
广义的文学(小说勃兴较晚,古人更关注诗文)与历史的关系并不复杂。简言之,就是既有交集(不可隔绝),又有差异(不能混同)。
鲁迅赞赏《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窃以为此句属上下互文结构。鲁迅不是说《史记》之历史记叙与文学描写各美其美,而是肯定司马迁之如椽巨笔,史中有文,文中有史。其史笔之优胜固多得文笔沾溉,文笔之生动亦多得史笔助力。两者交相为用,缺一不可。后人推崇杜甫毕生创作为“诗史”,道理相通,不必赘述。
小说中“文史”两种元素,相得益彰之佳例多矣,且不说伟大而又风格各异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艾凡赫》《九三年》《你往何处去》《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文史双美(这一点艾伟也高度肯定),也不说本身并无突出史才的巴尔扎克偏要以虚构小说来争取充当法国历史“书记官”的资格,即使刻意与历史撇清关系而聚焦于世情、人情、爱情乃至畸情的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或钟爱神魔狐媚的《西游记》《聊斋志异》,它们的文学成就也离不开巨大的历史感(从真实细节、夸张虚构直至整体构思皆可补正史之阙)。
缺乏历史知识的读者固然可以单单欣赏上述各类小说之“文笔”(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语言修辞、场面细节与心理描写等),但如果拥有丰富确凿的历史知识,以“文史互证”之法读之,则可以获得更多“了解之同情”。这也是老生常谈,无须词费。
但艾伟所谓“文学中的历史幽灵”,特指中国当代作家与批评家的历史癖一再伤害文学创作,既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也是必须牢记的教训。别的且不说,就说那些一味追求“史诗”效应的海量长篇小说吧,往往既无史识,亦无诗美,更谈不上诗史融合、相得益彰。最终既违背历史,也糟蹋文学。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然而这里的问题还是作者或批评家对历史既无精深之研究与体认(仅掇拾历史碎片、迎合或抗拒某种历史观念与历史叙述模式),对文学亦无个性之追求,贸然将文学和历史拉到一起,势必两败俱伤。简言之,不是不应该写历史,而是没有把历史写好。
既然如此,若要从“历史幽灵”肆虐小说的恶果引出教训,就应该是鼓励作家和批评家们更认真地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研究我们在处理文学与历史之关系时所获之经验与所得之教训,而不必因爱成恨,因噎废食,一拍两散,老死不相往来。没能写出“史诗”,不能责怪“史诗情结”,不能关闭历史这扇大门,搁置根本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问题,将历史视为与个人无关的外在公众话题弃若弊履,仅仅锐意探索个体内在的心理变迁与灵魂救赎,更不必一看到文学靠拢历史,就贬斥那是伪文学,一看到文学搁置历史而专写内心,就首肯其为真文学。
艾伟声明他“并不是主张小说和历史事件完全脱钩”,只是反对将重大历史事件和流行历史观念当作小说叙述的“动力源”,听任历史随便介入甚至取代小说;他更反对将未经深究的“历史”奉为文学的“隐性说明书”(以流行历史观念判断和阐释文学);他甚至建议不妨将历史事件放在小说叙事的“景深”,以便腾出手来,直指人心。
这些无疑都十分正确。
倘若由此反观艾伟个人的创作,我觉得他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恰恰在于较为出色地处理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他既能抓住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也能充分而真实地描画历史脉络、渲染历史氛围,在此历史事件、现象、脉络、氛围中写出了人物的情感逻辑、伦理纠葛与个体内心隐秘。因为聚焦历史中的人与人的历史,小说叙事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深描,小说结构立体稳健,层次完整,线索分明,故事推演与心理展开也都显得真实而自然。
比如谈论《爱人同志》,战斗英雄在社会风气转换后几无立锥之地的渐变过程和与之相关的各色人等,就会栩栩如生重现在我们眼前。一谈到《爱人有罪》,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严打”事件如何使当事双方成为互爱互害的怨偶。一提及《风和日丽》,世界范围内革命者的正义与亲情擦肩而过的悲喜剧就会爆发震撼人心的力量。
但艾伟或许不满足自己过去的历史书写所取得的成就,或许决心要跟“文不足,史来凑”的写作模式划清界限,又或许痛感真正历史书写的受阻,总之他想改弦易辙,尝试另一种写法了。他要看看小说叙事“有没有可能不依赖于既定的历史逻辑而独立存在”。比如,“‘偷情’无疑是对庸常的打破,使生活出现‘事故’,而小说真是庸常生活出现‘事故’的产物。这样的人物我们可以列举无数个,安娜、包法利夫人、德·雷奈尔夫人”,于是就有了《镜中》女主人公易蓉的养母的“偷情”。养母“偷情”直接影响到易蓉“偷情”的恶习。易蓉“偷情”间接导致丈夫润生与他人(子珊)“偷情”。这一系列“偷情”以一场车祸为分水岭发生逆转。易蓉最终自杀,并引导与她合谋的偷情者世平(润生助手)在火灾中以自己之死换得润生之生。润生和子珊则以各自的方式(捐献希望小学,在佛法与建筑中悟道,或者进入海外多元文化圈而逐渐与过往拉开距离)展开漫长的精神疗愈之旅。
同样描写“偷情”,《镜中》与《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的高下异同,自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托尔斯泰、福楼拜、司汤达是否既成功描写了“偷情”,又写活了当时俄法两国的精神氛围,写活了某种精神文化的“历史”?对此人们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在安娜、爱玛、德·雷奈尔夫人的情感纠葛中,她们所处的社会历史并未隐藏于某个“景深”,而是深深介入她们情感发展的每一步。唯其如此,她们的“偷情”才牵动全社会的神经,全社会的神经反应又强化了她们内心搏斗的酷烈。正是这两股力量的交战,成就了上述三部世界名著。
相比之下,易蓉的内心挣扎较少呈现她与周围世界的互动。她为何自杀?痛惜子女夭亡?忏悔无效?还是车祸之后整容失败,害怕色衰爱弛,不能跟世平保持罪恶、绝望又刺激的“偷情”关系?她临终前写给子珊的信展示了怎样的情感逻辑?自觉罪不可赦、陷入绝望与痛苦深渊的易蓉挂念她所亏欠的丈夫,为何选择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子珊作为求助对象,而非知根知底的世平?为何易蓉和世平没能克服精神困境,润生和子珊却获得了内心安宁?难道润生和子珊只是无辜的受伤者、受害者而毫无负罪感?他们疗愈的方式果真那么神奇有效?
我并非刻意挑剔《镜中》人物的情感逻辑,也并非要求艾伟在描写罪与罚、受伤与疗愈时,非要仰赖外在历史的介入。即使外在历史退场,人类内心的戏剧跟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也不可能隔绝,除非他们是先天性自闭症患者。《镜中》人物情感逻辑的问题就在于缺乏与社会历史可信的互动,好像每个人都被作者引入仅属于他们自己漫长幽暗的心灵隧道,只能靠自身修为走向光明,或者被黑暗所吞没。
当然不能说《镜中》人物跟周围世界毫无互动。润生和子珊一会儿身陷缅北监狱,一会儿闯入北美和缅北的黑道网络,一会儿跟美籍犹太人母子进行深深浅浅的文化与精神交流,一会儿与日本建筑师、贵族遗孀讨论建筑的精妙学问。这些文化主题和地理空间的频繁切换都是《镜中》人物伸向周围世界的触须,但恰恰是这些终究勉强的描写暴露了《镜中》的主要问题——作者营造了一系列仅属于人物自身的环境与历史,而非让人物在公共历史与公共环境中与他人真实互动,经历真实的罪与罚、受伤与疗愈。
《镜中》与艾伟过去创作的差异就在于此?或许这只是我的误读。不必将这篇创作谈视作艾伟对其创作转身的辩护。艾伟的转身还在进行中。他也在继续思考文学与历史之关系。此时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弋舟断然回避了“为何写作”之类的终极性提问,承认在社会分工日益明细的时代,自己经常被动地接受“计划经济式指令”或“市场经济式订单”。他是在此前提下探索小说的可能性——如果可能的话。
这是以降卑来升高。终极性提问并未取消,乃是转换为在不自由状态下对自由的坚持,在宏大叙事被耽延之后对写作这件小事的忠心。
弋舟将这种策略的最高目标归结为“以词证物”。
虽说“词”是他写作时“唯一可以凭借的抓手”,但并非苦心孤诣,自铸伟词,而是通过对习见的旧词进行陌生化处理,令其翻新出奇。
以鲁迅为代表的几代作家努力将带引号(更多不带引号)的文言成语融入现代白话文,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至今仍不失为汉语陌生化的一种典型。弋舟并未提到自身所属的这个传统,而是特别感谢了两位外国学者与作家的启发。
首先是米歇尔·福柯《伟大的异乡人》中的一段论述:“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我们总还有可能穿越现有的符号世界、词语世界和语言世界,扰乱现有世界最熟悉的意义,仅仅用几个相互碰撞迸发出奇妙力量的词语,便将一个异常世界呈现出来。”这段话给弋舟以逆向启发,他认为作家们很容易迷信自己拥有足以傲视世人理性的“文学特权”,亦即刻意“将一个异常世界呈现出来”的语言炼金术,因此他愿意剔除福柯的“即使”一词,而瞩目于“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这一令人发笑又无可奈何的假设,正面强攻,从世人“理性的”语言之网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语言之路。
换言之,要想实现真正的语言创新,作家必须充分了解大部分人对某些语词所拥有的“理性”惯用法,如此方能知己知彼,入室操戈。这也恰如鲁迅们活用文言时,必须充分了解文言的奥妙,才不会像当下某些作家们那样,每逢“文白夹杂”,经常左支右绌,大违初衷,让人不知所云。他们当然也会歪打正着,误导一些不明就里的读者以为其中必有深意,妙不可言。这或许是那些语言幼稚病患者之万幸,但肯定是汉语写作本身之大不幸。
启发弋舟的还有美籍匈牙利小说家山多尔·马劳伊《余烬》所言:“一个人必须掌握所有细节,因为他永远不知道其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要想在语言上有所创新,不仅要熟悉现成的语言,还须倾听小说叙事中每一场景、每一细节的内在召唤,这样才能从自己丰富的库存中拈出合适的言辞,就像王国维所谓“‘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弋舟将福柯、马劳伊的意思略加改造,变成自己的座右铭:以词证物,并且从细节之中找到词的对应。兜了一个圈子,他还是回到小说(或一切文学)的元命题: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决定内容?是熟悉生活,进而熟悉描写生活的语言,还是从已然习得的语言出发,推演、构造、召唤出一定的生活世界?
这个元命题曾经因为简单粗暴的“二分法”或“二元对立”模式而令人厌倦。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内容和形式(生活和语言)并不存在先与后、本质与现象、主与从、源与流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缠绕、互相创生,倘若强分先后、主从、源流、本质与现象,必然会凿破混沌,满盘皆输。
但话又说回来,上述发现一刻也离不开发现者的眼光。若无创造性发现,被动接受别人的“发现”,那么内容和形式、生活和语言诚然还是(也只能是)互相隔绝的先与后、本质与现象、主与从、源与流。于是有些作家会骄傲地声称自己拥有珍贵无比的生活(经历、体验、感情、感受、记忆、听闻……),另一些作家会同样骄傲地声称自己拥有高人一等的语言(语料库、文学修养、与某些大师的私淑关系、某些点石成金的叙事方法……)。前者自信满满“写生活”,其生活经验可能很丰富,却硬是茶壶倒饺子,因为他们匮乏写出这一切的语言。后者自信满满遵循汪曾祺的教诲,“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相信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维特根斯坦所谓“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但写来写去,总是在既有语言轨道滑行,在詹明逊所谓的“语言的牢笼”里转圈子,以词追词,以话赶话,结果一无所获。
在这一意义上,我理解弋舟的“以词证物”也包含着反题“以物证词”。所谓“从细节之中找到词的对应”,必定也是“从词语中找到细节的对应”。词与物如水中盐、奶中蜜,应该充分化合,一时俱现,尽管在具体写作中或许存在时空错位——词与物的吻合总要经过漫长艰辛的寻找,总要借助不同叙事情境的刺激,才能茅塞顿开,才能最终找到那些“在物的背后发光”的词语。
弋舟以他本人的短篇《化学》《缓刑》为例,现身说法,阐释“词/物”微妙关系。凌晨跑步的女化学家之所以能跳出自己的专业圈,将“化学”一词活用于当下生活,固然因为她邂逅了一对神秘的年轻密友,但如果没有专门的知识储备,“化学”一词也不会在“言之有物”的“物”的背后突然大放异彩。
《缓刑》从“漂亮的小女孩”视角出发,写她离开父母(已经离婚,却依然忍不住在全家最后一次外出旅行时重启争端),摆弄着并不熟悉的电动玩具“机器战警”,在空旷的候机室遭遇霸道小男孩(顺走她的玩具)、神秘中年胡须男(给她买回同一款玩具)。
“空中管制”导致大面积航班延误,大人(包括“漂亮的小女孩”父母)纷纷发出旅行(生活)不过是“缓刑”的抱怨。但小说始终将重心落在“漂亮的小女孩”身上,追踪她的纷乱思绪,看她如何琢磨根本不明其意的“缓刑”一词。弋舟显然并不想让小女孩弄懂何为“缓刑”,其内涵应该由大人们来洞悉,然而大人们只是在该词表层划出微不足道的痕迹,咀嚼该词的使命居然交给了“漂亮的小女孩”。有鉴于此,读者才会产生必须出手帮帮小女孩的冲动。
被小女孩念叨着的“缓刑”一词背后,既敞开又遮蔽着她“被抛”的整个世界(以候机室为隐喻)。不管弋舟给这篇小说取名“缓刑”,是否想到雨果的名言或圣彼得之训诲,以“缓刑”一词隐喻世界早已被设定的运行轨道,或许正契合弋舟的创作意图。“缓刑”适合小说涉及的一切人,包括那位叙述者用眼角余光中一瞥而过且完全处于故事边缘的练习倒立的神秘女子,但小说叙述的重心毕竟是“漂亮的小女孩”,“缓刑”一词始终在小女孩身上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众人(尤其女孩父母)所抱怨的含义暧昧的“缓刑”,在懵懂无知的小女孩未来成长的道路上,将要产生怎样的影响?诱导此类提问,才是弋舟的用心所在?
“既然写作的动力在大多数时间已经不是源自某种古老的使命感,就让我们在这个被规定了的世界里,在那些被指定好了的词库中,耐心地看看,仔细地闻闻,运气好的话,没准当我们掌握了一切细节之后,当词和词碰撞之后,就会知道了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尽管弋舟刻意宣示其写作的低姿态,却并未放弃“古老的使命感”。他的写作绝非碰“运气”,某个词语能否“发光”,也绝不能依靠词语间无序的“碰撞”,而是“当我们掌握了一切细节之后”水到渠成的收获。《缓刑》《化学》如此,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一切路的尽头》,以及发表在《十月》2022年第3期的《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也是如此。
弋舟短篇新作已编成多本“人间纪年”。祝愿他这个系列的语词都能发出应有的亮光。
2023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