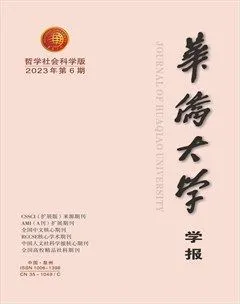谶纬与《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特征
2023-12-17林小云
摘 要:《吴越春秋》传奇色彩浓郁,具有“小说化”叙事特征。这与谶纬在东汉的兴盛以及赵晔今文经学者的身份有密切关系。在谶纬影响下,《吴越春秋》出现了诸如感生、受命、祥瑞灾异等内容,这些内容继承谶纬之说并加以演绎虚构,神奇浪漫,颇具文学色彩。《吴越春秋》受谶纬影响还表现在:虚构能力的提高,对奇幻之美的追求,对事物的细致描摹。这都使《吴越春秋》充满文学魅力。在谶纬的视野下,对《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特征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吴越春秋》自身文学价值,有助于梳理东汉时期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分流”过程,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谶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谶纬;《吴越春秋》;奇幻美;小说化
作者简介:林小云,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经学与文学 (E-mail:lxy2025654@126.com;福建 泉州)。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汉代传书与文史分流研究”(FJ2021B083)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6-0143-10
演绎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吴越春秋》,虽然题材为史,但更多虚构成分,故事曲折离奇,有着相当浓厚的传奇色彩。明代钱福《重刊吴越春秋序》认为“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吴越春秋》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1929年影印明弘治十四年邝璠、冯弋所刻《吴越春秋十卷》,第1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 778页。)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序》甚至直接视之为小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4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认为其“虽本史实,并含异闻”,属于“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10页。)现代学者如杨义、梁宗华、黄仁生等也视《吴越春秋》为小说。(参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87页,;梁宗华:《一部值得重视的汉代历史小说——〈吴越春秋〉文学价值初探》,《浙江学刊》1989年第5期;黄仁生:《论〈吴越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言长篇历史小说》,《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郭丹则认为《吴越春秋》保留了“史”的体式残骸而有小说之形态,体现了东汉“文史分流”的趋势。(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3—318页。)上述古今各家表述虽有所不同,但都认为《吴越春秋》具备了小说的叙事特征。那么,在文学尚未正式独立的东汉,《吴越春秋》为何呈现出这种“小说化”叙事特征?其文学叙事缘何侵入甚至取代历史叙事,从而实现从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的转化呢?我们以为,《吴越春秋》出现“小说化”叙事特征,有着多方面原因,而东汉谶纬的兴盛则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个重要因素。《吴越春秋》“小说化”的原因,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其与谶纬的关系却鲜有人论及,因此本文将就此问题作一番探讨,希望能探析《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的时代动因,并从某个侧面窥探东汉时期“文史分流”的原因。
一 谶纬的兴盛及赵晔与谶纬的关系
谶纬是两汉时期把经学神学化的学说,兴起于西汉哀平之际,盛行于东汉。谶纬的兴盛,源于其与政治权力的结合。由于光武帝刘秀曾利用谶语夺取政权,因此笃信谶纬。取天下后,他“宣布图谶于天下”([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4页。),确立了谶纬的官方统治地位。自此,谶纬在东汉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举凡断狱、决策、任免等,皆可见谶纬之深刻影响。汉明帝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唐]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41页。)。汉章帝则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基本围绕着谶纬进行,所编纂的《白虎通义》大量运用谶纬中的事例,处处流露出谶纬的气息。这一切都说明谶纬具有思想上的话语霸权。谶纬在政治及经学上的统治地位,也使其进一步将影响力渗透到其它领域,如史学与文学。要之,终东汉一朝,谶纬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了东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
由于谶纬的权威力量,谶纬成为当时学者的必修课,《汉书》《后汉书》等就记载了汉代很多精通谶纬的大学者。如史学家班彪,其著《王命论》,多以谶纬思想宣扬汉代君权神授,可见也深受谶纬影响。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2 573页。)。《吴越春秋》作者赵晔生活于东汉前期,这正是谶纬兴盛的时代。据《后汉书》本传记载,赵晔曾师从今文经学者杜抚学《韩诗》,而杜抚的老师正是上述善说灾异、受诏校定图谶的薛汉。杜抚本人也著有以纬证诗之作《诗题约义通》。另据东晋虞预《会稽典录》云:赵晔师从杜抚二十年,“抚嘉其精力,尽以其道授之”([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01页。),深得师门精义。今文经学谨守师法家法,因此,谶纬在赵晔所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本传还记载,赵晔除《吴越春秋》外,尚有《诗细历神渊》一书。但该书不传于后世,其内容已无从直接了解。本传载:“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第2 575页。)一般认为,《论衡》既是“疾虚妄”之作,而蔡邕将《诗细历神渊》与《论衡》相比,那么《诗细历神渊》应该也与之旨趣相似,亦为“疾虚妄”也即反对谶纬之作。事实是否如此呢?《论衡》一书,虽称“疾虚妄”,但其所疾之“虚妄”“多系世俗迷信,及书传中之神话乃至文学上常有的夸饰”(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6页。),而对当时最大的虚妄谶纬,王充并未全然反对,其书中多有引用纬书事典、化用纬书观点之处,且借助符瑞大力称颂汉代皇帝,如他在《讲瑞篇》中便说:“案永平以来,讫于章和,甘露常降,故知众瑞皆是,而凤皇骐驎皆真也。”(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45页。)蔡邕其人,《后汉书》本传载其曾上书言灾异,可见也非反对谶纬之人。因此,蔡邕对赵晔《诗细历神渊》的激赏,认为其胜过《论衡》,并不能说明《诗细历神渊》中无“虚妄”的内容,更不能说明该书反对谶纬。从赵晔的师承、该书与众多纬书类似的书名来看,《诗细历神渊》更可能是一部有关谶纬的著作。惠栋在《后汉书补注》中称“以历言诗,犹诗纬之《泛历枢》也”([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第901页。),也认为《诗细历神渊》是一部类似纬书的著作。综上,赵晔精通谶纬应该是可以肯定的。社会的氛围,自身的学养,这一切都决定了赵晔《吴越春秋》与谶纬的密切关系。
二 《吴越春秋》中的谶纬之说
谶纬内容庞杂,包含五德终始、感生、受命、灾异祥瑞乃至天文地理知识等。《吴越春秋》中的谶纬事件虽不是很多,但却涵盖了谶纬中的重要内容。
(一)感生。感生神话并非在谶纬之后才出现,《诗经·大雅·生民》即有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之说。《史记》之《殷本纪》《周本纪》也有类似的感生神话。但谶纬出现后,感生神话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谶纬创造了大量关于古帝圣王的感生神话,如黄帝乃其母附宝感雷电而生,商汤乃其母扶都感黑帝而生,文王乃其母大任感蒼帝之精而生等。谶纬虚构所谓的感生神话,是赋予圣王的出身以神圣性,以显示天命早定、君权神授。《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即承袭《诗经》之说,谓姜嫄履天帝之迹而生后稷,赋予后稷出生以神圣性。卷六《越王无余外传》载:“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本文所有《吴越春秋》引文均出自张觉《吴越春秋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这是关于大禹出生的谶纬化叙述。大禹出生的神话,典籍中有不同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山之郊。鲧复(腹)生禹。”(袁珂:《山海经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6页。)《淮南子·修务训》曰:“禹生于石。”([汉]刘安:《淮南子》,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 135页。)纬书中则有不少禹母吞薏苡生禹的记载,“夏姒氏,祖以薏苡生”(《礼含文嘉》);“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尚书刑德放》)([清]赵在翰辑:《七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1、217页。)。此外,纬书中尚有禹母剖背而生禹之说:“修己剖背,而生禹于石纽。”(《尚书中候考河命》)([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1页。)《吴越春秋》中大禹感生神话,很显然是在纬书“吞薏苡说”及“剖背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想象发挥而成。从叙事目的看,与纬书一样,也是赋予大禹出身以神圣性,以显示其天命所归;从叙事效果看,虽然故事内容与纬书基本一致,但有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较细腻的细节描写,大禹母亲女嬉的形象与谶纬相比,也更为具体生动。
(二)受命。受命也是谶纬中常见的神化帝王的手段。所谓“受命”,就是帝王接受上天所授予的天命。上天授予天命的主要方式是出河图洛书以授圣王。如《春秋元命苞》:“尧游河渚,赤龙负图以出,图赤如绨状,龙没图在。”([清]赵在翰辑:《七纬》, 2013年,第426页。)《尚书中候》:“河龙图出,洛龟书威,赤文象字,以授轩辕。”([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1994年,第400页。)除了受河图洛书之外,谶纬中还有一些受天书的例子,如《春秋元命苞》:“凤凰衔丹书,游于文王之都。西伯既得丹书,于是称王,改正朔,诛崇侯虎。”([清]赵在翰辑:《七纬》,第426页。)谶纬热衷于虚构帝王受命,是为了给现世的政权提供一个更高的权威,以体现政权的正当性、神圣性。受命的思想经谶纬的传播而深入人心,成为汉人的习惯性思维。《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大禹治水,有黄龙负舟,大禹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此天所以为我用。”此外,同卷中尚有禹受天书明治水之理的记载:
禹伤父功不成……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按《黄帝中经历》—盖圣人所记,曰:“在于九疑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赤帝在阙。其岩之巅,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瑑其文。”禹乃东巡,登衡山,血白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忽然而卧,因梦见赤绣衣男子……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岩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发石,金简之书存矣。’禹退又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
关于鲧禹治水的神话,最早出自《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袁珂:《山海经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6—337页。)叙述极其简单,并无禹受命的记载。《史记·夏本纪》对大禹治水记载得较为详细,但着重突出的是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1页。)的艰苦卓绝的作风及厚生爱民的仁德,也未提及禹之受命。此外,《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也有大禹治水的记载,虽与《山海经》《史记》的记载有所差异,但也均未叙及大禹得天帝授书。而谶纬中却有不少关于大禹受命治水的记载。如《尚书中候》:“禹临河观,有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表曰:‘文命治滛水,臣河图去入渊。’”“禹观于蜀河,而授绿字。”“禹理洪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6、406、408页。)《尚书刑德放》:“禹长于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图,故尧以为司空。”([清]赵在翰辑:《七纬》, 2013年,第217页。)《吴越春秋》大禹受天书而得通水之理的记载,显然是对谶纬故事的继承与发挥。一方面,它以感性直观的方式,神化了大禹厚生爱民的形象,表明圣王的至德所感,必致天命所归:大禹为民劳身焦思,其受天书正是上天彰明其圣德。另一方面,《吴越春秋》对大禹治水的谶纬化叙述,比之《山海经》《史记》诸书,更为具体生动。书中不仅刻画了大禹“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的仁德形象,而且还细致描写了其受命的过程:先是从《黄帝中经历》中得到有关天书的启示,而后登衡山血白马以祭,犹未得,最后才于梦中得到山神指点,找到金简之书。不仅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细节描写也更为丰富细腻,如写大禹“冠挂不顾、履遗不蹑”“愁然沉思”“仰天而啸、忽然而卧”等,使得大禹为天下百姓劳身焦思的形象更为鲜明,呈现出文学叙事的特点。
(三)祥瑞灾异。先秦以来就有的天人感应思想经董仲舒发展,到汉代大行于世。天人感应在政治上的运用就是灾异谴告说与祥瑞说。谶纬继承董仲舒谴告说的思想,将地震、山崩、洪水等灾难事件及日蚀、月蚀等异常之事与政治失道并置叙述,如“夏桀无道,山亡土崩”(《尚书中候》)([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9页。);“逆天地,绝人伦,当夏雨雪”(《诗推度灾》);“八政不中,则天雨刀”(《春秋演孔图》)([清]赵在翰辑:《七纬》,第240、382页。)等。这种叙述,强调的是统治者的政治德行。《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载,勾践欲僭越称王,范蠡劝阻:“昔吴之称王,僭天子之号,天变于上,日为阴蚀。”吴君违背周礼,僭越称王,上天以日食加以警告。《夫差内传》载,夫差穷兵黩武,不顾伍子胥之谏北上伐齐、与晋争长,耗尽吴国国力,又赐死伍子胥,导致吴国“连年不熟,民多怨恨”。吴国连年不熟,违背自然规律,很显然也是上天对夫差的警告与惩罚,是天命的表达。无奈夫差不悔悟,最终灭国亡身。
与灾异谴告相对应的便是祥瑞。谶纬兴起后,祥瑞之说更为兴盛。在谶纬的叙述中,祥瑞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王者受命。如“黄帝之将兴,黄云升于堂”(《春秋演孔图》);“帝王之兴,多从符瑞。周感赤雀,故尚赤。殷致白狼,故尚白。夏锡玄珪,故尚黑”(《春秋感精符》)([清]赵在翰辑:《七纬》,第379、528页。)。二是王者有德。如“王者德至天,则降甘露”(《孝经援神契》);“是以清和上升,天下乐其风俗,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神龙升降,灵龟晏宁”(《乐动声仪》);“制礼作乐得天意,则景星見”(《礼稽命征》)([清]赵在翰辑:《七纬》,第698、339、297页。)。在谶纬影响下,汉代士人对祥瑞之物十分着迷。如班固、杜笃、傅毅等人的赋中,宝鼎、祥云、甘露、醴泉等祥瑞之物屡屡出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不少祥瑞。《越王无余外传》载,禹即天子位,“调权衡,平斗槲,造井示民,以为法度”时,“凤凰栖于树,鸾鸟巢于侧,麒麟步于庭,百鸟佃于泽”。大禹有恩泽于民,这些祥瑞正是“天美禹德而劳其功”的表现,是上天对大禹的褒扬。更值得注意的是,大禹治水过程中遇九尾白狐而娶涂山氏之女的记载: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厖厖。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斯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女,谓之女娇。
大禹娶涂山氏之女的故事,《吕氏春秋》《史记》等书中均有之,但并未提及九尾白狐。而纬书中则有禹梦见九尾白狐的记载:“(禹)长九尺九寸,梦自洗河,以手取水饮之,乃见白狐九尾。”(《尚书中候考河命》)([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31页。)在谶纬叙事中,九尾白狐是王德的象征,如“德至鸟兽,则狐九尾”(《孝经援神契》)、“文王下吕,九尾现”(《易乾凿度》)、“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春秋元命苞》)、“黄帝先致白狐、白虎,诸神物乃下”(《春秋合诚图》)([清]赵在翰辑:《七纬》,第701、30、426、545页。)等等。可见,《吴越春秋》中大禹遇九尾白狐而娶涂山女的故事是从纬书中继承变化而来,“其九尾者,王之证也”,神化了大禹的天命,遇白狐而娶涂山氏之女则使圣王大禹添了一丝人间的气息,更加亲切可感,而涂山歌谣的吟唱,更是使行文摇曳生姿。
谶纬叙事中,祥瑞都发生在黄帝、尧、舜、禹等圣王身上,是上天对其圣德的褒扬。《吴越春秋》中祥瑞之事的主角则除大禹外,尚有越王勾践。《勾践阴谋外传》中,勾践为诱使夫差起宫室,耗费吴国国力,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寻找良木以献夫差,一年无所得。正当木工皆有怨望之心时,“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勾践当然称不上圣王,但其复国过程中,“缓刑薄罚,省其赋敛,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其行为虽以复仇为目的,但客观上却有益于百姓民生,故天生祥瑞以助之。可见,《吴越春秋》中这些祥瑞之事,与谶纬相一致,突出的是统治者的政治德行,体现了赵晔对仁德之世的向往。具体叙述中,其内容比谶纬更详细,情节更为丰富曲折,故事性也更强,因而其叙事也更具文学性。
(四)空间地理。谶纬所建构的空间地理世界很具有神秘感。这种神秘感首先体现在对昆仑山的神化上。昆仑山,作为古人认知中最高大的山脉,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因而在早期神话中对它有不少神秘化的想象与描述。如《山海经·海内西经》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袁珂:《山海经译注》,第244页。)《穆天子传》中昆仑山则是西王母所在之地。谶纬出现后,昆仑山进一步被神化了。《春秋命历序》云:“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墟。”([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885页。)《河图録运法》曰:“地之位起形于昆仑,坐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众仙之所集也。”([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 164页。)《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之山为地首,上为握契,满为四渎……”([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 091页。)这里,昆仑山不仅仅是渺远的一座神山,居住着帝王神仙,而且是地形、河流之始,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发源地。地形之始自当位于中央,因此在谶纬的想象中,昆仑山还是地之中央,“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其中有五山,帝王居之”(《河图括地象》);“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河图括地象》)。([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 089、1 091页。)位于地之中央又高峻无比,由此衍生开来,昆仑山还是天柱和地柱,既向下延伸,支撑着整个大地,又耸入云端,沟通天人:“昆仑山,天中柱也”(《龙鱼河图》);“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河图括地象》);“(昆仑)地下有四柱,三百六十四轴”(《河图括地象》)。([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 154、1 095、1 092页。)谶纬对昆仑山独有的认识在《吴越春秋》里也有所体现。《勾践归国外传》记载:
于是范蠡……筑作小城。城既成,而怪山自至……范蠡曰:“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闻昆仑之山乃天地之镇柱也。上承皇天,气吐宇内;下处后土,禀受无外。滋圣生神,呕养帝会。故五帝处其阳陆,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国也,扁天地之壤,乘东南之维,斗去极北,非粪土之城?何能与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臣乃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
勾践认为昆仑山是王者的象征,而越国地处偏远,远离政治中心,不具备统治地位,不敢企望昆仑之象。而范蠡则认为其筑城上应天意,有昆仑之象,预示着越将兴霸。这里,昆仑山不仅是天地之镇柱、帝王神仙之居所,且有神秘能量,能预示国家兴亡,在吴越争霸中以怪山形象出现,是越将兴霸的象征。这正是《吴越春秋》对谶纬中昆仑山神秘形象的进一步想象和发挥,为勾践复国的历史故事增添了传奇色彩。
谶纬中空间地理的神秘性还体现在对天与地、天地与人事之间神秘关系的描述上。如《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维,地有四渎。天有八气,地有八风。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 090页。) 《诗含神雾》则将各个地域与时间、音乐、节气、民风等关联起来,如“唐地处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风,音中羽,其地硗确而收,故其民俭而好畜,此唐尧之所起。”([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60页。) 这种种描述显示出谶纬所建构的空间地理世界是以“天人合一”为深层结构、经验与超验共存、人文与自然结合的世界。《吴越春秋》载:
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窗。筑小城,周十里。陆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矣。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西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阖闾内传》)
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西北立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以两蟉绕栋,以象龙角。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勾践归国外传》)
伍子胥造筑大城小城,象天法地,以求破楚绝越;范蠡筑作小城,拟法紫微星,以求破吴。这不仅是谶纬神秘空间地理意识的体现,更进一步发展了谶纬中“天人同构”的思想,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天人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作者把谶纬中的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春秋时人身上的表现。从叙事效果上看,也更强化了伍子胥和范蠡这两个智囊人物的传奇色彩。
“经典化的谶纬汇集了先秦以来各种虚构性故事,构筑起虚构的经典……他们吸收整理各种文化典籍和神话传说故事,并发挥想象进行改造,造作出一批关于五德终始、史传神话、灾祥谶应等虚构性事件。”(张泽兵:《谶纬叙事研究》,南昌:江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45页。)尽管谶纬神学大量继承了原始神话内容,但原始神话更多体现的是先民的集体无意识与共同记忆,谶纬神学则更多出之以统治阶级及士人后天自主的、目的意图明显的虚构,直接为现实政治文化需要服务。谶纬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正与今文经学旨趣一致。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序例》认为:“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页。)今文经学关注并热衷于参与政治,谶纬则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参与批评现世政治的途径。《吴越春秋》中众多谶纬现象的描写,正体现了今文经学与谶纬的合流。这些谶纬描写,既是赵晔基于今文经学者身份对历史的评价,以强调君权神授;同时也指向现实政治,希望统治者能上应天命,下应民心,富民强国,体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怀。从叙事效果上看,众多谶纬故事,内容奇异,想象奇丽,情节曲折,描写尽致,使《吴越春秋》在历史叙述之外,蒙上了一层迷离浪漫的文学色彩。
三 谶纬对《吴越春秋》叙事艺术的影响
在谶纬所建构的世界里,古帝圣王、名山大川、日月星辰无所不包,此外,如远国异民、鸟兽虫鱼、珍禽异木及宫殿器物等各种各样奇怪物事也囊括其中。儒生们虚构出这一想象世界,是为了给现世的政权提供一个更高的权威,赋予现世政权以天命依据,但由于其视野宏阔,想象奇丽,客观上却锻炼了人们的想象能力、虚构能力。也就是说,谶纬借助想象虚构获得权威地位,想象虚构也借助谶纬在叙事领域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反过来,虚构的想象世界也给文学提供了丰富新奇的词语以及意象。这一切,都为文学性叙事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谶纬的虚妄性尽管遭到后人批评,但其文学价值却随着文学意识的发展而被不少人所重视。挚虞《文章流别论》就指出谶纬“纵横有义,反复成章”(穆克宏、郭丹:《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2页。)。刘勰《文心雕龙·正纬》也说:“若乃羲农轩皥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1页。)这些评价都看到了谶纬叙事所具有的对文学的促进作用。
谶纬虚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其所带来的人们文学想象、虚构能力的增强,对文学叙事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能不体现在《吴越春秋》的创作上,使《吴越春秋》的叙事突破历史叙事的藩篱而走入文学叙事领域。首先,与《左传》《史记》等史书相比,《吳越春秋》更多虚构成分。除前所言对感生、受命、祥瑞灾异等谶纬故事的发挥,《吴越春秋》还通过对史实的踵事增华、对史料的重新组合以及将历史事件巧妙改铸、移花接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这种虚构已经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虚构。(林小云:《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从史料的运用看〈吴越春秋〉的叙事特征》,《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第194—198页。)《吴越春秋》甚至还“无中生有”,虚构出一些只要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就能看出其“谬误”的事件,如卷十《勾践伐吴外传》写勾践灭吴称霸后,徙都琅琊,射求贤士:
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王雅琴礼乐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茅,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德,故奏雅琴以献之大王。”越王喟然叹息道:“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王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说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
粗知历史知识就不难发现,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勾践灭吴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孔子于勾践灭吴后与之会面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是赵晔在历史常识上出错,因为作为一个浸淫经学二十几年的学者,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只能是赵晔的虚构,“它让历史上的孔子死而复活,在时空错乱中和春秋五霸之一的勾践同台表演了一出文化剧,从而在历史理性的角度上探讨了越王勾践的霸业,检讨了以他为代表的强悍尚武的越文化和孔子代表礼乐教化的周孔文化的异质性”(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页。),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寓言。尽管它经不起历史的考证,但却体现了作者非凡的文学虚构能力,而这只能是在想象虚构能力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其次,谶纬叙事之奇伟影响了《吴越春秋》对奇幻之美的追求。汉人本尚奇,司马相如等赋家即善于将神话、历史传说融合到描写对象中,创造出神奇浪漫的艺术境界。谶纬的叙述者用惊奇的眼光、夸张的言辞,建构了一个想象世界,这个世界也以意象的丰富新奇,带给人们超越现实世界的虚幻体验,进一步促成了汉人以奇为美审美倾向的形成。如与《吴越春秋》同时代的《越绝书》就表现了这种以奇为美的审美倾向。《越绝书》之《宝剑记》对铸剑过程的描写、对宝剑价值的夸张、对宝剑神性的渲染无不体现出作者对奇幻之美的追求。《吴越春秋》这一点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阖闾内传》写干将莫邪铸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莫邪曰:‘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干将夫妻铸剑,竟使得“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成了天地间至有声色的盛典;而宝剑的铸成,还需要铸剑之人的身体发肤、血液乃至生命!而这样铸成的宝剑有着灵性与神性,能预示国家的兴亡。《阖闾内传》还记载吴国另一个工匠“杀其二子,以血衅金”而铸剑,更是在神奇之外带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原始的血腥气息!带有如此灵性与神性的宝剑是不可多得的,当楚昭王问风胡子湛卢剑之价值时,风胡子答以善相剑者薛烛之言:“赤堇之山已合无云,若耶之溪深而莫测,群神上天,欧冶死矣。虽倾城量金,珠玉盈河,犹不能得此宝。”这里对宝剑价值的夸张无以复加。《吴越春秋》对宝剑的描写,充满神奇浪漫的想象,将我们带入一个奇丽壮美而又略带残酷的世界。他如勇士椒丘“袒裼持剑,入水求神决战,连日乃出,眇其一目”;伍子胥死后多年显灵,“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迫使越军改道;夫差败亡后逃入山中,呼唤被其杀害的公孙圣,公孙圣三呼三应;越女与袁公比剑,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等等,离奇虚幻,充满浪漫色彩,俨然有志怪小说之特征。有些传奇描写,如伍子胥、文种死后化为涛神,“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更是在一种想象的神奇世界里传达出作者对人物的无限景仰,寄寓着作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深刻的历史之感,传奇性与悲剧性融合,动人心魄,极具文学魅力。尽管《吴越春秋》这些传奇故事大多源于越地民间传说,但作者将之采入书中并进行文学化演绎,却也不无谶纬尚奇之风的影响。
再次,谶纬叙述虽渲染夸张失实,“虚而无征”,但却“有助文章”,带来了人们文学描写能力的提高。谶纬对事物的描写修饰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颜色,二是方位。颜色如“汤受金符帝箓,白狼衔钩入殷朝。”(《尚书璇玑钤》)“君乘金而王,则紫玉见于深山。”(《礼斗威仪》)“五府,五帝之庙。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尚书帝命验》)([清]赵在翰辑:《七纬》,第191、311、221页。)“凤凰止庭,朱草生郊,嘉禾孳连,甘露润液,醴泉出山,修坛河洛。”(《尚书中候》)([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3页。)方位如“黄河……南流千里,至文山;东流千里,至秦泽;西流千里,至潘泽陵门;东北流千里,至华山之阴;东南流千里,至下津”(《河图始开图》)([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 106页。);“春则星辰西游,夏则星辰北游,秋则星辰东游,冬则星辰南游”(《尚书考灵曜》)([清]赵在翰辑:《七纬》,第196页。)。颜色与方位在谶纬中还经常结合在一起叙述,如“帝之五旗,东方法青龙,曰旗;南方法朱鸟,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虵,曰旗;中央法黄龙,曰常也。”(《河图稽耀钩》)([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 113页)谶纬中的颜色与方位携带着丰富的文化密码,表达着作者的神学意图,客观上则造成了谶纬叙事想象奇丽、辞藻华丽、句式骈俪工整等特点,具有刘勰所说“辞富膏腴”的特点,颇具文学色彩。《吴越春秋》中那些文学色彩浓厚的描写,也可见谶纬的影响。《越王无余外传》中,大禹治水未成,“乃按《黄帝中经历》—盖圣人所记,曰:‘在于九疑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赤帝在阙。其岩之巅,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瑑其文。’”对天书及其所在之处的描写主要以颜色为主,色彩丰富、意象新奇、句式工整。同卷中,大禹治水,周行天下,“东造绝迹,西延积石,南逾赤岸,北过寒谷,徊昆仑,察六扈,脉地理,名金石。写流沙于西隅,决弱水于北汉;青泉赤渊分入洞穴,通江东流至于碣石,疏九河于涽渊,开无水于东北;凿龙门,辟伊阙;平易相土,观地分州;殊方各进,有所贡纳;民去崎岖,归于中国”。这里的描写则主要以方位为主,间以颜色,极力铺陈大禹足迹之广布,治水之艰辛,奇丽壮阔;句式上则骈俪工整,富有音韵美。《勾践阴谋外传》中,勾践得神木献之于吴王,文章一连用了十二句四言韵语对神木进行铺陈描摹,“阳为文梓,阴为楩楠,巧工施校,制以规绳。凋治圆转,刻削磨砻,分以丹青,错画文章,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状类龙蛇,文彩生光”,刻画细致、色彩鲜明、音韵和谐、句式严整。此外,如越女论剑道,陈音论正射之道,描写细腻、比喻生动,能化无形之道为有形之物,精彩异常。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描写功力。
四 结 语
《吴越春秋》受谶纬影响,在历史叙事之外,驰骋想象,细致描摹,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瑰丽多彩的历史画卷,虽是写史,却俨然是小说的形态。但是,对于《吴越春秋》“小说化”特点,历史上却不断有人提出批评,如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认为此书“文气卑弱语多俳,又杂以谶纬怪诞之說,不及《越绝》远甚”([明]张元忭等:《绍兴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1983年,第3 319页。);清代李慈铭则指责赵晔:“东海鄙儒,其撰《吴越春秋》,皆以乡曲猥俗之言影撰故事,增成秽说。”([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50页。)这些评价囿于传统的史传实录观念,批评《吴越春秋》的“谶纬怪诞之说”,而没有看到这些“谶纬怪诞”之说所带来的文学效果。我们以为,正是这些充满神奇浪漫想象的“小说家言”,使《吴越春秋》从历史叙事母体中脱胎而出,呈现出“小说化”叙事特点,展现了东汉“文史分流”的趋势。东汉以后,谶纬遭到打击,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权威地位,但影响并未消散,其政治功能逐渐向审美功能转变。在文学自觉的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如张华《博物志》、王嘉《拾遗记》及干宝《搜神记》等均多涉五行终始、符命祯祥等谶纬之事,其事件的意义却不再仅仅指向政治功能,而更多地指向审美功能。六朝之后,小说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也不无感生、受命、灾祥等谶纬之说,作者运用这些谶纬之说为小说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服务。谶纬对古代小说叙事的影响可见一斑。因此,在谶纬的视野下,对《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特征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吴越春秋》自身文学价值,有助于探讨东汉时期,文学叙事是如何从历史叙事母体中脱胎而出,从而实现“文史分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谶纬对中国古代小说在虚构、叙事模式、情节设置等方面的影响。
Chenwei and “Fictionalized” Narrative Feature in the Wu and Yu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LIN Xiao-yun
Abstract: The Wu and Yu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as a strong legendary color and a “fictionalized” narrative featur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Chenwei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identity of Zhao Ye as a schola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enwei, the Wu and Yu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ppeared content such as induction, acceptance, auspiciousness and calamity, which inherited the theory of Chenwei and was interpreted as fictional, magical, romantic and quite literary. The influence of Chenwei on “the Wu and Yu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fictional ability, the pursuit of fantastic beauty, and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ings. This makes the book full of literary charm. From the view of Chenwei, discussing the “fictionalized”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Wu and Yu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ill not only help us evaluate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Wu and Yu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tself, but also help us analysis the “diversion” process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on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also help us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henwei on ancient Chinese novels.
Keywords: Chenwei; the Wu and Yu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antastic beauty; fictionalized
【责任编辑:陈雷】
收稿日期:2023-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