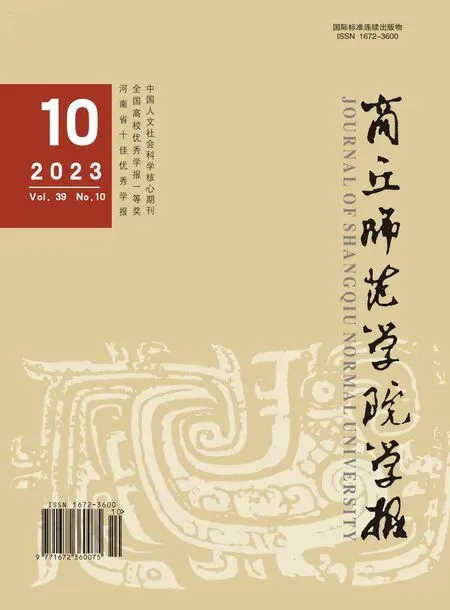体用关系视域下的庄子“坐忘”思想新诠
2023-12-17张景
张 景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范式研究院,江苏 徐州 221006)
庄子提出的“坐忘”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儒家、道教、佛教、世俗文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影响几乎涵盖了哲学、伦理、养生、道教、佛教等方方面面,甚至不少学者著书立说,专门研讨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如唐代司马承祯《坐忘论》、宋代徐彭年《坐忘论》、无名氏《坐忘枢要》《坐忘铭》,等等。然而,对于这一重要概念中的“忘仁义”与“忘礼乐”孰先孰后的诠释与解读,以及这一概念的实践意义,至今仍因集苑集枯而见仁见智。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更符合庄子原意的新诠释。
一、学界对“忘仁义”与“忘礼乐”先后次序的论争
庄子在论述“坐忘”思想时,依次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忘仁义”“忘礼乐”“坐忘”[1]68—69。我们依据这一次序去解读“坐忘”,或许更为切合庄子原意。然而现在面临一个理论问题:庄子对以上三个层次的顺序排列的理论逻辑基础是什么?把“坐忘”作为最高境界置于最后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在于“忘仁义”与“忘礼乐”孰应在先、孰应在后。依据心性修养应该由浅入深、从易至难的常识看,庄子应该把层次较浅、相对容易做到的“忘礼乐”放在前面,把深层次的、较难做到的“忘仁义”置于其后,于是不少学者依据《淮南子·道应训》的引文,认为应该把二者的顺序颠倒过来。刘文典与王叔岷均持这一看法:
《淮南子·道应》篇“仁义”作“礼乐”,下“礼乐”作“仁义”,当从之。礼乐有形,固当先忘;仁义无形,次之;坐忘最上。今“仁义”、“礼乐”互倒,非道家之指矣。[2]229—230
《淮南子·道应训》“仁义”与“礼乐”二字互错。审文意,当从之。《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淮南子·本经训》:“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道家以礼乐为仁义之次:礼乐,外也;仁义,内也。忘外及内,以至于坐忘。若先言忘“仁义”,则乖厥旨矣。[3]61—62
以《淮南子》为依据的上述观点可以代表多数学者的看法,如张耿光《庄子全译》也认为:“从整段文义推测,‘仁义’当与后面的‘礼乐’互换,忘掉‘礼乐’进一步才可能是忘掉‘仁义’。”[4]123即认为“仁义”无形而“礼乐”有形,“仁义”比“礼乐”更为根本,那么“忘仁义”的境界自然要比“忘礼乐”的境界高,所以按照由浅入深的原则,应当是先“忘礼乐”,再“忘仁义”,但《庄子》原文的排布与此恰恰相反。因为这些学者无法解释庄子为什么把“忘仁义”排在“忘礼乐”之前,所以认为这里似有倒误,其思想有违道家之旨。《淮南子》中的引文的确是“忘礼乐”在前、“忘仁义”在后,但《淮南子》的引文绝对没有《庄子》本文更具权威性与可信性。
当然也有学者是按照《庄子》原文排布顺序对“坐忘”思想进行解读,如成玄英在《庄子疏》中说:“礼者,荒乱之首,乐者,淫荡之具,为累更重,次忘之也。”[5]280认为相对于仁义,礼乐给人们带来的牵累更加严重,所以“忘礼乐”应在“忘仁义”之后。这似乎是从现实实践的角度作出的一种解释,但其道理讲得有些牵强。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上述观点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解释:
或谓仁义深而礼乐浅,仁义内而礼乐外,其忘也,应自浅而深,自外而内,本文不然,疑有倒误。《淮南·道应训》文与此同,惟先忘礼乐,仁义次之,似当据正。武曰:不然。仁义之施由乎我,礼乐之行拘于世。由乎我者,忘之无关人事;拘于世者,忘之必骇俗情。……此回所以先忘仁义而后忘礼乐,盖先易而后难也。《淮南》误倒,当据此以正之也。[6]176
刘武认为,“忘仁义”无关他人之事,“忘礼乐”就会惊世骇俗,因为后者难而前者易,故而“先忘仁义而后忘礼乐”。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其所说的对于难易的界定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以自身修养过程作为难易的评判标准,而是把外部对于主体的认可度当作衡量难易的标准;其次,这一解释忽略了“忘仁义”与“忘礼乐”之间在个体精神修养方面的内在密切联系,在这一层面上把“忘仁义”和“忘礼乐”单独分开,看作内在关系不大的两个概念,这明显是不可取的。
这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都是从修养论中的难与易、深与浅的关系入手,去解读“忘仁义”与“忘礼乐”的孰先孰后问题,而忽略古代哲学中更高层次的“体”与“用”、“本”与“末”的关系。我们则尝试从体用、本末的关系角度来诠释《庄子》原文顺序排列的理论逻辑的合理性,希望能够为这一学术难题给出较为正确的解释。
二、从体用关系看先“忘仁义”再“忘礼乐”的合理性
“体”与“用”是贯彻中国哲学始终的一对重要范畴,“体”指本体,属于根源性的、本质的;“用”指作用,属于派生性的、从属的。有体必有用,体消则用灭。关于仁义与礼乐的体用关系,我们可以从浅层次的伦理范畴和深层次的哲学范畴两个层面进行解读。
首先,从伦理这一较浅层次看,仁义为根本,礼乐为从属。对此,孔子反复强调:“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7]61没有仁义这一“体”“本”,属于“用”“末”的礼乐就无从谈起。换言之,如果没有仁义作为基础,礼乐就会堕落为虚伪的歌舞表演,完全失去人们赋予礼乐的应有作用。孔门师徒不仅从体用属性的理论角度论证仁义在先而礼乐在后,而且还明确从时间角度把礼乐放在仁义之后。《论语·八佾》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7]63
在老师的启发下,子夏悟到“礼乐应该放在仁义之后”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先具备仁义的品质,然后才有资格去修习礼乐。《礼记·郊特牲》对此讲得也很清楚:“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8]708“父子亲”是仁,有仁而后生义,有义而后礼作。《荀子·大略》更是一言以蔽之:“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9]488荀子认为,仁先礼后,是天道所施设,人必须遵循天道。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体用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时间顺序上看,都是先有仁义之心,然后在仁义之心的支配下,才能够制定出合情合理的礼乐。既然如此,那么要想忘却礼乐,必须先忘却仁义。否则,即使勉强忘却现有的礼乐,那些心怀仁义、以拯救民众为己任的圣贤一定会制定出新的礼乐,以期变混乱衰世为太平盛世。消除某种事物应该是拔本塞源,仁义是木之本、水之源,礼乐是本之叶、源之流,如果不能消除本、源,那么芟夷枝叶、堵截流水的行为就是一种无根本效益的短暂性行为。
其次,从哲学这一较深层次来看,心为根本性的“体”,行是从属性的“用”。而仁义属于心的问题,礼乐则属于行的问题。朱熹在解释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时引游氏语:“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7]61直接把仁义归结为“心”的问题,而“心性”同样是贯穿古代哲学始终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
儒、道两家皆承认心为体,行属用。孔子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仁与礼,而仁属于心性中的最重要内容,礼不过只是仁的附属品而已。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178孔子重礼乐,但礼乐并非体现在赠玉帛、奏钟鼓这些有形的行为上,其本质应该是仁心的一种恰切表达。孟子更是从心性入手,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关键就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人的修养目的归根结底就是“求其放心而已”[7]334。所以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反复强调:“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10]14王阳明把心、体、道视为一体,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恰切总结。
庄子更是如此,《齐物论》说:“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5]55—56庄子以各种人体器官代指万物,以“真君”比喻大道,大道是体,万物的产生与活动是大道之用,大道是万物的主宰者。然而这个主宰万物的无形无象的大道就隐含于圣人的心中:“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5]147有了含藏大道之心,然后就能够忘却仁义礼乐,齐同生死是非,甚至能够做到“无无”[5]760。“无无”这一境界不仅清除了万物的存在,甚至连庄子本身也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庄子“三遣法”》中有详细论证[11]。正因为如此,古人把心也称为“天君”:“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9]309道是体,万物的产生是道之用;道是“真君”,道就在圣人心中,因此心也可称为“天君”;其他万事万物皆要听从心的指挥与安排。庄子同样把心、体、道视为一体。
“坐忘”中的“忘仁义”就是忘心,心是体,礼乐的制定,则来自圣贤之心,是心之用的产物。颜回先“忘仁义”,实际就是先忘心,忘心的结果自然就是“忘礼乐”。可以说,忘心是抓住了忘却包括礼乐在内的万事万物的根本,忘心才能进入“离形去知”[5]284的“坐忘”境界。
我们还可以用顺逆两种行为方式的对比来证明忘心是“忘礼乐”的根本消除法。要想消除属性为“用”的礼乐,方法有两种,一是“逆”的方法,先不考虑忘心的问题,直接去忘却礼乐。这一方法犹如“扬汤止沸”,因为有因必有果,有体必有用,不消除“薪火”这一体与因,那么这一体之用、因之果——“沸”就难以消除;不忘却仁义,就很难消除礼乐。第二种是“顺”的方法,就是先去忘却仁义,然后再去消除礼乐。这一方法犹如“釜底抽薪”,先消除属于“薪火”这一体与因,那么属于用与果的“沸”自然就不会存在。可以说,庄子“坐忘”是从“体”入手,由忘体以达到忘用,最后是体用两忘——“坐忘”,也即“离形去知”。“忘”是“去知”,是消除属于“体”的心智;“坐”是“离形”,是消除属于“用”的行为。通过体用两忘以获取虚净、自由的“同于大通”[5]284的精神境界。
我们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庄子的“忘仁义”绝非是对仁义本身的否定,相反,是对仁义的更高层次上的肯定。庄子要忘却的只是世人对仁义的提倡与激励。这一主张同样与道家心性观有着密切联系。老庄是典型的性善论者,所以老子三番五次地要求人们“复归于婴儿”[12]116,庄子也多次提醒人们:“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5]317庄子认为,人的天性来自大道,形体来自阴阳二气;大道是完善的,那么来自大道的天性自然也是完善的。当人们能够遵循大道、保全天性时,他们的行为特征是:“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5]445在混沌未凿的理想社会里,人们顺应着自己的美好天性做事,处处善良却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善良,因此也就不需要人为的道德教育。对于天性泯灭的原因,庄子解释说:“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5]197天性犹如一面镜子,本来是明亮的,然而一旦蒙上灰尘,就不再明亮。当美好天性被社会上的各种因素破坏之后,发自天性的真诚仁义行为日益减少,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仁人志士才去提倡、奖励仁义的言行,这也就是老子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12]157。当人们能够按照大道、美德(天性)行事时,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提倡仁义。一旦提倡仁义,不仅意味着仁义的缺失,更严重的是会进一步破坏仁义本性。郭象对“坐忘”的解释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存夫仁义,不足以知爱利之由无心,故忘之可也。”[5]283
这里要澄清的问题是:既然人们的美好天性已经有所损伤,仁义已经缺失,为什么还反对提倡仁义呢?这是因为庄子认为,对仁义的提倡不仅恢复不了美好天性,反而会加剧对天性的破坏。《胠箧》说:“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5]346圣、勇、义、知、仁都是世人所竭力提倡的美德,然而却被盗跖运用到了劫财害命的勾当之中。更为严重的是,提倡、奖赏仁义还会使天性善良的仁人也蜕变为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小人:
西门疆尹河西,以赏劝民。道有遗羊,值五百,一人守而待。失者谢之,不受。疆曰:“是义民也。”赏之千。其人喜,他日谓所知曰:“汝遗金,我拾之以还。”所知者从之,以告疆曰:“小人遗金一两,某拾而还之。”疆曰:“义民也。”赏之二金。其人益喜,曰:“我贪,每得利而失名,今也名利两得,何惮而不为?”[13]351
西门疆竭力奖赏仁义行为,一位本来能够做到拾金不昧的仁人偶然发现行仁能够使自己“名利两得”,于是便开始了用假仁假义行骗的生涯。对此,庄子早就敏锐指出:“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5]861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论老子孔子“仁”的同异》中阐述得更为详尽,可参阅。[14]
同样的道理,庄子反对的是人为制定的礼乐,而提倡属于自然属性的“至礼”:“蹍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骜,兄则以妪,大亲则已矣。故曰:至礼有不人。”[5]808在市场踩了陌生人的脚,马上彬彬有礼地道歉;踩了兄长的脚,只需简单表示一下爱抚就行;踩了父母的脚,什么表示也不需要。在庄子看来,礼的出现,是人与人关系变得疏远的标志。提倡“至礼”的目的,就是要变关系疏远为亲密无间,做到人我一体。既然人我一体,视人如己,那么谁还会对自己讲究繁文缛节呢?庄子反对与人为礼相配的世俗之乐,而对“调之以自然之命”的《咸池》音乐却赞美备至,称之为“天乐”[5]507。
由此可见,庄子反对的不是发自天然的仁义礼乐,而是人为的仁义礼乐。庄子提醒人们不要去倡导仁义以损害人们的美德,更不要制定礼乐去约束人们的形体,重新恢复最根本的“体”——美好的天性。庄子的这一回归天性的主张及方法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但他指出的关于提倡仁义礼乐所带来的弊端,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概言之,庄子先忘仁义、后忘礼乐的主张,是一种由本及末的修养途径,也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根除措施,因此,庄子先“忘仁义”后“忘礼乐”的顺序排列的理论合理性不应受到质疑。
最后我们还要说明的是,庄子“坐忘”的目的,就是“同于大通”,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如果一个人时时刻刻惦记着行仁行义,就会“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5]373,就会像孔子那样“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7]70,心理上时时刻刻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仁义”包袱,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礼制对形体的约束也极为严重,庄子认为,人们头戴冠冕,手执笏板,腰束绅带,弯腰鞠躬,这就好比“罪人交臂历指而虎豹在于囊槛”[5]453一样,完全失去了形体自由。“忘仁义”是消除心理压力,“忘礼乐”是解脱形体束缚,而“离形去知”则是对“忘心”与“忘形”的全面总结。当心、身全部被解放之后,那么“同于大通”的自由生活自然就能够得以实现。
可以说,庄子的“坐忘”行文秩序由体至用,从本到末,理论逻辑清晰严密,我们没有必要把本不该颠倒的顺序给错误地弄颠倒了。
三、“坐忘”思想的实践意义
“坐忘”看似是一个地道的玄学命题,其后甚至有人从宗教的角度为“坐忘”披上一层修仙成佛的神秘面纱,使这一思想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们如果能够对这一思想作出选择性的恰当运用,这一命题则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适当的“坐忘”有利于健康。排除各种信息干扰,让大脑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完全空白状态,一直是古人修身养生的重要方法之一。《庄子》中的子綦就多次使自己处于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丧我”状态,《齐物论》说:“子綦曰:‘今者吾丧我。’”[5]45《徐无鬼》也说:“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颜成子入见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5]848年长的女偊之所以能够“色若孺子”[5]251,就因为他懂得忘却万物与生死。《达生》还有一段极具意味的话:“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5]662“忘足”“忘要”是忘形,“忘是非”是忘心,做到心形兼忘之后的“适”,自然有利于养生。白居易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适”之说:“褐绫袍厚暖,卧盖行坐披。紫毡履宽稳,蹇步颇相宜。足适已忘履,身适又忘衣。况我心又适,兼忘是与非。三适今为一,怡怡复熙熙。”[15]672(《三适赠道友》)让诗人无比惬意的“三适”就是建立在“忘履”“忘衣”“忘是非”的“三忘”基础之上。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坐忘论》更是把“坐忘”视为养生、长生的秘诀。“坐忘”对健康的益处也得到今人认可,2016年国家卫计委推出“5125”健康生活理念(1)《河南日报》2016年10月12日报道:“国家卫计委、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等11日共同在京启动‘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的子项目‘乐享健康生活’,倡导公众树立‘5125’理念……每天给自己留5分钟发呆时间;每天运动1小时、掌握1项运动技巧和加入1个运动社群;按照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食物,做到膳食多样化。”,其中第一个“5”就是建议人们每天“发呆5分钟”,即在紧张工作期间,让大脑暂时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空白状态以忘却各种烦恼,使大脑得到有效休息。这实际就是庄子提倡的“坐忘”。
第二,选择性“坐忘”不仅利于健康,还利于事业。《达生》记载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当别人请教他如何做到这一点时,他回答:“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5]658—659梓庆能把雕刻技艺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是因为他每次雕鐻之前都要进行斋戒,通过斋戒,逐次忘却名利赏赐、巧拙毁誉、自我存在与国家存在,使自己达到精神的高度专注。另外,《达生》的“痀偻者承蜩”[5]639—640、《知北游》的“大马之捶钩者”[5]760—761等故事也都反复论证选择性忘却、也即人们常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事业成功的重要作用。这一忘却艺术的有效性也得到今人证实,有人问著名球星迈克尔·乔丹:你为何在每场比赛中都能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乔丹回答:在每场比赛前,我都告诉自己,忘记以前所有的比赛,我做到了[16]。
第三,对于治国具有借鉴意义。由于对现实的绝望,庄子远离政坛,但站在政坛之外的庄子并未忘却苦难的民众,他依然在关注着社会政治。他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措施,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仁慈之心:“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17]6—7庄子虽有解民于倒悬的愿望与美好的政治理想,但他同历史上无数圣贤一样,知道自己“终不可用”,只好“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寄希望于“来者”[18]2068,而“坐忘”思想与他的美好政治理想息息相通。
在《逍遥游》中,庄子描写了“无功”的神人,这些神人的治国理念就是主观上忘却建功立业、万事万物,客观上却能够因清静无为而立了大功,立功后还要忘却自己的功劳,所以受到神人感染的尧在治理好天下之后,“窅然丧其天下焉”[5]31。这些圣君的治国理念就是忘我、忘功、忘天下。《在宥》记载,黄帝向广成子请教如何治国时,广成子却顾左右而言他,与他大谈修身养性,而修身养性的主旨就是“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依然是“忘”,为什么?因为“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5]381,天地各有主宰,阴阳各居其所,君主只要修养好自我身心,无须惦念治国,万物将会自然繁荣昌盛。接着的一个故事对此阐述得更为清楚,云将东游偶遇鸿蒙,便向鸿蒙请教如何改变“天气不和,地气郁结”等治国困境,鸿蒙犹如治国大医,不仅指出这一病症的原因是“治人之过”,而且还开出了“忘”的治国药方:
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5]390
君主治国的首要问题是“心养”,也即修养心性。修养心性的目的就是要学会忘却,这里讲的“堕尔形体,吐尔聪明”就是“坐忘”中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伦与物忘”就是“坐忘”中的“忘仁义”与“忘礼乐”,“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就是“坐忘”中的“同于大通”。只要君主能够做到这些,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就能够“自化”“自生”,社会就能够呈现太平祥和局面。这也就是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2]234,所谓的“无为”“无事”“无欲”,实际就是“忘为”“忘事”“忘欲”。
从这里不难看出,庄子关于“坐忘”的修心理念也是他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的确过于理想化,但其中的“不干涉”主张,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最后,我们还要强调的是,道家的修身养生、为人处世、治国理民的总体核心原则就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并视此为一切事业成功之关键。要想做到顺应自然,就必须忘却自我成见,这也就是《逍遥游》中倡导的“无己”与《人间世》强调的“心斋”: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5]147—148
所谓“心斋”,就是忘我、无己。如果一个人心里充满了个人成见,他就会处处与客观事物相对立、相抗衡,无法做到顺物而为。可以说,“忘”是贯穿于庄子学说中的一条时隐时现的思想主线。
古人早就慨叹“谈何容易”[18]2164,谈既不易,行则更难。“坐忘”要求忘却一切,包括庄子在内,没人能像木石那样做到绝对的恒久忘却,但短暂的、相对的、选择性的忘却,也即尽力忘却应该忘却的事情,通过努力或许还可做到。就像苏轼《定风波》讲的那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19]596记住舒心的吟啸,忘掉烦人的风雨。善于忘却,不失为一门难得的治国、生活艺术。
综上所述,对“忘仁义”“忘礼乐”的理解不能局限于狭隘的字面意思,应该把“坐忘”思想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体用关系的角度去诠释,将其与“忘心”“忘形”相对应,“忘仁义”即“忘心”,“忘礼乐”即“忘形”,“心体形用”是“坐忘”思想的基础,由“忘心”以达到“忘形”是“坐忘”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基本发展线索。在理清“坐忘”的理论逻辑基础之后,选择性地从“坐忘”思想中汲取有益因素,以为今天的生活服务,更是我们从事传统文化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