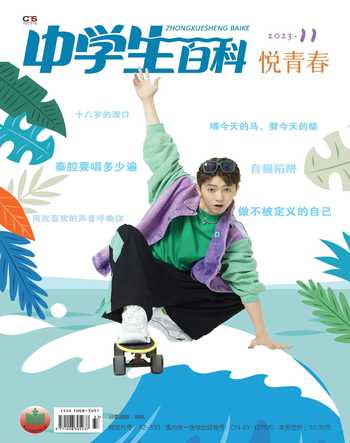当琴音消散
2023-12-14时暑
时暑
初中时走读上学,要经过一段种满合欢树的甬道。甬道旁边有一座琴房,時常响起练琴的声音。弹琴的人我认识,小学时曾帮我们代过几节音乐课。在甬道上骑车飞驰时,是我为数不多的与钢琴接触的机会,那空气中回响的琴声仍让我记忆犹新。
有一阵子,我总是听到相同的乐段——琴键反复敲击一个明亮的音符,然后逐渐爬升。如此明快、往复的节奏,让人的内心变得轻盈。但我不知道那首曲子的名字,后来朋友参加朗诵比赛,让我和她一起挑选背景音乐时,才知道那首曲子是《水边的阿狄丽娜》,弹奏者叫理查德·克莱德曼。
其实,在我知晓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姓名之前,已经在很多场合听过他的作品。学校的下课铃声是《爱的纪念》,听力考试前的试音是《梦中的婚礼》,就连常去的书店,也会播放他的作品来作背景音乐。想来,确实没有人的作品比他的更适配这些场景:熙熙攘攘的校园,屏气凝神的考场,浩如烟海的书店……他轻柔的曲风冲淡燥热,放松人们的神经,甚至在你打电话无人接听的时刻,其标志性的明亮音符也会抚慰你的失落。
理查德的作品,似乎永远跟优美、舒适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他受到音乐评论家诟病的地方——太过现代,缺乏严肃性。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理查德进入中国,是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后不久。他举止优雅,笑容温和,被称为“钢琴王子”。他的作品旋律简单,给了每一个没有系统学过钢琴的普通人接近音乐的机会;他的作品充满希望,与人们的心境相契合,成为鼓舞人的力量。正经学院派出身的他,选择拥抱新时代的音乐形式,创造出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风格。
后来我想,理查德的作品之所以能盛行于我的少女时代,大概因为那个时期正经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碰撞。
那时学校附近有几家大型书店,放学后同学们鱼贯而入,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一起向你涌来,宛如玛格丽特开满原野。我们三五好友会聚在一起,交流最近爱看哪本杂志,爱听什么乐曲,或是讨论成绩下滑、刘海下面生出痘痘等一些青春期的烦恼。
出门后,我将新书放进自行车筐,耳机里播放出《秋日私语》,一路心情舒畅地踏行。柔软的夕阳照着道路两旁的落叶,略薄的毛衫紧裹着手臂,我使出浑身的力气骑上坡顶。远处,新建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与此同时,我的膝盖开始隐隐作痛,好像有一根新的芽要从童年的躯壳中挣脱出来,走向新的未来。
就像那个世界。
如今,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热度早已消散,新的音乐和新的形式在数字屏幕中生根发芽。可当我回望我的少女时代,总能听见浪漫且充满希望的旋律,随风鼓满衣衫,送我到,另一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