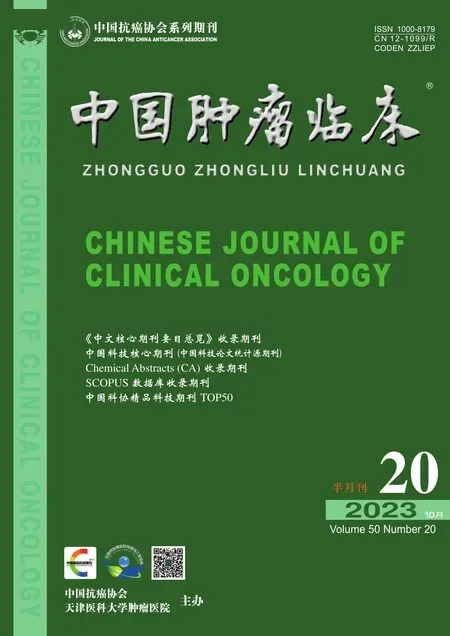髓外多发性骨髓瘤预后因素及治疗研究进展*
2023-12-11陈旭综述肖浩文审校
陈旭 综述 肖浩文 审校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由克隆性浆细胞异常增生引起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可引起高钙血症、肾功能损害、贫血、骨质破坏等症状。MM 病灶多数情况下局限于骨髓内,但有部分MM 患者的病变克隆性浆细胞会发展为软组织浆细胞瘤,并累及骨髓外器官/组织,称为髓外多发性骨髓瘤(extramedullary multiple myeloma,EMM)。EMM 是相对少见的骨髓瘤亚型,其发生、发展和治疗相比于骨髓内MM 具有特殊性。EMM 的发病率目前尚无统一数据。根据2018 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EBMT)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EMM 的发病率从2005年的6.5%总体上升至2014 年的23.7%[1]。近期总结分析显示,在新诊断的 MM 患者中,EMM 报告的发病率为 0.5%~4.8%,而在复发/难治性 MM(relapsed/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RRMM)中发病率为3.4%~14%[2]。
EMM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恶性浆细胞归巢受阻、侵袭力增强、细胞遗传学变异、肿瘤微环境变化以及浆细胞获得不依赖骨髓微环境即可恶性增殖的能力等方面有关。EMM 患者的预后较差,针对伴发EMM 患者的预后评估因素逐渐被重视。本文旨在对EMM 预后相关的预测指标及治疗进展进行归纳概述。
1 EMM 的预后因素
1.1 髓外疾病类型及数量
髓外病变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可分为原发性EMM 和继发性EMM,诊断MM 时即伴有髓外病灶称为原发性EMM,而在MM 治疗过程中发生髓外病灶的认为是继发性EMM,通常继发性EMM 的结局更差。有研究报道299 例伴发 EMM 患者的预后,其中95 例(32%)为原发性 EMM 患者,204 例(68%)为继发性EMM 患者,原发性EMM 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为43.2 个月,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为12.9 个月;继发性EMM 患者的诊断后中位 OS 仅为8.4 个月;初始治疗后的中位PFS 仅为2.9 个月[3]。
EMM 可发生在全身多个部位,在新诊断的患者中,EMM 多见于皮肤和软组织;而继发性EMM 受累的典型部位包括肝脏、肾脏、淋巴结、中枢神经系统、乳腺、胸膜和心包。其中,中枢神经系统EMM 相对罕见,但预后比其他部位的EMM 患者差,若发生软脑膜受累则预后更差[2]。根据髓外病灶发生的部位,可将髓外病变分为骨相关型EMM(EMM-bone related,EMM-B)和骨外型EMM(EMM-extraosseous,EMME)。其中EMM-B 指骨髓瘤通过破坏骨皮质直接浸润至邻近的软组织,EMM-E 则是骨髓瘤通过血行转移至不相邻骨病变的、不连续的内脏和软组织形成的结节、肿块或弥漫浸润器官。是否将二者均纳入EMM范畴目前尚有争议。Varettoni 等[4]的研究中仅将EMM-E 型定义为EMM,发现1 003 例新诊断MM患者(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NDMM)中有76 例(7.6%)为伴发EMM 患者,预后分析显示伴发EMM 患者的PFS 为18 个月,不伴EMM 的患者为30 个月(P=0.03)。Montefusco 等[5]的一项共纳入2 332 例NDMM 患者的大型荟萃研究,将EMM-B和EMM-E 型患者均纳入分析发现,267 例(11.4%)患者伴有EMM,比较伴发EMM 的患者与不伴有髓外病变MM 患者的预后发现,两组中位PFS 相似,分别为25.3 个月和25.2 个月(P=0.30)。未明确区分EMM-E 和EMM-B 患者类型,可能是导致不同EMM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EMM 确切定义尚未明确,狭义认为仅限于EMM-E 型,或称为严格定义的EMM(strict EMM,sEMM);广义的定义则还包括EMMB 型,两者的预后存在较大差异。Pourl 等[6]的研究分析对比了23 例EMM-E 型患者和32 例EMM-B 型患者的预后,结果显示EMM-E 患者的OS 明显短于EMM-B 患者(30 个月vs.45 个月;P=0.022)。虽然,髓外病灶的出现往往预示预后不佳,但单纯的存在EMM-B 病变位点似乎并不显著影响MM 患者的预后。一项分析伴发EMM 的患者临床基线特征对预后影响的回顾性研究,共纳入377 例NDMM 患者,其中80 例为伴发EMM 患者,结果显示,存在EMM-B的MM 患者(53/80)和无髓外病变的MM 患者具有相似的PFS 和OS,3 年PFS 率分别为48.6%和51.5%(P=0.662),5 年OS 率分别为59.2% 和51.7%(P=0.790),但髓外病变>1 处的EMM 患者的预后显著变差,3 年PFS 分别为28.1%,5 年OS 率为29.5%[7]。近期有研究将队列中的299 例伴发EMM 的患者,根据髓外病变发生的部位归类为内脏疾病组(157 例)和非内脏疾病组(142 例),并发现不论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EMM,内脏疾病组的OS 均低于非内脏疾病患者,原发性内脏疾病组的中位OS 为2.4 年,无内脏疾病患者为5.5 年,但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无显著性差异(P=0.17);继发性内脏疾病组患者的EMM 中位OS 为0.5 年,非内脏疾病患者的中位OS 为0.9 年(P=0.003)[3]。
1.2 分期系统及影像学
Durie-Salmon 分期、ISS 分期、R-ISS 分期系统等均在MM 患者的临床预后预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伴发EMM 这一特殊类型的MM 患者中检测其预后预测效能的相关研究有限。Zanwar 等[3]的研究表明ISS 分期对伴发EMM 患者预后仍具有肯定的预测价值。
随着MRI 及PET/CT 等较敏感的影像学检测技术的应用,EMM 的诊断率显著提高。潘博等[8]评估了21 例EMM 患者的PET/CT 显像发现髓外病灶的SUVmax 值异常增高且与骨髓病变SUVmax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ET/CT 通过一次检查即可评价全身骨骼病灶数量及髓外浸润情况,且具有较高敏感性,可为EMM 预后评估提供有力证据,被国际骨髓瘤工作组强烈推荐为评估MM 治疗反应的首选成像技术。
1.3 生化参数及血细胞分析
高血清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在血液肿瘤中可一定程度上反映肿瘤浸润及增殖程度,具有良好的预后预测价值。在Zanwars 等[3]的研究中,原发性EMM 患者队列中有33%(31/95)患者的LDH高于正常上限,危险因素分析证实LDH 升高与较差的预后相关(HR=2.6,P=0.02)。
正常人的血清游离轻链(serum free light chain,sFLC)含量极少,而MM 患者多伴有sFLC 增高,sFLC检测已被用于MM 的诊断。sFLC 水平在伴发EMM患者中的预后预测价值在Zanwar 等[3]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证实。在该研究中204 例继发性EMM 患者中,sFLC>100 mg/dL 与较差OS 的独立相关(HR=2.8,P=0.000 1)。
有研究报道血细胞计数的异常对伴发EMM 的MM 患者的预后具有潜在预测价值。在杨建柱等[9]的EMM 患者小规模数据分析中,单因素分析显示,血红蛋白<118.8 g/L,白细胞<5.92×109/L、淋巴细胞绝对值<1.72×109/L 是影响PFS 的不良预后因素,红细胞<3.86×1012/L、血红蛋白<118.8 g/L、淋巴细胞绝对值<1.72×109/L 及骨髓中浆细胞比例≥13%是影响伴发EMM 患者OS 的不良预后因素,但多因素分析证实仅白细胞<5.92×109/L 是影响PFS 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血红蛋白<118.8 g/L 是OS 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Zhang 等[10]通过对217 例伴发 EMM 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建立了一个EMM 患者预后预测模型。其中,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和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值(monocyteto-lymphocyte ratio,MLR)被纳入为该预测模型的核心指标,其认为NLR≥4.2 和MLR≥0.32 的EMM 患者生存率较低,且在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中,MLR 仍然是OS 的独立预后因素。
1.4 细胞遗传学
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in situhybridization,FISH)细胞遗传学检测已逐渐成为MM 的常规评估手段。贾静等[11]的研究显示携带高危遗传学异常是中枢侵犯EMM 患者的不良预后因素,中位生存时间较标危患者显著缩短(7 个月vs.24 个月,P=0.007)。Zanwars 等[3]研究提示MM 诊断时携带1q gain/amplification 和t(4;14) 是发生继发性EMM 的独立危险因素,1q gain/amplification 和t(4;14) 在原发性和继发性EMM 患者中均具有独立的不良预后预测价值。付庆华等[12]对原发性EMM 患者的预后分析发现,在具有TP53 基因检测结果的54 例患者中,4 例患者存在TP53 基因缺失,多因素分析显示TP53 突变为伴发EMM 患者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HR=3.697,95%CI:1.015~13.469,P<0.05),但考虑到该研究阳性样本量较小,其结果可能存在偶然性。
Ki-67 增殖指数在MM 患者中的预后预测价值已较明确,其在伴发EMM 患者中的预后价值还需进一步评估验证。陈婷等[13]检测分析了21 例伴发EMM 患者的髓外病变组织和骨髓组织的Ki-67 增殖指数,发现髓外病变组织的 Ki-67 增殖指数较骨髓组织显著增高(P=0.019)。贾静等[11]在MM 伴中枢侵犯患者队列研究中发现,骨髓活检Ki-67 指数>50%是MM 中枢侵犯的不良预后因素,表明Ki-67 可成为预测伴发EMM 患者预后的标志物。
1.5 骨髓瘤细胞负荷
骨髓瘤细胞负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EMM患者的预后。晁瑶等[14]研究提示骨髓中浆细胞≥60%是影响伴发EMM 患者PFS 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该指标在单因素分析中与OS 不良预后相关,但在多因素分析中未显示对OS 的显著意义,不排除样本量偏小的缘故。由肿瘤细胞释放到血液中的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ur DNA,ctDNA)已在MM 患者的预后评估中崭露头角。ctDNA 的检测也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非侵入性肿瘤负荷的标志物用于动态评估EMM 的克隆演变,具有伴发EMM 患者预后预测的潜质。
2 EMM 的治疗
2.1 新药治疗
EMM 的治疗目前尚无统一指南和共识。作为目前一线抗骨髓瘤药物,免疫调节剂(immunomodulatory drugs,IMiDs)和蛋白酶体抑制剂(proteasome inhibitor,PI)也是EMM 治疗的一线用药。相对传统化疗(如烷化剂、类固醇),免疫调节剂和蛋白酶体抑制剂的使用有助于改善EMM 患者预后[5]。即使髓外病灶出现在中枢神经系统,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亦具有一定疗效。
2.1.1 免疫调节剂 沙利度胺是第一代免疫调节剂,其对EMM 治疗有限。来那度胺是沙利度胺的类似物,研究表明其对EMM 患者的治疗有效,可能与来那度胺具有更强的细胞毒性作用及免疫调节功能有关。一项大型荟萃分析共纳入267 例原发性EMM 患者(EMM-B 型243 例,EMM-E 型12 例,未分类12 例),其中166 例 EMM 患者接受了基于免疫调节剂(均为来那度胺)的治疗。结果显示,与接受相同免疫调节剂治疗的1 279 例非EMM 患者比较,两组之间的PFS无显著差异[5]。Calvo-Villas 等[15]的研究回顾性收集研究了18 例伴发EMM 患者,自出现髓外病变后均接受来那度胺加地塞米松的联合治疗方案,8 例患者额外接受浆细胞瘤的放疗,结果显示77%的患者髓外病变得到缓解(46% 达CR),中位OS 为11 个月,中位PFS 为9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 年)。
泊马度胺作为第三代免疫调节剂,在抗EMM 治疗方面的疗效尚存争议。Mayo 诊所早年发布的一项评估泊马度胺加小剂量地塞米松治疗RRMM 的Ⅱ期临床试验结果,该研究共纳入174 例RRMM 患者,其中13 例伴发髓外疾病,结果显示伴发EMM 患者的总缓解率为31%(2 例CR,2 例PR)[16]。另有研究则显示泊马度胺对晚期EMM,特别是对既往多重耐药的EMM 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局限。有报道评估了泊马度胺联合地塞米松对EMM 患者的疗效[17],该研究共收集分析了21 例EMM 患者,其中38%的患者为EMM-B 型,38% 患者为EMM-E 型,另外24% 的患者两类病灶均有,所有患者之前均接受过以硼替佐米和来那度胺治疗为主的方案治疗。结果显示仅有2例EMM-B 型患者(9%)接受泊马度胺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后病情得到缓解,EMM-E 型患者均无反应,从泊马度胺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开始的中位PFS 仅1.7 个月,中位OS 为4.5 个月。
2.1.2 蛋白酶体抑制剂 硼替佐米是一种合成的二肽硼酸盐,能够抑制胰凝乳蛋白酶的酶促作用,促进骨髓瘤细胞凋亡,具有可逆性和选择性,可一定程度克服t(4;14) 或 del(17p) 等高危因素的不良预后影响,是目前推荐的EMM 患者一线治疗药物。有报道早年发布的一项评估含硼替佐米的3 药方案在MM 患者中诱导疗效的3 期临床研究,该研究共纳入207 例MM 患者,其中70 例患者伴有髓外病变,结果显示伴发EMM 患者在诱导过程中疾病进展率高于不伴EMM 患者(24%vs.11%,P=0.01),但相较于沙利度胺联合地塞米松治疗组(TD),接受硼替佐米与沙利度胺和地塞米松(VTD)治疗的患者,疾病进展率显著下降(12%vs.40%,P=0.02)[18]。
卡非佐米是第2 代蛋白酶体抑制剂,其在对硼替佐米和免疫调节剂治疗耐药的RRMM 患者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治疗作用。一项评估含卡非佐米方案治疗伴发EMM 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表明,基于卡非佐米的治疗方案在继发性EMM 患者的治疗中显示出一定的疗效。该研究纳入45 例接受卡非佐米治疗的EMM 患者,20 例(44%)为 EMM-B 型,25 例(56%)为 EMM-E 型,在接受含卡非佐米治疗方案后,59%的患者出现血清学应答,在可评估髓外病灶治疗反应的33 例患者中,9 例(27%)得到缓解,中位PFS 和OS 分别为5 个月和10 个月[19]。目前尚缺乏卡非佐米伴发EMM 患者疗效的大样本临床研究。从现有的临床研究看,基于卡非佐米的方案对伴发EMM 患者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但是卡非佐米和哪些药物联合应用于伴发 EMM 患者可获得更好疗效,以及后续的巩固和维持治疗方案等仍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伊沙佐米是第一种口服的蛋白酶体抑制剂,相较于硼替佐米,伊沙佐米半衰期更短,组织渗透性更强,对硼替佐米耐药的RRMM 患者仍然具有较好疗效。当前针对伊莎佐米对伴发EMM 患者疗效评估的研究数据较少,部分个案报道了伊沙佐米联合免疫调节剂和地塞米松的方案具有高效、安全的特性[20]。但因缺乏真实世界数据及对照研究,伊沙佐米对伴发 EMM患者的疗效还需进一步评估验证。
2.2 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如CD38 单抗daratumumab、isatuximab 和SLAMF7 单抗elotuzumab 可针对MM 细胞所表达抗原形成特异性杀伤,为RRMM 的治疗提供新的选择。评估单克隆抗体对EMM 患者疗效的研究较少。Usmani 等[21]的研究提示daratumumab 能够改善EMM 患者预后。该研究共纳入148 例RRMM 患者,其中18 例为伴发EMM 患者,多数患者前期对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治疗均耐药,在接受daratumumab 治疗后,总反应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达到31.1%,EMM 组患者的ORR 为16.7%(95%CI:3.6~41.4)。有研究分析了41 例对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耐药的RRMM 患者,其中13 例为伴发EMM 患者,在接受daratumumab 治疗后,ORR 为24%。但所有患者均出现疾病复发,中位PFS为1.9 个月。Isatuximab 可通过凋亡途径和溶菌酶相关途径诱导MM 细胞的死亡[22]。Attal 等[23]的一项随机Ⅲ期研究中,在泊马度胺-地塞米松的基础上加入isatuximab 可显著延长RRMM 患者的PFS(中位PFS:11.5 个月vs.6.5 个月)。SLAMF7 单抗elotuzumab已用于RRMM 的治疗,目前仅有elotuzumab 治疗EMM 患者疗效的个案报道。有研究报道了1 例经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病情复发的伴发EMM 患者,即使接受含有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daratumumab 等的治疗方案均无效,但在接受elotuzumab 联合来那度胺、地塞米松(E-Rd)的方案治疗8 个周期后,疾病缓解,髓外病灶消失。贝兰他单抗莫福汀(belantamab mafodotin)是一种与小分子细胞毒素结合的重组单克隆抗体药物,可与肿瘤细胞表面的BCMA 特异性结合,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RRMM[24]。在Trudel 等[25]的临床试验研究中,接受贝兰他单抗莫福汀治疗的35 例RRMM 患者,ORR 达到60%,中位PFS 为12 个月。
2.3 造血干细胞移植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SCT)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髓外病灶的不良预后影响,改善伴发EMM 患者的预后。有报道对伴发EMM 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130 例为原发性EMM 患者,接受ASCT 治疗的患者(n=67)中位PFS 显著延长(49 个月vs.28.1 个月,P<0.001)[26]。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工作组(EBMT)发布的一项评估伴发髓外病灶对接受ASCT 的NDMM 预后影响的研究,该研究共纳入3 744 例接受了一线ASCT 的MM患者,其中682 例为伴发EMM 患者,结果显示伴发单部位EMM 病变的患者与不伴髓外病变的患者,3年PFS(47.9%vs.50.0%)和3 年 OS(80.1%vs.77.7%)均相似,但伴有多部位髓外病灶的EMM 患者3 年PFS 仅为22.7%[1]。对于移植方式是否能影响EMM患者的预后尚存争议。前述EBMT 的研究[1]认为两次ASCT 序贯移植和单次ASCT 移植相比,对伴发EMM 患者的PFS 和OS 无显著影响(P=0.13)。但有报道在分析了488 例接受ASCT 治疗的伴发EMM患者的预后,认为与单次ASCT 相比,串联ASCT 移植改善患者预后的作用更加显著(P=0.03),而单次自体移植与自体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相比,PFS和OS 无显著性差异[27]。
伴发EMM 的患者,即使接受ASCT 治疗,仍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有报道显示原发性EMM 患者在单次ASCT 后的累计复发率为54%,在序贯ASCT 后为47%,在自体联合异基因移植后为30%[1]。一项研究使用异基因HSCT 作为一线治疗或在复发时作为挽救治疗,该研究队列的1/3 的患者为移植时伴发EMM 患者,49% 的EMM 患者出现髓外复发[28]。尽管其机制尚不明确,该现象可能与EMM 肿瘤微环境的改变及ASCT 后药物治疗的耐药性增加有关,移植时疾病状况的恶化也可能是增加EMM 患者髓外复发风险重要原因[29]。
2.4 CAT-T 治疗
近年来,嵌合抗原受体T 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CAR-T)免疫治疗的创新应用,为EMM 患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Raje 等[30]报道了靶向BCMA 的CAR-T 细胞疗法对RRMM 患者治疗的1 期临床试验结果。该研究共纳入33 例RRMM患者,27%(9 例)为伴发EMM 患者。所有患者的ORR 为85%,45% 患者取得完全缓解,中位PFS 期为11.8 个月,进一步亚组分析提示,伴发EMM 的患者中88%(8/9)的患者获得缓解。一项关于BCMA CAR-T 细胞治疗RRMM 的荟萃分析显示,纳入285例患者,CAR-T 细胞治疗后的ORR 率为82%,微小残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阴性率达77%,而EMM 疾病的存在并不影响患者的治疗反应率[31]。近期一项评估CAR-T 细胞治疗对EMM 患者髓外病灶治疗疗效的研究中,20 例继发性EMM 患者接受了CAR-T 治疗,总缓解率为75%,中位PFS 为4.9 个月[3]。

表1 评估伴发EMM 的MM 患者治疗研究总结
3 结语
通过对伴发EMM 患者的病例研究,目前已发现多种临床因素和实验室指标对伴发EMM 的MM 患者的生存率和预后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髓外病灶的位置和数量、基于宿主和肿瘤因素的分期系统、部分血细胞及生化参数、染色体异常和肿瘤细胞负荷等。基于这些预后指标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评估。但由于EMM 是一种罕见的疾病,研究中往往存在样本量有限的问题,这限制了对该疾病预后因素的全面研究。预后因素的研究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评估方式,也导致不同研究之间的结论差异较大,增加了研究结果的解读复杂性。未来仍需通过多样化的样本群体,扩大样本数量,进一步验证和确认已有的预后评估指标,并探索新的预后评估因素,以帮助医生更好地改善患者预后。EMM 治疗方案的选择,目前研究结果的可用数据几乎完全来自回顾性研究。基于新靶向药物的治疗方案已经显示出一定的疗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CAT-T 细胞治疗等也显示出具有前景的疗效,但由于缺乏前瞻性对照研究,尚不能提出统一推荐的治疗方案,伴发EMM 患者的治疗仍面临巨大挑战。
本文无影响其科学性与可信度的经济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