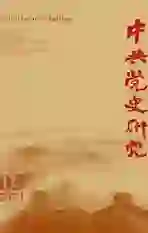自我与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新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转向
2023-12-11李志毓
李志毓
〔摘要〕20世纪20年代,数以万计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知识女性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她们在革命潮流中接受了国民意识的启蒙,也经历了“自我”的创伤和“解放”的失落,在实践中认识到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由追求个体解放转向投身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新知识女性的革命实践与主体成长,反映了“五四”新青年对于新生活、新人格的不懈求索,代表着新的历史主体与文化价值形成的过程。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理解中国革命动力的产生、革命队伍的集结和革命主体的形成,也有助于立足中国经验,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性、价值建构等问题。
〔关键词〕自我;革命;新知识女性;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D442.9;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5-0034-13
Self and Revolution: A Shift in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Chinas New Intellectual Women in the 1920s
Li Zhiyu
Abstract: During the 1920s, influenced by the ideologie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any intellectual women emerged from the domestic sphere to participate in revolutionary endeavors. They received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midst the revolutionary tide, concurrently undergoing the tribulations associated with “self” and the disillusionment of “liberation.” Through practice, they perceived the imperative need for a radical overhaul of Chinese society, shifting from seeking individual liberation to contributing to classbased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s. The revolutionary engagement and subj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se intellectual women reflect the persistent pursuit of new lifestyles and identities by May Fourth new youth, symbo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historical subjects and cultural values. Investigating this transitional phase of development is favorable for comprehendi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mentum,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and the molding of revolutionary entities.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insights into deliberations on individual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based on experiences derived from Chinese history.
20世紀20年代,数以万计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知识女性为寻求自我解放,投身国民革命。革命政权向她们敞开职业大门,为“娜拉”走后摆脱“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的困局、实现自我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新知识女性自觉突破“五四”个人解放话语,由争取女性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走向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并在变革社会政治同时,提出了变革主体自身的要求。她们从追求个人幸福、自我解放,到甘愿为大众的幸福而牺牲自我,为与工农结合为一个更大的战斗集体而不惮于批判自我、改造自我,代表的是更广大的新知识青年群体革命化的过程,反映出“五四”新青年对于新生活、新社会、新人格的不懈求索。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革命动力的产生、革命队伍的集结和革命主体的形成。
关于新青年的革命化,有以下三种论述产生过较大影响。一是“救亡压倒启蒙”说。该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以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启蒙实现社会进步,但其目标所指仍是国家政治,最终在国家利益和人民疾苦面前,政治救亡主题全面压倒了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启蒙主题。个体的我在革命中是渺小的,它消失了。(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46页。)二是对20世纪20年代青年“烦闷”议题的探讨。有学者指出,“烦闷”的本质是传统秩序解体时代青年对于“意义”的苦闷,“主义”提供了一套意义系统和解释框架,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在政治中解决了人生问题。“主义”不仅关乎救亡,还重构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意义感和世界理解,同时造成了“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现象。(参见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知识分子论丛》2015年第1辑。)三是女性主义论述。一些研究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的走向之一,是对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的追求,最终为民族解放和国家政治目标所覆盖(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早期中国的女权运动“确曾触及挑战社会性别权力等级关系议题”,可惜“这类议题很快在国家民族主义话语、党派政治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笼罩下被边缘化了”。参见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6页。)。这是一个“从风起云涌的高潮跌到低谷,乃至受政治拨弄的历史变化过程”,一个从“女性解放”渐渐“走进国家”的过程(柯惠玲:《她来了:后五四新文化女权观,激越时代的妇女与革命,1920—1930》,台湾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页。)。
以上论述各有侧重,但都指向一个问题,即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国族、政治对于个体权利、欲望,乃至价值和创造力的“压抑”,并引发了关于后革命时代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及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国族、政治关系的思考(参见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读书》2016年第2期;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90—108页;等等。按:“救亡压倒启蒙”说还包含两个相关的认识判断: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启蒙”能否充分落实,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二是由于历史的“偏差”,只有回头补上自由民主这一课,中国才能重新回到健康的现代化道路上来。至于新文化运动所召唤的“个人主义”有哪些具体内涵,启蒙价值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生长出了怎样的实际形态——这些内在于历史的真问题,却并非“救亡压倒启蒙”论述所关注的重心。)。本文将继续讨论这一关乎中国现代性展开的重要问题,以20世纪20年代新知识女性从追求自我解放到投身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转向为中心,探讨新青年革命化的历史逻辑,重视历史语境与个体的身心经验,关注她们在实践中的困境、磨砺和主体成长。新知识女性的实践表明,中国革命历史时期的救亡和启蒙、政治和个人、国族和女性等范畴,并非当代个人主义话语理解下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五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打造一个真诚勇毅、尊重个体、有感通能力、能自度度人的“新青年”群体,作为改造中国的历史主体,同时开启了建立中国现代个体和现代国家的议题。新知识女性自觉投身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革命运动,经受磨砺、考验,实现自我成长,代表了一种面向政治和现实开放、不断吸纳外部经验以形成更大“自我”的主体实践。研究她们的生命实践,有助于超越个人主义和身份、性别政治,基于中国实际经验,思考个体和国族、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而去想象和践行一种抱诚守真、刚健不挠、有反思能力、能不断突破自我本位的经验和认识,以及向广阔人类世界开放的现代“自我”。
一、参加革命与解放“自我”
20世纪20年代参加国民革命的知识女性,多接受过中等程度的新式教育。她们离家出走的动机主要是逃避包办婚姻。北伐时期曾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的黄慕兰,出身湖南浏阳一个开明士绅家庭,父亲是谭嗣同的同窗好友。黄慕兰自幼没有缠足,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可与父亲平等讨论问题。她说:“如果家庭给我包办的婚姻称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坚决地走出家庭参加革命,而且又适逢其会地立即投身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当时的知识女性,“大半是为了反对包办婚姻的封建压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以《从军日记》闻名的女作家谢冰莹同样如此。鼓动她当兵的二哥对她说:“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参加革命,婚姻问题和你未来的出路问题,才有办法。”她说:“我相信,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找寻自己的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军服,拿着枪杆,思想又不同了,那时谁不以完成国民革命,建立富强的中国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呢?”(艾以、曹度主编:《谢冰莹文集》(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逃避包办婚姻,并不等同于追求自由恋爱或创造基于情感体验的幸福生活。尽管确有一些新女性因追求自由恋爱而进入小家庭生活,但还有一些女性力图冲破家庭生活的狭窄空间,在更开阔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塑造新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质。对于后者而言,爱情的吸引力诚然强烈,却不值得因沉溺其中而牺牲前途。謝冰莹在长沙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生平第一次遇到有一个异性的影子”闯进脑海,盘旋不去,这种感情带给她强烈的痛苦。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牺牲我的前途,我不能毁灭我的生命,努力挣扎吧!从苦海中救出自己!……不要忘记了你是个非凡的女性,不要忘记为求学而自杀的苦心。继续奋斗呵,你应该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艾以、曹度主编:《谢冰莹文集》(上),第57页。)谢冰莹努力拒斥的是基于情感结合的新式家庭,在尚不具备独立经济能力的时候,这会让她失去独立的社会生活,陷入逃离大家庭之后的又一重束缚。
正当谢冰莹苦闷挣扎之时,北伐战争的号角声传到了湖南。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随即成立。学校首开先河招收女兵,这是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谢冰莹得到这一消息后,与200多名青年男女踏上长沙开往武昌的列车,对婚姻和爱情的苦闷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她描述投考军校途中的情景:50多名女同学挤在一节货运车厢里,齐声唱起歌,男同学听到也接着唱起来,歌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像疯了似的在狂笑,在高歌,在跳跃……”一位女生在反对军校复试的运动中说:“我们脱离了家庭来献身革命,目的是在救出痛苦的民众和痛苦的自己……政府既然把男女一同看待,使我们也有效命国家民众的机会,那是我们妇女的幸福,人类的光明。”(艾以、曹度主编:《谢冰莹文集》(上),第61、68页。)
女性飞出樊笼,是为了成为充分发展的、于社会有用的人。这条长路的起点是经济自主,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国民革命解决了女性独立最要紧的经济问题。左翼作家师陀在1934年创作的小说《鸟》中这样描述新女性投身革命的时代潮流:“大事变之来,往往由不得自己,风势向什么地方吹,人就向什么地方滚。大家都这样,便铸成一种勇气和力……那时代不同后来;只要伸出两手往上爬,只要胆壮一些,是不愁皮带披不到肩上的。于是同学们都小鸟一般尽量往外飞。”“那时代张大着嘴,只贪婪的需要人:什么县城里,什么后方医院里,军队中的什么部里,处处都向那大的都市招手,永不会餍足。”(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1卷(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鸟》的主人公易瑾,一个小杂货商的娇养女儿,此时也和同学们一起离校,到小县城做“委员”去了。
易瑾的形象塑造有其现实依据。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湖北省各县开始组织党部,两湖女子师范的女生纷纷离校去县城参加革命。至1927年初,各县农民协会、总工会及各行业工会、妇女协会相继成立。县党部、青年团、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工会、农会中都有女生任职。(参见《孝感市文史资料》第6辑,1989年印行,第123—124页。)在档案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些人的经历,如陈家瀛,考取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党务培训班,1927年被中央妇女部介绍到武汉军事裁判所工作(参见《中央妇女部致革命军事裁判所函》(1927年7月9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部”13913。);吴静贞,丈夫病故,遗产被夫兄剥夺,因生活无着参加妇女培训班,被介绍到武汉军事裁判所工作(参见《吴静贞上中央妇女部何香凝函》(1927年3月)、《中央妇女部致军事裁判所函》(1927年8月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部”13888、13920。)。
1924年至1927年间到底有多少女性参加革命,很难得到准确的数字。例如,成立于1925年5月的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在1926年6月拥有多少会员?广东省党部妇女部报告,有5000余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报告,有1500余人;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第三届执委报告,有3000余人(参见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1991年印行,第271、281页;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6页。)。当时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不健全,上级黨部无法准确掌握基层党部工作情况,因此这种误差现象比较普遍。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提到,他们曾派人到各地宣传党义、组织妇女团体、制定工作状况调查表分发各县妇女部进行调查,并要求各县每两个月将工作情况报给省党部,可却多次遭遇“屡发通告函件均置诸不理”的情况(参见《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第326页。按:关于国民党基层组织情况,还可参见王奇生:《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革命政权的扩大,国民党党员总数迅速增长,各地女党员和妇女团体数量也显著增加(参见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1册,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第148—149页;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民国政府卷》(上),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年,第100—101页。)。根据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报告,1924年国民党在全国共有女党员2000余人,到1927年3月超过1.3万人(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55、100页。)。还有研究表明,1924年12月广州市国民党员共15835人,女党员381人,占总数的2.4%;女党员中有244人来自学界,占64%(参见吕芳上:《娜拉出走以后——五四到北伐青年妇女的活动》,《近代中国》第92期(1992年12月)。)。到1927年初,国民党号称全国党员超过100万,女党员约占1.3%(有学者指出,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半年间,国民党党势极大扩张。1927年4月,广东、江苏、上海、长沙四省市党员总数已达47万余。根据这些省市党员人数增长率推算,全国党员总数100万余当非虚夸。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9—41页。)。
革命政权为新女性敞开职业大门,更明确支持女性摆脱旧式纲常伦理束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倡导妇女解放。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女子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等主张(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女子有财产继承权,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原则制定婚姻法,开放行政机关容纳女子入职(《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民国政府卷》(上),第78页。)。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宿舍门前大幅对联写着“斧钺纲常”,斩钉截铁地表示了向旧礼教宣战的决心(参见谭勤先:《中国女兵的感情世界——我党领导下第一代女兵的述说》,《国防》1995年第3期。)。和“斧钺纲常”一同出现的,是“浪漫女性”成为大革命的一道风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队长的朱其华,曾在回忆录中记述一位同时与三个男性恋爱的女秘书,认为“这决不是党国之耻,而是党国之光!我们应该自豪……这是表示我们至少已经相当的战胜了封建意识”(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第39页。)。
向警予曾将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女性分为小家庭派、职业派和浪漫派,并认为“五四”新女性多属浪漫派。她们的特点是:对现实社会一点一滴都不满意,却不负破坏或建设的责任;无偶像,无信仰,睥睨一切,唯我独尊;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快乐;一举一动纯任自然,将“做人”与“向上”斥为虚伪;在“社交公开”“自由恋爱”的口号下过着游荡飘忽的生活,并以为“这就是妇女解放”。她们“从未与社会接近,也从未受过意志的锻炼”,所以一接触现实,遇到打击,就灰心丧气、偃旗息鼓。当然,向警予不仅看到“浪漫女性”身上的弱点,也看到她们觉醒的自我意识和对真挚人格的要求,以及由不满走向革命的可能,因而真诚盼望她们能从知识、意志、人格方方面面改造自己。她说,“浪子的心是颗宝”,一旦觉悟,“努力改变浪漫的性质,把伊们自己的言论实际应用到事实上去,而且注重意志的锻炼和知识的培养,伊们也许可做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前锋”(参见戴绪恭、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1—153页。)。
国民革命吸收了很多“浪漫女性”,她们多在妇女部、政治部等机关任职。1927年曾在武汉政府任职的女作家白薇描写过她们的形象。茅盾早期的小说也塑造了一批革命队伍里的“浪漫女性”形象,最典型的当数1927年至1928年间创作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中的主人公。她们彻底打破了贞操观念,在两性关系中热烈开放,令那些贤淑女子相形失色。有学者从女性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她们既是欲望主体,也是人格主体,颠覆了性别权力关系,反映出茅盾的女性主义立场。(杨联芬:《茅盾早期创作与女性主义》,《厦门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目标之一是控制自己的感官享受,由男性欲望的客体反身成为欲望的主体。正如美国性别研究学者阿莉森·贾格尔指出:“激进女权主义政治最紧迫的目标就是为女性重新获得她们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美〕阿莉森·贾格尔著,孟鑫译:《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9页。)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后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程度高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妇女解放实践,前者提出了女性的自我发展、身体自主等议题,肯定了自然人性和欲望的正当性,后者则在强调男女平等同时,更关注国家、社会等整体性目标。
然而,以西方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中国革命,不能忽视战后西方历史语境与中国革命历史语境之间的距离,以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权诉求与后五四时代新知识女性的解放斗争在身心经验、行为逻辑和政治目标上的差异。历史研究的意义正在于力图回到历史情境当中,把握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以打破从当下观念和话语系统出发建构的历史想象,从而将历史实践转化为历史认知,真正变成我们的历史经验。在反思大革命的语境中,茅盾作为亲历者塑造的“浪漫女性”形象具有怎样的历史认识价值?国共两党的激进妇女政策和茅盾等人的文学实践所共同构造的“浪漫女性”话语与大革命女性真实经验之间有着怎样的张力?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真诚—创伤”逻辑与个体解放的困境
国民革命中激进的妇女政策和“斧钺纲常”的伦理实践是否构筑了两性平等?欲望自主的摩登女性是否体验着真正的身心解放?革命潮流中的“娜拉”经历了怎样的真实人生?茅盾在作品中留下了他的观察与反思。文学形象是基于特定话语系统对于社会现实的想象性建构,不能直接还原为客观实存的历史真实。但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学书写却有着相当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历史认识价值。作为早期中共党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武汉中山大学讲师和《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他亲历大革命的开展和失败,试图通过描写他最熟悉的群体反思那个变动的时代。他的创作活动本身即是一种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实践。(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83页。)
关于《蚀》三部曲的女性形象塑造,茅盾说,1926年上海有几位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这幻想便让她们参加了革命;也有人在生活上碰了钉子,便愤愤然要革命,“她对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点怀疑的心情。”怀有这样思想意识的女性也出现在武汉,并且性格更加鲜明。大革命失敗,茅盾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于是便以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女性作为《蚀》三部曲的主角。不过,他“没有写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参见《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38—442页。)
茅盾对于新女性的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笔下的“浪漫女性”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现实?曾有学者指出,《动摇》中孙舞阳一类的女性形象具有抽象性,缺乏现实依据。她们特立独行,不受社会关系羁绊,“仿佛生活在激情的历史里,逸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既带有苏俄革命胜利初期“杯水主义”的色彩,又有英法“颓废”文学中的“尤物”的影子。(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身处大革命血腥残暴、光怪陆离的背景中,这样的女性形象既给都市小资产阶级读者带来刺激,也“折射出一个男性作家的革命想象与疑虑、苦闷与希望”。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一度脱党,以撰稿为生,其创作既臣服于印刷资本的商业机制,又有心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预想读者(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第8—9页。)。那些欲望主体的塑造或许也和这种处境相关。
但正是这种带有想象性的将女性能动性与开放性推至高峰的文学形象塑造,反过来显示出以欲望觉醒、身体自主为表征的妇女解放话语的迷思。《追求》中的章秋柳是“浪漫女性”的极致,是放浪人间、热烈爽朗的唯我主义者,身体解放也很彻底。她不愿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也不能完全抛开享乐生活,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然而当大革命失败,理想中的热烈生活仅剩下纵欲无度时,她反观自己“在污泥中挣扎似的生活”,难免心中“充满了寂寞和荒凉”,分不清究竟是快意还是无聊,最终不得不承认,“所谓快意者,到过后思量仍不过是悲凉而已”。(参见《茅盾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69页。)
茅盾笔下的“浪漫女性”是可爱的人,也是受伤的人。她们身体健康,充满激情,有向善的焦灼,却往往所遇非人。她们目睹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不愿投降魍魉世界,又不能投身工农革命。她们解放了身体,但绷紧了神经,精神极度苦闷,毅然决然而无处施力,出路与绝路形影相随。与其说茅盾推崇女性主义,不如说他看到,女性作为欲望的投射物,在社会动乱中承受着可怕的暴力,反身成为欲望主体并不能改变女性的真实处境,欲望的追逐不是妇女解放的标志而是迷途。更重要的是,透过“浪漫女性”的挣扎和迷茫,他写出了个人解放的历史困境,反映出对“五四”话语的深刻反思。与向警予一样,茅盾在“浪漫女性”身上看到的也不仅是欲望觉醒和身体解放,更是一种觉醒的内在“自我”和真诚、反抗的人格,以及这种真诚的“自我”在现实中无路可走的扭曲和畸形发展。
《幻灭》中慧女士的浪漫,起于男性对她的伤害。她说:“像我,在外这两年,真真是甜酸苦辣都尝遍了!现在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但是我倒因此悟得处世的方法。我就用他们对待我的法子回敬他们呵!”(《茅盾全集》第1卷,第9—10页。)慧女士是刚强狷傲的人,当她第一次被男性欺骗后,就打定了报复的决心。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没有爱,对于过去只是愤怒,没有悔恨。她跳出了道德的圈套,无视旁人的讥笑。然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是一种有出路的反抗。事实上,她在内心深处仍然渴望着男性的真心对待和一个以婚姻为保障的“终身归宿”。她的浪漫不过是抚慰受伤心灵的无奈之举,失落的伤痛更多于解放的愉悦。
“真诚—创伤”的逻辑在《一个女性》中得到再现。琼华以诚挚光明待人,得到的是欺骗,她藏起“真我”,用私心鄙弃的“假我”待人,却在社会上高高升上去。她由憎恨现实到为现实所同化,“想不出一条路给自己勇敢的活着,没有勇气在这罪恶的世间孤身奋斗了”(《茅盾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2—84页。),最终被社会遗弃,悲惨地死去。扼杀她的不再是旧礼教,而是受新式教育的青年结成的社会,它复制了旧社会的虚伪、残酷,仍是覆灭“真我”的泥潭。
“五四”知识分子痛感传统礼教秩序僵化、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渴望去伪存真,建立一个尊重人性、人人平等、具有感通力的新文化和新青年主体。叶圣陶说他写小说是想暗示“人与人的隔膜不是自然的,不可破的”,有一天“大家会赤裸裸地相见。到时,各人相见以心不是相见以貌”(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茅盾则以天真洁白的女性被男性摧伤的命运,喻示了真诚的“自我”在腐恶社会现实面前遭受的伤害,写出了“五四”个人解放话语的局限,呈现了新女性在动荡、匮乏的半殖民地社会里的挣扎和无所适从。“(她们)是被觉醒了,是被叫出来了,是在往前走了,却不是到光明,而是到黑暗!呐喊着叫醒青年的志士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光明幸福的社会来容纳那些逃亡客!”(《茅盾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大革命失败后,还有许多像茅盾一样关注与思考新知识女性的命运和出路,并付诸文学实践的作家。师陀小说《鸟》的主人公易瑾在“一九二×的波涛”中投身革命,六七年间,“她由白褂青裙而军服,由军服而短袍,再改穿长袍”。她受到所谓“同志”的蹂躏和侮辱,虽计划过复仇,可是总没有机会,也想到过自杀,又怜惜自己的生命。她的未婚夫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下落不明,她前后有过三个孩子,但都不曾出世,自己的路也越走越狭。她原想做一番事业,“后来就单单希望一个惬意的丈夫”,再后来只望别人不要将她随随便便抛弃。最终,遇到“裁员减费”,竟连一个“可以马虎下去”的职位也丢掉了。小说情节至此终止,师陀没有为他的主人公想到一条出路。(参见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1卷(上),第283—298页。)
师陀1910年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大革命时期在开封读中学,大革命失败后,他亲眼见到很多同学被捕,后来写过几篇大革命后青年探寻出路的小说。1931年,他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同年以芦焚为笔名投稿给《北斗》,得到主编丁玲来信鼓励,并拒绝了信中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左联的邀请(参见解志煕、刘增杰编:《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65—369页。)。与茅盾的视角不同,师陀无意塑造自主的摩登女性,他准确把握了大时代面前人们随流沉浮的现象,塑造了一个思想较盲目、性格较软弱的女性形象。易瑾投身革命有追隨潮流的性质,但与身边各种龌龊的男性和放浪的女性相比,她仍是真诚善良而有所持守的人。师陀揭示了革命队伍中的女性不仅受到来自敌人的威胁,还会遭受身边男性的伤害,除非再起革命、根本改造社会,否则她们仍是无路可走。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贫穷、动荡,女性普遍被局限在家庭生活中,人们往往将革命队伍中的女性陷入各种恋爱关系视为“浪漫”。谢冰莹就是时人眼中的“浪漫女性”。她晚年说:“两个人一定要有爱情……要合不来的呢,不要勉强,就离婚,分开。我的思想是很新的……所以后来很多很有名的人都骂我说谢冰莹是浪漫主义,吹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吹了,真是浪漫得不得了。”(孟华玲:《谢冰莹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大革命失败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解散,谢冰莹无奈回到家中,为反抗包办婚姻再次出逃,一连四次才成功,到上海挣扎求生。没有了革命组织的庇护,职业、生计、前途重新成为问题,很多人在四处弥漫的恐怖、颓靡和失望情绪中堕落下去。谢冰莹目睹身边的女性,有的做了军官的姨太太,有的成了大都市中的色情商品。曾经为反抗封建婚姻不惜自杀的女孩,却逃不脱奢靡享乐生活的引诱,多少善良的青年在物质的诱惑下走上歧途。她不禁感慨:“上海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艾以、曹度主编:《谢冰莹文集》(上),第227—228页。)
谢冰莹想求学,想寻找自由,“求自我独立,不倚赖别人”。她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以一个单身女子能够自始至终不向金钱物质投降,宁愿忍受三天三夜的饥饿,喝自来水当饭吃……我没有像那几位主张‘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小姐一样,走上交际花、明星之路,过着灯红酒绿糜烂浪漫的生活。”(艾以、曹度主编:《谢冰莹文集》(上),第5页。)她拼命写作,凭借大笔稿费赴日留学。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政府加强了对留学生的防范,中国学生不但被严密监视,还经常受到侮辱。有日本教员在课堂上公然宣称日本占领东北是中国人的幸福,有日本小孩一边叫着“支那人”,一边向谢冰莹丢石子。她说,“我们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每天下课回来,大家互相诉说着被侮辱的情形”,“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每个人都感到沉重的压迫”(艾以、曹度主编:《谢冰莹文集》(上),第234—235页。)。1931年10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的追悼东北死难同胞集会遭到日本军警镇压,谢冰莹被驱逐回国。这次短暂的日本之行,让她深刻体会到贫弱国家国民的屈辱。全面抗战爆发后,谢冰莹抱持“只有抗战才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参加这样的抗战,中国妇女才能得到解放”的信念,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淞沪抗战前线。她说,“北伐后妇女的活动被‘到厨房去的口号封锁过”,今后妇女能不能“从家庭中打出一条血路来”,取决于她们是否能到前线去。(佚名:《谢冰莹会见记》,《抗战半月刊》1937年第1卷第4期。)
谢冰莹的好友白薇,也是时人眼中的“浪漫女性”。她15岁陷入包办婚姻,受到婆婆和丈夫残酷虐待,死里逃生后辗转来到日本,靠当女佣谋生,自修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白薇在武汉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工作,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参见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年,第9—23页;柳亚子等编:《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第1辑,光华书局,1933年,第27—39页。)她与左翼诗人杨骚的爱情几经波折,半生受着病痛折磨。谢冰莹说,白薇是中国所有作家中“最穷困,最凄苦,也是最孤独的一个”,而她是个倔强不屈的女性,有反抗精神,有正义感(艾以、曹度主编:《谢冰莹文集》(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白薇在《悲剧生涯》写了自己的经历,这是一个出走的娜拉的挣扎:“她的想向上,想冲出一切的重围,想争取自己和大众的解放、自由,不幸她又是陷到甚么世界,被残酷的魔手是怎样毁了她一切。”她说,那些不近人情的仿佛是虚构的悲惨故事,“都是百分百的事实!”(参见白薇:《悲剧生涯》,文学出版社,1936年,第1—3页。)
关于白薇和各种男作家的恋爱传闻是不是真相?她的领悟是:“在这个老朽将死的社会里,男性中心的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全由社会、环境、男人、奖誉、毁谤或谣传去决定她们!”然而一个出走的又在前进中的娜拉,不在意世人的评价,“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热烈的向上的心……只愿生活,生活,真挚地去生活,受难地去生活。生活就是她底整個。”(白薇:《悲剧生涯》,第5—6页。)
白薇有着清醒的女性自觉,终身书写着妇女的苦难、不幸和反抗,她认识到“男人的社会总是替男人说话的,女子没有正当的出路和给女子的公理”,但这不是两性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被压迫的妇女是所有被压迫大众的一部分。她在给谢冰莹的信中说,中国妇女的地位对于整个中国的进化,就像锅炉和煤对于火车一样重要,“我们为甚么活着?……就是要对万众的耳朵呐喊:不准对行驶的火车撤煤毁锅炉!……妇女们应该联合起来,为祖国的前进而奋斗!”(参见黄白薇:《地之弃子:寄冰莹》,《妇女月刊》1943年第2卷第6期。)1933年中华妇女解放促进会成立,白薇是发起人之一。她与同侪在建会缘起中写道:“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只要是一个被压迫的大众,他就有起来为着自己,为着整个被压迫大众而战斗的使命……我们要把一切被压迫的妇女们团结在一条战线上,一面为着整个被压迫大众的解放而斗争;一面促进妇女自身的解放。”(欧查等:《中华妇女解放促进会缘起》,《正路》1933年第1卷第1—2期。)
三、实践中的觉悟与重塑“自我”
投身革命运动、接触广大民众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让底层民众的痛苦进入了妇运工作者的视野,阶级话语也被纳入妇女解放实践。新知识女性在实践中认识到,女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与风俗人心的深刻变革,妇女解放是这一整体性变革的组成部分。只有彻底变革中国社会,妇女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解散,原妇女部干事陆晶清回到北平继续学业,同时担任《河北民国日报副刊》主编。她想借这一刊物“阐扬革命理论”,“实行革命的文艺政策”(晶清:《致辞》,《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1期(1928年12月1日)。),同时反省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思考今后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
陆晶清是20世纪20年代文坛活跃的女诗人,出版过《低诉》《素笺》《流浪集》等多部诗歌、散文集。她出身昆明一个小古董商家庭,1922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时曾编辑《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和《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与鲁迅有较多交往(参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第8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218—227页;潘松德、王效祖编:《陆晶清诗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2—247页。)。陆晶清和刘和珍、许广平都是女师大学生运动骨干,参加了女师大风潮,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后经李大钊、隋廷玫介绍加入国民党,进入中央妇女部工作。
陆晶清从妇女解放实践的现实问题而非激进革命理论出发,首先将目光投向革命中旧式妇女的遭遇。她看到,自从“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口号提出后,大量被丈夫抛弃或离婚后无法独立生活的妇女到妇女协会求援。她们在家庭中没有经济地位,在社会上没有谋生技能,一被遗弃就失去生活保障,孤苦无依而沦落者有之,濒于绝境而自杀者有之。虽然国民党明令经济上男女一律平等,女子有财产继承权,离婚男子应付给妻子赡养费,但事实上很少能履行。陆晶清认为,妇女协会不能空喊解放口号,而要在实际上为女性解除痛苦,在提倡婚姻自由时必须切实解决离婚女性的生存问题,如设立临时收容所,筹办妇女职业学校、培训女子职业技能等。(参见晶清:《离婚绝对自由以后》,《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4期(1928年12月4日)。)
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革命后一般新人物“第一个想的就是得一个时髦的太太”,重做新郎,又是蜜月旅行,又是新婚摄影,对于乡下那个无知无识,“做过机械式的太太,生过不期而遇的小孩”的旧女子,自然因其不革命而抛弃。“新女子解放了,旧女子应该入地狱吗?”(傲匪女士:《旧女子应该入地狱吗?——傲匪女士来信》,《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5期(1928年12月6日)。)陆晶清更进一步指出,时下号称“革命”的青年,岂只否认家庭代办的妻子,就连自由恋爱的妻子也随时抛弃,我们并不是反对男女自由结合自由离异,乃是认为今日“女子还禁不住这样的践踏”(晶清:《答信》,《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5期(1928年12月6日)。)。
女子既受旧道德压迫,又遭“新青年”践踏,说明在大多数女性尚无独立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而需要男性提供生活保障的历史条件下,片面强调自由和欲望的合理性,并不能给女性带来真正的解放和平等,反而掩饰了旧的礼教秩序瓦解后、新的伦理规范确立前,许多“新青年”的道德虚无状态和女性实际承受的伤害。陆晶清等人不仅清醒认识到女性的处境,更将讨论延伸到两性关系之外,提出了男女青年同样面临的经济压迫问题。她看到革命队伍中穷苦的男青年同样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丧失了人的尊严。她的小说《妻的像》,写1927年夏武汉政权的风雨飘摇中,一个在某军部任职的青年因军部欠饷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妻子被迫沦为舞女的故事。主人公地位低微,生活穷困,他的才力不算宏博,也无进身之阶,只能默默承受社会的欺凌。(参见晶清:《妻的像》,《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17期(1928年12月20日)。)小说的技法虽不高超,却真实展现了大革命中部分青年的窘况,揭露了革命队伍中的阶级矛盾。
大革命中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工农群众的痛苦和革命要求进入了妇女解放的视野。谢冰莹说,“五四”以来的妇女运动只看到“封建”的痛苦,忘记了女工是更苦的人,今后妇女运动要帮助女工实现“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优待童工及孕妇……种种最低限度要求”,为她们争得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冰莹:《几句贡献给做妇运工作同志的话》,《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135期(1929年6月9日)。)。陆晶清更认识到,过去妇女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未能深入下层群众,忽略了领导农工妇女共同革命,不但失去妇女运动的基础力量,且不切合“妇女解放”的真义。此外,国民党各县市党部妇女运动负责人能力薄弱、行动幼稚,不能深入底层,了解贫苦妇女的诉求,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如今革命势力崩溃,妇女运动不能不随之消沉,欲重振妇女运动,必须先挽救革命。(参见晶清:《从“三八节”说到中国妇女运动》,《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71期(1929年3月8日)。)
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深入女工之中开展工作,较早认识到女工的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最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是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戴绪恭、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第221页。)。大革命后,女工工作的重要性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1928年,原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刘蘅静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整理委员。她认为,中國的妇女运动已“过了女权运动的时期而入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时期”。然而,“妇女”不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其中有农妇、女工、学生、其他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她们的经济地位不同,找不出共同的利害和需要。例如,参政权为知识女性所重视,农工妇女看得并不重要;结婚离婚自由为女学生所重视,靠丈夫养活的妇女则最反对,她们更关心蓄妾问题。此外,女学生“智识能力在一般妇女之上,领导妇女运动本该由她们负责”,而上海的女学生大多“思想落后,行为腐化,重虚荣,轻人格”。惟上海女工在全国最多,她们受苦最深,要求解放最迫切,“是妇女运动的基本部队”,是目前工作急需注意的方面。(参见刘蘅静:《上海妇女运动槪况》,《青年妇女》国庆增刊(1928年10月10日)。)
这些实践中获得的觉悟与反思,说明经过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中国的妇女运动已经突破“五四”个人解放和女权话语,成为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底层的痛苦与力量,并不意味着能立即投身于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政治实践。若想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革命者,乃至坚强的、有觉悟的革命主体,还要经历艰难的求索和痛苦的锻造过程。
国共分裂后,原武汉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胡兰畦仍留在国民党左派阵营中,担任汉口市党部妇女部部长、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兼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她看到国民党中有很多青年对时局不满、立志改造社会,认为国民党还有革命的可能,遂与另一名妇女部职员(据胡兰畦回忆,此人为陆晶清:“我和陆娜君(陆晶清)不愿去南京,就决定派我接替刘蘅静的两个职务……陆娜君原是刘蘅静的秘书,职务不变。”据档案记载,此人为刘天素:“中央迁宁后,本部留职员胡兰畦、刘天素两同志,在汉指导妇女运动……特此奉达。”参见《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1页;《妇女部致中央工人部函》(1927年8月26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部”3478。)一起,团结一批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同学,继续奉行孙中山的农工政策。他们每天下工厂与女工建立联络,还将推粪车、倒马桶的女工组织起来,成立了有两千多会员的肥料工会。(参见《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第182—187页。)桂系军阀控制武汉后,这些国民党左派又聚集到江西,想在朱培德的势力范围下干一番事业。他们拥护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主张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打破军事独裁,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创造生产的、劳动的文化。胡兰畦担任革命行动委员会江西省委委员及南昌市委组织部部长,委员会在工人和学生中都有骨干,在政治和宣传上颇有影响。1929年4月,陈果夫曾致电蒋介石,称胡兰畦等11人寄生江西省政府内,阴谋破坏国民党,请电令拘捕,“处以严办”(《陈果夫电蒋中正》(1929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17-013。)。朱培德起初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参见《蒋介石电朱培德》(1929年5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60100-00018-031;《朱培德电蒋中正》(1929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106-00007-004。),但随后反蒋派系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朱培德又转而与蒋介石合作,国民党左派“联朱反蒋”的计划就落空了。
多年的闯荡求索让胡兰畦的思想渐渐发生变化,从最初追求女性个体和性别解放、谋求女性经济独立、不参与政治,到接受反帝反军阀、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革命思想、加入国民党左派,再到在一次次反蒋斗争中看清了国民党左派的弱点。她认识到,国民党左派总想避免剧烈的阶级斗争,从对立的两极中寻求妥协折中之道,但他们“既无得力干部,又脱离广大工农群众”,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缺乏力量,担负不起改造中国的重任。(参见《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第83、89、102、104—106、226—227页。)1930年,胡兰畦在柏林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她带来空前广阔的视野和前所未有的精神成长。1932年12月,胡兰畦在德国共产党反法西斯大会上演说,得到德共创始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蔡特金的鼓励,受到巨大鼓舞。
1933年,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胡兰畦也被投入监狱。在狱中,欧洲革命妇女的热情、勇敢、忠诚、对同志的友爱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使胡兰畦深受震撼。她说:“她们是英勇的创世者……像冒着霜雪正向春天生长的花木,在她们这一群光辉灿烂活泼泼的人面前,我只有惭愧,我只有警惕,我只有发愤……鼓起新鲜的勇气,来踏上艰难的路程。”在宋庆龄、鲁迅等人的努力下,胡兰畦终于获释。她写成《在德国女牢中》一书,告诉所有“被压迫的姊妹们”,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上,“要得到真正的同情和爱抚,只有在革命的队伍里”!(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生活书店,1939年,第91—92、1页。)
只有在革命的队伍里奋斗,才能实现妇女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理想,这也是黄慕兰较早就明白的道理。但她还要在革命队伍里经历很多的困难和考验。黄慕兰天资聪颖,受过良好家庭教育,既能写文章,又能做群众动员组织工作,在武汉“是红极一时的人物”(《黄慕兰自传》,第34—35页。)。1927年武汉“分共”前夜,已是中共预备党员的黄慕兰和丈夫宛希俨(宛希俨(1903—1928),湖北黄梅人,1923年在东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曾参与创建湖北黄梅的中共党组织,大革命期间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一起秘密转入地下,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陈潭秋领导的中共江西省委担任秘书和机要交通员。1928年4月,宛希俨在赣南领导农民武装斗争中被国民党杀害。黄慕兰在晚年回忆说:“这是我生平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他未竟的事业。”(《黄慕兰自传》,第62页。)
同年12月,黄慕兰接到党中央调令转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受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周恩来领导。一次,她在工作中受到委屈,又不慎丢失中央会议记录簿,自知犯了重大错误,竟纵身跳入黄浦江,幸而获救。周恩来批评教育黄慕兰,“我们既已把生命献给了党,那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了”,自杀轻生,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冲动,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严重的错误。至于同志间的误会、批评,更当虚心反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不能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他说:“你既已献身革命,就要一切从革命大局出发,而不应斤斤计较个人之间的恩怨。你是熟读古书的人,就应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这番严肃深长的教诲,将共产党人的行为要求和古圣先贤的人格理想贯通起来,在崇高的信念、大局观和历史责任感下,召唤主体超越个人局限,实现人格的升华。黄慕兰晚年在自传中说:“我心中豁然开朗,永志不忘。从此以后,我在革命征程上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曲折,受到多么严重的挫折、打击和误解,我都能以坚强的意志承受之。”(参见《黄慕兰自传》,第70—72页。)
四、结 语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从“自我”到“革命”的转向。妇女解放从冲破强制性社会制度与习俗的束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发展到要求与男性共同承担民族解放和阶级革命的重任,革命者自身也在自觉承担历史责任、重新落实伦理价值的过程中发生改变,成长为“新人”。这一转向的过程并非国族、政治对女性主体的“压抑”,而是新知识女性自觉的认识和选择,以成为政治主体和历史主体的方式形成女性主体,体现出一种突破“自我”、获得成长,超越个体、成为主体,立足女性、高于女性的现代中国女性意识。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以女性视角反思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研究逐渐成为妇女研究主流。有论者指出,女性主义伦理的目标在于提供行动指南和对道德本质的理论理解,使任何女性个体或群体的利益不会或公开或隐秘地屈从于任何他人或集体的利益(参见Jaggar, A.M.(1989).“Feminist Ethics: Some Issues for the Nineties”.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20(1-2), pp.91-107.)。它提供了一种批判视角,让我们得以发现中国革命的妇女解放实践中潜在的压抑机制,以及被国家、社会等整体性目标遮蔽的个体和身体诉求(参见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7—38页。)。然而,在这一伦理目标和研究视角下,中国革命女性那些不能为女性主义所整合的生命经验和主体实践,却常常处于失语状态。
有学者在1980年日本女作家田畑佐和子与丁玲的相遇中敏锐把握到这种“解释的焦虑”。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启发而参加女性解放运动、曾从丁玲作品中获得激励的田畑,在会见丁玲后坦言自己的失望。她发现丁玲对她兴致勃勃谈论的西方女性解放运动不感兴趣,且对女性话题有意排拒。“田畑……努力想把丁玲纳入自己所设定的‘女性主义脉络,但被视为‘先驱者的丁玲却固执地不肯‘就范……其实是丁玲丰富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写作实践,让田畑和她的同人们的‘新女性主义论述遭遇到了挑战和考验。”(参见王中忱:《女性视线:跨越时空的交错》,《人间思想》2017年秋季号第16期。按: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以女性主义理论解释中国革命经验的局限性,参见秦方:《在历史与性别之间——大陆地区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知识史路径》,《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6期;宋少鹏:《革命史观的合理遗产:围绕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讨论》,《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等等。)
本文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与女性主体意识转向的历史过程,试图把握新知识女性从“自我”走向革命的历史语境、生活实践、价值观念和主体意识,理解这一转向的历史逻辑。可以说,西方女权运动是在一个完整的国家结构和政治秩序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女性通过个体联合形成社会组织、进行社会抗议,去改变性别歧视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观念。现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则是在国家分崩、列强环伺的局面下,与革命和建国运动同步展开的过程。一些女性从清末起就以“国民”的自觉意识投身政治运动。向警予认为:“女权运动的真意义,绝不是性的战争……若妇女心营目注的只一个‘女权,而于‘国权漠不关心……是先已自己剥夺了自己的‘人格和‘民格,而反觍颜以求女权,岂非天下大愚!”(戴绪恭、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第141页。)在她们看来,“解放”意味着有资格去承担责任,女性只有成为政治主体,才能成为女性主体。
性别差异和性别的自我限定性也是中国革命女性力求突破的。红军女战士曾志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唯一的女生,她说:“男女平等,男的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比男的做得更好……我克服了生理上的種种不便和不利,要咬紧牙关战胜困难……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女性。”(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这种精神气质在极度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特殊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强化。1944年《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他写道:“有一次我曾放肆地向那边一位C女士说:‘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她反问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这种执拗的答语,竟使我无辞可驳。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第86页。)
20世纪20年代投身革命的知识女性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内在“自我”,因而能起身反抗压迫、限制女性自我发展的社会环境,同时又对社会公正和普遍的人类幸福怀有热望,认为女性从事自我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应当“朝个较高的较进步的理想走”,“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2册,1985年印行,第204—205页。)。正是对民族国家和更广阔人类命运的责任感,一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觉悟,让她们走向革命和社会主义,历经挫折磨难而不失掉在历史中实现人类解放的信念。丁玲在晚年说:“人生啊,实在是太曲折了,也太痛苦了。我们要革命,要做工作。可是,我们不容易取得很好的条件和环境,发挥自己的能量。有时我们得在很重的压力底下,倔强地往上生长。”(张炯等编:《丁玲全集》第6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3页。)她们的历史实践和身心经验,应可为今日女性的自我理解、精神解放和人格成长提供丰富的启发,也有助于我们立足中国经验,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性、价值建构等问题。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力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