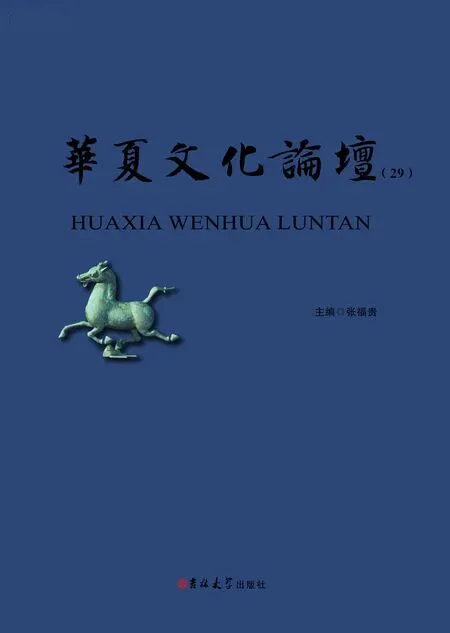论《典籍里的中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2023-12-11何国平傅倩影
何国平 傅倩影
【内容提要】2021年《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经央视播出以来,迅速出圈实现跨圈传播,成为近年电视文化综艺类节目创新的又一IP,更是通过电视节目形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案例。通过充分发掘电视场域的“通俗化力量”,《典籍里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体现在从典籍文本到电视声画文本、从记录文本到展演讲述文本的现代性转换,以电视为媒介化与再媒介化中介的媒体深度融合思维和对“激活其生命力”的方法论的综合运用。因此,从文本的现代性媒介转换、内容本体的情节性展演到剧场性(化)元素的发掘,三者的创新运用是该节目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法门。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因,更是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坚定“四个自信”的重要源泉。为进一步弘扬与发展传统文化,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2021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2022年10月)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0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国家战略,是发挥文化功能、实现传统文化“以文化人”的顶层设计。
作为一档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综合运用话(戏)剧、历史资料、影像、现场配音等影视剧场手段,2021年2月经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以来,不仅获得电视端的巨大收视成功,还迅速出圈实现跨圈传播,成为近年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IP。《典籍里的中国》的节目创新所产生的“现象级”的传播,引发学界关注。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在节目形态、跨圈传播、故事演绎等“技术”层面做了密集讨论,多以电视节目为本体,未能实现“文本间性”沟通,更未能从贯通顶层设计与节目本体的中观层面方面探求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然与应然,以及从典籍到《典籍里的中国》所实现的现代性转化的媒介化实践路径。
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典籍里的中国》为对象、以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方法,考察古代文化典籍实现转化—生产的关键环节与艺术特质,以及这种转化的最优媒介化路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①从典籍文本到声画文本的文本转化的必要性;②作为讲演(讲述与表演)文本的影像演绎的艺术特质;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可能的媒介化进路。
二、从典籍文字文本到电视声画文本
进入影像时代,对典籍进行跨媒介改编成为传承或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所谓改编,指对已知的作品进行公认的转换,是一种富有创造性和解释性的挪用或挽救行为,而改编的动力则来自保护那些值得被了解的故事的渴望。①[加]琳达·哈琴、西沃恩·奥弗林:《改编理论》,任传霞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页。典籍作为纸质媒介承载的文本,以纸质文字形式记载古老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正是有赖于古代典籍,当代人以史为鉴才有迹可循、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才有可诉诸的对象。但由于汉语语法的巨大变迁、汉字字体演化以及艰深深奥的古汉语语汇,典籍与当代普通读者的接受之间存在很深的文化区隔。以《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尚书》篇为例,该期节目是对以“佶屈聱牙”而闻名的典籍——《尚书》的跨媒介演绎。按《尚书》的“尚”,即“上”,意为“上古时代的书”。这部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与今天通行的简体白话文的差别巨大,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通假、古今异义、特殊句式等是横亘在普通读者与典籍之间的沟堑。试看《尚书·禹贡篇》的首句:“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何为“敷土”?“敷”,分也。敷土,即划分九州土地之意,在现代汉语中“敷”常用敷药、敷衍之意,“划分”义涵在今天已完全不用了。但是,《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将典籍文本《尚书》中的相关文本内容场景化,通过剧场化手段将开篇大禹定九州的空间延展,以电视媒介声画合一的方式活化呈现,节目复现场景、演员诵读和对话讲述等形式再现大禹划分九州的场景,实现跨越时空的连接,穿插融入主持人撒贝宁向伏生介绍九州在今天中国版图上的位置的立体画面。两个剧场演绎共同阐释了大禹之于中国的贡献,通过舞台上的情境还原性表演,佶屈聱牙的典籍变得通俗而鲜活生动,这就是剧场化的力量。
同样,《尚书·牧誓篇》,“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句话原意“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我要宣誓了”,是周武王在以四万士兵击败七十余万士兵的殷王朝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豪迈誓言。对于当代普通读者而言,“称”“比”“予”等词义与词性理解起来难免不太准确而有失信心,无法依靠文字在脑海中复现壮阔的历史场景。而经由电视声画文本转化后,受众通过角色设定、剧场布景、广电渲染等人物与装置设计实现典籍文本中梗概性历史场景描述的形象直观还原:众人物举戈、排盾、竖矛的气势及其所产生的感染力。
按照媒介决定论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冷媒介与热媒介的观点①[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36-49页。:冷媒介要求接受者高参与度,典籍作为象形文字记录的文本,显然属于冷媒介;热媒介接受者的参与度低,以视觉冲击力强为特点的电视属于热媒介。诚然,以《尚书》《史记》为代表的古代典籍建构的严谨而有时空距离的文字文本世界,需要读者调动多种感官来体验与想象“彼情彼景彼人彼事”而成为典型的冷媒介。作为热媒介产品的《典籍里的中国》,通过话剧在舞台聚焦空间演绎典籍里的故事与人的复杂关系,而“舞台是一个使无形能显现出来的场所”②[英]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邢历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8页。,节目中的舞台剧通过戏剧化的剧情和剧场化手段给观众的感官造成有冲击力的体验,转化成为屏幕前的“此情此景此人此事”,使不可见性具有直观可见性。通过冷热媒介转化,电视声画文本调适了“典籍”与“受众”之间由“他者叙事”造成的接受间距化矛盾。
纸质媒介记录历史的沧海桑田与更替兴亡,使古代典籍在本质上具有崇高美学风格。典籍文本进行当代转化后,通过剧场化等演绎手段以声画合一的电视文本形式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在优美审美范畴中展现典籍中“可敬”“可信”的中国,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感官,生成质感“可亲”的中国。
三、从记录文本到展演讲述文本
从文本形态而言,典籍总体上属于“书写史学”,是传统文史的范型,即通过书面文字来记录历史,陈历史兴亡之迹。换言之,中国文化典籍以书面文字实录过往言行事迹,生成典范性记录文本。在实物媒介(石器、青铜、竹简、丝帛、纸张等作为记录媒介)时代,记录性的文字依靠记录者“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通过口述、书写等形式记录历史,保存史实。对于书写史学来说,“叙事”是首要特征。譬如,篇幅长达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徐霞客游记》,记述徐霞客经历三十多年对中国名山大川的地理风物实地游历,特别是对广大南方地区地形地貌、人文风俗的践履考察。《徐霞客游记》中的名篇《游雁荡山日记》既有文学色彩浓厚的语言,如“顶有春花,宛然插髻”记录玉峰的形状,也有《溯江纪源》中的朴实文字,如“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勘正了关于长江源头的千年谬误。
在记录文本——传统典籍中,阅读的私人化和个体化体验赋予阅读者主体地位,实现文本个性化还原,但这种还原是基于个人较高的文化素养、人生阅历的抽象力和想象力,缺乏可直接听闻的声响和可视性帧幅化的动态情节。而对于新历史主义学家海登·怀特倡导的影像史学——以现代影像媒介记录历史而言,表演是“重述”历史故事的重要方式。就典籍等记录文本而言,表演是对历史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深度开掘和生动演绎。《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以“一部典籍、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为创作主线,以话剧艺术形式为观众展演典籍中的故事和人物。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的说法,故事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我们通过可信的故事去理解历史事件”,“听故事和讲故事是一种人类的基本欲望”。①[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6-87页。为了强化展演的戏剧性,《典籍里的中国》对节目展演方式进行了合乎话剧艺术本质规定的创造性转化,即从“故事”思维转化为“情节”思维,使“一系列按时序排列”的线性叙述的“故事”转化为以“因果关系”为重点的“情节”单元②[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72-75页。。对于观众而言,戏剧性的情节使节目更有吸引力,而符合逻辑推演与回味,激发观众的主体性,深度代入节目中侦破谜团。在这个过程中,典籍—节目—观众的三维关系从由上到下的训导式(典籍—观众)下沉到相伴相生的嵌入式(节目—观众)。
以典籍《徐霞客游记》为例,全书分为与徐霞客的人生轨迹密切关联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他青壮年时期问奇于名山大川过程中撰写的,第二部分是徐霞客晚年的“万里遐征”的产物。但剧场化的《典籍里的中国》的展演部分不是根据故事的“时序性”展开,而是通过设计体现“因果关系”的情节——由果溯因来实现。情节展演从晚年的徐霞客开始,寻找徐霞客“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理想来源,接着就有少年徐霞客受祖训引导“徐氏男儿可以不考取功名,但不可不立志”这一舞台场景,揭开徐霞客出游的动机,随着情节的推进,观众深切感受到徐霞客由志向迸发的征服力量。此处不仅体现沈从文先生倡导的“要贴着人物写”③郜元宝:《“要贴着人物写”——“这是小说学的精髓”》,《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以话剧这一舞台表演艺术为人物塑造开辟新空间与新境界,即通过情境与关系设计、舞台动作、语言表达等手段形象直观实现演员拟像化为故事人物。更为显豁的是,情节式的演绎不是简单地面向观众将典籍的文字世界重构为电视的影像世界,而是把训导式的文字转化为嵌入式的基于逻辑演绎情节模式,观众不再是单向地、被动地接受古代典籍,而是随着剧场化的节目展演结合自身生命历程进行主动的意义再生产过程,实现创造性转化。因此,基于“因果关系”情节化的展演文本具有摄人心魄的感染力与震慑力。
同时,《典籍里的中国》深度发掘、充分利用栏目化电视节目的本质规定,设定节目主持人——讲述人角色,毫无违和感地实现古与今、典籍文本与展演文本之间的勾连与缝合,展示节目的讲述力量。因此,讲述模式是典籍文本转化为电视节目这一现代性文本的又一本质特征。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肯定“讲故事的人”对于故事的传承、传播、扩散的作用,将他们区分为“水手”和“农夫”两个角色。“远行之人必有故事”,“水手”代表远方异乡的来客,能为人们带来远方的故事。待在家乡却见识广博的人熟知熟记本乡本土流传下来的历史掌故和传统,这类人以“农夫”为代表。①[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96页。《典籍里的中国》总体体现本雅明的“二分法”理想类型(ideal type),创造出一套适合电视节目的讲述模式,只是转化后“水手”与“农夫”身份判断从空间维度转换到时间维度。节目演绎模式是从典籍中提取一名当事人作为“农夫”,“当代读书人”撒贝宁担任穿越历史的“水手”,通过这两个角色不同的“讲述人”的古今对话实现典籍文本与电视节目文本的沟通。
从《今日说法》《开学啦》到《故事里的中国》,电视主持人的职业历练将撒贝宁塑造成一位优秀的“水手”型故事讲述者。《典籍里的中国》中的撒贝宁往往现身在剧场化的舞台框外,在那儿搭个台,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说评书的装置设计“水手”型讲述者置身事外的仪式化场景。此即《典籍里的中国》每期节目开头的固定形式:以舞台灯光聚焦于坐在书桌前的“读书人”撒贝宁,讲述者与节目故事情节演绎之间形成间离化效果。除“水手”型故事讲述者外,《典籍里的中国》还设计了“农夫”型故事讲述者。在《论语》篇(第五期)这期节目中,弟子仲由充当“农夫”型讲述者现身舞台作为当事人叙述孔子被困楚国的起因和结果,叙述孔子在楚国国君身亡后回到鲁国创立教育事业的经过。由于仲由自己也是故事中的人物,因此表演者需要时常“跳进跳出”进行人物和讲述者之间的角色转换,打破了易卜生式的戏剧结构。叙述过程不必制造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不再纠葛于网罗情节,而是由两位角色不同的讲述者——“农夫”与“水手”在舞台上自由地讲述、评论事件,拉近了节目—讲述者—观众的心理距离,以典籍为载体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故事展演与讲述中。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电视媒介进路
媒介化(mediatization)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主流进路,影像化②Stam Robert,“Beyond Fidelity:The Dialogics of Adaptation,”in Film Adaptation.ed.James Naremore(New Brunswick:Rutgers,2000).p.66.、空间(实物)化③曹凯中:《媒介化场所的建构:“被拓展的电影院”学派的空间影像叙事探究》,《当代电影》,2021年第9期。以及二者的数字化、数据化结合④Couldry N.,Hepp A.,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Cambridge:Polity Press,2016),p.7.是主要关切方式。21世纪初的《百家讲坛》以电视栏目为载体通过观众对讲座(坛)空间的现实想象建构虚拟传受关系,是传统文化电视媒介化进路的重要环节,也是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重要起点。2013年提出“两创”以来,以《朗读者》《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为代表的文化类节目在“文化+综艺”方面不断创新。从节目形态而言,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只做到两种文化载体(传统纸质媒介与电视媒介)之间的物理相加,文化内容的展示与电视载体声画合一的特征呈割裂状态,电视媒介的本体优势未能充分释放。
在媒介上,《典籍里的中国》实现纸质媒介、电视媒介以及各种新媒体小屏(端)在相融中的创造性转化,即以典籍文本为底本,以电视节目为对象文本,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发酵话题打造IP,在各类大小屏(端)以长视频、中视频和短视频收获长尾流量。这一转化过程以媒体深度融合中的“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为总纲领与突破点,以节目为载体,以电视为中枢性转换平台,充分释放电视媒体的本体优势——“通俗化的力量”①[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0页。。在内容生产上,典籍文本与电视媒介文本在融合中实现内容转化,在生产与传播过程需要转换话语系统,深入挖掘和打造典籍内外“有意思”的故事,实现剧场+讲坛的剧情化、穿插性展演,把“有意义”的典籍内容做成“有意思”的文化产品,通过电视媒介进路实现典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此处,习近平总书记既在顶层设计,又在操作环节为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提出明确的实施方案和终极目标。“激活其生命力”是以典籍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目标,也是方法论。文化典籍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与历史穿透力四个方面,也就是以电视为对象媒介、以节目为对象文本进行转换,其创造性体现在对典籍生命力四个维度的激活及其程度。在创造性转化的操作上,典籍文本通过《典籍里的中国》新型文化综艺类节目形态实现电视媒介进路的创造性转化,节目将“陈旧的表现形式”定位在传统典籍文本上,把“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落实在体现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文明精髓和社会人伦价值上。根据这些操作标准遴选一系列彪炳千秋的典籍文本,已播出的节目聚焦的典籍有:《尚书》《史记》等中国历史巨著、《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等凝聚科学探求精神的经典、《道德经》《周易》等体现中国宇宙观与思维观的典籍、彰显人文修养与精神向度的《论语》《传习录》等,这些典籍是中华文化的精神高地,整体形塑了“何以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气质。这一过程是以电视为中介的媒介化与再媒介化,以媒体深度融合思维跨越媒介和类型的“显著的差异”,实现 “讲述(tell)故事”“展示(show)故事”“与故事互动(interact)”③[加]琳达·哈琴、西沃恩·奥弗林:《改编理论》,任传霞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一版序言”第7页。贯通,即通过设置穿越性讲坛读书人(讲述),通过剧场性的话剧展演浓缩故事精华、强化冲突,通过多屏接受在新媒体平台实现强互动。
五、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是其所是”的“存在者”,在实践语境中摆脱“被抽象化”的命运,发挥“以文化人”的文化功能。④梁秀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研究进展与展望》,《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9期。因此,“激活其生命力”成为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终极目标与方法论。2013年中华文化“两创”作为国家战略规划提出以来,从节目形态而言,从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到竞技性真人秀(《中国诗词大会》),从脱口秀朗读(《朗读者》)到剧场化演绎(《典籍里的中国》),从讲坛型专题讲述(《考古公开课》)到揭秘性鉴赏(《诗画中国》《中国考古大会》)等,不同的创新发力点为形态丰富、灿若星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电视为进路、节目为载体提供了创造性转化的电视栏目化方案。在这些创新形态殊异的电视文化综艺类节目中,通过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中华文化弦歌不辍,汇聚成“认识中国”的新时代磅礴力量。因此,在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代表的电视文化综艺类节目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路径是:从典籍文本到电视声画文本、从记录文本到展演讲述文本的现代性转换,并在以电视为媒介化和再媒介化中介的媒体中实现深度融合,“激活其生命力”为这种转化提供方法论。这些妥帖而富有创新的成功实践使《典籍里的中国》在以电视媒介为进路、以讲故事为突破、从“可读性文本”跨界向“可写性文本”转换中,成功探索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电视节目创新样本,通过节目唤起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赓续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激发其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