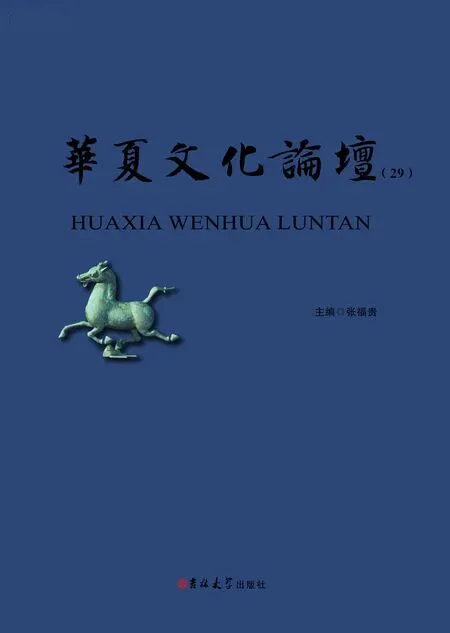并置的空间结构:北美华文文学中的家族史讲述方式
2023-12-11赵玉婷
赵玉婷 白 杨
【内容提要】北美华文作家们以其独特的异乡经历与家族感受,直觉性与技艺性地磨砺叙事语言与叙事形式,通过并置的空间结构进行书写,从而形成家族小说中独具辨识度的异乡叙事特色。这种异乡叙事最显著的结构特点是,两个并置的叙事层在进行形式互换后,并不会产生本质性的文本差异,即它们具有一种同质性的互换关系,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分歧或顺序联结,因此可以互相观看、彼此印证,构成每层叙事自身的线索是独立而完整的,它们共同服务于文本主旨意义的生成。本文通过空间理论的深化,进入北美华文文学作品内部进行探析,对矩阵对称结构、象征意涵结构两种空间并置形式进行剖析。在并置的空间结构中,强化特定的文本叙事场景及其次生的叙事哲学,进而借由小说文本延展出作家精神内部远离原乡却根植血脉的深层家族文化思考。
20世纪以来,北美华文文学中的家族书写一直与大陆家族文学相伴生,同时又受到自身迁徙经验的影响,而具有浓厚的身份追寻色彩。经过空间的转移与时间的演进,北美华文文学中的家族历史是经历过动荡离散的变迁之后,在新的土地上进行精神重建的家族史,移民作家们作为新生存土地中的异乡人,异乡视角与异乡经验贯穿家族叙事。在北美华文作家打造的异乡家族叙事中,薛海翔《长河逐日》、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张翎《金山》、薛忆沩《遗弃》等家族小说都明显具有一种显著的空间并置结构特征,主要体现为这些家族小说内部存在两个并置的叙事空间,并且两者呈现出一种共构却不互相打扰的互动关系,它们各自承载着相对独立的伦理世界,又服膺于共同的叙事主题,在重合与平行、交叉与对位的互动关系中两相互看。实质上,这种并置结构的叙事形式与华文作家们远离故土的生命经验具有相似性,迁徙经验赋予了华文作家们对于原乡与新质土地的双重家族经验,对这种复式经验的思考成为北美作家热衷使用并置结构的潜在心理,以此来展现出个人与家族、家族与世界的融合与冲突。
一、异地空间互相观看的并置叙述
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一文中,对文学作品中的“并置”现象进行概括,即“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事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从而形成一个整体”①[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8页。。在弗兰克看来,空间形式是一种试图克服包含在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而存在的文学补充物。约瑟夫·弗兰克针对空间研究提出“并置”的概念,正是文学“第三空间”叙事中的重要空间表现形式,也是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北美华文小说空间叙事中常用的说故事方式。以并置空间为形式的小说创作散见于不同阶段的北美华文小说中,成为一种北美华文作家们有意识布设的技法实验,作家们在这种使叙事空间互相并置的形式中,实现叙事与主题的交互融合。并置叙事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两个并置的叙事层在进行形式互换后,并不会产生本质性的文本差异,即它们具有一种同质性的互换关系,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分歧或顺序联结,因此可以互相观看、彼此印证,构成每层叙事自身的线索是独立而完整的,它们共同服务于文本主旨意义的生成。
北美华文作家薛海翔在家族小说《长河逐日》中以空间并置的叙述方式溯源父系与母系的家族历史,“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两个源头,父系和母系”②薛海翔:《长河逐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3页。,作家以“我”的视点作为空间观看的坐标,建构两系家史各自的生存空间,将出生于马来西亚的父亲郭永绵和出生于中国苏北的母亲薛联两个人各自的生命历程对照书写,以相同时间历程中的不同地理坐标作为并联空间的注释。在对父系、母系家族史的追溯过程中,作家不仅溯源了父亲与母亲殊途同归的革命参与历程史——由共产党用革命理论直接启发和因对当时政府不满而产生革命转向思维,还将其归纳且视为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席卷全球时,普通民众加入革命队伍的两种参与路径。小说以马来西亚怡保、槟城,中国江苏盐城、兴华、宝应等城市作为章节目录,从父母家族三代之前的历史开始,打造两种迥异的家族空间,并通过时间的横截面截取两个家族空间的不同景观,于是读者们能够在两系家族场域中对家族史进行横向观看,在“我”的讲述中,父亲七岁就读于马来西亚华人子弟办学的怡保公立义学之际,母亲四岁就读江苏省涟水县小镇的小学,这样的对照历史,父母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观看视角,以及两人各自的奋斗史与各自走出生命低谷的相似经历被一一展演,在家族空间的对写之间,家族故事被精心培育与生长。
这种双线并置的家史塑造有效扩充了文本的时空感与辨证内蕴,在叙事建构中摆脱了家族历史惯用的特殊性思维,将一般性的历史认知上升为普遍的具有革命生成性的家族境遇。从传统文学的叙事脉络看来,中国叙事文学自身的美学性并非教堂式的整合性建筑结构,而更注重填隙式的更替性美感,关注故事的循环性美学。薛海翔在他的小说中内置了一种独特的故事结构,以观念性的对称叙事支撑家族历史的构设环节,“父亲和母亲相差五岁,1920年代末期,相隔万里的两个小学生,各自开始了自己的启蒙之路。从空间上看,他们的人生轨迹永远不会相交……他们应该各自在自己熟稔的家乡,平凡地成长、谋生、繁衍、终老,一如众人,隔着望不到头的山川原野和波涛无边的汪洋大海,永不相交”①薛海翔:《长河逐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8页。,小说将毗连性的人物关系在文本中先拆分后又聚合,使关联化的历史思维在封闭的文本空间中功能性地相生,增强了小说的可视性与纵深感,进而获取一种建筑结构般的空间美感。
对时间与空间的探索是小说叙事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重要主题,“并置”作为对文本意义和话语的空间编织,是一种维护叙事的重要手段,它将散乱的意象收集、整合,这种空间意象的拼贴常以平行与交叉的方法来展现叙事的融合与冲撞。小说的双重结构作为并置结构的前身,其实并非现代的发明,而是一种具有长期生命力的古典叙事模式,在中西方小说创作中都曾被应用。而并置结构则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创造发明,文本中的各种意象与暗示、象征与关联以并列的方式置入文本,形成连续的参照与整体的呼应。可伸缩的意义单位被有计划地安置在文本之中,文本的统一性在空间关系的对应中获得完整。并置结构往往具有瞬时并现、静止并置、情节并置、情节重叠等不同的展开形式,在各个情节和空间线索的变式中,在小说内部区分形成知觉化的叙述空间。在叙事学范畴中,小说故事的意义本质往往潜藏在文本结构的底层,因此考察事件的结构往往要比讨论事件本身更重要。
北美华文作家张翎同样擅长以并置的空间作为小说的叙事背景,小说《邮购新娘》《唐山大地震》《金山》都将家族文本搬演到两个异地时空,以并置运行的叙事方式呈现家族故事。《邮购新娘》中收纳了故乡温州与加拿大多伦多两个城市空间中家族情感的逃窜与辜负,守望与歉疚,诸多人物在两个空间里轮番登场,唱的却都是那几出爱而不得的老戏,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组空间人物对比是在温州原乡空间里缓慢老去的杏娘,和抛弃杏娘而去到另一个异乡空间生活的江信初。杏娘在温州老家替江信初守孝,料理江家老人的余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个时空之间的裂隙与家族历史的伤痕。呈现北美华人移民史的重磅长篇小说《金山》,同样通过空间的并置展现家族的迁徙史。淘金客的金山家族史绝不单由淘金客在加拿大的异乡故事单独构建,与异乡相对望的原乡空间广州开平承载着方家父子背后繁复的家族支脉。两个场域里的家族故事双线并行,故乡与域外两个空间扎实地紧紧咬合,又各自独立,自成天地。母国的传统文化与游子之间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结,异乡的强势文化又无法回避地被灌输,以方得法为首的一众金山客们在原乡与异乡的文化空间中反复穿行。作家通过对家族人物生活脉络的双线并置,完成了这部移民心灵史、精神磨难史的搭建,两个并置的叙事空间以两相咬合的角力拓展了家族故事的时空跨度,并在厚重驳杂的国、族历史叙事中向家族回沉、聚焦,作家将文本的统一性融合并安置在空间关系的互动中,以期逐渐形成一种微妙的空间平衡。
由中篇《余震》拓展书写而成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再次发挥了北美华文作家张翎运用并置空间进行叙事的技巧,两个不同时空中的人物生活史——中国河北唐山丰润县的李元妮及其曲折复杂的家庭命运,加拿大多伦多圣麦克医院精神科中由于自杀未遂而接受心理治疗的华人女性王小登所口述的个人历史,并置地向文本中心突围、会师。来自同一家族中的两位女性同时坚守在各自的生活空间里,回忆和讲述她们共同的灾难记忆,使文本实时性地处于一种混合编码式的并行叙事当中。在这段震后家族历史中,李元妮如原点坐标般坚守在唐山丰润县的老家,不免因此与儿子儿媳产生嫌隙,却依然固执地坚守家的原始空间。尽管象征着家族聚落场域的房屋早已在震后进行重建,灾难中身为一家之主的方大强落难,至亲去世,家族涣散,但李元妮执着的坚守凝结为并置空间中家族叙事的精神支撑。王小登则是家族坐标轴里不断游移变幻的不确定坐标点,在不停歇的生存迁移中试图摆脱灾难性的童年创伤,最终通过对原始家空间回归,完成对创伤的治愈。作家在对灾难创伤的精神治愈中,聚焦个体,回沉家族,深度参与家族心灵史的搭建现场,以并置的空间逃避叙事的单线结构,使灾后重建的家族故事在矩阵对称的并置空间中获得复调的生存话语。小说的视角限制着叙述的权力,单一叙事视角的故事能够忠实而集中地呈现出单一人物意识,同时也可以视为作家在叙述中的自我限制。因此在许多时候有必要放弃视角的统一性,来呈现家族的双城生活与异地经验,以视角的越界与空间的相隔,来呈现家族的分合聚散。
北美华文家族小说中,以不同城市空间的对照来容纳人物同一时间范畴内不同的生活轨迹,从而形成并置的文本内容结构,有效地扩充了文本的时间感、空间感,延伸出更广阔的文本地理背景。空间并置的叙事共同补给着相同的家族主题,在同一时间之内相继展现不同空间中人物生活的样貌,贴近了华文家族小说中的家族迁徙形态,这种平行与交叉的复线叙事,增加了叙事的主体层次,这类叙述常常自我暴露出小说镜头的内部冲突,进而形成文本意义的垒加与组接,呈现两个空间之间具有流动性和视像性的叙事关系。
二、文本矩阵对称结构的空间并置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了“元叙述”这一小说叙事概念,这种叙事形式颠覆传统故事的单向度演进层次,转以戏中戏、书中书、画中画的嵌套模式,充分暴露隐含作者的叙事意图,渲染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元叙述”的形式成为北美华文作家在家族故事中常用的叙事方式,其中既隐含着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学的强力渗透,又源于文学生产自身的内在驱动性。“文本中的文本”也作为双层结构的形式之一,使小说在外层文本与内层文本的共同建构中,获得更广阔的言说空间。北美华文作家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空间双拼式的家族故事,在小说中,作家频繁地以双重视线推进叙事,并有意通过两种视线的交叉切换,增加叙事的陌生化意味。第一重叙事空间以主人公范笳河留下的“战事信札”所展现出的第一人称叙事为主线,可视为一次个体对战争历史的见证。其中以延缓叙事的方式,凸显出主人公个人内在的心理叙事,进而拉长了叙事时间,将叙事的镜头聚焦并拉近人物的精神世界。第二重叙事空间收纳了主人公范笳河移居海外的家族后代们及其各不相同的异乡生活片段,范白萍、浪榛子、喇叭等人纷纷以第三人称叙事呈现他们的战后异乡经验,支撑起信件与战争之外更加具象化的家族生活空间。
在第一重叙事空间里,隐匿在“战事信札”中的范笳河以日记体的方式讲述自己的前半生,读者得以从紧张与非我的临时应战状态中读到与之相关的家族痕迹——身为一名航空兵的范笳河生长在中国南方范水山区的个人记忆。范笳河的家乡范水以出孝子而闻名四方,那里有着为了让长辈高兴而为难小辈的陋习,范笳河恰恰是典型的范水产物,他的懦弱与愚孝行为给他个人的情感选择造成后悔终生的结果。信札中记述了“祖父”和“父亲”的参战历史、“祖父”为国捐躯后的家族迁徙、“父亲”与“我”截然不同的政治身份选择等繁复的家族历史。并且牵扯出怪异的家族秘密——名义上的“父亲” 其实是“我”的大哥,而“祖父”才是“我”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范笳河在向爱人坦白心迹时自白:“我终于没有胆量选择‘背叛家族’,你爱错了人,我欺骗了你,我实质上就是一个范水男人”①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75页。,以“范水男人”自嘲的范笳河深知个人乃至家族的软弱性,却始终难以克服这种窝囊、缺乏担当的劣根特性,因而在背叛家族、兑现爱情承诺与回归家族、放弃爱情的对立选择中为难纠结,他在私密的信札中向爱人舒暖倾诉自己的无助与自责。在信件之内,不可预测的流动性叙事是主人公心理时间与空间的外化,在刻意放缓叙事进度的书信之间,人物的精神世界得以被一一呈现;在信件之外,客观化的外在叙事与隐秘的内心世界产生对撞。文本“内视角”与“外视角”的混合并置,使小说在反复地视线切换中获得“入其内,出其外”效果的叙事自由。
在“战事信札”之外的叙述层中,范白萍由于在出国后积累了一定的心理学知识,敏锐地识别出来父亲范笳河战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与其根深蒂固的愚孝文化之间潜隐的内在关联。在她看来正是中国人与大多数中国家族中视长辈的认错为毒药的共性心理,才衍生出了一代人对战后PTSD的忽略,在一些愚孝的中国家族中,长辈们即使犯了错也不允许被晚辈指正,认为那样有失身为长辈的尊严,殊不知被强行建构出的尊严并非真的值得尊敬。这个逻辑用在心理病症上也同样扭曲,生了病却不正视病症而以逃避的形式来掩人耳目,“要么你和我们一样,要么你是疯子”②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93页。,这种讳疾忌医、文过饰非的民族心理致使一代人对PTSD的恶劣影响无知无闻。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范白萍觉得父亲范笳河心里似乎一直有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使他不断地自我指责与内耗,而一切的根源似乎可以追溯到当初令他两难的家族与爱情选择题。他选择了家族,也因此余生都不自觉地活在自责自毁之中。“要是我们范水一族人,经历了太多的暴力和灾难,它会不会全族患上PTSD 呢?”③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93页。借范白萍之口,袁劲梅在信札之外的第二重叙事空间中,注入了她对民族文化与心理的批判性思考,借助叙事空间的营造进行关于良知与毁灭、疯狂与理性的伦理探讨。随着“战事信札”和信外叙述的反复切换,信内信外的并置时空为读者提供了有效的文本对比范式,叙事结构的设置带领读者形成对历史多角度参考的契机,文本的空间复调效果拓展了叙事的张力。
在这个复式故事结构中,每一条情节线索都承载着相对完整的故事空间,尽管在被读者阅读之际,这两个叙事空间呈现出互相交织的文本形态,并形成外视角包裹内视角的书写秩序,但它们之间并不具备实际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或阅读秩序,它们不仅可以互换被读者阅读的顺序,甚至可以被独立地抽离阅读。双线交叉叙事强化场景的非连续性,在场景的间隔中,各自场域中的叙事仿佛得以在文本的暗线中自动生长,形成矩阵对称的文本形态。
三、叙事嵌套形态的空间并置书写
在空间关系里,以主线的并置形式开拓文本,并不会削弱文本自身的紧密度,反而能够增强文本空间的统一性。文学叙事中潜隐着叙事者的情感立场,承载着叙事的伦理价值。以并置方式建构出的叙事空间模糊化、复杂化了叙事者的伦理取向,在叙事空间的跳转、接续中,叙事者的真实情感与价值判断跟随空间而流动和拉扯,叙事的张力在空间的切换中渐渐生成,在文本中能够绘制一种具有空间感的双拼图案。
北美华文作家薛忆沩在家族故事《遗弃》中,以叙事空间的复调分层和嵌套,藏潜了小说隐含叙事者关于虚构与真实、虚无与存在的辨与思。其中以“书中书”形式呈现出的19则短篇小说系列故事在形式上与主层叙事有所区分,在内容上又充满一种对生存哲学问与答式的对话关系,它们与主层叙事看似呈现一种主次包裹关系,本质上却暗自生长为一种并置的文本空间,展现出的不仅仅是两个叙事腔调中不同的故事分层,更注重并置后文本意义的叠加与衍生。作家在《遗弃》中以元叙事的形式建构两个并置又独立的叙事空间,通过对小说中虚构故事的再创造形成叙事“书中书”,将小说内部的真实和虚构相区别,在双重印证的小说技艺中推动故事演进。《遗弃》中的两个叙事空间互相观看、互为家族书写的证词,两个叙事层次既相交又重叠,展现后革命时代一个与集体格格不入的人类个体及其生活的慌乱表象与其中潜隐的内在秩序。
文本的第一个叙事空间以主人公图林第一人称的日记为视点,作家在展开这个层面的讲述中着重对生活细节的突进,来完成对主人公及其家人重复性日常生活的演绎。通过对家族生活空间的意义编织,重审个人与集体、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通过对家族生活的刻录,完善家族空间的建制,维持主人公的肉身与家族他者存在的这个世界,以对重复性日常生活进行对抗乃至克服,实现个体的精神胜利。“生活的意义正好就是它的形式,而生活最高的形式就是形式的消失”①薛忆沩:《流动的房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年,第 217 页。,作家在小说中对家族生活片段的采集不求深刻烦琐,而是以形式主义体式的文本呈现方式勇敢地将主旨停留在事物表面,去除深意,通过对形式的探索和对语言的突破,浓缩还原了历史的奇异诡辩和命运的乖讹无常。
第二叙事空间以图林创作的十九篇小说故事为主线,将其对日常生活与人类生命的思索由世俗意涵转调为象征意蕴,这里以“书中书”形式出现的小说并没有沦为主声部叙事的意义副本,而是独立地成长为新的意义主体,承载着不可替代的叙事功能。其中的第一篇小说《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诞生于图林对一次车祸的旁观,“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意外的事故”①薛忆沩:《遗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页。,对“事故”的具体定义和思辨在第一层生活叙事中没有全然展开讨论,作家刻意将其留到第二层创作叙事中,借由精神病患阿奇的视角展开思辨,在阿奇看来,“说定了星期五带你去公园的”②薛忆沩:《遗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页。,是他人的一句承诺,其中却充满了可以被定义为事故的嫌疑,“说定了”“星期五”和“你”都存在着不可知的变数,也因此构成了酿成事故的前提条件。图林这次对于“事故”为题材的创作以精神病人阿奇赶走他的探望者们为结局,这种独处的生命状态以伏笔的方式呼应了第一重叙事空间中图林离开体制独立生活的人生选择。回到第一篇小说被陈列的文本空间内部,图林与处长在工作中的互相欺骗和互相拖延恰恰印证了《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中所呈现的“事故观”——一种对生活中的一切他者产生警惕的生存哲学。文本的两个叙事空间以互相印证的方式各自展开言说,最终共同作为“自愿失业者”图林展开对生活的双重证词。
这种并置的空间叙事还能够打破读者对不规则叙事空间的阅读习惯,有效拓宽对当代日常生活与近代家族历史乃至民族历史的理解路径。以“书中书”的第三篇小说创作《铁匣子》为例,祖先留下了铁匣子要老爷爷看管,并将保住铁匣子的意义上升至保住家国的关联程度,后来铁匣子在战争中保住了,战争也真的取得了胜利。到了和平年代,老爷爷热爱给家族后代讲关于战争的故事,他的故事里有好几次敌人把房子全烧光了,把银子全抢走了,把书籍都烧毁了,把女人全糟蹋了,但族群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生存,而是又建立起了很多房子,又培养出了很多写书的人,人们又开始使劲地生孩子……爷爷故事的结尾总是这样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在短篇的最后,一生未打开铁匣子的老爷爷因男孩打开匣子偷看而气绝身亡,小说的悲剧性结尾预示了第一叙事层中图林外公的死亡,也隐含着作为孙子却对长辈屡次不孝的歉意。铁匣子的象征寓意深化了第一叙事空间中被简单化的家族生活,使小说脱离个体记忆的当代面相,在家族化的熔炉内,将记忆烘焙出时间的厚度,以厚重的历史感刻画表达个体与家族、民族与世界的家族故事,在并置的叙事层面,营造时空冲撞的荒谬感。
图林的所有小说创作全部能够展现他对个体与世界关系、家族关系之间的哲学思考。通过对并置叙事空间的使用,强化了其小说叙事的纵深性,拓展了家族时间的自然跨度,以其笔下主人公“书中书”式的虚构创作,进行家族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具象呈现,使文本脱离被简化和类别化的叙事空间,巧妙地以隐含作者与小说主人公图林之间的隐秘交流,演绎图林日常家族生活的后革命生存论,同时守护其精神世界的抽象延展,将对重复性生活的思考与抗辩融入文本内部。作家在空间并置的叙事文本中完成了由生活片段到生活革命的范式互换,将小说的嵌套空间结构设定推向极致。
四、结语
北美华文作家们通过以上种种并置空间叙事来呈现家族书写,看似混乱与形变,却往往更符合个体在历史的第一现场所真实感知到的迷惘感与未知感。许多时候,恰恰是作为时间之后见者的我们,才能在知识视角中把握住既有历史的现实流向,从而形成个人脑海中的事件脉络。在历史现场中的个体却全无顺序、平整的时空感知,唯有对时空的流动性体验,散乱的、重叠交错成历史现场人物们的具体感知。这种复线并置结构的家族的呈现,剥夺了读者作为后见之明者原有的清晰时空认知,转以一种身临其境的含混感知替换清醒感,让庞大而迷人的异乡家族记忆穿梭在实存真相与心造镜像的文字迷宫中。北美华文作家们以其独特的异乡经历与家族感受,直觉性与技艺性地磨砺叙事语言与叙事形式,从而形成家族小说中独具辨识度的异乡叙事文化,这类叙事在运用了繁复的技艺性后反而获取了叙事感受上的真实,拉近了阅读者与故事的贴身距离,使阅读获得了比语言陌生化更迷人的时空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在同期的华语家族文本中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