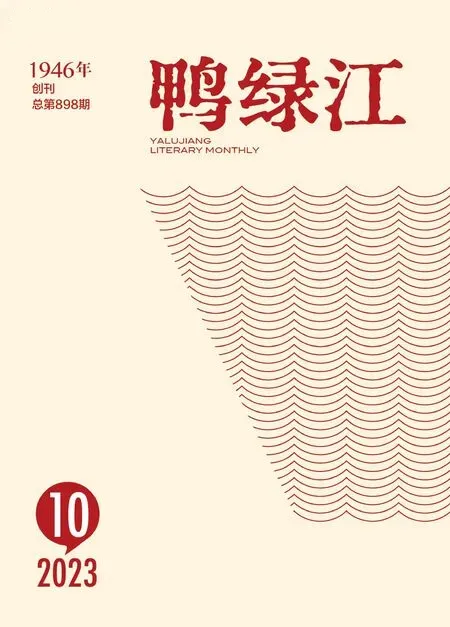醒着,读着,写着长信(散文)
2023-12-10高海涛
高海涛
青春啊
我们的青春是从20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的两三年,醒来的。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上大学的,年纪有点大,但我们读的是英语专业。大学三年级,开始选修第二外语,我选的是法语,你选的是日语,而我的同桌老董,上海来的,快三十岁了,他选的是德语。
问他是怎么想的,老董说,他崇拜康德、尼采,还有李尔克。
多么意气风发啊!那时候都这样,记得我从图书馆借到的第一本法语书,就是《青年马克思》(Le Jeune Karl Marx)。
那年的元旦晚会,忘了吗?我们都报了节目,老董报的是诗朗诵:《秋日》,作者:李尔克。这本来很正常,他是用汉语朗诵,而且是冯至先生的译本。但排练的时候,李敬爱却发现了问题,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说也没什么大问题,就这首诗的开头第一句:“主啊,是时候了”,好像不恰当,听起来别扭,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公开宣扬基督教不好吧?老董毕竟是上海人,并不倔强,说可以折中一下,“主”这个词可以用德语念。另一个女生,吉林来的,支持老董,说就是啊,应该解放思想嘛。但李敬爱还是很犹豫,说你们都是团员,要不开个支部会表决一下?那个女生本来坐着,就忽地站了起来,说这属于个人自由,你们要表决“我们”有没有这个自由吗?
我当时并不在场,是听你学说的,你说那个女生说“我们”的语气很特别,含混而有力。后来恰好陆老师走进了教室,听了大致情况,嫣然一笑,说可以变通一下,用“青春”两个字开头吧,说完翩然而去。
啊,陆丽霞老师,只有她能这样举重若轻。整个大学期间,可以说陆老师是我们最爱戴的老师。当时她四十多岁,不仅英语教得好,还极有气质,朴素而雍容,总系一条淡红色的纱巾。
元旦晚会陆老师来了,还替我们请来了系主任、德语教研室主任,以及陆老师的先生,后来教我们翻译课的屈老师。这可是我们班前所未有的光荣,所以大家演节目都特别卖力,尤其老董,他蓄势待发的朗诵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青春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这首诗写得真好,译得真好,当然,改得也真好!青春啊——仿佛这是历史隐忍已久的召唤,而我们的青春感、青春意识、青春自觉,也前所未有地被召唤了出来,混杂着春天的感激、秋天的思考和对成熟的渴望。是的,许多年了,同学们早已天各一方,老师们也都没有了音信,但我还一直记得那次晚会,老董接过了那个女生勇敢而羞怯的献花,并赢得了同学们意味深长的掌声。系主任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还有陆老师,她在红纱巾的衬托下简直面若桃花,她和屈老师相视一笑,那嫣然的笑影就定格在所有同学的心中。
青春啊,是时候了!中国啊,是时候了!80年代,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感觉,不是吗?还有那句“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你说很喜欢这一句,我也是,这么多年一直记着。那是我们80年代整体的样子吧?一代人的精神肖像。仿佛春天遇见了早晨,一切都醒了,那时候我们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长信啊!
而如今,虽然书有时还读着,可长信却无缘再写了。这不仅是因为书信都电子化了,变成了短信、微信或E-mail,而且,谁还有写长信的时间和心情呢?就算你有时间和心情,但写给谁呢?
目光
让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她说。
那个夏天的傍晚,一切都很开放。你们坐在校心湖边的长椅上,谈起什么是美的话题。后来又谈起突创论,她相信美也是突创的,和生命一样。说着就笑了起来,有点莫名。事实上她笑得前仰后合,一头秀发,梳理着幽幽的目光。
有几颗星星,月光很淡。她说月光很美,但月亮是个贼,它的光是从太阳那里偷来的。你知道这是莎士比亚的话,出自《雅典的泰门》。她说世界上所有的光,包括月亮和星星的光,其实都是太阳的反射。这是常识,没什么好说的。你欲言又止,过了一会才问她,突创论就是神创论吗?
当然,她收住笑,很庄重地复述了一句话,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你问,那这光是来自太阳吗?
她突然缄口,半天才嗫嚅着说,那倒不是,上帝创造世界用了七天,第一天创造了光,第四天才创造了太阳、月亮与星辰——可这是怎么回事啊?都怪你,把我问糊涂了。
然后你开始无语,但能觉察到她的目光,含情脉脉,幽幽闪亮。一阵风吹来,她抱紧你的胳膊说,咱们走吧,要下雨了。
你说,等一等,我要让你见证一种与太阳无关的光。
什么光?她问,声音有点紧张。
你站起来,拿出打火机点烟,她抢过去,替你点上。松了口气说,还以为是什么光呢,打火机的光也算?
不,打火机不算!你吸着烟,更加淡定:火柴、油灯、电灯都不算,我说的是自然光。
那是什么光呢?她颤抖着,目光缠得更紧。你用手指着天边,回答两个字:闪电!
哎呀真是!她雀跃着说,闪电是自然光,也好像真和太阳无关呢。你再举个例子,除了闪电,还有什么吗?
还记得吧,当时天已骤然变黑,雨上来了,你望着她的眼睛,故作深沉地说,还有,你的目光。
不眠之夜
“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抬头就看见满天星辰”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歌,那么深信,那么深思,又那么深情。词作者是你的同龄人,也是你的校友,你们一起毕业留校,住在同一个“青椒楼”(青年教师宿舍),但他是中文系的,你是外语系的,见面只是偶尔打个招呼。
那时候的白天很白,黑夜却不怎么黑,白天与黑夜之间,那个宿舍楼的所有“青椒”,无论男女,似乎都只做两件事,不是失眠,就是看书。
记得整个夏天,你都在看《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这是何老师推荐阅读的,英文版还不到二百页,但你却读了整个夏天。
正是从那个夏天开始,你真正学会了失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失眠甚至有点奢华,那么多如花似玉的憧憬,冰雪聪明的联想,都翩翩而至,和你共度良宵。而这样的夜晚,和盖茨比的故事几乎是同构的。盖茨比的故事也发生在夏天,一个年轻的少校,因为战争与初恋分手,而当他王者归来,女友早已嫁入豪门。所以,夏天的盖茨比,了不起的盖茨比——他之所以了不起,并不在于他传奇般的发迹,而在于他太爱自己的青春和初恋了,他对那个叫黛西的女子一往情深,不仅买下了城堡式的豪宅,与黛西家隔水相望,还每天晚上举办盛宴舞会,灯红酒绿,宾客不绝,通宵达旦,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吸引昔日的恋人前来相见,续写有始无终的故事,完成意味深长的悲剧。
那些挥金如土的夜晚,多么像你的不眠之夜啊。
80年代,一代人的多梦时节,一群人的萤雪时光,好像只有那时的不眠之夜,才是真正的不眠之夜。
吻别花
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年代。
关于那本英文小说,还有个小插曲,就是你在阅读中看到一个很生僻的词:kiss-me -at-the-gate, 直译是“在门口吻我”,出现在小说第五章,当盖茨比带着尼克和刚刚重逢的黛西去他的海边别墅和花园转转的时候,黛西用她迷人的低语称赞了园中几种花草的香气。
所以你能断定,这个“在门口吻我”也应该是某种花草,但字典里没有,好几种字典里都没有,你就去问何老师。何老师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说,你去问问陆老师吧,她是教词汇学的,这种构词法很特别。
你去见陆老师,她低头笑了又笑,说这种构词法很常见啊,像勿忘我:forgetme -not, 含羞草:touch-me-not。至于你说的这个词,我看就是忍冬花,也就是金银花,你看原文不是这样写的吗——“淡金色的味道”。你也可以去问问屈老师,他是教翻译课的。
屈老师不愧是教翻译课的,他很坦率,说可以直接译成“吻别花”,因为这是文学作品。至于是不是忍冬花,他没有判断,说要不你再去问问何老师吧,毕竟他是教英美文学的。
你没有再去问何老师。你听说过,当年三位老师从南方同一所大学毕业,是一起分配来到你母校的,那是许多年前,他们风华正茂的年代。然后他们就走过了冬天,又走到春天。但吻别花到底是不是忍冬花呢,直到现在,你也不能确定。
叶芝不老
发生恋爱了,到另一个城市去看她。冬天,萧索的林荫道,拐角处的教堂。你们在松花江边来回漫步,说着古往今来的恋人絮语,比如叶芝的诗:“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沉沉……”
就像树上的雾凇吧?她笑问,想象着某种白发苍苍的样子。
《当你老了》啊,你由衷感叹,说这首诗是叶芝写给爱尔兰女革命家昴德·冈昂的。叶芝对她一见倾心,似乎毕生都在追求她,也毕生都在被她拒绝。但叶芝就是叶芝,被虐千遍,仍如初恋。可以说,叶芝对冈昂的追求是纯粹的,就像是对追求本身的追求,这首诗也因此名扬世界。
——这个冈昂像个男孩儿名,她比叶芝的年纪大吗?
——不,应该比叶芝小一岁,你说你记得。
——那为什么这样写呢?当冈昂老了,叶芝岂不是更老?难道他自己就不会变老吗?她咯咯笑着,一连串反问。
没想到她会这样问,你说当然了,叶芝一直优雅到晚年,他从不穿深色衣服,总是那套宽松的浅色外衣,但也会老。实际上叶芝结婚时五十多岁了,与海德李斯小姐——这是女孩儿名。然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女儿,叫安妮。叶芝非常喜爱安妮,经常带她去玩。有一天父女俩下了公交车,走到家门口,安妮刚要按门铃,叶芝赶紧上前说,小姐你找谁啊?噢,一定是找我的女儿安妮,她和你年龄差不多大……
突然感动了,你发现她的睫毛上若有雾凇,声音很轻地说,是我错了,你也错了,叶芝不会老!即使冈昂老了,海德李斯老了,安妮和现在的我们都老了,叶芝也不会老!
深情遗忘
是这个女孩儿吗?也许不是,反正她后来离开了你。
那次她离开你去南方,在你的记忆里有两个版本,都是那样如诗如画,不知是两个人离开,还是一个人离开两次,但季节都是在春天,地点都是在车站。吻别花可以开在花园,而更多的是开在车站。
——四月印象:穿着牛仔裤,提着旅行箱。买一张车票,去诗和远方。喜欢说英文,带点东北腔。这些杂乱的事情让你想起她——年少、轻狂、迷人、开放。
——暮春倩影:你默默送她上火车,你在站外,她在站里。车要进站了,你看见她扬了扬手,一甩长发,就那样走了——黄昏背影,脉脉余晖,那一年,她三十二岁。
后来你们还有几次通信,每次都写得很长,南方杏花,北方桃花的。但这么多年,所有的通信都已不知去向。春天消失了,连同姑娘们芬芳的手稿。
有一天你发现,你竟然想不起她的名字了。
为此你深感不安,直到有一天,你在一本关于康德的书中找到了例证。据说康德曾因为什么事,导致他与相伴多年的兰普先生分手。后来他对此有所愧疚,并担心这名字会留在他记忆里,于是就在日记中写道:“千万记住,兰普这名字必须被忘掉!”
啊,康德,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
这例证不仅让你感到安慰,而且简直是迷人的——为了忘掉一个名字,伟大的康德竟如此郑重,提醒自己千万记住,必须遗忘!也许世界上真有一种遗忘,是饱含深情的遗忘,因为太刻骨铭心了,所以才不得不遗忘,也必须遗忘吧。
成熟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有一首诗叫《蓝莓》,他写道:“大小就像你的拇指尖,蓝莓/是真正天空的蓝色……其实你应该看见,所有的蓝莓/都是一起成熟的,而不是/有些熟了,有些还绿着”。
这首诗虽然短,却很有意思,就像你和你的同学们,都成熟了,即使有个别青涩的,也要努力装出成熟的样子,唯恐被遗忘在什么年龄段或时间点上。
这首诗是你的同桌老林译的,献给大学毕业三十周年班庆。老林也在大学教书,却不太搞学术,迷恋翻译,这些年译了很多东西,大都是诗歌,东一句西一句的。大学是依靠翻译的,但却不相信翻译,因为论文少,人脉差,老林五十多岁了,职称才是副教授,而且据说夫妻关系也不好,妻子抱怨他不求上进,甚至怀疑他出轨,原因是妻子听老林的同事讲,老林好像不够忠实。老林急了,就和妻子一起去找同事对证。同事说误会了误会了,是说你的翻译,有的译文不忠实原文。老林松了口气,让同事举例,逐一反驳,滔滔不绝,最后还高傲地扔下一句话,好像是引证哪位大师的“有时候,原文也不忠实译文”。
这句话让妻子更加恼怒,忍无可忍,非让老林说清楚,到底谁对谁不忠实。在妻子心目中,她就是原文,而老林是译文。
所以那次班庆聚会,听老林朗诵了他译的《蓝莓》之后,同学们都笑了,说是啊,我们都成熟了,只有老林,似乎还绿着。其实大家心里,也有点欣赏老林。不是吗?至少他还绿着。
四十年后
毕业四十年了,还记得范婉珍吗?
她是教我们口语课的外教,来自美国波士顿,全名叫弗朗西斯·史密斯。范婉珍是她的中文名,不知谁给起的,听起来很中国、很淑女。
很淑女的史密斯小姐金发垂肩,眨着快活的蓝眼睛,讲课时往往会坐在讲台上,有时还嚼着口香糖。这给我们的感觉不太像老师,倒像个偶然来到中国的一个波士顿女孩儿。事实上,范婉珍的年龄也真不大,也许才二十出头,比我们许多当学生的还要小。尤其班里的几个男生,都三十多岁了,有时答不上问题,坐在位子上发呆,范婉珍走过来,顺手抚摸其头发,就像小妹妹在教诲和鼓励不成器的兄长,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忍俊不禁。
所以范婉珍上课很受欢迎,每当她走进教室,我们的气氛就活跃起来,因为这样上课,很像做游戏,今天这个游戏,明天那个游戏,我们虽然大二了,但和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史密斯小姐在一起,没大没小的,就如同小学生或中学生。比如那年万圣节,她亲自指导,让大家各种装扮,然后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闹了一个晚上,让系里很紧张,好在有惊无险,给那个冬天和我们的大学生活留下了陌生的嘉年华般的记忆。
当然,范婉珍有时也会认真讲一些东西,比如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我啥都不是,你是谁?/你也啥都不是,我们正好是一对儿/但有人会到处散布,所以别说出去。”还有一首,也是狄金森的,我们班的王妍同学最喜欢,她译出来之后,大家也觉得非常美,几乎超过舒婷的《致橡树》:“在这些日子里,众鸟飞还/但总有一两只,要回头看看/在这些日子里,天空找回古老的六月的语言/那些蓝色的错误,金色的诡辩。”
史密斯小姐喜欢狄金森,可能和她的家乡有关。波士顿是马萨诸塞州的首府,而狄金森也恰好是马萨诸塞的。范婉珍说她爸爸是个工程师(engineer),妈妈是个登山运动员(mountaineer),两个“尼尔”(-neer)相爱,生出了她,一个喜欢唱歌和游戏的女孩儿,当然,她也喜欢中国。有时她一边讲课,一边打口哨,或者哼起她家乡的小调。
对了,范婉珍还教我们唱过许多英文歌,我至今会唱的几首,如《很久以前》啊,《克莱门泰》啊,《将来会怎样》啊,好像都是她教的。特别是那首《四十年后》,说是一所著名中学的校歌,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回旋——
四十年后,天各一方,声名远扬
那时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歌唱
……
这首歌的时间顺序正好颠倒,从将来说到现在,所以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如今,我们大学毕业真的已四十年了,虽然没有谁声名远扬,却早已天各一方了。还能穿越四十年,再回到唱那首歌的时候吗?史密斯小姐给我们打着拍子,她那么年轻,一头金发却闪耀着秋叶般的光芒。
黄金时代
在秋天的街头漫步,风吹银杏,落叶如金。走着走着,你会不时地停下脚步,突发奇想,在这些落叶里,会不会有一张纸条呢?就像你在卡夫卡的某本书中读到的那样,落叶里发现一张纸条,不知是谁写的,也不知是写给谁的,上面写着一句很重要的话,重要到你必须付诸行动,必须做点什么才行。
是的,谁的生命中不曾有一张重要的纸条呢?而你的那张纸条,却是同学们都见证过的,虽然时隔多年,大家可能已淡忘了。
你说那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的毕业晚会上。中间有个游戏,让每个同学都在纸条上写一句话,叠好交上来,然后让男生抽女生的,女生抽男生的,不管谁抽到谁的纸条或纸条上写的是什么,都要当众读给大家。这有点像现在超市里的盲盒,不过写纸条的人也要站起来示意,就好比能和厂家直接见面。
你抽到的盲盒是这样写的:黄金时代永远在你的前面。字体娟秀,没有落款。
站起来吧,哦,是她,嘴角有颗好看的美人痣。你说谢谢,她说不用谢,然后就都坐下了,但不知为什么,男生有打口哨的,女生有抿嘴笑的,再看那个女生,好像很不自在的样子,咬着嘴唇,眼圈发红。幸亏轮到下一个了,否则她可能会哭出来。
后来你才知道,这个女生和班里的另一个男生是恋爱关系,这张纸条,应该是写给那个男生的,被你抽到了,客观上有点横刀夺爱的味道,但那也没办法,盲盒嘛。
大学毕业这么多年,许多同学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包括那个女生,可你却从没忘记那张纸条。“黄金时代永远在你的前面”,仿佛这是一句耳语,一段歌声,一个预言。总之,这句话给了你很多鼓励,仿佛有了这句话,你就理所当然,会前程远大。
但近几年不同了,你说开始有点不太喜欢这句话,觉得它很空泛,而越不喜欢,就越会想起,每当夜深人静,你打开床灯,这句话就会浮现脑海,仿佛黄金时代就是橘色的灯光,橘色的灯光就是黄金时代。这几乎影响到你的心境,就连做梦,有时也会梦见这样的灯光,空空地照着。
你问我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有点矫情?还是已经失去了理想?
理想,你说得对,我们这代人从小就没离开过理想主义,但说到底,理想并不等于人生的具体目标,它更像是我们天真的向往,朴素的初心,需要不断回去看看。我想起了堂·吉诃德,他骑在马上,漫无边际地说:“黄金时代与黄金无关”。其实世界上许多东西,你向前看,是抒情性的;你向后看,是叙事性的。这就像灯光,灯光在本质上是叙事的,而世界上所有的叙事,同时也具有抒情的特质。所以真正的灯光,总是既能照亮后面,也能照亮前面。
而且你的故事并不完整,当年的晚会上,还有另一个女生,她的纸条是写给你的,忘了吗——“你的幽默,你的歌声,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但抽中这张纸条的却是另一个男生,人老实得像个农具,从来不开玩笑,更很少唱歌。所以他读纸条的时候大家也都笑了,并把祝福的目光投给你和那个羞答答的女生。这一段你怎么忽略了呢?当然,她和你并没有走到一起,正像你抽到纸条的那个女生也没有和她心中的男神走到一起一样,毕业后都没怎么联系。同学就是同学,游戏就是游戏。先哲有言: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才充分是人。说得多好啊!
总之,正如人们常说的,黄金时代是朴素的,没有人看重黄金的时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它更多是一种精神向往的隐喻,青春憧憬的隐喻,而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转身,这些都还在那里,就在我们即将分手的毕业晚会上,因为,那是我们正在游戏的时候,充分是人的时候,你说是吗?
匆匆数言,和你共勉。秋天的落叶里总会有一张纸条,不知是谁写的,也不知是写给谁的,但如果你能找到它,那就意味着找回了一切。俯身拾起,字体还是那么娟秀,话语还是那么温馨,黄金时代还是在你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