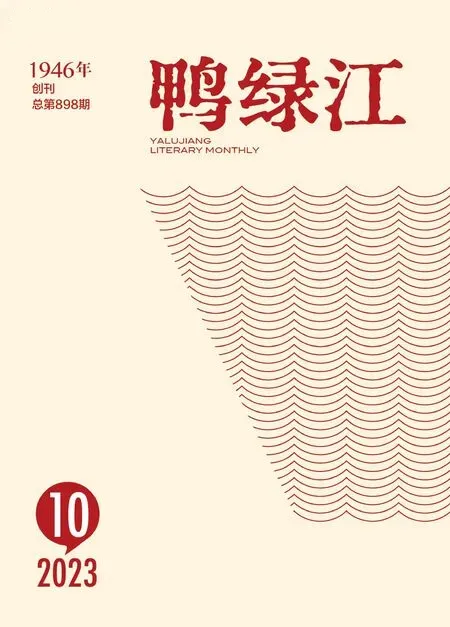静夜思(组诗)
2023-12-10季士君
季士君
局部
一个人坐在山坡上
听着远处传来
时断时续的萨克斯曲子
那位初练者
正试图将一首曲子
演奏得更加完整
鸟儿背负道路飞行
白云在消失之前
擦尽天空的泪水
远处的曲子依然时断时续
我两手空空
缓步走上归途
一部分秋天
被我留在山中
两座山
两座山的中间
是一道峡谷
深深的峡谷
装着无数的石头
装着无数的白天和黑夜
也装着一座小小的寺庙
深深的峡谷
装不下一场大风
也装不下行色匆匆的过客
为了让峡谷
能装下更多事物
两座山从不分离
也从不靠近
更多的时候
它们只是安静地
坐在峡谷的两侧
彼此对视
直到相互厌倦时
才会一道等待一场大雾降临
每一条河流都穿过回忆
你并不清楚
一生中会遇到多少条河流
但你知道
每一条河流都穿过记忆
上游,或者源头
依然需要溯回
而你从不过问
哪些河水,会在流淌的过程中
不知去向
也不记述
哪些水在河流的尽头
等待另一些水
现在,你还站在岸边
凝视着一条河
像穿过回忆一样穿过你
静夜思
一座山
怀抱着石头入睡
星星即将在天空和水中往返
风在河里顺水推舟
徐徐降临的夜幕
在一群飞鸟的协助下
把大地一寸寸埋在月光里
练习抒情的人
一再埋首
蘸着夜色
在白纸上写下黑字
名画
古人稍动笔墨
便让我们陷入想象
一些树已经结果
一些树刚刚开花
它们在纸上相遇
两只鸟在枝头上
打着哑语
山水尽头
砍柴的人面容模糊
似隐者
不动声色
拒遇来访
这是一幅真迹
来自六百年前
他们一边谈论
一边将画取走
在墙上留下
一枚钉子和钉子周围的空白
暮春
我习惯称春天最后的一段时间为暮春
而同样是秋天的最后几日
我一般都叫晚秋
尚未破土的种子继续为大地疗伤
晚霞替天空补给爱的火焰
蚂蚁的防洪工程尚未启动
暮色罩着田野里劳作的人
也罩着把羊赶回圈里的人
刚刚长高的蒿草
开始在山坡寻找出路
我时常站在山上
在迎来朝阳的地方
和山峰一起送走落日
直到月亮又一次升起
反复照亮它眷顾的那些地方
春天,像秋天一样
都有所剩无几的时候
扫地的人
一把扫帚
是他唯一的工具
用来扫门前雪
也扫梦里花
扫一屋
也扫天下
有一天晚上
他把影子扫净
堆放在墙脚
让空空的院落
只剩下一片月光
收割
我看到
一把镰刀正用石头
擦去身上的锈迹
它的光芒
被秋风一点点召唤出来
红着脸的高粱们
在风中又挺了挺
即将被收割的头颅
我即将看到
月亮把自己挂在夜空
在黎明之前
它将对那片高粱
完成最后一次笼罩
数沙子
有些时候
我喜欢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
就像现在
我坐在河滩上
数着一粒粒沙子
只有数着沙子
才会忘掉沙子
或者说为了忘掉沙子
我必须一直数下去
总是没能将沙子数完
我就开始数着岸边的树
数着在树梢上
飞来飞去的鸟儿
日食之日谈及忧伤
这个下午我们坐在一起
不谈论夏至,不去看日食
而是谈及许久未曾谈及的忧伤
曾落满花瓣的园子
又落下被枝头抛弃的果子
我们掸了掸空无一物的衣襟
假装能将那些花瓣遗忘
光为影子而存在
河流将自己拖往远方
我们坐在石桥上
风把水面上的影子吹出一道道波纹
这个下午,我们感到莫名地忧伤
以至于谁都没抬头看看天空
只剩下四分之三的太阳
文物
被岁月遗弃的
又被岁月捡拾
这些器皿出土后
就来到博物馆
在玻璃柜里
它们正努力回到自己
并暗示摩肩接踵的参观者
相继回到青铜时代
寒暑易节
万物共用的时间
让山川褪色生命衰枯
也让一些无用之物价值连城
雨中山行
因为一场雨的加入
我与山中万物
重构了一段往事
伞成为回忆的道具
可以遮掩
或者躲避
树木的生长
只是为了饱经沧桑
没有一片叶子
会放弃秋天
正如没有一滴雨
肯随我下山
从往事走出
总有一条路会将我们带向墓园
一条陌生的山路
把我带向墓园
在此之前
我并不知道墓园
就是这条路的终点
就像我不知道这一天
是秋天的尽头
既来之则安之
索性坐下来
想一想有关余生的事情
以及一首未完成的诗
只是我暂时
还不配占据风水之地
夜幕已经悄悄降临
死亡正将我包围
先于黑暗
后于宁静
自责
不知孩子把什么东西弄丢
我正在读一本诗集
听到窗外传来
一位母亲责备孩子的声音
我放下诗集
一边听着孩子的哭声
一边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我知道这些年
自己弄丢了很多东西
可是再也不会听到
母亲责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