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物考古报道何以情有独钟
2023-12-07庄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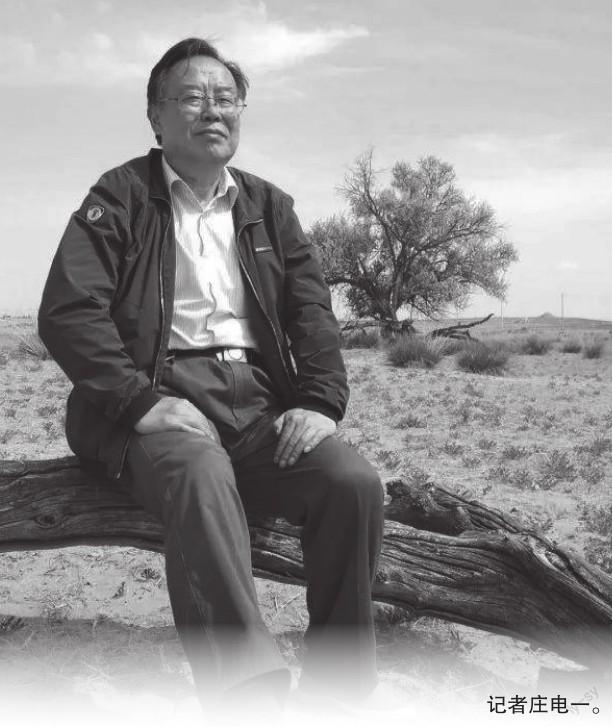
一个记者,面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有机会了解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这是其他行业都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这个特点和优势,既可以让记者具有广博的知识、有望成为社会活动家,也容易让记者浮于表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自以为是,好像什么都懂,实际上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
能否深入到某些领域、进而成为业内的知音、乃至“行家里手”呢?这是我一直探索和追求的。
我有30多年的新闻工作从业经历。其中,关注文物和考古,对相关报道保持足够的热情,是我一以贯之的。
一本书的特殊“礼遇”
现在,许多人退休之后都颐养天年了,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关注的人也会越来越少。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退休后出版的《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学术界和各界读者竟然如此关注,给了我在职时都没有“享受”的礼遇:一是出版社和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二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慨然为本书写了序,三是有关部门联合为这本书召开了出版座谈会。
《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是反映考古成果、追踪西夏研究、探寻西夏文明的,多是我采写的新闻稿件,基本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因为此前尚无这类图书出版,所以也算填补了一个空白。大概正因为如此,2020年9月,这本书在甘肃文化出版社一面世,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全国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不仅在百忙中拨冗作序,而且高度评价了这本书。尤其让我感动,也让相关学者感到不同寻常的是:他不是一般地应付了事,而是认认真真、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千字。在序言的开篇,他就写道:“在西夏学界,提到庄电一先生无人不晓”。他还称我是“西夏学前行的鼓手,也成了西夏学专家们的知心朋友”,还说我“这种浓烈的历史文化情怀和对传统文化矢志不渝的坚守值得大家学习”。对史金波先生的过高评价,我是受之有愧的,但说我是“西夏学专家们的知心朋友”,却是个事实,也令我特别欣慰。
专门为《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出版召开座谈会,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此前我已经出版过十多本书,对包括自以为分量较重的书籍在内,我都没有,也没有谁提出要举办座谈会。为《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举办出版座谈会,是寧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甘肃文化出版社的一致意见。2020年11月10日,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郧军涛一行数人专程从兰州赶到银川,郧军涛事先还写好了发言稿,对全书做了精辟的分析。座谈会开得很热烈,著名民族史学专家陈育宁教授、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西夏学专家、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汤晓芳等到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到场采访的十多位记者全都发了言。
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议论都因这本书引起。这样的“礼遇”,对我这样的普通记者来说,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一群相互信任的“知音”
在我看来,称我为专家学者的知心朋友,是史金波先生对我的充分理解、高度信任。他把我当知己,我也把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都当作知己。2009年,史金波把新出的西夏学专著《西夏社会》从北京寄给我时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我在认真学习、研读之后,觉得有报道价值,就写出报道《〈西夏社会〉再现西夏社会面貌》,《光明日报》将它放在了头版的突出位置。
要做好文物、考古报道,不仅要了解文物的价值、了解考古的意义,而且要了解专家学者的学术追求和价值观念。
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展示厅,有一张报纸被装入镜框,那是2010年6月10日的《光明日报》。之所以能“享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是因为这张报纸在报眼位置刊登了我的一篇稿件。有人会问:报道西夏学研究成果的媒体很多、相关稿件则更多,为什么只有这一篇独享“尊贵”?因为这篇题为《宁夏大学研究成果再次印证:“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的报道,不仅反映了西夏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表达了他们的学术追求和科研志向。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曾担任宁夏社科院院长、银川市市委书记、宁夏大学校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的民族史学专家陈育宁,在西夏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所以在辞去一个个官衔之后,就出任西夏学博士生导师,这种“传奇”经历实不多见,也非常人所能。有感于他在教育界、学术界、党政界的从容转换,我写出了《陈育宁:政坛·杏坛·书案》的长篇报道,《光明日报》编辑部不惜以半版的篇幅刊登。这篇报道也因为准确的定位和如实的报道而被陈育宁特别看重,便有意将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著中。
在文物、考古界,我真的有许多心心相印的知音。曾获“毕昇奖”的西夏学考古专家牛达生,是在退休后才“崭露头角”“广为人知”的,他曾不被人“待见”,但我在深入了解了他的学术研究和精神追求之后,深感对他值得大书一笔,于是便在《光明日报》上发出了整版报道。中央民族学院历史专业毕业的周兴华在归队后担任过宁夏博物馆馆长、宁夏文物局副局长,但因他曾经长时间担任乡、县领导干部、脱离过所学专业而被个别人质疑,但他具有非常敬业的精神,即使在年过七旬之后仍然坚持野外考古,我认为仅此一点就值得给予肯定,为此,我写出了《实地考察不辞劳苦,勤奋笔耕孜孜不倦:周兴华年逾七旬新著不断》等多篇报道,他也以我为知音。远在甘肃武威的孙寿岭,在当地发现的西夏文泥活字印刷品遭到质疑之后,为了找出西夏文泥活字的特征,亲手雕刻大量西夏文泥字并在家中土炉子烧制,然后按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方法印制成书,这样的“壮举”,非常人所能为。有感于他刻苦钻研的精神,我为他写出了七八千字的长篇报道,他也将我列为知心朋友。
一点知名度的“效应”
了解考古、理解学者、懂点学术,让我成为专家学者们的知音,也让我的采访格外得力,格外顺畅。
因为对文物、考古做了许多深入的报道,我渐渐在这个领域有了点知名度。1994年,《光明日报》编辑部抽我到总部的“重点报道组”,专门采写重点报道。其间,我抽空到国家文物局采访,结果一报单位和姓名,不用出示记者证,他们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原来,这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因为看过我的许多报道,对我都有相当的了解,有位负责人竟然说:你采写的考古报道,我几乎都看过!有了“相知”的基础,我的采访便出人意料的顺利,他们不仅热情地接受我的采访,而且向我介绍了从未向他人透露的线索,我也因此得以发出了四五篇独家新闻,其中,《更新展览:博物馆振兴之路》还刊登在了《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中央电视台摘要播出了其主要内容。
2006年,我参加中宣部组织的“建设新农村”主题采访到了甘肃敦煌。在同行者去参观时,我單独采访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因为我在1987年曾兼管过甘肃记者站,还参加过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写了一些报道,便被她记住了。这次见面,她专门提到此事。这次采访,研究院的秘书要求我与樊锦诗的交谈不要超过20分钟,结果我的采访远远突破了这个限制。这个采访,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在三四个小时里,我们几乎无话不谈,最终,我发出了五篇颇有特色的独家新闻,其中,《让敦煌国宝有个“喘息”》准确地反映了樊锦诗的忧虑和设想,在《光明日报》上占了半版。
1999年,尘封多年的西夏塔群遗址,在贺兰山拜寺口双塔附近被发现。当地一家信息灵通的新闻单位记者“捷足先登”,但他们的采访却被拒绝了,因为考古尚在进行中,许多问题尚未搞清,宁夏的考古人员不想先捅出去。这位记者朋友不甘心,特意打电话给我,他十分肯定地说:你去采访,一定没有问题!果然,正在现场清理遗迹的考古人员见我来了,不但没有拒绝,反而做了详细介绍,还热心地提供了考古图片,这也让我这篇报道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被大量转载。
就是这点“知名度”,让我在文物考古报道中常常抢占先机,我的新闻报道也因此进入良性循环。
一块必须坚守的“领地”
人们常常讲“守土有责”,这一点,对记者来说尤其重要。作为《光明日报》常驻宁夏的记者,我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应该密切关注,如有报道价值就该及时报道,不能有遗漏。我常常提醒自己:我是光明日报社派驻到宁夏的记者,也是光明日报社在这里唯一的记者,如果我不采访、不写出报道,相关的新闻就不能反映在《光明日报》上,如果重要的新闻被别的媒体抢占了先机,那就是我的失职。
1990年11月下旬,位于贺兰山深处、人迹罕至的西夏古塔,被不法分子用炸药炸毁。宁夏考古人员闻讯立即要去现场考察,他们问我去不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成为唯一去现场的记者。我的想法是: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去现场。不去现场,写稿就不踏实。当时,我未做任何准备,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和笨重的棉皮鞋就上路了。在三四个小时的攀爬,甚至“丢盔卸甲”之后,我精疲力尽,最后一个赶到现场,但我抓到了第一手资料。虽然往返七八个小时的跋涉累得我几天都腰酸腿疼,但我却写出了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的独家新闻。此后,我跟踪报道,相继写出许多广受关注的新闻。
实事求是地说,与陕西、山西、河南等“文物大省”相比,地盘小、人口少、文化基础薄弱的宁夏,文物资源还算不上特别丰富、新闻报道的优势也不明显,但宁夏的文物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只要深入发掘、抓住特色,还是有许多东西可写的,我就是以石头缝里抠新闻的韧劲抓文物考古报道的。对贺兰山岩画、水洞沟旧石器遗址、吴忠市隋唐墓葬群、固原南塬双拥合葬墓、海原县菜园新石器遗址、同心县古生物化石、西吉县古钱币、贺兰县宏佛塔、盐池县“骨简”,我都做过连续的、有影响的报道。
一份始终不变的“职业执着”
关注文物、关注考古,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渐渐地就变成了职业“执念”。在宁夏,我守土有责,关注文物、考古不放松;走到外省、乃至外国,我也特别留意文物考古的情况,如果可以写稿就不会轻易放过。早年,我奉命到河南省采访一起突发事件,忙里抽闲抓到了几篇考古报道。1987年、1989年,我两度兼管甘肃站,期间采写了多篇文物考古稿件,其中《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有重大发现》《天水放马滩出土战国木板地图》都曾引起高度关注。调回总部值班时,我抽空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和在北大红楼办公的国家文物局采访,都有多篇“斩获”;2002年,参加中宣部组织的主题采访活动,我“顺手牵羊”采写了多篇文物、考古报道。2004年,我奉命到青海采访时任青海大学校长李建保,在采访任务完成之后,我走进青海省博物馆进行采访,相继发出了4篇稿件。2006年,我又一次踏访西北5省区,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我弄了几个“自选动作”,仅在敦煌一地就采写了8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独家新闻”。其中,《莫高窟北区洞窟神秘面纱被揭开》《敦煌百年出土汉简超过2万枚》,是对这些考古成果的首次披露。在敦煌市博物馆,我发现游客稀少、馆内冷冷清清,就发了一篇“记者来信”:《旅游别冷落了博物馆》。在深入交谈中,敦煌市博物馆两位馆长向我披露了一条“隐藏”很久的新闻:馆内珍藏着一片写有文字的西汉麻纸!我如获至宝,立即展开采访。《敦煌发现写有汉字的西汉麻纸》刊登出来后,立即引发中央、地方多家媒体的跟踪报道,仅中央电视台就连播了4次,其中有的报道直接抄录了我的稿件。
走出国门,我不仅关注文物古迹,而且也总想写点东西。2002年,我到泰国访问,抽空采写了3篇稿件,其中两篇是与文物考古有关的:《古代建筑艺术的大观园》《一段历史,几处景点》展示的都是泰国的历史文化。2023年,我到吉尔吉斯斯坦旅游,实地踏访了碎叶城,写了《大诗人李白在这里留下了童年的足迹!》。
在2012年出版的《胜日寻芳》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都与文物考古、古迹名胜有关。
2016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心中有个遗憾,就是没有去过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西夏故地黑水城。2017年8月,听说西夏学论坛将在内蒙古阿左旗举办,会议期间将考察黑水城,我立即请求参会。会后,我和与会代表一起穿越无人区、奔波七八个小时考察了黑水城,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先后发出了4篇报道。其中,《黑水城,黄沙掩盖不住的文明》,是在现场考察后满怀深情地写出来的。
一片冰心在玉壶
报道考古动态和相关研究成果,我不遗余力;对文物保护中的问题、批评破坏文物的现象,我也毫无顾忌。其中,有的报道还制止了破坏、扭转了事态:《没有库房,没有措施,缺人管理:基层馆藏文物受损、被盗严重》《古都洛阳大量文物流散民间,应尽快划拨专项经费征集收购》《洛阳盗窃和走私文物犯罪为何禁而不止?》《警惕对文物的“建设性”破坏》《基建施工与文物保护的矛盾亟待解决》《贺兰山岩画在“呻吟”》《西夏古塔被炸案应予高度重视》《让文物保护法“硬”起来!》《中宁石空大佛寺呼救!》《宁夏岩画保护:路在何方?》《长城还有多长,还能保存多久?》,都是一针见血、毫无遮拦。宁夏发生的西夏古塔被炸案、吴忠城建古墓破坏案、青铜峡盗墓人被埋致死案,我都在深入采訪的基础上做出了客观报道,不仅引起广泛关注,而且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旅游开发中如何兼顾文物保护的问题,我则做了具有思辨性的报道。
2003年,宁夏某地大规模进行城市改造,但他们事先未进行考古钻探,在施工中发现了文物也不报告,当地文物部门下达停工通知不管用,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再下通知,他们仍然不予理睬,照旧施工。自治区文化厅厅长、文物局局长深感事态严重,便会同专业人员一起前去督办,仍然毫无结果,最终也无功而返。我以记者身份应邀到场,目睹了当地个别人员的嚣张气焰和专业人员的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我感到非常压抑、也非常愤怒,当即表示:你们可以就这样算了,但我绝不能容忍!有人嘲笑我“天真、幼稚”,但我坚持认为:如果容忍此类行为,今后的文物保护将难以为继!我要“摸一下这个老虎屁股”。在其他媒体都不介入的情况下,我单兵作战,发出了旗帜鲜明的批评报道。稿件在二版头条发出后,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跟踪前来并两次做出报道,有关人员的嚣张气焰很快就被刹住了,他们不得不到银川向文物考古部门道歉,拨出专项经费并做出郑重承诺,表示一定要积极配合文物部门的清理工作。宁夏的文物保护工作,自此也纳入了正轨。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因此对我一再表示感谢。
之所以毫无顾忌地做出批评报道,完全是受责任心驱使。在采写文物保护类的稿件时,我没有私心杂念、没有个人企求,不看谁的脸色,也从不怕得罪谁,我的底气,来源于深入采访,来源于实事求是,来源于客观公正,也来源于文物考古人员的理解和支持。
一个不能缺少的“话语权”
文物考古报道很容易流于肤浅,而肤浅的东西是很难激起读者兴趣的。让文物考古报道更有知识性,更耐看、更有可读性、更有吸引力,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在文物考古报道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看出记者的学识水平、文字功力、工作作风、职业操守。为此,我把采访的过程变成学习的过程,也努力将自己从“门外汉”变成“门内人”,力争将每一篇文物考古报道都写到位,将其承载的信息“吃干榨尽”。
2001年至2002年,考古人员对西夏陵三号陵进行清理发掘,我驱车到工地采访。一连串提出了许多记者都不会问到的问题,考古领队对我的提问有点应接不暇,便毫不客气地发泄不满:“哪个记者会像你这样,问得这么细、这么多!谁不是了解一点情况就走了?我们就发现这点东西,如果都告诉了你,以后还怎么写考古报告?”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就很熟悉,也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也不客气,情绪激动地回敬:“问不问、问什么在我,这是我作为《光明日报》记者应有的素质;你可以少回答,也可以回避,但我不能不问!不搞清这些问题,我的稿件就写不深、写不透,读者就不爱看!”当时,现场气氛有点尴尬,这也是我头一次遇到的情况。过了一会,这位领队又要求我在所写的报道中署上在场那位考古队员的名字。虽然感觉自己写完的稿件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还是抽空请这位领队审定,结果,这位领队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我接着咨询了署名问题,没想到,原来那么坚持要署名的领队,竟然改主意了:“你的这篇报道,我们并没有提供文字材料,你所用的也都是你自己的语言,我们就不署名了。”
具备相关业务知识,才能争取应有的“话语权”,才能与专业人员平等的交流、深入的对话,否则,知识贫乏,作风漂浮,专业人员就不愿意多谈,采访就深入不下去,也就不能了解到别人了解不到的东西,这是我工作多年的切身的感受,也是我不断学习的一个动力。
30多年来,我采写的文物考古类的稿件,几十次走上《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二版头条或其他重要位置,编辑部也多次给予充足的版面,我的这类稿件也多次获奖。特别是有些稿件一经发表就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进而扭转了事态、改变了人们的旧观念,让我感到充实、也有了成就感,这也是我对文物考古报道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原因。回头审视以往采写的这些稿件,尽管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需要改进的方面也有不少,但我还是可以说:我竭尽全力了,也对得起这个职业了。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