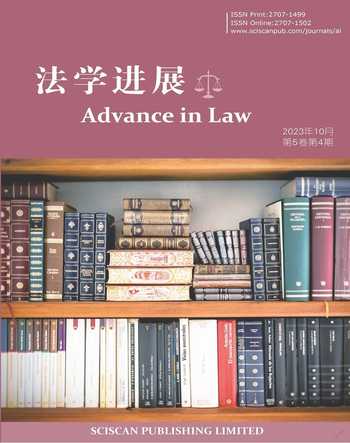家长主义视野下性侵害儿童犯罪的出罪路径
2023-12-06张锐
张锐
摘 要|在性侵害儿童领域,刑法家长主义发挥重大保障作用,正向现代软家长主义发展。刑法家长主义的运用应当具备四大要素,即必要性、相当性、强迫性和有效性。儿童性权利保护模式随家长主义变化而变化,从“家长本位”转型为“儿童本位”。我国现行性侵害儿童犯罪规定在儿童性同意年龄和年龄相仿条款落实上具有合理性,有效维护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儿童优先原则。受制于法律本身的落后性,无法对青少年间的性探索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法不可轻变,“但书”条款在现行法律体系下,通过间接指导法官的个案判决,能够发挥出罪机能。司法解释应当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正,发挥其能动性。
关键词|刑法家长主义;儿童本位;年龄相仿条款;“但书”条款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中国加入《儿童权利公约》,为了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我国逐渐建立、完善种种有关儿童的机构、制度和规范,以保障儿童权利和利益。新时代高新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使得儿童获得性信息的方式和数量呈指数级递增,同时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变化也促使儿童过早地接触和了解性行为,从而增加了性侵害儿童犯罪的概率和机会。然而,如果为了保护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全面、绝对性地优先保护儿童利益,乃至于将与儿童进行性接触的行为一律视为犯罪,则会导致青少年之间自愿的性探索也会被评价为犯罪,从而不当地扩大性侵害儿童犯罪的范畴。
《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并对猥亵儿童罪的刑法体例和加重情节进行修正,表明我国对儿童保护的模式处于转型期间。更有甚者,网络时代的“隔空猥亵”也被司法裁判评定违法。种种现象表明,我国有关性侵害儿童犯罪的范畴在立法与司法上均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性侵害儿童犯罪的成立,无疑与儿童的自我决定权有关,而刑法对于儿童自我决定权的限制,其背后是刑法家长主义在发挥作用。本文立足于刑法家长主义,探寻现行法律机制下性侵害儿童犯罪的出罪事由,以求实现儿童权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协调与平衡。
一、刑法家长主义的变迁与儿童性权利保护的发展
(一)刑法家长主义的概念及原则
刑法家长主义富含道德关怀,刑法具有严厉的刑罚制裁,所以具有家长的形象,既可以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又可以保护被害人,对个人法益进行制约。刑法家长主义最初在经济领域得以适用,国家为了经济干预的需要,通过控制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来保障国家经济发展。此后,它在安乐死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刑法通过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从而限制不恰当的意图帮助他人自杀的人实施犯罪。刑法家长主义并非直接限制自杀者的行为,而是通过对他人——即那些有能力帮助自杀者的人的行为进行规制,从而间接维护自杀者的利益。至于各国对安乐死的规定存在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对刑法家长主义的不同价值认定。在私法领域视为至高无上的自我决定权,在公法领域应受到何种程度的制约,这一问题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法律家长主义并非需要指导人们应该去做什么,而是要防止人们遭受他们并未选择承受的损害或风险。”
在当今的法律制度下,刑法家长主义的适用仍有其存在的意义。默认个人自我决定的行为无需刑法干预,但个人在错误的认知或时机下做出的决定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刑法家长主义的适用应与自我决定权形成动态平衡,遵循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原则进行。自由、平等和正义等基本价值都具有指引原则设立的功能,对此我们需要强调正义的优先性。正如罗尔斯所表达的,“正义是优先于善的,法律的设立尽管满足社会最大剩余额的提高,但是其若违反契约论的原初状态约定,那么该法律的设立也是不合理的。”
刑法家长主义的具体适用原则可以解析为四要素:(1)刑法家长主义的适用是为了保护个人自我利益以及生存发展;(2)个人作出的决定必须是自身的真实意愿表达;(3)通过价值判断,认定该个人行为会损害个体的自我发展;
(4)刑法干预了个体作出的决定,并且最终没有损害个体的利益。上述四个刑法家长主义的适用原则,体现了刑法家长主义的正义性、强制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不论是硬家长主义还是软家长主义,都对个人身体的自主意愿产生了干预。在这种家长主义下,对于个人行为的过分控制,会影响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信任感。甚至可能使个人对自己的内在行为逻辑产生疑问和困惑,最终导致个人道德伦理体系的崩溃。个人的行为,即使没有维持或者促进自身的利益,只要其没有损害自己的利益,刑法就没有干预的空间。只有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自由,法律才能有更大的空间发挥作用。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在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有时需要适当的法律干预来防止不利影响。这是一个需要细致考虑和审慎处理的平衡问题。刑法家长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框架,使我们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能保护社会的整体福祉。
(二)儿童性权利保护的家长主义内涵
在儿童权利的保护体系中,性权利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这种权利与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其侵犯可能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對于儿童自愿的性探索行为采取了负面的态度,这基于对儿童长期利益的保护考虑。然而,这无疑涉及对儿童性权利的价值判断,进而引发了儿童性积极自由与性消极权利的法律调控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情况也深刻揭示了家长主义在儿童性权利保护中的特殊性质。
随着社会性观念的逐步开放和进步,传统两性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家长主义也突破了传统的过度溺爱和管制观念,展现出更多的包容、理解和放手。刑法在维护儿童权益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刑法对于社会与个人均有其副作用,只是在法律制度或法律制裁制度中迄今尚未能找到更完美的法律手段之前,勉强继续沿用的不完美手段”。刑法认为儿童在性行为方面缺乏成年人的决策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因此规定儿童自愿进行的性行为一律无效。这可能会给儿童带来社会认可方面的负面影响,给儿童贴上“性受害者”的标签。
当儿童成为性侵害的受害者后,家庭和社会对儿童的关注往往会强调性行为的消极性,甚至会对儿童进行道德上的批评和指责,这使得儿童的“受害”与性行为的自愿产生了割裂。尽管儿童在某些情境中可能体验到性行为的积极性,法律仍然坚定地规定性行为仅适用于成年人,这可能与他们的生理本能和实际需求发生冲突。弗洛伊德的性欲阶段理论揭示,“6至11岁是性欲的潜伏期,而11至13岁则进入青春期。”在物质丰富和精神成熟的环境下,儿童的青春期可能会提前,这显示了“早熟化”的社会现象。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儿童根据其合理需求进行的自愿性探索定性为犯罪。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重视儿童性权利的双重保护,即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实现。在综合性的儿童权利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全面考量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需求,尊重他们的意愿和权利,同时,也需致力于防止他们遭受任何形式的伤害。这一过程要求法律、社会,以及家庭齐心协力,共同营造一个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
二、刑法中有关性侵害儿童犯罪规定的利弊
(一)性侵害儿童犯罪的现行刑法保护
1.儿童性同意年龄的规定
刑法对儿童性权利的保护主要集中在性消极性方面,强调任何与儿童发生的性行为都将构成犯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未满14周岁的儿童不构成犯罪,同时,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两条法律既否定了14周岁以下儿童的刑事责任能力,也确立了14周岁为我国的法定性同意年龄。此外,刑法对“奸淫”与“强奸”做出了明确区别。该区分利用语言结构的细微差别,突出了对儿童的特殊保护,从而使得强奸罪的成立无需再证明行为人手段的“强迫性”。立法者在考虑中国的道德、社会和生理因素后,综合确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性同意年龄。这个规定预设了14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具有任何性自我决定权,任何与他们发生的性关系都可能对他们的未来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3款中,将猥亵儿童罪附属于强制猥亵、侮辱罪,规定“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这一方面显示了国家对于儿童保护的优先,但另一方面,刑法将性侵害儿童的条文规定与性侵害犯罪之后,未独立规定性侵害儿童犯罪的法定刑幅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儿童权利保护重视的不足。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模式的显著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刑法第十七条新增了一项规定,作为第三款,明确“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条款规定,年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在满足法定条件下,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次,在奸淫幼女罪的处理上,刑法增加了加重情节,明确规定在公共场合奸淫幼女、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或造成幼女伤害的行为,将受到更重的处罚。最后,猥亵儿童罪的立法结构发生了变化。猥亵儿童罪从原来与强制猥亵、侮辱罪并列的引证罪状,转变为独立的简单罪状。同时,法律还新增了若干加重情节,如多次或多人猥亵儿童、猥亵造成儿童伤害,以及存在其他恶劣情况的。以上改变反映出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模式正处于向“儿童本位”过渡的时期,更加充分地保护了儿童的消极性权利,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对儿童性利益的侵犯。
2.年龄相仿条款的落实状况
强奸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行为。而奸淫幼女类型的强奸罪,与此不同,它并不需要具备“违背女性意愿”这一构成要件,只要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并主观上故意实施奸淫行为,就足以构成犯罪。在这里,“明知”指行为人认识到女方高度可能是幼女,或者对于女方幼女身份的认定持放任态度,都构成奸淫幼女类型的强奸罪。在社会现实中,儿童间的自愿性关系以及儿童隐瞒年龄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当前法律规范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显得不足。为了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最高司法机关已经制定并发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明确指出,只要行为人明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无论幼女是否自愿,均构成奸淫幼女罪。这一规定使得14到16周岁的未成年男性与14周岁以下的幼女,即使是自愿发生的性关系,也被刑法规范认定为犯罪。这种法律认定可能导致青少年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的隐患,甚至可能引发青少年交往秩序的混乱。例如,青少年双方在生理本能驱使下自愿发生性关系后,幼女可能在不良家长的引导或逼迫下,出于追求非法利益或损害他人名誉的目的,对性关系的另一方带来严重风险,从而使得青少年的正常交往变得错综复杂。
最高司法机关之后发现在现实适用法律仍然存在诸多困惑,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中的第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我国对“年龄相仿条款”的具体落实。通常,“年龄相仿条款”是指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对未成年人之间发生的自愿性行为给予特殊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通常会减轻或免除处罚,并将这些行为排除在犯罪范围之外。这些规定通常仅适用于年龄相近的未成年人之間的自愿性行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年龄相仿条款”存在差异。美国将“年龄相仿条款”,称之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条款,是为了防止在双方同意的性活动中,当双方参与者的年龄非常接近,并且一方或双方低于同意年龄时,对从事这种活动的个人进行起诉。因此,我们可以说,该《解释》第六条就是“年龄相仿条款”。
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坚持双向保护原则。除了严厉处罚性侵害儿童犯罪,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也要依法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2013年,四部门制定《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第二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二)刑法中有关性侵害儿童犯罪规定的评析
1.司法裁量中年龄相仿条款的落后
随着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逐渐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国家以家长主义视角代替个人对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年龄相仿条款被视为对刑法家长主义的一种调整,试图赋予未成年人更多自主权。我国年龄相仿条款在2005年开始实施,但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发生了立法者无法预见的变化。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儿童的性交往和性探索行为逐渐从现实世界转移到网络世界。在互联网时代,儿童使用电子设备进行社交已是常态,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可能传输私密照片甚至进行裸聊。检例43号“骆某猥亵儿童罪”中,二审法院审理认为,通过网络对女童进行猥亵,观看女童裸照的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隔空猥亵”在司法实践中构成犯罪。
《意见》第二十七条颁布较早,立法者无法预料到网络空间出现符合“猥亵”犯罪构成的行为。首先,《意见》中的年龄相仿条款主要针对男性对幼女实施的强奸行为,对青少年间的性探索行为没有进行规定,即无法作为猥亵儿童罪的出罪事由。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判例并不像判例法国家具有很强的指引裁判的作用。“网络猥亵”构罪的法理基础仍然存在争议。其次,《意见》第二十七条规定,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只有在满足“偶尔”“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三个要件时,才能作为出罪事由。在这三个要件的认定中,法官价值判断发挥重要作用,法官自由裁量权未得到較好的限制。与之对比,在美国,双方年龄达到一定界限,年龄相近的青少年自愿发生性关系,检察院就不能提起诉讼。相比而言,我国对于年龄相仿条款的实施仍显不充分、落后,无法充分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和修正当前的法律体系和社会观念,更为科学和合理地保护儿童权益,实现对儿童的“解放”,而非简单的“拯救”。
2.性侵害儿童犯罪的年龄结构的错乱
刑法体系中的犯罪年龄要素呈现规范性,一方面,立法机构需要考虑到国际刑法的通行规定,确保本国刑法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提高刑法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法制历史和社会经济情况也需要被充分考虑,以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刑事年龄规定。随着公民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提高,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立法。2018年湖南发生一起“少年弑母案”,少年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母亲后,编造理由误导他人,延缓犯罪事实的发现时间。此时,12周岁的儿童已具有刑法上的意识和行为能力。《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了未成年人在面对情节严重的刑事案件的负责年龄,年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触犯了故意杀人最后依旧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国家立法对于社会舆论予以积极回应。所以,刑法对于年龄相仿条款的设定,实际上是家长主义下国家价值衡量后,对儿童能力的预测。然而,《意见》对年龄设定的模糊化以及刑事年龄设定之间的矛盾,对我国性侵害儿童年龄结构的构建造成了不利影响。
例如,《意见》明确规定,与12岁以下的幼女发生关系的行为人,应视为明知对方是幼女,即不具备刑事上的同意能力。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的加重情节。但是意见对于儿童利益的完全保护以12周岁为限。对此,使人思考10周岁以下与10岁至12周岁对于性犯罪评价意义的区别在何。立法机关会将10周岁作为儿童最低程度保护年龄,这与司法解释产生强烈的割裂感。此外,刑法规定14至16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强奸罪等八大重罪承担刑事责任,这意味着法律认为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具备相对成熟的社会观念。限制责任年龄体系受制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当今的儿童性观念存在矛盾。当今10周岁以上的儿童事实上就已经产生性别意识。因此,我们不能过度固守适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这实质上是对性侵害犯罪年龄体系的破坏,是流于表面的机械性形式适用。在性侵害儿童犯罪的年龄设定上,我们必须坚持平衡和审慎的立法原则。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发展程度,以及他们在理解和判断自己行为后果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面对现实,认识到青少年犯罪的存在,以及其对社会和个体的严重影响。对此,我国年龄相仿的司法解释应当与时俱进进行修正,以实现法律的公正和效率。
三、我国刑法中性侵害儿童犯罪范畴的限缩
通过对我国目前对儿童性积极权利保护的缺失进行审查,我们发现这导致了青少年之间自愿的性交往和性探索行为被定性为犯罪。法律不应轻易改变,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是其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重要依据。因此,在当前的儿童性侵害犯罪治理体系中,《刑法》十三条“但书”条款能够作为出罪事由适用。
(一)“但书”条款的功能、性质和定位
我国《刑法》条文第十三条后半段是“但书”条款,“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书”条款中对于罪量的规定,使我国犯罪概念是混合犯罪概念,兼具“定罪+定量”要素。这是我国独特的区分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方式。仅凭类型化的行为性质无法认定犯罪,必须结合行为程度,将达到刑事违法性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这是“但书”条款的入罪功能。对此,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但书”只具有单纯的宣示功能。“但书”条款仅仅起宣示性的作用,并没有实质指导入罪的功能。例如抽象危险犯和行为犯,刑法条文并没有规定罪量要素。该观点是存疑的,以危险驾驶罪为例,其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犯罪”。从文义上看,凡是醉酒驾车一律构罪。但正是由于“但书”条款入罪功能,将定量因素隐藏在定性之后,司法解释出台认为醉酒驾车情形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不构成犯罪。
“但书”规定具有出罪功能是公认的,但是对于“但书”规定是否能够在我国一元刑法体系内发挥作用存在争议。我国是一元刑法体系,即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有学者认为,当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内容时就构成犯罪,此时运用“但书”条款是在刑法体系外运用,在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并无“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责任”的栖身之地。无论是将“但书”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还是将“但书”转化为“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责任”理论融入犯罪构成模式之内,发挥出罪机制都存在理论的缺陷。事实上,“但书”条款的运用并不需要与犯罪构成内容的认定相分离或者将“但书”条款转化为超法规阻却事由。相反,“但书”条款与犯罪构成内容的认定是共同进行的。正是在认定犯罪构成要件时,兼顾“情节”和“危害”因素的认定。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社会危险性和应收惩罚性的不法和责任层面的认定,是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实质认定的。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需要兼具形式解释为主,实质解释共同认定方式。对此,“但书”条款的运用并没有破坏我国刑法体系的稳定性,相反,运用“但书”条款能够实现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
但需要强调的是,“但书”条款不能直接适用,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否则,“但书”条款会不当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且造成各个法官在自身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作出同案不同罚的判决,刑法致此无法发挥其指导社会民众的作用。著名大法官卡多佐曾说道:“即使在当今时代,权力应严格且永久分立的观点——法官是法律的解释者,立法机关是法律的创造者——依然在司法界一呼百应。為最大限度地发挥“但书”条款的作用,最高司法机关应当结合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及时对于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制定具备“但书”条款性质的司法解释。唯有具体而明确法律,才能实现法律的自由与正义。在最高司法机关尚未制定司法解释的空白领域,法院也不能将“但书”条款作为普遍的裁判依据。法官仅能在个案裁判中,遵循相关领域的精神与原则,间接适用“但书”条款。
(二)《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对性侵害儿童犯罪的限制
《意见》二十七条“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该出罪规范与《刑法》十三条“但书”条款相似,实质上是最高司法机关对于“但书”条款的出罪功能的运用。通过上述论述,可知无法通过扩大解释适用《意见》二十七条。刑法规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保障工具,刑法需要保持谦抑性。刑法的适用应当受到我国特有的文化要素,价值观念和民众认同感的制约。在当前儿童领域保护理念转换为“儿童本位”的权利保护模式,对于青少年间自愿实施性探索的行为,不能一律归罪。刑法需要克制对儿童性自我决定权的限制,在现代家长主义指导下,充分尊重儿童的性积极权利。
青少年在双方自愿下,实施的私密的性探索行为,通常不具有违法性,根本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调整领域。在目前最高司法机关未对猥亵儿童罪作出明确出罪规定下,法官必需在个案裁判中运用“但书”条款,对青少年性探索行为进行出罪认定。具体认定案件事实能否适用“但书”条款,如何理解“情节显著轻微”和“危害不大”的关系是首要问题。两者是必须同时具备的递进关系,还是两者具其一的并列关系。“但书”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与危害不大,其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但书”规定的适用应当是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进行综合性的整体判断,对于适用“但书”规定来说,情节显著轻微与危害不大必须同时具备。其次,“但书规定作为一种出罪事由,是对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一种体现,彰显了我国刑法对于行为相对的社会危害性的要求。情节的定义是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一切主客观情节。”“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和“危害不大”蕴含着违法性程度的定量因素。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本身就是违法性阶层的体现。当某一社会行为、事实行为不具有违法性的因素时,其本身就不应被评价为构成要件行为。因此,当具备“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和“危害不大”时,其本身就是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根本无需进入违法性阶层进行评价。随着年龄接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程度得以反映。从风险的角度来看,针对青少年的交往行为,刑法应该作为最后手段原则,作为后置性的严厉制裁手段。法律作为一种严密的控制手段,必须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由于性价值观念的变迁,性犯罪的社会危险性也随之变化,因此入罪情节也需要相应调整。虽然刑法没有对猥亵儿童的入罪情节做出明确规定,但这为司法裁量提供了契机,有助于实现刑法的立法目的。但是,这种司法裁量权并不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扩大。在刑法家长主义的基础上,为了确保法规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在保护儿童性利益和自由的同时,给予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
四、结语
个案判决中,法院需要根据具体案件的情节与危害结果对“性侵害儿童”行为进行认定。在“但书”条款指导下,将不具有形式违法性的性探索行为出罪,是实现司法的程序和实体正义的重要途径。但是司法判决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也会严重损坏社会大众的信任感,个案间接适用“但书”条款并不是长久之计。对此,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尽快出台性侵害犯罪的最新司法解释,使儿童性权利保护体系符合现代家长主义理念,发挥司法解释的能动性。
The Criminal Path of Sexual Offences Against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alism
Zhang Ru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sexual assault on children, criminal paternalism plays a significant protective role and is developing towards modern soft paternalism.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paternalism should have four essential elements: necessity, equivalence, coercion, and effectiveness. The protection mode of childrens sexual rights has changed with the changes in paternalism, transitioning from a “parent centered” to a “child centered” approach.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on sexual assault on children in China have rationality in implementing provisions on the age of childrens sexual consent and age similarity, effectively safeguarding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prioritizing children. Due to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law itself, it is impossible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sexual exploration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The law cannot be lightly changed.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the proviso to Article 13 of the Criminal Law can indirectly guide judges in their individual judgments, which can exert the function of a crim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keep up with the times and be revised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initiative.
Key words: Criminal paternalism; Child centered; Age similarity clause; Notwithstanding cla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