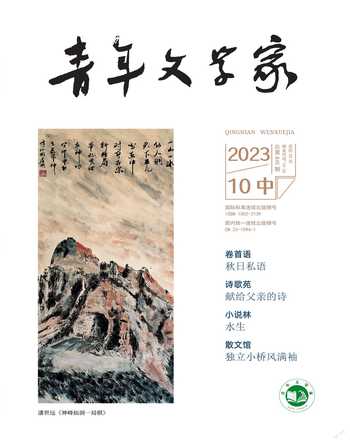浅析郭嵩焘域外游记的复合文体模式
2023-11-27陈宇卓
陈宇卓
清朝光绪元年(1875)和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作为首位驻外使臣出使英国,在为期两年的出使过程中写下《使西纪程》与《伦敦与巴黎日记》,成为晚清域外游记的两部名作。本文从文体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探讨。郭嵩焘的域外游记呈现出复合型的文体特色,他对于各类文体运用自如,尽管《使西纪程》与《伦敦与巴黎日记》使用日记体例,却将散文的风格、小说的手法与古典诗歌的创作囊括于一书之中,内容极为丰富,反映了时代更迭、新旧交替之际中国传统古文写作的嬗变。
在一定程度上,创作者认知图式的嬗变与游记文体格局的裂变互为表里,相互影响。梅新林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将晚清域外游记视为古典游记与现代游记之间从衰变到新生的新旧转型期产物,这里的“转型”,不仅指域外游记的批判启蒙作用,还指其具有面向世界、经世致用的文化使命,以及在文章体式与语言形式上的流变,这是传统古文语体与写作模式已无法完整呈现异域行游经验的必然结果。其表现就是力图将西方世界的新体验通过传统写作模式转化成古典经验,最终呈现文体、语言的复合与杂糅。本文着眼于这一变化,对于郭嵩焘域外游记中呈现的日记、诗歌、小说、散文体式的杂用分别进行梳理,并探讨其文本中丰富的潜在内涵。
一、双重语境的日记体式
日记体式和散文语体是晚清域外游记文体发生新变的两个基础,这一时期出使大臣的域外书写,所采用的几乎都是日记体,这是出于官方的强制规定。在郭嵩焘之前,清王朝曾于同治五年(1866)派出了一支由斌椿领导的非正式的临时出访使团游历西欧各国。斌椿在记录此次考察的《乘槎笔记》中写到,出国前接到的官方命令中,要求“将所过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后来,郭嵩焘于次年使英时,总理衙门亦特意下令:“凡有关系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仍按月汇成一册,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这些文献表明,出使日记不再是单纯的私人秘录与风景见闻,更是需要接受官方监督的外交任务下的规定性产物,写作者不仅要详细汇报所见所闻,还要考虑官方统治机构对于这部日记的期待视野与意愿诉求。
在郭嵩焘的游记中,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碎片式的、无逻辑的事件呈现,一切记录只遵循线性时间原则,而不加文学裁剪与艺术修饰,从航程路线、异国风物、聚会人士、对话礼仪,到起居出行、言谈举止,郭嵩焘始终有意识地彰显着自己使臣的身份,并因其这一身份限制,而主动将其写作放置于中央朝廷的监督之下,那些历历可察的行动流程、对外交事宜与西洋见闻碎片化地排列杂处,凸显着使臣日记的任务性质。在这种朝廷尺度的规范与把控下,作为游记的文学意趣与审美要求反而退居次席了。
然而,郭嵩焘作为一个早年便对西方世界具备深刻认识的思想先觉者,一个亲身体历域外生活,接受西方器物文明冲击与制度文化洗礼的鲜活个体,他的域外书写无法始终匍匐于朝廷谕旨的规训之下,使臣式的目光与实录化书写,可说是对官方章程之“表”的遵循,而对于统治阶层在使臣游记中所期待看到的“里”—以“道统观”维护国家的文化优越性和文明中心地位,他则表现出了相当的批判与反叛。
郭嵩焘并不隐瞒自己在体验西方时的任何直观感受。在赴英途中,他见到外国船舰互相升旗致礼,感叹“彬彬焉见礼之行焉,中国之不能及,远矣”(《使西纪程》);参观西式学堂时,观西洋教育“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使西纪程》);听说西洋交兵不杀俘虏,则“足见西洋列国敦信明义之近古也”(《使西纪程》)。郭嵩焘对于西方礼仪、教育、制度、民情毫不掩饰地加以赞美,自己国家建立在文化礼仪、道德政治等文明本质之上的优越意识几乎站立不住。向来“华夷”之别不仅是地域、民族之别,更是文化高低、文明优劣之别。清王朝在吃了西方几场败仗之后,仍能够通过“彼夷我华”的文明观念修复现实层面的溃败,保持大国荣光的高蹈不坠。而到了郭嵩焘这里,他却在游记中直言“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甚至声称“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使西纪程》),认为西方的礼制仪规较自己国家上古时期也毫不逊色。
这些言论几乎颠覆并瓦解清王朝一直以来基于文化优越感,得以傲视西方的自我认知。这类书写已经是对历来笼罩于出使游记创作之上的朝廷规训的破坏、对维系华夷秩序的传统理念的叛逆,是出自个体经验与价值判断的言说,尽管其与官方期待和社会集体的认知并不相符,却并不被作者着意修正。
二、意蕴高深的诗歌体式
郭嵩焘的游记中一共记载了九首诗歌,这些作品大多没有题目、没有指向、没有注释,有些甚至还没有完整成诗,似乎只是某种情绪的瞬间捕捉、一段隐秘心境的幽微呈现,但其中七首都有一个共同点:于梦中偶然所得。
这些“梦诗”表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茕茕孑立、踽踽独行,难用于世的自伤与孤独。郭嵩焘早年积极入仕却几经挫跌,主因便是思想与主张上的不合时宜。当清王朝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节节败退时,满朝官员大多只会作激愤之词,盲目主张武力对抗,而郭嵩焘一贯主张了解西方文化,以诚相待,向其学习富强之术,这种发言于激昂的时论中不能不被视作异端。且他虽有心为国做事,却一直难以施展,在当时的京沪、广东屡次遭同僚构陷中伤,使他几乎灰心到要彻底隐退求去的地步。又因其使英“通好谢罪”一事,被激进的主战派认为是辱国之举,对其大肆攻讦,甚至有湖南乡试诸生商议要捣毁其宅。就是这般举世非议之下,郭嵩焘以望六之年,多病之躯,毅然命道,全出于为国家求索济困之道,于是写下“临老腰肢健,犹能一据鞍”来表明自己的决心,其平生所思何等慷慨!
郭嵩焘在异国仍受到来自朝中保守派的多方掣肘,其副使劉锡鸿即为守旧派大臣李鸿藻派来牵制他工作的,党派之争让他更觉世事艰难,难有同俦。“同生世上独苦悲”“独立天涯谁与偶”(《伦敦与巴黎日记》),正是其幽愤寥落之心情写照,他自觉“行尽天涯”而无人与共,处于众人之中而如乌鹊处于燕群,不能勠力为国,岂不是“一样焦劳两样心”“投胶激水误相伤”(《伦敦与巴黎日记》)。自然,苦闷中也有自我遣怀,又如“此腹空如瓠,枵然无一有”(《伦敦与巴黎日记》),非但自嘲,且聊以自解;“天地容身无碍小”“支窗容我一开颜”(《伦敦与巴黎日记》),不乏明朗疏爽之处。
另一方面,梦中得诗也是郭嵩焘对古典传统的潜在认同与文化复归,他虽然钦服彼时西方文明的进步,但骨子里仍是浸淫旧学的典型晚清文士,他并非全然向往西方,而是希望通过对西方的学习使清王朝重回“政俗皆美”的上古黄金时代。他斥责满朝士大夫论事者皆如南宋边患日深之际“乐持虚论而不务求实际”的宋儒,却也在身处西方时夜梦与周敦颐、张栻、韩维等人同席而坐,清谈学问。他远赴海外,梦中所见乃是“太白雪晴”“洞庭波渺”的故国风光,哪怕是写伦敦新雪,想起的还是故乡湖南的“妙高峰”“岳麓寺”。郭嵩焘的这些梦诗,要比其他域外纪游诗更加情辞动人、意蕴深远,它显示了郭嵩焘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见识的晚清士人阶层代表在时代新旧交替之际的苦闷与愁思,以及在扶弱济危的求索之路上的文化选择与复归。
三、求奇探怪的小说体式
除却使臣日记中折冲樽俎的外交细节、巨细无遗的日常记录,郭嵩焘还在不少地方运用了小说笔法,来描绘西方逸闻奇事。奇、险、新、怪是对于异域殊方所产生的心理观念的自然投射,西方作为“他者”,天然具备神秘性与陌生感,旅外之人在域外往往抱有一种搜奇探怪的求异心理。在始终客观平实、枯燥寡淡的案牍文书式日记实录里,于行程道里、机械器造、工商政治、会议交谊的琐碎中偶然得见文辞生动、意趣盎然的逸闻奇事与生活场面,足可令人耳目一新,如写斯坦利非洲探险的故事,长达千字,记述精于藏学的英人非色尔里(即斯坦利)往探阿非利加(即非洲),偶入一土著国,以洋枪慑服其国人之事,不仅情节完整,语言简练,且描写传神而富畫面感。且看《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斯坦利于土著面前施放洋枪一段:
土人仍以危词胁之,非色尔里笑曰:“吾有神术,不汝惧也。”视其旁高树上立一鹰,举洋枪击之,一发而鹰已落地。土人闻声大惧,皆跪曰:“此雷公也,请无再施雷。”旁立一人谓曰:“鹰,小物也。山有野象,能击乎?”非色里尔应曰:“能。”导入山,一发复弊一象。于是乃白其王,请妻以女,留使掌兵。非色里尔固辞以归,白之挨及王,谓其地可以经营。
这类文字不仅传神,且人物形象也十分鲜明。斯坦利面对土著时从容不迫,其人欲王之时毅然辞归,又为埃及开疆献策,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中国读者阅读时不难感觉叙述与语汇上的亲切,然而其音译地名、人名与“洋枪”等词又随时提醒着读者此为海外逸事,这种中西杂陈的新奇感,正是域外游记中使用小说笔法的精彩之处。
小说笔法的运用在郭嵩焘的域外游记中屡屡出现,且多为探险故事,如记古罗马普林尼叔侄经历火山爆发的故事,澳洲土人嗜饮火酒而多患渴死的故事,会见北极探险家、听其讲北极冒险的故事等,皆写得流逸生动,极有趣味。
如上这类笔墨,显然已经突破了官方规定的使臣视野的条条框框,这打破了使臣游记原有的案牍公文的体制局限,呈现文体互渗的态势,使得游记文本更具丰富性与多义性,显示出游记文学在新旧转型期的文体新变态势,并呈现出独特的文学创造力。
四、议论深彻的散文风格
大体上郭嵩焘的游记仍旧是以散文式语体为主,但其中也掺杂着连篇累牍的实用科学式语言,来描述机器形制、运作、工业设施等。与此类平直务实的描述性话语相较,游记最具可读性与思想性,彰显了文体语言特色的还要数其中的议论性内容。
郭嵩焘充分发挥了日记这一文体叙事状物的实录功能,将其对西方文明的切身体验、心灵震动都予以秉笔直录,议论风发。在这层意义上,郭嵩焘的域外游记不仅是使臣日记,也是郭嵩焘用以输出观点、表达情感立场的“载道立言”之作。
郭嵩焘在游记中的议论内容,几乎都是围绕中西国情、兴衰之理与匡救之法所展开,这种针砭时弊、经世致用的作文意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所属的桐城文派的学术滋养。桐城派自姚鼐所定“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说,其学派文人便始终贯通这一文化态度与思维习惯。晚清以来,被视为桐城派中兴之主的曾国藩,又在姚鼐之外大力提倡文章“经济之学”,格外重视文章的现实政治研究与实际功用。在其域外游记中,郭嵩焘也充分发挥了这一风格,其辞章畅达简明而义理深彻,最为突出的是如下特点:
第一,缘事入理。郭嵩焘的域外游记呈现出散文的政论化倾向,然而不同于传统游记寄情于景、寓理于景的构架,他往往采用缘事入理的处理方式,使论述更具说服力。例如,其盛赞彼时西方优越的教育制度,从参观英国“客来斯阿市布洛达学馆”一事引入,因闻其广收贫寒子弟,风貌整肃、礼节彬彬,每就食必先“教士宣讲,鼓琴作歌以应之”(《伦敦与巴黎日记》),乃论其似“圣人之教”;又论西洋富强在于其行政务求便民,从信票(邮票)制度引入。正因有实事实证作为支撑,循理而入,使得论述具有遒劲雄健、锋锐难当的气势。
第二,以古喻今,以西喻中。就议论策略而言,郭嵩焘广泛援引古代事例,以达到借古鉴今、因古论今的目的。例如,要驳斥朝中士大夫的主战攘夷论,其则以南宋危亡之时儒生空谈误国作例,直指宋儒“一意矜张”“置君父于不顾”,将南宋时局与当下时局对应,提出应审时度势,以免重蹈南宋覆辙。其又常引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勇效西方,在制度、器物、外交方面皆效西制,“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钟叔河《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郭嵩焘的此类文字,皆讲求有事可证、有实可循,着眼于实际,旁征博引,以助文势,正是对他所认同的谈论洋务者应当广通“六经周秦古书”、博识“儒先论著”,“准以历代之史,参考互证”的践行。
这两部域外游记虽是日记体例,同时又杂用古典诗歌与小说,呈现出文体杂糅、互渗的情况,使得游记文本更具丰富性与多义性。一定程度上,这得归功于郭嵩焘的时代,当时的域外游记还处于新生阶段,该写什么、该如何写都尚无一种规定准则,特别是由专命委派的出使大臣所作的游记,官方虽然规定了大致体例与考察内容,却在文章布排、文体选择上为作者留出了些许自由选择的余地,使得作者面对陌生新奇的西方世界时可选用多种文体来承担不同的域外体验之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