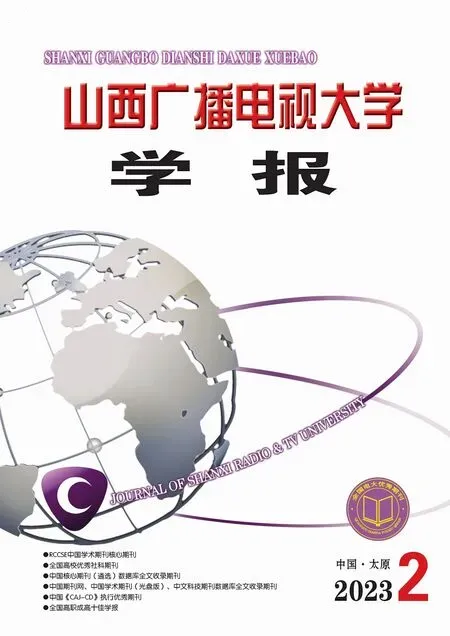论唐诗中的琵琶意象
2023-11-26王爽杨勇
王 爽 杨 勇
(山西开放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7)
琵琶虽自西域传入,却与中原文化完美融合。作为乐器意象,它历经唐代发展,融入边塞诗、悲怨诗文,以及宴饮诗作,一次次将唐诗送上新的高度,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并为后世提供典范。它为唐诗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打开乐器与唐诗结合的通道,成为灿若星河的诗歌长河中,无法被忽视的存在。
一、琵琶的起源与发展
枇杷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应劭《风俗通·枇杷条》对乐器的记载:“以手枇杷,因以为名。”[1]这里的“枇”“杷”指的是演奏手法。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释乐器》则解释得更加详细:“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之所以由“枇杷”改为“琵琶”,应是受到乐器“琴”的影响。据《通典》记载,唐代琵琶类乐器分为三种:即阮咸琵琶、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阮咸琵琶为直项琵琶,又称“秦琵琶”。为乌孙公主远嫁猎骄靡之时所制,圆体修颈,四弦十二柱。在曲项琵琶传入中原地区后被称为“秦汉子”。相较于阮咸琵琶,曲项琵琶出现较晚,最早由西域乃至阿拉伯伊朗传入。《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项琵琶、竖箜篌,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北魏宣武帝极爱胡声,琵琶、五弦、箜篌、龟兹皆为心头好。”周昊《刘朝门·简文帝》:“曲项琵琶催酒处,不图为乐向谁云。”这首诗说明,至少在南朝,已经出现“曲项琵琶”这一名称。《全唐诗》中除寥寥几首涉阮咸琵琶诗外,大部分琵琶诗所指为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盛行于唐,甚至远渡重洋,传至日本,至今日本奈良正仓院仍有一面珍藏。它的体型小于四弦,兴盛于唐,但是到了宋代,已鲜有记载。西域乐器、乐曲、歌舞大量涌入中原,与中原地区传统音乐融合,促进了音乐的繁荣发展。
唐文人崇尚自由,不受礼法束缚。节奏明快、奔放热烈的琵琶乐更适合表情达意。音乐风格的改变也促使诗歌的改变,大量琵琶诗的涌现即为佐证。同时,唐诗的音律性也更为突出。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成为琵琶抒情的千古绝唱。诗人描写了琵琶演奏者的高超技巧和艺术造诣,同时也表达了对琵琶女遭遇的同情,最终引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这篇作品将音乐和诗歌巧妙结合,兼顾叙事、写景和抒情,堪称中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安史之乱后,部分宫廷乐师流落民间,将高超的弹奏技艺也带到民间。荆州一带更有俗语“琵琶大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可见琵琶在这一地区的普及程度。又有“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2](李颀《古意》)、“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2](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等,可见在辽河以东及甘肃境内,琵琶都曾是广受欢迎的乐器。
二、唐诗中的琵琶意象
自北魏开始,西域乐器进入中原。现有记载的隋朝音乐,可以看到大量为西域音乐影响的痕迹。北朝以来,琵琶、箜篌、胡笳等西域乐器流入中原,以其高亢嘹亮、哀怨婉转的曲风,影响中原音乐格局。始现“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的情况。“唐之胡乐多因于隋”,这种影响,在唐代达到顶峰。宽松的政治氛围、包容的文化环境,富裕的人民生活共同构建起一个空前的文化盛世。丝绸之路的畅通便行,贸易的自由往来,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更是将这种融合引入极致。多种西域文化符号包括葡萄酒、服饰、乐器等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文学创作。这些异域符号在诗作中出现,拓宽了诗人的创作题材,点燃了诗人的创作热情。在此时期,边塞诗、乐舞诗大量出现,名篇佳作不胜枚举。
所谓意象,指的是承载意义的客观事物,是创作者将主观情绪置于客观事物中,使其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3]。在主客观高度契合的基础上,历经时代的发展,客观事物从承载意义的模具,发展为意义本身,这便是主观情绪的具象化。以西域乐器为代表的西域意象,以强势的态度融入中原文化,在唐诗中频繁出现。以琵琶为例,最初只是吟诵唐诗时的陪衬、辅乐,唐贞观年间,琵琶弹奏技法由拨子演奏改为弹指技法,这一改动使得琵琶乐声更加具有穿透力,也更符合当时的音乐审美。赞美琵琶乐曲或琵琶弹奏技法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全篇无一冗言,句句经典,其中对琵琶演奏“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描写历经千年,流传至今,仍被奉为经典。除了乐曲与演奏技巧,琵琶本身被视为哀怨与忧愁的载体,成为唐诗中一个典型意象。杜甫“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右迹”(其三)]李峤“半夜分弦出,丛花拂面安。”(《琵琶》)而此时的琵琶已大不同于初入中原时作为辅助乐器的诗歌意象,而是成为悲戚寂寥或哀伤婉转的物化代表。
三、唐诗琵琶意象的发展
琵琶意象贯穿整个唐代的诗歌创作,历经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成为唐诗中不可或缺的意象。
(一)初唐起始期
作为中国诗歌繁荣的准备期,初唐诗歌的发展动向预示了即将到来的鼎盛局面。诗歌作者从朝廷官吏扩大到寒门士子,诗歌主题从宫廷楼阁扩展到了边塞大漠。历经南朝诗歌的清新独特与北朝诗歌的刚健豪放,二者相互融合使得诗歌风格摒弃了绮丽奢华的痕迹,兼具清朗与豪放,开创一种新的境界。“莫吹羌笛惊邻里,不用琵琶喧洞房。且歌新夜曲,莫弄楚明光。此曲怨且艳,哀音断人肠。”[2](乔知之《倡女行》)。
(二)盛唐繁荣期
盛唐诗歌代表着中国古代诗歌作品的巅峰,是古代诗歌创作独一无二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家都有着明显的个人风格,是中国历史上鲜有的“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的时代。此时诗歌极具“盛唐气象”,“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在情思格调、意境意象、声律形式等方面均可谓登峰造极,堪称完美。
此时的琵琶诗作也极具盛唐气质,加之与边塞诗的完美结合,诗作慷慨豪迈,独具一格。在描绘白草黄沙的边境风貌之余,加之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边愁孤寂的思乡之苦、友人迁谪的哀伤不舍、战争胜利的慷慨不羁。整体诗风深沉壮阔,昂扬奋进。“横笛弄秋月,琵琶弹陌桑。龙泉解锦带,为尔倾千觞。”[2](李白《夜别张五》) “袅袅汉宫柳,青青胡地桑。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2](李颀《古塞下曲》)此时的琵琶意象比初唐时期的指向性更为明显。作为文化符号,其内涵也更加丰富。边塞诗和琵琶意象相辅相成,共同成就这一时期的完美作品。作为创作者,急需“望而知其所指”的边塞意象或边塞符号,用以准确表情达意。而由西域传入,却也沾染中原特点的琵琶就变得无比适合。王昌龄、岑参等一大批优秀边塞诗人的出现,更是将边塞诗引入新的高度。
(三)中唐兴盛期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至衰。巨大社会变动也带来了文学作品风格的变革。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和流离失所的百姓,诗人们正视自身的彷徨无力,作品风格也转为孤寂清冷,史称“大历诗风”。这种风格与哀怨婉转的琵琶乐曲十分相称,两相配合,琵琶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意象之一。“微月东南上戍楼,琵琶起舞锦缠头。更闻横笛关山远,白草胡沙西塞秋。”[2](李益《夜宴观石将军舞》)
公元805年,唐宪宗即位。宪宗治国有方,政治清明,史称“元和中兴”。随之而来的是诗歌领域的革新: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兴起,开创了又一个诗歌高潮,琵琶诗也迎来了自己新的发展阶段。白居易所作《琵琶行》堪称千古最佳叙事诗,写同病相怜之意,抒发恻隐之情。中唐的琵琶诗,不仅质量上乘而且数量众多,说明琵琶诗已经成为唐诗创作中的重要类型之一。琵琶意象也借由琵琶诗的增加,内涵更加稳固。究其原因,自安史之乱后,文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使国家恢复到开天盛世绝无可能,只能寄情于乐舞,耽于享乐。加之皇室上下对于西域乐舞的热衷直接促使了琵琶作为一种辅助乐器,频繁出现于宴饮场合之中。 “庭前雪压松桂丛,廊下点点悬纱笼。满堂醉客争笑语,嘈囋琵琶青幕中。”[2](刘禹锡《更衣曲》)“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2](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琵琶意象不仅蕴含着边塞诗中凄凉孤寂的意味,同时也具有宴饮、欢聚时歌舞升平之意。
(四)晚唐式微期
唐代末年,政治经济逐渐走向颓废甚至灭亡,诗歌自然也是一片苦吟之声。诗歌题材狭窄,缺乏创新,除了李商隐、杜牧等极少数诗人外,大部分诗作平常。且晚唐诗歌延续中唐特质,对自身及国家的希望更加渺茫,转而投向乐舞之中,寻找慰藉。琵琶作为唐诗众多意象之一,以其明确的符号内涵,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2](李商隐《王昭君》)“救兵方至强抽军,与贼开城是简文。曲项琵琶催酒处,不图为乐向谁云。”[2](周昙《简文帝》)文人咏史诗中的琵琶意象,表现了对国家衰败与灭亡的悲叹。
四、唐诗琵琶意象的情感表达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写道:“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每一类的诗歌中,都有琵琶的参与,琵琶意象完美诠释了诗歌的主题。作为诗歌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意象是表达作者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在“情”与“意”的融合过程中,选取最能够承载自己感情的物象,生成最为贴切的艺术形象。全唐诗共有128首涉及琵琶的诗作,琵琶意象随着不同类型的诗歌展现出的不同风貌和内涵,依照情感表达侧重不同,将其归为三类:表达慷慨悲壮,抒发哀怨忧思,烘托宴饮氛围。
(一)表达悲壮慷慨
西域的地理环境和物貌特征开阔了中原诗人的想象力,拓展了诗歌创作题材。部分亲历边境的诗人将自己的所见所感书写于纸上,创作出以边塞风貌人情为主题的“边塞诗”。边塞诗始于先秦,早在《诗经·大雅·江汉》中,就有表达周人边疆观念的“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4]。历经汉魏六朝的发展以及隋朝的兴盛,于唐朝达到鼎盛。王翰《凉州词》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如此明快、奔放的叙事手法,很难说不是受到西域音乐风格的影响。此时的琵琶意象,象征的是边疆将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旷达情怀,是边塞诗奔放豪迈的大漠气质。
作为唐代最著名的边塞诗作家,岑参两度戍边,他的边塞诗以浪漫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边塞雄奇壮丽的景色。《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将送友远行的伤感情绪与变换的雪景巧妙联系,在描写边塞苦寒的同时,抒发了对友人迁谪的不舍及浓浓的思乡之情。“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2](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2](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二)抒发哀怨忧思
戍边将士常年远离家人故土,面临战争死亡威胁的同时,还要忍受边地恶劣的气候,因此边塞诗中蕴含的不仅有豪迈气概,也有哀怨忧思。“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2](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2](李颀《古塞下曲》)倘若琵琶诗主题涉及演奏者的坎坷经历,尤其是演奏者为女性时,其哀怨意味则更加浓厚。“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2]。(白居易《琵琶行》)“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2](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昭君出塞是其中最为哀伤悲戚的主题。王昭君怀抱琵琶,在荒凉大漠中尽显哀怨。而最初的昭君与琵琶本无任何联系。从汉宫女王嫱和亲到唐诗中的昭君怀抱琵琶出塞,想来是一个漫长却毫不违和的演变过程。“昭君出塞”始现于《汉书》,以寥寥数语记载了匈奴呼韩邪单于“乡慕礼仪,求娶汉女为阏氏一事。”并明确写道“原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赐单于……号宁胡阏氏。”这一事件在的流传过程中,故事性明显增强。《琴操》《西京杂记》等书增加了昭君美艳聪慧、自请出塞及毛延寿贪财等情节,琵琶作为最合适的意象在此过程中被人为地附着到昭君怀抱之中,奠定了作品哀怨的基调。
(三)烘托宴饮氛围
琵琶音色高亢婉转,感染力强,经常与笛一起,烘托歌舞表演的氛围。在宴饮聚会的场合中,经常能够见到琵琶的身影。异域歌舞辅以西域乐器,营造出热情欢快的氛围。“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2](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2](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琴筝箫管和琵琶,兴满金尊酒量赊。歌舞留春春似海,美人颜色正如花。”[2](唐彦谦《春日偶成》)。琵琶意象在唐诗人笔下,既有精致又有韵味。它的加入,使得唐诗变得更加灵动,或哀婉,或怜惜,或悲愁,或欢快,完全不同的情绪表达却能在它身上和谐存在。从存世的唐诗中我们看到,上至宫廷皇室,下至民间百姓,从中原腹地到边境驿站,琵琶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存在于每一个历史空间之中,谱写诗歌的曲调。
五、结语
作为西域乐器的一种,琵琶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正因如此,它才会被唐诗人寄予情感,成为经久不衰的诗歌意象。唐代诗人在乐曲构成的世界里挥洒笔墨,宣泄情感。在意象的流动变化中感受异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文化交融带来的创新与欣喜。唐诗中的琵琶意象描绘出西域文化意象在中原诗人笔下大放异彩的精彩过程,也记录下与唐代诗歌发展息息相关的琵琶诗发展历程,反映出中原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包容与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