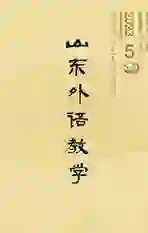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法国的译介:现状与反思
2023-11-21周俊平胡安江
周俊平 胡安江
[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译介界在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译介中始终坚持思想与美学并重、地方性与世界性兼顾的原则,其成果值得肯定。但如今,偏激功能主义译介说在我国愈演愈烈,必须警惕它对中国文学外译构成的误导。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聚焦以下几个核心问题:以社会文化为视角,考察偏激功能主义译介说在我国得势的根源,以及对其予以抵制的必要性;以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世界文学”说和朱利安(Franois Jullien)的“间距”说为参照,探讨文学外译当以维护并突显文学文化异质性为原则的学理依据;基于以上论证,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应坚持以建构以异质性文学文化之跨文化互文为内涵的“世界文学”为目的。
[关键词] 中国文学“走出去”;世界文学;间距;跨文化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识码] A[文献编号] 1002-2643(2023)05-0123-11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ew-period Literature in France: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s
ZHOU Junping1 HU Anjiang2
(1. Postdoctoral Research Center,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China;2. Graduate School,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as New-period Literature, the French translators and disseminators have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s of giving equal importance to ideology and aesthetics,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since the 1980s, and their works are remarkable. Meanwhile, we must be alert to the fact that the radical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which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in China, is misleading the foreig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such cases, this paper launches discussion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from a socio-cultural point of view, we examin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opularity of radical functionalism in China and the need to resist it; inspired by David Damroschs “world literature” and Franois Julliens “ lécart”, we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literary culture in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arguments, we propose constructing “world literature”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cross-cultural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different literary cultures based on their heterogeneity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Chinas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world literature; lécart; cross-cultural intertextuality
1.引言
20世紀80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法国译介的成果和效果出色,但译介得以发生的缘由在国内学界收获的关注不多。通过回顾彼时中法两国相似又相异的文学景观以及法国的学术环境,我们发现思想与美学并重、地方性与世界性兼顾是法国译介中国新时期文学自始至终的原则。当下,偏激功能主义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我国文学“走出去”造成了一定干扰和误导。该论调得势的根源何在、应如何纠偏是我们目前急需正视并深入讨论的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法译介的背景,然后着力探讨偏激功能主义的谬误,并参考“世界文学”说和“间距”说尝试澄清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真正目的及其应有的坚守。
2.20世纪后20年的中法文学景观
无论中外,文学与社会及历史的关系,尤其是文学在社会及历史中应有的功能和实际地位,始终是文学批评的核心议题,也是创作美学的基本构成部分。依此视角,批评家马柯斯(William Marx)勾勒出欧洲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17世纪末至20世纪末扩张、自治、失信的三个发展阶段,并将社会对文学的责任诉求指认为文学在法国得势、失势、自杀后濒临死亡的根源。
马柯斯(Marx, 2005:39)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试图消除诗歌与神圣之间的全部界限,将诗人视为《圣经》里先知的后继者”①。布瓦洛(Nicolas Boileau)于1674年在法国翻译并阐发朗吉努斯(Longin)的《论崇高》(Traité du sublime),暗中助力文学的逐步神化,使文学“与宗教相互支撑,以人类的福祉为召命”(Marx, 2005:44)。17世纪的批评家们认为文学不应限于反映世界,还须影响并改造之;作家应成为“文学宗教”之祭司、人类命运之先知,负有为社会立规范、为人类谋未来、引导人们走向自由幸福的使命。18世纪末的艺术自治则在欧洲催生并壮大了另一类文学景观。康德打破寓教于乐的法则,区分了美与真和善,强调艺术的非功利性。艺术和文学由此开始寻求自治,尝试摆脱说教任务,但也因此走入另一种两难之境,不得不面对社会向它发出的责任诉求和它避开尽责指令的欲望间的矛盾。双道并行的作家多少会被免除指责,例如雨果(Victor Hugo)于革命如火如荼的1830年背对历史写出“一无用处的”“贫弱的与世无争的”(雨果, 1980:97)诗集《秋叶集》(Les Feuilles dautomne),同时在该诗集的序中声称即将推出另“一本政治诗集”(雨果,1980:102)。而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和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则均于1857年被法庭指控为有伤风化。这两起诉讼案并非出于“当局以审察手段迫使文学屈从社会的企图,而是社会向文学发出的求助”(Marx, 2005:70),是社会请求它所仰仗的文学担起道德导师之责。
类似事件在百年后的20世纪下半叶也有发生。当时,萨特(Jean-Paul Sartre)主张“介入文学”,要求作家为时代写作,要在作品中“尽力构形有建设力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Sartre, 1948:266)。他谴责百年前的“为艺术而艺术”之作“无意教导,不反映任何意识形态,拒绝道德训诫”(Sartre, 1948:171),谴责与他同时代的加缪(Albert Camus)在《鼠疫》(La Peste)中将战争隐喻为自然的病毒却不予以历史政治定位(阿隆森, 2005:71)。如此我们能够看到,20世纪50年代后,法国再次出现了两种并驾齐驱的文学景观,各自表现出对社会责任相反的态度:一方面是承担社会责任、针对彼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历史方向进行的宏大叙事,如对殖民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社会责任力不从心、与历史保持距离,在纯文学的自治地带探索文学本身的可能性并进行形式实验的写作,如“新小说”和“乌力波”(Oulipo,又译“潜在文学坊”)。其中后者是百年前兴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之延续,最终也使文学走向自我指涉,囿于语言之茧,乃至在70年代末因“竭力自我净化,最终元气耗尽,虚弱不堪”(Compagnon, 2007:783)。
法国文学的危殆之势在80年代出现转机。伴随故事、想象等传统文学元素的回归潮,法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学。文学开始低调,作家不再以救世神医或英雄自居,而是做回凡人,将自身的生命经验形象化,寻求理解日常的无限可能。文学终于走出语言牢笼,与写作者思想情感的内部世界以及现实生活的外部世界重新发生关系。日常经验成为创作关注的对象,指点江山的宏大叙事日渐式微,关注接近生活的事物、捕捉触动心灵激发幸福的日常事件的小叙事日益月滋。这一势头的典型代表人物莫过于开创细微主义(le minimalisme)的德莱姆(Philippe Delerm),其作品仅名称便可显示出这类写作的旨趣,如《一切安好》(Cest bien)和《尤其是,什么也不做》(Surtout, ne rien faire)。究其缘由,《颂扬无关紧要》(loge du rien)的作者博班(Christian Bobin)关于何谓生活意义的回答颇能说明问题——他引用了加缪的名言“应当想象幸福的西西弗”(Brunel & Huisman, 2007:315)。拋开将文学导入死胡同的实验写作不谈,继“介入文学”的宏大叙述之后,作家及知识分子的困顿心态可见一斑。松动哲学和政治的桎梏,将文学的触角伸向人的内心、伸向现实生活的深层肌理,成为80年代以来诸多创作者的共同追求。
介入现实和政治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被概括为“救亡”和“启蒙”的中国现代文学更是有光辉的政治化传统。与之并存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去政治化的自觉意识和实践,如林语堂的性灵小品、沈从文的牧歌小说。具体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仍是国内两道主要的文学景观。作为对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政治化的反应,中国文学在70年代末显出对抗之态,但吊诡的是这种对抗“在去政治化的表面诉求中实际上已将自己推入某种特殊的政治化形式”(曾念长, 2017:333)。具体而言,彼时我国文学界期许的“独立文学”主要体现为“一种逃脱了意识形态话语网络因而具有合法性的新叙事”(贺桂梅, 2021:376),既要求“走进文学”,“注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强调形式特征、审美特征”,又要求“走出文学”,“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贺桂梅, 2021:377)。在此气氛下,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意识下,在拉美“文学爆炸”震惊中国文坛并走向世界的示范效应下(滕威,2006),“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构,来重新确立中国的主体位置,并形成某种或可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新表述”(贺桂梅, 2020:21)的寻根文学应运而生。寻根作家群体放弃对政治现实的热切关注,把挖掘和建构主流之外的非规范文化作为主要叙事策略(贺桂梅, 2020:32-33)。然而,由于“独立文学”的内涵建构始终处于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中,80年代前中期我国文学非政治的设计及施行始终以政治为参照,最终落入反政治化的政治化。而在80年代后期,新写实派、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等返回人的内心世界,直接探测人的隐秘情感、感觉和欲望,令文学终于摆脱了与政治二元对立的封闭结构。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市场被“想象成文学继续去政治化的一种再生空间”(曾念长, 2017:346),市场化写作遂成为文学去政治化的一种实践路径。与这种文学去政治化趋向并存的,是来自强调文学干预现实的新左派的质疑,以及恢复文学介入现实之话语能量的责令。1998年的自由主义之争是这种非政治的“人的文学”与政治的“人民的文学”之争的炽热化表现。概言之,20世纪后20年整个中国的文学景观皆可统合于政治焦虑之下。但这种焦虑并非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制,而是作家及知识分子对文学介入社会之能力及责任的迎与拒。
并置观照,20世纪后20年的中法文学景观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双方都有撼动并摆脱既有话语体制的诉求;都试图让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使文学卸下干预社会现实的重压而进入更广阔、更多维、更立体的空间;都期望文学同时向内和向外挺进,在保持自律的前提下与人、与社会重建对话。对作为欧洲汉学重镇的法国而言,中国的文学经验既熟悉又陌生,加以观察或可为在危机中求新生的法国文学提供有益启示。事实也是如此,该时期的法国汉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都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目光炬炬,为后者在法国的译介做出了准备。
3.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法国的译介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旧有的影响研究寻求确立中心和渊源,平行研究寻求探察相似和契合。为克服这两种方法的不足,尤其是各自可能携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法国汉学泰斗艾田伯(René tiemble)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应结合历史考证和美学沉思,以发掘不同民族文学所含的文学“不变量”,即民族文学间的共性及普遍价值;20世纪80年代末,他又对当时“世界文学”实践中中国文学的缺席表示不满,要求在全球基础上重构“世界文学”。更具开创意义的是他主张的探察文学“不变量”的方法,即“美学不是从思辨原则上加以推导的,而是在对体裁的历史演变或者从各种不同文化体形的特点和结构上做了细致的研究之后归纳出来的”(艾田伯, 2006:42)。归纳法可防范演绎法以某一先在的、抽象的一般法则对个案自上而下施行粗暴归化,抵制研究中可能的文化殖民。艾田伯的纠偏在法国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建构了良性的译介环境。
针对8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法国学者观察到“中国作家日益关注纯粹美学追求,文学创作应有的环境也终于在中国形成”,新文学最具意义的发展“无疑是创作主题明显的去政治化,这甚至比创作技巧的演进更重要”(Giafferri-Huang, 1991:251)。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深研究者及译者何碧玉(Isabelle Rabut)曾撰文指出中国新文学对法国译者的吸引力,诚言“三十年代的文学与当下的感性日益不合,诸多译者转而投入到更具温度的当代文学”(Rabut, 2004)。所谓“温度”,即文学对生动鲜活的日常的关注。而最先引起法国译者及出版人关注的寻根文学,其魅力便在于寻根作家试图“通过写作与古老的文化魂恢复联系”(Rabut, 2004),而译介目的则是“让公众超越简单的政治维度,感触一方民众的日常脉搏,进而触及人性本身”(Kevin, 2015:79)。随后,借鉴法国新小说、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的先锋文学在法国并未引起太大反响,而相比而言,池莉、刘震云等人的新写实小说因“更具‘古风的叙述、节制的语言,以及看待社会变革的现代的、超脱的新目光”(同上)博得法国译介界的青睐。从地方性中发现世界性,是法国翻译界及出版界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核心期待。诚然,在实际的译介过程中,部分译作可能会刺激并满足法国读者某种“东方主义”的“好奇心甚至窥视欲”(栾荷莎, 2022:69),或是成为法国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变革的历史文献,最终导致文学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流失,甚至西方化,扭曲中国文化形象”(Hao, 2019:372)的客观结果。但我们无需夸大事实,也无需妄论译介主体是否具有这样的意图。
法国知名汉学家、中国文学翻译家雷威安(André Lévy)在80年代中期提醒法国公众警惕异国情调可能携带的“东方主义”,并提出对中国新秀作家应有的期待,希望他们“写出具有普遍性的作品,摈弃过分狭隘的‘异国情调,而同时又不要失去中国魂”(转引自钱林森, 2019:251)。何碧玉和她同为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的丈夫安必诺(Angel Pino)在2014年指出,余华《兄弟》的畅销“是因为法国读者想要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的演变”(季进, 2022:298)。何碧玉2008年就已表示,自己欣赏余华的小说,就是因为其中“美与丑的紧张关系”(唐利群, 2010:26);而早在2004年她就强调,余华的作品真实再现了巨变中的中国,但读者阅读的兴趣不仅是为了解中国,更是为了体验作品中的震惊、恐惧或感动并反观他们自身存在于世的状况(陈嘉琨, 2022:62)。从事莫言作品法文翻译工作多年的杜特莱(Nol Dutrait)也反复强调坚持互通视角的必要性,声明自己选择翻译作品时始终秉持思想与美学并重原则(刘云虹, 2019:105)。三位译者的所言所行在法国译界不仅并非稀有个案,而且极具代表性。关于译介工作的具体方法,何碧玉曾明确表示反对改写:
随意删除原文的内容、跳过一些细节不翻译的话,很可能损害原作者的表达。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我们认为正是在一些细节中隐藏了文学的美,而作为译者,我们无法替代读者决定哪部分应该被保留,哪部分应该被删除或者改写,因此我不太赞成改写式的翻译。(季进, 2022:304)
由此可见,紧贴原文翻译是法国译者对作者、原文本、读者没有偏倚的共同尊重,是对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的“使译者双向地忠于译源与译入两方面”(方梦之, 2019:368)的“忠诚”(loyalty)翻译伦理的自觉践行。总体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译介界从文化、思想、美学等多维度综合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对“忠诚”译介原则的坚守也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松懈。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浪潮的诱惑和本世纪市场销售的压力下,也未改选择译介作品的标准。以销售数据为风标,以迎合甚至讨好读者为目的进行改写的译介现象在法国并不多见。
另外,近40年来法国主流媒体也表现出对译入法语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普遍性价值及美学特色的持续关注、发掘和展示。例如,有评论将余华与巴尔扎克相联系以论说前者作品中展现的时代变革;也有论者将苏童《妻妾成群》的语言与法国当代文学大家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的语言进行类比观照(陈嘉琨, 2022:62)。有论者将这种现象评价为“西方文学杰作依然不可避免地成为衡量中国文学作品的对照物和标尺,尽管这一现象有缓和的趋势,但中国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普遍价值仍有待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承认”(陈嘉琨, 2022:64);对此我们难以完全认同。拒绝比较貌似是在维护中国文学的独一性,实则以异之名压制了同,因为类比的“内涵和任务是协调同与异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金雯, 2021:18),一味拒绝只会阻断中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对话路径。比较研究自有价值。一方面,作家始终都要从自身的阅读中汲取资源,创作就是在前辈巨擘辉煌成就的阴影里与之交锋的过程,因此,一个作家的作品内必含“另一些艺术家的梦想、呼唤或沉默”(陈永国, 2022:145)。另一方面,比较研究并非必然出自文化殖民的意图,也并非一定产生如此结果。阐释的本意“是在对视之间”“相互观照,并进而以‘他的事实为根据做出‘我的解释”(彭兆荣, 2022:99)。将中国作家與欧美作家共置一框,可为外国读者指路,使后者经由熟悉的西方作家走向相对陌异的中国作家,进而发现别样的中国文学。毕竟类比是“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条件和标志”(金雯, 2021:14),以已有知识类比进而认识陌异世界是人类自始就有的重要认知手段。
综上,法国译界、出版界、研究界坚持兼顾思想及美学价值的独特性及普遍性,为中国新时期文学良性进入法国文化系统提供了有力保障。加之法国汉语言教学及中国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完善,中法作家交流活动和文学研究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多样(张寅德, 2019),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译介在法国始终享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目前,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法国的译介总体呈现以下特点:其一,汉学界时时关注中国文学动态,发掘并译介新作家、新作品;其二,出版界对译介目标作家跟踪翻译、系统介绍;其三,中国文学研究者、译者和主流媒体对作家及作品进行专业、系统的研究评介(陈曦, 2017);其四,译介界兼顾思想与美学,发掘并突显中国作家的独特性及其作品的普遍性,以使作品跨越地域及文化距离,与法国受众在精神与情感上共振共鸣;其五,自2010年以来,以科幻小说、悬疑侦探小说为代表的大众文学被密集地译介到法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国际可见度”,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新的增长点(曹淑娟, 2021)。
4.文学外译可能的歧路及正道
从译入角度看,法国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译介实践及成果值得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会始终一路坦途。从译出角度考察,目前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的干扰总的说来有两点,即“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承认焦虑和全球经济化背景下的商业利益刺激。两种因素合力,使偏激功能主义译介说日益得势,对当下文学外译的推进产生了一定误导。
我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是我国文学界经过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话语转换,继五四运动之后再次力图将西方现代派文学内化,以求与新世界同步并融入其中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出而参与世界”主流叙事的强烈意愿,与之共存的是“基于现代化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中国落后于世界和时代的‘落后意识”。就文学而言,进化论文学观在文学界生发出“参照西方而指认自身的‘落后意识”(贺桂梅, 2021:178),将西方现代派文学置于进化的顶层;于是实际上,“对‘西方现代派的‘发现同时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的重新建构”(贺桂梅, 2021:182)。将欧美文学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再次成为滞后文学,这种对“世界文学”的想象是当代“中国‘打开国门朝向全球资本市场进军这一历史情境在文化问题上的投影”(贺桂梅, 2021:183)。由此,我国文学界长期陷入向欧美文学系统求认同的焦虑。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被承认的焦虑又表现为取得以销量为指标的读者认可。这种以读者“买单”为己正名的偏激功能主义论调无疑将妨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良性发展。
功能主义译论面向目标语读者,其中“功能”指翻译的传意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体现为“接受者对文本的使用或文本对接受者的意义”,它允许译文功能与原文意图存在一定差异。功能主义译论将受众纳入考察,是对原文中心论的纠偏。但偏激功能主义论调走向另一极端,以目的论证手段之合法,轻视甚至无视原文文本意图,以可接受性为一切改写正名,落入受众中心之谬。作者授权往往是支持改写的有力理据,但由功能主义译论而出的读者视域是以“作者已死”为口号消解作者权威的结果。彼时为服务读者而杀死作者,此时又以同一理由招魂作者,颇有矛盾之嫌。且不说作者同意改写的意图为何,作者是否有权大肆更改已经流通的文本也有待进一步商榷。面对偏激功能主义,学界必须对中国文学“走去出”的真正目的持有清醒认识。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为了进入他者文化空间,成为“世界文学”的构成因子;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又译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学”说可为深入考察该问题提供有益参考。达姆罗什在三个层面界定了“世界文学”,在此我们仅讨论与文学外译相关的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丹穆若什, 2014:309)。椭圆的两个焦点是源文化(source culture)空间与宿主文化(host culture)空间。翻译是以原作为起点,使其携带的源文化空间民族性与宿主文化空间民族性相遇、协商、共存而无压制,使前者向“世界文学”作品蝶变的过程。蝶变出的译作同时面朝两个焦点,呈分裂与统一之势,其所在是两个文化空间折射出的间性空间,而非任何民族性的焦点空间。“世界文学”的世界性是不同民族文学性在间性空间中相遇对话而生发的,并非某种形而上的、整合殊性的一般法则,而是一种跨文化互文性。换言之,“世界文学”即民族文学的跨文化互文文本。如此,“译者对译出语怀有的道德责任”(达姆罗什等, 2012:6)便可解为“在内在精神层面上忠于原文,忠于作者的原创精神”(顾明栋, 2020:109),突显原作的民族文学异质性,使之与译入语民族文学性构成有效的跨文化互文关系,最终将原作引入由文学世界性构成的椭圆空间。在第二个层面,“世界文学”是“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阅读模式(丹穆若什, 2014:326),具备“世界文学”意识是读者正确打开译作的前提。“世界文学”意识,首先是对译作世界性的意识。这既是达姆罗什对读者的要求,也是对文学教育培养读者“世界文学”意识以及互文阅读意识和能力的要求,同时还是对译者的要求。其一,译者要心怀“世界文学”读者而非民族文学读者;其二,译者对译出语和译入语的民族文学文化都要有深刻认知,并有意识和能力使二者在译作中形成互文关系。
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说解构了翻译的原作中心论以及作者或读者中心论,使翻译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建构了非此非彼、既此又彼、具备互动对话力的文学跨文化互文新空间。将“世界文学”说与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ois Jullien)的“间距”说综合考察,对我们开拓中国文学外译的新空间有所启发。
翻译及翻译研究无以回避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哲学表明,分裂的自我始终会去他处寻找“自我存放在‘他性中奥秘”(彭兆荣, 2022:103),朱利安正是在此认知基础上展开“间距”哲思的。他思考的核心在于出离自己生长其中的运思框架,走向高度异质的他者,“策略性地从侧面切入,触及我们的未思”,而“未思”(limpensé)即我们的“思想在不知中所依靠”的基点(Jullien, 2022:18)。“绕道走出自己思想的偶然性,或换言之,在自己的思想中获取后撤”(Jullien, 2008:22),与自明性保持距离,此为“外部解构”(la déconstruction du dehors)。绕道即走向他者,其目的并非补充知识,而是观照他者,以悬置用熟悉性遮蔽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在不假思索的先见中日益迟钝的已有视点,最终反思、解构、重构自我。外部解构操作的核心是拒绝差异比较,是在差异间拉开距离使之互观并反思。比较差异被朱利安指认为文化霸权的同谋,其上游暗含先验的、本质论的种属,其下游暗含认同的目的。比较差异是用一己世界观分析、定性和吸收他者世界,最终将导致文化多元性的消失,而拒绝比较即拒绝先验的、本质主义的抽象法则。朱利安主张在差异之间打开“间距”(lécart),使自我跳出既存规范,在他我之间制造张力,使他我互观。在这种观照过程中,熟悉性突然破灭,隐于自明性的“未思”顯出他者的陌异面貌,来自他处的他异性使内含于自我的他异性袒露并引发反思。依此观之,他者是冲击自我既存认知框架、革新自我视力的力量,是反思的动力,是自我去范畴化进而再范畴化的观照工具(Wald Lasowski, 2016:738)。
“間距”并非将殊性隔离在绝对他异性中的封闭空间,而是多视角转换、解除曲知之蔽的开放性生产空间。朱利安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其哲思与其翻译理念共出一源,可以互相发明;他也正是通过“间距”在鲁迅作品中观出异于西方象征主义、承自“春秋笔法”的“迂回”运作所造就的象征写作(梁海军, 2019:71)。不同的运思出发点构成不同的地方文化对“人之共有”的异样认知方式和认知结果,但人人共有的智性又使共有经验可以被理解。兼具世界性和地方性的文学作品,是本族群体观照“人之共有”之视角和方式的文学表述,而翻译将译出语文化意指“人之共有”的殊性呈现给译入语文化受众,进而激发文学之间的间性空间特有的互观和反思的动力。译者当尽力立于两种语言之间,维持二者的“面对面”(le vis-à-vis),以使“这一方的可能也被另一方识别并且认可,并且渐渐地找到作为反思条件的事物”(朱利安, 2014:123);而译作的语言是翻译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开启的、可使异质的情与思互观并反思的生产空间,其力度是对不同文学语言机制本身的显现力度;理想的译本则当对读者施以有力的外部解构。“间距”所启示的文学翻译旨在促成异质文学的相遇和对话,唯如此,本族文学才能在观照他者的过程中解构并重构自身,探得最具生产力的新生路径。“间距”说下的翻译理念关注他者文学的译入,是对本族文学新生的关怀,但它对文学外译也不无启示,因为我们可借之了解法国译介界对我国文学的期待,即以中国文学之他性解构并重构法国本土文学。
综合达姆罗什和朱利安的思考,我们认为文学外译应以读者为导向。这并非以偏激功能主义鼓吹的方式去迎合读者,而是为其提供一种异质文学文化得以互文对话的间性空间,这样做的基础是译者对原文文学地方殊性的维护和突显。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赞助人应选择译介展现我国文化对人类共有经验的特有之思的作品,推广传播者也应深刻认识并在传播中保存和突显我国文学文化之于宿主文学文化的他异性。经由宿主文化空间折射的译作应同时面朝宿主文化空间和我国文化空间,而非与其中之一重叠。如此而为的重要意义在于借助他者孕育一场我国文学文化新生的外部解构,因为我国读者所见的译作他异性,不仅有宿主文学文化的他异性,更有我国文学文化“未思”的自我他异性。
5.结语
20世纪80年代,中法两国的文学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两国文学界均有摆脱既存话语规范、向人的心灵纵深处和私密处挺进的诉求,法国比较文学界也意欲以全新的、平等的目光考察新生的中国文学。这样的文化景观和学术环境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法国的译介提供了可能。法国译介界始终坚守思想与美学并重、地方性与世界性兼顾的原则,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法译介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但反观国内,希望被西方文学系统承认的焦虑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的市场效益的双重刺激令中国文学外译生发出一种极端的功能主义倾向,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产生了一定误导。在此情势下,我们应坚定中国文学“走出去”以走向他者文学文化、建构异质文学互动对话的“世界文学”为目的,文学外译应为“世界文学”读者构筑中国文学与他者文学跨文化互文的“间距”空间,谨防出产没有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
注释:
① 本文对外文文献的直接引用均为作者自译。
参考文献
[1]Brunel, P. & D. Huisman. Littérature Frana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M]. Paris: Librairie Vuibert, 2007.
[2]Compagnon, A. Chapitre XII Lpuis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son éternel recommencement[A]. In J-Y, Tadié(ed.).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Dynamique & Histoire II[C]. Paris: Gallimard, 2007. 783-802.
[3]Giafferri-Huang, X. Le Roman Chinois depuis 1949[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1.
[4]Hao, Y. Vers une théorisation de la traduction fran?aise de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chinoise[J]. Antipode S, 2019, 2(1): 369-383.
[5]Jullien, F. Une déconstruction du dehors de la Grèce à la Chine, ou comment remonter dans les partis pris de la Raison européenne[J]. Synergies Monde, 2008,(3): 21-36.
[6]Jullien, F. Mose ou la Chine, Quand ne se déploie pas lidée de Dieu[M]. Paris: ditions de lObservatoire/Humensis, 2022.
[7]Kevin, H. Séparer la fine fleur du chiendent: de la sélection des uvres littéraires chinoises proposées au grand public francophone[J]. Parallèles, 2015, 27(1): 72-88.
[8]Marx, W. LAdieu à la Littérature: Histoire dune Dévalorisation (XVIIIe-XXe Siècle)[M]. Paris: ditions de Minuit, 2005.
[9]Rabut, I. Un siècle de modernité chinoise[J/OL]. Zone littéraire, 2004. https://www.zone-litteraire.com/litterature/enquetes/un-siecle-de-modernite-chinoise.html.[2023-2-1].
[10]Sartre, J-P. Situations II: Littérature et Engagement[M]. Paris: Gallimard, 1948.
[11]Wald Lasowski, L. A. Panorama de la Pensée dAujourdhui[M]. Paris: Fayard, 2016.
[12]阿隆森.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M]. 章天乐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3]艾田伯. 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M]. 胡玉龙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4]曹淑娟. 中国当代类型文学近十年在法国的译介[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21, (5): 126-128.
[15]陈曦. 法国视阈中的中国当代文学[J]. 当代文坛, 2017,(5): 70-74.
[16]陈嘉琨. 近三十年法国报刊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接受、评价与阐释[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2, (5): 59-65.
[17]陈永国. 阅读何为:文本·翻译·图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18]达姆罗什, 李锐, 王菁. 世界文学 民族语境[J]. 中国比较文学, 2012, (2): 1-18.
[19]丹穆若什. 什么是世界文学?[M]. 查明建, 宋明炜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0]方梦之(主编). 翻译学辞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1]顾明栋. 读者型翻译与作者型翻译——谈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翻译理念[J]. 山东外语教学, 2020, (6): 106-117.
[22]贺桂梅. 打开中国视野:当代文学与思想论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23]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24]季进.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家访谈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25]金雯. 在类比的绳索上舞蹈:比较文学中的平行、流通和体系[J]. 中国比较文学, 2021, (3): 13-26.
[26]梁海军. 论弗朗索瓦·朱利安的鲁迅研究[J]. 鲁迅研究月刊, 2019, (6): 67-73.
[27]刘云虹. 翻译家的选择与坚守——杜特莱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之路[J]. 中国翻译, 2019, (4): 104-110.
[28]栾荷莎. 法国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历程与阐释流变[J]. 外语学刊, 2022, (1): 66-72.
[29]钱林森. 中国文学在法国:18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9.
[30]唐利群. 何碧玉教授访谈录[J]. 国际汉学, 2010, (2): 23-27.
[31]滕威. 拉美“文学爆炸”神话的本土重构[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6, (1): 85-91.
[32]彭兆荣.“我”在“他”中[J]. 读书, 2022, (2): 97-105.
[33]雨果. 论文学[M]. 柳鸣九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34]曾念长. 断裂的诗学:1988年的文学、思想与行动[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聯书店, 2017.
[35]张寅德. 法国比较文学的中华视野[J]. 国际比较文学, 2019, (2): 321-332.
[36]朱利安. 进入思想之门:思维的多元性[M]. 卓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杨彬)
收稿日期:2023-04-28;修改稿,2023-08-06;本刊修订,2023-09-1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效能、影响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XW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俊平,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研究、中法比较文学。电子邮箱:lamerthomas@163.com。
胡安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研究、中国文学外译。电子邮箱:1251524220@qq.com。
引用信息:周俊平,胡安江.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法国的译介:现状与反思[J].山东外语教学,2023,(5):12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