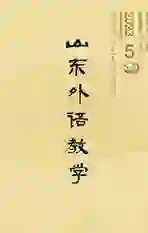拉各斯的诱惑
2023-11-21杜志卿张燕
杜志卿 张燕
[摘要] 赛普瑞安·艾克文西的长篇代表作《城市中的人们》和《贾古娃·娜娜》把尼日利亚旧都拉各斯描写成既是自由、平等和充满机遇的理想之地,又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堕落之地,生动体现了作家对拉各斯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两部小说的城市书写虽延续了欧洲城市小说中城乡对立的主题,但对乡村和宗教的救赎力量持保留态度。在作家眼中,城市里的人们追逐物欲和肉欲满足,在堕落中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即使传统的乡村生活和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也无法为他们提供救赎力量。艾氏对城市的矛盾情感反映了他对独立后尼日利亚何去何从的迷茫以及男性至上的性别歧视意识。
[关键词] 艾克文西;《城市中的人们》;《贾古娃·娜娜》;拉各斯;城市书写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23)05-0080-10
The Allure of Lagos: Urban Narrative in C. Ekwensis People of theCity and Jagua Nana[JZ)]
DU Zhiqing1,2 ZHANG Yan1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En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1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age of the city Lagos in Cyprian Ekwensis best-known novels, People of the City and Jagua Nana. These two works depict Nigerias former metropolis Lagos both as a dreamland full of equality, freedom and opportunities, and as a corrupt place shorn of morality, which impressively reflects Ekwensis ambivalent love-hatred attitude toward the city.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Ekwensis depiction of Lagos in the two novels extends the motif of city-country dichotomy prevalent in European city writings. However, different from European authors of city writings, Ekwensi is pessimistic about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the country and religion. In his view, people in the city have degenerated in the satiation of their desires for sex and material profits so much that neither the traditional country life nor the Western Christian belief can be their salvation. Ekwensis ambivalence in his urban narrative reveals his sexism, as well as his bewilderment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newly independent Nigeria.
Key words: C. Ekwensi; People of the City; Jagua Nana; Lagos; urban narrative
1.引言
早期尼日利亚的英语小说常把故事背景设置在前殖民时期或殖民初期的乡村,鲜有对与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相伴相生的现代城市进行书写。图图奥拉(A. Tutuola)的《棕榈酒酒徒》(The Palm-Wine Drinkard,1952)和《我在鬼林中的生活》(My Life in the Bush of Ghosts,1954)、阿契贝(C. Achebe)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和《神箭》(Arrow of God,1964)以及阿馬迪(E. Amadi)的《妃子》(The Concubine,1966)莫不如此。赛普瑞安·艾克文西(Cyprian Ekwensi,1921-2007)被誉为尼日利亚“城市小说之父”,是最早把笔锋对准城市生活的尼日利亚作家。虽然他早期不少作品将背景设置在乡村,但其重要作品如《城市中的人们》(People of the City,1954)(以下简称《城》)、《贾古娃·娜娜》(Jagua Nana,1961)(以下简称《贾》)、《伊斯卡》(Iska,1966)以及《贾古娃·娜娜的女儿》(Jagua Nanas Daughter,1986)等都把故事背景设置在尼日利亚旧都拉各斯(Lagos)。与阿契贝及其他作家不同,艾克文西的自我定位是不为“艺术而艺术”的通俗小说家。他声称,“在我们的社会中,作家不可能为艺术而写作,因为有许多刺痛良心的问题存在”(qtd. in Dogon-Daji, 2016:10392)。他强调自己不是那种文学形式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能直击普通人看得出的事实的核心”(qtd. in Oti-Duro, 2015:43)。
虽然艾克文西将自己定位为通俗小说家,但不少学者都认为他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典作家。珀维(John Povey)和帕尔默(Eustace Palmer)是重新发现这位作家的重要学者,他们认为,如果评论者能看到艾克文西作品的社会关怀,就能更好地欣赏其文学价值(Ola, 1985:48)。尼日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伊曼尤纽(Ernest Emenyonu)认为小说《贾》在西非英语文学的发展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Tariq, 2004:210)。 帕里(J. Parry)甚至认为《贾》可以比肩阿契贝的《瓦解》和图图奥拉的《棕榈酒酒徒》(Emenyonu, 1974:79)。目前我国学者对艾克文西的研究尚未有效地开展,仅对他的创作生涯、主要作品进行过较为具体的介绍(颜治强,2019:132-148)。本文将深入分析这两部作品中人物在城市空间中的生活体验,旨在凸显作家矛盾的城市观,并揭示独立前后尼日利亚人民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辛酸和迷茫。
2.梦想与欲望之城:令人爱恨交加的拉各斯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城市總是有着矛盾的情感,文学作品中的城市书写也大抵如此,常给人一种爱恨交加的印象(徐刚, 2010:66)。艾克文西的城市书写也不例外。正如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所言,艾克文西对拉各斯的城市情感“是分裂的”:他热爱城市,所以能把拉各斯写得栩栩如生,但他又不断批判“城市的贪婪、冷漠、欲望以及腐败”(qtd. in Okonkwo, 1976:34)。在艾克文西笔下,拉各斯表征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城市里较好的基础设施能使居住者过上与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城》中的大比特丽丝(Beatrice I)毫不避讳告诉主人公桑果(Sango),吸引她到拉各斯的正是以“车、佣人、高级食物、体面的衣服”为代表的新生活方式(Ekwensi, 1969:72)①。这也是弗雷迪(Freddie)抛弃其显赫的酋长之子身份来到拉各斯的主要原因。
拉各斯是一个以自由和开放著称的城市。在19世纪50年代,拉各斯的人口有一半是前奴隶(Boostrom, 1996:63)。1866年尼日利亚首次人口普查表明,该市的居民除了来自本国各地不同族群,还包括1826年至1835年间从塞拉利昂的“自由镇”(Freetown)迁移过来已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及从葡萄牙前殖民地巴西迁来的那些获得人身自由的约鲁巴奴隶(Folola & Salm, 2004:275-276)。《贾》中,南希(Nancy)的父母就是从“自由镇”迁至拉各斯,但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受到任何歧视。艾克文西笔下的拉各斯可谓不同种族、部族和文化的融合之地。《城》中所描写的“普语俱乐部”(The All Languages Club) 是一个崇尚平等、自由以及部族融合的公共空间。它的创建人“想要朝着世界统一迈出实际的一步”(42),希望创建一个能让操各种语言、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互相了解的空间。或许是由于这种跨族群的平等理念深入人心,《贾》中来自尼日利亚各地的人们在拉各斯都使用洋泾浜英语。小说叙述者借主人公贾古娃之口说,拉各斯人之所以说洋泾浜英语是因为人们“不想要太多让人想起部族或习俗那些令人尴尬的东西”(Ekwensi, 1979:5)。正是拉各斯这种自由、平等的氛围让《贾》中贾古娃相继与弗雷迪、泰沃恋爱,并促成了《城》中若干青年男女的跨国恋情。
在艾克文西笔下,拉各斯还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实验地。尼日利亚首个政党“尼日利亚国家民主党”就是在拉各斯成立(Folola & Salm, 2004:33)。《城》写道,这座大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和政党,它们为了去殖反帝的共同目标——为尼日利亚人自己决定“能挣什么钱;吃什么食物;什么时间点睡觉;看什么电影”而战(56)。在拉各斯,除了成立政党和团体,人们还通过各种报刊杂志自由表达政治观点和立场。尼日利亚最早的现代报纸,如《拉各斯标准报》《英裔非洲人报》《尼日利亚先锋报》等都是在拉各斯创刊(Folola & Salm, 2004:33)。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些报纸以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敏感以及大胆的揭露而著称。艾克文西本人当过多年的新闻记者,深知报纸的政治力量(Riche & Bensemanne, 2007:41)。《城》中桑果供职的《西非知觉报》(West African Sensation)就是一份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报纸。作为该报的法制新闻记者,他常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大胆的揭露并提出辛辣的批评。他对东格林斯煤矿危机事件的报道曾让该报在全国热卖。更重要的是,他的报道使各部族的政治家们纷纷放下分歧,团结起来与制造煤矿危机的英国殖民政府作斗争。总之,尊重个性自由和倡导民主政治的拉各斯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吸引贾古娃到拉各斯的正是那种男女平等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拉各斯的女性可以“和男人一样在办公室里上班”,也可以“跳舞、抽烟、穿高跟鞋和窄腿裤”(Ekwensi, 1979:167)。
在欧洲的城市书写中,城市常是欲望和物质主义的代名词。在《城》和《贾》中,处于新旧秩序转型期的拉各斯也是充满物欲、肉欲的堕落之地。拜金主义操控着人们的生活,人们挤到城里往往是想“通过更快的手段挣到钱”(Ekwensi, 1979: 6)。对金钱的病态渴望致使城市里的人们道德沦丧。正如艾克文西所言,独立之前的尼日利亚“城市居住者没有选择,由于经济压力,他们不得不昧良心”(Nganga, 1984:282),在拉各斯不断上演着丑陋的“剧场秀”(154)。女性由于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能靠出卖肉身获取金钱,《贾》中的贾古娃和《城》中的大比特丽丝莫不如此。在拉各斯,穷人还常以诈骗和抢劫为生。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城》中的爱娜冒险行窃,贝约不惜出售假药,《贾》中的丹尼斯从事抢劫的勾当。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从不为自己那种“只在乎瞬间的快乐”和 “孤注一掷”的生活方式感到羞愧(Ekwensi, 1979:124)。相比之下,有钱人的道德沦丧也触目惊心。拉基德虽已腰缠万贯,但为了挣更多的钱也常常不择手段——他曾让人假扮警察扣押盗贼从军队里盗得的赃车,不费吹灰之力就发了一笔横财。而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政客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们背地里常为了金钱而玩弄政治、草菅人命。艾克文西认为,尼日利亚独立后的政府官员尤其是第一共和国的政客与小丑无异(Nganga, 1984:283),他们眼里只有权力和金钱,一旦身在高位就会把为大众谋福利的承诺都抛到九霄云外。《贾》写道,弗雷迪从英国留学归来后并没打算报效祖国,而是马上投身于大选并伺机敛财;而在泰沃大叔这个老政客眼里,政治除了能满足他的权力欲和虚荣心之外还带来巨额的灰色收入。见钱眼开的他认为“人命一文不值”(Ekwensi, 1979:155),企图挡住其财路的政敌弗雷迪就被他设局谋杀。总之,如艾克文西本人所说,拉各斯犹如阿里巴巴故事中四十个大盗窝藏赃物黄金的洞穴,任何知道咒语的人都可以进去自取想要的宝贝,但有时贪婪会让人不知不觉中了芝麻的圈套,下场就像阿里巴巴的兄弟一样(Emenyonu, 1974:29)。
城市里的物欲和肉欲似乎是孪生姐妹。艾克文西笔下的拉各斯不仅物欲横流,也是肉欲肆意流淌之地。有学者指出,现代城市人因为视觉而神魂颠倒,城市里的一切都能被转化成为各种可以采集的景观。在城市里,由于视觉比嗅觉、味觉、触觉、听觉更具优势,身体仅被简化为外表,而身体的其他多重知觉则被边缘化(厄里, 2008:158)。女人身体给人的视觉印象尤为容易被转化为色情景观。贾古娃就经常穿着暴露,在各个公开场合把身体的性诱惑力发挥到极致。“热带风情”俱乐部的姑娘们也在这座“现代的超级性交易市场”(Ekwensi, 1979:13)里放纵自己。《城》中除了贾古娃这类风尘女子,普通已婚和未婚女性也在“普语俱乐部”撩人的音乐声中诉说着自已的原始肉欲:“一听到桑果演奏的音乐,(她们)就放下手中的毛线活或针线活,抖动她们的屁股、腰肢和胸脯,……而那些还没找到男人的姑娘会在爱慕她们的男人面前以一种诱人的方式扭动着屁股”(Ekwensi, 1979:7)。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拉各斯就像一个原始肉欲恣意流淌的城市。
在艾克文西笔下,女性的堕落是城市欲望的重要表征。在拉各斯,似乎没有适合女性的正当职业,那里似乎也没有打压性交易的法律。在“热带风情”俱乐部生意不好的时候,女人们就肆意在街上揽客。贾古娃首次踏上拉各斯的土地时就被一个皮条客收留并被转手给一个英国男子当情妇。作家或许想以这种夸张的表现方式说明拉各斯女性的集体堕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他的城市书写中出现大量将女人欲望化的身体意象。也正是这种“对女性不加掩饰的解剖”导致一些宗教和女性组织对《贾》进行猛烈的抨击(Emenyonu, 1974:78)。
伊曼约努指出,艾克文西善于描写城市里人们如何运用自身的天赋及后天习得的能力来操控他们的生活和环境——他们未能实现生活目标的根本原因并非充满敌意的命运或他们同胞的恶行,而是他们自身的缺陷(Emenyonu, 1974:13)。奥比艾奇纳(Emmanuel Obiechina)则认为,与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1925)相似,《城》里的人物由于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而走投无路,甚至到了否定他们主体性的地步(Dunton, 2008:71)。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对金钱的迷狂以及对肉欲的本能追逐常使城市中的人们丧失理智和尊严。在《贾》中,艾克文西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呈现拉各斯人狂野的生活:对金钱的追逐使贾古娃仿佛变成追逐猎物的母狮,在拉各斯这个“天然的栖息地”伺机追捕猎物;那些与贾古娃一起疯狂挥霍青春的姑娘们常在那个绝佳的狩猎地点——“所有进城及出城道路的交汇点”等候她们的猎物(Ekwensi, 1979:106)。汉斯(Z. Hans)和希尔福(H. Silver)认为,在艾克文西的城市书写中,“人物虽是活的,却劣于造就他们的环境”(qtd. in Dunton, 2008:70)。不言而喻,在拉各斯,对肉欲和物欲的追求致使人们丧失了主体性,沦为城市动物,而拉各斯这个非主体性的存在却如奇拉姆(D. Killam)所言,“扮演了人物的角色,控制、界定、组织而且经常摧毁居民的生活” (qtd. in Dunton, 2008:70)。这个追逐金钱和肉欲的城市注定会毁灭人性:《城》和《贾》中的重要人物“都是毫无成就的个体”(Obiechina, 1975:103),而且都一一命丧拉各斯。贾古娃虽没有死在城里,但在那失去了用身体换来的所有钱财。桑果也同样一事无成,没有实现在拉各斯出人头地的愿望。伊曼约努认为,这两部小说中各种人物的悲剧性遭际表明,艾克文西在小说中“既是原告,又是陪审团,他的《大宪章》中只有一句话,罪恶的代价是死亡”;这些死亡同样也说明拉各斯俨然是“小说中的恶棍” (Emenyonu, 1974:43),“每年(要)吞噬许多无辜的生命”(149)。这两部作品显然隐含了作家对欲望之城的伦理批判:拉各斯并非普通民众逐梦的理想之地!
3.从城市到乡村:寻找救赎的力量
从《城》和《贾》的故事情节中,不难看出城乡的差异与对立:城市只要结果,不在乎手段,为达目的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城市充满混乱、腐败和堕落,因此道德与法律几乎无用武之地。而乡村仍保留着较强的是非观,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依然是人们生活的根基。在《贾》中,艾克文西通过人们对待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不同态度来折射城乡的差别及对立。在乡村,女性裸露身体比较常见,并无太多的性暗示,男性在观看时通常不会有色情的联想,因为 “在这一部分的世界里占上风的是自然,裸露并不是什么稀奇事”(Ekwensi, 1979:71)。然而在城市里,女性的身体往往已被客体化,通常就是肉欲的代名词。因此,从未到过拉各斯的桑果母亲给儿子写了许多信让他当心城市生活。在桑果母亲眼里,城市充满邪恶。为了预防堕落的城市女性对儿子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她在乡下挑选了一个“来自好人家的正经姑娘”艾莉娜当他的未婚妻(8)。纯洁、无邪的艾莉娜可谓乡村姑娘的典范,她被精心地保护在一个“看不到世界的邪恶,只谈论美德和纯真”(82)的乡村修道院里。久居城市的桑果见到纯真无暇的艾莉娜时便“因自己的城市背景而诅咒自己”(83),觉得自己的身体“必须要实施某种净化处理”(82)才能配得上她;修道院纯洁而宁静的氛围一度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看不到“得救的希望”(83)。
城乡对立是英国乃至欧洲城市书写中的重要母题。艾克文西的城市书写似乎没有偏离这一经典母题,但他笔下的城乡对立主要是通过两性关系的描写展示出来,而且城市的罪恶更集中体现为女性的性堕落。在《贾》中,贾古娃在离开家乡奥戛布(Ogabu)之前接受了其父为她安排的婚事,她“想安顿下来,做个贤妻”(Ekwensi, 1979:167)。但她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城市新生活的诱惑而前往拉各斯成了风尘女子,完全把自己变成欲望的奴隶。实际上她对精神生活没有兴趣,而且也没有足够能力去理解诸如“白人帝国主义在尼日利亚终结的个人记忆”这样的讨论内容。《城》中大比特丽丝也是城市堕落女子的典型代表,为满足虚荣和欲望,她不惜成为男人们的玩物,最后病死在拉各斯。或许作家就是想以她的死亡来隐喻女性堕落而遭受的惩罚。贾古娃虽未客死他乡,但失去了所有的财物以及当母亲的机会,最终不得不离开拉各斯又回到乡村。与此不同的是,桑果是诱惑良家妇女性堕落的城市男性,他“完全拒绝乡村生活、传统价值及其内在美”(Emenyonu, 1974:39),但他却未遭受任何惩罚,反而还获得了作家的同情,被看做是受“妖妇”爱娜引诱的受害者(151)。艾克文西甚至通过不太可信的“情景剧方式”(Emenyonu, 1974:43),让桑果心仪的对象小比特丽丝的男友出车祸而死,从而使他得以顺利和她结婚,如愿以偿留在本不愿离开的拉各斯。小说《贾》中也是女性在拉各斯受到诱惑而堕落,男性却能自如应对城市里的声色犬马,在作家眼中,似乎只有女性才需要远离城市,接受乡村生活的保鲜。因此,可以说他在该小说中进行了城市—乡村之间的“空间性别化区分”,把城市空间的主导权交给男性并按他们的意图来描绘,女性只能囿于传统角色。这种空间话语权力的分配是福柯所指的“通过移植、分配、划界、对领地的控制以及一些领域的组织等策略构成了某种性别地理政治”(Riche & Bensemanne, 2007:44),體现了作家明显的性别偏见倾向。
从堕落的城市回到传统的乡村,洗心革面、重整道德秩序是18世纪前期英法文学城市书写的惯用模式(陈晓兰, 2014:103)。那时城市文学中净化的力量主要来自宗教和自然。按照莱切和本赛曼的看法,贾古娃在乡下的父亲身为神职人员,这一细节安排绝非偶然。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看,城市象征着罪恶,而优美的乡村则代表着善,是上帝用神性创造出来的。因此,他们将贾古娃从乡村到城市之旅理解为她从善向恶的堕落过程,而她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则是一场救赎之旅(Riche & Bensemanne, 2007:39)。不过应当看到,乡村的新宗教,即西方的基督教并不能成为贾古娃的救赎力量,因为当她从拉各斯回到家乡时,她的牧师父亲已经去世四天,她已没有机会接受父亲的宗教劝导。巴兰迪亚(G. Balandier)在《歧义的非洲》中指出,比起尼日利亚其它城市,拉各斯更像是由英国人建立的城市(Dunton, 2008:70)。从本质上讲,艾克文西在书写拉各斯这座欲望之城的同时也把批判的笔锋指向英国的城市文化,因为拉各斯毕竟是英国殖民文化的产物。
小说《贾》在情节上与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娜娜》(Nana, 1880)颇为相似,两位女主人公还名字相同,因此有论者认为《贾》受到左拉的《娜娜》的影响(Nganga, 1984:281)。在左拉笔下,美丽的大自然唤起了妓女娜娜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和羞耻感,也唤醒了她的母爱,使她懂得了爱情并最终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而得到了救赎(陈晓兰, 2014:140)。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拯救了贾古娃?我们发现,与左拉笔下的娜娜被大自然所拯救不同,艾克文西笔下的贾古娃·娜娜是在回归乡村老家及传统的生活方式之后才开始过上有尊严的新生活。她似乎在提及儿时生活时才幡然悔悟自己在城市里的堕落,后悔自己忘记了“在奥戛布自由而简单的生活”(Ekwensi, 1979:178)。拉各斯践行的是英国城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其居住者却无法安居乐业。笔者认为,艾克文西让贾古娃回归乡村或许还隐含了他这样的观点:传统的非洲价值观并没有奴役非洲女性,奴役非洲女性的是西方殖民文化,它把非洲女性变成欲望的客体和消费主义的奴隶。作家让贾古娃回归乡村或许源于想让她重新“赎回”在城市中因西方殖民文化奴役而失去的尊严。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贾古娃在城市里一事无成却能在乡下过上体面的生活,完成自我实现。
在艾克文西眼里,非洲人如果忘记乡村老家,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就会失去自我,永远没有归属感。他曾在访谈中说,“没有一个真正的非洲人会忘记他的家。他总是想着某一天会回家。……如果一个人想要找到生活的方向,家谱是最重要的”(Nganga, 1984:282)。在其《非洲作家的两难处境》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读者可以在他的小说中清晰感受到其非洲思想背后的心理以及作为他小说源泉的哲学和文化模式(Lindfors, 2010:175)。贾古娃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往复演绎了一种环形的生命轨迹。谢尔顿(Austin Shelton)认为,这一环形生命轨迹展示了“非洲性的环形原则”,暗示她重新回到其非洲传统并得到了升华(qtd. in Lindfors, 2010:175)。换言之,贾古娃通过这种“本体论上的撤退”获得了心理上和哲学上的充实进而得到救赎:她不仅在乡村实现了其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的当母亲的梦想,而且她还“被置于奥戛布神祇般的地位”(Emenyonu, 1974:91)。
非洲作家倾向于将社会的部分变化视为个人的文化身份从完整到分裂、迷失的变化,他们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坚持传统或回归传统所认可的行为来“重获自我的完整性、行为的正确方向以及应有的嘉许”(Emenyonu, 1974:91)。但必须指出,艾克文西对乡村的救赎力量并未持乐观态度。或许这也是他在《城》和《贾》中对乡村着笔不多的重要原因。艾克文西的一生都在城市里度过(Nganga, 1984:281)。奥贡喀沃也指出,与阿契贝、阿马迪、恩瓦帕等作家不同,艾克文西出生的环境、早年的生活以及职业生涯使他无法系统获取有关乡村传统的第一手资料(Okonkwo, 1976:34);他认为艾克文西对乡村生活着笔较少是因为他对尼日利亚传统乡村生活缺乏了解。笔者不太赞成这一观点。艾克文西虽生长在城市,但他父亲是颇受欢迎的口传表演者和著名的说书人(Emenyonu, 1974:70),一生都在传承尼日利亚传统。正是受到其父的影响,他才萌发了文学创作的热情。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里,但在业余时间总会到农田帮忙、喂养家里的山羊或看他父亲雕刻或割棕榈酒(Emenyonu, 1974:47)。艾克文西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创作的小说都将背景设置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他在这两部小说中对乡村着墨较少或许是源于他对以乡村为代表的尼日利亚传统文化的态度。与阿契贝和阿马迪不同,艾克文西并不具有浓厚怀旧主义情绪,也不向往乡村牧歌情调。对他而言,尼日利亚传统乡村社会的瓦解不可避免,他甚至期待那种缺乏杂交影响的乡村旧模式的消亡(Okonkwo, 1976:34)。 因此,他在《城》和《贾》中用较少的笔墨来描写乡村及其传统文化,或许只是想把它定位为非洲女性逃避西方文化奴役的避难所而已。
事实上,读者可以从《城》中桑果对乡村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贾》中贾古娃的乡村经历中清楚地感受到艾克文西本人“在彻底的西化以及回归非洲传统之间来回摇摆的态度”(Lindfors, 2010:175):尽管桑果在返回乡村期间到修道院探望未婚妻艾莉娜,并被那里纯洁的气氛所感染而突然忏悔,但小说的叙述者告诉我们,当他看到纯洁而笨拙的艾莉娜时,丝毫没有要娶其为妻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在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意识到,艾莉娜曾是一种激励他远离堕落城市诱惑的力量,但“现在他感觉这种推动力已经消失”(83)。桑果的想法表明,乡村的纯真已无法对抗城市的堕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他在结婚之际想象艾莉娜的乡村生活时,心里“夹杂着局促不安、喜悦和悲伤之情”(157)。其实在艾克文西笔下,遭受西方殖民文化围剿的非洲乡村传统文化今非昔比,其纯洁性已受到严重挑战:在《贾》中,贾古娃在离开家乡去拉各斯之前就和村里多名男子有染,她不检点的行为虽然受乡村伦理道德制约,但她本人却很难践行传统道德理念。传统乡村生活于她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另外,虽然她在城市里撞得头破血流之后又回到乡村重新开启新生活,但假如她没有得到泰沃大叔留给她的那笔不义之财,也是不太可能过上有尊严的独立生活。由此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艾克文西矛盾的城乡观:乡村虽在一定程度上是逃避城市邪恶的避难所,但其传统的价值观念已很难对抗城市文化的侵袭。柯林斯指出,阿契贝等作家对独立后尼日利亚的未来流露出灰心丧气和无所适从的困惑(Collins, 1969:65)。笔者认为,上述那些细节或多或少也折射出艾克文西本人关于新尼日利亚何去何从的困惑:尽管英国殖民者给尼日利亚城市带来了一些改变,但人们却深受西方殖民者物质至上以及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不知如何去創造一种适合自己的新生活。
4.結语
艾克文西被誉为“现代非洲文学中的查尔斯·狄更斯”(Riche & Bensemanne, 2007:37),是“当代的记录者”(Okonkwo, 1976: 33)和“成功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家”(Tariq, 2004:225)。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艾克文西的文学地位不断上升,其作品的经典价值日益彰显。有论者甚至称,“五十份政府报告都没有他的小说如《城》等告诉读者那么多有关西非的情况”(Emenyonu, 1974:1)。艾克文西曾指出,小说家应是一面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qtd. in Emenyonu, 1974:125)。事实上,尼日利亚独立前夕许多人都陶醉于“镀金的国家形象”(Emenyonu, 1974:2),但他作为一位通俗作家却能较客观描写“拉各斯的暴力、欲望、混乱、残忍以及各种压力”(Ola, 1985:52) ,生动地展现殖民语境下尼日利亚社会的真实风貌。萨特曾言,“作家有责任将小说视作一种反思历史、改变现实处境的不朽力量”(转引自程彤欣、刘白,2023:92-93)。如果说阿契贝、索因卡聚焦的是尼日利亚受过教育的少数精英人群的命运,那么艾克文西最关心的则是城市里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他坦诚直面转型期尼日利亚社会的各种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虽然他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他带着极大的同情对其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Emenyonu, 1974:11)。艾克文西对拉各斯这座城市爱恨交加,其城乡观不乏矛盾,表露了他对尼日利亚何去何从的迷茫,但其城市书写体现了当代尼日利亚的现实主义图景,无疑反映了非洲知识分子努力寻求历史根基、思考现代文化和表达自尊的努力,“迈出了(非洲)文化解放的第一步”(Emenyonu, 1974: 122)。另外,我们看到艾克文西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作家把目光投向城市,投向拉各斯,作为非洲城市书写的先驱者,艾氏自然功不可没。
注释:
① 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详注。
参考文献
[1]Boostrom, R. Nigerian Legal Concepts in Buchi Emechetas The Bride Price[A]. In M. Umeh(ed.). Emerging Perspective on Buchi Emecheta[C].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6. 57-93.
[2]Collins, H. Amos Tutuola[M]. New York: Twayne, 1969.
[3]Dogon-Daji, U. M. Thematic Analysis and Significance of Cyprian Ekwensis Novel The Burning Gra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6, 6(11): 10388-10395.
[4]Dunton, C. Entropy and Energy: Lagos as City of Words[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08, 39(2): 68-78.
[5]Ekwensi, C. People of the City[M]. New York: Fawcett World Library, 1969.
[6]Ekwensi, C. Jagua Nana[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9.
[7]Emenyonu, E. Cyprian Ekwensi[M]. Ibadan: Evan Brothers, 1974.
[8]Folola, T. & S. Salm. Nigerian Cities[M].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04.
[9]Lindfors, B. Early West African Writers: Amos Tutuola, Cyprian Ekwensi and Ayi Kwei Armah[M].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10.
[10]Nganga, B. An Interview with Cyprian Ekwensi[J]. Studia Anglica Posnaniensia: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984, (17): 279-284.
[11]Obiechina, E. Culture, Tradition and Society in the West African Nove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2]Okonkwo, J. I. Ekwensi and Modern Nigerian Culture[J].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1976, 7(2): 32-45.
[13]Ola, V. U. Cyprian Ekwensis ISKA Revisited[J]. UTAFITI: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85, 7(1): 48-52.
[14]Oti-Duro, N. A. The 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Novels of Cyprian Ekwensi: A Study of Jagua Nana, ISKA and Jugua Nanas Daughter[D]. Kwame Nkrum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15]Riche, B. & M. Bensemanne. City Life and Women in Cyprian Ekwensis The People of the City and Jagua Nana[J]. Revue Campus, 2007, (8): 37-47.
[16]Tariq, G. G. Traditional Change in Nigerian Novels: A Study of the Novels of Tal Aluko and Cyprian Ekwensi[D]. Sri Krishnadevaraya University, 2004.
[17]程彤歆, 劉白. 以幻想演说历史:科尔森·怀特黑德《地下铁道》中的非洲未来主义书写[J]. 山东外语教学, 2023,(1): 85-94.
[18]陈晓兰. 性别·城市·异邦: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19]约翰·厄里. 城市与感官[A]. 汪民安等主编. 城市文化读本[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55-163.
[20]徐刚. 1950至19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叙述[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0,(6): 66-72.
[21]颜治强. 论非洲英语文学的生成:文本化史学片段[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责任编辑:翟乃海)
收稿日期:2023-03-01;修改稿,2023-09-05;本刊修订,2023-10-0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项目编号:19ZDA29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与历史语境下的尼日利亚英语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3BWW0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志卿,硕士,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族裔文学、非洲英语小说。电子邮箱:chrisduzq@163.com。张燕,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女性文学、非洲英语小说。电子邮箱:sallyzhang7206@163.com。
引用信息:杜志卿,张燕.拉各斯的诱惑——艾克文西《城市中的人们》和《贾古娃·娜娜》的城市书写[J].山东外语教学,2023,(5):8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