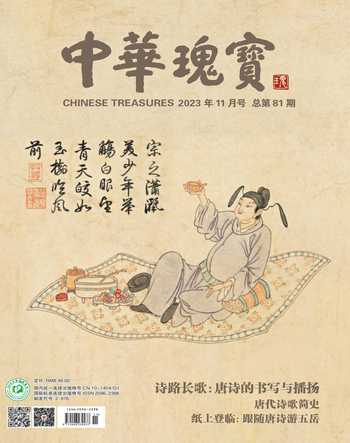诗中两曜 永放光芒
2023-11-09徐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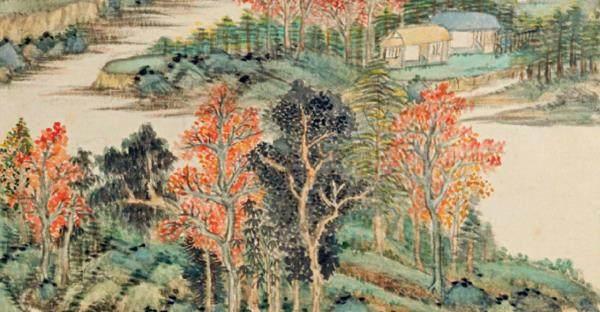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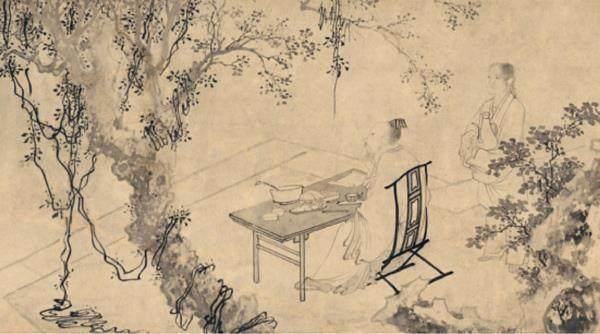
李白和杜甫是闪耀在唐代文化夜空中的双子星座,其诗作沾丐后人,跨越时空,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则是中国诗歌的高峰。有关论述不胜枚举,笔者最喜闻一多先生所言:“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闻先生“诗唐”说的重要内涵之一便是唐代“诗的形式和内容达到极点”,另一内涵则为“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说他们的诗是生活化了的”。
李杜双星为共识
闻先生“诗唐”说十分简洁地概括了唐诗的成就及其繁荣的原因,颇有特色。人们把唐诗称为“真正诗国之代表”,其犹如巍然耸立的珠穆朗玛峰,令人仰望。而李白、杜甫是“诗中的两曜”,即大唐诗空中最明亮耀眼的星辰。闻一多先生对此同样有精彩的论述,他这样描写李、杜的初次见面:
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
如椽大笔,浓墨重彩,惊心动魄。1962年,郭沫若在杜甫诞辰12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诗歌史上的雙子星座》的著名讲话,称“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里对李、杜的评价是公允的,其渊源便是来自闻一多。从此,“双子星座”成为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李白与杜甫的专称,代表了世人对李、杜的普遍看法,这也是当今学界的基本共识。
清人赵翼《论诗五首·其二》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气魄和观念值得肯定,但创新与传承其实并行不悖,如陆游《读李杜诗》所写:“濯锦沧浪客,青莲澹荡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风尘。士固难推挽,人谁不贱贫。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可见李、杜之诗,价值永恒,常论常新。
李、杜彼此孰优孰劣,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1971年,郭沫若曾撰《李白与杜甫》,一改9年前李、杜地位并列的评价,抑杜扬李,引起轩然大波。历史上学界虽然总体认可李、杜二人地位相当、各有优长,对古典诗歌的独特贡献无可替代,但由于受众性格、年龄、阅历差异等各种原因,对李、杜诗歌有不同偏好,导致扬此抑彼也是长期的客观存在。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元稹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称赞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云“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又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是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请而作,高度评价杜诗,合情合理。在此之前,已有杜甫生前挚友樊晃赞誉其“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并无异议。但接下来元稹将杜甫与李白进行对比,认为李白在乐府诗歌方面可勉强比肩于杜甫,其他许多方面却远远不如。由此引发一场扬杜抑李的千古公案,成为李、杜优劣论之滥觞。
元稹的观点影响很大,甚至为《旧唐书》《新唐书》等官修史书所采纳,但同时也常为人所非议,以至有人说韩愈《调张籍》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就是对其有针对性的批评。虽然此说并未证实,但韩愈及大多数诗人显然都是将李、杜并列的。宋、元、明、清时期,杜甫被推到“诗圣”的崇高地位,但人们总体还是比较平和,崇杜却并不抑李,虽有个人偏好,却愿意做出客观评价。如苏轼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南宋严羽更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李、杜数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蛩吟草间耳!”这些堪称公允之论。
虽然元稹最早将李、杜进行比较,但将“李杜”之名并举并非始于元稹。早在唐元和之初,韩愈《荐士》诗就写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感春四首·其二》曰:“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韩愈在诗作中多次将李、杜并举,可见其对李、杜崇敬之情。而在此之前,大历九年(774年)中举的诗人杨凭即有《赠窦牟》(一作《窦洛阳牟见简篇章,偶赠绝句》)诗云:“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南荒不死中华老,别玉翻同西国人。”该诗以“李杜”并称,时间早于韩愈。
《新唐书·杜甫传》记载:“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这一说法将李、杜并称直接提前到杜甫青少年时代,显然不可信,因为当李、杜相会时,李白早已名满天下。我们不妨按照以杜解杜之法,看看杜甫自述。晚年杜甫有《长沙送李十一衔》诗道:“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因为李白是杜甫仰慕的兄长,诗中表达了与之齐名的惶恐自谦,可证明杜甫晚年已经出现李、杜并称的情况,也反映出杜甫入蜀后创作成就已逐渐为诗坛所认可。
李杜相异亦相同
在众人眼中,李、杜二人在性格、诗风等多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一者飘逸浪漫,一者沉郁厚道。然而,他们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这是二者能够成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的知交的基础,也是二者成为诗坛双子星座的重要原因。
就人生追求而言,李、杜同样志存高远,胸襟博大。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崇高理想,为世人熟知。李白则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为了实现报效国家的理想,他“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别匡山》)。从中可见李、杜二人志同道合。
尤其可贵的是,李、杜二人虽历经坎坷,却壮心不已,针砭时弊,同情人民,不改初心,九死未悔。杜甫自称“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从居于长安的《兵车行》《丽人行》和“三吏”“三别”到迁居巴蜀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直至辗转湖湘的绝笔诗“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他真正是“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
李白在赐金放归之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强烈抨击愚贤不分、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五》),“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四》),“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写出了盛世中隐藏的危机,也写出了底层百姓的辛酸—“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真实揭露叛军的残暴—“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他积极投身平定叛乱,在蒙冤下狱流放归途中,听闻李光弼招兵消息,不顾老病之身,毅然前往参军,因病半道而还,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诗,其伤时忧国、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杜甫高度一致。
与此同时,我们从李白《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诗中可以感受到他同杜甫一样重情重义的至诚,从《将进酒》等诗多种手稿版本中可以看到天才诗人李白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之杜甫相近的炼字功夫,以及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此外,从李白与杜甫同样的平等和睦、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观念中,我们可看出这位谪仙与人间烟火的现实关联,以及其仙道外表下积极入世的态度,所谓“并庄、屈以为一心”。
反之,李白性格的狂放不羁和诗风的浪漫飘逸,在杜甫诗作中同样不乏其例。与李白相似,杜甫大胆追求自由和个性,虽然他常常口称“腐儒”,实则无丝毫的懦弱胆怯或拘守礼法。史书每每称其“性褊躁,无器度”“旷放不自检”。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云:“太白旷而肆,少陵旷而简。”杜甫《赠李白》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诗作是写李白还是自述难以分辨。《壮游》所写则是自画像无疑,诗云“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今夕行》(自齐赵西归至咸阳作)诗云:“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飞鹰骑射,痛饮狂歌,博塞呼卢,何其快哉!其与李白何其相似,哪有半点腐儒的样子。
以饮酒为例。人们称李白为酒仙,这与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的诗句有关,而杜甫嗜酒程度及其所作酒诗比例毫不亚于李白。从其诗“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寄薛三郎中据》),“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逼仄行,赠毕曜》),“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中,其嗜酒之态可见一斑,知其确实不为礼法所拘,雄放豪气不减太白。
此外,李、杜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共同特点,便是与巴蜀文化的特殊关系。魏颢《李翰林集序》以李白为“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的代表,杜甫则是“天下名人例入蜀”的杰出代表,二人先后将巴蜀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中华地域文化良性互动的典范。
古典文学研究家缪钺先生曾指出:“杜甫一生中,有时不免要与官僚们敷衍应酬,所以他诗集中也偶尔有一些庸俗浅薄的作品,但是这一点白璧微瑕,无损于他整个诗歌的光芒万丈。”李白也是如此。李、杜在怀才不遇、愤激不平之时,难免产生彷徨退隐、避世独善之念,“非无江海志,潇洒度日月”,但最终还是儒家入世思想占据上风,佛、老观念退居幕后,“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种矛盾中抉择的心路历程更显出其与常人情感相通、共鸣可亲。二人历经苦难,依旧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天人合一,吸取道家之营养,却未遁隐入道。
李白、杜甫广泛吸收包括儒、释、道传统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化基因,乃至域外文化等丰富的人类文明营养,并将其融会贯通,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之典型代表。李、杜诗作沾丐后人,跨越时空,得万世景仰,成为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也是现代社会建设精神家园不可缺少的食粮。李、杜双子星座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的夜空,带给人们光明、自由、温暖和理想,启迪人们追求公平与正义、良知与希望,向着诗和远方!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