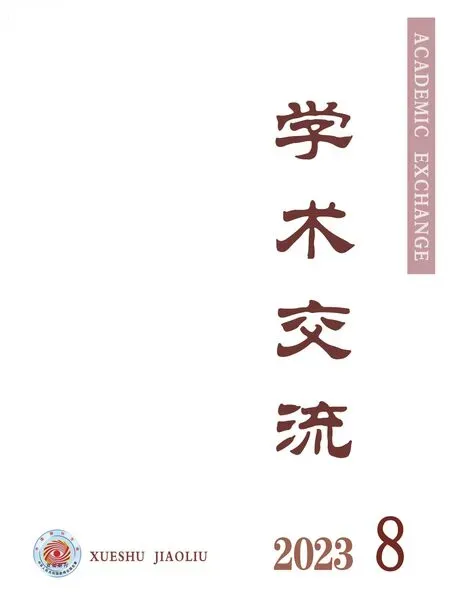“我们”何以要向左转
——威廉斯的“我思”与其“内在的语境主义”
2023-11-09陈德中
陈德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尽管“我们”是一个“棘手的词汇”(a slippery word)[1]186,威廉斯仍然花了相当的精力来处理之。原因在于,威廉斯要想对作为“生活形式”的文化、伦理与政治等人类实践有所反思,就不得不面对人们经常使用的“我们”这一概念。(1)威廉斯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讨论了主格的“我们(We)”,宾格的“我们(us)”,以及所有格的“我们的(Our)”。
本文提出,威廉斯对于“我们”概念的思考,植根于他对于笛卡尔的“我思”结构及其特征的分析。威廉斯提出“我们”乃是“我思”中的主语之“我”的复数形式,它在“我思”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而谓语“思维”本身则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批判性反思”使得作为生活方式的“我们”具有了一种自我改进的内在动力。这一思考路径促使威廉斯将晚期维特根斯坦左翼化,并进一步促使其借鉴社会批判理论(提出用“批判理论检测原则”反思我们的实践),主张“反思与启蒙的理智不可逆”。本文认为,威廉斯的上述左转倾向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也与其自身的其他哲学考量之间存在着矛盾与抵牾。
一、“我思”结构与两类“我们”
威廉斯对于“我们”这一概念的思考源于其1970年代。我们可以在其1973年的《维特根斯坦与观念论》演讲(1974年以论文形式发表)与1978年的《笛卡尔:纯粹探究计划》中觅及其踪迹。在这两篇文献中,威廉斯提出“我们(We)”乃是“我(I)”的多元复数形式。讨论“我们”,涉及从第一人称单数到第一人称复数即“从我到我们的过渡”(“I → We”)。[2]364这种过渡是“我们”这一概念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概念确实性的必要条件。在其后一部文献中,威廉斯重申了上述过渡,并且还特别强调: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具有第一人称单数的“我”所不具有的独特特征。
在(同一时期)《论科林伍德》(生前未发表)的文章中,威廉斯首次提出了两类“我们”的区分:“‘我们’可以在一种全包性的意义上(inclusive sense)(2)本文把“inclusive”译作“全包性”的,旨在强调其所修饰的“We”的单一性(single and unitary)。[3]65使用,指的是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条件;也可以在一种对比的意义上(contrastive sense)使用,在此意义上,此时此地的‘我们’不同于其他时间其他地方的他者,后者生活在其他不同的可理知的人类结构之中。”[2]358可以看出,威廉斯对于从“我”到“我们”的过渡的讨论,与他对于“我们”的两类含义的使用的划分的思考是关联在一起进行的。
威廉斯在其(完成于1990年代早期)对内格尔《定论》的书评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可以区分作为“对比性的”“局地的”(local and parochial)我们(us)”,和作为全包性的普遍的我们。前者多用于讨论伦理、文化共同体,后者则通常指“正在或可能共同探究这个世界的任何人”。或者说,后者是“科学与逻辑的我们”。[4]372-373在其1999年鲁汶讨论班文献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威廉斯对于“全包性的我们”(inclusive We)与“对比性的我们”(contrastive We)的这种对照使用。[5]26
在威廉斯这里,“全包性的我们”是一个“单一”的普遍性(认识)视角。与“全包性的我们”对应的是“绝对知识”,“绝对知识”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局地视角或追问癖好来表征世界”的知识。[1]184-185而“对比性的我们”则是一个“局地性”的“我们-他者”的对比性概念。与“对比性的我们”相对应的知识是局地性的、视角化的。前者具有先验观念论取向,而后者具有经验观念论取向。
威廉斯作出这种区分,其落脚重点在于“对比性的(局地的)我们”。他欲借助这种区分,探讨经验性的伦理知识与道德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威廉斯区分两类“我们”,这是其20世纪70年代的思考重点。这一思考关联于他对于晚期维特根斯坦“我们”概念的两种可能理解的解读:“我们”可作先验理解,这种理解对应于“全包性的我们”;“我们”也可作经验理解,这种理解对应于“对比性”的我们。而在其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论文《多元主义、共同体与左翼维特根斯坦主义》为代表,威廉斯的思考重点转向了处理“对比性的我们”的“内在的语境主义”,也即转向了对于我们的实践或生活形式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的思考。这种“主张在其2002年的《真理与真诚》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确认与阐发。威廉斯晚期思想强调经验意义上的“对比性的我们”具有一种敏感于语境的“批判性”与“反思性”。“批判性”与“反思性”同样是“我们”的概念的内在特征,或者说是固有特征。这些特征因而就是“我思”中的“思”之基本特性。
有意思的是,威廉斯将笛卡尔的“我思”拆分为两个部分来分别加以处理。第一部分涉及“我思”中的思之主体即“我”。在笛卡尔那里,单数的“我”作为“第一人称结构”而存在,威廉斯则进一步将其展开为复数的“我们”的概念,从而强调了第一人称结构的复数性特征。第二部分涉及“我思”中的思之活动即“思”。威廉斯提出,思之本身具有对于自我思想活动的“意识”“反思”与“批判”。威廉斯暗中假设,两个部分的特征分别以及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将让我们完整把握现代性展开以后的人类思想特征。而且,正是“我思”结构中的“思”之特征,赋予了“对比性的我们”以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威廉斯的思想呈现为对于笛卡尔“我思”结构的展开。
在《笛卡尔:纯粹探究计划》一书中,“反思”一词并没有被威廉斯作为专业术语来使用。反思只是在作为哲学活动的一般特征时,被威廉斯未加限定地引入使用。不过,作为名词的“反思”(reflection)在该书中出现了六十次之多。而在进一步论及“我们对于知识的信念”这样的专业问题的时候,威廉斯还有意识地引入了“批判性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这样的表述。威廉斯声称:“批判性反思不仅针对信念的内容,而且针对一个人获得这种信念的方法。首次地,问题因而不再是‘事情是怎样的’?而是‘在那件事情中,我能知道什么?’和第一类问题不同,第二类的问题涉及某个人自己。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反思,并不只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某人关于世界的经验的反思。(笛卡尔的)纯粹探究似乎一开始就暗含了某种第一人称形式(或结构)。它是暗含的,它只是作为一种反思的和自我批判的事业。”[6]53
这段表述,典型地体现出从“思”向着思之主体的追溯,体现了威廉斯对于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主体哲学的阐释解读。作为“我思”主体的“第一人称结构”以及对应的“思”之活动在这里同时并存。威廉斯醒目地将思维与我们对于知识的信念联系起来。在我们对于知识的信念中,笛卡尔的“我思”中的“思”之特征被威廉斯特别地阐发为“批判性”与“反思性”。(3)我们说这是威廉斯的“特别的阐发”,是因为“思”与“反思”之间毕竟存在着张力。威廉斯则认为“反思”为“思”提供了辩护。
接续上述论述,威廉斯进一步强化了对于“我思”结构中的反思性作用的认识:“我们不仅假定任何存在的知识都是某种反思性的个人知识,我们同样还假定,如果一个人知道P,那么他就同样应该能够在反思中复原该知识,并能够断定,可辩护地断定,‘我知道那是P’。”[6]54反思是对于我思之思,是我们对于意识内容的思考。反思确证信念,从而使得信念指向的知识内容得以可能。“‘我思’这一陈述本身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彻底的反思其所包含的内容表明,经由反思本身,满足了其为真的条件,从而相信其为真。”[6]171反思可以提供这种辩护。[6]174
正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作为主体的“我(I)”与“我们(We)”的关系问题,也即,将第一人称结构作出复数解读的问题。在笛卡儿那里,认识的主体必是单数的“我”。“我思(Cogito)特别地与思有关,并且特别地与第一人称有关。”[6]76威廉斯则特别强调,我们要引入复数的“我们”。在寻求“绝对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属于“我们的”“集体的表征”。[6]54在这里,集体知识或信念不能够最终还原为个体的知识或信念,它也不是个体知识或信念的相加之和。而这也就证明,理解集体的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确有必要。
威廉斯对于“我思”结构作出哲学分析并不独特,而强调第一人称结构的复数性即“从我到我们的过渡”(“I → We”),则体现了威廉斯的独特关注。他在其上述两个文献中均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威廉斯对于复数之“我们”的强调,意图是要为“全包性的我们”概念作出辩护,从而凸显认识意义上的主体的“全包性”特征。为此,威廉斯刻意要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作为生活形式的“我们”解释为先验观念论。只有作此解释理解,“我们”才可以是全包性的,才可以作为认识世界的行动者。
本文特别提醒读者威廉斯对于笛卡尔的“我思”结构在两个方向上的解释。因为,第一人称结构的存在,以及从单数之我到复数之我们的过渡,蕴含了威廉斯对于现代道德生活的主体性地位的强调。现代世俗化世界的道德生活必是“基于我(或我们)”之思,而不是像“超级传统社会”那样主体隐身缺位,伦理体系作为稳固基础,我们基于“去主体的”沉思来认识这种伦理体系。与此同时,“我思”结构中的“思维”之“批判性”与“反思性”,将最终促使威廉斯诉诸内在的反思批判,来为道德与政治的规范性寻找内在动力。
二、对于“我们”的“先验理解”与“经验理解”
维特根斯坦经历了从《逻辑哲学论》时期的“我(I)”到晚期的“我们(We)”的转变。其早期持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逻辑图式的“唯我论”主张,晚期则持有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我们”的主张。威廉斯典型地接受了晚期维特根斯坦的主张,认为一种“生活形式”对应着一种“我们”的观念。学界通常认为,强调“生活形式的”晚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先验观念论。而威廉斯则尝试证明,晚期维特根斯坦并未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毫不含糊地抛弃了先验观念论。我们可以对于作为生活形式的“我们”作出两个方向上的理解,一个就是作为“全包性的我们”的先验理解,另外一种就是作为“对比性的我们”的经验理解。
威廉斯强调,维特根斯坦晚期立场具有先验观念论特征。说它是观念论的,就在于维特根斯坦不认为有不受我们看待事物视角影响的独立实在。说它是先验的,是因为“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不是某种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得到解释或定位的东西。
威廉斯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观念论是基于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性质的看法,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我们”不过是其早期“我(I)”的多元后裔(派生物),晚期维特根斯坦思想表达了这样一个基于复数的我们的主张(WEC):“我们的语言界限就意味着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这种‘我们’根本不是世界当中的某个群体,而是从观念论的我——这个‘我’不是世界当中的某个现存者——所衍生而来的复数形式。”[2]376从早期表述到晚期表述,得到正确理解的观念论完成了从单数之“我”到复数的“我们”的过渡(“I→We”)。威廉斯主张,晚期维特根斯坦可以包容这种过渡。
这种WEC主张中所包含的语言观具有如下三要素:a.接受一种狭义的语言;b.把这种语言视为对于世界观的说明;c.人类不同的亚群体持有各种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依赖于a与b而进行说明或被说明)。[2]370
对于这种语言观,有着两种方向相反的解释的可能性。我们对于WEC既可以作先验理解,也可以作经验理解。如果我们更多考虑语言与世界的意义显示,或者说我们更多考虑语言与世界观的关系(“a←b”)(上升说明),我们的理解就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先验理解。但若我们更多考虑以特定视角看待事物的方式(“b→c”)(下降说明),这个时候依赖语言说出的事物就更多的是经验性的事实而非先验事实。
依赖上述的上升说明和下降说明的区分,我们可以分开对于WEC的先验理解与经验理解。“a←b”的理解是先验理解,“b→c”的理解则走向经验理解。威廉斯把“b→c”视为可内部理解的,而把“a←b”视为全包性的。在不同的“我们”之间,不同的世界图景是否可对比评价,这一点则是存疑的。威廉斯提出:“我们如何走下去取决于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言谈,如何有意地合群地引导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的经验。”[2]369WEC将使得我们走出“唯我论”。局地的生活形式是经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则是先验的。
不过在这里威廉斯又马上指出,维特根斯坦关注想象力,而非任何经验意义上的现实取舍。经验意义上的“我们”并不是他的首要关注。[2]376威廉斯认为,我们可以基于“b→c”来说明与我们的实践相联系的各种意义,但是,维特根斯坦所关注的是复数意义上的WEC。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先验的“我们”,也就是说,关心的是“a←b”。[2]376-377“(维特根斯坦)晚期著作也可被看作为利用其固有的复数化的观念论要素来走出自身的一种尝试,或者说起码它并不阻止那样做。”[2]377
当我们不再设定世界乃经验的世界,而是把世界看作我们所说的一切得以存在的经验条件的时候,我们的表述就有了一种“先验观念论”的形式。[2]367“从‘我’到‘我们’的转向是在先验观念论自身之中发生。”[2]364维特根斯坦的“a←b”的思考将会使得他得以“将经验观念论驱逐出去”[2]378。“这种新的意义理论,……指向一种先验观念论的方向。”[2]379
基于其对于维特根斯坦所作的观念论化解读,威廉斯引出了一个全包性的“我们”概念。他期望这样一个全包性的“我们”可以克服对比性的“我们”的局限。后者的局限在于它是一个地方性的、局部性的“我们”。而威廉斯这里追求的是一个去人格化的、非局地化的视角。威廉斯这样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在观念论的解释中,问题不在于我们是这个世界上众多他者中的一个,……而在于,对于我们来说的世界是由我们可以理解一些事物,而不是由我们可以理解他者这一事实来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对某些事物,而不是由对某些他者的理解这一事实决定的——这一理解不再有其剩余的经验的第三人称的冗余。”[2]368
事实上,威廉斯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先验观念论解释一直存在着争议。摩尔提出:“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先验观念论者,而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则不是。”[7]174M.威廉斯提出,在《维特根斯坦与观念论》一文中,“威廉斯非常矛盾地(ambivalance)接受将维特根斯坦解读为一个‘先验观念论者’。”[8]70“维特根斯坦的语境主义和我所说的他的内在学说并不构成一种先验学说。”[8]87赫托认为,“即便我们接受威廉斯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解释,也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主张任何形式的先验观念论”[9]1996。
很明显,将维特根斯坦作先验观念论解释,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对于维特根斯坦是否可以被解读为先验观念论者,就连威廉斯自己也相当犹豫和谨慎。不过,即便将晚期维特根斯坦作先验观念论解释并不成功,也不影响威廉斯对于“全包性我们”的关注。重点在于,“全包性的我们”承诺一种“绝对概念”,这种概念可以为一种可超越局地性的普遍统一的视角认识作辩护。就其“全包性的我们”这一概念的功用来看,它更多地指向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而“对比性的我们”这一概念,则更多地用来理解不同的局地群体。晚年威廉斯辩称,两种“我们”的划分不存在高下之分。但是这种辩护的理由需要依赖于他对哲学作为一种“理解”事业的界定。
两种“我们”的区分还关联于威廉斯的“想象的面对”(由此产生“距离的相对主义”)和“真实的面对”的划分。我们认为,在讨论“想象的面对”的时候,威廉斯将哲学界定为了理解事业,而在“真实的面对”的时候,威廉斯又将哲学界定为了认知事业。威廉斯用全包性的“我们”处理科学和科学哲学相关的问题,而用对比性的“我们”来处理与人文相关的问题。
三、“反思批判”促成“我们”向左转
在1998年荷兰鲁汶大学的伦理学讨论班上,围绕伦理反思与伦理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威廉斯回应说:“现在你会问,谁是我们(us)?那我会说:我们就是尽可能多的可被有意义地包含在这一反思中的人们。”[5]244问题来得骤然但却也顺理成章。谈论“我们”,与说话者谈论的“反思”概念相关,而且紧密相关。因为,反思自涉“我们”,自动设定了一个“我们”的存在。反思涉及谁、针对什么范围内的内容进行思考,反思结果在什么意义上、如何可能或不可能影响所假定的对象等问题。事关伦理,反思涉及伦理共同体,以及理性反思与经验地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威廉斯之所以将晚期维特根斯坦同样作观念论解读,目的也是为了给“我们”概念赋予特定的内涵。威廉斯理想中的“我们”需要有着一种反思批判的内在动力。一种非反思的保守的“我们”不是威廉斯的理想选项。“观念论的解释不是简单地把任何给定的‘我们’置于世界之中,然后对其作斜睨旁观。”[2]368“观念论”是实现这样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最佳哲学选项。这两个词汇合在一起构成了“批判性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观念论在哲学上能够满足并且赋予“我们”概念以反思性和批判性,从而使得“我们”概念具有内在动力,并且使得我们得以合乎逻辑地解释规范性的来源问题。
如果说,威廉斯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先验观念论解读是为“全包性的我们”服务的,那么,1992年威廉斯提出的“左翼维特根斯坦主义转向”则明显地是要为其所要处理的“局地性的我们”赋予内在动力。威廉斯认为:“没有理由表明,以维特根斯坦哲学所暗示的那种方式为特征的那种非基础主义的政治思想不能出现一种激进的转向。”“可以有一种左翼的维特根斯坦主义。”[10]37
维特根斯坦主义者通常都被认为是保守的,他们不但批评人们有关哲学的错误观念,而且批评人们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所抱有的那样一些激进抱负。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种保守解读是一种右翼维特根斯坦主义主张。在右翼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看来,哲学追问总是有其尽头的。哲学的理由追问要听命于社会和政治的实践。
右翼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显然继承了维特根斯坦哲学方法所具有的内在静态特征。(借用奎洛兹和奎尼的总结,)右翼维特根斯坦主义具有如下四个典型属性:第一,历史地看待生活形式,将其视作精准校正过的功能整体。(如我们对于植物形态的观察。)第二,假定我们的生活形式是不存在内在紧张的。第三,由于前两者,既定状态之外无变化。第四,现有的生活世界不仅无物促动,而且“合理地难以理解”。最后一点的意思是,若非事物先已发生,否则任何激进的改变都是难以理解的。[11]760-761这也正应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喜欢的那句名言:哲学就是让一切如其所是。
维特根斯坦的“我们”是对于生活形式进行观看的约定的“观看者”,他们(这些“我们”)观看的是可辨识的事物的形态和结构。在“看而非想”的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这里的“我们”乃是包容的和无界的,是一种“一视同仁的接受”。而现在,威廉斯希望谈论的是“形成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实践”。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是一种对照性的。这是“相对于‘他者的’‘我们的’”,“我们”隐含了与他者的对照。[11]761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出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备选的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的对照,奎洛兹和奎尼声称,因而“它促成了这样一个意识,也即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历史地生成的,缺少回应这样一种历史效应的理论注定是一种没有内在紧张性的体系”[11]762。很显然,这样一种有历史的“我们的”生活形式,探讨的不是维特根斯坦右翼所讨论到的同质的、融贯的结构,而是异质的,充满了内在和外在概念紧张性的实践。这是一种“承载了紧张”的实践。
左翼维特根斯坦主义不预设一种基础主义,但在面对概念变化时仍对我们的生活形式抱有合理信心。[11]762传统哲学设定,哲学就是回答无时间性的问题。左翼维特根斯坦主义则在此转向回答关联于时间性的局地问题。“承载了紧张”(内外之别的紧张)和“基于特定观点(point-based)的解释”(对于概念实践的局地解释),这是左翼维特根斯坦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11]764对于右翼维特根斯坦主义的前述四个假设,左翼维特根斯坦主义也都作了翻转性的解释。“它要求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实践看作可靠的功能总体,而要看作基于多样竞争需求的、历史地生长而形成的混杂结构。相应地,其本身充满着各种紧张。这又反过来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概念实践看作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实践,需要内生性地理解这一变化,这种变化起码部分地是理由驱动的,并非简单的因果事实。”[11]764-765
如果说右翼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我们”是出于工作方便而作出的一种“至大无外”的一视同仁的假设的话,那么左翼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我们”就是一个紧贴着事物的实际存在而不得不作出的内外分别。左翼思想锚定于伦理和政治实践等“生活形式”,我们乃是这些实践中的我们。这与右翼更加“科学地”、中立地“看”的哲学在对象上就已经有别。相对于右翼的“至大无外”以及既包括人类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也包括独立于人类的自然和逻辑实践,左翼的眼光是“我们的生活”与“他者的生活”之别。不出所料,这个时候的我们是在所讨论的“生活形式”之中的。如果说自然和逻辑实践需要我们对于知识的起码信心的话,那么生活实践就进而需要一种“合理的信心”,它需要一些基础,使得我们可以据以进行“反思性区分(分辨)”,“分辨何种概念实践值得支持,何种概念实践应被拒斥。”[11]765由于这种分辨是内部的,并且描述者和研究者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同时随着生活形式的历史生长而存在的,因此这种“基于特定观点的解释”就既应是内生的,也必然是反思的。这也就是说,左翼立场必需一个反思的维度。奎洛兹和奎尼因而提醒说,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从何处起(思考重心)折返向了反思之铲?”[11]765
威廉斯直接地将文化、伦理和政治的“我们”特别地从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的一般性的“我们”那里划出。这种(因区别于“他者”而)承载了紧张的局地的“我们”当然有其特别意义。但是相较于右翼维特根斯坦主义,左翼的进路更像是一种“别子为宗”。威廉斯的意图在于对于我们的文化、伦理与政治生活形式的反思批判。他假设了批判性是反思性的一个特征,其中背后又优先假设了反思性乃是上述生活形式的一般特征,甚至是其内在特征。所以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反思性以及相应的批判性上。“批判性反思”才是威廉斯所真正希望确证的方法论命题。威廉斯意图让“我思”在特定语境之中“内在地”有所作为。只有到了这一步,威廉斯才认为我们找到了对于局地文化的合理理解。
很明显,威廉斯所提出的理解“生活形式”与维特根斯坦从形态学角度看待“生活形式”时的角度已经大为不同。维特根斯坦只是观察不同“生活形式”之形,或者说观察不同的“生活形式”中的人们如何以不同的形式遵守规则。威廉斯则对于同一“生活形式”再次反观,向一种“生活形式”本身二次注入了实质性的“观念论”理解。对于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是自外而观之,威廉斯则是自内而观之。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不要想,而要看”,威廉斯却二次回返,提醒我们“不仅要看,而且还要想”。
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形式”,到底是“不要想,而要看”,还是“既要看,又要想(反思)”?观看和反思,二者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理智活动。威廉斯想要表明,对于维特根斯坦思想所作出的静态化倾向的右翼理解,就其作为对于“生活形式”的研究而言,不太符合被研究对象的规律。“生活形式”作为观念实践的总体,终归是人的观念。人在其中有其位置。我们可以将“生活形式”作维特根斯坦的形态学的形式观察,但是这完全不影响我们对于“生活形式”本身作出观念性的理解。既然个人内在于“生活形式”,我们就可以对于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形式”加入一种反思力量。
维特根斯坦晚年提出“不要想,而要看”的哲学主张,引导着我们贴着事物客观形成的类型形态,来审视各种可能的类型呈现。就其对于客观世界的贴合方面来说,它注定是静态的,保守的。维特根斯坦既不排除,也不鼓励对“生活形式”作出更多解释。[2]371这是维特根斯坦关于该问题的基本态度。威廉斯的关注点则在于:“因而随着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变化,多样性改变是可能的。随着这种可能,可假定我们可以对这些多样性改变可以拥有不同解释。看待世界的别样方式在我们的在想象中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维特根斯坦的意图之一就是鼓励这种想象。”[2]372
在这里,我们确实可以沿着威廉斯的暗示进一步推论说,随着人们的“旨趣与关注点的不同”,可获得不同的世界图景。[2]372但这样一种推论性表述已经开始出现视角的内在化挪移。威廉斯援引维特根斯坦的“格式塔说明”来进一步强化上述主张:“我们不关心不同世界观的认识论,也不关心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以及探讨世界观的方式。我们关心想象,……以及借助于想象,让不同的实践成为对于我们来说更为熟悉的观念,从而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实践。”[2]375-376
毕竟,维特根斯坦的“看”的视角仍然是外在的,观察的。而威廉斯的“看”开始加入解释,加入“反思性”审查,加入了对于我们的观念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加入“批判性反思”意义上的“想”。“看”与“想”的结合指向一种虚拟的“我们”。“被想象到的各种可能不再是给予我们的可能,而是为了我们的可能,成为不管我们能够走多远,我们仍然留在其中的我们的世界的标志。”[2]376到此为止,威廉斯已经完成了对于维特根斯坦的一种内在主义的解读。而这样一种内在主义解读的动力在于:主体具有以自我意识为代表的反思性评价能力,此即“批判性反思”。科学意义上的不同世界观总体和我们对于它们的观察,消融于一个共同的“我们”的视野。在这里,不再有相对主义。[2]374-375
四、“内在的语境主义”的内在困难
沿着对于“我思”结构的分析路径,威廉斯对于“我们”这一概念的讨论线索已然呈现:第一,笛卡尔式的“我思”结构及其特征。第二,“我思”结构中的“我”需要一个从第一人称单数到第一人称复数的过渡(“I → We”),此即第一人称结构的复数性。第三,“我们”被区分为“包容性的”与“对比性的”。第四,“我思”结构中的“思”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两个特征。第五,在知识的意义上,伦理知识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在反思的意义上,伦理知识的相对客观性有可能丧失殆尽。“反思摧毁(伦理)知识。”第六,“我思”结构中的“思”所具有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可将维特根斯坦作为“生活形式”的“我们”左翼化。第七,基于“反思性”与“批判性”的“反思检测原则”,可为我们赋予规范性动力。我们的“实践不只是实践之实践,同样也是批判之实践”,是为“内在的语境主义”。[10]35-36
这种路径的首要特征是关注“反思”。威廉斯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开篇就提出,苏格拉底问题,即“(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或者“我该怎样生活”的问题“是个反思性问题”,“良好生活之为良好必须包含反思”,“未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一过”。[12]27-29威廉斯认为,在非反思(前反思)的意义上的超级传统社会中伦理知识或许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这种客观性依然不同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在苏格拉底问题层面,反思的介入将摧毁知识。[12]182-187真正彻底摧毁理论知识客观性的,乃是反思的介入。
对于“对比性的我们”,即地方性的我们,威廉斯的处理进路,就是本文第三部分所分析的内在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依赖于“批判理论检测(CPT)”。威廉斯认为其“批判理论检测”就是一种“批判性反思”,它与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最大相同点,是它将对权力的觉知引入反思,其判断高度依赖于权力,其反思考虑到了权力结构的存在。[13]291威廉斯称这种反思是一种“内在的”“语境主义”。[13]286
就其对于权力结构的觉知与自觉地将权力结构作为反思的限定背景而言,威廉斯的“批判性反思”与柏拉图、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拉开了距离。柏拉图的思想是一种外在的理念论,寻求的是对于道德生活的超越支撑。康德的思想虽然是内在的,但却是一种还原主义或基础主义的理性主义。二者的共同点是无时间性、无历史感。威廉斯提出,对于我们的生活形式的反思应该是内在的,并且应该是历史性地敏感于每个时代的“我们”所处的建制结构。如前所述,这是一种承载了紧张的有历史的我们。我们因而不再需要外在论,也不再需要依赖理性主义式的内在论。
威廉斯进一步提出,在现代社会中“反思无处不在”。在《真理与真诚》的最后一章,威廉斯在两个地方反复表达了其“启蒙的理智不可逆”主张。[13]320;333实际上,早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中,威廉斯将反思程度的增强与现代生活的展开视为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在那里,威廉斯提出,“近代(现代)世界的标志正是反思程度奇高。”“比起以往任何时候,现代社会更深广地渴求对社会及人类活动的反思性理解。”[12]196“无路可从反思折返。……这一自我意识现象,连同支持它的建制和进程,都部分地说明了以往的生活形式对于今人不是现实的选择。”[12]196至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威廉斯理解的启蒙与“批判性反思”联系到一起。不但如此,启蒙以来的“批判性反思”是在理智上不可逆的。
威廉斯把“我思”结构中的主体反思等特征加以放大,并且将其作一般化理解,提出“我们”乃是“我”的复数形式,反思及反思批判乃是“我思”结构的核心。威廉斯用这些思想来解释和理解现代伦理观念与政治观念。而威廉斯依赖的这种“批判性反思”资源,因其对于以反思为其核心特征的启蒙持有一种不可逆的过强立场,恰好构成了托马斯所说的“超级反思立场”。[3]58这种立场与他所提出的“超级传统社会”构成明显对照。威廉斯用上述立场来将维特根斯坦作左翼理解,并将黑格尔的观念论作一般化理解,最终得出实践不只是实践之实践,同样也是批判之实践,将批判当成介入实践的一支独立力量,并进一步认为此乃现代性的基本特征。[10]36
威廉斯对于“我们”所作的左翼理解,或者说其最终持有的“内在的语境主义”有其固有的理论困难。本文第三节我们展示了维特根斯坦立场与威廉斯的解释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威廉斯的向左转并非必然,而只是诸多理论可能性之一。本文所勾勒的威廉斯思想线索,还与威廉斯自己的其它一些理论努力之间构成张力。这些张力同样体现了理论的不同可能性之间的相互竞争。
首先,威廉斯的理论面临着“超级传统社会”与“超级反思立场”之间存在着张力。威廉斯一方面承认传统社会意义上的伦理客观知识乃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却又假设现代社会反思无处不在。在反思的摧枯拉朽的批判能力面前,现代道德哲学不再可能获得完全客观的道德知识。很显然,非反思的传统社会与反思的现代人之间存在着张力。我们质疑威廉斯的“反思无处不在”立场,就是质疑现代人全都整齐划一地进入饱满的反思状态这样一种假设。我们认为,现代人可能是超级反思的,而现代社会也会容纳并不进入反思状态的人对于部分传统的接受。因此,“超级传统社会”与“超级反思立场”,反思与非反思的张力,客观的伦理知识与充满内在批判精神的主观的反思活动的张力,乃是威廉斯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两难问题。威廉斯雄辩地宣称的“反思无处不在”如果成立且无可置疑,面对现实复杂性而感到“不安”的就会是他的理论的阅读者与倾听者。
其次,威廉斯对于“比较性的我们”的概念使用与其欲倡导的古典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理论旨趣上的巨大差异。威廉斯区分两类我们,重点是要说明一种“比较性的我们”在“比较的”意义上有何特征。但其其内在的语境主义却掉头向内,转而讨论一个“我们”全都生活于其中的“生活形式”。这已经近乎一种广义的“全包性的我们”。这种向内转的全包讨论自有其意义,但是它却留下了全然“对比的”意义上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后面这一个问题涉及我们对于威廉斯所宣扬的当代政治现实主义与其所宗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差异。古典现实主义典型地是在思考“对比的”意义上的不同的“我们”的关系问题,那样一种思考典型地坚持了如下三个原则:真理与正义问题上的相对主义;人性及其历史发展问题上的悲观主义;在理解政治互动中的“权力的优先性”主张。这也就是说,经典的政治现实主义认为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是“我们”与“你们”之间永恒的竞争关系,互相之间无法在认知意义上可理解。
而威廉斯的内在的语境主义如果成立,内在的批判反思即威廉斯所提到的“理性的力量”就会与权力的力量竞争优先性地位。这种力量同样也会改变我们对于道德和伦理的信心,把一个无需区分缘由的“盲目的”信心改造成为“合理的信心”,从而改变我们对于真理与正义的相对主义主张。“合理的信心”则又进一步赋予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形式”的积极态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对于人性和历史的悲观主义。古典的政治现实主义考虑的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威廉斯的现有立场却已经事实上将“他们”这个维度排除在外。威廉斯在此路径选择过程中已经避开或者转移了古典现实主义的初始话题。
第三,晚年威廉斯援引尼采的谱系学,尝试带来对于道德与政治思考的新解释。这些新解释意图超越当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刚性主张,比如对于正当性概念的截然二分的理解,对于正义问题的超越时间性的逻辑化理解等等。威廉斯对于“我思”结构的信念与他对援引谱系学欲图达到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张力。威廉斯意欲引入敏感于制度环境的语境主义,也即引入有着时间敏感性的历史概念,用一种有历史的哲学替代无时间意识的概念逻辑理解。但是他的“反思无处不在”以及“启蒙的理智不可逆”主张则更像是一把双刃剑,该主张一方面引出敏感性和历史性,另一方面却又诉诸诉诸理智反思的理性力量。对于二者之间的这种明显张力,威廉斯及其追随者仍然缺乏充分合理的解释。这不能不危及他对于谱系学方法的援引与使用,甚至会逼使他改变自己对于谱系学功用的理解。
第四,威廉斯较多援引黑格尔,以此来批判康德式的道德哲学。但是威廉斯对于黑格尔的思想的援引将会强化“我思”结构中的“反思批判”特征,其极端使用将会使得威廉斯自己的思考绝对观念论化。同样,威廉斯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内含保守倾向)的共同体主义有着同情,但是目前的左转倾向并不有利于对于这种同情理解做出完善性对接。而且,晚年威廉斯具有很强的批判理论的倾向,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甚至提出他的分析与社会批判理论共享基本框架。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很好地澄清他的思想与社会批判理论的距离。凡此种种,均关联于威廉斯思考“我们”问题时向左转的倾向。囿于篇幅,这些问题只好另作处理。
威廉斯阅读者的一个困惑就是,与众多的当代自由主义者相比,威廉斯思想清晰地表现出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姿态,处处展现出其对哲学主张的别样探索。威廉斯乃是一个“基于多元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威廉斯的落脚点依然是自由主义,不过他确实倒溯性地引入了现实主义、多元主义、谱系学(有历史的哲学)等等主张。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学理逻辑上,威廉斯最终仍会宣称自己“留在启蒙阵营之内”,他至多是一个“狐疑的”启蒙之子。威廉斯所为,乃是撑开一种有质感的“启蒙-自由主义”。其间的婉曲,乃至由此带来的各种真实的“两难”与“不安”,则需要我们细心地加以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