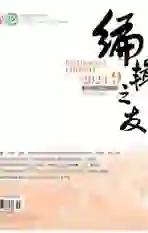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媒介化治理:关键概念与应用场景
2023-11-03许可黄楚新
许可 黄楚新


【摘要】在媒介化理论与治理理论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媒介化社会的双重现实背景,使得“媒介化治理”成为媒介化研究与治理研究跨学科融合的新突破口。但在理解过程中,首先需要界定媒治、媒介治理与媒介化治理的区别,媒治不成立、媒介治理的混淆性转向媒介化治理的可行性。在关键概念辨析的基础上,更需要对“媒介化治理”进行在地化的现实观照,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要求媒体的多元参与,当前政治层面的“国家—社会”沟通、风险社会中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城乡发展与基层治理都成为媒介化治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应用场景。
【关键词】媒介化治理 媒介治理 政治媒介化 国家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9-035-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9.005
媒介化不断推进媒介与其他社会要素相互建构,媒介逐渐从技术要素拓展为制度结构,深度嵌入社会发展,特别是媒介化与整个融合传播生态转型对社会转型、国家治理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针对国家治理体系提出社会协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媒体正是社会协同的重要主体之一。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媒介系统,以自身发展推进社会完善与国家发展,逐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媒介与治理的结合也正是媒介化的发展逻辑不断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的过程。媒介化发端于媒介与政治、媒介与治理的互动关系,媒介与治理的契合使得媒介化治理具有了中国语境的解释框架,展现出可供研究的独特内涵和本土价值。对于媒介化治理的把握,应始终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同时结合具体的媒介实践。
一、关键概念区分:媒治的不成立与媒介治理的不明确
从媒介与治理的关系视角看,媒介化治理涉及不同的概念要素,包括媒治、媒介治理、治理媒介等关键概念,理解媒介化治理需要先从社会发展中理解政治系统与媒介系统的相互关系,并充分界定与厘清这几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
1. 对媒治概念的质疑与探讨
媒治更多被社会理解为媒体治理,在学术指向上与法治、人治等相对存在。媒治概念的研究争议源自社会事件中媒体的舆论监督发展和业界、学界的观点探讨。2010年4月13日,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提出媒治概念,[1]其重点针对的是社会问题被媒体曝光后相关部门重视并解决的过程。白岩松将媒治界定為处在人治与法治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人治的传统社会向法治的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并认为媒体作为社会公权力,对社会负面问题的揭露、报道和批判会直接推进相关部门就问题形成解决方案,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他同时也提到这种治理存在的问题,即媒体发现并报道,社会问题才得以解决;媒体没有报道,问题不被发现就难以解决。从他的观点中不难看到,其将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界定为治理主体或治理手段。
学界由此对媒治这一概念及其引发的理论思考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回应,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对这一概念质疑,从法学、新闻传播学等角度论证其不成立。第一,对媒治明确批判,将媒治与法治、人治对比,并指出媒治的弊端。从法理层面而言,媒治与法治不同,媒治在中国是发挥中国特色权力监督的媒介形态,如果将媒体纳入法律体系会带来媒体牟利特权,造成新闻报道不客观,甚至形成多数人的“暴虐”。[2]评论员曹林直言,媒治其实是个伪命题,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治。[3]媒治现象的实质乃是人治传统的历史延伸,[4]其弊端在于阻碍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正确发挥。第二,从传媒的本体性出发,围绕传媒角色、基本职能等,论证媒治不成立。陈力丹明确提出媒治理念不成立,认为媒治是对传媒职能认识的误解,[5]其功能发挥有赖于传媒监测社会、信息报道的基本职能。如果将媒治看作一种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会造成媒介审判等负面影响,其实质是传媒的越权、对法治的否定。[6]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更加多元,如何发挥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第三,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视角进行概念调适。在管理向治理的转型中,有学者提出媒治是法治、民治的替代品,具有体制自我完善的临时性特征,暴露了治理模式缺陷与自身的先天不足。[7]
立足于我国的传媒发展实际,对媒治的讨论实则涉及传媒体制与权力结构。从我国的传媒体制看,中国的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政策、方针的宣传外虽然具有舆论监督的智能,但在社会发展中更多发挥信息传播系统的结构性作用。媒介创新的意义在于以信息系统的完善助力社会治理的创新,而非越俎代庖式成为社会问题治理的前置方和主体。总体而言,针对媒治的概念,从业界提出到学界探讨,再到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即媒治概念不成立,这一阶段只是针对媒治概念本身及其相关性进行驳斥与反思,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媒介治理、媒介化治理概念不能等同,媒治概念的不成立在于其当时的研究阶段处在治理理论引介的早期,并未意识到治理理论对传媒系统、传媒实践的影响和渗透,只是本土意义上对舆论监督、传媒功能拓展的越位或错位思考,本质上在于其并未深入探讨媒介与治理的互动关系。
2. 媒介治理研究的两种取向导致概念不明确
媒介与治理相结合的概念源自欧美,媒介治理横跨北美传播理论与西欧媒介公共政策治理。[8]目前,国内外学界引用较多且普遍认可的媒介治理概念,最早来自2002年爱尔兰学者肖恩和布鲁斯·吉拉德的著作《全球媒介治理引论》中对媒介治理三个层面的论断,即媒介对公民社会的自治与完善、对国家(政府)的监管与共治、对超国家机构的跨文化治理。[9]2006年,社会治理理论学者丹尼尔·考夫曼在其著作中从社会分化及社会网络复杂性的现实危机出发,将媒介看作社会的中介系统,是一种核心的协调力量,促进社会由权威控制转向多元治理。[10]以上是学者从宏观的整体视角关注复杂而存在危机的社会,将媒介作为社会子系统,是对媒介本身主体性的认可,但媒介治理并未离开媒介与政治关系的整体框架。
国内媒介治理研究经历了从概念引介到指导实践再到媒介治理本土化的历史演进过程,[11]不断强化传媒作为社会多元主体的功能或作用。伴随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形成,媒体在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出现以善治导向的“媒介善治”概念,即在政治导向与传媒实践的基础上生成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关注信息、媒介与外部社会系统的互动与影响,以实现“媒介善治”的目标。[8]但从媒介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来看,媒介治理还有一种传统的概念指向和研究路径不能忽视,可称为治理媒介或传媒治理。这一概念将媒介、媒体作为治理对象,简言之,即国家、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行业政策(伦理规范)等对媒体的管制、监管与治理,主要聚焦到传媒组织结构治理、媒体负面效应治理及当下网络空间治理等多个方面。由此,目前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是治理媒介,即将媒介作为治理对象,可称为媒介内部的结构性治理;二是媒介治理,即媒介作为治理工具或治理主体,可称为媒介外部的参与式治理。
质言之,治理媒介与媒介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媒体的客体性或主体性,即媒介本身是治理对象还是治理主体。同时,有学者从二者关系的视角提出“治理媒介是媒介治理的一部分”,[12]即媒介治理包含治理媒介,这便弥合了二者在主客体相对层面的绝对化分歧。这两种研究路径并不相悖,且并不存在从治理媒介向媒介治理的转变,而是受控与施控的一体化、专业性主体与治理性主体的一体化。[11]因为媒介治理体系处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框架内,媒介系统同样需要行业自身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而才能以传媒现代化推进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正如从治理到善治一样,媒介治理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媒介善治”,而其必要前提是作为媒介的信息系统内部诸要素规律及治理平衡,[8]进而才是政府等社会主体的多元参与。
虽然这一概念的两种取向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利用媒介治理来表述主体性视角下的媒介参与社会治理,在严格的语义表达和理论建构中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关键在于语义表达的歧义与模糊,因为媒介治理既可以理解为对媒介的治理,同样可以理解为以媒介来治理,一个词可以涵盖主客体指向的两个概念,就造成了媒介治理指向的混淆与不确定性。由此,需要寻找一种传播学与政治学、社会学融合互动、平衡且均衡的跨学科概念。当下,结合媒介化理论与社会治理实践的媒介化治理概念,正在成为媒介治理发展与完善的进阶。
二、本土研究演进:媒介化治理概念的合理化建构
与媒介治理相对,媒介化治理则基于媒介融入社会且建构和影响社会的背景,更多以传媒的公共性、主体性为出发点,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政策导向,探讨媒介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因此探讨媒介化治理需要回溯媒介化研究如何与中国的治理现状相结合。媒介化研究始于欧洲,但近年来国内逐渐形成媒介化社會研究,通过理论引介与本土调适,媒介化研究逐渐在宏观的理论框架中找到了在地化的研究领域。
1. 理论视角的转变:从政治媒介化发展到媒介化社会
关于媒介化研究,国内外普遍认可制度化传统与社会建构传统两种研究路径。[13]制度化传统以施蒂格·夏瓦为典型代表,强调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这种双重性使得媒介建构成为半自治的制度。[14](21,25)社会建构传统以尼克·库尔德利和安德烈亚斯·赫普为代表,强调媒介化是媒介逻辑介入并建构社会的过程,[15]两种研究路径的共同点在于,均将媒介化作为一种过程,即媒介影响、建构社会的过程。
在社会发展中理解媒介化,最早应用于政治领域,早期的媒介化就被用于指涉媒介对政治传播的影响,[14](13)即政治媒介化。肯特·阿斯普较早提出“政治生活的媒介化”,[16]马佐莱尼和舒尔茨也将媒介化应用到政治领域,认为“媒介化政治”指的是政治逐渐适应媒介逻辑,依靠媒介互动得以形塑。[17]兰斯·本奈特等的《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基于网络、信息等新媒介环境,认为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18]上述都强调了媒介对于政治领域强有力的影响,媒介逻辑在政治发展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在政治媒介化研究中,斯托姆贝克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媒介化四个阶段的论断,[19]认为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已不局限于媒介化层面,媒体对于政治行动者的影响已超越了媒体的信息传播层面,媒介逻辑深度介入政府治理、政策制定等政治活动,完善了政治媒介化的概念与框架(见图1)。
之所以探讨政治媒介化,不仅是因为媒介化最初聚焦政治领域,而且国内关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也较早借鉴并发展了政治媒介化理论。国内媒介化研究初期更多研究媒介化社会的概念及相关问题,孙少晶将斯托姆贝克关于政治媒介化四个阶段的框架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中国语境下媒介化社会的四个维度(见图2),[20]作为媒介化社会的理论框架,四个维度互相影响与制约。
从四个维度的描述看,从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出发,媒介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媒介逻辑成为影响媒介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使得社会各系统采纳并逐渐适应媒介化。对比斯托姆贝克和孙少晶两种研究,虽然媒介化社会四个维度只是简单将政治媒介化四阶段中的政治逻辑替换为社会逻辑,从理论层次上缺乏创新与独立性,但从在地化的内在逻辑看,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符合中国政治、媒介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基于这种媒介研究的视界融合,国内有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的分析中提出媒介政治社会学的概念,致力于探讨媒介的政治与社会基础,从媒介技术、生产、话语等维度描绘媒介与中国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互动的过程图景。[21]
2. 治理理念的影响:从政治媒介化聚集到媒介化治理
聚焦在地化层面,夏瓦认为研究中国的媒介化政治,首先需要考虑中国国内具体的政治架构和发展。[22]相对于西方视角下媒介对政治的形塑,中国语境下强调媒介对于政治的形塑这一说法并不成立,更多应该是在政治逻辑的建构下,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互动使得媒介成为政治社会发展的中介或工具。从政治媒介化到媒介化治理,体现的是我国媒体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契合,是媒介与政治关系互动的进阶与聚焦。由于媒介化对政治领域的深入渗透,媒介化对治理结构、模式及效果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媒介化研究与治理研究存在明显的相似及重叠之处。[22]从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而言,目前的政治语境已经从管理转向治理,治理也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围绕治理这个关键词,当前的治理实践与治理研究蓬勃发展,显示出中国语境的在地优势。治理研究成为热点,不仅是政策导向的渠道,也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的可行性发展模式。
与媒介化概念相似,治理也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比较丰富的概念体系,不能再将媒介化与治理两个概念简单叠加进行宽泛的解读,而要聚焦到实际治理场景中的媒介实践和治理过程,且不能把所有与媒介相关的治理实践或研究都纳入媒介化治理领域,比如治理媒介视角的媒体内部结构性治理并不是媒介化治理所聚焦的媒体介入治理过程。
从媒治的不成立到媒介治理容易造成混淆和分歧,媒介化治理將媒介化与治理有机整合,其概念内涵较为明确,简言之就是媒介融入治理过程,即经过媒介化的治理。目前国内最早提出且受到普遍认可的媒介化治理概念是潘忠党等提出的“媒体嵌入治理、二者相互依存的形成过程”。[23]这一概念的指向与逻辑比较明晰,具备明显的描述性、分析性和适用性。从这个角度看,媒介化治理作为传统媒介化研究的新突破口,也是媒介参与社会治理实践、介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回应。作为一种新兴理论或传媒实践,媒介化治理不仅需要连贯性的逻辑建构,更需要在逻辑建构的基础上与实践环节相融合,即媒介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方式,现阶段中国传媒最主要的实践,就是在社会变迁、政策变迁和媒介变迁的大背景下参与社会治理,[24]这正是媒介不断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
三、应用场景拓展:中国媒介化治理的具体面向
目前媒介化治理虽处在研究起步阶段,但在中国语境下,复杂社会结构与治理对象的多重影响表现出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包括电视问政、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城市与乡村治理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等。这些具体面向避免了将媒介化作为空洞和模糊的概念框架,而将媒介化治理作为一种过程,放置于特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中反思媒介化理论的适用性,并以媒介实践的治理创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助力。
1. 政治民主沟通中的媒介化治理
基于深度媒介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现实,媒体被认为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这与当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战略背景相呼应。深层次看,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互动并遵从政治逻辑,媒体中介的行动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标。[23]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处在政治、社会与市场转型期,当时在媒体与政治互动中盛行的是舆论监督导向的批评报道,而批判报道实质上也需要在政治逻辑的框架内得到认可,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媒介行为,媒介被看作国家(政府)权力结构运作中一种特定的“治理技术”。[25]政府行为具有较强的主导作用,政治逻辑的落脚与实施主体是政府,政府及相关部门利用媒体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行为,也被称为“媒介施政”。[26](98-99)
但随着政治改革与市场转型的成熟,“施政”这一传统概念已经不再适应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与社会语境,媒体在施政向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过程中也由单纯的行政框架内的规定动作扩展到多元的主动参与模式。转型期媒体在政府主导的框架内的主动性与自觉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以协商合作为核心的媒介参与式治理成为政府工作不可忽视的合作主体。[27]而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占据主导,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等政治话语不断驱动社会多元主体的主动意识增强。媒介参与治理的专业化优势不断凸显,媒介议程、媒介平台与媒介监督[28]等形态形塑了媒介的参与治理功能,进一步巩固了媒体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发端于舆论监督的批评报道,到媒体内容议程设置,再到当下的电视问政及网络问政,媒介化治理的主线是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互动与形塑,媒介逻辑在我国政治、社会及文化语境下卷入治理具有特定的规则,媒介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程度逐渐加深,媒介服务国家治理的功能和定位也更加凸显。
2.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媒介化治理
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数字技术变革与深度全球化等多重背景下,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多,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处置风险便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29]媒介逻辑建构的媒介系统不断嵌入发展中的社会,媒介化治理显得恰逢其时。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作为理论基础,将后现代社会的风险社会与当下中国实际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等相勾连,媒介化治理又增加了应对风险社会的应用场景。
在媒介化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双重现实下,风险应对离不开媒体行为,媒体监测功能在风险情境中得以展示和检验。[30]在监测功能的基础上,传媒的吸纳、评论和动员又构成了传媒参与社会风险治理的新型机制。[26](23-42)伴随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媒介化社会的深入,媒介化治理对传媒功能或媒介效能的需求更为多元。媒介化社会的全面到来,使媒介治理成为社会系统、媒介系统、风险系统等的有效链接。[31]
众多学者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切入,提出各有侧重的媒介化治理的概念,包括“多元治理主体中的新型治理主体”[32]“特定主体运用媒介参与社会治理”[33]“媒介作为治理对象与治理工具形塑政治、经济与社会”[34]等。诸多概念都将媒介系统作为应对风险社会、进行社会建构的重要主体,媒介化治理中媒介系统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拓展媒介的引导、动员与达成共识。在应对风险危机的同时,媒介系统不仅起到连接社会发展与风险应对的功能,更实现了媒介化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3. 社会发展空间中的媒介化治理
在众多应用场景中,作为媒介化存在与发展根基的社会,是媒介化治理的核心场景,因为治理所指向的必然是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各类社会问题。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社会治理又分为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城市的多元、开放与融合造就了城市治理的多元协同格局,数据、技术、媒介的互动融合也成为城市媒介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传播体系是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以更加开放的多元协商平台、数字治理枢纽参与智慧城市建设,[35]传媒在聚合社会资源的同时建构了边界融合的城市网络体系,而城市的媒介化治理本质上是从行动者网络体系入手将城市的融合特征与社会主体的行为选择联系起来,解释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的社会化结构影响主体人的选择行为,进而重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增长新动能的社会文化技术逻辑。[36]与此同时,在乡村场景中,乡村社会的媒介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中介,更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在地化的实践主体,立足乡村文化治理的视角,将媒介置于治理的中间,前端是文化和价值,后端是实践和操作,媒介化治理是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有机的传递和联结方式。[37]而数字公共媒介通过重构主体、强化交流、建构共识与促进交流四个环节,形成新型媒介化整合治理,以“媒介化连接”和“媒介化团结”的形式重建乡村社区,从而实现乡村善治。[38]
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县域范围,出现了一种以政策导向为重点特征的治理主体,即县级融媒体中心。自产生之日起,县级融媒体中心便以政治逻辑主导进行自上而下的媒介行动,并被纳入媒体融合的四级布局。从重大的政治意义进行分析,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谈治国理政思想落实到基层的重大举措。[39]而在政策落实与行动策略上,2018年中宣部提出“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的建设目标,进一步造就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服务与发展定位自然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层治理相契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国家治理的“托底”工程。[40]
在国家治理的宏观背景下,基层社会是重要的治理应用场景,而居其中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政治逻辑的引导下拓展媒介属性与基本功能,将信息传播系统、服务系统与治理系统融为一体,以数字化平台链接基层社会与用户,从“集成媒体的新机构”到“治国理政的新平台”,[41]这个平台起到的功能和作用已经超越了媒体建构媒体—用户的关联,以治理媒介化为旨归,进一步成为构建国家—社会的互动平台。[42]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社会媒介化治理的重要主体,具备自身发展的媒介逻辑,同时又受到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多重影响。但相比其他应用场景将治理放置在国家、社会的宏观层面,这其中的媒介化治理有了更具象化的主体落点,更加突出了媒介的主体性作用,在探討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有充分的治理场域和媒介实践。
结语
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媒体深度融合的战略背景、社会深度媒介化的基本现实,媒介化治理围绕国家治理与媒介参与这一主线,以媒介化、治理为关键词,以媒介实践深度介入治理过程,对于传媒转型发展、治理模式创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均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媒介化治理可尝试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突破传统媒介化理论的思维,由媒介的参与性与介入性转向媒介的主体性与协同性。从中国的治理思维与治理实践看,传媒现代化需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顶层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也需以传媒现代化作为现实行业应用。媒介化治理从媒介与治理的互动中拓展了媒介的功能与价值,创新了治理的模式与手段。媒介与治理的联动,或者说媒介化与治理现代化的融合,不仅是媒体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或主体在起作用,更是媒介化通过改变传媒生态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使得国家治理体系在结构、方式、过程与效果等层面均受到媒介的影响和作用。未来的媒介化治理研究,需以更加协同的思维整合跨学科理论,真正面对国家治理的各类问题,拓展更多现实应用场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宏观维度,将媒介化治理更好地与治理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等时代命题相结合。
参考文献:
[1]《新闻1+1》处理?作秀?[EB/OL].[2010-05-07].http://news.cntv.cn/program/xinwen1jia1/20100507/103785_3.shtml.
[2] 张天培.“媒治”非“法治”[J]. 青年记者,2010(27):30-31.
[3] 曹林.“媒治”其实是个伪命题[N]. 广州日报,2010-04-15(22).
[4] 向长艳.“媒治”现象的负面效应及其治理对策[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9-83.
[5] 陈力丹. 质疑“媒治”[J]. 当代传播,2010(5):92.
[6] 陈力丹,陈雷.“媒治”理念不成立[J]. 新闻记者,2011(2):18-20.
[7] 杨于泽.“媒治”是民治与法治的暂代品[N]. 中国青年报,2010-12-03(2).
[8] 郑恩,杨菁雅. 媒介治理:作为善治的传播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12(4):76-83.
[9] Siochrú Seán, Girard B., Mahan A. Global Media Governance[M].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12-20.
[10] Kaufmann D. Media,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ing Convention: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M]. Washinton The World Bank Institute, 2006: 19.
[11] 胡远珍,吴诗晨. 中国媒介治理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6):54-68.
[12] 虞鑫,兰旻. 媒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媒介角色——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政治[J]. 当代传播,2020(6):34-38.
[13] 戴宇辰. 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J]. 南京社会科学,2021(7):104-112.
[14] 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 刘君,等,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15] Couldry N, Hepp A.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Traditions, Arguments[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3(3): 191-202.
[16] Asp K. Mäktiga massmedier: Studier i politisk opinionsbildning(Powerful Mass Media:Studies in Political Opinion Formation), Stockholm: Akademilitteratur——"Medialization, Media Logic and Mediarchy" [J]. Nordicom Review, 1990(2): 47-50.
[17] Mazzoleni G, Schultz W.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J]. 1999,(3): 247-261.
[18] W.兰斯·本奈特,罗伯特·M. 恩特曼. 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M]. 董关鹏,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
[19] Strömbäck, Jesper.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8, 13(3): 228-246.
[20] 孙少晶. 媒介化社会:概念解析、理论发展和研究议题[M]//马凌,蒋蕾. 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
[21] 谢进川. 媒介政治社会学分析[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23-24.
[22] 罗昕,林蓉蓉. 制度视角下媒介化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哥本哈根大学施蒂格·夏瓦教授学术访谈录[J]. 新闻大学,2022(7):106-115.
[23] 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 媒介化治理——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11):37-56.
[24] 李良荣,张华. 参与社会治理:传媒公共性的实践逻辑[J]. 现代传播,2014(4):31-34.
[25] 孙五三. 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社会运作机制[J]. 新闻与传播评论辑刊,2004(1):459-474.
[26] 谢进川. 传媒治理论:社会风险治理视角下的传媒功能研究[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7] 蔣琳. 转型期媒介参与治理的现实向度——由兰考火灾媒体实践引发的思考[J]. 新闻界,2014(3):33-38.
[28] 胡远珍,张文君. 治理理论视域下媒介参与治理功能的检视——以武汉台电视问政《整治“新衙门作风”,建设“三化”大武汉》为例[J].决策与信息,2017(12):101-107.
[29] 丁柏铨. 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研究[J]. 编辑之友,2022(8):5-15.
[30] 张涛甫. 再论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风险[J]. 新闻大学,2011(3):38-43.
[31] 李春雷. 风险、技术与理性:媒介治理的逻辑脉络[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28-32.
[32] 沈正赋. 新型治理主体: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能力建构研究[J]. 编辑之友,2022(8):17-24.
[33] 陈相雨.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现实基础、介入逻辑和实践准则[J]. 编辑之友,2022(8):25-31.
[34] 焦德武. 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挑战与思路[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20-24.
[35] 罗赟,朱晓芸. 多元共治视角下的媒体融合实践研究[J]. 当代传播,2022(2):110-112.
[36] 史文静. 基于深度融合的媒介化城市治理系统研究[J]. 中国出版,2021(24):36-39.
[37] 沙垚. 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J]. 南京社会科学,2019(9):112-117.
[38] 牛耀红. 媒介化整合治理:数字公共媒介何以破解乡村治理碎片化困境[D].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2.
[39] 方提,尹韵公. 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现路径[J]. 现代传播,2019(4):11-14.
[40] 张涛甫,赵静. 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11):69-83.
[41] 张诚,朱天. 从“集成媒体的新机构”到“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方位坐标及其功能逻辑再思考[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27-133.
[42] 朱亚希,肖尧中. 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治理媒介化”视野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9):151-156.
Mediatization of Governan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XU Ke1, HUANG Chu-xin2,3(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45, China; 3.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tization theory and governance theory, the dual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mediatization society makes "mediatization of governance" a new breakthrough i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mediatization research and governance research.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it is necessary to first def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dieum plus governance", "media governance" and "mediatization of governance". "Medium plus governance" cannot be established and function, whereas the confusion of "media governance" lends itself to the feasibility of "mediatization of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key concepts,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take a realistic look at "mediatiz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local contex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onstantly requires the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of the media. At present, the "state-society" communication at the political level, the response to major emergencies in a society,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have all become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mediatization of governance and China's social reality.
Key words: mediatization of governance; media governance; political mediatiz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