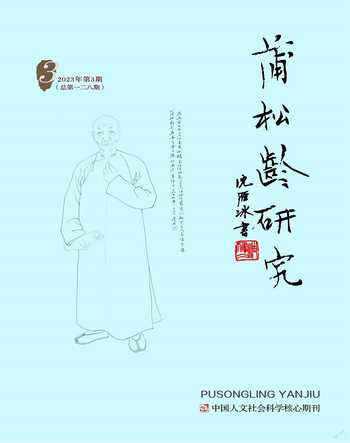蒲松龄的《画壁》与波提切利的《春》
2023-10-28朱丛丛翟玮
朱丛丛 翟玮
摘要:蒲松龄是中国伟大的小说家,波提切利是意大利伟大的画家。两人相隔二百年和千万里,所从事的艺术种类也不同。但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蒲松龄的小说艺术竟和波提切利的绘画艺术相遇相通了。蒲松龄通过想象虚构了一幅壁画,给我们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傅雷通过波提切利的画,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欣赏名画的无限可能。蒲松龄的《画壁》和波提切利的《春》,都以“爱娇”的魔力,把读者给吸引住了。
关键词:蒲松龄;波提切利;傅雷;《画壁》;《春》;爱娇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
蒲松龄(1640—1715)是中国十七世纪伟大的作家,其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闻名世界的文学名作。桑德罗·波提切利(1445—1510)是十五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画家,其著名画作《维纳斯的诞生》《春》等,也都是举世闻名的美术作品。蒲松龄和波提切利相隔两百年和上万里,所处之时代氛围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所操之艺术种类也不同,但是在小说《画壁》和画作《春》中,我们却嗅到了相同的艺术气息和相通的美学韵味。这大概就是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吧。
蒲松龄的《画壁》,写的是主人公朱孝廉看到一幅“散花天女”的壁画,不由想入非非,也让读者跟着想入非非的故事。
江西人孟龙潭和朱孝廉客居在北京城里,闲来无事,就到一座寺院游觀。寺里只有一个临时挂搭的游方僧人,便给他俩做起了导游。寺院的大殿正中有南朝僧人保志的塑像,这没有引起游观者的注意,可是当抬头看到墙上的壁画时,画面就生动起来了。这是怎样的一幅壁画呢?
两壁画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1]15
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除了三十一岁时到过江苏的宝应和高邮外,足迹未出山东。关于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及其素材的大致来源,他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 [1]1
《聊斋志异》的分卷,既不是按创作先后编排,也不是按题材或主题编排,但是排在《聊斋志异》卷一开头部分的这些作品,照常理推算,应是其早期作品,从作品中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正和蒲松龄创作初期的年龄气质相对应。因此,这篇《画壁》,应该不是“久之”之后“所积益夥”的作品,不是别人通过邮筒把故事邮寄给他的,可能是他直接听孟龙潭讲述的,或者是由别人转述的。北京这座寺院的壁画,他也不可能亲自看到,这就说明,《画壁》这篇小说的故事和其中所说的壁画,都是蒲松龄根据传闻创作出来的。
尽管《画壁》中这幅令人心驰神往的壁画是蒲松龄杜撰出来的,但也并非一点依据也没有。汪曾祺先生在评论范仲淹和《岳阳楼记》的关系时,就有过精彩论述:
写这篇《记》的时候,范仲淹不在岳阳,他被贬在邓州,即今延安,而且听说他根本就没有到过岳阳,《记》中对岳阳楼四周景色的描写,完全出诸想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他没有到过岳阳,可是比许多久住岳阳的人看到的还要真切……范仲淹虽可能没有看到过洞庭湖,但是他看到过很多巨浸大泽。他是吴县人,太湖是一定看过的。我很疑他对洞庭湖的描写,有些是从太湖印象中借用过来的。[2]70
汪曾祺先生先说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却比岳阳人看到的岳阳楼景色还要“真切”,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可是他又说范仲淹对洞庭湖的描写,有些是“从太湖印象中借用过来的”。那么,没有到过岳阳的范仲淹对岳阳楼的描写,也就是可思可议的了。
根据汪曾祺先生这一理论,可以推测,蒲松龄虽然没有到过北京,没见过这座寺庙的壁画,可是他一定在别的寺庙里见过“散花天女”的壁画。因为“散花天女”是佛教中的著名神女,“天女散花”是佛教中的著名公案,很多寺庙都有与之有关的壁画。再说,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北京的某个寺院,其实这幅壁画不一定就在那个寺院的那面墙壁上,它或许只存在于蒲松龄的大脑中。
也就是说,蒲松龄通过想象,给读者描画了一幅有关“散花天女”的迷人画面。
二
蒲松龄通过想象来描绘这幅壁画,展现的是一种什么心理机制呢?联系上引汪曾祺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印象”的“借用”。所谓“印象”,就是指人接触客观事物之后,在头脑中留下的迹象。因为已经时过境迁,彼时彼地的具体事物已经不在此时此地的感知范围之内,所以“印象”在同一人的印象中是不确定的,在不同个体中,更会随其社会地位、艺术修养、认知能力等不同而有所不同。以阅读《红楼梦》为例,虽说认识对象是相同的,认识过程也是相通的,可认识所得到的“印象”却是大相径庭。鲁迅先生说:
《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3]145
同理,通过一个“天女散花”的故事,人们也可以得出种种不同的“印象”,来为自己的小说、美术创作等服务,以实现其主旨的传达,起到小说家、画家所拟应该起到的或艺术感染作用、或道德教化作用,等等。而世人对于这些“印象”的运用,大多已经脱离了“天女散花”的本意,故与其说是运用,不如说是“借用”——因为适用,所以只是临时借来一用,借题发挥而已。
“天女散花”的故事出自佛教典籍《维摩诘经》卷中《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结习未尽,华著身耳;结习尽者,华不著也。” [4]135其中“天华”即为“天花”。关于这段公案的微言大义,我们不去深究,我们只来看蒲松龄是怎样借题发挥、借机行事的。
《维摩诘经》只说“有一天女”,而“画壁”却说“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表明壁画中有一群散花天女,“垂髫者”只是其中一个。这从下文的“群笑而去”,也可以得到验证。佛教经典中明明只有一个天女,蒲松龄为什么“借”来把它“画”成了一群天女了呢?这当然是为了接下来的既天真烂漫、又通情达理的“群聊”有关。就如同一组电影镜头,从头到尾只有两个演员,故事未免太单调,声音未免太单薄了。只有众声喧哗,画面才热闹,才会使观众感到“真切”,才能赢得好的票房收入。
再说,佛教经典中的天女只是散花,并没写到其面部表情,可是《画壁》却说她“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其中“拈花微笑”出自《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尔时世尊即拈奉献金色婆罗华,瞬目扬眉,示诸大众,默然毋措。有迦叶破颜微笑。” [5]9“拈花”的是释迦牟佛,“微笑”的是其大弟子迦叶。一笑之间,师徒二人算是心有灵犀了。蒲松龄把这则公案中两个人的动作借来一用,画到这位垂髫少女的身上,就使得北京城里这幅凭空想象的壁画,俨然成了二百年前、万里之外的那位佛罗伦萨画家波提切利的名画《春》了。
凡是读过《画壁》这篇小说的人,没有不认为此段文字逼真如画的。就算对佛教没有任何根底者,只把该段描写作世俗文字看,也不得不叹服蒲松龄的传神造化之功,假设真有这么一幅壁画,蒲松龄一定把它的精神气质传达殆尽。或者,就算那座寺院中真有这么一幅壁画,如今也早随着墙皮的剥落而化为尘埃了,可是蒲松龄这段文字还依然活色生香,甚至就像汪曾祺先生所说,比许多当时的人“看到的还要真切”。这应该是文学作品胜过美术作品的地方——文学作品有更强的抗实践性,因为它不褪色,不变形,有时还愈显“真切”。
设若看过傅雷先生那本久传不衰的名作《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一定会认为,蒲松龄之于《画壁》中的这幅壁画,就好比傅雷先生之于波提切利的名画《春》。蒲、傅二人都是名画解读的高手。
三
波提切利的《春》,也是一幅有关神灵的画作。关于这幅画作所表达的思想意趣和艺术蕴含,九十多年前,傅雷先生就有精妙绝伦的阐释。傅雷先生就画论画,没有联系蒲松龄《画壁》这篇名作,我们今天将《春》与《画壁》联系起来,做一下跨文化、跨艺术门类的研究,或许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艺术火花和思想精光。
在希腊人的传说和信仰中,大自然中栖居着无数神灵,春天来了,女神们在月光下回旋着跳舞。傅雷先生说:
波提切利的《春》,正是描绘这样轻灵幽美的一幕。春的女神抱着鲜花前行,轻盈的衣褶中散满着花朵。她后面,跟着花神(Flora)与微风之神(Zephyrus)。更远处,三女神手牵手在跳舞。正中,是一个高贵的女神维纳斯。原来维纳斯所代表的意义就有两种:一是美丽和享乐的象征……一是世界上一切生命之源的代表……波提切利的这个翡冷翠型的女子,当然是代表后一种女神了……
草地上、树枝上、春神衣裾上、花神口唇上,到处是美丽的鲜花,整个世界布满着春的气象。[6]5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佛教一直是庄严神圣的,可是通过《画壁》中生动活泼的文字描述,把神灵庄严神圣的光环去掉了,剩下的都是日常烟火气象,因此画面也像《春》一样,是“轻灵幽美”的。在《春》中,春的女神抱着鲜花前行,衣褶中落满花朵。《画壁》描写的画面里,这位垂髫少女“拈花微笑”,花朵虽然没有落满她的衣褶,可她的笑容却如同《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洇满了整个画幅,散花天女们的“群笑”,也落满了寺院的所有角落——这不仅仅是美术,更是飘满音符的音乐。
在《春》中,女神维纳斯是生命之源的代表,在《画壁》中,寺中才片刻,壁上已数日,朱孝廉和垂髫少女缱绻缠绵,可能也孕育了生命。在《春》中,傅雷先生否认维纳斯是美丽和享乐的象征,可是在《画壁》中,这位垂髫少女却更进一步,成了令人向往的美丽和享乐的象征。尽管朱孝廉被其美貌所吸引,飘飘然飞到壁上,尽享欢乐后也有极大的恐惧,但那恐惧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快乐的诱惑。
这位垂髫少女“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这是蒲松龄描写青春少女笑容的典型笔触。一个人的“微笑”从什么地方最能看得出来?答曰:嘴巴和眼睛。她的樱桃小口是将动未动,她横展的眼波是将流未流,这不就是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信中所说的“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 [7]341吗?这不也正是钱钟书先生最为欣赏的“包孕最丰富的片刻” [8]48吗?
傅雷先生是优秀的文学家和美术鉴赏家,他能把自己欣赏画作时的所思所感用优美的语言记录下来,传达给读者,让读者也心有戚戚焉。他说:
春神,抱着鲜花,婀娜的姿态与轻盈的步履,很可以用“步步莲花”的古典去形容她。脸上的微笑表示欢乐,但欢乐中含着惘然的哀情,这已是芬奇的微笑了。[6]52
蒲松龄《画壁》中的这位垂髫少女,虽然不是春神,但她手里拈着鲜花,也是春天的象征,虽然仙女不一定缠小脚,但在清朝人的潜意识中,壁画上的女孩一定也是“三寸金莲”。《春》中的仙女尽管都是光脚天足,可傅雷先生这个“‘步步莲花的古典”,却正说出了《画壁》中仙女“婀娜的姿态与轻盈的步履”。傅雷先生说《春》中春神的微笑“欢乐中含着惘然”,《画壁》中的垂髫少女脸上,大概也含有青春的欢乐与惘然吧,那也“已是芬奇的微笑了”。那么,什么是“芬奇的微笑”呢?
傅雷先生分析达·芬奇的名画《瑶公特》,也就是那幅著名的《蒙娜·丽莎》时说,达·芬奇的作品有一种“销魂”的魔力。他说:
这神秘正隐藏在微笑之中,尤其在“瑶公特”的微笑之中!单纯地往两旁抿去的口唇便是指出这微笑还只是将笑未笑的开端……这微笑,是一种蕴藏着的快乐的标志呢,还是处女的童贞的表现?这是不容易且也不必解答的。這是一个莫测高深的神秘。[6]61
“瑶公特”的微笑完全含蓄在口缝之间,口唇抿着的皱痕一直波及面颊。脸上的高凸与低陷几乎全以表示微笑的皱痕为中心。下眼皮差不多是直线的,因此眼睛觉得扁长了些,这眼睛的倾向,自然也和口唇一样,是微笑的标识。[6]62-63
傅雷先生所说的这“将笑未笑的开端”“蕴藏着的快乐的标志”“处女的童贞的表现”“微笑的标识”等,都使我们联想到蒲松龄笔下描写那位垂髫少女的八个字:“樱唇欲动,眼波将流。”除了两幅画作上人物面部构造的民族性不同,中国的这位少女比意大利的那位少妇更年轻、更有活力,两幅画几乎就是表现了相同的青春郁勃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在波提切利的《春》中,同样存在,并且整幅画面对此表现得更为明显。
傅雷先生還说,“瑶公特”那谜一般的微笑,给我们以最缥缈、最恍惚、最捉摸不定的感觉。在这一点上,达·芬奇的艺术和东方的艺术精神相契合了。东西方的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登顶相会,这应该也是傅雷先生所乐于肯定的。
总之,蒲松龄通过想象,在一座小小寺院的墙壁上,给读者描绘了一幅名画;傅雷先生通过想象,把一幅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的名画搬到我们眼前,并给它打开了辽阔的欣赏视野,让我们可以把东西方的两种艺术放在一起欣赏,美美与共。
傅雷先生解读波提切利的作品,说他的人物特具一副妩媚(grace,可译为妩媚、温雅、风流、娇丽、婀娜等意。在神话上亦可译为“散花天女”)与神秘的面貌,即世称为“波提切利的妩媚”。拿它的“妩媚与神秘”来解读《画壁》中的拈花少女,也十分恰当。
傅雷先生解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时还说,达·芬奇的人物同波提切利的人物一样,同样具有“妩媚”的品质。但是达·芬奇的作品,更给人一种“销魂”的魔力。我们读《聊斋志异》,对其中人物的感觉,除了“妩媚”也是“魔力”。正如法国悲剧家高乃依的一句名诗所言:“一种莫名的爱娇,把我摄向着你。”面对波提切利和达·芬奇的名画,傅雷先生舌灿莲花、滔滔不绝;而面对蒲松龄虚构的壁画,我们也同朱孝廉一样,都有一种身不由己、飘向壁上的恍惚感,最恰当的一个词,就是“爱娇”的魅力——我们都被画中或小说中人物的“爱娇”给摄走了魂魄!
傅雷先生还说,《春》这个名字,不是波提切利原作的名字,是后来意大利画家瓦萨里给起的。假使蒲松龄的小说《画壁》也没有名字,最恰当的名字也应该是《春》!
参考文献:
[1]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散文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3]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赖永海,主编.维摩诘经[M].高永旺,张仲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5][宋]普济.五灯会元(上)[M].毛寔,校订.北京:华龄出版社,2022.
[6]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M].北京:三联书店,2022.
[7]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Pu Songling's The Painted Wall and Botticelli's Primavera
ZHU Cong-cong 1 ZHAI Wei 2
(1.Department of Fine Arts,Zibo Normal College,Zibo 255130,China;
2.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Zibo Normal College,Zibo 255130,China)
Abstract: Pu Songling is a great Chinese novelist,while Botticelli is a great Italian painter. Two hundred years and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the two men engaged in different forms of art. However,despite the geographical and temporal disparity,there is a surprising convergence between Pu Songling's literary art and Botticelli's painting art. Pu Songling created an imaginary mural in his fiction,opening up endless imaginative possibilities for readers. On the other hand,Fu Lei,through Botticelli's paintings,demonstrated th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of appreciating famous artworks. Pu Songling's The Painted Wall and Botticelli's Primavera both possess the enchanting power of love and charm,” which captivates readers.
Key words: Pu Songling;Botticelli;Fu Lei;The Painted Wall;Primavera;love and ch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