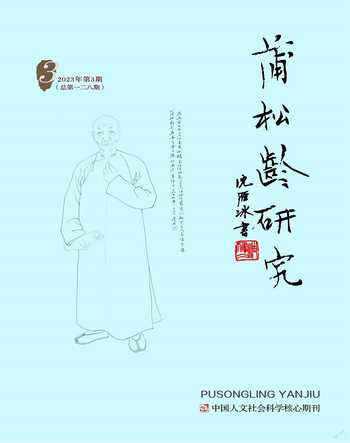《聊斋志异》中花妖形象的生态意蕴
2023-10-28房倩格
房倩格
摘要:《聊斋志异》是我国志怪小说中的经典,书中诸多篇目借助志怪故事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其中花妖形象与自然的联系尤为紧密,与生态美学存在一定契合之处,本文探讨《聊斋志异》中花妖形象的生态意蕴。
关键词:生态美学;自然美;蒲松龄;《聊斋志异》;花妖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
《聊斋志异》作为我国文学瑰宝,其内蕴的精神价值得到学界公认。《聊斋志异》中以志怪故事为载体表达出独到的人与自然相处观念,其中花妖故事中的花妖形象尤为突出。蒲松龄塑造了性格鲜明、活灵活现的花妖形象,体现出难能可贵的生态美学价值。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蔚为大观,经典有多种分析视角,本文探讨《聊斋志异》中花妖形象所蕴含的生态意味。
一、《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形象与生态美学
《聊斋志异》所涉及的题材极为广泛,不仅包罗奇谈异闻、市井人文、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还借各种故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小说成书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按照蒲松龄自己的评价即是“强梁世界,原无皂白” [1]10。正是在这种社会的批评中,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甚至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生态美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自然写作的代表性作品。
在生态视野中,人类作为一种有限性的存在者,生态审美经验要成立的前提,就是要将这一有限性存在方式视为一种人的根本的、独特的存在方式,并将这一存在方式视为对自我的肯定。对自我有限性的经验,是生态审美经验的基础,是一种肯定性的经验。[2]180-185当代生态美学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使人类肯定自身有限性的同时,仍然认为自然充满美感,甚至自然因为人类的有限性而美。人类的发展史即是对自然的征服史,先前人类的劳绩是基于对自然改造之上。因此,如何使得人类意识到自身有限性还能够领会自然之美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聊斋志异》受各种传统美学思想、古代志怪小说、民间信仰影响,表达出善恶有报、热爱自然、尊重规律、物我和谐等自然观念。读者通过书中的志怪故事,将个人情感由人类社会转移至自然环境,对动物、植物产生爱护之情,对自然具有敬畏与敬爱之心。《聊斋志异》的诸多篇目中,花妖形象与自然结合紧密,花妖形象源于自然,凝结于人形,花妖形象中自然美与人性美相交融,体现的自然观念与生态美学所探讨的内容存在一定契合之处。
二、花妖形象中人与自然的交融之美
花妖的名字多数来源于相应花朵的别称或品种名称,隐喻花妖原形为自然中的花朵。《聊斋志异》中共出现《荷花三娘子》《绛妃》《葛巾》《黄英》《香玉》五篇花妖小说。[3]4小说中的花妖形象是作者精神世界中道德品性与美感的凝结,是自然之美与人性之美交融的结果。
(一)花之样貌与人之外貌的契合
在对花妖外貌形象的描写中,作者对花妖形象的塑造多将花朵的样貌、意象与人的外貌、仪容相对应。花妖外貌形象多源于花朵的样貌以及传统文化中由花朵样貌而产生的意象在人身上的投影。
《香玉》篇中,香玉作为开白色花朵的白牡丹花妖,衣着白衣。绛雪作为开红色花朵的耐冬树花妖,身披红衣。对于二位花妖的外貌描写为红白相映,艳丽双绝。《荷花三娘子》篇中,荷花花妖荷花三娘子的外貌描写为“垂髫人,衣冰縠,绝代也” ① ,恰似荷花之脱尘不凡,清雅高洁之貌。《绛妃》与《葛巾》二篇都以牡丹花妖为主要人物。绛妃衣着华贵,环佩锵然,仿若皇宫中的嫔妃。同为牡丹花妖的葛巾则宫妆艳绝,令人眩迷,具有大户人家的富贵艳丽。牡丹花妖外貌中的贵气之美恰如牡丹盛放之华贵雍容。《黄英》篇中对菊花花妖黄英的外貌描写则为“二十几许绝世美人也”,对菊花花妖陶三郎的外貌则描写为“丰姿洒落”,寥寥几字恰合菊之淡雅。
(二)花之姿态与人之神态的融合
花妖神态是花之姿态与人之姿态的融合,花妖灵动的神态使花妖形象更加立体。花妖的姿态与花的姿态息息相关,花妖原形花朵不同,神态便大不相同。作者将花的姿态与人的神态合理融合,赋予到花妖形象中,使得花妖形象各具魅力,各有千秋。
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荷花三娘子》篇中,荷花三娘子矜持清高,洁净孤傲。几经宗湘若拜求方才现身,与狐女的热情奔放形成鲜明对比。牡丹具有“花中之王”的美称。牡丹花妖的神态恰是牡丹花地位高贵、绚烂无双的映射。《绛妃》篇中,牡丹花妖绛妃自称花神,统领合家眷属,姿态高贵,前拥后簇,高不可攀。《葛巾》篇中,牡丹花妖葛巾身伴桑姥姥、玉版等人,自称世家女,面对强盗临危不惧,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兼具气场与气度。《黄英》篇中菊花花妖黄英性格高爽通达,风趣不俗。陶三郎悠然大方,潇洒隐逸。恰如菊花之顽强不屈,淡雅高洁。姐弟二人自力更生,生活有滋有味,妙趣横生,恰似菊花之绽放生命,直面霜寒。《香玉》篇中,黄生以香玉为妻,以绛雪为友。白牡丹花妖香玉温柔多情,耐冬花妖绛雪冷静自持。香玉软玉温香的姿态与绛雪聪慧矜持的姿态,均是将花之姿态与人的神态融合而成。花之姿态不同,花妖神态也形成对比。
(三)花之特性與人之品性的联合
《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形象联合了花之特性与人之品性,花的特性中包括人们为花赋予的意象品格,人的品性也来源于爱花人的历史典故,这一点在花妖的处世方式中亦有一定体现。
《荷花三娘子》中荷花花妖对宗生了却缘分后便请求告别,宗生思念时对旧物呼唤“荷花三娘子”,旧物便立即化作莲女,容貌如昨,只是不说话罢了。这种超尘脱俗的品性恰如荷花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花之特性。牡丹花妖绛妃出场便明示花神身份,身份尊贵却不蛮横骄矜,知书达理,气度不凡。绛妃初见男主人公时预备行礼,又以宴席美酒招待,男主人公再三请命,才明言托其写声讨檄文。牡丹花妖葛巾因常大用爱恋专一而私奔,因常大用的心生猜疑而离去,其高自尊、高底气的设定恰是牡丹花王的尊贵身份的解构与重构。唯一的男性花妖陶三郎的原形为菊花,极为嗜酒,酩酊大醉化为醉陶,便是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作者陶渊明嗜酒的品性投射而成。菊花花妖黄英善雅谈,巧纫绩,迁就随和,恰是菊花真情高洁、情操高尚的引申。黄英具备独立品格,通过经营菊花生意自力更生,坚强自立,不再是先前事事以夫为尊的依附性女性形象,恰似菊花不怕霜打,直面寒风的花之特性。
三、花妖故事的生態美学意味
蒲松龄笔下的花妖形象,是人与自然融合的艺术化表现。花妖生存的世界可能缺乏逻辑,但可以是万物有灵的诗意国度。人类不应单以自我的尺度衡量万物,还应与自然共生共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体现了人类和合共生的家园意识。
(一)诗意栖居
“诗意的栖居”诞生于工业社会,是科学机能异常发达之后个体的生命情感反思,主要侧重审美对个人内心的感化作用。花妖故事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友好关系,从审美的视角看待自然,体现了人在自然中以审美为视角进行生存,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自然之美的向往。
《聊斋志异》从审美视角出发,把花妖故事作为美景、美人、美事的承载体,将花的自然之美与人性之美相交融,借助花妖形象促生超凡脱俗的审美体验。作者紧扣自然界之美刻画花妖形象。对牡丹花妖葛巾的形象刻画紧扣“香”字,“女郎近曳之,忽闻异香竟体”“玉肌乍露,热香四流,偎抱之间,觉鼻息汗熏,无气不馥”是将自然中的花香投射在人身上。对香玉重为花神的描写为“次年四月至宫,则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摇摇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将花朵含苞欲放与人之神异重生相融合,体现了自然神秘之魅。
《聊斋志异》中花妖的人设构成元素皆是来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典故。花妖故事中融合山水文化、田园文化、隐士文化,更容易激起人们对于自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传统文化中,荷花被认为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雅,在《荷花三娘子》中对荷花三娘子的塑造便突出了高洁明莹的形象。《黄英》篇中突出了陶渊明爱菊的历史典故。黄英与陶三郎姐弟虽善于经营,但并非缘于贪婪。借黄英之口说出“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陶三郎是《聊斋志异》中唯一的男性花妖,作为陶渊明身份的投射,承袭了陶渊明的姓氏与喜好。陶三郎醉死最终化为醉陶,用酒浇灌则更加茂盛,则是将陶渊明嗜酒与爱菊的诗意联合。
(二)家园意识
“家园”是个人精神归属的空间感知,文学对于“家园”的描述,反映了不同时代作家对于精神家园的追求。在家园中,栖居便有温暖、安全的“在家”之感。我国作为农业古国,安土重迁、重回故土的家园意识较强,但何为家园,必须在不同作品的叙述中具体体味。花妖故事中的角色折射出了作者特殊的家园意识。
花妖故事中,家园意识作为故事中的隐性线索,将物质性、社会性、精神性的家园相融合,体现了情感与特定环境的交融。《黄英》篇中,陶三郎在马子才家中居住一段时间后,便离开马子才的家乡,重回故土金陵,与马子才丧失联络。分别一年后,马子才偶然路过金陵见菊花正盛,怀疑是陶三郎所培育,才再次寻见陶三郎。马子才劝陶三郎回到有姐姐黄英、姐夫马子才所在的家,陶三郎却说:“金陵,吾故土,将婚于是。积有薄资,烦寄吾姊。我岁杪当暂去。”体现了蒲松龄笔下的花妖也具有留恋故乡,对家园有所执着的安土重迁观念。马子才不应,唤仆人替陶生将花铺中的菊花贱卖,逼着陶三郎准备行装一起归家。陶三郎方才回到了马子才家中。然而,这种归家也只是从故土所在的家园回到了亲人所在的家园,依然具备一定家园意识。《葛巾》篇中,葛巾与常大用私奔回千里之外的常大用的老家,还将自己的妹妹玉版许配给常大用的弟弟常大器。在常大用的老家受到强盗威胁时,葛巾与玉版挺身而出,捍卫家园,亦是花妖形象具备家园意识的体现。
(三)共生共存
蒲松龄借助花妖故事,传递出了人与自然共存的精神内核以及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理念。生态美学倡导人类将共存作为旨归,认识到人与自然本为一体,而非主客对立的二元关系。《聊斋志异》花妖故事中表达的内在价值观念便有共存之意,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圆融观照。
花妖故事中,人们对于自然是持喜爱、认可的态度,与自然和谐共存。《葛巾》篇中男主人公常大用喜爱牡丹,听闻曹州牡丹甲齐鲁,借住曹州官宦人家的花园里,整日流连于牡丹园中,作了一百首怀牡丹诗,花光了盘缠,忘记归家。《黄英》篇中男主人公马子才家里世世代代喜好菊花,到了马子才这辈,喜爱之情更甚,对于未曾见过的菊花品种千方百计地谋求,求得便如获至宝。五篇花妖故事中有两篇是由于人类极其喜爱自然中花卉而先行结缘,进而开启了花妖故事的正文篇章。
牡丹花妖葛巾的母亲是曹州名列第一的牡丹花,被封为“曹国夫人”,享曹州盛誉,引得文人赋诗夸赞。菊花花妖黄英姐弟培育的菊花引得市人争相购买,车载肩负,络绎不绝。可见对自然的普遍喜爱与认同已是普遍现象,赏花种花蔚然成风,这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自然之美的侧面体现。
花妖故事的结局则更带有神异色彩,人与植物不仅能够共生共存,甚至人与植物间可以转化。部分故事的结局中消融了人与自然的界限,人能够化为植物。《葛巾》中葛巾与玉版的两个孩子化为两株牡丹。《香玉》中黄生作为人类,死后也能够化成不开花的牡丹,作为植物继续陪伴香玉与绛雪。在神秘色彩的笼罩中表现出天人合一、万物齐一的至高和谐状态。
四、花妖形象对“自然复魅”命题的回答
“自然的复魅”是生态美学观希望达成的结果。事实上,每一代情感健康的人,都会对自然之美心生触动。而在当下,科学理性的发展与冰冷计算利益的人心令艺术的欣赏者同自然之美变得疏远。
“祛魅”用某种定量的尺度丈量世界,自然被物化为僵死的物质,祛除了鬼怪神异之魅,同时也祛除了自然神秘之美。为此需要恢复“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潜在审美性” [4]39。这种“自然的复魅”并不是回到原始的、对自然充满畏惧的蒙昧状态,而是打破人类与自然的人为对立,意识到人类与自然本为一体,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具备家园意识,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自然看做人类的家园而爱护、敬畏、共存,对自然的内在价值表示认同。
“‘自然的复魅到底如何操作才能既不使人复归于蒙昧乃至重新被迷信所主宰,同时又能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5]35这一问题还会继续探讨下去。《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形象充满自然美与人性美,具备较高的美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对“自然的复魅”命题做出了独到的回答。
参考文献:
[1]曾繁仁.《聊斋志异》的“美生”论自然写作[J].文史哲,2020,(5).
[2]孙丽君.现象学视阈中生态美学的方法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3]王芳.《聊斋志异》中花妖世界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1.
[4]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李文斌.对生态美学的两点质疑[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the Flower Spirit in Liaozhai Zhiyi
FANG Qian-g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China)
Abstract: Liaozhai Zhiyi is a classic of mystical novels in China. Many articles in the book express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the help of mystical stories. Among them,the flower spirit is particularly closely related to nature,and there is a certain fit with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the flower spirit in Liaozhai Zhiyi.
Key words: Ecological aesthetics;Natural beauty;Pu Songling;Liaozhai Zhiyi;Flower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