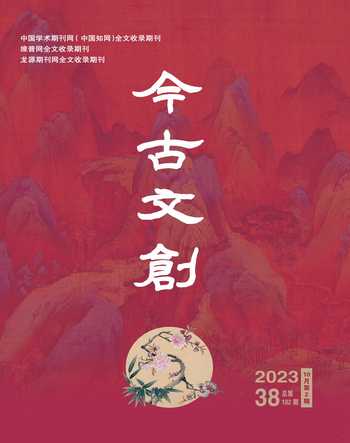《杀生》中的替罪羊机制解读
2023-10-27马肖遥
【摘要】勒内·基拉尔认为在创世之初就存在着迫害行为,迫害行为成为社会秩序创始的秩序和结构的原则。在社会出现危机时,通过调整相互的暴力,一个人的死亡来换取全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便是替罪羊机制。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迫害文本,但是受制于封建礼教与理性约束,替罪羊的迫害事实是合乎逻辑的,是一种法则的文化,但是为了全社会的持续发展,又不得不对此事实隐蔽。本文对《杀生》中受迫害的替罪羊形象进行解读,揭示其替罪羊机制的运行和迫害的扩张与变形。
【关键词】替罪羊;迫害文本;集体暴力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8-008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8.026
杀人如儿戏,诛心亦无声。电影《杀生》改编自陈铁军的中篇小说《儿戏杀人》,讲述了在中国西南一偏远隔绝的“长寿镇”的故事,此地因其人皆长寿而得名,在这个规矩自成之地,主人公牛结实却游离于礼教之外,特立独行上天入地搅得全镇不得安宁,文中写道:“夜掀寡妇门,昼掘绝户坟,总之凡是被人所唾弃的事情没有他不干的……一个人一旦活到这个份上,被人杀掉只是迟早的事儿……”某日,小镇突发瘟疫,朝廷指派医生在去诊治的路上发现了濒死的牛结实,随即带回小镇,而全镇的人对于医生救治牛结实一事极其抵触并百般阻挠。在医生的一步步深入了解下,长寿镇的秘密也公之于众。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迫害行为,牛结实这个替罪羊的死才能换取小镇盛名与安宁。替罪羊一词的起源与古犹太教“赎罪祭”有关,《圣经旧约》第三章《利未记》记载了亚伦用羊代为赎罪的章节。在中国文化中,《孟子·梁惠王(上)》也有“何以废也,以羊易之”的记载,此后也日渐泛指一切代人受过者[1]。基拉尔从模仿欲望出发考察人交往中的模仿与竞争,并揭示了在人际关系中充斥着永久的暴力,人类社会就是在暴力和迫害的危机和解除的交替中发展的,这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他在大量的文本里面发现了迫害事实,统治阶级极力掩盖集体迫害和暴力行为,甚至粉饰迫害,通过替罪羊机制来让社会回到正轨。基拉尔最先在西方神话里发现大量暴力事件,他认为神话都是迫害文本,而普通迫害文本与神话文本具有相似性,基拉尔以诸多迫害范式以及扩张与变形来研究叙事文本,具有重要的揭示意义。《儿戏杀人》改编为子电影《杀生》,其文本叙事与电影叙事都存在替罪羊机制,并掩饰集体迫害。
一、《杀生》的四种迫害范式
(一)社会危机状态的描述
基拉尔认为,我们所了解的迫害多是发生在危机时期,并且这个社会处于未分化的状态。在神话文本里,可以看到许多原始的、混沌的、天地初开,混乱伴随着暴力冲突的场景。在普通迫害文本里,这一特点依然存在。
社会危机在野蛮荒芜的文化环境里滋生,總结来说也无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外部原因,如天灾人祸,自然破坏的力量所引发的危机;二是内部原因,如文化冲突或政治动乱[2]。若从文化的多视角来看,宗教仪式和传统部落更易成为煽动人群实施集体暴力的目标,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都与主流人群相差甚远,血缘宗亲和非理性因素是其显著特点。当社会发生危机时,这种区分就尤为显著,反犹太主义就是典型替罪羊案例[3]。在这场社会危机里,被迫害者总是遭受集体间接迫害或者直接迫害,社会本身的文化秩序已然崩塌。
“长寿镇”位置偏僻,与世隔绝,以镇长为首的村民思想固化,长期被假仁假义的道德礼教侵蚀。为了维护小镇“长寿”的声誉,给快到120岁的圣祖禁欲上药,为了小镇集体利益迫使个人意志屈服。主人公牛结实也作为“反派”不断把走在正轨的小镇带向偏离的路线。祖爷爷的死亡让小镇的人终于无法忍受,在此也埋下了牛结实必死的伏笔。由于小镇对不合规矩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驱逐,牛结实每次都能完好无损地回到小镇,且小镇对明目张胆的暗杀极其避讳,这在牛医生对众人的疑问中可以看到:“他问道:‘大家是不是都想杀死牛结实?’众人眼神躲避支支吾吾:杀人?这不太好吧,是啊,杀人是不对的。牛医生嘴角一撇又问:‘好,那我换个说法,大家是不是希望牛结实永远消失?’大家忙着点头,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既有秩序和祖宗律法的约束,让他们不能对恨之入骨的人表露出一丝杀意。诬陷牛结实得了瘟疫,这也是这个小社会人们心里的瘟疫,这是不治之症。此时,依山而建的小镇摇摇欲坠,丝毫没有注意到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即将来临。
(二)替罪羊的罪行
指控捣乱者所犯下的罪行,基拉尔归结出三种混乱者可指控的具体罪行。
一是对他者实施暴力行为,侵犯最高权力掌控者,或者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儿童。牛结实无恶不作,圣祖虽无实权,但他是小镇的精神象征,牛结实拔掉氧气罐,甚至灌酒导致圣祖猝死,让小镇盛名毁于一旦;他无视一切清规戒律,不尊老爱幼,和小孩比赛撒尿;使手段让屠夫赊账酒肉;夜以继日偷窥粉刷匠夫妇行房……这一切祸乱社会意识形态的异端行为,让他成为那个罪恶滔天的替罪羊。
二是性犯罪: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牛结实偷来用于家禽繁殖的催情粉倒入全镇的水源,在那一夜,整个小镇全然陷入了“未分化”的状态,距离和规矩彻底被打破,欲望之火在小镇蔓延,人的本能欲望喷薄而出且无视对象。在山头的小镇高层领导,身披黑色道袍服面色凝重地俯视着这一切。这也一步步宣告牛结实死刑的到来。
三是宗教犯罪:违反教会圣令,亵渎神明圣物等。在圣祖死后,作为小镇传统,马寡妇要陪同殉葬并迎接圣水,在马寡妇将要被献祭时,又是牛结实不顾这神圣仪式,将其救下并扛回自己的住处。在这第二类范式中,指控扰乱者的罪行是根据作者以谋害的偏见和艺术的需要进行虚构和杜撰的。这个社会不需要偏离,传统的社会规则以绝对优势压迫个人人性自由,像牛结实这样鲜活、有生命力的“异端”角色,打破了小镇千百年来的安逸。他无疑是这个社会进化前被迫害者的绝对人选。
(三)替罪羊的优先标记
在神话和普通迫害文本中,身体残疾、长相丑陋或有异于常人的体貌特征,总之异于常人的一切标志都会成为替罪羊的优先人选。基拉尔认为,他们的过度和至极都会引起迫害者的凝视,因为他们的独特奇异偏离社会的“均衡”和“典型”[4]。牛结实本不是小镇原住民,他爹是早年间路过小镇的一个商贩,无奈患癌而死,留下牛结实这么个孤儿,村民见其可怜,也就将其收留,他的外来者身份也是他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始终没有融入这个以追求长寿为人生信念和价值目标的小镇里,反而一次次冲击着小镇封闭落后人们的固有思维。在这个范式里,马寡妇同样是被迫害者,她只因是寡妇和哑巴这个特殊标记,就成为被迫害的不二人选,而她对此却无能为力。
不论是文化和宗教用以区分替罪羊的标准还是身体标准,它几乎体现在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所有方面。只要偏离社会所认可的“正常系数”,不管是高于还是低于这个系数,都会面临成为“替罪羊”的风险。祖宗的机制在再生产的潜意识里,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
(四)集体迫害的暴力描写
基拉尔替罪羊机制的第四类迫害范式即暴力本身。欲望引起暴力,为了满足共同欲望,一个小镇的安宁,一个对共同秩序的维护,共同推举出一个替罪羊,通过替罪羊的牺牲来维护和净化社会。多数人的赞同和权力的倾斜使暴力合法化,文中有三处典型的集体迫害,但作者都将其艺术化隐晦处理。牛医生协同众人欺瞒牛结实,采取心理战术“心由境生”让其相信自己时日无多,掰手腕作弊、屠户好心送肉、小青年提前结婚、初春冷雨里诱导其脱衣祈福。最终在小镇的集体努力下,牛结实终于倒下了,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它深信自己患癌——心理疾病。
基拉尔认为,集体迫害在历史的遗迹里始终具有淡化甚至消失的趋势,这是统治阶级所极力想隐藏和删除的。在这个范式里,人们将危机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将现实中所有偏离正常轨道的猜忌、慌张和一切负面情绪都集中到这个格格不入的人身上。他们煽动人群,将牛结实视为异类,以集体暴力的方式来消灭和摧毁他。只有清理掉这个毒素,人们才会感觉如释重负,这个世外桃源才可以恢复往日秩序,重新得到和解。
二、替罪羊机制的运行
(一)迫害的淡化与消失
在一个迫害文本里要得出迫害事实,不一定需要存在上述所有范式,一般存在两种或以上,就可确定是否存在集体暴力与替罪羊的产生:一是暴力行为确有其事;二是危机是现实的且迫在眉睫;三是仪式献祭的牺牲品,不是根据自身罪恶,而是根据他们具有替罪羊特殊标记,根据任何可聯想到他们罪恶行为的标记;四是机制运行的方向,也是将一切罪恶都顺理成章地嫁接到“受害者”身上,在抹杀掉他们栽赃的证据和受害者本身,危机也自会得到平息[2]。
同时,基拉尔认为,西方文明的特点就是神话色彩的衰弱,集体迫害在历史进程的描绘中,也逐渐弱化,把被迫害者的死,写成是自愿的,自我牺牲的,剔除集体迫害和个人暴力行为表述的意向主导着神话的演变[3]。
在柏拉图理性主义的影响下,暴力内容甚至被粉饰、被神圣化。通过前文学(神话)的影响,这种趋势也逐渐渗透到普通文本里。在这个民风淳朴的小镇里,如果不是牛结实的出现,镇民们会长久地安居乐业下去,而牛结实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镇民感觉到危机感,但也正是封建思想的约束,以及长寿镇不杀生的传统,才让人们没有暴怒而起杀了牛结实,而用极其隐蔽的手法来掩盖集体迫害的事实。
(二)替罪羊的转变
基拉尔认为,在迫害主题和迫害范式上,神话迫害文本和普通迫害文本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但也有些不同之处,除了神话里的被迫害者被描述成人兽同体的怪物外,它还会进行从被迫害者到神圣化的转变,最终成为被人神共同崇拜的人物。在神话里,受害者既是破坏者也是建设者,他所蕴含的转变重生后的力量,让他变成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4]。
在《杀生》中,牛结实作为破坏者并没有第二阶段神圣化的转变,但在这个迫害事实里,他却进行了一次从被动到主动的身份转变。牛结实在全镇人的蛊惑下已经深信自己患癌,不久于人世,可是小孩的一句话:“你没病,他们唬你的”,也曾让他动摇,当得知马寡妇已怀有自己的骨肉,而全镇人要谋杀自己的孩子,从马寡妇口中得知二者只能活其一时,他挨家挨户跪求原谅归还财物,只求放孩子一条生路,随后拉上自己的蓝色棺材,缓缓地走出小镇。他完成了从桀骜不驯反抗迫害到放弃斗争慷慨赴死的替罪羊身份的转变,而小镇也随着马寡妇和孩子的出逃,毁灭在了大地震下。
三、替罪羊的归宿
基拉尔通过对神话文本的考察得出人类社会在面对危机时,通过社会各成员间的暴力行为,推举或是指认某一个受害者,牺牲这一人来换取全社会的安定。这是社会发展亘古不变的规律和内在逻辑。基拉尔没有停留在这种悲观的论述上,而扼要地指出:“牺牲的方案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合乎社会机制运行的潜规则。”[2]但是,要反对历史对于替罪羊机制的掩盖,淡化甚至消除迫害事实,勇敢承认他们的牺牲是无辜的。基拉尔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宗教解释的道路,他认为:“正是我们拥有了犹太——基督主义,宗教日常欺骗的游戏才停止了。”而基督的救赎道路在被迫害者经历神圣化的阶段后,就会发生从被迫害者到迫害者的转向,基拉尔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为了避免自相矛盾,也就没再继续深入。
《杀生》替罪羊机制的揭示是通过外来医生的视角一步步呈现的,在牛结实被众人拷打摔下山崖,正好和外来医生的车碰在一起,牛结实怒斥道:“你欠老子一条命。”随后拉开探究牛结实死亡的迷局。迫害者们更愿意相信极个别者,甚至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都有可能危及现有封建意识形态和文化秩序。范式化的指控起到一个中介桥梁作用,允许和支持这种控告,无限放大受害者的罪行,最终被扣上罪恶的标签,推向死亡的深渊。
基拉尔认为,社会是由简单的差别结构和模仿机制联系起来的,文化秩序是受到控制的差别系统,在后者中,个人之间的差别被用来建立公共认同和相互关系[5]。而差别受到迫害,这不仅是被迫害者的话语,也是文化永恒的话语,在封闭的文化中,人自认为自由,浸润在“开放”的温床里,他们闭关在最狭窄的文化范围内,他们的区分特性使他们认为这里面是取之不竭的,对于任何想打破这常规的人,损害他们这种幻想的东西都会使他们恐慌不安,从而唤起了心底隐藏的迫害倾向[2]。而牛结实打破常规的举措无疑让这种迫害倾向逐渐变成不可更改的决定,可是他们不会知道牛结实劫马寡妇这个祭品,只是不想让鲜活生命白白牺牲,他割手放血只为治马寡妇的贫血症,偷挖祖坟不愿让一贫如洗的新婚夫妇潦倒度日,牛结实不恶,只是在释放自己纯洁率真的天性,来对抗这陈腐愚昧的传统礼教,反而是主张杀人先攻心的牛医生死在了自己的境由心生中,镇长死在了怂恿牛结实在春雨中祭祀后,缘由心生,一念成魔。迫害者关注的从来不是“偏离”,而是他不能理解和表述的对立面——未区别的混乱[2]。
四、结语
替罪羊机制是勒内·基拉尔在模仿欲望的基础上对社会暴力的探源研究,力图揭示历史进程中被掩盖的集体迫害事实,他对宗教隐喻的“牺牲”在文学人类学层面上,进行深入考察,探讨了替罪羊机制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维系与推动作用。替罪羊机制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文学材料上的,中外文学虽有很多差异性,但通过研究可知,在替罪羊机制下,“暴力”和“迫害”的本质不变,它是当原有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用以解决危机的重要手段。用替罪羊机制来研究文学文本,可以使迫害形象具体化,也可更加深入了解其暴力行为的深层逻辑。
参考文献:
[1]侯璐.从中西文化审视替罪羊意象[A]//外国语文论丛(第4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490-495.
[2]勒内·吉拉尔.替罪羊[M].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3]张凝,李永平.“替罪羊”与献祭危机——勒内·吉拉尔替罪受害者机制的内在逻辑寻踪[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03).
[4]冯寿农.勒内·吉拉尔神话观评析——兼论《西游记》的替罪羊机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6):78-84.
[5]郭宏珍.仪式暴力的公共性与合理化——勒内·吉拉德论宗教与暴力[J].河北学刊,2016,36(06).
作者简介:
马肖遥,男,陕西宝鸡人,宝鸡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