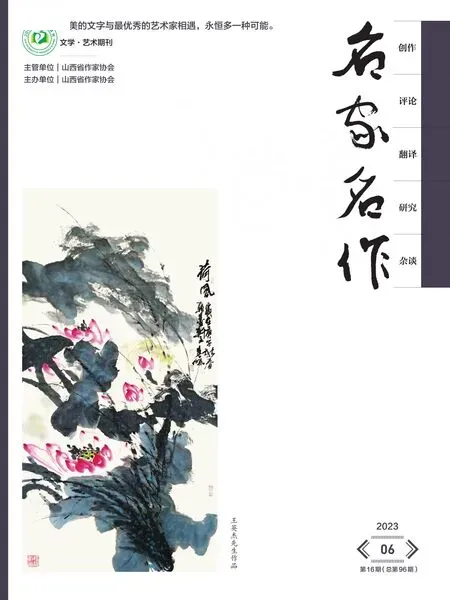浅析《金瓶梅》中李瓶儿的善与恶
2023-10-23刘婷
刘 婷
生活在《金瓶梅》场域中的人们,烙着时代的印痕,几乎都囿于物欲和性欲的围城中,而无太多的人生境界追求。作为《金瓶梅》中的二号人物,李瓶儿的人生轨迹也是这种演绎。她的性格在嫁给西门庆前后有着不同的倾向性,这两种倾向性到底是背道而驰还是一脉相承,这需要从文本中仔细揣摩。
一、未被满足的情欲导向的“恶”
李瓶儿在嫁予西门庆之前经历了三段婚姻,但是无一例外,都没有获得自身情欲上的满足,未被满足的情欲引导李瓶儿一步步走向张扬人性的“恶”。
在梁府做妾时,李瓶儿过得就不算安稳。按照常理,男主人的妻妾都应该生活在内院之中,但由于蔡夫人善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于是她不得不在外边的书房住。她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老鼠一样在外书房里躲躲藏藏、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就入了娘家强势的主母眼里,而自己的夫主并没有足够的能力甚至是根本没有强烈的意愿去保护她,女人可以再换,但是如果惹怒了权势滔天的岳家那就得不偿失了。李瓶儿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像梁中书的其他妾室一样变成后花园里的一抔黄土,在这段畸形的婚姻关系里惶恐度日,时时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又何谈情欲的满足?可以说在梁中书府上为妾的这段经历是造成李瓶儿缺乏安全感、情感空虚,以至于后来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求满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来梁府突遭变故,李瓶儿“与养娘妈妈走上东京投亲”。到了东京之后她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被花太监之侄花子虚娶为正室。从小说叙说的蛛丝马迹来推测,李瓶儿其实是以与花子虚的婚姻为遮掩,与花太监作对食。或许在嫁进花家之前,正值好年华的李瓶儿对花子虚是抱有期待的,她也许还在欣悦自己可以迎来正常、安稳的生活,但是很快她就知道了她的丈夫不仅让她独守空房,在外飘风戏月,而且由于自身只能依靠花太监生存,便默许她落入了没有男性正常生理能力的公公手里。在这段屈辱的婚姻关系中,李瓶儿承受着精神压抑和身体摧残的双重戕害,渴求一个青春少妇正当的生理欲望,渴望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仍然只是她美好的梦。好不容易熬到花太监死了,花子虚依然眠花宿柳,“整三五夜不归家”,不理李瓶儿的寂寞孤冷。可以想见,李瓶儿在花家一直持续着情欲被极度压抑的生活状态。
直到此时,李瓶儿压抑的情欲一直在累积,还没有找到宣泄口。不过很快,她遇见了西门庆。一个人在无能为力的年纪缺失什么,在她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之后就会疯狂地追求什么以期加倍补偿自己。所以,在西门庆“安心设计,图谋这妇人”之后,李瓶儿怀着对之前两段婚姻的极大不满投入了西门庆的怀抱,并且视西门庆为此生最值得依靠、信赖的男人,视西门府为自己最后的港湾。于是,她开始放肆地释放自己的“恶”,在她与西门庆终成眷属的路上,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花子虚打了一场官司后,在一惊一气中害了一场伤寒。初时,李瓶儿还为他请太医,后来怕使钱,只挨着,就等着他死。如果说潘金莲是以暴力、血腥的方式杀死了武大郎,那么李瓶儿就是用一把杀人不沾血的软刀子结束了花子虚的性命。
花子虚死后,李瓶儿更是一门心思想着进西门府。可惜天不遂人愿,西门庆的亲家出事,他担心连累到己身,“把娶李瓶儿的勾当丢在九霄云外去了”。对李瓶儿“怀觊觎之心,已非一日”的蒋竹山乘虚而入,在他的挑拨与“一团谦恭”的形象的促使之下,实在是太想找个依靠的李瓶儿走进了她的第三段婚姻。但这段缘分终究还是因为她在情欲上的不得满足而惨淡结束。越是强烈的压抑就越是难以遏制,在西门庆手里经历过“狂风骤雨”的李瓶儿对蒋竹山的中看不中用“颇生憎恶”,极尽羞辱谩骂。蒋竹山因西门庆的报复被敲诈三十两银子,哀告李瓶儿帮他归还之后,“两个就开交了。临出门,妇人还使冯妈妈舀了一锡盆水,赶着泼去,说道:‘喜得冤家离眼前。’”在蒋竹山这里,李瓶儿依然因循着她的“恶”,哪怕蒋竹山对她言听计从,比之西门庆不失为过日子的好人选,但在这个人欲滔天的世道里,刚刚尝到甜头的李瓶儿不会为了蒋竹山带给她的家庭安全感而收束,她只会飞蛾扑火般地追求情欲的极致满足,尽管要付出从颐指气使的妻主沦为任人宰割的妾婢的代价。
二、情欲满足与母性关照导向的“善”
进入西门府后,随着宠爱与子嗣的傍身,李瓶儿逐渐收束了自己的恶,走上了一条“向善”之路。
由于之前与蒋竹山的婚姻,刚进西门府的李瓶儿的境遇是十分糟糕的。李瓶儿被西门庆空了三日房,她险些自缢,又吃了西门庆一顿鞭子。她还要面对吴月娘、潘金莲还有小玉等妻妾、奴仆的嘲讽戏侮与排挤,几乎是腹背受敌,所幸很快她就得到了西门庆的宠爱,也重新得到“药”的疗愈,再次满足甚至是沉溺于有着她心中理想的夫主形象的西门庆带给她的精神慰藉和生理慰藉,她不想失去这种尚算安稳的生活,更不想回到孤苦无依、颠沛流离的境地里去,她只能选择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她用她的钱财讨好吴月娘、潘金莲甚至是下人们,不争不夺。很快,她的转机出现了——官哥出生。
官哥的出生不仅使李瓶儿摆脱了无法融入西门府的窘境,成为西门府上可以和吴月娘平分秋色的妾室,还使李瓶儿与西门庆之间的情感发生极大变化。官哥把她和西门庆的生命连结起来,两人作为父亲和母亲共同孕育一个孩子,这种微妙的感觉将她与西门庆之间导向真正的夫妻之情。与其他妻妾对比,西门庆也的确只给予了李瓶儿些许真情,家里的妻妾们对西门庆都有过劝诫,但他只对李瓶儿的劝说耐心温和。其原因就是在面对李瓶儿时,他能体会到有人不觊觎他的金钱、单纯依恋着他的幸福。这份真情反馈到李瓶儿身上就几乎是专房独宠,对李瓶儿来说,在这个最初她希冀可以站稳脚跟的宅院里真真切切有了自己稳固的位置,也有了与她血缘相系的孩子和给予她独一无二关爱的丈夫,她如浮萍般的人生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在世俗的价值体系里,她已经获得了圆满,在她自己心中也获得了情欲的满足,既然如此,她又何必去争去抢?能够拥有在她眼中正常的夫妻生活,对她而言弥足珍贵。历经多次失败婚姻的李瓶儿在正常的婚姻状态下其人性中的光辉慢慢占据了她性格的全部,加上她身家富庶、教养得当,更使她成为有仁义、好性儿之人。对丈夫与儿子的关爱,对姐妹的关怀,对下人的照顾,都让她人性中的“善”大放异彩。
官哥的出生也意味着李瓶儿由一个女人成为一个母亲,从某种意义上去掉了她的某种女性性征。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之后,“母亲”这个身份就会成为她社会身份中最重要的一个,而在社会约定俗成的观念里,母亲就意味着一个非完整的个人,就应当牺牲自我主体性,母亲不应该有“我”,于是这种期待让李瓶儿逐渐折损了前期一直在追寻的自我。她的情感寄托也由于孩子的出生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母性的关照使身体情欲的满足渐渐退居其后。因此,虽然西门庆总往李瓶儿房中去,但是李瓶儿却经常将他推向潘金莲那里。一是由于李瓶儿要照看被潘金莲整得一直体弱多病的官哥,“孩子才好些儿,我心里不耐烦,往他五妈妈房里睡一夜罢”。二是向潘金莲告饶示弱,她可以把西门庆的宠爱让给潘金莲,只求潘金莲不要再折磨官哥。在西门庆和官哥之间,她选择官哥,甚至于她对西门庆的痴情也是由于官哥的出生而逐渐丰沛。在女性与母性之间,她选择母性,收束了自我对欲念的全部追求。李瓶儿从来不用官哥争宠,对她来说,官哥的平安长大高于一切。实际上官哥作为西门庆膝下唯一的男嗣,李瓶儿是可以凭着这张王牌在西门府中无往不利的,但是她一直都对周围所有人谦逊有礼,对潘金莲的恶意极尽忍耐,一直默默地养育自己的儿子,为了自己的孩子多次劝西门庆积德行善。母性将她改造成一个新人,但也正是这份母性戕害了她的性命。在孩子屡次受惊一命归西之后,她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完全沉浸在丧子的悲哀之中无法自拔,最终也追随儿子而去。
三、由“恶”向“善”的转变是断裂还是顺理成章
李瓶儿在进入西门府前后的性格反差一直是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嫁给西门庆之前,她伙同西门庆谋夺花子虚的家产、气死了花子虚,充分展露出她的“恶”,但在嫁入西门府之后,她处处忍让、事事谦恭,性格似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在笔者看来,李瓶儿的性格一以贯之的是以追求自身情欲满足为核心,这种急速的角色转变并不突兀,这是李瓶儿自己的生命选择,是她人生追求得到满足后的彰显。
与蒋竹山之间的纠葛是最能反映李瓶儿前期性格乃至完整性格的缩影。从花子虚到西门庆再到蒋竹山,李瓶儿一直追求的都是个体的情欲满足,当一个人阻挡了她寻求满足的脚步,她就会毫不犹豫地舍弃他。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体系,人格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由先天的本能、欲望所组成的能量系统,包括各种生理需要,只考虑自己的欲望是否得到满足,按照趋乐避苦的原则行事。在与花子虚、蒋竹山的关系之中,李瓶儿的“本我”层次占了上风,“本我”的欲望完全不受控制,在此时进一步逼仄“自我”。李瓶儿的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所以她努力寻求满足,在这条寻求个体欲望满足的路上,她无意识地使用了非道德的做法扫清障碍,但是“本我”本来就是无意识、非理性、非社会化、非道德的。这种无意识的追逐外化表现为世俗意义上的狠辣无情、恶毒刻薄。与此相反的是,西门庆和吴月娘在人后都夸李瓶儿是温厚性子,西门府上的仆人也都认为她从来都是好性儿,可见李瓶儿平日的行事作风甚佳。她与西门庆第一次偷情后就马上开始讨好他的妻妾,想着为吴月娘与潘金莲做鞋子,认潘金莲做姐姐,她从来没有对西门庆的妻妾也就是她的情敌们释放出一丝一毫的恶意,而是在她们面前频献殷勤、做小伏低,大事小事上出钱出力。一直以来,她对西门庆或者说对除了花子虚、蒋竹山之外的其他人柔情似水、温文尔雅,对花子虚、蒋竹山冷酷无情、刻薄狠毒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与李瓶儿的情欲联系非常紧密的男人不能使她的情欲得到满足。花子虚辜负了她,她投向有能力给予她情欲满足的西门庆,设计使花子虚失去一切含恨死去;西门庆因变故不顾她,她再次嫁给温和谦恭的蒋竹山,但是当蒋竹山无法满足她的胃口时,她当即毫不留情地舍弃蒋竹山,再次回到西门庆的身边。在《金瓶梅》中被着意刻写的潘金莲也是一个处于“本我”层次的女性,但较之于她,李瓶儿更为接近“自我”这个层次,因此潘金莲的性本能展现出更强的内驱力,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所谓的“恶”,以至于潘金莲最终沉沦在永不能满足的欲望里,而李瓶儿能够走上一条和她相反的回归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李瓶儿一开始并不爱西门庆,否则她就不会因为西门庆家中的变故和对欲望的追求迅速决定放弃西门庆、招赘蒋竹山,她后来多番思念西门庆实际上是思念西门庆带给她的官能快感。除此之外,正值盛年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性对长时间处在情感空虚之中的李瓶儿来说无疑是无比震撼且喜悦的,她在西门庆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魅力,得到的是情感层面的满足。因为花子虚,正值花期的她过得暮气沉沉,西门庆向她重新灌注了生命力,“医奴的药”很好地解释了一开始李瓶儿对西门庆的情感,她将西门庆视作她无趣、凄冷生命里的光亮。在爱上西门庆之前,李瓶儿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追求自我情欲满足为导向,她一心一意嫁给西门庆是因为他是治病的良药。
嫁给西门庆之后的行为变化也是李瓶儿进入西门府这个特殊环境的必然选择,从当家主母到第六房小妾,一进门就受到夫主的鞭打与羞辱,又有后院妻妾带给她的下马威和妒忌,李瓶儿不得不低头忍辱;由肉欲满足到专房独宠再到母凭子贵、妆奁富裕,李瓶儿又何必作如潘金莲之恶态?时、势、命、运,限制着李瓶儿;色、欲、情、宠,蒙昧着李瓶儿,使她陷入深渊而不能自拔,使她沉于孽海而难以自明。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官哥的降生,她真正爱上西门庆,将自己的一切包括儿子托付给这个不该托付的人之后,李瓶儿的悲剧结局开始徐徐展开。
李瓶儿的性格转变过程也恰恰是她人格完善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李瓶儿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之前的欲的、物的形象了,她开始有了人的伦理道德思维,她看见已经死去的花子虚,她觉得是自己罪孽深重害死了孩子,遭了恶报,在又悔又怕中香魂远逝。她那么不忍离开、那么委屈,可这个世界于她也实在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四、结语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作者早在李瓶儿刚与西门庆偷情时就已经预示了她的结局,她将自己的金簪儿送予西门庆,西门庆转头就交给了潘金莲,就如同李瓶儿将自己的人生交予西门庆,最后死在了以潘金莲为首的西门府妻妾们的步步紧逼和西门庆的放任之下,死在了那个花园里,死在了那样荒唐的时代里。
《金瓶梅》的作者细致地描画了人欲横流、冷漠炎凉的世界,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出腐朽黑暗。张竹坡在《金瓶梅寓意说》中谈道:“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物同声一哭。”财色皆罪,作者想要展现的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李瓶儿,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美的世界里,做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最终只能“瓶中水尽”,为这个荒诞无序的社会殉葬,复归苍凉和寂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