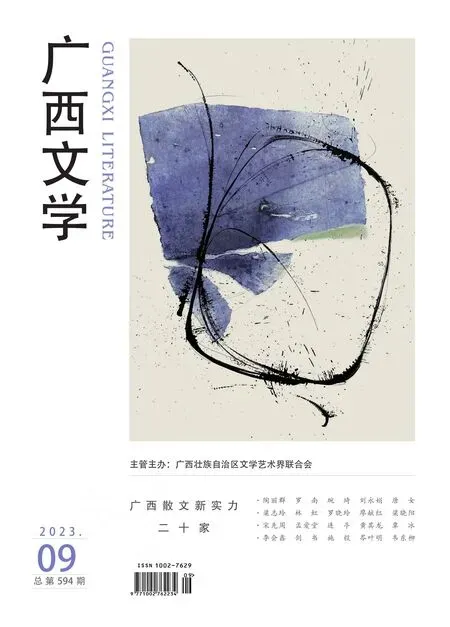等风来(外一篇)
2023-10-22孟爱堂
孟爱堂
在山之巅,青草地上,表演师穿着飞行装置,像一只大鸟,张开双臂,等风,来一场天与地的热烈拥抱。
风不来。风向标矗立在半空,像一只寂寞的手。他温柔地等,知道风终将要来。大风起兮云飞扬。等大风起,云飞,他亦飞。
风始终不来。他躬着腰,保持起飞的姿势,坚毅地等。那个装置一定很重,我看见他的肩膀抖了抖,我的肩膀也跟着抖了抖。
阳光烈烈地从表演师头顶上刺过来,我眼前一片电光石火。金光闪闪中,一个身影向我走来。他身材高大,穿蓑衣,戴斗笠,站在高高的晒谷楼上。黑黑的蓑衣像横空里冲出来的翅膀,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立在他宽厚的肩膀上。他看见我,宽大的嘴往两边咧开,亮堂堂的声音像一口洪钟朝我敲来:等大风来,我就飞起来喽。
这个人,是我的满爷。我爷爷最小的胞弟。
我对我爷爷没有任何印象。我对我爷爷奶奶都没有任何印象。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奶奶更是着急,竟然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们好像约好了赶着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硬是不让我知道,不让我看见。以至于爷爷奶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符号。他们有时在过年时烟雾缭绕的神龛上,有时在清明节杂草丛生的黄土中。他们在父母的嘴里翻滚,在大姑小姑的眼神里绵延,就是没有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面前过一次。直到满爷、满奶奶从遥远的贵州老家搬到我家旁边居住时,我才知道我爷爷长成什么样子。至此,满爷、满奶奶终于代替了我的爷爷奶奶。
满爷说要飞的时候,大风忽起。他迅速张开翅膀,从高高的晒楼上往下飞,一瞬间就“飞”到我跟前。我都还没看清他飞翔的样子,他粗糙的大手就在我蓬乱的头发上揉了揉,然后盯着我橘子皮一样黄黄的眼球说:等我们糖糖眼睛变黑了,也可以飞哩。
那个时候,我的双眼并不是黑白分明,而是所有黑色的地方依然黑着,所有该白的地方却没有白。它们像变魔术一样,在一个清清的早晨,把所有该白的地方全部换成了黄澄澄的颜色。很漂亮。我很喜欢。这是别人没有的东西。可我的父母却非常害怕,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亮晶晶黄灿灿的眼睛。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充满急躁和担心。他们惊慌失措,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们十岁的三女儿,害怕她忽然变成一个神秘的小妖,风一样飞走。
是满爷的手,救了这个随时会飞走的小妖。这只手,拨开深山里尖利的荆棘,在潮湿的泥土里、清冽的寒水中、坚硬的石缝间,抓来一样样植物,或者动物。他把它们晒干、捣碎,倒入黑黑的陶罐,用大火、小火煮了半天,才滤出一碗臭烘烘、黑幽幽的水,哄我捏着鼻子喝下去。
正是这一碗碗墨汁一样的水,把我的眼睛一天一天扳回原来的样子,也把我混沌的脑袋一天天拉回人间。因此,当我在逐渐清醒的过程中,听到满爷说他要飞,竟深信不疑。
在十岁小女孩的眼里,满爷就是神仙。他会在急冲冲的河水里造我们从来没见过的水车,让河里的水在一个个圆滚滚的竹筒里三百六十度飞一圈,然后倒入水渠,晕晕忽忽地奔向干枯的田地。他还会用稻草编柔软的草鞋,走起路来,脚底下散发出香喷喷的新鲜谷子的味道。会吹木叶,引来无数的鸟儿围在他身边叽叽喳喳地歌唱。会吹唢呐,方圆百里,哪里有婚丧嫁娶,哪里就有他的唢呐在如泣如诉。最厉害的是,他竟然会“魔法”,可以把我的眼睛由黄变白。
满爷从晒楼上飞下来的那一天,他正要赶着在大雨来临之前去检修水车。见我不去上学,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蹲在墙角,便纵身一飞。看到我笑了,他开心地牵我的手一起去看他的水车。那天,他走路有点特别,腿一瘸一拐的。
风把水车吹得屁颠屁颠地转。风大,水车滴溜溜转得飞快。风小,水车慢悠悠地摇啊摇。
满爷围着他的水车转了一圈又一圈。忽然大声对我说了一句:你们女娃子就是风哩。然后又说了一句:我们父母就是水车哩。
那时候我还不懂,但我记住了女娃子是风。满爷的话,我深信不疑。
从那时起,我便以为,女人如风。
有时候,微风拂面,让人心旷神怡。有时候,狂风咆哮,令人胆战心惊。但风不论怎样吹,总有宽阔的天地将它围住,有坚硬的东西挡住它,柔软的东西缠绕它,它终究不能撕开一角天地,撞将出去,自由自在、无法无天地乱吹。
后来,读了《红楼梦》,看到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才知道,女人亦如水。
这样看来,女人既如风又似水。一个女人就是一部风水。好的女人就是好的风水。
满爷一定也把她唯一的女儿当成最好的风水吧。在那个偏僻的山沟沟,他推脱了无数上门说亲的媒婆,硬是摆脱了村里从小就定娃娃亲和不让女娃子上学的传统,把花一样的女儿,我的花姑姑送上了学堂。那时候,满爷是不是也期待她的女儿像风一样,来去自由,人生自主?
满奶奶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满爷一个人待在村里的老屋。傍晚,他常常独自坐在家门口,把目光从村头拉到村尾,再从村尾扯回村头,仿佛要在村里拉出一个人来。村庄这几年来,像一张撕裂的画,东掉一角,西落一块。先是表姐家搬出去了,搬到几公里外离新修的通乡水泥路很近的田边。跟着,几户人家也搬走了。我家最终也在父亲的艰难同意下搬走,只有满爷家孤零零地留在村尾。
工作二十年来,我尽管离开了家,但从未曾离开家乡。家乡这条美丽的红水河,常常让我无端升起一种幸福感和优越感。如今的红水河,因为龙滩大坝的下闸蓄水,龙滩天湖的宽大包容,沉淀了红褐色的泥沙,变清变亮变绿了,人们记忆中那条红褐色的“龙”,那条在暴风雨里轰隆隆地冲下一根根木头、一棵棵大树,或者一头头尚未来得及逃跑的猪的河流已难以重现,红水河变成了绿水河,变成一条绿色的丝带。这条绿丝带温暖了多少颗冰冷的心啊。它抚平了这条河流曾经制造的无数个急流、险滩、漩涡,阻止了无数个悲伤故事的发生,以最柔软最温顺的姿态袒露在人们面前。
我虽然常常怀念红水河曾带来的惊喜和震撼,但更喜欢绿水河现在留给我的宁静和柔美。它翡翠般的透亮,仿佛可以让人洗尽铅华,只留一个干净的灵魂。
谁不想拥有一个干净的地方,用来安放一颗纯粹的灵魂呢。所以那些可以离开家乡、远离村庄的机会,我统统没有抓住。我还是那么喜欢看红水河,看我的村庄、我的娘。
每次回娘家,我都要去看老屋,看满爷。
那天,远远看到从老屋的窗口射出灯光时,那些潜伏在心底深处的童年记忆潮水般向我扑来。哭声、笑声、叫骂声,它们清晰而热烈地穿越沉寂的黑夜,滚滚而来。是谁还在这苍凉的老屋里守着日月星辰?
进屋,入座,喝一杯暖茶。才知道原来老屋一直有人住着。尽管它已残缺不全,陈旧而狭小,但还能为人遮风挡雨,屋里的灯光还那么温暖,让我心里宽慰不少。
入住的是远房表妹和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两岁多,小女儿还在月子里。此刻,她们像两只温存的小猫,偎依在母亲的身边,温柔而安静。小女儿像一只刚破茧的幼虫,柔软、滑嫩,她新鲜的肌肤在白炽灯光的照映下,圣洁而光亮。
她还在月子里!那么门前的大红灯笼呢,为何没有高高挂起?
在老家,一直流传这样一个传统:哪户人家的女人要是新生了儿女,月子里,屋前都要挂几盏红灯笼。还要在大门口插上红色或黄色的小旗子。红色代表男孩,黄色代表女孩。这样路过的人看见红色小旗子就知道这家人生了男孩,看见黄色的就知道是生了女孩。红灯笼在红色或黄色的旗子上飞呀飞,像一只只燃烧的火鸟。哪家门前的灯笼越大越多,就意味着这家人越高兴越富有。有时候,新生的孩子特别多,整个村庄一片火鸟。它们从这家飞到那家,从这个屋前飞到那个屋前。寂静的夜空里,灯火通明、红红火火,整个村庄都在回荡着火鸟明亮的欢唱。
等到孩子满月那天,孩子的外婆、舅妈、姑姑等女人们就会给外孙(甥)送来花背带,还有甜酒、花糯饭、鸡鸭等。送背带是布依族一个重要的习俗。花背带是孩子的外婆亲手绣制的。布依族姑娘从十二三岁起便开始跟母亲学习蜡染。她们白天上山劳动,晚上加班纺织。把蜜蜡加热熔为蜡汁,用三角形的铜制蜡刀蘸蜡汁,在自织的白布上精心描绘各种漂亮的图案,再放入蓝靛缸中渍染成蓝色或浅蓝色,最后将布入锅煮掉蜜蜡,捞出后到河水中反复荡涤,晾干,成为独具特色的染布。染布制成后,开始裁剪背带。布依族妇女,把绣制背带看得格外重要。她们对背带的选择与构思十分慎重,非常讲求精巧、工整、对称。绣一幅五彩斑斓的背带,是每一个当母亲、当外婆的布依族妇女最重要、最得意的技艺。她们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策划、构思后,才一针一线绣制。她们绣出各种飞禽走兽、花草鱼虫、湖光山色。然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和三姑六婆们浩浩荡荡地把它送到外孙家,第一时间用新制的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整个村庄的女人们于是便围着背带左瞧右看,啧啧称赞。外婆成了当天最威风的女王,最尊贵的客人。
可此时,我家破败的老屋前,清静、冷寂。它们在空落落的村庄里,显得那样落寞、悲凉。
后来问了母亲,才知道表妹嫁的是一户三代单传的人家。表妹连生了两个女儿,怀三胎的时候,她们不敢回家。那时候,三孩还没有全面放开,她带着二女儿和婆婆东躲西藏,跋山涉水,从遥远的老家来到我家老屋待产。不知道表妹挺着大肚子东躲西藏的时候,步履如何艰难,心情如何沉重。她穿过苍凉的大山,蹚过清冽的河水,胆战心惊地走向她的未来。
表妹分娩的时候,正是腊月初八的夜晚。老村庄里唯一的人家,我的满爷正在煮腊八粥。腊八粥浓烈而香甜的味道绕着村庄到处跑。村子上空弥漫着浓浓的香甜。表妹闻到那个香味时,肚子一阵翻滚、搅动,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流和疼痛向她袭来。
她知道,肚子里的小东西怕是闻到腊八粥的香味,要出来了。她仿佛看到,一只火红的飞鸟正从老屋的墙角飞升起来,它清脆的鸣叫划破了香甜而颤抖的夜空。
孩子呱呱坠地的时候,婆婆愤怒而悲伤。“又是一个赔钱货!”她用力拍了一下床头,丢下一句话,转身走出门外。
表妹看到,那只火红的飞鸟忽然变成一只黑鸟,它伸出尖利的爪子,凶猛地扑向自己。
表妹哭喊着伸出双手颤颤地掐着黑鸟的脖子。
“你去死吧,去死吧!”她双手触摸到新生女儿的脖子。那脖子像一朵棉花一样柔软和细小。仿佛她稍一用力,就会把它捏断或揉碎。这样想着的时候,她颤抖的手加了一把劲,孩子的哭声猛然提高了一下,惊得她快速撒开双手。
“要动手就快点。”婆婆的声音从门外飘进来,硬邦邦的,像一块铁。
表妹惨白的双手再次伸向女儿的脖子。那脖子那么精致,那么脆弱,正随着哭声微微地鼓动着。一阵暖流传到表妹冰凉的手心,她的手僵硬了,不听使唤地颤抖。
“快点!”婆婆厉声催促。
表妹闭了闭眼睛,双手在细弱的脖子上颤颤握住。由于颤抖,那力道便紧一阵松一阵,那哭声便也高一阵低一阵,像一条条鞭子抽在心上。
“用力!”婆婆的声音冷漠而凄凉。
表妹哀号一声,握住柔嫩脖子的双手筛糠似的发抖。孩子的哭声猛然提高了起来。仿佛过了几个世纪。那哭声渐渐微弱。有一下,没一下。没一下,有一下。不久便沉寂下来。
彼时,北风呼啸。
我神一样的满爷,怀抱花姑姑小时候用过的背带,不顾族规里男人不能进产房的忌讳,一脚踹开表妹的房门,用绣满花儿的背带,轻轻裹住女娃的身子,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女娃身上的背带,像一面坚韧的墙,将她紧紧围住。墙上,桃花殷红,李花白。一轮新鲜的太阳,在万花丛中冉冉升起。
满爷扯开嗓子对着表妹和她婆婆一顿臭骂。最后,满爷哽咽的声音轻轻飘荡在桃花上:女娃子是风哩。
今年三月,桃花开得最艳的时候,表妹的大女儿,开着一辆宝马,带着她奶奶、妈妈和小妹从遥远的贵州,顺着红水河畔,来看满爷。
满爷老了,他现在需要戴厚厚的老花镜,才能看清是否有风从村口吹来。那天,他照例坐在家门口,刚把目光的丝线拉到村头,这根线就远远牵回了四个女人。四个女人像风一样走到满爷的面前,一字排开,深深地鞠了个躬。最老的女人哽咽着喊了声“叔”就再也说不出话,只是紧紧地握着满爷的双手。最小的女孩,把抱着的花背带轻轻放到满爷的怀里,然后跪下,磕头,用百灵鸟一样鲜亮的声音喊:太爷好!
花背带被整整齐齐地叠好,两只长长的袖带环绕着紧紧裹住背带面,像抱着一个婴儿,静静地躺在满爷怀里。满爷伸出枯瘦而颤抖的手,一遍遍来回抚摸着背带上的桃花。它们依然像十年前一样鲜艳而饱满,柔软的花瓣在满爷粗硬的手指下静静开放。
如果风知道,满爷现在像一口破旧的老钟,每天在时间的褶皱里摇摇摆摆,思女成疾,病痛交加,它会不会飞呀飞,飞到遥远的城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一把揪住我的花姑姑,把她拖到我满爷的跟前,让她看一看她老父亲满头的白发,摸一摸他老牛一样粗糙的皮肤,唤一声:爹,我回来了。
那时候,满爷浑浊的眼睛才会变得明亮起来。
可是风不知道。它只知道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吹来了燕子,吹醒了青蛙。风不知道我的花姑姑在哪里。
满爷也不知道花姑姑在哪里。她有十多年没有出现在村子里了。哪怕在她母亲,我满奶奶去世的时候,她也没有出现过。
有人曾看见她在县城的车站里,一手牵着一个孩子,登上了回村里的汽车。她在车子最后的座位上偷偷抹眼泪。后来,她们在半路下了车,从此不再出现。
没有人知道花姑姑为什么来到半路又走了。狐死首丘,更何况是自己最亲的人离开人世。她开始在亲人们的眼里、嘴里变得不孝、绝情、冷漠。她像一只渐行渐远的白眼狼,悄无声息地离开村庄,离开亲人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有人说她做了传销正被禁锢。有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还有人说她去了大城市,已看不起这个贫瘠的村庄。
满爷不信他的花姑娘是一个冷漠的人。她一定是遇到生命中摆脱不了的劫难,在度着,不让家人跟着受牵连哩。满爷坚信,万物皆有因缘,何况女儿和他流着相同的血。只要他每天坚持做一件善事,花姑娘的劫难就会减少一点。当劫难过去,她一定会回来。
满爷说女娃子是风哩。风儿轻轻吹,水车慢慢摇。满爷这辆老车,会摇到花姑姑回来的那天吗?
十多年过去了。满爷越发苍老,他仍然像一个信徒,每天做一件善事。若是哪天实在没有善事可做,他便拿起祖传的经书,念一段佛经。满爷悲怆的声音随风飞荡在幽暗的老屋,让我沉迷。他还是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门口,把目光拉成一条丝线,像一个等风的表演师。
空房子
一
车子驶入高速路收费站,结束了五六个小时的狂奔,向城市滑进。收费站前,挤满了不同颜色款式各异的车子,它们的喉咙无一例外地发出低沉的喘息,像等待跃入大海的鲤鱼,等待龙门的打开。这样的等待在周末和节假日尤为漫长,每一分钟都是煎熬。明明城市就在眼前,你却无法逾越前面的阻碍,走近它。车子这时候完全失去了它奔放的魅力,垂头丧气地跟在一条条“鱼”后面,等待放行,奔向城市各处。
先生这个时候急躁不安。他在路上冲锋陷阵了五六个小时,眼看就要拿下阵地,可一声令下,他不得不停下所有的奔突,像一匹被忽然勒住的野马,愤怒而茫然,不知道这茫茫车海,什么时候才像一把扇子,各自散开。
我却是轻松而愉快的。因为城市就在眼前,无论等得久或不久,终将都会到达。早一点或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一路的风驰电掣,窗外一闪而过的人、车、树、房子、蓝天、白云,远处的山和田野,甚至诗和远方,这时候都慢下来,像一股温热的粥,慢慢地抚顺、填满一路上痉挛而虚空的胃。只要胃得到放松,我的眼里就会有光。那光像两把刷子,在扑面而来成千上万个火柴盒般堆砌起来的房子上来回摩擦。那些房子有一样的眉眼,一样的妆容。它们骄傲而冷漠,像训练有素的犬,忠诚而坚韧地等候着它们的主人。
看中哪一套?买!
一定是我眼里的光太过明亮和锋利,它们过关斩将,穿透一层层坚硬的墙后,又一路杀回我的眼里,以至于先生明显地感受到了那道光。他对着那道光,像一个粗鲁的暴发户,右手用力往我肩上一拍,拍出了五百万的豪迈。
我把两把刷子收回来,拍在他脸上,笑了笑说,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谁还不是个爱做梦的人。
此时此刻,我的梦翻山越岭,千回百转,回到了十八年前年轻的春天里。
年轻真好。年轻可以随意地唱《大花轿》,可以抱一抱月亮,抱花轿,抱妹。
在这样美好的春天里,我们一遍遍地寻找着我们的梦。一套房子,便是我们最幸福的梦。
是哪位先人最先提出了门当户对?那个活得像水晶一样通透的女子,或者汉子,曾在阳光温软的春天里细数过哪家门前的“门当”和“户对”吧,精雕细刻的石鼓和门簪,精致而神秘。花虫鸟兽人,山川江河湖。金光闪闪的“寿”字,运日月之精华,滋养万物于坚韧的石头之中。女子或者汉子也曾抚石探月,深究这主人的家道吧。或经商世家,或官宦府第,它们在他(她)们柔软的目光中,一半是柴米油盐、绫罗绸缎,一半是痴男怨女、花前月下。
我和先生竟也逃不掉门当户对的宿命。我们两手空空。我们背后家庭的两手亦是空空。我们最幸福的梦那样艰难而空洞。
如果幸福有颜色,在我心里它一定是青的、灰的、白的。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这一直是我梦中生活的样子。门前有水,屋后有林,霁潭发发,春草呦呦。我可以在檐下煮酒,也可以抱着竹篾,铺设在幽静的树林间,用瓜果呼唤林中的鸟雀。河面上的莲花像摇动的白色羽毛,篱笆上延伸着青翠的藤蔓。最好还养有一只猫,一只眼里碧波荡漾的鹿。
然而生活却给了我黑色的幸福,那些日子里,为了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白天拼命工作,晚上拼命找房。我们像两条黑色的飞鱼,游荡在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县城年轻而苍白。此刻,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型水电站正在县城上游波涛汹涌的红水河上修建。猛然间,县城像一个张开大嘴的口袋,不断地往自己狭小却深幽的肚子里塞满各种东西。挖掘机、压路机、水泥罐车、大型拖车;粗大而坚硬的钢管,白色粉末和石头;大腹便便的男人,美丽而神秘的女人。县城忽然像个风情万种的产妇,生出各种我们见过或没见过、想到或想不到的事物。
街上一天比一天躁动,肩膀擦着肩膀,脚挨着脚。昏暗而暧昧的灯光在这个角落那个角落妖娆地吐露暗香。我看见那个美丽的女子,永远记得她。那时候,街上忽然多出来的女人,大都浓妆艳抹、唇红齿白。只有她白皙而清纯,她来到我的窗口,递过一沓厚厚的钞票,轻启朱唇,说一句轻飘飘的“喏,存钱”。
她的钱比别的女人都多,一百、五十、二十、十块的都有。我每数一张钱,似乎都有一个男人从我眼前飘过。他们都有一双贪婪而绝望的眼。女人很年轻,听说刚大学毕业,从遥远的江南涉水而来。大家都知道她租住在这个县城最好的酒店里,做一些隐秘的事。
我也是刚大学毕业,刚到这个银行做营业员。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在我像风一样撞击到她的哭泣之后,我忽然对她有了不一样的情感。那时候,她正蹲在银行自动取款机的窗口前,双手掩面。哭泣从她指缝间流出,被风切割成一片一片:娘,你、千万、要挺住,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等我、攒够、了钱,带你、看最、好的医生,住、村里、最、好的、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只知道她离开了这个县城,窗口前再也没有那句温软的话“喏,存钱”。有时候,看到漂亮的女人来存钱,我竟有些恍惚,忽然怀念起她来,我一直在想,不知道她后来攒够钱没有,她的娘是否看上医生,住上村里最好的房子。我真后悔,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没有走过去轻轻地拥抱她一次。
县城不会忧伤一个人的离去或到来,它不断在膨胀,空气黏稠而热烈。新开发的七区八区九区,新鲜的泥土被翻垦出来,如同埋藏在地底深处的酒坛被打开,让人垂涎欲滴。那些最先嗅到香味的开发商、土豪、大款,目光热切地盯着那一块块土地,把它们盯成一栋栋整齐划一的楼房。
我穿梭在这些房子里,像穿梭在一个冰冷而坚硬的梦里。这些土地和房子都太贵了,我不吃不喝攒个十年二十年都望房兴叹。罢了,租别人的房子,过自己的日子。
房子小而旧,楼下做米粉店。每天早早,米粉的香辣酸甜,各种味道像一条河流,不断奔向我的鼻子,拽着我的胳膊喊:起来,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早起来,到楼下唆完一碗粉,再心满意足地上楼睡回笼觉。那些迷蒙的早晨,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脑海里总是回荡着这个县城最诙谐的歌谣:小小天峨县,三家米粉店,××吼老婆,全城听得见。
米粉让我油腻而肥胖,我的身体里血管里毛孔里每天都游荡着一种叫粉的分子,赶也赶不走。
买房子再次成为强烈的梦。
二十年前,城镇化建设正在迈开大步伐,县城周边新开挖的土地被分成一块块,一个个小区。土地开发商将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或转让,或搞房地产开发。有钱人纷纷买地建房,或囤地转让。我们在七八九几个区东奔西突,终于在九区路边的一桩地上达成共识:几个人合伙共买一块地。一家建一层,费用少,划算。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一手交钱,一手交地。因为钱未凑够,我们必须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呼朋唤友,呼唤那些花花绿绿的钱。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第二天,当我们心潮澎湃提着一袋现金,踏上那块曼妙的土地时,那个头天满口答应转让土地给我们的老妇,却翻着白眼说:不好意思,那块地亲戚抢着要了,他们多付了两万块钱。
我们澎湃的心一瞬间仿佛从天堂坠入地狱。
关于房子的梦想,这般难。
两年后,我终于贷款在这个县城最偏僻最幽静的学校里转手购了一套集资房。尽管比别人多付了一倍的钱,但终究是圆了那个幸福的梦。
房子背后,是一片悠远绵长的山。山不高,但林木丰茂,花果灿烂,连接着这个县城最原始、最具魅力的森林。房前远处有水,红水河像一匹绿色的绸缎穿越县城。尽管离梦中的样子相差甚远,但总算是门前有水、屋后有林,我很满意。
我们不断地往自己的房子里装东西。先是锅碗瓢盆、木水火土。后来是我们的女儿。再后来,多了一个小子。在此期间,我从未停止过往里面装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我如痴如醉地书写父亲挂在堂屋的唢呐、藏在地底下的酒、飞在山谷的牛群。写他梦中飞来的子孙,他在深夜里火塘边孤独地歌唱,他与自己亲生儿子悲伤而漫长的“战争”。
我们的房子因此变得丰满而沉甸。
二
我借十五万给你,买!
她说得那样轻而易举而又斩钉截铁,仿佛那十五万不是钱,而是一坨屎。嘿,金钱如粪土。
我在心里爆了一句粗口。当然我骂的不是她,而是为什么一样的年纪,她有十五万,而我连十五千、十五百都难拿得出手的悲哀。
当悲哀还在蔓延,另一闺蜜马上应和:我也可以借给你七八万,凑凑就够首付了。
疫情期间,房价低迷,赶紧下手。她们的脸红扑扑的,眼睛闪亮,十二字方针快狠准。仿佛要买房的不是我,而是她们自己。
此时,新冠病毒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肆虐袭击,省城的房价一再跌落。身边的朋友、同事纷纷前往买房。
忍不住内心的惊异,我颤颤地问:你们去哪里搞到那么多钱?
我妈的。她们笑意盈盈。
不孝女,老娘的钱你们也敢动。我在心里又骂了一句。我知道她们的娘已并不年轻,身体也不再硬朗,她们还指望着那些钱养老呢。
催促再三,几番思量。最终我坦然接受了她们的建议。困难会有,希望也会有。
你们不怕我还不起?我黑着脸问。
等高速路过你家杉木地,领得补偿款了再还。她们笑嘻嘻,仿佛高速路过不过我家杉木地,由她们说了算。
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才让我在今生遇到你们啊。来生我要做一棵树,就站在你们家门前。风来了,我就和风搏斗,让它不要去撕扯你们挂在窗前的长裙。雨来了,我就和雨商量,叫它轻轻抹上夜晚的睫毛,让你们在叮咚的乐声中悄然入梦。或者做一匹马,让你们策马奔腾,“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我满心感动,却莫名想起六岁那年,在村头那间一二三年级混杂在一起的教室里,十几个孩子用粗粝的声音一本正经地读,或者唱:
农民把玉米种到地里
到了秋天收了很多玉米
农民把花生种到地里
到了秋天收了很多花生
小猫看见了
把小鱼种到地里
他想收很多的小鱼呢
我忽然想起这些,主要是想起那只猫。它顶着一身黄灿灿油亮亮的毛发,迈着欢快的猫步,跳跃在温暖而湿润的土地上。此刻它多兴奋,多快乐啊。想想就是多么幸福的事儿。一条条大鱼从地里被翻出来,滑溜溜、肥嘟嘟的。口水都被它们勾去了魂,哗啦啦地从嘴里流出来,像一条甜蜜的河流。
我就是那只猫吧。我们在老家高高的山脚种下一排排幼小的杉树,用潮湿的泥土覆盖它们柔嫩的根须,在它们四周撒下饱满圆润的肥料。于是我就像那只猫,天天想着那小树苗变成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杉树。它们的身影飘荡在清露欲滴的春天里,在微风无声的呼吸间,在蝼蚁疯狂地啃啮中,甚至在一片火红的钞票里。杉树无所不在。
后来,我确实变成了那只猫。我们的杉树像一条条埋在地里的鱼,长着长着就不见了。它们去了哪里,猫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不管杉树是否变成钞票,反正它已经与省城的某个房子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比第一次买房还要艰难,我们最终还是贷款在省城买了一套房子。房子小而精,书房漂亮,像一首诗,是我喜欢的样子。也是我忧伤的样子。往后余生,我要用三十年的肩膀来扛着一块“百万负翁”的牌子。牌子很重,但因为有了诗和远方,我心依然欢喜。
三
去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坐车近七个小时,前往一个偏远的大城市。住在这个城市温馨的酒店,我却备感孤独。也许是对这个城市太陌生了。那一夜,我像一只孤独的羊,在酒店后面的湖畔默默游荡。酒店后面是一片沙滩,绵长的沙滩上,却只有一家人在白白的月光下游玩。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在一架秋千上荡啊荡,月光也就亮亮地在他身上荡啊荡。他的笑声太过明亮和清朗,以至于我不得不把目光从手机屏幕上拉回来,再深深地投到他脸上。一时间,我的心不由得痉挛起来。这多么像阿语啊!我不得不用手紧紧捂住怦怦跳的心。我真害怕它会忍不住跳出来,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一遍遍呼唤:阿语,阿语。
我知道这不是阿语。阿语怎么会在地上呢。他应该飞在高高的月亮之上。他的眼角膜此刻也许正紧贴在一双温润如玉的眼睛上,这双眼睛原本迷蒙而绝望,而他的心脏正跳跃在一个温暖的身体里。
我真想拍一拍他的面容,他琅琅的笑声,把他传给远在县里的阿语母亲。她一定在无数个绵长的夜晚,深深地思念着那个乖巧得令人心疼的儿子。她的悲伤像一条幽深的河流。河水逆流而上,忧伤而绝望地冲向天堂。
我后来没有拍成照,只是把目光艰难地搬到了湖的对岸。彼岸,灯火微阑。黏稠的空气被一声声男高音撕裂成一片片。是谁在不停地重复着腾格尔的歌: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
天堂一定很美。那里没有车来车往。阿语可以自由地飞到街道对面,不用担心忽然飞驰而来的车辆。他的娘也不用心痛得无法呼吸。这样想着,刚抬头向天上望去,我的目光便被一排排高大漂亮的房子拦腰砍断。
多么美好的江景房啊!我不由一阵惊叹。但仅仅是三秒钟的美好,内心却莫名空落起来。那么多的房子,那么多的窗户,一排排、一层层,密密麻麻,像一堆叠在一起的蚂蚁。然而,有灯光亮起的窗户却那么少。稀稀拉拉,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仿佛浩瀚天空里的几颗星子,孤独而冷漠地发出颤巍巍的光。
大城市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空房子啊!
我刚在省城买的房子,还有很多我的闺蜜、朋友、同事在省城的房子,它们此刻也是黑灯瞎火的吧。它们在自己空旷的肚子里装满了城市的声音、气味,装满各种喧嚣和繁杂。然而,它们却那样孤独和寂寞。像一个留守的老人,眼巴巴地盼。
愧疚一下子就占满我整个身心,就像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好看的新娘,却把她晾在一边,在偶然想起的时候,才去温存一番。大多时候,这个美丽的新娘要独守空房,独自面对漫漫长夜,而我们却需要花费大半辈子的辛劳,来守住一个一年才见几次的“新娘”。常常有人会问我:值得吗?
我没有想过值不值得。很多事情,值或不值,不是可以用辛不辛苦、累或不累就能衡量得出来的。
房子装修的时候,先生和我争论,他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房间里能够铺上更多的床。他说在农村的困难亲戚多,要让他们到省城来的时候有地方睡。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一幅画。画里,一个骨瘦嶙峋的老人,坐在浣花溪边,对着滚滚而去的江水,沉痛地吟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悲痛的声音穿越历史的河流,汹涌地向我奔来。我心一痛,便和先生一起在房间里安上高低床。
住进房子那天,隔壁大爷大妈也扛着大包小包进门。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寒暄过后,才知道他们是东北来的候鸟人。家乡太冷了,羸弱的身体已抵不过寒风,他们要在温暖如春的绿城住到过年再回去。我便知道,他们的房子,很长的时间里,也是空的。
城里的房子和阿语家的房子靠近,有时候我会和阿语的母亲香一起去看我们的房子。
我永远无法忘记,香说,阿语出事前几天,在新房子住的样子。阿语太快乐了。他的笑声贴满房里的每个角落。我永远无法抹去。香的声音缓缓地抖动,像黑暗里的一条波浪。
香现在心很空很空,很想很想阿语的时候,就去看看那个房子,哪怕只看几眼。每一眼,阿语都会在目光深处亮晶晶地对着她笑,甜甜地喊她妈妈。香的心里这时才觉得是满的、实的,才找到了停靠的地方。
阿语,你长高些了吗?香轻轻地在空荡的房间里抱了抱。
每次回县城的时候,香都要对着空房子轻轻说:阿语再见,妈妈下次再来看你。她把手围成一圈,在空气里掂了掂。阿语,你还是那么轻,那么轻。香叹息一声,恋恋不舍地关上房门。楼梯里,久久回荡着一串缓慢而杂乱的脚步声。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为了救回阿语,香花了很多钱,欠了很大一笔债。阿语离开后,家人想把房子卖掉还债。香痛哭,坚决不让。
哪怕生活再苦再难,我也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守住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并不是空的。香有一天对我说。
我一时怔住,心却一点一点温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