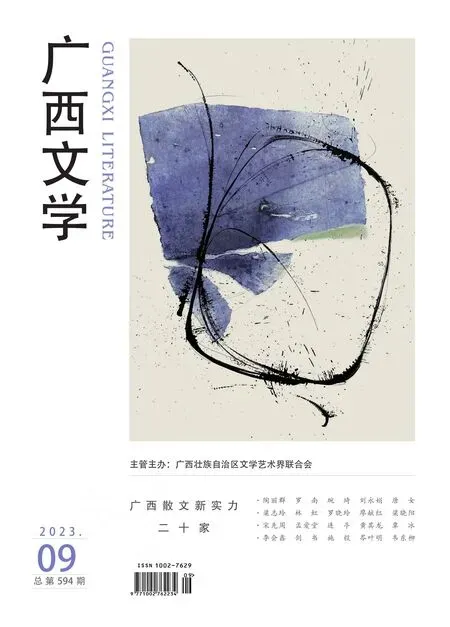水声喧哗
2023-10-22剑书
剑 书
一
一场下在童年深处的暴雨,牵引我一头闯入河流的疆界。
那场暴雨自桂西北山麓撕扯黑云纷纷扬扬而来,大风呼啸,草木倾身摇晃,老宅对面的红旗山乱云涌动。顷刻间,雨点啪啪打到屋瓦和泥地上,水花连同尘土飞溅,温热而淡香的草木味、泥巴味升腾弥漫。
那时,我还没上学。站在石墙黑瓦的老宅前,天空的锅底被砸破,雨打额头,飞奔尖叫跑到野马河上游,那块往常被我当作滑滑梯的巨石已经有浑黄的浊水流淌。兴冲冲脱下衣裤一把丢到草丛里,光溜溜从巨石上头滑到下头,又从下头爬到上头,反复光屁股哧溜滑下。尖声怪叫是此时野性的狂欢,刺破四面高山对一个孩童的禁锢。
流水越来越大,四野昏暗。一道雷电劈空打下来,白光闪耀撕裂天空,恐惧像只沉睡惊醒的猫一跃而起,赶紧手忙脚乱爬上高过人头的土坎。顷刻间,山洪自高处咆哮奔涌而下,石头翻滚撞击发出怪响,仿佛千百只虎豹齐头并进杀出密林。不禁颤抖后怕起来,要是还没离开那块光滑的巨石,山洪肯定把我卷下去,等待我的只会是身首异地断臂残肢。
目击——桂西北的野马河赠予我具备在场性质的语词。雨中,我目击幸运女神折断一根树杈抽打乌云,用电闪雷鸣将我赶出山洪暴发的河流。我全身而退,毫发无损,但也命悬一线,凶险异常。
上小学后,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吱呀推开老宅木门,走出桂西北一个叫巴额的小寨子。有时清冷的月牙挂在山头,镰刀一样收割残夜的尾巴。有时天地黑得认不出爹娘,只能一步紧挨一步往前走。
走着走着,惊动草丛中潜伏的虫类和停落灌木丛的小鸟。蟋蟀惊慌弹跳,螳螂昂头怒视,草丛沙沙作响。强壮的鸟儿张开翅膀一飞而起,幼小的雏鸟把头埋进枯叶,灌木丛哗哗摇摆。
走着走着,我就跑起来。
跑过茶油林,这里埋葬着早夭的孩子,小小的坟包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白幡随风飘摇。每一次硬着头皮钻到里面寻找黄牛我都心头哆嗦,一有风吹草动便如惊弓之鸟逃出山林。
跑下黄泥坡,泥巴路又弯又陡。读小学那几年,我目睹漫向天边的野草绿了又枯,枯了又绿,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儿在树梢上起起落落,它们总是一消失就有大半年,到了来年春天,又像走失的人找到回家的路飞回树梢。
跑上野马河边,每到插秧季节,河岸上的田坎都是湿滑的,我飞奔而来,很多次脚底一滑,仰面跌倒摔到田里。爬起来下到河边,脱下裤子搓洗泥巴拧干再穿上,等到进了教室坐下,凳子就湿漉漉冒着热气。有时,我还会在野马河边踩到滑溜溜的东西,低头一看竟是吐着芯子的蛇,吓得我魂飞魄散。我生性怕蛇自此而始,如若有人迎面丢来一节干枯的黑树枝,有时候我会误认为是蛇,导致的结果是立马怪叫一声逃之夭夭。
野马河是孤单寂寞的,但给我的快乐却是如此欢畅。春寒料峭时,我在细雨中踽踽独行,砍下根系伸进河里的柳树枝条,插进老宅屋角的泥地,用不了多久,那枝条便发出嫩得让人心疼的新芽,再几个月过去已是满目青翠,货真价实活成了柳树的样子。节假日时,把牛赶到山上,我便跳进野马河里扑腾,赤条条打开自己的肉身,水面上的阳光和云朵晃晃悠悠拍向岸边,恰如多年以后我在河岸上打开自己的心扉,空茫的慨叹在胸腔里萦绕回旋。那些个独属于少年的傍晚,跟着一甩一甩的牛尾巴走回家,手里拎着用草茎拴住的几只螃蟹,螃蟹钳子在动,钳不住我的手指,只夹住炊烟升起的晚风。
每天,我这个走读生要沿野马河畔来回走四次,早晨上学一次,中午放学一次,下午再重复一次。只要不是暴雨倾盆的雨季,这条河流都用潺潺流淌的水声伴我奔走。有的河段鹅卵石光滑硕大挨挨挤挤,青草野花漫成一片。有一次脚板带风跑过河边,一株野花撑着修长的茎秆开出鹅黄色的花朵,像是撑起一轮小小的太阳。她开得孤寂孤傲,遗世独立,旷野里除了我停下脚步注视,再难有人一睹她很快凋谢的芳容。
读中学时的一年中元节,也就是壮族人俗称的鬼节,一个号称大力士的屠户硬是藐视洪水季节的野马河,在众人面面相觑中,把两袋各一百斤的尿素扛上肩,深一脚浅一脚蹚过河,嘿嘿两声放下尿素袋。返回又蹚过河来,又把两袋尿素扛上肩,身子踉踉跄跄,到了水流最急的河中心,扑通一下,尿素袋落水,屠户手脚挣扎拍打河面,眨眼之间就被冲下河道。慌乱的人群只看到河水激起千层浪奔腾而下,听到急流的嘶吼在高山之间震荡。
三天之后,屠户的尸体浮出野马河下游的石马湖。那一阵子,人们对洪水的畏惧从野马河延伸到石马湖,从石马湖扩大到溪流、山涧、水塘。他们都把自家的小孩看得紧紧的,只要孩子脱离视线范围,呼儿唤女的声音就在村寨里心急火燎地响起。
天空垂落河流,河流拥抱天空。野马河就是以这样或温情脉脉或残酷惨烈的方式,给予我与河流有关的初始感知。既接纳我这个裸身戏水的孩童,也把屠户猛地揽入怀中,仿佛鱼虾和螃蟹、鹅卵石和野花野草,都是河流的怀抱之物。
后来,我真切明白,与一场暴雨迎面相撞,每个人概莫能外。恰如生命中总要遇到几条形貌嗓音各异的河流。这种观照方式在漫长的时光里以无意识的方式潜藏,当我此时回头一望,体内日夜流淌的水声就奔腾而出,不可遏止。
二
从小学毕业,进入野马河畔石墙泥瓦的中学,我咬牙苦读下去。参加中考不久,一个大雨滂沱的清晨,我收到了宜州民族师范学校公费生录取通知书。我那走出野马河、走出山野对既定命运团团裹围的渴望终于如愿以偿。
坐上卧铺车远赴宜州那一天,到了东兰县地界一座长长的钢筋水泥大桥,车上的人抬头侧身望向窗外。“看,红水河,红水河!”有人叫起来。
透过车窗,伸长目光,我看到一条水面宽阔清幽的大河横亘在两岸高山之间。在此之前,我只在野马河见识过山洪滚滚而下的样子,宽不过五六米的河面似乎也只容得下寂寞的野花野草,以及大力士屠户在水里无力地挣扎。十七岁第一次出门远行,像红水河这么宽大,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河,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自野马河出发,跨过奔腾的红水河前往两百多公里的宜州求学,对当时的我来说极具改变命运的象征意义。自此一去,三年毕业后我将不再和父辈们一样,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刨食,经年累月把自己熬成满脸褶皱,端着粗瓷大碗欲说还休的农民父亲形象。尽管多年以后,这样的认知在黑夜中发出自嘲的冷笑,但当年跨越红水河闪现的欣喜却是真实得无懈可击。
在师范读书三年,我六次往返跨过红水河。如果是夜晚到达红水河大桥,这条河流就用两岸稀疏零落的灯火迎接我的到来,天光笼罩下的红水河,依稀看到朦胧的河面轮廓,有渔民亮着灯摇船撒网,网落网起,不知收成几何。若是白天,红水河就伴随飞驰的汽车,画卷一样在我的注视里呈现她的奔流不息和绿水滔滔。河边,入水玩闹的孩童光脚上岸,沉寂的河面白鹭飞翔,草叶之上晚霞火红。长龙卧波,浪花拍打礁石,岸上的稻田谷穗头颅低垂,茫然张望的蚁虫听到水珠轰然下坠的声音。
此时,就在万家灯火的此时,两手扶住方向盘的东叔开着小四轮,突突突一头闯入二十多年前的红水河岸边。
那时,东叔是乡里唯一开小四轮搞长途营运的人。车子车厢不大,能容下六个人。但东叔不管这些,满满当当塞下八九个甚至上十个人,用铁条摇把插进车头柴油发动机孔洞,摇,手臂抡成飞旋的圆圈,摇。嗒嗒嗒几声,排气管冒出黑烟,柴油的气味瞬时四下弥漫,在旁边或站或坐的旅客咳嗽几声,抬脚上车。东叔挂了挡,车子老牛爬坡似的从野马河边向弯弯曲曲的沙石公路开去。到了县城,放下短途旅客,又捡上一车人,突突突,紧赶慢赶继续前进。六七个小时过后,车厢里的人满脸土灰,头发板结,颠簸得全身快要散架才踏上东兰县境。
拉客到了金城江,东叔并没有开着空车回来。他从批发市场低价买下时髦的男女时装、红糖大米水果、香港电影电视剧录像带,又是满满当当一车拉回乡里转手卖掉。几年下来,东叔腰包鼓胀,讲话的声音拔高好几度,原先低矮破烂快要塌掉的木楼,换成了两层水泥砖小白楼。我第一次知道录像机这个东西,是在街上的录像厅看到的。当录像带灌进机子里,摁下播放键,彩电就大放异彩,有时是周星驰的《赌圣》《赌侠》《逃学威龙》《武状元苏乞儿》,有时是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四大天王的演唱会。而有时呢,是三点式的漂亮女人,在游艇上、沙滩边,轻步徐行,起舞歌唱。总之是,“比基尼”唱碟和东叔带回来的种种新奇东西,让我们目瞪口呆,大开眼界。
有一阵子,街上浅抹口红的时装店老板娘望着空阔的马路,盼不到熟悉的小四轮突突突开过来,更不用说会看到东叔刹车熄火,风风火火跳下驾驶室,从车厢抱下五颜六色的服装,重重丢到店面地板上。录像厅的平头老板也久不久站到马路边,朝路的尽头张望。他手头里的录像带已经反反复复放了好几遍,客人已经看腻了,等不到东叔回来换上新片,只能反反复复把旧片放下去。食品店的母夜叉张妈干脆骂起来:“这个死鬼老东,该不是在金城江讨了新老婆,不回来了吧!”
结果在一个一街人沉沉睡去的黑夜,东叔回来了。不是开着突突突令人讨厌又令人想念的小四轮回来,也不是被人骗光钱财光着脚板走回来,而是躺到一辆专门替人收尸的车上回来。天亮的时候,人们听到东叔的小白楼传来呼天抢地的哭丧声,铙钹咣当咣当响。这样的声音响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清晨,东叔被埋葬到房屋的后山上,白幡在风中轻轻摇摆,仿佛他连人带车坠入红水河时,一棵翠竹无风而动枝叶摇曳的样子。纸钱飘舞,孝男孝女长跪不起,哭泣声远。长眠的东叔大概不知道,红水河在一百公里之外用涌动的怒吼祭奠他的死去。
此刻,凝神回眸,记忆拉回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的一个夜晚。
那一晚,我借宿县歌舞团朋友的宿舍,刚住进去不久,听到隔壁房间一个男子放声号哭。朋友说,这个哭得不像样子的人是他们歌舞团的编剧,平时大家都叫他老渔。
我们走进编剧的房间,那里已经是满室焦黑,原来是刚刚经历了一场火灾。那一晚全城停电,编剧点燃蜡烛把写到一半的剧本继续写下去。写到半路出门解手,回来时房间火光冲天,大概是蜡烛翻倒,点燃了手稿。大院里的人都赶来救火,火是扑灭了,编剧却瘫在地上放声大哭,不是心痛被子衣服全被烧毁,也不是压在枕头下的几十块钱烧成了灰,而是他历年来写下的剧本稿子全都付之一炬。
众人都安慰他只要有命在,剧本可以重新写。
“写不回来了,写不回来了!”
编剧带着哭腔来来回回重复这句话。大家苦劝不住,只好先行离去,留下他静一静。
我和朋友一人一边架住他的胳膊拉到我们的房间,让他躺到另一张床上。全城黑暗,雨也紧一阵松一阵下起来,风吹刮着大院哪一扇没关紧的窗户,啪啪啪响。
朋友点了一根蜡烛,在跳动的火苗里,编剧裹紧被子,身子还在瑟瑟发抖。
“知道人家为什么叫我老渔吗?我是在东兰红水河边打鱼长大的。”编剧自问自答。
在老渔的讲述里,我的眼前跳出绵延不尽的大山,红水河在崇山峻岭之间奔涌而出,沿着河道一路高歌向前。一个裤管高高卷起的小孩脚踏竹筏,手撑竹竿划向河中心,手起手落,撒网收网,鱼在网里活蹦乱跳。远处的河面雾气弥漫,寨子人家在暮霭里打开家门,老人站在竹竿编排而成的晒台上,破开嗓子叫唤儿孙。
回到家把鱼下了锅,吃完晚饭侍候老人睡下,老渔伏在桌案前埋头苦读。炸鱼电鱼的多了以后,红水河的鱼越来越少,等到老渔三番五次收网捞到的只是水藻和少得可怜的鱼虾,他知道红水河已经养不活他一家人,更供不起他去学校读书的学费。
老渔在红水河边洗脚上岸。他在沙场抡锤砸过石头,摸进矿窿偷过矿被追打得鼻青脸肿,也赶过马把原木运到锯木场,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一篇篇稿子投到地方小报上。写着写着,几年过去,从一所学校毕业成为小城歌舞团的一名编剧。
每写完一个剧本,老渔就把手稿放到一个雕刻有花鸟虫鱼的木箱子里,像是完成一道仪式一样,当合上箱盖,他就点燃一支香烟,大口大口地吸,目光一遍遍抚摸箱子,仿佛里面装着他的天地、他的一切。
“写不回来了,写不回来了……我的稿子,半生心血,全完了……”
老渔捂着脸再次放声大哭。我跟着伤悲起来,一个人把文字看得如此重要,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即使我搬出种种说辞安慰他,甚至讲出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手稿被烧,万念俱灰后又重新燃起写作激情,最后写出《法国革命史》的故事,老渔也没有被打动。我正要再说下去,呼噜打鼾的声音响起,他在泪流满面中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黑麻麻的,我穿衣下床,悄悄离开了这间宿舍。老渔躺在被窝里,不知依然在睡梦中,还是睁着双眼等待天色大亮。
在东兰差不多一百公里的流程里,红水河泛起的浪花无数,东叔和老渔只是她的波涛所达之处溅起的两朵水花,大可忽略不计。但微小如我,与红水河有关的最深记忆,却不是她的惊人长度和碧波浩渺,而是那些从她的怀抱里走出来,以及一头坠入她的襟怀里的人。如此一想,接通了与她相距一百公里的野马河给我的记忆,和老渔从红水河边走出来一样,我蹚过野马河才走出山门。和东叔葬身红水河一样,大力士屠户在野马河也终止了人间呼吸。
我在回忆里旁观野马河传奇人物东叔葬身红水河。在红水河的回响中倾听老渔如何痛失手稿。
旁观、倾听——河流再次将语词不假思索赠予我。它们兼具置身事外、又身在其中的特质。河流日日夜夜流淌,她还要继续赠予我川流不息和风起浪涌。
三
在和东叔有关的讲述里,我反反复复提起金城江。实际上,金城江既是一条河,也是一座城。发源自贵州荔波的打狗河顺流而下,流经广西南丹、环江,进入河池市的六甲镇后始称金城江,江岸的小城即和此江同名。金城江和小环江汇合后流入宜州境内,称为龙江。
二十多年前,我从家乡的野马河出发,跨过东兰县的红水河,抵达金城江,再转车风尘仆仆到达龙江河畔的宜州民族师范学校。这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对十七岁出门远行的我来说是多么遥远。一天一夜地辗转颠簸,白天就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江河,夜晚仿佛两岸亮着灯火微光的湖泊,我如一粒尘埃在江河湖泊上游弋,尘土满面,发如乱草,方才浑身酸痛躺到学校宿舍一张窄小的铁架木板床上。
毕业后,我原路返回。从龙江河畔出发,到达金城江,越过红水河,回到野马河边教书。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从此以后,龙江河畔的茂林修竹、苍翠青山只能成为记忆。两手空空、才学平平,那时的我几无返回宜州求职就业的可能。
蛰伏山野,那支撑躯体的精神一再遭遇重重击打,难以言说。乡村,远观谓之诗意地栖居,身临却是如漫山遍野的斑茅草,虽是柔弱无骨,但锯齿也能将人割得遍体鳞伤。有一天,一个中年人满脸怨愤闯进办公室,大声质问高坐其间的人,为什么私下里要把他调到荒凉的大石山深处工作。“我是抢了你的饭碗,还是打烂了你家的锅头,你要对我这么毒辣?”……他们吵得唾沫横飞,一个把巴掌拍到桌面上,另一个捏紧拳头挥向对方的额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挤得密密麻麻,脸上泛出一丝丝兴奋,似乎是生怕这场全武行很快戛然而止,生怕寡淡的生活一下子又陷入冷寂。
这两个人,一个蜗居乡村二十几年,一个把官当得有芝麻粒大,他们都是微小的人物,但微小里的强势者也能把权力用到极致,同样能左右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把易碎如蛋壳的生活死死摁在墙角里。
同室操戈的事件过后,有一次我站在高楼栏杆边,望着野马河对面的高山恍惚出神。一位长者走到我身旁说:“这地方,能逃离尽量逃离……但是你怎么走出去呀?”他的意思我懂,身无银两,背无倚靠,凭什么逃离乡村?我的眼前又闪现出一幅画面:一个三十有几的人借了一笔款,兴冲冲敲响一间办公室的门,意在把鼓囊囊的信封送出去,以图从乡下调到城里。结果开门的人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个人碰了一鼻子灰,当天就把钱还回去,创下个人史最快的还款纪录。
呵,逃离,一个转身出走的动词。我在空想中心驰神往却又滑步跌倒。很多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精神的我从肉身的我发肤之上抽离,用陌生和惊讶的眼光将我内视打量,之前我那所谓的十七岁跨过红水河即象征命运的改变,只不过是脚踩虚空的浅薄之言——肉体的饱食无忧,如何包裹得住精神的迷茫与困顿?冷笑声里,这另一个我甩出愤怒的耳光,打到麻木颓废的那个我脸上,疼痛钻心入骨。我仿佛从睡梦中大汗淋漓醒来,试着扯下眼瞳上的蛛网,擦拭内心蒙尘的锋刃。
在野马河边几经挣扎徘徊,从泥淖中拔出脚来跨过红水河,抵达金城江作稻粱谋,已经耗费了十年的漫长时光。如果时光眸眼炯炯,在返回乡村现场的路途中,一定看到我扛着试图再次走出山野的愿念,跌跌撞撞走在野草漫过脚踝的老宅土路上。夕阳燃烧如巨盆的黄昏,我独自爬上高山,远望的目光被连绵起伏的群山阻挡、折断。星星眨眼的黑夜,我来到夜虫鸣叫的荒坡,把写烂的稿子一页页撕碎点燃。
火光扑闪,不熄不灭。我想说的只是一个人在精神沼泽地里的跋涉与彷徨,还有那脚踩坚硬的黄泥地,试图以长矛大战风车的鲁莽与荒诞,去与现实和解。于是寄居金城江,一个人沿着江岸缓步行走,有时候我什么都想,更多的时候什么都不想。
秋冬季节,金城江碧波荡漾,晨光晚霞在水面上晃动,鱼钩一甩就钓到头顶的天空。到了春夏,亚热带季风裹挟丰沛的雨水铺天盖地而来,暴涨的江水漫过突兀耸立的礁石和高大茂密的刺竹林,向水位警戒线进逼。站在被我称为边桥的桥头上,看到碧水柔波已经被浊水横流替代,江面上的木头、枯枝、杂草跟随打着旋的湍流向下游漂移。
有时候坐上岸边伸向江边的巨石,十几步远的凉亭里,一个白发如雪的老者拉着二胡,脑袋随着悠长的乐声摇来晃去,似乎沉浸在音符拉起的往事里。他有时来,有时不来,凉亭空寂无人时,我支棱耳朵试图捕捉缠缠绕绕的二胡声,空茫中听到风中的树叶哗啦哗啦响动。白鹡鸰在树梢上啁啾跳跃,有时它们突然飞出树林聚合成一朵云,又倏地分开各奔东西。
如果来得恰是时候,我会在河岸公园的小广场草地上遇见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把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放到柔软的草地上,孩子抬起手臂,一步一步试探摸索着走,鸭雏绒毛般稚嫩的笑声溅落草尖。不远处树荫下的垂钓者鱼竿晃动,拉竿收线,一尾河鱼跃出水面,水波晃荡,水纹一圈圈奔涌追逐。
走着走着,一时兴起我就跑起来。跑过边桥,跑过沿岸马路,跑过观景台,跑出薄雾弥漫的拂晓,跑进夕阳牵出月亮的黄昏。
跑,向前跑。很多次,跑过金城江边的健身步道,一个坐着轮椅的平头中年人和我不期而遇。他双手扶轮向前,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似乎岁月深处的至暗时刻都在这笑容里一一消融。他遇到了什么以致坐上轮椅,又如何放下所经历的一切,用笑容抵抗和承受了生命的重击?我无从问起,每次和他目光相撞,然后错开身子,他继续扶轮向前,我双脚踏地继续奔跑。
跑,向前跑。跑过河岸上的一家车行门前,我把目光投放到过往的影像里,记起店主是一个离异的女性。有一次朋友应她之邀拉上我来这里吃晚饭,酒喝到半酣,她突然问我平时看些什么书。我说我之前偏重于读路遥、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陈应松、阎连科等作家的成名作,现在倾心于张宏杰、祝勇、蒋蓝、陈启文等作家的非虚构文本。女店主眼光迷离了一下,似乎对我说出的一串作家名字闻所未闻。我自认为对话是无法沟通,不知所云。但她却说:“我现在晚晚读《西藏生死书》,一本没多少人去研读的经典。读着读着,我就觉得,人既要不怕死,也要不怕活着……”我大感诧异,没想到貌似高冷、目光绝不轻易长久垂落他人脸庞的人,竟然对这本讨论严肃生死课题的奇书产生兴趣,而且平地起风,语出惊人。
跑,向前跑。如果时光也是一条可以容纳脚步飞奔的大道,我也要再次跑过野马河,向东跨过红水河,继续向东踏进金城江地界。牵扯风声的身后,大力士屠户、东叔、老渔从睡梦中醒来,翻身下床。
大力士屠户把锋刃闪光的屠刀挂在屋檐下,肩扛犁耙走上稻田。
东叔从木箱里翻出小四轮铁条摇把,丢给打铁铺的老刘,让他打出一把上好的菜刀。
月光斜斜照在窗台上,老渔把头从稿子上抬起来,兴奋得拍腿大声叫好。
跑,继续跑。一路奔突,迎风向前。
而江水不见惊涛拍岸,泛起粼粼波光拥抱人来人往,光影重重的彼岸,那些被河流赠予目击、旁观、倾听、逃离、寄居属性的人,一一浮出此岸喧哗的水面。
静水深流抑或暗流汹涌里,唯有江月孤悬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