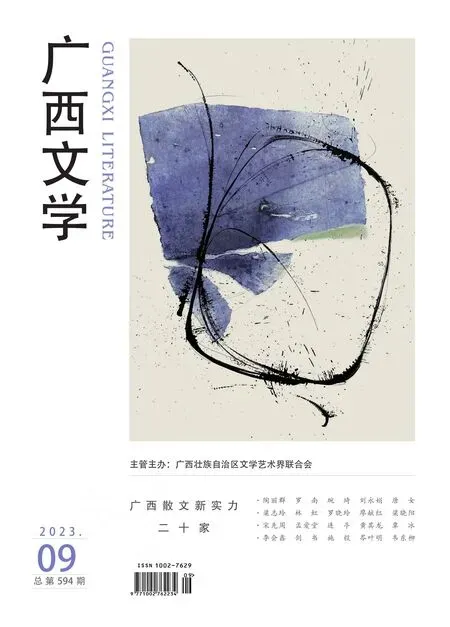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2023-10-22韦东柳
韦东柳
秋已深,雨绵绵,我遇见了一棵树。树在风中摇晃,它很高大,朝北倾斜,顽强地朝天空伸展而去。我在风里停下来,触摸那斑驳的树皮,交错弯曲的纹路像一条河流,引着我走进林海深处。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嘉陵江边到红河水边,故乡从指尖流到心间。
一
想起故乡,就会想起那个小村庄。村庄坐落在桂西北群山中。东边有座山,西边也有一座山。从家门口远远望去,前方也是一座山,一座山连着一座山起伏。山上森林密布,杉树上覆盖着厚厚的苔藓,古老的桫椤枝叶宽阔,粗壮的藤条攀缠着挺拔的枫香、榕树和樟树,松鼠在林间跳跃,鸟群在上空盘旋。
村庄紧贴脚下的土地,倚靠身后的高山,野蛮生长。
村庄叫更旦屯,规模很小,只有三四十户人家。村里的人,大半姓韦。村里没有祠堂,也没有家谱、姓氏或宗支的脉络,整座村庄的历史,都无迹可寻。那些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过去的生活,都是老人们口口相传。
那是一座完全木质的村庄。村头村尾、屋前屋后都种满梨树、桐树、枇杷树、桃树……村口有一棵老榕树,稠密的枝叶覆盖了整个村庄的日出月落,小孩子在树下嬉闹、唱歌、捉迷藏,大人坐在木墩上唠家长里短。榕树脚下有一个香炉,每到盛大节日,人们会敬上三支香。出远门,或是遇到难事,人们都会插上三支香,拜一拜。村庄的房子是干栏样式的,房柱、房梁、门窗、墙壁都是木头做的,就连牌匾上的字、大门上的对联、装饰性的物件,都是实木雕刻的。家家户户墙角边堆着高高的木桩,水井边斜躺着湿漉漉的木桶和木瓢。每当抚摸那些老物件,闻着木头特有的气息,像是闻到一股源自光阴的醇酿,那是村庄的符号,它们一直在承载着整个村庄的世事沉浮,丰满了几代人的记忆。
二
在莽莽大山中,目光所及皆是山林,树像土地一般,成了父亲的命根子。
父亲是在山林里长大的。他的心灵和性情被森林的强大和深邃所涵盖。林地面积和树木的粗壮是壮乡儿郎娶亲的本钱。小时候,父亲就跟在爷爷身后,整日整日地泡在山上。稍大些,爷爷带着他开荒种树。从此,那片荒地就跟他姓,他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在那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父亲开辟了几十亩林地,植被十分茂盛,远远看去就像一片原始森林,那片山林成了他的天下。他自己也活成了一棵树的模样,高大、健硕,面对狂风和雨水依旧挺拔。那双布满裂口的手,紧握锄把,将锋刃对准生活,摒弃荒凉,耕种和谐、殷实的生活。
父亲说,一棵树从无到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立春过后,山风依旧低沉,天还没亮,整个村庄还静悄悄地笼罩在迷雾中,父亲早已起身,穿梭在森林里。
以前,树苗不是摆在地摊上任人挑拣的商品,而是自生自长在森林里。父亲会装上一桶山泉水,带上自家林地上的泥土和各种不同尺寸的铲子。父亲会观察自家林地的日照时长、泥土质地和植被覆盖种类,根据湿度和质地,以及树苗的生长状态判断是否可以移植。他没读过什么书,对树木的深情虔诚得像个科学家。确定可以移植的树苗,他弓下腰背,扒开树苗下的泥土,先用小尺寸的铲刀挖开泥土,观察树苗根茎部长势,再用锄头顺着根茎生长的方向挖土,确保不斩断树苗根部。起地后,将水倒入坑中,掺和自家林地的泥土,形成泥浆,涂抹在小树苗根部,用宽大的叶子连同泥浆包裹,草绳绑住,轻放在簸箕里,盖上芭蕉叶,走路都要轻轻地,生怕颠簸了这脆弱的小生灵。挖开小树苗的土坑,要把泥土填回去,将落叶杂草覆盖在上面。父亲说,那是一个伤口,要给大地一份体面。朴素的哲理在沉默的生活中得到明示。
树和人一样是有情感的。将一棵小树苗从熟稔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带到陌生的地方,要尽快恢复树的创伤。种树要把握好树与树之间的距离,站得挤,会憋闷,离得太远,会孤独。种树的坑要挖深,尺度要掌握,要在新泥和老土相结合的地方停顿,既能保持根须的稳固,又能保证充足的水分。填土完毕,就完成了第一步移植搬迁。他会以父亲名义爱护每一棵树苗的生长环节,除草,施肥,扶正树身,掩虚土,压紧,一套重复的劳动程序,在无数的日子里耐心地进行。
父亲长时间与山林为伴,对森林里的一切了然于胸。他说,松树每生长半年,树干上就会留下一个树结,树结的数量就是树的年龄。父亲知道每一棵树的心事,不同的海拔、气温、湿度、水文,树会用身体的表征传达出喜好和情感。父亲还知道森林里的知了会在黄昏之夜叫得最响亮。他还能分辨出杉树、桦树、楠树、柚木树、栗树、松树等树木风穿过树叶时不同的声音。父亲身处丛林中,置身于树木无数丰富复杂的语言网络之中,和它们进行无声的交流和对话,他深入每片落叶纹理之间,从经验中挖掘出刻画经久且内在的生命密码。
父亲还说,现在种树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种树,更多考虑景观价值、绿化效果,忽视了树本身。每一棵小树苗就像病人一样,拄上拐杖,挂上吊瓶,缠上绷带,搭乘大卡车一路颠簸,从森林来到公园、湖边、马路上,将血液重新注入坚硬的水泥地板中,车子呼啸而过的鸣笛声和风声,愈加刺激那颗背井离乡的受伤的心。森林里被翻卷的泥土,遗弃的快餐盒,白色的、敞开的、破损的、污秽的,就像用过的创可贴。看着眼前的山林,父亲时常感觉到与眼前的生活产生了剥离,他的内心很复杂。
三
父亲一生的年轮都围绕着木头旋转。他成为一个木匠。
天还是没亮,大地还在沉睡中呓语,父亲轻推木门,木头与木头摩擦发出的声音,在寂静的凌晨格外刺耳。他走出村庄,踏过灌木,无数的树、无数的叶、无数的草和无数的花将他包围起来,他在深林里穿行,森林里一草一木也在他的生活和岁月里穿行。
抵达山顶,父亲在山林里绕来绕去,打量每一棵树,就像许久未归家的父亲打量我们个头有没有长高,胖了还是瘦了。打量片刻,父亲在树下点三支香,鞠三次躬,他坐在树下,拿出腰间那壶米酒,提到嘴边,猛喝一口,再喷洒在三支香上,细长的烟雾缭绕着朝天际飘去。一切准备就绪,父亲取出寒光闪闪的斧头,咬紧牙根,锋利的斧子富有节奏地砍在粗壮的杉树上,没有电锯的年代,父亲用板斧一斧一斧地砍伐,斧头与树木之间的摩擦发出沉闷的响声,声音悠悠回荡在整个山间。
砍树是一个体力活,如何把砍下的树扛回家,是一件更加考验体力的活。父亲除去树的枝条,两手推着刨子,树的满身斑驳变得光滑。父亲将刨好的树一高一低斜放,蹲下,重心放低,咬着牙,手一抬,树沉重地压在父亲的肩上,肩膀上瞬间勒出鲜红的印痕。父亲一步步踩稳土地,缓缓朝山下走去,汗珠早已湿透了他的衣衫。
一年冬天,天早就黑了,父亲还没回到家里,母亲带着村里人上山找他,他倒在地上,额头上布满了鲜血,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伤口,怎么叫唤也不醒来。母亲露出惊恐的神情,号啕大哭。众人齐力将他背下山,处理好伤口,躺了一夜才醒来。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长年累月经受劳苦,父亲的双手充满了褶皱,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
父亲的木匠活做得好、做得细,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不仅村里人找他做活,连隔壁乡镇都来找他。因此,伐木归来,父亲又迅速投入了工作中。父亲就在自家的院子里干活,整个院子都是父亲的天地。记忆中,总看见父亲站在长条凳的一侧,耳朵上夹着红色的木工铅笔,手里拿着推刨,斜扑着身子,一下一下地刨木头,刨花卷堆了一地,雪白雪白的,整个院子里弥漫着刨花卷和木头屑淡淡的香味。父亲的木工工具装在一个大木头箱子里,有些是他亲手做的,有锛、锉、推刨、墨斗、锯、木钻之类的。那些工具暗藏的锋利和父亲手臂的力量达成了某种默契。他马不停蹄地忙碌着,我深夜从睡梦中醒来,锯子发出的吱吱声,刨在愈渐光滑的木头上发出的嚓嚓声,回荡在我耳边。躺在床上的我一个翻身,吱吱的响声也跟着带入梦里。
一觉醒来,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木制物品。木制的烟管、木凳、木马,还有木柜、桌子、红箱子等新婚物品,踏碓、马鞍、牛轭等农具,就连女人用的木簪、梳子也是经父亲之手,甚至连人们死去置办的棺材也能刨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的背弯得更低了,手臂上的肌肉硬邦邦的,手掌又厚又阔,长满了一颗颗老茧,摸上去就像小石头一样。他一头牵着大自然的手,一头牵着对某种更好生活的渴望,以埋进泥土的姿态,匍匐向前。
四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普通人,打工的浪潮席卷到寂静的小山村里,大家朝着相同的方向迅疾奔涌。父亲也离开了,脚步声渐行渐远。山风依旧在林间闯荡,我和母亲站成一棵树的模样,向上生长,枝叶朝天空延展,朝更远的地方张望,渴望见到身在远方的父亲。
父亲外出打工,他依旧和树木纠缠在一起。父亲在老乡的介绍下,进入一家木材加工厂工作。在充斥汽车尾气的城市里,桦木的清香,松木的浓香,整齐码放堆积如山的原木,唤醒了父亲心底久违的味觉记忆,那熟悉的木香抚慰了父亲一颗身处异乡孤独的心。
城市里的木材厂对木材的处理加工方式和父亲以前的做法大相径庭。父亲说,木匠除了有一双巧手,更需要一双慧眼。要根据不同材质的木材做不同的家具,这样才能发挥木材的真正价值,加工厂都是用同一种木材。父亲还说,木匠干活前,脑子里构思制品,实际操作时不断调整矫正每一个细节。而工厂车间的工人都是按照预先设计的图纸,根据图纸切割、刨边、打眼,木材的大小、长短、宽窄不再是木匠所能控制的。在喧嚣嘈杂的车间,他不再是一个木匠,就像一只鸟,关在无形的铁笼子里。天黑了,望着故乡的方向,他听到了雨穿过树叶的清脆水声,灌木丛里虫鸣唧唧,那些声音盖过了窗外的鸣笛声和呼啸声,他在梦中回到了那片林荫莽莽、苍茫广阔的山山岭岭。
关于父亲在外打工的过程,我并不详知。他本就沉默寡言,不会主动提及他的经历,只报喜不报忧。我曾问过,他搪塞敷衍。我发觉他在有意地模糊记忆,生活的碎片被他扔在城市的角落,然后封上封条。无意间,记忆的碎片又无处不在,像是不死的活物,长着针芒的眼睛时刻在注视着他,滚烫而犀利。我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一些碎片。他在那家木材加工厂待了四年,工厂就倒闭了。后来,他又辗转去别的城市。曾在工厂流水线上当工人,切割机就切断了他的小拇指。曾睡在满是尘土、水泥和钢筋的工地,尘土中没有故乡的清香和湿润。他先后五六次在大街上被抢劫,一次被摩托车拖在地上十几米远,沙砾揉进他的肉体。
父亲在走南闯北中慢慢变老,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像波浪一样摇动。他离村庄越来越远了。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赚钱养儿育女的决心,对他来说,城市的灯红酒绿只是照亮了黑夜的路。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为学费发愁,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穿,双手柔软,皮肤白皙,性格天真烂漫,这一切,是父亲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是父亲一件衣服穿了五六年省来的,更是父亲日夜艰辛劳作换来的。父亲就像那棵生长在森林中的树,远离那片熟悉的土地,流浪他乡,他有过水土不服、孤独无助,在与生活的博弈中满是伤痕,但他依旧将根深扎在泥土里,强忍疼痛破土而出,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硕大的枝干和茂盛的枝叶,遮住毒辣的阳光,挡住粗暴的风和冰冷的雨,我这棵小树苗得以慢慢长大,父亲在慢慢老去。
五
在外打拼的人,时间长了,有点积蓄了,纷纷到城里买房子,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把户口转到城里,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很少再有人回到村里。父亲越走越远,我随着父亲的脚步,越走越远,故乡被遗弃在记忆中。
今年春节,村里一位老人走了,他活了九十九年,是村里最长寿的人,也是村里最后一位老人。他一个人守在村庄里,见证一个个人离开。年轻人离开村庄,到城市里生活。老人离开村庄,长眠在森林里。去年冬天,老人打电话给父亲,叮嘱父亲要给他制作一具棺木,这件事一直成为父亲心里的牵挂。父亲特意提前两个月回家,给老人制作一具棺木。
父亲还是和以前一样,天还没亮就出门了。如多年前一般,爬上弯曲的山路,走过七弯八岭,回到那片森林。点香、洒酒、砍树,曾经一幕幕又在眼前浮现。不同的是,曾经的斧头变成了一把电锯,父亲曾经浓密乌黑的头发,此时已爬满白发,嘴角两旁的皱纹宛如桦树皮上的纹路。岁月的幽深和强势,像车轮子一样骨碌碌滚过他的身体,滚过他的一生,留下弯曲又明晰的辙印。电锯声响彻山间,大树轰然倒下。父亲除尽枝条,用黑布包裹上,确保不染尘土。给老人做棺木,是村里的大事,乡亲们闻讯纷纷从田间地头赶来,从深山野坳赶来,这些人平日里始终是分散的,或在河边码头,或在山沟田坳,即使说话也是隔着很远很远的山头,唯有与生命、死亡相关的事情,才能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家合力将原木一寸一寸地挪下山,给老人提供一个好的尽头。夜晚,院子里又传来了有节奏的刨木声,木屑在灯光下飞舞,我闻着熟悉的木香,感受来自草木生命磁场的吸附,陷入梦中,梦中有青山、大树、鸟鸣、溪流和父亲。
两个月后,一具黑色棺木静静伫立在院子的角落里,庄严、大气。老人抚摸着棺木,整只手颤颤巍巍地,眼里满是浑浊的泪水。老人说,手艺不比当年了。父亲说,多年没做了,手生了。老人反复呢喃,知足了,知足了。后来父亲说,老人一直怕死,村里没人了,他怕死了没有人知道。一个月后,大年初一凌晨,老人永远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乡亲们高高地托起棺木,往森林深处走去。原本就很冷清的小村庄,愈加安静了,天空下,只有风吹过的声音。
春节过后,父亲再也没有走出小村庄。他养了一条大黄狗。每天,迎着第一缕阳光出发,大黄狗在前边探路,父亲优哉地在后面跟着。父亲有时带把锄头去除草砍枝;有时拎着新买的小树苗,重新栽种一棵棵树;有时两手空空,朝森林深处走去,腰间的酒壶当啷作响,埋没在杂草丛中的坟冢重见天日。父亲没有让自己闲下来,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父亲常坐在村口那棵老榕树下,眯缝着眼睛晒太阳,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座雕塑一样。我坐在他身边,他总说一些以前的事情,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将记忆的褶皱展开。他说,以前森林有一棵百年老樟树,树干粗壮,几个人都围不住,树心是空的,却还活着,有树神庇佑。他说,森林里的树很高、很大,抬头望天,终日不见阳光,潮湿的泥土或树干上,撑开形色各异的菌盖。林中有各种各样的鸟,乌鸦、麻雀、百灵、喜鹊和各种叫不出名的鸟,有时候,一棵树上就有好几种鸟在枝头叽叽喳喳,它们白天在林子里飞来飞去,夜晚在林子里睡觉,林子里可热闹了,死后埋在林子里,就不会孤单了吧。
我看着父亲,我看到了一棵树,父亲变成了一棵树,他在山风中摇摆,弯腰,再摇摆,再弯腰,像是进行某种古老神秘的仪式,以谦卑的姿态叩拜脚下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