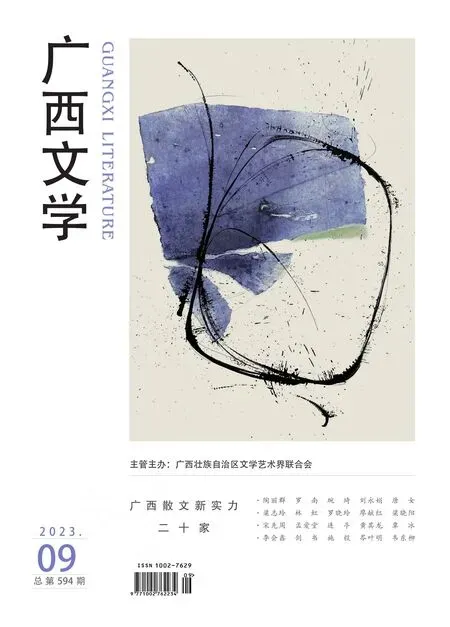一个人热闹
2023-10-22岑叶明
岑叶明
一
十多年前,村里修水泥路,每家每户都要按人头出钱,钱多可以捐。捐得最多的是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大老板,十几万,当时的我觉得天上的星星都没这么多。有了大老板的天文数字,水泥路修完,还剩钱,大家便提议立个功德碑。
功德碑建在村口的空地上,刻上捐赠者的名字,从大老板开始,按照数目大小往后排列。立了碑还有钱,又在碑后建了面墙,顶上加檐,用来遮风挡雨。我家人的名字没出现在上面,与玩伴们去到那里,总成为被笑话的那一个,说我爸肯定把钱赌光了,再说我妈因为我爸太穷跟别的男人跑了,最后说我不捐钱所以不能走路。好在我的嘴巴也够毒,说这块碑像墓碑,祝贺你或者你爸你妈被刻了上去,明年清明节记得来烧香放炮,不然他们就成孤魂野鬼啦。
没过几年,功德碑旁建了个垃圾池,其他空地被人用来晒稻草,有时用来晒牛粪,不知道大老板作何感想。不过大老板很少回来,关于他的事我们所知甚少,除了很有钱。有时捐钱不到位,大家背地说他小气,传到他那里,他索性不捐了,便有人骂他,在言语和气势上排挤他,即便他曾对村子里要钱的大小事有求必应。我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和他感同身受,因为父母离异、家庭贫穷,我也是被排挤的对象,区别在于他能离开村子,而我的远离只存在于幻想中。
我性格顽劣,喜欢热闹,也不排斥独处。前者源于天性,喜欢独处则是不想回家。父亲与母亲离婚后性情大变,常常无故疯癫,骂人,砸东西,我将那栋矮小阴暗的瓦房视为地狱。我不想待在里面,便独自在外面晃悠。我自幼便深知农村妇女们议论某个人偷鸡摸狗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源于谁家确实丢失了什么,而是被议论的那人有机会让别人丢失什么。就像常年在外工作的母亲,不是她确实做过什么,而是她有机会做什么,闲言碎语在这些模糊的暗示里最具有生命力。为了不成为她们的目标,我选择往人稀少的地方走,鬼怪对我而言不比她们可怕多少。夜晚的村子幽静、安详,房屋里的光偶尔逃逸,大多地方幽暗。我带着手电筒却不打开,借着月光引路,去寻找能一起出来玩耍的人。大人们觉得小孩夜晚出去必做坏事,实际上我们也做过不少,因此在夜幕下呼朋唤友不能明目张胆,而是学着什么叫,有时学狗,有时学牛,有时学鸡鸭,有时发出的声音四不像。有时唤得出玩伴,有时唤得他们父母的叫骂。
大多时候玩伴们回家了,我还不想回,便沿着村路走到村口,爬上功德碑,躺在上面发呆。那时没什么书看,眼睛好,能数清天上的星星。我比较它们的明暗,遥想那里居住的外星人长着什么模样,和地球的战争什么时候才结束。偶尔有飞机闪烁出红光绿点,我的视线跟着它们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反反复复。
有时我只是望着星星,心思却不在星星上,而是想到跟随母亲离开的姐姐,她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父亲总是在吃饭时咒骂母亲,有时蓄谋着骂,有时毫无征兆地骂,我要一起表现出憎恨的模样才能避免被一起骂。在那些独自仰望星空的夜晚,我偶尔也会偷偷想念母亲,即便记忆中跟她相处的时日屈指可数。
千百个夜晚里,我只见过一次流星,或许它们多次出现,我都错过了。我赶忙对流星许愿,希望以后能过不一样的生活。我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觉得只要跟眼前不一样就好。
我厌倦村子,厌倦家庭,厌倦各种恩恩怨怨,自觉人不应该只为这些事而活。
二
听父亲说我出生没多久就被母亲带去乐业,两岁后回来,印象里只有些模糊的记忆。儿时的清晰记忆都离不开那个叫大桥头的村子,辐射出最遥远的地方是三公里外的横岭圩。我喜欢热闹,却不总是能靠近热闹,父亲常警告我不要往热闹的地方挤,因为事故和意外也喜欢循着热闹而去。
父亲总想着付出一点心思就有很多回报,我刚学会拿筷子,他就要求我学写字。我短时间难学会太多,他也不想太费力教,又想要我练好,便让我反复抄写自己的名字。在反反复复中我听到老房子外飘荡着充满诱惑的欢笑声、蝉鸣声、狗叫声,感到厌烦,感到厌恶,字越写越歪。父亲便大发雷霆,强迫我写更多。我自知逃不出眼前这张纸,便在上面展开想象:每个方格都可以看成一个独特的世界,或从自己的名字延伸出歪歪扭扭的线条作为迷宫的路线,周边空白的区域则可以画出具体的图像……完事后的纸张一片狼藉,像等待打扫的战场,有时能撕开重抄一张,有时挨一顿骂。父亲没能如愿,我练了很多字也不能写好,反而越来越害怕写字,持续至今,用笔写字像被蚂蚁咬一样难受,恨不得把笔折断。
日子空旷漫长,百无聊赖,能在很多细微的事物里生出纷繁的灵感。奶奶大病一场后,生活无法自理,父亲离不开村子,打不了工,赌瘾难戒,生活陷入困境。我家有些田地,又种些别人的,如果父亲不把收成放上赌桌,勉强能糊口。周边的楼房陆续崛起,我家还住着瓦房,晒稻谷时只能借别人家的楼顶。
天气闷热,稻谷、玉米、花生都怕雨,淋一下得发芽,发了芽做不成粮食。父亲不让我下地干活,只让我看天。这个任务不复杂,需要随时注意四周天空的动静,有云也不能慌,可能是吓人的碎云,得等到云层显露更多,要是满天乌云就得马上收,小碎云就随它过去。有种云最具迷惑性,是碎云,但又厚重,能带来“云吊雨”,且轨迹不定,有时直直走,有时拐弯走,有时谷物收了大半绕走了,有时不想收又被淋了,十分令人头疼。好在大多时候晴空万里,无害的白云飘来荡去,我忍着刺眼的日光,尝试和它们说话,问它们从哪里来又要去往哪里,也跟他们说我的烦心事,说我对各种人和事的理解和看法,说我对未来的愿景。想象是慰藉无聊的解药,我总是与它们叽叽喳喳,十分有趣,别人不得而知。
十二岁那年,我的顽劣达到峰值,和许多人在国庆假期翻墙进学校,烧厨房,往锅里拉屎撒尿,撬开办公室,抛撒试卷,还想着要把学校炸掉。过后不知经过了复杂的筹谋还是自发的共识,总是被孤立的我成了替罪羊,老师不是不怀疑一个人怎么能造出那么大的破坏,可能也只想找一个替罪羊,或者出气筒。老师把我关进厨房殴打,强迫我跪在教室后面听了几天的课,再罚我冲厕所扫地一个学期。老师深知最残酷的惩罚是孤立,他不允许其他人对我表现亲近,更别说帮助。当然,也没有人想要帮助我,他们大多幸灾乐祸,在我扫过的地方丢碎纸屑,憋着屎在我冲过厕所后才拉出来,以此为生活的大乐趣。
我为此颓废过一段时间,像条掉进粪坑没人打捞的土野狗。为了应对逐渐绝望的生活,在放学后空荡的教室里、厕所里,在回家路上看日落的黄昏,在许多无人的情景里,我构思出那些并不存在的玩伴,与他们交谈、玩乐。他们性格各异,善良或凶恶,胆大或怯弱,忠实地陪伴我熬过了许多漫漫长夜。
三
终于可以离开村子读初中了,别人能去到学校再买新的生活用品,我要从家里带去,旧的水桶、旧的碗筷、旧的蚊帐、旧的被子……都是旧的,只有心情是新鲜的。从横岭圩坐大巴,大巴也是新奇的,我目不转睛望着窗外,途中路过房屋散落的村庄,一块块玉米地、水稻田、树林,和我成长的村子没有什么不同,却又完全不同。尽管只有十多公里,但对我而言也是一次远行。
学校位于城乡接合部,离市区四五公里,出了校门就是国道。国道好直好宽,我从未见过这么宽的路,路边的房子也有五六层高,比村子里整齐多了。周末跟同学们去市区玩,第一次进城,不知道怎么坐公交车,又羞于问询,便磨磨蹭蹭排后面,看别人怎么投钱,怎么找座位坐,怎么告诉司机要下车。其他的学一次就会,让座不太好学,有时没在最恰当的时候起身,有时候别人先让了。第一次让座成功难免激动,脸颊发烫,觉得周边的人都在崇拜地看着自己,接着脑补一场又一场做好事不留名的大戏,直到为了拯救世界献出年轻的生命。
我在许多时候付出过自己的生命。比如学校进行升旗集会时,大家都在认真聆听领导的教诲,而我的世界中,恶魔正在进攻这里。恶魔可以是哥斯拉,可以是三头龙,可以是泰坦,但体型必须硕大,脾气必须暴烈,必须所有人都看得见,所有人都惊恐、绝望,期盼救世主的出现。氛围铺垫得恰到好处时,我猛然抬头,周身散发金色光芒,如离弦的箭矢从地面射起,穿透恶魔布满鳞片的喉咙,撕裂恶魔强壮的身体。当然,有时候不会那么顺利,恶魔十分强大时,我会无数次被击落,在地面砸出深坑。周围的人尖叫、哭泣,这种时候心仪的女孩子一定要看见我,并且鼓励我,不然哪怕我毫发无损也不会重新振奋。在激烈的战斗中,心仪的女孩总会成为转折工具,她们流下爱的泪水、发出信任的鼓励,或者她们面临危险绝望时,身负重伤的我发出怒吼,躯体里的力量呈指数爆发,壮观程度丝毫不弱于超新星爆发,甚至只需眨一下眼皮,恶魔便被轰得灰飞烟灭。
年轻时的幻想和女孩们分不开。我从闭塞的农村走出,对爱情的渴望源于青春期本能的冲动和对电影书本的效仿。大家都有暗恋的对象,我也暗恋着,憧憬与她海誓山盟、白头偕老。爱情的幻想对象有时是具体的某个姑娘,与她在烂漫的樱花树下相遇,眼神对视的那一刻便互生情愫,在诸多巧合后相识相知相爱,经过一些误会和挫折,最后都能牵手、亲吻。
在最初的幻想里,亲吻是青春最僭越的行为,仿佛亲了嘴就能圆满大结局,过上幸福的生活。往后看了些少儿不宜的东西,也随着年龄增长,生理的欲望加大,幻想的对象变得广泛起来,幻想的尺度也随之加大,有了许多不可言说的冲动、猥琐与变态。然而在现实中,我和女孩们的爱情总不会很顺利,有时暗恋某个女孩,幻想了无数的恩怨纠葛,自始至终却未说过一句话。
进入青春期后,我变得外向、开朗、搞怪,能给身边人带来快乐。可我明白自己骨子里是自卑的,源于肉眼可见的矮个子,源于耻于承认的囊中羞涩,也和童年的遭遇分不开。我害怕再次被孤立,刻意隐瞒过去,想要更多人的关心。我变得心口不一,有时心里觉得是这样,说出来又是那样,审时度势,见风使舵,提前戴上成年人才有的面具。只有独处的时候,才能让身心彻底放松,找到一种回归自我的轻松与舒适。
我由此觉得独处并不可怕,慢慢挖掘其中的乐趣。
我逐渐着迷于乘坐交通工具,这是一种非常安全的独处,周边嘈杂的都是陌生人,景象不断变化,无人能打扰。我最喜欢坐在后排位置看窗外,情绪酝酿足够,眼前变化的景象还可以有另一种意味:时光倒流。这样的场域构建出完美的回忆之屋,尽管我明白深陷其中不利于放下过往,却生不出丁点逃避的念头。
中学时比较拮据,只能坐公交车,一块两块,可以绕着城市兜兜转转。我对外面的一切充满好奇,像个错过功课的好学生狠狠补习。我缩在公交车角落观察这个世界,观察道路两边应接不暇的铺面、琳琅满目的商品、神色各异的行人,仰望高耸的大楼,也看上车下车的人,观察他们的动作和神态,猜测他们的内心。我成了偷窥者,窥视眼前所见的种种,回溯过去消逝的种种,揣摩即将发生的种种,尽管许多事暂时不得而知。
上了大学,坐大巴、动车去更远的地方,从周边县镇到其他城市,有时候呼朋唤友,有时候独自一人。大三寒假去得最远,从玉林坐了一夜火车去重庆,坐飞机去拉萨,又坐大巴到日喀则,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止步,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一次壮举。在异乡的冰天雪地遥望南方时,心中浮起许多情绪和感怀,不承想当年连坐公交车都紧张的小男孩,已经能心静如水穿梭在山川人海中了。
四
十三岁那年,我看了几本小说,写了点故事,有了成为作家的理想。要实现理想意味着需要更多时间独处,而非无聊能描述,需要另一个更沉重的词:孤独。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孤独。我的目的很简单,写一部世界名著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作品才能叫世界名著,具体写起来都是把心中臆想的东西落在纸张里,觉得这样就能朝名著进发。
听说网络小说很赚钱,我非常缺钱,便开始写些又臭又长的蹩脚故事。在小说里,我成了主角,配角都是周边人的化身,兄弟忠诚于我,女孩们仰慕着我,讨厌的人都是反派,虽一时嚣张但最终都要跪地求饶。我长期浸淫在这种情境中,每一部开篇都觉得有成为世界名著的潜质。白天在自习课和英语课上写,晚上在厕所里写,再晚一点埋在被子里用二手按键手机录成电子文档,还没攒够签约的字数就开始考虑申请哪个银行的卡收钱,结果无一不被拒。颓废后马上自我安慰,自己写的故事中主角也会受到挫折,坚持坚持就好了,再走几步就好了,又磨了十多万字,网站依旧拒绝,便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大骂文坛腐败、世界无望。
头脑里奇奇怪怪的想象有了寄托,即便没有一部小说的构思能完整实现,我依旧信心满满,享受这种冲刺的激情,忘了自己曾是害怕写字的人。我觉得自己是最独特的那一个,早早贴上作家的标签,想让周边人刮目相看。很多人认为我只是自娱自乐,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只有外公相信我的话,支持我的理想。高二那年,外公去世,我因将太多心思放在写作上,成绩一落千丈,理想重重摔在地上。我体会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放弃了网络小说创作,开始阅读经典名著与现当代名家作品。
我对自己的水平有了新的判断,别说世界名著,就算追上活着的作家也很难。于是我决定分期支付理想,第一步是先追上活着的作家们。我看他们的书,模仿他们的写作,偶尔投给一些校园杂志,都收不到回音。高三停笔一年,早起晚休,勉强考上一所二本院校的物理系。彼时我对理想更加狂热,即便中学最擅长物理,也要转去读汉语言文学。我接触到活着的作家,阅读经典和专业理论,了解文学史,视野逐渐开阔,懂得鉴别文学作品的优劣,迫不及待想提高创作水平。
我疯狂挖掘适合自己的素材,那些儿时陪伴过我的,不知何时消失的玩伴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长大了,他们还停留在过去。他们或青面獠牙,形象恐怖;或小巧可人,惹人怜爱;或平平无奇,宛如常人。他们都充满怨气,质问我为何将他们关在黑暗中。我说只是忘记他们的存在了。他们说遗忘的底色是黑暗,黑暗早已根植在我内心。他们整日在我耳边絮絮叨叨,我感到烦躁、抑郁。终于,我难以忍受了,对他们大吼大叫,你们这群恶心人统统离开我的世界,不然弄死你们。在幻想中,我双眼喷射火焰,身躯高大威猛,手提缠满雷电的开刃大砍刀,宛如战神与恶魔的混合体降临尘世,俯视着这群聒噪的蝼蚁!他们全都被吓住,哇哇大哭起来。他们不得不告诉我真相:我无法粗暴地消灭他们,他们死去的唯一结果是成为我的一部分。
他们说,我如果想让他们安静,就得找到适合他们的去处。是的,我恍然大悟,他们与我同根同源,我要给他们找到住处,或者说找到坟墓,不然他们会让我永世不得安宁。他们该去哪里呢?那些并不存在却又鲜活的小人儿,我该如何安顿你们?某个深夜,敲打键盘的我猛然醒悟,望着屏幕上干瘪的字句,找到了答案:我的兄弟姐妹,请住进我的文字里吧。
从此我的写作不再如无头苍蝇,开始以自己的成长为基底,写真实发生过的散文,写由真实改编的小说。我的生活里全部都是与写作相关的事,学习与爱情都得排后面。
我喜欢把自己关在不被打扰的地方写,即便周遭有人,也能快速调整到精神状态完全聚集于自身再写,唯恐自己的小世界被窥探。为了真正免受打扰,有时到深夜才起床奋笔疾书,第二天迷迷糊糊上课。有时写着写着下雨了,站在窗边看雨、听雨,想起悲情的诗句,想起过往的不顺,继续融入更多相关的想象,不多时便进入一种自我坍塌的情景中,觉得人生多寒凉,如梦幻如泡影。
描摹往事是痛苦的过程,为此常常写到疲惫不堪。我在河边跑步,爬上山顶看日落,安抚内心躁动的小人儿。校园的风景无法缓解,我会背上书包,像多年前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坐上公交车荡来荡去,偶然换一辆,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戴上耳机,安静地凝望窗外变换的景象。有时候也会不坐车,背着书包在城市里游荡,有时快,有时慢,有时候还喜欢绕开闹市,环绕在闹市周边的破败小巷,觉得能看到城市的真实样貌。我还痴迷于追求真实……城市的真实,人的真实,模糊记忆中的真实,小说情感的真实,爱情的真实,理想的真实。
五
真正的作家似乎对其他语言也非常敏感,我由此认定自己身上没有作家天赋,源于创作多年依旧成绩不佳,更源于对外语的迟钝。我学不好英语,甚至字母都背不全,靠着理科拉分挤进大学,又因为英语没能顺利毕业。
我没办法继续待在学校,回到贵港一家事业单位。单位的领导是作协主席,一位博览群书、脾气温和的前辈,觉得我将来能有所成,给我争取到了单位宿舍,让我有个地方继续没日没夜敲打键盘。
经济是个大问题,没有毕业证签不了合同,连实习也算不上,有绩效,最低时一个月八十五元,不够吃一次夜宵。大学时有资助,偶尔有稿费和奖金,加上去做些兼职,勉强能过得去。而今要偿还贷款、债务,要给家里,加上日常各种开支,存款很快见底,又不愿意再继续借钱,过去只在书本网络里听说过的残酷社会给我迎面一巴掌,最擅长的幻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当父亲早年在广东打工落下的旧疾复发,不得不再次向朋友开口借钱——诸如此类琐碎的事让我感到挫败。我心烦意乱,偏头疼如鬼魅难缠,有时发呆到深夜,手上的键盘也敲不出字。
那种可怕的坍塌重新降临,如绵软的爬虫从童年蔓延而来,包裹着我,啃食着我,淹没了我。我再次看到赌博失利后的父亲暴跳如雷,看到奶奶困于穷苦的生活唉声叹气,看到那些人把我堵在角落威胁我成为替罪羊,看见为了土地费尽心血的亲朋……我为此焦虑、恼怒,彻夜难眠,好不容易睡着也常常惊醒,身体里像空出一个大洞,要用食物填满才有安全感,换来的是日益肥胖。
浑浑噩噩时,我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他还是一个小孩,笑死人,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竟然有那么疲倦的眼神。他透过遥远时空凝视我,那双眼胆怯又顽强,灰暗中摇曳着些许亮光。他似乎在说,过去那么艰难都过来了,现在害怕什么?我如遭雷击,是啊,我在害怕什么呢?我害怕无法摆脱童年的梦魇,我害怕实现不了理想,我害怕陷入父辈的轮回。这些害怕阻碍着我,却也是我前进的根本,所谓理想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
那段时间是成年后的低谷期,我没有击败消极,幻想中的勇敢、果断终究是虚幻。不过还是慢慢度过了,生活中的许多坎坷都是这样,过着过着就成了闲谈。我继续保持创作,关于过去的文章一篇篇写出,也慢慢得以发表。新的一年,我拿到毕业证,签下工作,收到了些用稿通知,获得了一笔可解燃眉之急的奖金。我继续写,我知道自己停不下来,文学是一条不归路。我调整状态,告诉自己太阳准备升起,熬过眼前这段黑暗就能到达明天。
我慢慢满血复活。我的创造力是一口年轻的喷泉,铺满一页又一页的电子屏幕。我不再满足于书写过去。过往记忆是时间持续死去的尸体,我要看到时间还生动跳脱的模样,看到现在,看到未来,于是我提笔写科幻小说,构建遥远未知的图景。面对过往让我感到沉重,却是一件为了往前走而不得不去做的事。科幻创作让我感到满足,这是接受自我后的释放,是摆脱粗劣模仿后幻想的决堤。回头遥望,从初二阅读第一本书后提笔,已经写了十年,将整个青春奉献给了这件令人着迷的事。从第一次接触文学开始,它就不断给我前进的力量,让我大胆迈出一步又一步。
六
成长不只是身体的长高与肥胖,也是经过迷茫、解构与顿悟的心灵史,和大多数人相似,又不完全一样。
童年的遭遇让我对外界充满警惕与疑惑,为此进行着一场漫长的追问,通过阅读与写作,通过偷窥世界、独自思考与背起行囊远行。这场追问在西藏之行时最强烈,身体越向西,越进入高原与荒凉寒冷地带,心灵越朝故乡走,回到童年深处与苦难开始的地方。我已得到许多答案,我想我还会得到更多答案,虽然最终难免一个又一个都被否定。
世界纷繁多变,记忆杂乱无章,我隐约记得最开始的创作源于一堆破烂玩具。父母劳燕分飞后,父亲性情暴躁,我不太愿意与他说话,生活愈加贫困,唯一能缓解乏味的黑白电视机被他霸占,我又不得离家游玩时,只得把心思放在那堆玩具上。玩具有的从幼年积攒而来,有的是去捡破烂时意外所得,洗干净后成为宝贝收藏,有折翼的飞机、断腿的机器人、铲斗丢失的铲车……我将它们分成两个阵营,互相攻击,嘴里发出机枪嗒嗒嗒或者开炮轰隆隆的声音。父亲朝我的屁股踹过一脚,觉得脑子有病的小孩才自言自语。我不再配音,将战场移到更隐蔽的地方,从两个阵营到五六七八个派系,小石子与冰棒棍也成为人物、势力、权力的象征,也不再是杂乱无章的攻伐,逐渐有了复杂的利益关系,你来我往,纵横捭阖,一个故事或一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需要持续演绎好几天,我将童年的漫长岁月消耗在这些大人认为毫无价值的事情上。
难以忘怀的年月,爸爸有一辆忠诚的、任劳任怨的二十六寸永久牌自行车。自行车前轮爆胎了没钱修,尽管只要几块钱。没气不敢骑,会荡坏轮毂。可没自行车骑也不行,那是我家唯一的交通工具。爸爸想到办法,把从垃圾堆捡回来的旧轮胎削成条,卷好,塞进自行车前轮填充。虽然没有气胎稳,但不伤轮毂,不怕钉子尖石,更耐用了。此后我再骑出去,成了被嘲笑的对象。不过我不在意,我生来就被嘲笑。我斗志昂扬,拼命地踩,要和他们争个高下。他们的车太宝贝了,在平坦的水泥路上或许很快,但到了野外的坎坷小道,只有我敢不顾一切向前冲。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梦想不过是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我渴望长大。如果我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完好的自行车,我绝不像他们那样懦弱,我要骑出光一样的速度,冲进狂风暴雨中。他们会害怕未知的恐怖,我不怕,我会挥舞双臂呐喊,像最后一个战士冲向千军万马,跌跌撞撞但不会倒下,雨滴是密集的箭穿透我的血肉我的心脏却穿不透我的勇敢。隆隆雷声多吓人,万物颤抖哭泣,我发出疯癫的笑声,骑着我的自行车朝未知的前路冲锋。哈哈,我要碾碎闪电,碾碎乌云,碾碎一切阻挡我的妖魔鬼怪。我的自行车碾碎一切,我的想象力碾碎一切。看看吧,我从小就与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也能写出和他们不一样的文字。
我终于长大了。写作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在构建各类文字中得以心安、得以蜕变。天马行空的想象伴随我走来,成为我赖以生存的资本。因此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感到孤独,反而觉得这个世界热闹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