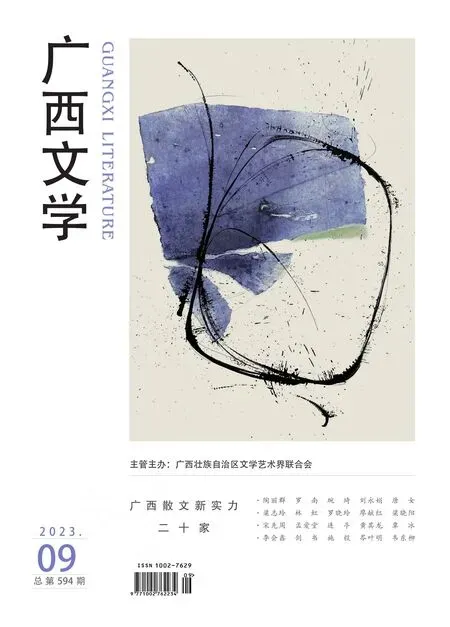追逐,向暗处
2023-10-22宋先周
宋先周
一
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清晰记起那场追逐……
那天午后,阳光正好,天空微蓝,洁白的云朵在空中闲逛,秋蝉声疲惫嘶哑断断续续。
突然,一只油亮金黄、身形硕大的老鼠,从屋后草垛里窜出来,它轻轻地将虚掩的灶房木门挤开,在门口贼眉鼠眼地好一番扫视,在没发现异样确定安全后,鼠步便轻缓舒展起来。它熟练地顺着墙角爬上灶台,到它熟悉的铁锅里翻找食物。
灶房门轻轻的“咿呀”声和鼎罐盖细细的“嘎嘎”滑动声,惊动了正专注往灶孔递柴火的父亲,父亲抬起迟缓而沧桑的头颅,往灶台上一望,瞬间就与老鼠对上了眼。他俩四目相接,人鼠都瞪圆眼珠,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下来。一人一鼠,一动不动,各自都试图以眼神射杀彼此。说不清是愤怒还是惊慌,片刻之后,他们又各自忙碌起来,老鼠连滚带爬落下灶台,父亲飞快奔向灶房那扇木门,封堵了老鼠退路。老鼠在灶房里胡乱转了一圈,又往堂屋方向逃窜而去,父亲叫嚣着紧紧跟随,人与鼠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
他们经过厢房、卧室、小楼……
他们躲藏、翻找、逃窜、怒吼……
老鼠在前面抱头鼠窜,父亲在后面步步紧逼。
老鼠身手矫健,对屋内的所有房间驾轻就熟。如果不是父亲的步步紧逼,我猜这老鼠的脚步应该是安适的、惬意的,是可以自由踱着方步的。从它逃跑的路线不难看出,它是我们家的常客,是不敢和我们团聚偷偷躲在暗处的重要家庭成员之一。
可是,父亲决定要将这个不受待见的家庭成员驱逐,决然要灭掉这个仿佛很重要实际却很讨人厌的成员。今天,奔走在老鼠身后的父亲,更像一只身手敏捷的豹猫,他老去的身形仿佛回到青壮年模样,原本笨拙的身体突然灵动起来,在老鼠身后步步紧逼穷追不舍。老鼠跑到哪儿,父亲跟到哪儿,好几次都差点把老鼠生擒活捉。无奈,关键时刻,要么老鼠从父亲胯下一转就逃走了,要么老鼠躲进旮旯里,父亲想捉却捉不着,只能踢打障碍物,用高分贝的怒吼把老鼠赶出来。有两次,老鼠穿过墙洞一下子就逃到另一个房间。父亲也是急红了眼,在房间里跟着老鼠转来转去。老鼠慌不择路,突然逃到火坑边,这老鼠速度实在太快,差点没刹住车,直接冲进火炕里。刹那间,机敏的老鼠转了个急弯,将身子扭成直角,硬生生从火炕边折转,绕到柴尾巴来。急切追来的父亲忍无可忍,脱下他右脚那只漏了个大洞的解放鞋,狠狠地砸了过去……
可惜正在火炕上煮着的豆腐菜,一整锅被打翻,汤汤水水浇进火里,扬起一片白茫茫的火灰,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
“吱、吱吱、吱吱吱……”那只硕大的老鼠惨叫着,歪弹歪弹地在角落里挣扎。
“操他娘的,坏透了的家伙,这次你逃不掉了吧!”父亲喘息着,长长地舒了口气。
那只“扳弹扳弹”的老鼠在角落里努力折腾,它的身体弹起来又落下去,反反复复,身体和火炕右侧的板壁相撞,发出“咚咚咚”的响声。
二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体形如此硕大的老鼠。
这只被砸中的老鼠,体形大得实在吓人,体重怕是要有一斤多了吧!
那时候,我正在灶火边煮菜,父亲和老鼠的到来,扰乱了火炕边的秩序,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弄得不知所措,战战兢兢地站在对面的角落里。
心情稍稍平复之后,我把目光从老鼠身上转移到父亲脸上,我看见父亲那张漆黑的脸由凝重变得舒展,最后渐渐弥漫起胜利者的神态。
当天,我们家中午的菜泡汤了,全家人都不说话,母亲从老坛里掏出腌制的酸辣椒,抠来两块豆腐乳,拌着米饭,我们都吃了个囫囵。
父亲没吃午饭,不知他是对自己打翻菜锅有所愧疚,还是害怕面对母亲那幽怨的眼神,或者是对鼠辈们的仇怨太深,使他没了食欲。
父亲从大门背后找来废弃钢筋打造的“捅猪棍”,将那只还在挣扎的老鼠拎到堂屋,用“捅猪棍”朝着老鼠的肚皮狠狠地扎下去,将老鼠稳稳地钉在堂屋正中央。
再次疼痛,使老鼠叫声更加尖锐凄惨,它不断蹬脚,试图挣脱,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它越是挣扎,失血就越多越快,断气的速度也在加速。我看见老鼠的两只眼珠子已经滚出了眼眶,血肉模糊,整个场面让人不忍直视。
活该。我在心里骂了一句。
也许这老鼠本该命绝于此。
按常理,大白天,大老鼠很少出动,哪怕要出动,也得先派几只小老鼠出门试探敌情。
或许,在我们家,这些老鼠太过安逸、太过嚣张了吧!
我不知道,父亲对老鼠的仇恨究竟到何种程度,才会下如此狠手。要知道,平日里父亲连鸡都不轻易宰杀,甚至都很少大声训斥孩子,我们兄弟五人,哪怕做错事了,父亲通常也是跟我们讲道理。不像母亲,手里时常提着马鞭,有随时抽打我们的可能。今天,父亲却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收拾这只老鼠。看到父亲将老鼠钉在地上时那种青筋直冒咬牙切齿的狰狞表情,我突然发现父亲和原来不一样了,他对这只老鼠的暴虐,彰显他凶悍的另一面。
父亲的行为让我感到了恐惧。
面对这场血腥,家人们多选择逃离,那只老鼠还在堂屋里呻吟着,我打那里经过,总会不自觉地瞄它几眼。
母亲忍不住问:“他爹爹,你就给它个痛快得了,然后拿去菜园里埋起来,往后还能化成肥料,你搞这种丧德的事,让人心里瘆得慌,会不得好报的。”
父亲说:“你懂个屁,我特意放在这里,让所有的老鼠看到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让它们感到害怕,以后不敢再来侵犯,我要把它钉到明天早上。老鼠喜欢在夜间活动,我要让那些夜晚偷偷摸摸进家来的老鼠看到这只老鼠死亡的惨状,让这种恐惧成为老鼠们今后的噩梦,这场噩梦最好笼罩它们一辈子……”
父亲顿了顿,再一字一顿地说:“这叫‘杀、一、儆、百’,晓得不?”
母亲不再说话,从老鼠身边绕过,下地干活去了。
我们也跟着母亲各自散开。
但是,这一整天,我都安不下心来,书读不进,家务干不了,家庭作业也没完成,心里慌慌张张,总在惦记着那只老鼠,总在心里猜测,那只老鼠究竟断气了没有?它还有多少血可流?别的老鼠看到这场面真的会害怕吗?父亲这么做,真能杀一儆百吗?我们家之后会不会就能告别鼠患?
想着想着,我又到堂屋去偷偷瞄它,看一眼又转过头来,有点害怕,我不知道我是怕老鼠死了,还是害怕它有神灵附体,又突然活过来。
晚上,我在小矮楼上,睡得浅浅的,我想听听其他老鼠进家来看见这场面的反应。但是我啥也听不见,家里非常安静,往常老鼠相互追逐打闹的声音,今晚我是真的一点都听不见了。
今夜,家里到处静悄悄的。
午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就想爬起来,再去堂屋看一次老鼠。
但是,父亲临睡前专门叮嘱:“夜晚,谁也不能到堂屋来。”
爷爷过世的时候,将他的“魔公”道法“吐词”传给了父亲,父亲接过家族秘传的重任,经过几年的“修炼”,也懂一些“歪门邪术”,做过几个道场,办过几场法事,上过“刀山”,下过“火海”,帮人消过灾、驱过邪。在那些蒙昧的年代里,父亲在周边村寨有点威望。当晚,父亲临睡前,在堂屋的神龛上了香,做了法事。他嘴里念念有词,手里的铃铛摇得叮叮当当响……
父亲说,他要在我们家里办一件大事,要一次性消灭老鼠。父亲认为灭鼠不能仅靠捕杀,因为老鼠是捕不尽杀不绝的,灭鼠重点还得让它们惧怕,让它们自觉逃离。
我睡不好,也不敢起身。我害怕父亲那种阴森森的吟唱以及念念有词的表情,害怕万一真有一大堆老鼠在堂屋集结,来报复我们。
可是,今夜,平安无事。
三
真应验了那句老话:“越穷越见鬼,越冷越吹风。”
鼠患严重的年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家才刚刚解决温饱,老鼠就在我们周围泛滥成灾。越穷的地方,老鼠越多。那些老鼠像是从四面八方逃荒来到岩洞平,在这里安顿下来并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再也不走了。
岩洞平家家户户,为鼠所困。
父亲对老鼠应该是隐忍到了极限。他枕头的棉絮被老鼠偷去垫在鼠洞里,村里唯一的老学究许三爹临终前送给父亲的两本古书,被老鼠撕咬成一堆细碎的纸屑。父亲作为大队会计,记账的本子也被咬烂了,好多细账对不上,难怪他要对这只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自闯进家里来的老鼠动用极刑。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堂屋来,想继续看看那只老鼠的最终结局。可是堂屋空空如也,“捅猪棍”回到墙角,那具老鼠的尸体不见了。
我斗胆问父亲:“老爹,那老鼠呢?”
“被昨晚进家的其他老鼠吃完了。”
“不会吧?老鼠也食自己同胞?吃得一根鼠骨都不剩?”
“你不懂的事情多着呢。”
父亲话语坚定,表情自然,容不得我不信。
我一头雾水。不知所以然。
其实,那只老鼠尸体,清晨被父亲拿去撂了。这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但是那时候,我却深信是夜里闯进家里的老鼠把它吃掉的。
这事过后,还真是神了,连续好几天,我们家里一只老鼠也看不见了。我感觉是父亲那种“非遗”的驱鼠法事初显成效了。
如果不是后来老鼠经常来犯,而且来得更凶猛,我想,我一定会缠着父亲,跟他学习那些神奇的“歪门邪术”,让他像当年爷爷给他“吐词”一样,将祖传的“绝学”“吐词”给我。
可惜,这种难得的清净仅仅维持了五天。五天之后,我们家的老鼠精神状态似乎又复原了,鼠患恢复如初。不,应该是愈演愈烈。
不知道是父亲的捕鼠“邪术”失灵了,还是老鼠和人类截然不同。人类的“道法”制约不了它们。但是,我们不敢质疑父亲,都知道有“马失前蹄”,何况还是我的父亲。
习惯少说话的父亲,又一次陷入沉默,他的沉默持续了两天。两天后的傍晚,父亲把我们召集起来,说要做一个重大决定,他要将捕鼠大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开展大规模捕鼠行动。
最初,父亲想到了养猫。猫捉老鼠,天经地义。
那些年,猫很贵,又很难买到。关键是不知谁在岩洞平一带散布谣言,说:“养猫穷,养狗富。”还举了几个例子,说你看彭老三,之前家境不错,后来整了只流浪猫回家,整天抱着猫玩,现在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相反,你看韦老大,儿女多,家里穷,后来养了一只狗,现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日子越过越红火……谣言有板有眼,说多了,大家也就信了。这导致我们岩洞平家家户户都养狗,却很少有养猫的。岩洞平零零星星地养了三只猫,父亲托了好多亲朋好友,好不容易才从贵州亲戚家顺来了一只白猫。
奇事天天有,我家特别多。
来到我家的这只白猫,是猫家族的另类,是一种很奇葩的存在。
自从白猫进我家以来,就没有过猫的样子。它每天只顾自己梳妆打扮臭美,我看见它最多的动作就是不断地用两只前脚给自己刷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猫洗脸”。奇怪就奇怪在,我家的白猫它不捕捉老鼠,不知道它是害怕还是不会,或者是它厌倦了鼠肉。反正,它每天准时在猫碗里等着我们喂食,这只不捕鼠的猫还特别挑食,它吃不惯素餐,隔三差五就想着我们给它点肉。那时候我家逢年过节才能见到肉,别的时间,我家生活素得连猫都怕了。猫在我们家渐渐瘦下来,我们只能从炒菜省下来的猪油里,挑一点给白猫做成油炒饭,炒得非常香,还加点香菜,猫才喜欢吃,只有吃了这油炒饭后,这猫才焕发出精气神。
为训练这白猫捕鼠,我好不容易生擒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老鼠,担心老鼠崽子逃跑太快,白猫追不上,我又把老鼠弄得半死不活,把老鼠的尾巴砍去,才丢到白猫跟前。哪里想到,我们家白猫不为所动,只象征性看了那小老鼠几眼,然后就渐渐后退,最终转身离开。那种画面,反而让我感觉在猫的面前难为情起来。
有几次,我发现白猫看着有胆大的小老鼠到它吃剩的猫碗里觅食,它竟然也装瞎,毫不理睬。
这种状况,又让父亲忍无可忍了。父亲决定把自己亲手抱回家的这只白猫处理掉。他当然是要拿去卖掉,这样可以换几个钱补贴家用。毕竟“坏事传千里”,我们家白猫不捉老鼠这事大家都知道了,父亲抱着白猫三次去集市上都没卖出去。父亲又想,算了,拿去送人吧!可是也没有一家人愿意收养这只白猫。“养猫穷”的谣言已经流传开去,大家都穷怕了。后来,父亲把白猫抱到离我家比较远的另一个村子,狠心地把它丢弃了。
异地丢弃这白猫时,父亲站在原地,思绪翻飞,目光迟滞,胸口起起伏伏。
“天生天养,由它去吧。”
最后,父亲甩开衣袖,抹一把额头的汗珠,背过身撂下这句话,就匆匆返程。
可是,当天晚上,那只白猫又自己寻了回来,半夜,它在我家门前“喵喵”地叫唤,父亲拉开门,那猫一看见,便躲躲闪闪,有点胆怯,不敢进屋。
母亲的恻隐之心再次被触动,跟父亲说:“他爹爹,算了吧!别折腾了,这白猫虽说不会捉老鼠,但家里有它的叫声,那些不熟悉白猫性格的老鼠也会被震慑,不敢太放肆,就留着吧。”
白猫就这么又一次在我们家待了下来。
四
生活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下去,老鼠仍然时不时骚扰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鼠尿的腥臭中,我们的米饭里,时不时会夹着几颗老鼠屎,我们把那些老鼠屎挑起丢弃,照样把米饭香香地吃下去。都说“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汤”。那个年代,老鼠屎在我们餐桌上变成了常态。
我们心情极度糟糕,又无可奈何。
再次回到我家生活的那只白猫,在半年后的一个夜里,像着了魔似的,突然疯狂地上蹿下跳,边跳边蹿还撕心裂肺地叫,那叫声惨无人道,叫得人心惶惶,让人毛骨悚然。父亲拿起扫把去追打,边追打边骂,你这只背时的猫,你这只懒鬼猫,你这只嘴馋的猫……
白猫逃过了父亲的追打,换一个地方又继续叫。
白猫的这种叫声,不只我们无法入睡,就连放肆的老鼠们也不敢出洞来了。那几天,家里除了这猫叫声,都安安静静的。
白猫一边叫唤,一边用屁股擦拭门框,门框的方楞上,白猫的血迹清晰可见。
母亲认真审看了白猫的举动,跟父亲说:“他爹爹,不得了了,这猫想谈恋爱了,它这是想找伴呢!”
父亲斜眼瞧了瞧白猫红肿的屁股,说:“是嘞。不得了了,可这如何是好?”
母亲说的“想找伴”,就是说猫发情了,这猫撩骚了。
听到这话,我又来气了。这整天不务正业不捕老鼠,彻头彻尾窝囊至极的白猫,它也好意思有七情六欲?谁给它的自信和资本?
这让我对白猫的鄙视又加重了几分。
我们家的白猫是一只母猫。不只我们家,我们岩洞平喂养的猫,都是母的。大家就想让它们生出更多的猫崽来,希望它们能把整个岩洞平的老鼠赶尽杀绝。但是,没有公猫,生猫崽的问题,母猫们也无能为力。
正因为如此,我父亲母亲才都发出“不得了了”的感慨和无奈。
在一个月朗星稀寂静的夜里,我们家白猫朝着后背山奔袭而去。
母亲说,这下好了,由它去吧。母亲早就知道,山后面有一只野猫,是公的。
我们家的白猫终于被爱情俘虏,和那后山野猫私奔去了。
白猫一走,我们家的老鼠又猖狂起来,成群结队,在楼上,在瓦檐缝隙里,在墙洞中,有时在床底,到枕边、蚊帐顶上……
我们家里,老鼠脚印一排排,老鼠屎一堆堆,老鼠尿臭烘烘……
每天早上,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上去,扫出一大撮箕的谷壳,清理一大堆老鼠屎。父亲一边扫一边骂“挨刀的老鼠”“滚坡的老鼠”。
我们家用来装稻谷的大箩筐,被老鼠咬出各种各样的洞,装白米的木柜子也被老鼠啃出四个大洞来。散放在楼上的苞谷棒,被老鼠们糟蹋成一个个狰狞的模样,每一个苞谷棒都被咬几口,每一个苞谷棒又都留有几颗玉米粒。
母亲也骂开了:“可恶的老鼠,养崽没有屁股的老鼠,挨刀的老鼠啊,你们偷吃苞谷棒,倒是一个个给我吃干净呀?吃干净一个再啃下一个不好吗?你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我如何收拾呀!”
五
总得有个了断吧,人和鼠的斗争,总要有个交代吧。
这个世界,不可能做到“人畜共存,相安无事”。
“再让老鼠这么泛滥下去,无休止地糟蹋粮食,我们一家人恐怕又将回到饿饭年代。”父亲在神龛面前无可奈何地自言自语,他的头颅左右晃荡,像拨浪鼓。
提到饿饭年代,我们全家就又恐慌起来。
若不是为了能吃饱肚皮,若不是爷爷把最后的那根皮带都炖来吃了,我们家也不会背井离乡,从黔南州边陲之地,来到这个比老家更闭塞的地方。虽然这里山高路远,但是地肥水美呀!只是,这些年,粮食种出来后,却凭空让一群老鼠分享,让人咬牙切齿。如果这些老鼠单就偷食也就罢了,关键是鼠疫严重,很多人都会患一些莫名其妙的病,寒战、高热、头痛、呕吐、呼吸困难,甚至全身脱皮,手脚溃烂……
至今石家爱唱歌的大儿子石飞鱼都还躺在屋子里,瘦得不成样子,半死不活的,喉咙已经沙哑,说话都很困难,哪还能唱出歌来。我们不知道石飞鱼是不是患了鼠疫,但他的病症总让人不自觉地往这方面去想。
想到这些,就难免让人冷汗直冒,手脚发麻。
父亲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安排人员去高楼上看守粮食斗老鼠,老鼠来了,能捕杀的就当场消灭,不能捕杀的就努力驱赶,决不允许老鼠在家里横行霸道。
正在读小学的我,被父亲首先选中,似乎也只能选我。大哥已经成家立业,另起炉灶,就住在我们家隔壁,跟我们一样被鼠所困。二哥在县城上高中,每学期才回家一次。三哥在乡里上初中,只能周末回家,姐姐又出嫁了。而我,在村里上学,每天早出晚归,只有我的时间符合。
父亲在高楼上那几大箩筐稻谷的中间铺一张席子,撂一床毯子,要我睡到高楼上去。
我不得不应承下来。但是应承下来,我就害怕了,不只是怕老鼠,还怕那高楼里的空旷。我一个人在楼上,感觉太宽太空了,我的心失去了依靠,我魂不守舍。但不敢说出来,怕万一惹父亲不高兴了,父亲捕杀那只硕大老鼠的场面在我心里晃荡。
我不得不跑到隔壁寨子里,叫来三姑妈家的二表哥。那时候,比我年长四岁的二表哥和我同班,他胆子比我大。在班里,我的成绩比他好很多,所以我讲的话,表哥也愿意听,我有请求,表哥也会满足。因为我跟二表哥承诺,夜晚到我家来我可以帮他补补课。
二表哥本来就要求上进,恼恨上学晚了,加之农忙时,读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一跟他说,他求之不得,马上背起书包,和我一起来到岩洞平。
夜晚,点一盏油灯,我们兄弟俩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功课。偶有窸窸窣窣的老鼠来犯,我们站起来吼几声,那些老鼠就又退了回去。
后半夜,我们都犯困了,我们轮流睡,醒着的可以一边守老鼠,一边预习功课。我让表哥先睡,我值第一班。二表哥一躺下去鼾声就起来了,不知不觉中,我也被鼾声感染了,跟着表哥进入梦乡。
第二天,父亲又扫出一大堆空谷壳。但是比我们不在楼上看守时要少得多,父亲觉得看守老鼠初见成效,要我们再接再厉。
为了解决我们后半夜的瞌睡问题,我和表哥到对面坡采摘一大筐酸酸的杨梅放到床头边,瞌睡一来,我们就含两颗在嘴里,我俩一边皱眉,一边清醒过来。那些夜晚被“酸醒”着,我和二表哥都不做功课了,我们闲聊,说学校的事,说那个经常欺负我们外号叫“歹毒”的韦衡同学。一说起韦衡,二表哥就咬牙切齿。韦衡在学校经常逼迫同学们给他“保护费”。他把这些钱拿去小卖部买饼干买糖果。我和二表哥藏了很久不舍得花的两毛钱,就是被他强行搜走的,二表哥不从,跟韦衡拉拽,还挨韦衡狠狠揍了两拳,二表哥的泪水都被打出来了。
那天夜里,在我们心中“歹毒”的韦衡比老鼠更可恨,他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硕鼠。我们诅咒他,上山砍柴跌下坡,下河捉鱼被水淹。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像父亲钉老鼠那样把他钉住。当然,我这只能是空想,我们把怨恨撒给这些来犯的老鼠们。那夜,我们在米堆的背阴处发现一个鼠窝,里面有六只刚出生的小老鼠,我们靠过去的时候,鼠妈妈迅速往外逃跑,但跑到安全距离,又回过头来盯着我们。我们不动,鼠妈妈也不动,我们追过去,它又快速撤走,我们走近鼠窝,鼠妈妈又赶过来,龇牙咧嘴。二表哥一棍子扫过去,鼠妈妈当场毙命。鼠窝里的小老鼠都还没长毛,全身红粉粉的,感觉有点恶心,我不敢触碰,二表哥一个个捉来,打一大碗水,把这些老鼠崽子都溺进水里,直到它们都死去。
二表哥是咬着牙齿干这事的,仿佛他摁进去的不是这几只小老鼠,而是十恶不赦的“歹毒”韦衡。
整夜不合眼,换来了我们整楼谷子的安宁。到学校我们就开始犯困,整天昏昏欲睡,被家访是必然的了。
我们的郭老师喜欢喝两口,平时没去家访,他就自己在家喝。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郭老筛”,也叫“筛二两”。他只是喜欢喝,酒量不大,二两即可。我父亲跟郭老师是酒友。可我父亲的酒量是郭老师的好多倍。
郭老筛刚走到三岔路口,就大声喊起来:“老宋,在家吗?”
“在呢。郭老师来了。”父亲应和着。
那时,父亲正在用一根长长的竹子做“响篙”,父亲将一头均匀破开,另一头绑实了,拿着绑实的那头一摇,就会发出响声。在院子里晒谷子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这东西驱赶偷吃的鸡群和鸟雀。父亲做这根“响篙”,是打算要我们带到楼上去,夜里用来驱赶老鼠。
“老宋,看看你忙啥?”
“不忙,谢谢,进来,进来……”
父亲放下手中活路,迎上来,拉着郭老师的手说。
“难得老师到家,我们进家坐下来,今晚好好喝两口。”
母亲杀了一只母鸡,炒了一碟黄豆。父亲和郭老筛就喝上了,他们边喝边聊,今天他们说话有点绕,他们先聊收成,再聊谁家孩子读书好,谁考上哪儿了,最后才把话题引到我身上。
郭老筛说:“老宋啊!这两天你的老幺不对劲,上课老想打瞌睡。”
说到这里,郭老筛又抿了一口酒,接着说:“老宋啊,大家都知道你望子成龙心切,但也不能揠苗助长哦,要讲究规律。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夜晚你给他加码了?”
父亲遮遮掩掩说:“是,是,是,我关心不够,晚上他太用功了。这不,为了学习,他都把他二表哥一起叫来,晚上两个崽子点着煤油灯看书,煤油都消耗了我好几斤呢。”
父亲没有把安排我守老鼠,保护粮食的事情说出来。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当晚,我不知道“筛二两”的郭老师究竟筛了几两,反正他是醉眼迷离摇摇晃晃回去了,没喝多少的父亲好像也有点醉意,红红的眼睛盯着我和二表哥,仿佛要看透我们的未来。
六
自那晚后,我又回到我的小阁楼上,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床上,再没有去跟随那些老鼠消耗时光了。
我从高楼下来了,父亲拿出决斗的姿态,自己上到高楼去。
白天,父亲找来一些黄泥与少量细沙搅拌均匀,用这些泥沙将我们家墙脚低楼板间那些被老鼠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鼠洞给封起来,堵住老鼠的通道。
夜里,父亲拿着他专制的那根“响篙”在我和二表哥睡过的席子上躺下来。
此后的夜里,楼上断断续续会有“响篙”敲打楼面的声音。好长一段时间,我感觉家里的老鼠真的少了,偶尔一两只进到家来,也被父亲就地处置了。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见父亲提着一两只老鼠尸体埋到菜园里的柚子树下。但是父亲捕获的都是一些鼠兵鼠将,是一些个小年少的鼠辈,并非实质性的可称“鼠王”的大老鼠,至少没再发现任何一只可以跟父亲钉在堂屋中央的那只毛色油亮金黄的老鼠相提并论。
我心里有一点隐隐约约的恐慌,我想这样的平静里,会不会正在孕育一场盛大的鼠荒?
果然,平静在一周后被打破了。一群老鼠从楼上回到地面,它们避开与父亲正面交锋,取道防御相对薄弱的地面,它们翻箱入柜,掀锅揭盖,火坑边、堂屋里、厢房后,到处都是老鼠的痕迹,满地都是老鼠屎。
真是防不胜防啊!
这天大约凌晨两点,挂在空中的下弦月还非常明亮,飘在天空里的云朵绕着月亮走,让月光直直地泻到地面上来,把夜晚照亮成另一个白天。这时候,我突然被母亲叫醒。母亲的叫声是从堂屋传来的,声音的恐慌里夹杂着一丝兴奋。
“老幺,快起来,快来帮忙……快点,哦哦哦,快快快,来不及了,老鼠要逃跑了……”
母亲的声音惊悚、慌张。叫喊声掺和着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的声音。
我穿着个大裤衩,翻身爬起,尽管睡眼惺忪,却不敢放慢脚步。
我跑到堂屋,看见母亲用一只大竹筛子,牢牢罩在堂屋右角的大石磨上。石磨孔里有东西不断撞击筛子。不用猜,那是一大堆的老鼠。母亲用尽全身力气,咬紧牙关压着筛子,不让一只老鼠逃出来。
我冲上去,爬到磨盘上,一屁股坐到筛子上,将那群老鼠压在我身下,压在石磨孔里。我发现,我竟然那么勇敢。
这时候,楼上的父亲也快速滑下楼梯,我们三人联起手来,与这群被控制的老鼠决斗。
父亲找来火钳,拿来一只铁碗。他用火钳在竹筛子上打了一个孔,将火钳插进孔里,一只一只把老鼠夹出来,夹出一只,马上就叫母亲用铁碗罩住竹筛的孔。父亲夹出一只,就敲死一只,再夹下一只,再敲死下一只,如此反复。
老鼠的惨叫声和我们各自忙乱的脚步声叫喊声撞击这午夜的月光。
忙碌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将石磨孔里的老鼠全部清空。父亲、母亲和我全身湿得可以拧出水来。我们歇下来的时候,天也渐渐亮起来,天边泛红,下弦月还没落下山去,和朝阳一起挂在天上……
那些年,我们家那大石磨尽职尽责,每天都要磨出若干玉米粉,拿去煮猪潲喂猪。石磨孔里经常残留玉米粒和玉米粉,老鼠从食物丰富的高楼上下到地面,可食用的东西少了,当发现这处有较多的食物后,就聚集起来,扎堆地往里挤。
父亲上高楼去以后,母亲晚上也没睡好,她偷偷关注这群老鼠好几个晚上了,母亲发现老鼠经常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出动,先是一两只进来,再是三五只,直到凌晨一点钟左右才聚集完毕。
这晚上,母亲把竹筛半盖在石磨上,留出一个半大的缝隙,然后不动声色地藏起来,待鼠群几乎全都进去之后,母亲蹑手蹑脚来到石磨边,猛地一下,将竹筛盖住……
这天晚上,我们共捕获老鼠四十四只,其中毛色泛黄的鼠王八只。算是大获全胜了。父亲将这群老鼠的尸体用麻绳绑成一大串,挂在门口的晾衣竿上。第二天迎来全寨人赞赏的目光。起初,大家怀疑我们家用了老鼠药,当他们看到我们家堂屋一大堆的老鼠血肉残留之后,才把拇指竖在我们面前。
七
这次胜利,让我们家在村子里自豪了好长时间。
诚然,老鼠毕竟还是老鼠,越捕杀,它们似乎繁殖的速度越快,我们全寨的人都在捕杀,但岩洞平的老鼠并不见减少。
村民们绞尽脑汁,用一切可用的方式,想一切可想的方法,捕杀一切可以捕杀的老鼠。彭家、谢家、韦家、冉家都是全员动手,男女出动,老少上阵。大家在捕鼠问题上,各显身手,献计献策。有安装铁猫的,有设置陷阱的,有装套索的,也有用弹弓气枪射杀的……
韦二哥甚至还把自己精心喂养的“撵山狗(猎狗)”训练成了捕鼠能手,那狗晚上出动,每天早上都能叼回一两只老鼠,尽管是“狗拿耗子”但并非“多管闲事”。看见这为捕鼠奔忙的“撵山狗”,我又不自觉地想起那只白猫,不会捕鼠的它,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大干促大变。岩洞平的捕鼠成效逐渐显现出来,各家各户每天都能捕捉三五只,多的时候有十来只。地里的庄稼似乎也趋向平安了。
可惜,这事又没长久。老鼠不是没有,只是它们行事更小心了,出动更谨慎了。为了生存,老鼠不惧怕也不消停,经常冒险出没在风险之地。但凡在同一个地方,只要有一只老鼠被捉,别的老鼠就再也不会出现,它们经常采用“工兵战术”,用一些小老鼠去试雷。
大家无不感慨:我们岩洞平的老鼠怕是都成精了吧!
这些老鼠已经进入一种无法描述的境界,它们有吃喝不愁的快感,有行稳致远的谋略,有躲避捕杀的方法,并且繁殖的速度比起我们没大规模捕杀前要快得多。
这天,我家对门,彭老光的小儿子,在熟睡的夜里,竟然被一只老鼠将他右边耳朵咬了一大块。彭老光对老鼠的憎恨到了决绝境界,说起老鼠,他都把嘴唇咬出血来。无可奈何的彭老光从集市买来几包老鼠药,他把老鼠药拌了一小盆玉米,撒在他家房前屋后。第二天,老鼠的尸体随处可见,彭老光一大早就在清理战果。那早上他捡老鼠尸体捡到腰酸背痛,最后把那些大大小小的死老鼠堆在一起,药死的老鼠尸体共计一百三十九只,这还不包括没找到的和在死亡边缘逃走的。当然,他们家也搭上十八只鸡的性命。他之前打过招呼,我们其他家都将鸡关在笼子里,暂获免死金牌。
本来,这种自残式的灭鼠,在寨子里是杜绝的,就怕引起恐慌,各家各户都有些害怕,一怕牲口死于非命,二怕小孩子出于好奇,触碰了老鼠药拌过的食物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种用药的捕鼠方式本来就是一种冒险,但是大家原谅了彭老光,谁的孩子被老鼠咬了谁还不憋着一口气呢?
为缩小牲畜死伤范围,彭老光又把撒在屋子周围剩下的玉米粒扫干净,深深地埋进土里。
八
时光飞逝,外出读书工作好多年,岩洞平也大变样了,寨子里的人家都陆陆续续搬到镇上居住。岩洞平变成了一个空空的山寨,烟火气没有了,牲畜都被赶进山里集中放养,房前屋后的鸡鸭不见了,就连猪圈也荒芜废弃了,寨子里的人们走出来常被外人问起:“你养了几头猪?”回答的总是:“看情况。”因为岩洞平都有杀年猪的习惯,这些年,大家都把猪“养在口袋里”了,大家在外务工,口袋鼓起来了,需要宰杀的年猪,买就是了。
想吃土货,岩洞平已经很少有了。
老去的父亲,在我们家还没搬到镇上前,就在岩洞平提前走完自己不太长的一生,他的生命定格在五十七周岁。
这天,正逢父亲祭日,我走进寨子里,突然感觉一种死一般的寂静,我的心也突然变得没落。我想起父亲,想起那些年跟老鼠斗智斗勇的岁月。此时我很想知道那些老鼠还在不在?与鼠为敌的父亲,坟地周围有没有老鼠出没?老鼠会不会打个地洞,进入坟墓里骚扰父亲尸骨?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会不会也遇见老鼠?他们还会不会继续争斗?
当然,我也想知道原先寨子里的那群老鼠是否安好?它们有没有足够的食物,岩洞平“空心了”,它们如何活下去?
我进到老屋里,老屋已被厚重的霉味包裹,屋内的空气带有一点淡淡的涩味,湿气很重,蜘蛛网随处可见。我在屋里到处转,从灶房到堂屋、厢房、卧室、小楼、高楼……我把老屋的角角落落走了一遍。最后回到门前,我又看见那盘石磨。如今,各家各户都用电磨了,石磨便被遗弃了。我家的石磨已经从架子上卸下来,摆在大门两侧,成为两个空洞的石礅,它们一阴一阳,孤独地在门口坚守。我弯下腰,坐上去,隐隐感觉到屁股下好像有东西撞击,我抬起屁股,里面空空如也,我仔细端详,那石磨孔里,还有一些或明或暗的斑点,像极了当年那些老鼠的血迹。
这次回到岩洞平,我多想再寻得哪怕一只老鼠,我要和当年的父亲一样,跟它们再来一场追逐。如果追到老鼠,我可能不宰杀,我要活捉它,我要跟它逗一逗,然后用一个精美的笼子把它装起来,带回城里。
但是,我看不到一只老鼠,就连一颗老鼠屎都寻不见。我竟然有些淡淡的感伤。
原来,有些斗争或仇恨是生活的必需,就像多年前,那场不休不止的捕鼠行动,就像那场鼠灾,就像我们经历的诸多事件一样。失去的真的就失去了,错过的也终将错过。
近几年来,我在城里,偶尔会遇见老鼠,它们依然躲躲闪闪,但我不再与它们斗争,不再追杀它们,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当年那样的敌视与仇恨,老鼠没进到我屋里,它们在它们的地盘,我在我的小屋。一旦有了残羹剩饭,我不自觉地想到那些老鼠。
我想,我近旁的这些鼠群,会不会与岩洞平有关。想着想着,我又翘首,面朝桂西北,向着岩洞平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