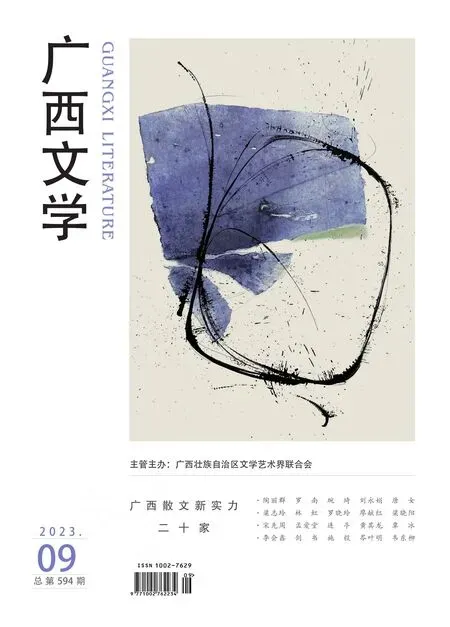布爹布奶
2023-10-22梁晓阳
梁晓阳
一
傍晚,我正在自家粪坑屋蹲着,突然听到了隔壁锅铲和锅头乒乒乓乓的碰击声,闻到了炒菜的香味,突然觉得有些滑稽,忍不住笑出了声。
隔壁是我布奶家,与我家的粪坑屋仅隔着一条五米小巷,布奶的厨房有一个用木格子做的窗户,有大人高,里面的声音和香味都从窗口飘出来。
1962年夏天,我的二布奶梁传兰嫁给了与她娘家房子仅有二十米距离的苗屋,布爹叫苗定德,苗家的老二。我阿婆陆氏对我父亲和我十一爹说,苗屋有两头牛,做田不辛苦,传兰是我的小女,嫁她到隔篱屋,好平时回来看看我同英寿,你们姐夫以后亦可以帮帮你们。
1963年秋天,我们老家的房子开建,先是锄屋地,在山边开锄,大屋占地按照房间分配要六百多平方米,就要锄掉半座丘陵,我父亲和一帮兄弟全部开锄,不分白天黑夜。隔壁的苗定德在传兰布奶的劝说下,也过来帮忙了。几个堂伯父都说,看来传兰到隔篱屋是嫁对了。我阿公阿婆在一边听了就嘿嘿嘿地笑。
我阿公未到五十岁就因木薯茎戳穿了脚背,此后一直生疮不能下地干活,靠偶尔给人算个八字挣几角钱,不久因毒疮发作去世了。七年后我阿婆过世。阿婆走前对我父亲和十一爹说,你们两兄弟要识得互相照顾啊,又对在床前哭哭啼啼的女儿传兰说,隔壁还有你这个大姐和大姐夫,生面人都知道有事要搭把手,何况你们是一家人。
第二年春天,屋前屋后的荔枝树开满了淡黄粉白的花,我父亲正在给屋背的荔枝树根除草,苗定德拿着钩刀上来,一声不响就把伸到他杆栏的三根荔枝树杈连枝带叶削了,那些盛开的荔枝花纷纷扬扬落地。我父亲好不容易种了这棵荔枝树,眼看长得快,还开了满树的花,却不料被这个称作姐夫的人削了个枝断叶落花飘,不禁大怒,大声质问他,苗定德,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就斫了我的荔枝木杈?苗定德一边往用钩刀将落到杆栏上的树枝钩走,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我斫错了吗?木杈遮住了我的栏杆,阻到我的牛吃禾秆了。
苗定德和一个细舅的吵架就这样开始了。我母亲也出来帮我父亲,把苗定德过去的所作所为全挖了出来,说到了两家隔邻田灌溉的事,把田坑全部拦住,水全部灌进自己田里,想不给别人生路了啊?就算对待外人你都不应该这样吧?何况是你细舅!布爹听了这话暴跳如雷,是不是姐夫细舅都是你们讲了准,有没有亲戚都由你们定!父亲就恼火地骂,讲这种话就知道你没文化!没想这句话气得苗定德暴跳如雷,我没读过高小,没读过农中,不是教师佬,就你读过高小,读过农中,做了教师佬!你一肚文化!你有文化做什么你大姐又嫁给我做老婆?
布奶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她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干脆说,你们爱怎吵就怎吵,反正我两边都不帮!唉,我真是好难做人了!这话激怒了苗定德,骂她,既然两边都不帮,你就是多余的货!布奶顿时嗷嗷大哭。
五月里的一个周六,我答应母亲一大早去放牛兼捡一把柴。我家的水牛是在我专心捡柴的时候闯到山脚下禾田里的,禾苗正在扬花,牛放肆地吃禾,蹄子践踏着禾田,米白色的禾花纷纷飞扬,从山脚下一直飞到山腰的我面前,还飞到了山顶和天空。我看见这些飞扬的米白点子时心里惊呼不好,赶紧扔了手里的柴就往山脚下冲,当我冲进田里牵到牛时,足足三分地的禾苗全都只剩下三十公分的禾头了,我吓得呼吸都变得紧张起来。偏偏这时,苗定德扛着一把铁锹来了,他习惯一天来三次他的责任田看水,没想到把田里发生的一切看了个正着。他当即像有人割了他的肉一样呼叫怒骂,我倚在田边牵着牛,大气都不敢出,听他骂,他越骂越难听,也越骂越来气,突然举着铁锹往我家的牛背上啪地来了狠狠地一记,牛背上腾起一阵青烟,接着又是啪地重重一记,又一阵青烟,牛背的皮都破了,看见了血的颜色,牛连续两次往下蹲,尾巴夹在屁股上,稀牛屎一下子就啪嗒啪嗒出来了,撒了一田地。我大惊,这牛可是我家的重要财产,春耕夏种离不开它,要是被他打死了,那我家就比他的禾被吃了还要惨。我赶紧牵着牛就跑,牛的两条后腿踩到田塍边缘,一个趔趄,啪的一声又挨了他追上来的一记,我又怕又恨,哭着说,你打死我的牛了,我讲给我阿爸阿妈听!我的哭声和骂声似乎让他愣了一下,但他马上又骂,讲给你阿爸阿妈听?好呀,你去讲给他们听啊,你的牛吃了我的禾,你还有面皮去告状?我讲你听,你不赔我一担谷我就不放过你,你们种田都不识种,我看你们拿什么赔我。
我牵着水牛,刚才拣好的柴也不要了,快步从另一条田塍回家。
母亲用鸡毛蘸了山茶油往牛背上抹,边抹边说,看看这个佬,落手这么狠啯。父亲气得发狠话,这样的姐夫,我还认他?就算晚造我没有一粒谷收我亦要借来赔通他。
七月收了稻谷后,按亩产计我们已经减收了。湿谷变成了干谷后,父亲亲自装了一担,上了秤,足足一百斤,父亲担着和我一起来到苗定德家,苗定德二话不说就接过,沙啦一声倒进了自家的谷桶里。
二
在我们与苗定德吵架的过程中,布奶是最痛苦的,她曾经悄悄走到猪栏边和正在喂猪的母亲说,你姐夫就是那种人,我有什么法子?同我亦不停地吵,我劝他不要同你们吵,我讲,再怎样他们也是我外家的人,是你的细舅啊,你做姐夫的怎能跟他们吵?在队里几丑啊!可晓阳布爹骂我,丢那妈,你条胳膊肘是外翻啯啊?不帮我反而帮他们,我娶错人了!你叫我怎讲?你们吵,我谁都不帮,我就听。怪只怪当年阿舍阿娘看错人,嫁我到苗屋,我真是命苦!晓阳阿公识算命啯,怎么算不出我不应嫁苗屋呢。母亲就一边望着那头猪嗒嗒嗒嗒地吃潲,一边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命定啯,算也算不出啯,有什么法子呢。
1992年秋天,我要上大学了,先是嫁到三唛尖山脚的大布奶给我送来了一百元,接着是我的大舅爷送来了五十元,我父亲的亲哥、远在广东海康的我九爹寄回来二百元。我即将出发上学的前一天,我的堂二爹、三爹、四爹、十爹都送来了二十三十不等的钱,十一爹送来了一百元,他们说,我们都望晓阳有出息。
令我父母想不到的是,布奶在我母亲当天傍晚去猪圈喂猪时,蹑手蹑脚地走来了,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闪进猪圈里,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元,塞进母亲手里,还着急地说,收紧,收紧,毋等晓阳布爹看见。母亲虽然惊愕,却也识相地赶紧放进了自己裤袋里,才压低声音说,你哪里得到的?你不要用咩?布奶看看母亲已经收好了钱,才吁一口气,说,我的大女英芳来时给我买猪肉吃的,我收起来,不让定德知。看看四下无人,又压低声音说,定德记仇啯,那年传志讲他没文化,他跟传志吵了一场,回来讲,我就要跟有文化的佬斗到底!一直到今日他都不放过你们。
可是当天晚上苗定德就知道布奶拿钱了,据说是他的小女儿英敏告的密,她母亲掏钱时她正好在我家猪圈边的竹林里抓心乞旺玩。二布爹先是劈了二布奶脸上一巴掌,骂,丢那妈,拿我的钱去送人家读书,你得过他们几多使?你给了他们几多?你去要回来!苗定德将布奶往门外推,布奶死死抓住门轴不放,哭道,我嫁到你屋里这么多年,你打打骂骂这么多年,我侬儿都帮你生了三四只,我算对得住你苗屋了吧?我给几文纸我外侄上大学使都不行啊?你还叫我去拿回来,你还是他们的布爹吗?你还是人啯吗?你还要不要我做人啊?你要我去问回来,我宁愿死我都不去了。
幸得苗定德的兄弟苗广德和他老婆耿秋菊、苗远德和他老婆李芹赶来劝,都说,给都给了,就算了,是给外侄读书,不是给别人,以后可能人家不忘本呢,来报答呢!苗定德才气哼哼推了一把布奶,出门作罢。
三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不见布奶已经五年了。2006年,我父亲患绝症去世,终年只有五十八岁,我们的大小亲戚都来参加丧礼了,金瓜屯的布奶却没有来,更没有派儿女来,这让十一爹愤愤不平,说,像什么大姐,细舅不在了都没有一个人来行行礼啯。我母亲在事后听到过屋的苗广德老婆耿秋菊说,讲句本心话,定德做得是不对,传兰的细佬传志不在了,去看看都不准啯,还骂她,我就不准你过去,我吞不下那口气。做传志法事那日,传兰又哭又骂定德,你这个发瘟,我细佬死了我做姐的想回去望一眼都不准啯,你不是人啯,雷公不劈死你就是劈死我。母亲和我们三兄弟说,传兰我不讲她了,她有她的难,有苗定德管住,她想来都不敢来,怪就怪苗定德,他不是人啯。
一个周末,我终于有空去看布奶。记忆中,苗家老屋尽管是泥砖黑瓦,但一直显得高大堂皇,宽敞整洁。走近围墙大门时,我惊讶地发现看坪坑洼不平,屋厅墙体有两道手指宽的裂缝,泥砖缺损严重。屋檐有好几处的黑瓦不知是被大风刮掉还是自然跌落,檩子都露出来了。檐街上除了处处都有的凹窝,还有这一摊那一道的鸡屎鸭屎。
从那个我以前熟悉的灶房门口出来一个人,尽管衣衫陈旧,满脸沧桑,目光浑浊,还赤着脚,我认出那就是当年常跟我们家吵架的布爹苗定德。他惊讶地说,我以为是谁,原来是晓阳。他接过我拎来的水果、面条和猪肉,一边说,你来就来吧,还拎这么多东西来。他放好东西,给我倒了一碗粥水,仿佛知道我来的目的,不等我喝一口,马上说,我带你去见见你布奶。我一听就放下了还没来得及喝的粥碗,跟随他进了屋厅旁的一间光线暗淡的房子,他边走边说,传兰,晓阳来看你了。就听地板上一阵翻身的响声,在一扇陈旧的门板上,一个盖着单被的身体吃力地一点点爬起来,我赶紧弯腰去扶,却像扶着一把轻飘飘的棉花,又像举着一个干枯的竹架,她那死水一样的眼睛里突然亮起一点光,看着我说,我外家人来看我了?我外家人来看我了?等我终于扶住了她,她却认不出我了,空洞的眼睛里那点光也在慢慢弱下去。我说,我是晓阳啊,布奶!她却茫然地望着我,说,晓阳来看我了?哦,我知了,我阿娘屋里的人来看我了。我黯然。
我早知道他们没钱也不想送医院,就询问医生来看过没有,布爹说,上个月来过,是平旦村的李家尊来看啯。我问是什么病,他说,家尊讲是中风偏瘫高血压,还有什么大脑萎缩。正说着话,布奶突然指着布爹说,他好坏啯,我想吃点肉都不整给我吃。布爹生气地说,你真是懵人乱告状咯,外家来人了你就这样讲,我哪日不整猪肉给你吃?昨晚我还煮了二两瘦肉汤给你吃,你告状都不能够这样告我啯啊。
布奶的瘦小黑麻让我惊愕,又长又瘦只剩骨头的手脚让她活像一只长时间没有觅到食物的马骝。但是因为她麻黑的五官轮廓,和我父亲以及十一爹是多么相似,我意识到即使她变成一只老鼠,我也能认出她来。她的头发掉了一半,可能是长时间没洗澡的缘故,看着更显稀棱棱的,身上还有一股长期不翻晒的被褥混杂着尿臊屎臭味。她的两腮深深地塌进去,脸上都是癞蛤蟆皮一样的老年斑,牙也只剩下一张口就见的两颗犬牙,鸡屎一样的颜色,红黑的牙床和紫黑的嘴唇嚅动着,宽松的黑裤子里伸出两条像鸭脚木一样的小腿连着脚丫在门板上拖着,看样子就算是扶她也站不起来了。
有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门口伸头看了一下,接着听见一个女人尖厉的声音,阿东,出来吃饭,你这只死猪,去看什么看?臭气熏天啯,你在里头人都被熏傻了!我正猜测是谁的孩子,布奶突然破口大骂,娶这个新妇有什么用?回到这间屋不肯煮过一餐给我吃,恶死咁恶,教出的侬儿也是这样,人家的孙儿捧粥给阿婆吃,我的孙儿嫌我臭!什么样的新妇教出什么样的仔,总有一日他亦像你对我这样,有报应啯。外面的女人接口骂,你这个老嘿,还不死,拖这么久不死是浪费水米。
我愕然。外面的女人就是布奶的大儿子英金的老婆阿花。几年前母亲就跟我说过,此女人是英金在广东打工时认识,贵州人,刚带回家时境挺好讲,见人都问,还喊我舅奶,本地话都识讲了。母亲说。
几年后,阿花的性格就完全变了,我是听秋菊讲过,你布奶脚不便,喊阿花舀勺洗脚水都不肯舀,餐间吃饭也是,炒好的猪肉分两份,瘦的留给自己同侬儿,肥的就给家母婆,你布奶哪里吃得落颈?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满腔愤怒了,却强压怒火问,难道英金总不管管?我母亲说,你说那个佬,正宗老婆奴,秋菊讲,英金衫裤都是自己洗,你想咯,谁娶只老婆不是想她帮自己煮吃洗衫裤啯?但是听讲阿花的裤衩英金都要帮洗,你讲这样做只男子佬有什么用。
我塞给布奶五百块钱后快步离开,才走到门口,她就在后面喊,我不要你的钱,我要钱有什么用?买回的肉我又不得吃,全部是他们吃完。我回头,看见布奶卧在门板上剧烈地挣扎着,黑手黑脚四下伸动像一只八爪鱼,蓬头散发地向我挥动着几张钞票喊。我心一狠就跨步出去了。
我一出了苗屋大门后就已控制不住,等到走进屋边那片竹林,我双手扶着一根丹竹,哗哗哗地流出了眼泪。
四
2015年春节,布奶的二儿子苗英银在邻村平旦赌博,一夜就输了四万元。
知道这个消息后,苗定德在厨房里跳着大脚痛骂苗英银,房里的布奶挣扎着想起来,骨瘦如柴的双手撑着床板,可就是撑不起自己的身躯。自从五年前得了肺病又中风卧床,几乎岁月就在床上度过了。
我母亲和十一奶曾经两次去看望过她,帮她翻身,发现她的背脊已经肿烂了,甚至看到了蛆!在几个血肉模糊脓水外溢的小洞里乌央乌央涌动着蛆!吓得十一奶低低地叫了一声,脸色苍白,我母亲也胆战心惊,出去喊布爹,定德,定德,你快来!苗定德慌慌张张地跟着进来,脚还哐当一声绊倒了一只小矮凳。我母亲指着布奶的脊背对他说,你看,你看。苗定德凑近一看,吓得脸色如土。十一奶说,苗定德你个佬,传兰背脊生这种嘢了你都不知道啯啊?苗定德一脸惊慌地说,谁想到会这样啯喏。我母亲说,快点拿双筷子来。苗定德就去厨房拿来了一双筷子,十一奶撩着布奶的背后衣服,我母亲伸出筷子,小心翼翼地伸进小洞去夹,筷子每伸进小洞去一次布奶就浑身发抖,发出哀号一次,十一奶说,传兰,你忍忍,忍忍。布奶哭道,定德,你害我。苗定德正经道,传兰,你怎么这样讲?我怎会害你。十一奶说,不争不争,先整干净再讲!我母亲继续小心地夹,一条一条白瘆瘆的蛆被夹出来,丢在地上,十一奶就伸脚一搓,蛆成了稀巴烂。我母亲足足夹了半个小时,把三个洞里的蛆全夹出来了,地上十一奶踩死的蛆的尸体,有巴掌大。我母亲让苗定德拿来半盆淡盐水,她用小布条浸了慢慢洗,布奶又浑身发抖,发出阵阵哀号,骂道,苗定德,你害死我了,你害死我了。苗定德又变色道,传兰,当着你两个细妗在这里,你骂我是吗?你讲话都没有本心啯,我日日都煮粥煮饭喂你,捧屎捧尿服侍你。十一奶说,那你总不看看她背脊怎样啯咩?苗定德无言以对。
布奶痛哭流涕说,我死了算了,不用折磨我,也不想折磨他们!我生有两只仔有什么用?英金是娶了老婆,但是粥都不肯给我吃!英银长年在广东,一年到头不回来看过我一次!苗定德也不是人,喊他煮点瘦肉粥给我吃都不肯煮。苗定德怒气冲冲地说,传兰你讲话一点本心都没有啯,你吃我煮的肉粥吃蒙了啯!
我母亲和十一奶离开金瓜屯布奶家,两个人刚刚走到粪坑边的丹竹林里,就各自弯腰扶着一根竹子哇哇地干呕起来,一边呕一边号啕大哭。
五
布奶是在第五天夜里十一点多寂然过世的,享年六十八岁。当报丧的大炮声突兀而惊天动地响彻长田垌,响彻天堂山坳后,刚刚入睡的十一爹走出地坪,长叹一声说,我这个大姐去了,不用受苗定德的气了。我们老豆老母那年嫁只女这么近,本心就是想借点苗家的力,帮帮我同传志啯,几十年过去了,他又帮得我们什么喏?传兰自己都没享到福,嫁这个佬跟我们争了半世。去了好,不用在阳间受这么多苦。
布奶走的第二天早晨,山里刮起了大风,天色也阴暗一片。主事的人都说,赶紧办,派人去问日子佬,几时入土。
因为布奶的两个儿子和大儿媳的奇怪表现,哭丧仪式有些潦草,幸得她还有两个女儿,那哩哩哇哇的号啕增添了一点悲凉。布奶这辈子为苗定德生了两男两女,结局让我感到辛酸。
在得知苗定德只是给布奶做了一副厚度只有三公分的薄棺材后,我十一爹出面进行了干涉,当得知苗定德明明自留山上还有一棵粗如门扇的杉树却不肯砍伐时,我十一爹愤怒了,责怪苗定德,我这个大姐难道不是命咩?在世时没享到你的什么福,辛苦一世,去了连睡一副厚棺材都不得!苗定德似乎就没有任何悲伤的样子,振振有词地反击,我山上就有三棵杉木,一棵大的两棵细一点的,我要斫了大木,以后我过世了让我使细木?哦,你大姐过世了可以睡厚寿材,我过世了难道就要睡薄寿材?如此的反驳争辩让我十一爹七窍生烟,连在一边看热闹的十爹传仁和西垌梁的景江老人也看不下去了,都说苗定德,死者为大,你还在世好好的,讲那些话做什么?自己揾衰啊?传兰去了你就使上好的寿材殓她嘛,以后的事,日子还长呢,考虑咁早做什么?苗定德却不乐意了,说,你们以为我身体好好啊?我寿得好老啊?我身体比传兰还要差,都不知几时就去了,你叫我把厚寿材给她,我不做啯!你们山上亦有大的木,你们看不过眼给一根传兰嘛!一番话气得十一爹十爹景江几个人说不出话来。
师公佬给布奶做法事的时候,天上突然就飘起了蒙蒙细雨。幸亏搭有灵棚遮着,干活的人都在灵棚下忙。
师公佬们在唱一篇很长的词,听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一月行孝新又新,讲起当初行孝人,
郭巨埋儿为藏宝,挖泥三尺见金银。
二月行孝系丁兰,母死黄泉哭冇返,
刻木来作他母亲,烧香侍奉过日神。
三月行孝系百佳,百佳做官忘双亲,
朱氏在屋侍父母,罗裙包泥结山坟。
四月行孝系曹安,曹安杀儿救饥荒,
只见曹安行孝义,杀儿取肉救娘亲。
五月行孝系董永,董永家贫去卖身,
卖身捋钱葬父母,玉帝女儿结成亲。
六月行孝系黄香,黄香行孝最高强,
夏天扇枕亲娘睡,冬天温暖献亲娘。
……
我看了一眼俯伏在屋厅内棺材前的苗英金苗英银以及英金的老婆阿花,他们一会儿跪着,一会儿又坐在后面的小矮凳上,茫然望着地坪上,那里是边打镲边喃唱的师公佬,是配合师公佬摆设道具的本屋人和邻居,是坐着看喃斋的人们。我在想,布奶的两个儿子和那个儿媳,他们听了这首词吗?他们听明白这首词了吗?
天亮时,蒙蒙细雨变成了中雨,瓦顶上开始滴滴答答,很快瓦坑就流下小瀑布。主事的苗远德急忙让自己的大儿子找来我们东垌梁的芳军、芳兵和西垌梁的芳智、芳坚,说,你们几只揾几根长竹篙,一张最大的薄膜,去太平岭把那只坑遮起来,再拎一只胶桶水勺去,有水了你们先戽出来,否则等一下出山,如果入了一坑水,孰放得入那副木。芳军芳兵芳坚芳智就赶紧忙起来,一番准备后,出门而去。据后来芳军说,还真的进了一坑水,四个人轮流进去舀水戽水,外面一个人在坑边接过胶桶倒掉,足足忙乎了一个小时,四人一身泥湴,水戽完了,这边也到出山的时间了。我十一奶听了芳军的话后抹着眼泪说,传兰就是命苦,你看咯,天都哭了。
布奶是在一场蒙蒙细雨中被抬上太平岭的。响器在响,山路渐渐泥泞,红色的棺材覆着白色的挽幛牵一路的黑幡,蜿蜒在碧绿果树杂木掩映的山径中。
六
布爹的大儿子苗英金早些年在东莞水泥厂工作,水泥厂技术革新后,他没文化年纪也大了,就回到了老家,却落下了肺病。二儿子苗英银在广州跟人做水磨,一直嗜赌成性,一发工资就去赌屋,一年没有几个钱带回家。队里人都在传说,他的大儿媳即苗英金的老婆阿花一直对两个老人不好,闹着和他们分家。他们家二十多年前就起好的一层砖混楼,如今故园依旧,一直没有加高,且已墙皮剥落。
布爹脸上布满了褐色皱纹,连走路也颤颤巍巍的了。2019年大年初二晚,我跟母亲说想和景瑞景平景威他们过去看看他。我母亲有些记仇,想起当年他对我们家的歧视和咒骂,一直愤愤不平,对我说,你要去看他?当年他咒骂我同你们的阿爸,现在你们的阿爸又去了这么多年,我想想都不愿原谅苗定德,如今你们要去探望他,等于向他讨好,抑或去施舍?讲老实话,我真放不落这个面子。
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看,大年初三上午,我们跟景平和景威一说这事,他们就答应了。我们便捧了两箱水果、六扎面条和两大块猪肉,还有六个礼包一起去他家。我们还考虑到了村里的习俗和他的处境,特意不带我们的孩子去,省得过新年他要为打赏红包而为难。他大概没有想到,当年曾经与两个小舅子反目成仇,今天他们的儿子结伴来探望他。他有些诚惶诚恐,一直弯着腰亲自捧茶,还亲自下厨生火做饭。
我们在他家吃中午饭。阿花煮饭择菜,苗英金做了猪肉汤给我们喝。临走时,我们三兄弟除了给他们的小孩打赏了红包,还一人给了布爹两百块。他慌得双手对着三个红包又推着又捧着,一脸感激和惊愣的样子。
我再次见到布爹是在旧晒场上。他躬着腰,青筋暴突的右手点着面前的猪肉对猪肉佬说,要条猪利。我心里一阵难受,不知怎的,我想起了布奶那双枯瘦如竹枝的手。我掏出二百块钱给他,也许是当着猪肉佬的面他不好意思,不停地推辞,后来我坚持把钱塞进他的起了许多线头的口袋里,他就低声说着唔该唔该,眼里闪烁着一种惶恐,还有一丝温情。
布爹常来我们东垌梁,他已经满头白发,身上的粗布衣服洗得水白,脚穿一双鞋底磨得薄如胶垫的黄拖鞋。看见我从楼里走出来,脸上有一丝疑乱的表情。我喊了一句布爹,他说哎,听起来竟然十分亲切,与三十多年前我听到的骂骂咧咧声判若两人。
十一奶说,阿花还是常常跟他吵架,骂他还不死,浪费米。不久就怂恿苗英金跟他分家了,分了家的布爹一人煮一人吃,柴也要自己上山担,要吃肉了也只能是自己去买。有一次布爹厨房没柴了,去大儿媳妇厨房抱了一小把,结果大儿媳妇瞪着眼指着他的厨房破口大骂,你还不死?柴都找不到烧。气得布爹咳出了血。
2019年清明节,一大早,我去旧晒场买猪肉时又见到了布爹。布奶走了四年,布爹更老了,佝偻着,一脸松树皮一样的皱纹,头发几乎全白,衣服的肩膀上有两个洞。我问他,是不是买肉去拜山?他说,是。我再问,有谁去?他说自己去。我又问,英银呢?他说,几年都不回拜过山了。
我把身上仅有的一百块钱递到他手上,他两掌拱着往外推,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收下了,却一把抓住我的手,望着我,手不停地抖着,浑浊的泪从陷进去的皱纹堆里荡出来,嘴唇嗫嚅着,晓阳,我对不住你阿爸阿妈啊,那年你阿爸不在了,我着鬼迷了,竟不准你布奶回去送送你阿爸……我也对不住你,更对不住你布奶,那年你考上大学,你布奶拿了五十文纸去给你阿妈,本来系好事,给你读书嘛,但是我那晚打了你布奶,你布奶嗷嗷哭,我现在想起都难受……是你布爹眼拙,看不出你今日有出息,你布奶去了这么多年了,我对不住她啊……
他走了。他手弯曲着放在肚子前,紧紧地攥住那张钞票,佝偻着腰,低头看地,像一只发现了食物的鸭子,用力往前伸着脖子瞪圆眼睛,迈开穿着鞋底磨得薄如胶垫的黄色拖鞋的蒲扇大脚掌,啪啪啪啪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