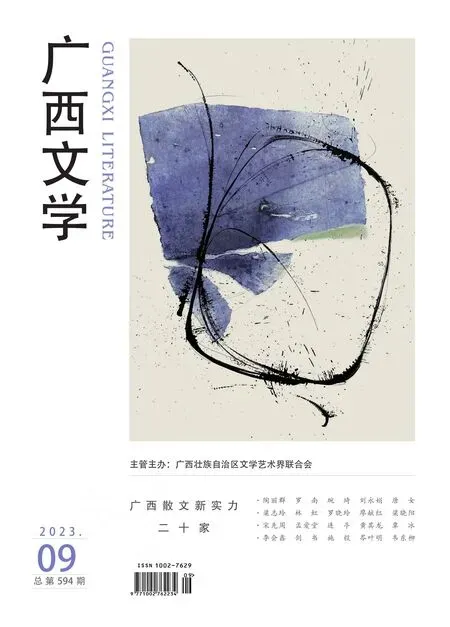大田面的鸟儿们
2023-10-22廖献红
廖献红
一
大田面,是一个村名。村里的田块大多呈梯田状,小而狭长。梯田依山形地势而修,从水流湍急的山脚到云雾缭绕的山顶,从葱茏的杉竹林边到石块的缝隙,凡有一点土的地方,都开凿成田。最大块的面积不超过一亩,最小块的只能插十来株禾苗。用“青蛙一跳三块田”和“一床蓑衣盖过田”来形容,并无夸张之意。所以,第一次来到大田面,看到村里人种着那么小的田块却取了个大气的村名,我就不服气,甚至觉得这里的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好高骛远。
大田面方圆不足三公里,处在两座大山形成的冲槽之中,房子散落在稍为开阔的山脚及山腰。人口最多时住有两百多号人,如今常住的包括国胜老汉两口子在内,剩下不到十人,且全是七十岁以上的。每天清晨和黄昏,国胜老汉都会坐在门口的磨盘上,左手托着水烟筒,右手拿着打火机对着烟嘴点火,嘴贴着烟筒口子,咕噜咕噜猛吸一阵,抬起头,吐出雾,目光越过一块块梯田朝不远处的鸡毛松看。这棵鸡毛松经园林部门鉴定,有六百多岁了,树冠常年茂绿。自国胜老汉记事起,它就有这么高,这么大。鸡毛松上栖息着很多鸟儿,有燕子,有布谷,有画眉,偶尔也停留乌鸦。大田面一年四季,碧水荡漾,草丰林茂,鸟儿喜欢在此嬉戏、安家、繁衍。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祥和景象一直保持到今天。国胜老汉尤为喜爱这些鸟儿。然而,这天早上,他照常一边吐着浓浓的水烟,一边透过缭绕的烟雾眺望鸡毛松,突然觉得鸟儿的叫声让他变得心烦。
他的心烦是老伴催促他尽快动身,到马贵镇上吃席。国胜老汉埋下头,啪嗒啪嗒,又猛吸一口,直到烟丝再也点不燃了,他才起身上到二楼,换了身走亲戚或赶集穿的衣服,开着大门,关上腰门,出门去了。
大田面家家户户如此,出门赶集或走亲戚,白天都是大门敞开,暮色四合时,若你一时还没回来,村里有人会帮你把门关好。天黑不久,大家吃完饭早早就睡了,整个村子,没有任何机器的轰鸣与街市的喧闹,只有青蛙和虫子小声地鸣叫,还有“长河落日圆,夜深几帐灯”的静谧。那种心安理得的与世隔绝,让我每次回到这,就想象成马尔克斯笔下《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小镇。
二
这个位于广东省云开大山余脉的小山村,离县级市高州市行政中心九十多公里,需要翻越好几座大山。大山高到什么程度,可以用气温量化:在市区气温是二十五度,这里只有二十度。这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充满乡野气息。它太小了,即使在比例尺最大的地图上也难找到它的位置。二十来户人家清一色地姓陈,取名也全部是按字辈,一听名字,长幼尊卑便一目了然。原因是大田面的陈氏全由一个祖先开枝散叶而来,始祖以下的辈分,顺序是达、世、日、荣、华、国、家、振、兴、作、术、文、英……
铭兄是国胜老汉的大儿子,“家”字辈,是这个字辈的大哥。因缘际遇,我成了大田面的大儿媳和大嫂。我俩结婚时,二弟、大妹和二妹都已结婚生子,“振”字辈的侄儿侄女已有两三个,于是,我又顺理成章成了大伯母和大舅妈。我和铭兄的女儿在广西出生,取名时铭兄把“振”字弃掉了,取单名“粤”。小丫头说的是柳州话,爱吃麻辣,成了像模像样的广西壮族人。
大田面的地势,也叫风水,是极为少见的。村子有两条出路,一条路沿着对门岭盘旋而上,再盘旋而下,“写”下十多个S后才到山脚与280省道相接。另一条小路沿着小河蜿蜒伸出山外,中途也有好几个“之”字形。这种群山环抱式的地势,出路都被高大严实的对门岭挡住了。在中国风水学理论中属于“插翅难飞”。视野不开阔,生龙生凤简直是天方夜谭。事实也是如此。自新中国成立后至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的这段时期,大田面从未走出一个大学生。应征当兵的,也都因种种原因审查不过关,没有一个得益于读书和当兵吃上国家粮的。大田面就是这样寂寂无闻。铭兄十九岁那年,一心要走出大山改变命运,做梦都想离大山越远越好。终于,他费尽周折将户口迁至柳州,落户一远房亲戚家,才有机会到柳州一所高中复读,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分到乡镇中学当英语老师,消息传回大田面,大家咋咋呼呼地说,我们老陈家总算出了个教育局长了。后来,我进了县政府当文书股长,乡亲们又传大嫂当上了副县长。这是后话了。
可是,人的命运,真不是读书就能决定的,虽然那个时候要想“鲤鱼跳龙门”,唯一途径就是读书或当兵。铭兄考上大学不久,三弟在他的感召下,破天荒考上了广州一所专科院校。毕业后分配到县供销社下辖的一家食品厂,也算吃上了国家粮。然而,不出几年,企业破产,下岗了。刚下岗那些年,他创业雄心勃勃,试图进军好几个领域,终究还是缺少资金和眼界,屡战屡败,至今仍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相反,二弟没有上过高中,却闯出另一条路,初中毕业外出打工,进了一家民营模具厂。国胜老汉勤劳本分的基因在他身上得到传承。他在厂里如鱼得水,埋头苦干到现在,成了厂里元老级骨干,收入稳中有升,这不,他到镇上全款买下五室两厅大户型的商品房,日子过得比三弟滋润多了。
我第一次跟铭兄回大田面,打了一辆两轮摩托,铭兄坐在中间,我坐在最后,行李绑在货架上。车屁股冒着黑烟,很吃力地爬上山,幸好我那时的体重不过百斤,没有出现坠尾。但上到最陡的地方时,车头突然翘了起来,我吓得不轻。显然,司机是有经验的,他双脚撑到地上,将车头往下摁。就这么一个动作,摩托又稳稳地向前爬了。
待摩托爬到半山时,我出现了耳鸣,明显感觉到了海拔的上升。山高,盘山公路自然就弯曲了,几乎像是在悬崖上走钢丝。我扭头往下看,惊出了一身冷汗。铭兄坐在中间,好像没见他冒一点冷汗,而是兴致勃勃地给我当向导,介绍当年他是如何沿着这条山路走出走进的。说着说着,他就扯到了这几座大山的典故,还有山外高州府的冼夫人。这位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冼夫人就出生在这里。她的一生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历经梁、陈、隋三朝,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在世界上的女性中极为罕见。上到山顶时,铭兄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冼夫人可是我辈及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啊。
后来,我在高州市志里看过相关记载,文学作品中也有描述,但是放在大田面这样的小山村身上那绝对是牵强的了。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大田面,与冼夫人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八竿子打不着啊。跟梁、陈、隋三朝,那更是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大田面的历史也只不过六百多年,村头那棵鸡毛松可以作证。但我没有戳穿他,我知道,铭兄极力夸赞大田面曾有过的辉煌,纯粹是爱我。他想用冼夫人这样的名人做他的亲友团,告诉我,他的大田面也是人杰地灵,有着千年文化血脉的,以此消除一点内心的自卑罢了。
村头寡居一位老妇人,我们称她二叔婆。她满头银发纹丝不乱,喜欢用一根红头绳扎起来,很是抢眼。每次见她颤颤巍巍到河边洗菜洗衣服,我就会将大田面与马孔多对号入座一番。眼前的二叔婆对应着伟大的乌苏拉老祖母,她活得忘记了岁月。
第二年回大田面,多了女儿。我跟铭兄说,千万不要再打摩的了,险多。于是,在茂名下了火车转班车,在高州下了班车包了一辆微型车,直驶大田面。女儿在我怀里,可能是被崎岖的山路晃晕了,起初是哇哇乱叫,然后就开始昏睡,眼睑下有两颗晶莹的泪珠,欲掉不掉,看得我心疼。摸了她的额头,体温正常,呼吸正常,心放了下来。心一旦放下来,我便开始晕车。当翻过第一个山包后,车飞快下坡,我的胃开始翻江倒海。我在心里一次次默念,挺住挺住,坚持坚持,还真的挺到了对门岭。车子是没能直接开进大田面的,前方没有路了。沿着山路往下走过一片梯田后,一条小河横亘在进出的田埂中,必须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头,像上岸的鸭子样一步步跳过去。
来到河中间,我蹲下来,给女儿和我洗了把脸,原本混沌的脑瓜慢慢清醒了。再做几下深呼吸,整个人变得精神起来。一进家门,婆婆便捧出刚烧好的姜枣茶,喝下两大杯,半个时辰便“回阳”了,整个人神清气爽。铭兄归结于这里空气好,水土好。是啊,怎能不好呢?他在这片水土中出生,又在这片水土中成长发育,他的血液与身体里储存的能量都是这片水土给予的。而我,因缘来到大田面,自然要学会慢慢接纳,识别这片水土每一滴水、每一丝光的密码。
八个月大的女儿是第一次回来。回来前,铭兄用矿泉水瓶在幽兰码头灌了大半瓶洛清江水土,拧紧盖子,塞进了旅行箱。回到大田面后,他将这大半瓶水土投放到后山接引山泉的水柜中。以这样的方式祈求婴儿时期的女儿尽快与家乡的水土对接上。其实,我心中有数,父女连心,铭兄血液里储存的这片水土的基因,会不打折扣地遗传给女儿,即便不带上那半瓶洛清江水土,女儿也绝不会出现水土不服。
前年春节回去,这条小河长满了粗硬的野草,真可惜了这条自然小河。一问得知,那是大田面受凡亚比台风袭击,泥石流淹没了部分田地和庄稼,山上的毛竹杉木损失严重。政府救灾送来了一些草籽,鼓励村民利用山泉水种草养鱼。头一年村民按上面教给的方法种了草,也养了鱼,可回报率实在太小。第二年就没有多少家愿意养鱼了。人们将草连根拔起,丢弃到河里。鱼草任意生长,很快便将小河塞满。若不走近,根本看不见河水,原本河里的鱼更是难觅踪迹。入夜,河水潺潺的声音被夜色放大,当年那种昌隆的感觉才又回来了。
然而,这样的“昌隆”也仅仅是感觉。每天清晨和黄昏,有炊烟冒出的烟囱,也不过是四五家而已。逢年过节,村里的年轻人从深圳、广州、东莞、珠海、湛江回来,也只是匆匆地在祠堂里上炷香,祭拜一下先祖,再燃放一串鞭炮,烟雾尚未散尽,他们便发动车子绝尘而去。我知道总有一天,这神仙般的田园生活会不复存在。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总会升腾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
三
在广西一个叫里定的小山村,山头有一座坟墓,铭兄、我和女儿的名字以嫡亲的身份刻在墓碑上。这座墓的主人是国胜老汉的亲叔叔,排行第五,我们称五叔公。早年的他嗜赌成性,在广东败光了家产,输掉了老婆,步行三个月,来到里定村入赘安家。当年铭兄从大田面出来,率先落脚到这里。叔公的墓碑立起那年,女儿还不到五岁,我觉得我们也算是远房了,将我们的名字刻上去,没有必要。但铭兄和五叔公的儿子执意要刻,我也就随了他们。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尤其是读到马尔克斯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亲人埋在这里,这里就不算你的故乡。猛然地,我为自己当年的想法很是惭愧。我的目光无疑是短视的。铭兄十九岁离开大田面,到广西求学,最初投靠的就是五叔公。他在这块不是出生地的土地求学、工作、结婚、生子,不经意间三十年过去了。这无异于是重建一个故乡的过程。前几年,我的父亲去世了,老人家的墓碑也刻上了铭兄的名字。每年清明去扫这两座墓时,铭兄烧香焚纸祭拜都会格外虔诚。家乡是什么?家乡应该是不仅有人出生,还要有人死去,要有亲人埋在那里,肉身化为泥土的一部分。墓碑上刻有自己的名字,才意味着在此扎下根。
大田面至今留存的乡村风俗更为明显。祭祀,送灶,扫尘,年夜饭,贴对联,放烟花,吃糖粑,初一、十五到祠堂、庙宇敬香。所有这些都完好地保留着。每年回去,都要到四个地方敬香拜神。第一个点是距大田面五公里的厚元村横垌屯。那里有一座陈公老祠堂,供奉着七代先人的灵位。我成为陈家儿媳那年刚好修建,赶上了捐功德钱。国胜老汉以我和铭兄的名义各捐了五百元,于是,我俩的名字便被镌刻到功德碑上,镶在祠堂一侧的墙壁里。它像是大地上鲜活的遗存,成了一方最独特的“陈氏印”。陈氏子孙在这里能寻找到自己的根,看到自己的“胎记”,还可看到散落四处的父辈子侄姓甚名谁。祠堂里有着先前的风气和老规矩,供奉的不仅是祖太公牌位,还供奉着天地人的大道理。第二个点是村口的开天庙,供奉着日月神和土地公公。第三个点是大田面的祖屋,供奉着陈家的太公太奶,前来祭拜的后辈们基本是五服之内的了。第四个点是小河边的社王。社王是由一棵牛奶树和一块大石头组成。牛奶树看起来像无花果,是一种很好的中药。大石头脚下的空地,无论什么时候来,都插满了燃尽的香烛。人因树而得福,树因人而得寿。这棵奇丑无比的树,竟然成了大田面最神圣的树。人们已不把它当树看,而是有几分成神成仙、护佑众生的意思了。
据说这个社王是有来历的。农业学大寨那年,一位军转干部到大田面带领农民开荒种粮。大田面的耕地大多是依山开垦的,岩石多,一块好好的可以耕作的地常常躺着一两块大岩石。石头能搬走的就搬走,太大块的,用炸药炸碎了再搬走。某一天,军转干部按往常一样指挥村民用炸药炸一块一半在河边、一半在田里的大岩石。埋下炸药,点燃引线,一声轰鸣后,这块大岩石在巨大的火力下,出乎预料地只是开了一条缝。人们都认为这块岩石太硬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天晚上军转干部肚子突然绞痛,上吐下泻,本以为是受凉引起的,扛一扛就过去了,可一连几天全身软困,不能出工。村民看着军转干部的病有恶化的趋势,慌了神,这天刚好有一风水先生途经大田面,有人让风水先生瞅瞅这块炸不开的大石头,其结果是,这块大岩石与大田面的其他石头不一样,而是一块风水石,不但不能炸不能搬,而且还要供奉。于是,人们第二天就到这块石头前烧香祭拜,将香灰冒开水让军转干部服下,军转干部病情很快好转了。
事实上,军转干部是吃了老婆煮不熟的野蘑菇,才导致发病的。那时的香灰,其实就是草木灰,有碱的作用,服下能止吐止泻。但村民们不认这个科学道理,只归咎为动了龙脉坏了风水,从此把这块岩石当成社王石祭拜。后来,不知是什么鸟儿衔了颗种子扔在这里,长了这棵弯脖子的牛奶树,与社王石连在一起受到供奉,久而久之便成为社王了。
铭兄出生不久,病痛多,三天两头发烧感冒拉肚子。有一次竟拉到了脱水,祖母用麻搓成线,点燃线头吹熄火苗,红通通的线头摁在他两边太阳穴和肚脐周围,痛得他哇哇大哭。烧过后,母亲便抱他到这棵树下烧香祭拜,摘了些树叶搓出汁冒水喂服,第二天便痊愈了。
祖太公们生前到过最远的地方,恐怕也不过二十公里之外的马贵镇。铭兄却把他们的灵魂带到了千里之外的远方。在柳州,我们家的客厅安放了香火台,逢年过节上香祭拜。不仅如此,他还把大田面的社王也带来了,当我和女儿有个头疼脑热,吃药打针一时好转不了,他也会在十字路口烧纸祭拜。我曾笑话他,没有大田面的神灵庇护,难道大柳州的世界就充满凶险?他不怒不躁,默默地操作。现在想来,对于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人来说,早已没有了远方,剩下的只有乡愁。
陈公祠堂供台有十级台阶,最上面的那一级摆放着始祖夫妇的灵牌,二级摆着始祖的五个儿子及配偶的灵牌,依次类推往下安放。灵牌全是用杉木板制作而成,原木色,上面刻有逝者的姓名、生辰八字和死亡时间,字体端庄俊秀。十级台阶中,除了最下面的三级还空着,七个台阶密密麻麻地摆满了牌子,庄严肃穆。面对先祖,每一个来此祭拜的子孙都不会大声喧哗,脚步也会不自觉地放轻了。所谓的树大从根起,这些灵牌伫立在供台上,恰似一棵倒立的大树,越往下,越枝繁叶茂。从第一级到第五级有增量,从第五级台阶到第七级,树杈开始稀疏,树冠变瘦了。每次随铭兄来到这,恭敬地上香祭拜后,我的思绪都会信马由缰,想,待我和铭兄百年后,灵牌是不是应该摆在第十级的位置呢?
四
国胜老汉和老伴是最纯正的中国农民,一日三餐吃的、喝的,全是自己一手种养出来的。国胜老汉上过几年学,年轻时曾在茂名一个茶场务工,但几十年的大山生活,之前的那点见识早已折耗完了。老伴识字不多,只会用智能手机给儿女们打微信电话和语音留言。他们掌握的知识,就是什么时候上山剥树皮修竹枝,什么时候泡谷种插秧苗,什么时候种番薯播花生,什么时候耘田收谷子,什么时候伐木砍竹。而且他们只会一种语言,那就是粤西的一种方言。看电视时也是选择讲粤语的珠江台和岭南台。这些年因有我的加入,孙儿们也逐渐长大外出上学,学校推广了普通话,全家人团聚时使用的语言也就多了普通话。老人家听多了,也跟着学讲那么几句。慢慢地,他们看电视多了中央台。他们喜欢看天安门广场,喜欢看万里长城。我提议带两位老人飞一趟北京,实地看看天安门爬爬长城,亲身感受一下京城的繁华和热闹。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迟迟不能成行。我知道,那是他们心疼钱。
在大田面,所攒下的钱无一不是为了完成三件大事:盖房子,娶妻子,生儿子。大田面出现的第一栋楼房,是国胜老汉省吃俭用在1998年建起来的。将原来的泥砖换成了青砖,黛瓦也换成了琉璃瓦。随后几年,大田面的楼房如雨后春笋多了起来,比赛似的一家比一家高大、漂亮。几年时间,村子原来的泥砖房不复存在了。从房子可以看出,村里没有一个不成器的人。
大田面的土地稀缺,族内兄弟也常因一些利益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如:为廊檐水流向而争吵,为一蔸毛竹的归属较劲。早些年,国胜老汉与胞弟也曾为屋边的一棵橄榄树掉下来的橄榄,由谁捡拾而争吵,他一怒之下,提刀将树拦腰砍掉。可橄榄树生命力顽强,第二年又冒出枝杈,慢慢地又枝繁叶茂了。
就这样一个处于深山老林的大田面,“城镇化”还是将它的利爪伸了进来,伸进原本顽固不化的国胜老汉们的体内。
有本事的,除了在村里建一栋楼房外,纷纷到镇上新开发的楼盘又买一套商品房。商品房在镇上,骑个摩托车回大田面三十来分钟。用他们的话说,也就是几脚油门的事。那些靠起早贪黑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回镇上购置商品房的,成为村里人的标杆。国胜老汉们满以为,他们这一辈在村里建起楼房也算给儿子们垒了安乐窝,完成了人生大事。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几年后,儿孙们又比赛似的到镇上买屋。断崖式的社会变迁,让国胜老汉们猝不及防,仿佛隔着星空那样隔着世界,但又顺理成章地跟大田面融合在一起,闻所未闻的人和事,相继粉墨登场了。
大田面第一个在镇上买房的人是阿贵。早些年,阿贵外出打工攒下钱,回大田面建了一栋三层楼房,就不再出去了。在家里管护山林,种草养鱼,还被选举当上了队长。在外打工时,他学会了装潢,回到大田面后,他一边在村委当差,一边在村里承接装修工程。镇上开发楼盘后,他迅速又买了一套商品房。为了不荒掉土地和鱼塘,每天下午五点骑摩托回大田面割草喂鱼、捞糠喂鸡。刚开始,国胜老汉不明白,大田面好好的房子不住,有必要跑到镇上再买一套吗?来来回回浪费汽油。慢慢地,国胜老汉对所谓的城市化逐渐理清了认识。有一次,村里留守的六七个老人聚集在他家门口又扯起这个话题时,他吐着水烟,悠悠地说,城镇化嘛,不就是大田面的人向马贵迁移,马贵上的人向高州迁移,高州的人向茂名或者广州迁移……
是的,国胜老汉的认知是准确的。二儿子要到镇上买商品房,国胜老汉起初反对的强硬态度慢慢软了下来。要知道,最近几年,国胜老汉在已建的二层楼房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右侧又加建了半边楼,构成两间门头一字排开的三层建筑,外墙全贴上了白瓷砖,雄伟、亮堂。二儿子一家六口常年在外务工,他们在大田面的房间常年闲置,逢年过节回来住那么三五天。现在又到镇上再买一套房,其实是买个面子,一年到头住的时间不会超过半个月。唯一的孙子大学毕业,在广州一家证券公司谋了份差事,据说收入不错,也算是白领了。新房装修好后,国胜老汉和老伴去参观过一次。坐电梯时,两老都有些眩晕,不像在大田面,一出门,就可脚踏大地,就能闻到泥土、青草和溪流的气息。商品房是一格一格的,进屋要关门,天、地全都切断了,国胜老汉感觉到人是悬在半空、困在格子里。从窗户看出去还是窗户。整个屋子像一只倒扣下来的钟,沉闷得窒息。
五
镇上一家可同时摆设三十桌宴席的宏源山庄,张灯结彩。院子里临时撑起了几顶简易帐篷。三四个男女系围裙戴口罩在帐篷下忙碌。案桌上摆放一碟碟全鸡全鸭,肉皮微黄,翠绿香菜和紫荆花点缀其间。
二儿子和二儿媳笑容满面地在门口迎客。国胜老汉和老伴进门时,二儿子交代说,阿爸你们坐主桌。国胜老汉用鼻子嗯了一下,算是作答。大厅里电视播放着“好日子,那个好日子……”
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一连阴了几天的梅雨放晴了,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宴席上。刚还在大田面时,国胜老汉的心里还积着一股气,但到了酒席上,气顺了许多,一半是出于应酬,一半是被这喜庆的场面感染了。他应该高兴。亲朋好友都来贺喜。儿子靠打工在镇上全款买下这套一百六十多平方米的大户型,他脸上有光。自己十多年前耗尽所有积蓄建起的三层楼房,空着就让它空着吧。它存在世间的意义,居住的功能越来越弱。但是,如果没有这栋楼房,还有什么可以代表他曾经的人生呢?
吃完席,国胜老汉和老伴便匆匆赶回大田面了。对老人来说,哪里能让他们安详待着,哪里就是天堂。一回到家,他立即换上那身出工才穿的衣服,扛着锄头来到玉米地。春节后播下的玉米,已长出了筷子那么高的嫩苗,一起长高的还有稗草。他锄上几锄,直起腰来,撑着锄头仰视四周的群山,像一个国王思考他的江山社稷和前途命运。村里能交流的人越来越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喜欢跟稻草人对话,跟花草树木对话,跟起起落落的飞鸟对话,跟晶莹闪烁且缓慢流淌的河水对话。当然,很多对话都是在他心里完成,花草听不到,飞鸟听不到,河水肯定也听不到,可他知道想说什么。那是他向内的情感,在另一个维度上向上而生。有时,他也会蹲在当年那棵涉事橄榄树下抽烟,落下的黑橄榄撒了一地,早已无人捡拾了。
我愿意相信,国胜老汉和老伴能活一百岁,但是人终将会离去,村里的人们包括我们这一家子也终将回归自然各安其好。每想到这,我就觉得亲情是多么珍贵。大田面这个在大山荒凉的褶皱里垒起的村庄,终将会成为海市蜃楼。如《百年孤独》里描述的马孔多一样,随着最后一位亲人的离去,它将从世人的记忆中根除。陈氏家族这棵大树,不会像村头的鸡毛松那样永远枝繁叶茂。但是,大田面也不会像彻底消失的马孔多。大田面毕竟还是人间真实存在的大田面。村里的人们一个个搬走了,但这里仍屹立着陈氏祠堂和开天庙,还有社王石和社王树。它们将是一束永远不会熄灭的光。它们似一块大磁铁,将散落在四面八方的陈氏血脉凝聚在一起,鸟儿们会在每年的春天准时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鸡毛松上欢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