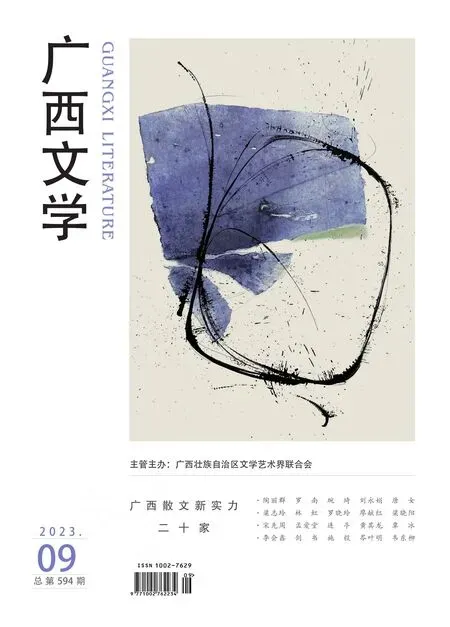目之所及
2023-10-22梁志玲
梁志玲
一
黄昏,门口系的风铃急促晃响起来。宠物医院进来一家三口,两夫妻很胖,但年轻,女儿七八岁吧,婴儿肥,穿的是校服,紧绷绷的,蓝白配的齐膝背心裙子,白袜子,横扣的黑鞋子。小女孩小心翼翼把一团布搁在宠物店的就诊台上,拂开布团,是一只瑟瑟发抖的狸花猫,是小奶猫,八月的南方不冷,它是疼得哆嗦。女人目光一直游离在女孩和猫之间,男人则一直在低头玩游戏。
小奶猫看见我抱的狗,那一瞬间它本能警惕,忍住痛全身炸起毛。
小女孩慢慢地一下一下一寸一寸抚平它耸立的胎毛。
我的狗在舔着我的手,医生说:博美犬的基因缺陷就是容易有心脏病。
此刻,它们都是病友。
女人说,这猫从七楼掉下来就是这样了,你看看情况怎么样。记得我们窗户都关得很好,回来不见它,到楼下就发现它落在冬青树下。
小奶猫去拍片了,拍片室断断续续传来“小心”“轻一点”“别动它那里”“哦哦,别叫,忍一点,两下就好了”。
他们重新来到就诊台。医生说,现在拍片初步判断就是臀骨骨折了,它掉下来的时候估计是屁股着地。也不知道内脏受伤没有,两个月的猫太小了,不建议手术,我就只能开点消炎的药,看这几天能不能靠自己熬过危险期,实在不行顺其自然吧。你们看是带回家,还是留在这里观察。
女人对小女孩说,你做主吧,是你捡来的流浪猫,是你的缘分带来的,你要对它负责,学会对它负责。
女人在“负责”这两个字上稍微加重了语气。
小女孩说,留在这里吧。有医生呢。
过了一会,她又嘟嘟囔囔:带回去吧,有我们陪着它。
女人说,给它打止痛针吧,它喊得嗓子都哑了。
小女孩一刻不停抚摸这小奶猫,恨不得替它疼一下,仿佛疼也是有温度的,可以顺着手的接触传导过来,挥发在空气里。她理解的“负责”就是对它好。
在后颈处打针时,猫挣扎起来,医生示意他们都离远一点,说这猫没打过疫苗的,急起来会抓人,不要让人陪着受伤。
医生说,要补点钙,让骨头好愈合,你们家里都有吧?
女人说,钙片我们都有的,我们其实都是同行,只不过你是给动物看病,我是给人看病。人的钙片和动物的还是不同的,你开点药吧。
在一来一往的交谈中,我大概知道两夫妇都是医生。这让我又特别看了他们几眼,因为他们是见惯生死的人。一直低头玩游戏的男人,我以为漠不关心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拿来了一个纸箱,小心铺上布。他们小心把小奶猫托进纸箱,付了六百多元就诊费。
门口的风铃哐啷响过。他们走了。人到中年,我已经不习惯用“爆浆”的语言描述一个场面了,“爆浆”总是与美有关的,比如唇齿留香的美食,比如激情四射兴奋的情绪;“爆浆”和场景有关,比如烟火气十足的夜市摊,比如温馨浪漫的生日烛光;“爆浆”和气味有关,比如撸串的香辣味,比如奶油芝士的甜腻。在这里,从头到尾,我这个旁观者只说了一句话,没事的,猫有九条命呢。世间万物都得承受属于它的命运。在命运手起刀落之间,如果一定要淌血那不是爆浆,它只是一种有颜色的悄然而至的冷,只是它的气味是腥的。
我还在抱着我的狗,那团柔软的生命。医生说,狗是有点心脏肥大,心脏病是不能治愈的,只能缓解,保养好的话和人一样也能活很久,当然有时候你也得接受它突然离开,顺其自然吧。他又说了一次顺其自然。他小心避开“猝死”这个词。
门口的风铃哐啷再次响过,我也离开了宠物医院,路上行人很少,路灯下的人背影踉踉跄跄。我缓步走在路上,踩着自己的影子,只要我活着我的影子就是活的,永远踩不死。这条路有两个“口袋公园”,白天看时小而精巧,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晨练的人挟风而至,汗津津的。这是世俗世界里的园林。
我一年年活着,我的心也活出一个庭园了,只是它一定是日本枯山水庭园,侘寂,只有沙石、苔藓、不开花的树、象征岛屿的岩石堆叠。侘寂接受生活是复杂的,崇尚简单。它承认三个简单的事实:没有什么能长存,没有什么是完成的,没有什么是完美的。
我经常在我的庭园陷入冥想。
二
一天遛两次狗是我恒定的生活日常。我的狗叫瓜皮,既傻瓜又调皮。
早上六点钟,小区还是很安静的,有雾,清冷。
小区的私家车在路灯下静默,白色车和黑色车居多,车身某个角度和路灯对上时,折射出一道道冷白的光。每一辆车的大小都不同,起起伏伏肃然陈列着,像一座座空心灵柩,等待着天亮后填充成实心的灵柩,这是车严肃的使命。其实,每一个人都奔跑在去往死亡的路上,只是是否借助工具、快与慢而已。“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台词,我不记得是哪个角色说的了。带点反光的车牌数字隐匿着主人神秘的寓意,或是出生日或是夫妻姓氏的头一个字母或是某个纪念日,这一切在黑暗中更像碑文了。几辆僵尸车围着一圈草,花圈一样。偶尔有几只野猫从车轮下蹿过,惊扰了夜的素寒。一只三条腿的黑猫,稍微落后,却兀自平衡着身体,跳跃着经过垃圾桶,在城市的丛林法则下顽强生存。
瓜皮就吠叫了一下,声音在林立的楼间回荡,刺耳。耸立的楼就亮了一两个窗口,吐出一道光掉出窗外,像嗑瓜子的人在虚掷时光,本来是要吐出瓜子壳的,却不小心吐出了瓜子仁,瓜子仁一样的光落在地上,没有人去捡,也捡不起来。
我牵着狗走过那片绿地,我不忌讳走过去,也不怕走近那栋楼。
那栋楼曾经有业主跳楼身亡,一个癌症患者不愿拖累家人,在清晨做好家人的早餐后,选择从阳台跃下了楼。正是上班高峰期,涌出小区的车辆纷纷避让着开进来的救护车,救护车逆流而上,车顶灯闪烁,人心闪烁,一切让人心绪难言。
相对于活着,自杀是一种逆行。
我住的小区就在市人民医院对面,住户大多数都是医护人员。走的人本身是一名医生,她肯定温和地鼓励过来问诊的患者,但是当她成为患者时,她没有和癌症奋战,她是通透的。
那天早上九点,业委会在小区群里@全体成员:“小区各位业主,在困难和病魔面前,我们要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每一个人要坚强起来。家人、爱人、邻居,我们都要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打造美好生活。”看着这样的话,觉得人其实不是孤立的,总有一些人在做出努力,眼睛润了起来。
瓜皮喜欢和一只名叫虎妞的腊肠犬玩,腊肠犬是我同事养的,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是一个能够把早餐和中餐放到下午三点一起解决的人。我不明白一个作息不正常、生活潦草的人怎么会想起养一条狗呢。
他说,我是夜猫子,当时也没睡着的,就是听见砰的一声响,以为是楼顶晒的东西掉下来。人一定经过我的窗口才落地的。
他还说了一句,说不定还往我屋里看了一眼。他惊疑的表情里,暗藏了想象,想象了那“一眼”里面的五味杂糅。
很久以后同事说,狗是辟邪的啊。一黑二黄三花四白,黄色算是棕色吧,棕色狗也蛮辟邪的。他是舞蹈编导,却一直只能为大妈们编创广场舞,舞蹈界不大入流的广场舞。他话头突然转到舞蹈,竟自痴迷起来,站起来扎马步曲手臂比画了一下,说是用舞蹈呈现“外圆内方”的东方哲学,外部的浑圆内部的方正。我却仿佛看见他家的腊肠犬飞快地从时空穿梭门中跃过,把一脸怀才不遇的他撞了一个满怀,无论富贵贫穷地舔了他一脸口水。
我明白了。他是在坠楼事件后养的狗,皮毛油亮、棕色的狗。
一个小区,相继有两个人跳楼身亡,不免唏嘘。死亡虽然是一个殊途同归的事情,只是我们在乎的是先与后,我们承认生命的循环往复,只是我们在乎往复时画出的圈是大的还是小的,对于死亡很多人不愿争先恐后。
自杀的人是争先的人,在深夜里抽掉几盒香烟纵身跳下,他不是争先,是挣扎,挣扎掉牵挂挣扎掉陪伴。
冬至,雨后,小区的三角梅开了,各种颜色。冬天的三角梅,你喜欢哪一种?对于我,玫红色开得太滥了,滥得咄咄逼人,浑然不自知自己的肥厚和油腻。而水红色和黄色,是几种色谱杂糅而成的颜色,立场未免有点含糊而混沌,但也能讨巧不少人。
我喜欢的是白色的三角梅,在庞杂的枝干中,它决然凛冽渲染出自己的白,斩钉截铁的姿态,是清洌更是孤绝。那是中年的我回头看见的“致青春”。当然,我们以为的花其实是叶子,有颜色的叶子罢了。靠近花的叶子都揣着各种心情,在花开之际,憋出一脸的心思,玫红、水红、黄色、白色的心思。我知道,我明白。
我心灵的枯山水庭园,偏白色调,一定要种花的话,一定是白色的花,花下打盹的一定是我家那只白色的博美犬——瓜皮。那种不同层次的白,是白色在颤动地汹涌,企图掩埋流动的时间。我给它喂食药物,希望它的心脏病发作迟一点,远离猝死。我需要它的陪伴。可是我要努力接受生命是不完美的。
三
冬季,风不大却刺骨。下楼时碰见老奶奶拴着她的博美犬,棕色的狗。老奶奶穿得棉墩墩的,狗也穿得棉墩墩的,很亲子款。老人和一条狗走在路上,有一种古老的温情结构,构图放在影像里,背景往往是香槟色的夕阳,而不是朝阳。
她说,妞妞拉肚子几天了,下楼都走不了几步了。
近年来,电子商务课程越来越受到高校重视,它不再只是经管专业的必修课程,很多高校都将其融入到人才培养的目标中。因为电子商务课程是一门涵盖信息技术、网络营销、国际贸易、财务管理和物流等方面知识的复合型课程,能够培养学生广阔的互联网思维,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所以它受到各类学校青睐,并被纳入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电子商务课程改革要想紧跟时代的新需求和新方向,必须以创新创业为导向,将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和目标融入其中,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需求的电子商务技能型人才。
我看了看她的狗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她说,能说什么,它陪了我十三年了,博美犬的寿命大概就是这个年龄了,我从医院退休那年,我女儿买给我的。老了就这样了。
我说,自然规律了。
她说,老了就老死了呗。能怎么样啊。
我一时无语。风掠起老奶奶凌乱的头发扑在她的皱纹上,头发和皱纹交织成一张网,网住一张平静的脸,却网不住时间。
在小区里,我还看见一个老爷爷拄着拐杖,颤巍巍遛一条同样颤巍巍的吉娃娃犬,是公狗,抬后腿尿尿已经成为它一种沉重的负担。
他说,它十六岁了,不知道还可以活多久。
他问了一个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他以前是中学数学老师,知道各种公式和解题技巧,但是他算不清属于生命的数学题。他想说的应该是,不知道谁先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狗已经相当于人的一百岁了。阳光斑驳,光影轻晃,把他拄的拐杖拉得很长很长,像纤细的杠杆,撬不起厚重的时间。
我上班的地点是文化艺术中心大楼,那是一栋隔音非常差的楼,楼上的歌舞团传出的音乐总是不由分说拜访各个办公室,走亲戚一样喧哗。那对新招聘来的双胞胎姐妹花演员却非常安静,她们表演的节目——杂技柔术是安静的。在演出时,她们的身子超越极限地向前向后拗过来又拗过去,抻拉、反弓、团成圆球,有时候像不断张合的剪刀,两个人一起折叠出一把大剪刀,双腿张合折叠出小剪刀,双臂翻转折叠出一把美工刀,大大小小的剪刀迷惘地剪向各个方向。我觉得她们迫切需要剪辑掉的是逼迫到她们面前的时间。紧身的衣服勾勒出她们的丰满,这种丰满是危险的,与情欲无关的危险,丰满在磨损平衡力和柔韧度。演员是吃青春饭的,柔术演员的舞台生涯更加短暂。柔术需要孩童般的身段。她们应该也是二十多岁了,矮小,多肉,却不再是婴儿肥。
我们默默看着,背地里议论一番后,叹口气收尾。我们都知道学杂技柔术要很小的时候就学,除非家境很差上不起学,否则父母是不轻易让自己的子女去学的。
让我吃惊的是这对双胞胎姐妹养了一只非常大的阿拉斯加犬。她们带阿拉斯加来大楼时,狗坐下来,支棱起上身,高高昂起头,三个身影的高度几乎是一样的。我曾小心翼翼摸了一下狗的毛发,心里担心这两姐妹控制不住这大型犬。
姐妹花在歌舞团是不能单纯只表演柔术的,她们也得演小品。因为矮小只能演孩童。我在楼上俯瞰她们排练。她们穿上了膨胀感十足的校服显得更矮了,书包沉甸甸压在后背,两束头发高高绑起来。她们扮演的是留守儿童,她们努力龇出天真无邪的笑容,努力爆出银铃般的笑声,努力蹦出修饰性很强的童音。她们努力表演爱与关怀,表演梦想成真与皆大欢喜。她们的表演动作不断被导演纠正再纠正,让她们熟练掌握笑容、笑声、童音。无论她们最后演成什么样,我只记得她们是一对心事重重的成年人。
排练结束,她们牵着阿拉斯加犬坐上电驴,狗从车头探出脑袋,掩饰不住的兴奋与傲娇,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亲昵地摸了一下狗的脑袋,她们的表情是欢欣的、稚气的、松弛的,她们以毫不掩饰回报狗的毫不掩饰,所谓坦诚吧。但是只是一刹那而已,然后她们恢复了惯常的平静和倦怠。
我突然理解她们为什么养一只威慑力十足的阿拉斯加犬了。常年租房子在外谋生活的姐妹,无依无靠,这狗是陪伴更是防身。
对时间对年龄束手无策的姐妹花在楼道里和我默默擦肩而过。
时间这个东西总是让人心情复杂。有段时间我对“回放”有种神经质的迷恋。
我开的移动套餐赠送了一个监控器,我把它安放在客厅,我不知道装这个监控的意义是什么,只是觉得是白送的就要了。我经常在手机上打开回放,像穿越时空一样打量某个时刻的我,我在窥视我自己。大多数情况下,我的行为刻板单调,吃饭喝水打哈欠打喷嚏蓬头垢面挤青春痘抹润肤露涂口红拉开窗帘伸懒腰。我手指经常滑到提示有画面变化的时段。
凌晨五点,回放的视频提示画面有变化,我反复看着这个视频,沙发上的抱枕还在原来的位置歪着,冰箱的门是关着的,狗也没溜到客厅。暂停放大画面,客厅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变化啊,难道监控可以觉察到绿萝在缓慢地舒展叶子吗?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如果监控如此敏感,反倒没有监控的意义了。我再一次观察画面,看见了,右上角那里,很小的一个光斑,另外一栋楼倒映在落地窗里,楼上有一个房间的灯亮了一下就灭了。是要奶孩子的女人起夜?还是夜尿急起身上厕所?不得而知。我窥探我自己,其实也在窥探别人。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宇宙中安装一个巨大的监控器,让几百年后的人类回放看到今天的我们。他们的目光就可以穿越,很有在场感地看着我们,看着人类,如何一步步衰老一步步死亡。因为回放,我们会是《楚门世界》里的楚门,被众人全方位打量。
遛狗时,一个少女默不作声在身后跟了我很长一段路,最后她似乎鼓起了勇气,说,我可以抱一下你的狗吗?我说,可以啊,你不怕狗就行。她蹲下身子,抱起狗,脸颊反复蹭着瓜皮,手机自拍了很多张相片。她泪光盈盈恋恋不舍放下狗,说,长得真像我家的狗,它前两天去了汪星了,不在了。少女背影单薄地融进了无穷的夜色,融进了这个充满秩序感的城市,我不知道她的原生家庭是怎样,但是我知道她的柔软。狗的一岁相当于人类的七岁,相遇注定着离别,没有谁比谁更能拥有永恒,在地球之上,起起落落的太阳知道这些生命的秩序。
春天,我躺在沙发上发低烧,也懒得吃药,听天由命等着自愈,即使不发烧大多数的时间我都躺在沙发里,把摆烂状态艺术地化为静待花开宁静致远。身上的热度使我厌世般地胡思乱想,想象死亡的触角,触角上的小吸盘探入自己的血管,想象死亡的苍白,横着出门的肉身,迫于电梯的狭窄,竖着下楼的肉身,惊扰了平民百姓的俗世生活,想象死亡亦是不易的。世事的纷繁与割裂蜂拥而上,被边缘的各种处境让人意难平。但是我努力戒掉自己的倾诉欲,倾诉只能显得矫情,很多事情只能埋在心里,沉淀成为一坨冰……迷糊中,脚指头酥痒温润了一下。瓜皮在舔舐我的脚趾,然后它大大方方昂首挺胸看着我,一览无余清澈地注视我,汪汪汪,忘忘忘——主人啊,你今天忘记喂我了,忘记出门遛我了,忘掉不高兴的事情出门吧。那份注视瞬间把我的社会属性清空了,只感觉它是一个生命,我是一个生命,是生命的相视相伴,我们都是活的生命。我得以从容地叹了口气,起来倒上狗粮让它吃了,拉它出门。在电梯里我被动微笑地回应左邻右舍的招呼;路过杂货店,积极营生的店主养有一只比熊犬,我被动接过他们的招揽话头;踉踉跄跄学走路的孩子跌在我脚前,我不得不被动地扶起他,被动地接受他父母的谢意;在草坪上被动地和别人谈了一下物价天气时装团购。几次打起精神被动互动后,似乎我借着惯性主动起来,我低头,看见瓜皮依然清澈地注视我,它用它的需求来督促我出门与这个烟火气十足的世界进行触摸。木棉花“吧嗒”落在草坪上,紧接着又有一朵砸在我头上,吓了我一跳。
我居然被猝不及防的春天吓了一跳,瓜皮叫起来,似乎嘲笑我。南疆的木棉花已经开了,昂扬铿锵,飘落的桃花邀约叶尖的晨露一起到草坪撒野,瓜皮自然要快乐要打滚,桃花、露珠一起沾到了它背上,外面的世界如此生机勃勃野气横生,这只小狗把我从幽闭的洞穴里叼了出来,世间毛茸茸的气息令人百感交集。
瓜皮不知道富贵荣华、社会等级是什么,但是它知道出门就有遇见,它要我陪它出门,我是它的全部,我在一个生命面前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了。
冬天,我继续缝布垫子,用我自己的旧衣服缝制一个暖和的垫子。瓜皮坐在旁边仰头看着我,它知道我在给它缝,我知道买一个垫子也不贵,但是我喜欢缝制有我气息的垫子。取暖器在一旁亮着红光,吱吱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冬雨绵密,窗外的雨声,一滴、两滴……一更、两更……时间的滴漏声悠长,每一个生命都听见了,自然包括狗,我们一起听见了。
我把线剪断,蘸了点口水把线团了一下打结。布垫子摊放在冰冷的瓷砖地板上,它马上很欢喜地卧在上面,掩饰不住的宠溺感。暖老温贫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吧。
我让瓜皮看手机视频里:它走在阳光里左右摆动屁股,腾起四肢身影生机勃勃,尾巴像蒲公英在风中支棱……它却傲娇地掉头不看,不认识自己,它以为是另外一个动物在和主人争宠。
这样的时光能够回放暂停多好。此时我特别喜欢小狗文学里的一些话:
——世界不让狗狗说话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爱和忠诚是要通过行动来表达的。
——小狗的心事就算化成雨,也不敢淋湿你。
那些话语就像它脚板上肉垫子的摩挲,热乎乎毛茸茸的质感。
四
然而我的瓜皮还是离开了我。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2022年12月20日,搞活动忙碌了一天,我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狗一如既往用热切的眼神督促我遛它。遛狗回来我又困又累,但感觉到它搭在我床沿看着我,很依恋,我努力睁开眼睛摸了一下它的头,它很快出去了,我又睡迷糊了。模糊中我听见客厅有抓刨的声音,我起床看了一下,满地的呕吐物,瓜皮口吐白沫倒地抽搐,我抱着它大声呼唤,它不动了,但是身子还热乎。我慌忙打宠物店电话。
我语无伦次地说,它已经不动了——
老板说,看视频估计是中毒了,这种中毒是很难救活的。
突然瓜皮在我怀里又动了一下,喘了气。我大叫,它还在动,还有气的,我没有宠物医院电话,你们帮找个医生来救救它吧。
他说,快一点钟了,我帮你联系医生到店吧,你马上过来。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我抱住了它,它努力回应了我,回光返照。
到了医院,医生很快地进行输液,打各种针。询问我是不是吃了异物。我说,没有的。我遛的时候一直牵着绳子,只是在树底下的时候,它脱离了我视线一下,但不久我就拽回来了。你还不拍片?
他说,来不及了,先输液吸氧。你先签字。我赶紧签了病危单。病因那里,医生叫我填上“中毒”。
瓜皮不断地抽搐,腰弓起来,四肢颤抖,我扶着氧气面罩,不断呼唤它抚摸它,它的眼睛一直看着我,我在它耳朵边喃喃:瓜皮别这样,我在这里,你要好好活下来。医生忙着按压做心肺复苏,有时候会缓下来听一下心脏,量体温,他说:再这样不断抽搐,它会因为心脏衰竭而死掉,得打镇静剂。我说,打啊,赶紧打啊。
稍微安静以后,它又抽搐起来,我急急地说,再打镇静剂啊。医生说,不能打大剂量的。我看见它啃着面罩壁,我叫起来,它是不是口渴要喝水,嘴巴在咂巴。医生说,中毒的小狗神经会受损,会不自觉地咬东西。我痛恨医生的实事求是。
按压停顿中,我一遍遍问:缓下来了?没事了?医生说:没过危险期的。
在不断反反复复按压后,瓜皮不再抽搐了,平静下来了,我松口气,迫切地说:好了吧,没事了吧。医生拿起听筒听了一下,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瓜皮去了汪星,此时是2022年12月21日凌晨1点15分。
我紧紧抱住它,心都碎了,哭起来:不会吧,就这样走了,不会的。我反反复复撸着它的四肢说:不会的,你们看,它四肢很软很热的。还活着吧。
我看见它歪在嘴角的舌头,无力地长长下垂,似乎随时要滑落地板上,我愤恨地说,怎么能让它的舌头掉出来,还是紫色的,以前它的舌头都是粉红的。
医生赶紧说,我帮你处理一下。他小心地用镊子和棉签把它的舌头托起来,有那么一刻我还担心那冰冷的镊子会把它的舌尖弄痛,那段舌头从两排牙齿中一点点挪抬回原来的地方了,它的嘴巴已经不认识舌头了,不肯再张大了。我多么不忍心这样描述曾经无数次扮萌的小舌头。
我看着它的大眼睛,黑漆漆的一片,又伤心地叫起来:它还在看着我,你们赶紧帮它闭上眼睛啊……它是不是没有死。
医生说,狗去世和人不同,眼睛是不闭上的。
这说法是真的吗?但是它真的瞳孔已经放大了,看不见我了。它最后那一刻似乎都是微笑的。
店老板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说,阿姐,别难过了,只怪缘分太浅了。我陪你坐一会吧。
很久以后我一直记得他说的,我陪你坐一会吧。就好像瓜皮不会说话,在我难过时,用眼神告诉我:我陪你坐一会吧。我都懂。
我祥林嫂一样地说,好后悔,我今晚就不应该还出门遛狗,我一直牵着绳子的。怎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中毒就不能救了啊。
小伙子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只是用手扶了我一下手臂,说,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中毒,不排除是老鼠药中毒,现在是冬天,很多人要吃狗肉,有些毒,只是给狗闻一下,几分钟狗就死了。
他为什么给我讲那么详细,我不想听。间歇停顿下来,我问,你们一般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小伙子说,我们一般会帮埋在对面公园的山头上,山头短时间不会铲平。我去帮你拿个纸箱吧。但是负责埋葬的员工已经是新冠阳性高烧不上班,等明天看看。
小伙子拿来了纸箱,我一看又伤心地叫起来,怎么拿那么烂那么难看的纸箱,还没有垫子,瓜皮会冷死的。
小伙子说,目前没有其他箱子了,我再垫一点其他垫子吧。你看你是放在宠物医院还是拿回去,拿回去你会越看越伤心。
我说,我要拿回去,它还有很多衣服垫子玩具。
我是觉得它怎么能自己待在这里。总觉得放上一晚万一它又活过来,我电脑坏了,有时候第二天打开又能正常运转了。
小伙子说,要不我送你回去吧,你这样子我怕你开不了车。
我控制了一下情绪,不哭了,说,我自己开车回去吧。缓一下后,我把治疗费通过微信转账给你们。
我把它放在客厅,替它包上那条蓝色的褥子,放上它喜欢的玩具。我盖上褥子,再也不敢看它,客厅的灯亮着,我整夜都在迷糊中。我发现它在中毒的煎熬期间,依然挣扎着跑到卫生间把尿液和大便排尽,它知道我不喜欢它乱尿。
天亮时,我驱车来到小姨家,乡下的山坡有果树,我选择一棵橙子树亲手埋葬了它,愿它化作春泥更护花更护果。这个山坡往年清明扫墓我都会路过。很多天我都在心碎中,打开门的刹那再没有小可爱从门缝探头出来了,以前它总是垂着粉红色的舌头笑意盈盈迎接我。湿漉漉的舌头,摇来摇去的尾巴,还有永远仰望着我的眼神,它对我的感情如此真切,我一把抱住它,我对它的真切回应得如此热切。
我一遍遍重走那天我遛狗的路线,那是我惯常走的路线,我一会儿后悔那天很晚了才遛它以致看不清它吃了啥,一会儿觉得它走得很痛苦,也许我应该让它安乐死,一会儿自责忘记给它洗澡再埋葬。看见一个垃圾桶旁边有一个打开的老鼠屋,我愤恨地想,怎么能把打开的老鼠屋乱扔呢,这样会毒死多少动物啊。我动手把老鼠屋安放好。
这段时间我周围很多人新冠阳性,我打开自己的健康码依然是绿的。我又伤心了,民间有一个说法,家里的狗突然去世,是因为它在为主人挡灾。可是我宁愿是阳性,也不愿它以性命挡灾,是它默默陪我度过了无法言述的低谷期。
我轻轻撕掉冰箱上写的“瓜皮减肥”的纸片,低语:
——瓜皮,那时候医生说心脏病肥大要减肥,我控制着不给你吃肉,你就馋着路边的食物。现在想想还不如不减肥了,爱吃啥就给你吃啥。
——瓜皮,好几次我把你写进我的小说,发表得了稿酬,你自己为自己挣来了足够的狗粮和零食,可是你只活了五岁,还有很多狗粮和零食都没有吃完。我刷到抖音说某小狗被撞,埋葬后,假死又复活了。那一刻我又后悔我把你埋葬太早了,说不定你只是假死,还能回来。你回来的话春天就不用来了,甚至什么名利都不用来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宠物医院推出一条信息“近期发生多起宠物于××地玩耍时中毒事件。希望广大宠主在宠物玩耍时多观察宠物情况,尽量少去出事地点,若有任何紧急情况请及时就医。望各位宠主广而告之。”
“××地”“多起宠物中毒”——我心里又刺痛起来。
五
没有一种时间滴漏是脱离地球吸引力的,时间不急不缓勇毅往前,我们拽不住它的衣袖,时间就这样丝滑地过去了。
后来,姐妹花也带着阿拉斯加犬辞职离开了这座城市,不知所终。
后来,老奶奶还在一板一眼跳广场舞,老爷爷还在颤巍巍散步,只是他们身边的狗都不见了。
我会和他们对视一下,看向他们身后,然后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我们路过互为风景。我不知道他们心灵的庭园是什么样的,我们不互相邀约,不互相打扰。
大地之上,楼宇之间,人也好、狗也好、三角梅也好,此消彼长。
因为尊重和平等,有了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推文总是说得如此催人泪下。被挤压的人生总会被一些细细碎碎的爱治愈。
一个人在惯常走的路线上散步,我和一位阿姐打了照面,她养有一只英姿勃发的边牧,是瓜皮的玩伴。她吃惊地说,我好久不见你拉小狗散步了,我以为你搬家了。我都习惯你早上六点就出现在这里了。我平静地说了。阿姐说,你别难过,我家的布偶猫刚刚生了一窝小猫,我送一只给你养,陪你玩。我笑笑,说,我家的阳台是敞开式的,不适合养猫。
我笑别,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走向下一个路口。夕阳硕大,宁静,冷静。
此刻,我再次想起一个词:侘寂。带着蜘蛛网和苔藓气息的一个词,阳光斑驳地照着生命的补丁,针脚粗粝,却每一根线都被人的手细细捻过,扯长。打结断线时,会有人偏过头,用牙齿咬断线,口水润湿了线,手心汗浸润了线。这样的气息,这样的补丁在着、暖着。就算生活百孔千疮,总有温润的补丁,总有温润的针线,把你的目光拉长再拉长,长得越过山高水阔,长得像世间的路带你走向下一个路口。
目之所及,城市楼房挨挨挤挤,无数的生命偶遇同行,他们互相投射自己的心理,以此支撑走完短暂的一生,爱与尊重在这样的城市里无声地演绎着。
目之所及,那些或长或短的生命互相盘结在一起,无关物种,激荡也好徘徊往复也好,终是浑圆一体,轰隆隆碾压过浩瀚的时间广袤的宇宙,前仆后继地让世界更加有质感。
目之所及,万物生长,直至华盛华美,再转至荼蘼,唯有无限包容无限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