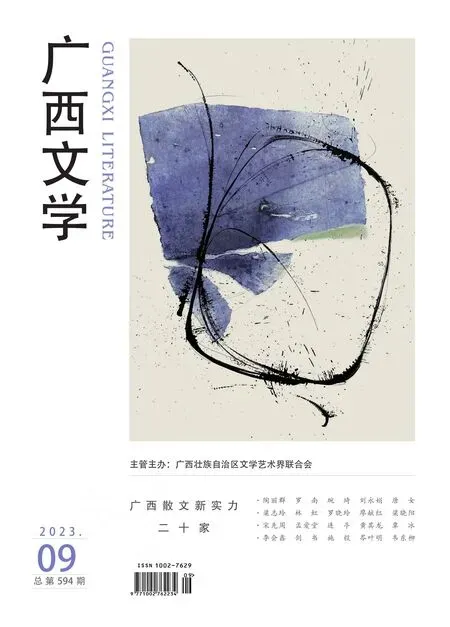怜 悯
2023-10-22刘永娟
刘永娟
1
下了课去按摩,照例和师傅先说些家常话。
师傅长得好看。一双柳叶眉,玉葱似的鼻梁,头发柔顺齐肩,走起路来,那腰扭得像水蛇。美中不足的是,因为眼疾,她双眼皮下的两只大眼睛显得灰暗。不过也正因如此,她的气质里竟带上了这个年纪难得的一丝纯真。
她不戴墨镜,也不套白褂子,总是穿各式时髦的衣衫。
我说:“你这条裙子真是好看呐。”她问:“是不是向日葵的颜色?”我说:“不是,是米色。那种没经过抛光的米,带一点点黄,看起来又不是黄,养眼。”她就笑,说:“我女买的。”停一下,又加一句:“鞋也是她帮买的。”
趴在按摩床上,脑袋陷进床头的窟窿里,我看着她的裙角飘来摆去,听着她的鞋跟嗒嗒作响。她从我左侧绕到右侧,又从右侧绕回左侧,不需要言语,却总能摸到我肩颈肌肉的僵硬的结块,然后稳准狠地三下两下把它们推松开去。
忘了怎么起的话头,师傅说她已经一年多没来大姨妈了。
她说闭经前的那段日子,大姨妈有时两三个月不来,有时一个月来两三次;有时量大得惊人,有时又只来一点血泡泡就结束。身体冷热不定,一下子一股热浪涌过来出一身汗,一下子又冷得想要找棉衣。心情也阴晴不定,偶尔莫名其妙就想唱歌,更多的时候是无缘无故想掉泪,觉得活着没得什么意思。有时正给客人按摩,突然涌来巨大的悲伤,就只能拼命忍着,等客人离开才关上门大哭一场。
“两三年间也都没个安生觉,深更半夜在床上煎鱼干,也想过干脆慢慢死掉算了。你晓不晓得,如果不吃不喝,到底几天能死?”她问,没等我说话,又自己回答,“我问过百度,最少也得七天。结果我只饿了半天就眼冒金星,肚子一空,那些想死的念头也一起瘪了,就爬起来做一顿好吃的。”
说完,她带着点羞涩笑了起来。
“后来慢慢也就想通了,再难受的事也都会过去。现在我的大姨妈不就彻底和我断清了吗?那些折磨人的症状也没了。有时候也会觉得惶惑,觉得自己的女人期结束了,黄土快埋到颈嗓了;有时候又觉得轻松,想想没有那一屁股血的日子真的好清爽。”
临走师傅拦我,说她女儿早几天带回来两盒智利车厘子,要分点给我尝尝,还说上次我带给她的荔浦芋又糯又香。
递给我车厘子的时候,师傅又说她女儿这段时间焦头烂额,在给公司弄一个宣传企划,问我能不能帮看看企划书的草稿,还说她在女儿面前提过我很多次了。
我就让她把她女儿的微信推给我。
这样我们又站在门口说了六七分钟的话,直到下一个客人推门要进来。
我和师傅是微信好友,但我们除了预约按摩从来不联系。我从挂在墙上的营业执照知道她的名字叫李美娇,不过我从没叫过她名字。我总是叫她“我的师傅”。
却觉得和她亲近。
那种感觉,就像两个人偶遇在坡度平缓的螺旋楼梯,开始说的都是家常话,外面天好热了房子不好卖了之类的。不知不觉间,楼梯慢慢变陡了,两人毫无察觉嗖嗖地就走进了通往隐秘空间的窄门,随后继续毫无目的地沿着慢慢恢复平缓的楼梯往下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却触到了常人难以抵达的深处,瞥见了生命破碎的真实。
这是四月,尧山上开满了杜鹃花的季节。
2
师傅五十岁,在骖鸾街开了十二年的按摩店。
起初她倒是请过人,但骖鸾街的客人也是刁得很,他们大多数宁愿坐在小杌子上闲扯,或者到穿山公园走一圈再回来,也要等到她的轮次。这种情况下,请的师傅都做不久。开始,人走空了,她就发信息招聘,中间也稀稀拉拉来过几个,可也都是做不长,有的甚至做不到一个礼拜就走人了。
后来她懒得再请师傅,就自己一个人守着店,守着三张并排的窄床。
过一阵子她转让出去一张按摩床,买回一张长沙发,靠墙角摆着。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自由得很,有事了想关门就关门,平时想吃好的就做好点,想简单点就简单点,不想做,对面店里一碗米粉就对付了。今天中午一碗白稀饭配两个红薯,加一小碟萝卜干,吃得就很好。要是请了人,吃方面就要考虑得复杂些。”
“经常你来的时候看见我在沙发上瘫倒。没得人来我就听喜马拉雅,有人来就做事。故事频道上各种故事有意思得很。你上次给我推荐费勇讲《心经》,这几天我一直在听,听得都想关门到庙里当尼姑去。你晓得的嘛,一个人待着经常会生出些麻烦事。”
师傅零零星星地和我说过那些 “麻烦事”。她说得委婉,其实都是些烂污事,装起来一箩筐一箩筐的。
骖鸾街的那些臭男人,有的一走进来就嬉皮笑脸不怀好意地问:“给前列腺推油好多钱吗?”“可不可以专门帮我按下趾骨,点一个钟的。”有的是开始的时候假装一本正经,等按摩的时候,猛然探头要咬她的耳朵,或者伸手摸她的大腿。有的男人没动手动脚,但嘴里总要说些下流话,占口头便宜,什么“该吃晌午了,我们到后面厨房,我下面给你吃”之类。师傅只好装作没听见,衣服却是穿得愈发严实。
其中有个中学的化学老师,严重肩周炎,从师傅还和男人在漓江路开店的时候就找她按摩,每次并不多话。等到师傅自己在骖鸾街开店的时候,他还是隔一阵子就来,嘴却慢慢变碎了。一天喝醉酒来按摩,师傅正准备给他开肩,他猛然把裤子褪了下去,说:“美娇,好想抱着你睡一觉饱的。”
师傅退后一步,义正辞严:“周老师,你今天喝得有点多了哦,从来还没见过你喝成这个样子。”说完她推开玻璃门跑到大街上。
过了几分钟,他听到那位周老师拉开玻璃门,走了,走时裤腰带上那串钥匙贴着他的屁股咣咣响。
“我给他按摩少说也有十五年了吧!每次进来都说你好,离开不忘说谢谢,看起来蛮文雅的一个人,为什么也是这样的呀?你说。”
“喝醉了自己把不住自己那根蔸把了呗。”我宽慰师傅。
“老话都讲了,酒醉心明白。他就是醉得瘫成一团,你看他敢去他们校长面前脱裤子没?不可能噻。”
“你没想到要报警吗?”我问。
“报什么警哦,报了警警察要找你去录音,可能光录音就要花掉几个钟。你也没出个血也没断个手,警察恁子帮你主张正义。再讲咯,好多警察都是男的,拿个摄像头对着你喊你讲了一轮,又讲一轮,你说是不是比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还磨人?”
“也是哈,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大夏天走在菜市猛然被一个男人抓了一把胸,结果脑子蒙了,眼睁睁看他走进人群,甚至都没来得及大喊一声,人就不见了。”我说。
“就是说嘛,那个周老师倒一点事没得的样子,还是隔段时间又来找我按摩,还是进门说你好,离开说谢谢。我嘴上肯定不会再提这个事,但心里没办法当它从来没发生过噻。”
我灵光一闪,说:“要不你网购几个摄像头装上,从进门就开始,无死角全监控,把他们露出来的汗毛都给收摄进去,看他们有哪个还敢露出自己的小蔸把。”
她笑起来,说:“你倒是蛮鬼精哦!我是想,反正女也工作了,房子小是小了点,不过女回来我们各人都有个自己的房间也可以了。钱嘛,少赚了就少花点,反正不愁吃喝。我就只做女客,安静又干净。有时间就上网听音频耍,还是值得。”
3
“我生完女出来脑子全部断片。前面痛了十几个钟头,生的时候我女头大了点,医生一刀侧切,然后一针一针地缝,和补衣服一个样,还是无麻的。结果一出产房,我家婆就和我讲,第一个生了个女,过几年生个崽,就凑成一个好字了。我那时懵里懵懂,也是想肯定要再生个崽嘛。现在想想,好笑得很。”师傅边往按摩床的窟窿垫毛巾边和我说话。
“你去听那个日本的上野千鹤子的《厌女》嘛,很多女的也厌女,自己都晓不得。”我说。
“好的嘛,只是不晓得我读得进去没。不过按你讲的,读什么都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读,应该也可以读读看。我跟你说,以前看电视,里面的男女猛然生大病,我会觉得是瞎编的。到自己身上才晓得,真的是无常。”师傅绕过床头,说。
“可不是,想想五年前我查出乳腺癌,一瞬间,我就懂了。”我说。
“不是有一句话喊置之死地而后生吗?”师傅的力道从手掌传到我的肩胛骨,又传到我的手臂,我感觉小指和食指都麻了。
如果师傅没有经历那场病,她应该还在漓江路那家按摩店里忙得飞起。尽管现在外国游客少见,但凭她和男人的技术,光赚人民币收入应该也还不错。我想象她身姿曼妙地在店里飘来飘去,手上力道老辣,脸上笑意盈盈,钱一张张地被关进五斗柜里的抽屉,一盒子的红人头,偶尔间杂几张绿色的美钞。顾客点了男人的单,她就坐在帘子后的沙发上吃艾叶粑粑、嗑瓜子、喝豆奶,吃完对着镜子咧嘴补口红。
她应该生了第二个孩子,她相信会是一个儿子。算起来,儿子该上初中了。女儿上大学不用管了给生活费就行,她每天除了按摩就是想着儿子的陪护和教育,忙得不可开交,却有着随大流的充实和幸福。
她应该跟着流行,带儿子去上各种班,钢琴、围棋、跆拳道,梦想着儿子跨越阶层的未来,梦想着儿子高光时刻自己的与有荣焉。梦想自己年纪大了不再干了,住进物业管理配套令人咋舌的高档社区,人车分流、豪华电梯间,连厨房都装上空调,跟左邻右舍打麻将,跟广场舞姐妹报团新马泰游,去老年大学唱歌。
男人爱看手撕鬼子的电视剧就让他在家看个够,她才懒得管。
按摩完,师傅说我湿气有点重,要给我拔罐。我就背上扣着几个玻璃罩听她继续讲。
穿山桥头漓江边建筑公司前的小公园广场,晚上经常有人跳舞。
那天上午,师傅去接上完培训班的女儿。那时她的视力还在慢慢恢复,她看得模糊,但舞曲从大喇叭传遍大街,她想到应该有人在跳舞。大白天的竟然有人在跳舞,不过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呢?接了女儿她还要赶回店里开张,有客人早早预约了她的按摩。
等接了女儿往回走的时候,再次路过,女儿停下来,身子明显往高音喇叭的方向扭,她让女儿快点走,女儿却说:“等我再看一下子嘛。”
过一会儿,师傅摸女儿的手板心,问:“你恁子出那么多汗?”她女儿不做声。
一阵凉风吹来,师傅再次拉紧女儿的手,说:“走了嘛,等下要下大雨了。”
漓江路上北风猎猎,行人都在加快脚步。女儿挽起师傅的胳膊,师傅感觉到她女儿一身冷汗。她问:“你是不是感冒了?等下到铺子我给你熬碗姜糖水喝。”女儿低声说:“不是,不要。”
师傅就拉着女儿的手急急地往回走,终于到店里了。她掏出钥匙开门时,女儿把手拢到她耳边,说:“刚才在那个公园,我看到我爸搂着一个阿姨在跳舞。”
师傅的脑子“嗡”一下,眼前模糊的景象似乎刹那变得清晰。
接着,哗哗哗,瓢泼大雨真的就来了。
4
师傅半夜收摊,出门踩到一块晓不得哪个短命鬼丢的西瓜皮,脚下打滑,脑壳碰在台阶坎子上,出了一脑门血。她用左手压住脑壳,右手摸钥匙打开铺子的卷闸门,拉开五斗柜的抽屉摸到几个创可贴,可伤口太大了,创可贴压不住。她就又到柜子里找给客人垫枕头用的毛巾,把毛巾叠好压着额头,用一根绳子绑住,仰着躺在按摩床上,等着血慢慢凝固。
她在按摩床上躺了一夜。
没睡着的时候,过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像一团飞蛾,在眼前盘旋不停,闪着幽光。
男人原来在供销社上班,两人领了结婚证没多久,正好赶上供销社改制,他选择领了一笔遣散费,成了自由职业者。按男人的说法,反正他一定要生两个崽女,不离职也会挨开除,还不如提前接受遣散拿一笔钱。
离职后他们试过各种挣钱的招,最后男人的一个远房亲戚带着他到杭州学了半年的按摩,学成后,男人带着师傅先是在县城开过一段时间的按摩店,后来听说桂林生意好做,才来到桂林。刚来时先在别人的店里帮手,差不多两年才找到机会接手了漓江路的按摩店。夫妻搭档,有几年外国游客多,确实很好赚。
这之前男人筹划过贩卖乳猪挣钱。那年夏天,他开摩托搭着师傅去乡下,走了很多村子,都没有谈成一单生意。傍晚六点多回城,天已经暗了,路过茶江,索性停下来看一阵江流,看桥上钓鱼的男人,看对门的青山。那个傍晚,男人抓着师傅的手,对着夕阳中烫金的茶江喊:“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乳猪生意没做成,男人又想着收废品,他畅想资金充足的时候开一个废品回收站,由他开着车到处跑,师傅就在茶江码头对面的铺子里拨算盘珠子,一分分、一角角、一块块地攒,好日子总能攒得来。等钱攒够了,就在茶江边买块地建一栋房子,再生一子一女,日子不要过得太舒服。
“那时我心里是很感激他的,因为是他帮我买了个城市户口。”
“农民真的是最辛苦的职业!我就是小时候日头大下火的天去挖红薯、栽秧,晒得背后像烤鸡一样,脱了一层皮,才下定决心一定要跳出农门的。”我插话。
“真羡慕你能考出来,还当了大学老师。我没这个命,也只能认。不过我也常在想,到底是什么事情推着我,使得我单身一人,脑壳上压着一块毛巾,躺在一张按摩床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师傅好像在问我,其实她有自己的答案。
男人时常要喝点小酒,偶尔叫上几个弟兄。
给客人按摩的男人,散出去一身气力,倒绷紧了自己的身体,喝几杯小酒让自己松弛下来,师傅原本很支持,觉得和自己躲在纱帘后面嗑瓜子喝豆奶是一个道理。
葱爆牛肉、红烧鸡块、炸花生、炒上海青,再加一锅排骨海带汤。男人去买的菜,师傅有点不舒服,却还是在厨房里把菜烧好了。男人的面子,一定要给足,特别有外人在的时候,妈妈从小这么教她。
给每个人倒上酒,男人客气道,没什么好菜,大家多喝酒。
师傅不喝酒,盛了一碗饭,想坐在桌角,男人却说桌子有点小,让她用勺子舀一点菜到厨房去吃。
师傅摸索着用勺子去舀菜,结果袖子一带,男人的酒杯给弄倒了。
男人猛然站起来一推师傅,大声叱骂:“你还没全瞎呀!”
师傅愣了一小会儿,什么都没说,端着一碗白米饭退回到厨房去。
5
梅雨季节一来,这痛那不通的人总是很多。师傅和男人在漓江路的小店生意火得很。
师傅说,其实她的头已经痛了蛮长时间,因为生意太好,开始就在药店买了些止痛片吃,后来实在痛得头筋都要爆炸了,而且还想吐,才到附近的第五人民医院挂了号。医生诊断为偏头痛,说应该是太疲劳引起血管扩张产生压迫导致的,还说偏头痛在中青年女性中很常见。
师傅也就放心地拿着药回家了,每天还是顶着头疼忙忙碌碌。
“如果没有生那场病,说不定我还认不得你,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有那么多空闲听得到《心经》。”师傅边给我放松颈椎边说道。
她说,感觉像一场梦,又好像自己成了某部韩剧里的女主角。
她患的是泌乳素瘤,一种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病。
当时桂林最好的医院都治不了她的病,她只能转到广州,先后做了两次微创手术,把脑袋里的瘤子捣碎了,从鼻子里吸出来。
其实是一种良性的肿瘤,只是因为拖太久肿瘤长得太大压迫了视交叉神经,导致她的视力持续下降,最终只能模糊地看到眼前的大型物体。
医生建议她多住一段时间院,用最先进的疗法尽量恢复视力。她断断续续地住院,不住院的时候就在医院外面的小旅馆凑合。
“在医院就是嗖嗖地花钱,男人一个人在店里忙不过来,还要管女。妈妈丢工来照顾我,又无时不惦记着恭城的那个家。妹妹到杭州打工就远嫁在那边,弟弟在北方读大学,家里就剩爸爸和奶奶。爷爷死了,奶奶老了。农活就爸爸一个人做,鸡鸭不喂,就会瘦;芋头不挖,就卖不到钱;红薯藤不割,猪就没得吃的。”
她觉得自己成了所有人的负担,想过自行了断。
“可是终究还是害怕。”
她让妈妈给自己买一副墨镜,似乎戴上了墨镜,那些悲伤和恐惧就都可以遮盖住了。
可是戴了不到一个钟头她又把墨镜丢到了垃圾桶,好像墨镜成了她病魔的罪魁祸首。
她开始在病房里练习摸着走,还去参加医院举办的公益盲文培训班。
男人带女儿去广州看过她一次。在医院里,女儿懂事地抠着她的手心什么都没问。男人则一手撑着她的腿弯,一手抬起她的下巴,仔细端详她的脸。看着看着,他忽然哈哈大笑,说:“我们的店可以正大光明地挂盲人按摩店的牌子了呀!”
从广州回到家不到一个月,她就开始上钟,毕竟这场病几乎花光了他们十几年的积蓄。
神奇的是她的客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前,来他们店的客人很多都是奔着男人的名声来的,现在他们喜欢找她按。
“可能真的有一个老天爷吧,是它指引着我慢慢学会靠自己。”师傅说。
“是因为你视力受损,触觉和听觉等其他的感觉就慢慢变得灵敏了吧?书上说人的潜能大得很,大多数人都还没发挥到百分之十。”我说。
“可能是吧!前段时间我女回来,拉着我去雁山的植物园逛了逛。山上开满了杜鹃花,黄的粉的白的红的,我眼睛不好看得模糊,可是听到了各种声音,闻到了各种味道,倒有一种比以前离春天更近的感觉呢。”说这些话时,师傅眼底烟波淼淼。
6
“你信不信命?”在给我从背上把罐子取下来的间隙,师傅又开始了她的自问自答。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年轻的李美娇在恭城县城一栋居民楼里哄小孩。她身上挂一件松松垮垮的绿毛衫,正拿脚去勾桌子底下的塑料球。楼道尽头有人炒菜,正在用葱花炝锅,油烧得旺,葱花猛一下锅,咝咝作响。窗外不远处就是石山,秋高气爽,山风习习,楼道里的油气一下子就散开了。房间门口,一个男人正在敲门,是李美娇主家的弟弟。
李美娇当住家保姆,说好了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和教育都归她管。因为从小带妹妹和弟弟,李美娇看孩子相当有经验。她在一张旧日历上写满了:早上、中午、晚上吃什么,上午、下午、晚上学什么玩什么,几点上床睡觉。小女娃的作息被她安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她感觉得出来,主家对她很满意,所以当主家提前给她结了一个月的工资让她回家,她感到突然。
她提着手提袋,若有所失,沿茶江边走。她走过万豪来歌舞厅,走过良缘茶楼,走过菜市场,走过几个按摩店、中药铺、大排档,一直到茶江拐弯了,她才向反方向拐弯,转向迎宾路。
县城往北,栗木镇五福村,这是她应该要归的家。这个时辰,家里应该只有弟弟妹妹在。弟弟妹妹可能在写作业,也可能在看电视。当然,妹妹也可能被爸爸吩咐去割猪草了。至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肯定不是在山上就是在田里。他们弓着背、弯着腰,日日辛苦劳作,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孙子和儿子身上。
李美娇是不想回去的。
“你要说我爸我妈对我不好?倒不至于。你要说他们对我很好?也不是。可能就是网上说的中等程度的重男轻女吧。”
李美娇初中毕业没考上中专,她想去复读一年。结果爸爸对她说:“你要是能考上我就肯定不得不供你,现在你没考上就不要复读了,女娃子家家的,最后都是嫁人生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我想象,年轻的李美娇,面颊红润,长发飘飘,在稻田里挽起裤脚除稗草。一年四季,挖地、栽秧、种菜、挖红薯、喂猪,乡下的农活总是没完没了,即使冬月,也还得日日不停地挖马蹄削马蹄。
“养你那么大,嫁出去之前帮家里多做一些,不都是应该的。”妈妈也这样说。
一个亲戚的亲戚要找一个住家保姆,拐了好几个弯,晓不得哪个推荐了李美娇。爸爸同意她去县城当保姆,但要求她每个月把工资往家里拿,说是弟弟以后上大学、讨老婆,用钱的地方多得很。
坐在一张金属靠背椅上,李美娇心底迷茫,看候车室人来人往。隔一阵子又有乘务员进来喊,去观音乡的走了啵,去西岭乡的走了啵,去栗木镇的走了啵。
一个乘务员看李美娇坐好久不动,走过来问:“这个女娃子,你到底是要去哪个乡嘛?”
李美娇不想回家,她不想回去干农活,不想把好不容易养白的皮肤晒黑。可除了当保姆的那一家子,县城里她一个人也不认得。她也想过干脆搭车到广东去打工,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她在电视上看到过连女大学生都被拐卖。
正犹豫不决,门口进来一个人,焦急万分,东张西望。李美娇觉得眼熟,抬起头多看了几眼。
是主家的弟弟。
男人问:“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吗?”李美娇答非所问,说:“唉,肚子有点饿了。”
蒸笼上套着蒸笼,总共是四层,每个蒸笼里六个小笼包。碟子里舀点辣椒酱、倒点酱油,再滴点醋。男人听说李美娇不爱吃面食,又去隔壁买来一碗米粉。两人不说话,闷头吃。李美娇三下五除二把米粉吃完了,百无聊赖,在矮板凳上叠纸壳耍。
7
“他们说属鸡的是落地的凤凰,天生喜欢打扮。我是属猪的,为什么也喜欢打扮?你说。”我的师傅——李美娇,边给我放松手指边问。
“因为你长得美,长得美的人就总想美上加美。贪嗔痴慢疑,贪字排第一。”我和师傅开玩笑。
“如果我的皮囊生得没那么好看,我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命了。”师傅平静地说,“不过也不一定比现在就好。一个人还真是落地八分命。要改命,真的好难呐。”
她记得很清楚,男人为了让她上户口,还给公家交了两千块钱。爸妈本来不同意这门亲事,男人给了她爸妈三千块钱,他们才松口,拿出了一直藏着的户口本。
男人离婚李美娇没参与。“结婚几年都没有生养,房子也给她了,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男人说。
“年轻的时候以为这就是爱,还认为自己漂亮有吸引力,根本没想到自己对另一个女人的伤害。造孽呀!”师傅在网上听了佛学课,言语间经常蹦出一些相关的词。
赶上圩日,李美娇就到他们县城的街上逛。她最喜欢逛的是化妆品店和服装店,一般逛到十一点钟这样才去往菜市场,买菜,回出租屋,给男人做饭。
茶江水流平缓,江上有人撒网,金色的阳光似乎被他们一起拢到网里收了起来。几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子在江边闲坐,李美娇想,老奶奶们可都在家干家务带孙子孙女呢。
出门前,李美娇好生装扮了自己。眉毛、眼影、眼线、口红,扎得整齐利索的长辫子,烫得没有一丝皱褶的衣裤,样样都要妥帖舒展。
手上拎着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野生菌、鸡肉和水果,袋子晃来晃去,一个青春美少女蹦蹦跳跳地在表演自己的人生。
那年秋天,她才和男人同居的时候,还没满十八岁,男人一直没和她同床,却供着她吃喝供着她穿,自己很辛苦地去赚钱。
“十八岁生日那天晚上,我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他。至今我还记得他看着床单上的血,和我说一生一世都要对我好的样子。”
她说手术过后给男人拨电话,电话声嘟嘟嘟,她感觉自己顺着电话线滑到了漓江路的按摩店。她好像看到男人将手机放在桌子上,抽了支烟出来,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再吸一口,才摁了接听键。
男人皮肤黝黑,手部肌肉发达,抬头纹深似海。
他说:“你问问医生,你这个病做完手术一般好久可以恢复来名堂,我们还要生个崽的嘛,了解一下。”
她的表情黯淡下去,说:“医生说我的瘤子太大很有可能不会再来名堂了。”
她告诉我,她是故意这样说的。做手术前医生就和她说了,做完手术要吃一种调节内分泌的药,有的人几个月就会恢复来月经,也有的人就这样绝经了。大多数的人其实是可以恢复的。
“结婚十几年,也和他生了个女了。结果,你做了一个可能要命可能瞎掉的手术,他打电话第一句不是关心你的身体,而是问候你的大姨妈。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嘛。”
和男人通话的时候,师傅歪着身子坐在医院门口小卖部的木凳上。手术前后消耗太大,她瘦了差不多二十斤。尾椎骨顶着硬板凳,生疼。
男人拿出所有的积蓄给她到广州治病,妈妈丢下家里的农活去照顾她。
在小旅馆里,她给妈妈染头发。
染完发,她远远看着妈妈左顾右盼地照镜子。结实丰满的背影,一头栗色的长发,妈妈一下子变得年轻时髦了。
她在妈妈的背影里看到了自己。她看到了,自己正在走着妈妈的老路。
“难道就没有另外的一条路可以走吗?”那一刹那,我的师傅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
做完治疗从广州回到家那十几天,她不太出门。两次微创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尿崩,医生交代她每次喝水和撒尿都用量杯精确测量,记录数字,他需要根据数字峰值变化调整她的药量,以保证治疗效果。
“我看不清量壶的刻度,男人又不管。我女就让我每次尿在不同的桶里,她放学回来给我量了登记,那时她才读四年级呢。”
她感激老天给她一个这么贴心的女儿。
她慢慢恢复了力气,视力也比才出院强了不少。她摸索着给自己化妆,走到楼下去等女儿放学,去等她的小灯泡、小太阳。
“其实我的大姨妈没过几个月就又来了。只不过那些陷进肉里拔不出来的刺,很多时候不舍得割肉是取不出来的。”
她找了骖鸾街的门面自立门户。男人最终同意离婚,还把剩下不多的积蓄都给了她。
“其实他也称不上有多坏,就是一些执念还没法清除。转头想想,我自己又是什么白莲花?”师傅眼神里带着清澈。
“男人现在过得怎么样?”我忍不住八卦。
“人家毕竟是有手艺的,挣得来钱,现在崽都上小学三年级了,还是应该为他高兴。”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蛮好蛮好。”我真心地说。
“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听喜马拉雅上各种各样的故事,太有意思了。我常由这些故事想起我女,想起我妈,想起曾经的男人和他的第一任前妻,想起我爷我奶我爸我弟,我家婆我大姑姐,想起我的客人,还有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真的是人各有命,每个人的苦都只能自己吞。”说完,师傅叹了一口气,沉默地把盖在我肩膀上的毛巾拿走,示意我,按摩结束了。
在师傅绵密的话语和轻轻的叹息里,我看到了无数个她,也看到了无数个自己。我看到了无数的女人,也看到了无数的男人。我看到了,正午阳光下,经历了无数潮湿春天的鸟雀,正飞往炽热的盛夏。
我和师傅已经认识一年多了,可我甚至都还没有和她握过手呢。我们应该互相拥抱才对。此刻,我是多么真切地想要紧紧拥抱我的师傅呀!
于是我起身,站立,张开臂膀。
我凝视着师傅略显灰暗的眼睛,等待她心有灵犀的回应。
这是多么难得的庄严时刻!让我们把大街上的喧嚣隔绝,平静地待在屋子里,和另一个自己紧紧拥抱在一起,同时拥抱那些我们还无缘相遇的陌生人。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值得被疼惜的阔大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