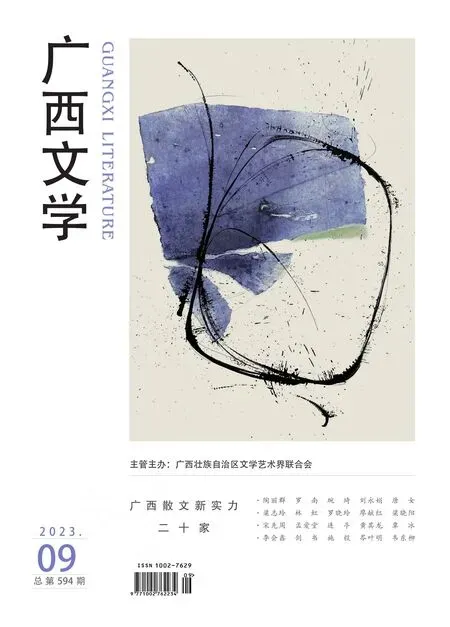散文的回溯与沉浸
——《广西散文新实力二十家》专号述评
2023-10-22刘军
刘 军
2015年,笔者曾给《广西文学》散文新锐专号写过一篇述评。八年过去了,重读这一年度的散文专号,虽然所阅读的作品是崭新的,但重逢的感觉依然在内心荡起。文学写作,在本体意义上,其实质就是一种重逢,重返记忆现场,重访童年往事,在人自身这一容器里,洞见加减的内容,进而触摸到存在的实体。阅读的重逢则在浅层次上发生,比如熟悉的作家对象,比如个人生活史中更换的生活场景以及所停靠的不同的岛屿。当然,重逢并不意味着曼妙的产生,也不意味着走出荆棘丛生的山地丘陵进入到开阔疏朗的地方,重逢的意义在于,在彼此的认识之外,进入到更宽的认识状态之中。写作是如此,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需要承认的是,散文作为经验文体,在文体跃升上存在着自身的限制。就经验的表达来说,情感的凝结和释放并不具备连续性,回望与解剖的过程,尽管距离痛苦的原点越近,情感的传达与文字的抒发就愈发酣畅淋漓,而这种抒发其实也是一次结痂的历程。一旦结痂过后,重新揭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总的来说,散文写作对于多数作者来说,皆面临着经验耗散的问题,只有那些超越经验写作进入思想力范畴的个别散文作家,方能够不为题材、情感所限,进入洞察和穿透的层面,创作水准始终在高位运行。客观而言,本次散文专号的一些作者,比如罗南、剑书等人,都曾写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尤其是罗南的《药这种东西》,分量很重,有资格进入最近十年散文佳作的方阵。另有唐女的“重返故乡”主题之作,其中的女性意识和性别自觉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堪为近些年来典范的女性散文作品。剑书的小镇叙事在80后散文作家群体中亦是独树一帜。
本期散文专号集结了广西中青年散文家二十人的作品,比之上一次专号,呈现出两个变化。一方面,在题材和写法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除了常见的乡土经验和童年经验的叠加,城市生活和都市生活的片段也被捕捉并加以内化。另外,更加内省式的作品也出现了,罗南的《下一个路口》就是她摆脱叙事倚重的新尝试。同时一些作品也冲破了熟人社会的关系限制,在自我与陌生人的关系上,在人与宠物关系上开拓出新的疆域。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恪守基本现实主义风貌的境况下,现实关怀也呈现出多边深入的倾向。关于城市生活的亚健康与精神世界的联系问题,关于抑郁症带给家庭的创伤,关于陌生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及共情问题,还有生态反思以及代际间的理解,这些直击当下生活现场的话题皆得到这批作家的真诚回应。另外,作者的代际构成指向70后、80后、90后三大群体。最年轻的一位作者还处于硕士在读的状态,而在这位最年轻的作者笔下,我们会看到熟悉的乡土经验和苦难表达,足证乡土记忆和经验内容的后延是多么强劲,也能够说明,苦难书写在小说散文中如此地同频,且其拉伸出的时间长度几乎涵盖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批评家洪治纲曾就小说中的苦难书写的密集有过反思和批判。而就散文文体来说,苦难表达集中于乡土散文和家族叙事两大题材之中,苦难是历史的产物且普遍根植,个体记忆一旦回溯,很容易迎面撞上。苦难之于散文而言,只要没有走向迷恋,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的问题了。除了刚提及的韦东柳的这一篇,这期专号里的多篇散文皆触及苦难底色的问题,物质贫困带来的生存压力,精神愚钝带来的幽深洞口,这些都是历史与时代交织出来的产物。尽管在具体作者笔下,苦难打开的方式不同,流向也有差异,但苦难作为历史的底片被揭露出来,也从侧面说明,散文的记录功能使得它超越了个体回忆的层面,以个别反映一般,进而确立普遍性的内容。就像《巨流河》一样,既是个人史的起伏,也是家国史的沉痛述说。
除了苦难底色这一共性因素之外,在散文的容量上,本期散文专号可谓长散文的集成。在这里有必要谈谈长散文盛行的问题,长散文和散文的长度不是一回事,长散文涉及二十年来散文的不断扩容问题。周晓枫的《野猫记》《男左女右》,夏立君的李白篇,张锐锋的《飞箭》等作品,基本都是五万字的规模,张承志、詹谷丰、傅菲的近作单篇大多在两万字以上,至于万字散文,随意翻开一本省级文学刊物,皆能寻见。长散文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散文的长度则涉及篇幅的设定,它是一个文体问题,往往与散文之短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不容回避的是,长散文的泛滥是当下散文现场的高度不同且高度突出的一个问题。何以长散文频出?根本原因在于期刊以及散文奖项的主观引流,文学刊物的散文版面,在字数要求上大体同频,通俗地讲就是五千字及以上。而散文奖项的考虑在于,字数的增加有益于分量的加重。文学期刊对于散文何以开出字数要求的条件?在笔者看来,因素有三,其一是抒情散文和游记的遗祸,抒情散文和游记易于模仿和上手,其庞大的数量对于编辑审阅构成了巨大压力;其二是近些年散文的叙事转向,叙事的加重以及多线头的处理急速扩容了散文的容量,如果说情感是个体经验的凝结的话,那么故事则是作者人生体悟的综合,在这种综合里,散文作者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如此可以纵横捭阖;其三的考虑是精简数量增加分量,容量并非必然可以带来分量,但容量无疑是构成分量的某种前提条件。长散文风行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根据笔者的个人观察,它首先是提高了散文的准入门槛,自然淘汰那些观念陈旧写法老套文字驾驭能力普通的作者;其次引发了散文写作普遍注水肥大而不结实的后果,无效的场景书写,历史材料的随意剪裁,个人记忆的任意穿插,这些损害散文的节制之美的情况频频发生;最后,一篇非常出色的长散文足以和好的组诗以及优秀的短篇小说抗衡,进而提升散文文体的地位和影响。总体来讲,有益处也有坏处,而对于处于上升期的作者来说,他们承担坏处的风险是颇高的,这恰恰是应该自省和自查的地方。莱辛说过:“最明晰的对我来说始终就是最美的。”福楼拜在教导写作之际,也曾对小莫泊桑说过:“无论你所要讲的是什么,真正能够表现它的句子只有一句,真正适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只有一个,就是那最准确的一句、最准确的一个动词和形容词。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福楼拜所强调的真实和朴素,对于散文则更加重要。
这些年的批评现场,“地方性”是一个热点话题,尽管这一话题更多地结合小说加以展开,但在笔者的认知里,散文的“地方性”呈现比之小说更加清晰,站位也更高。在愈发同质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学因为始终捍卫其个人性、差异性、异质性的立场,在滔滔若是的时代车轮中,也许会被甩落,然而不会被取消。生活在别处,存在可能性的探究,如磁石般贴近人们的灵魂深处,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独属于他的风景,而文学艺术恰恰能够实现供给。米沃什宣称他终生钟情于他的“小地方”,“地方性”当然不能等同于“小地方”,它是故乡故居、民情风俗、山川风貌、饮食水土、个人记忆、文字滤镜之后搭建的美学形式等因素的综合。它的物质基础与文学地域特征重叠,但它还拥有由此蒸腾出来的美学气息,这种美学气息具备格式塔美学中的整体感。如果散文作家拥有足够的观照能力、文字能力以及形式转化能力,那么,他在整体感的建构上大概率会超越小说家,其作品的虚指功能也会轻易地被读者辨别。美国作家格林说过:“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在空间与地方加速分离的当下,散文恰恰可以重新缝合空间与地方,让它们凑拢和贴近,如此搭建一个不独属于个体也属于众人的记忆共同体。广西作为西南边陲,作为拥有不同山系和河系的地方,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天然地存留了诸多“地方性”的物质基础。本期散文专号中的一些作品,触及了“地方性”的局部,如剑书笔下红水河与人的生活的交互。但在整体的营造上发力不够,而作为整体感的“地方性”,或许应该是广西散文作者以后要着重开掘的区域。
二十人的作品中,黄其龙的《人潮漫卷》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是一篇凸显共情照进现实主题的散文作品,作者的共情能力、觉察与理解他者的能力,借助三次出车经历呈现出来。从题目来看,所谓“人潮漫卷”,实则象征着每个人在人群中的位置,尤其是在陌生人群中,镜像功能愈发突出,一切的交互其实都是在照见自我。远方的陌生他者何以与我们息息相关?非洲草原生活的象群,一只失独的小象会得到其他成年雌性大象的照顾。只要是具备群居特征的动物,相互的陪伴和照顾则为常态。群居是人这一生物种群的基本属性,根据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人又是宇宙智慧生命中唯一可知的拥有自我折返意识的生命,这里的自我折返意识指的是人作为主体知道自我具有反省、反思的意识。经过文化和文明的熏陶,人的同类相怜和相爱意识会不断提升,而这恰是人性中非常高贵和纯粹的内容。因此,难得的是作者超越了常见的道德意识和戒备心理,能够将心比心,将悲欢加以打通。不过,作品的三个小节各有侧重。第一小节与“我”交互的是两个返乡的打工妹,在小小的车内之所以能够形成释放瞬间,概源于自我道德意识的去除,也就是有色眼镜的摘下,所以,这样的时刻,快乐可以迅速传染。第二小节则是“我”与一个家庭的交互,母亲的小心翼翼和装扮出来的热情,使得负重的人生如同后视镜中的内容。第三小节则是“我”与一个身染恶疾的女性的交集,她的自我放逐与飘零状态,如同河流上的枯叶,只需短暂的一眼,就会下卷到视线之外。而这短暂的一眼里,隐藏着世界的深渊和人生的无常。所以,对于散文来说,至深的体悟不一定非要借助自我的经历方能见出,他者同样承载了命运或人生的深刻,关键在于你能否“看见”而已。刘永娟的《怜悯》篇,彰显出上佳的艺术处理能力,同样关注的是他者,作者叙述的不是片刻的交集,而是追踪式的了解。这篇作品里出现了许多对话的段落,对于对话的把握,余华认为其是小说写作第二难的关口。那么,在叙事性散文中,对话的处理难度可想而知。除了对话之外,闪回、穿插、时间重组这些叙事技巧,也被作者运用起来,并较为自如,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违和感。从叙事内容上看,作为以人物为主题的散文作品,一位从事按摩工作的中年女性,经历过少女时代的私奔、感情的失和、目盲的困扰,也有过与女儿相依为命的甜蜜时刻,而关键的地方在于,源于工作种类和两性在私密空间的相处,那些赤裸裸的言语和行为挑逗,构成怎样的细沙在心间萦回?作者的笔触伸向女性、弱势、隐秘的骚扰这些角落,思考的是女性的自省、自觉、自主、自立的严肃内容。
陶丽群的《疾病》、唐女的《万物安生》、梁志玲的《目之所及》,这三篇作品可以放在一起谈。她们皆和生老病死中“病”主题相关联。《疾病》一章触及的是都市生活中的亚健康问题,个人的病灶在肉体感官层面可能并不显著,但在精神层面上,疾患却深入骨髓,重要的不仅仅是日常物品的清空,而是内心杂多的欲望、念头的清空。离开乡土这种半自然的环境,进入城市后,个体与自然的交换关系被斩断,这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精神疾患的问题。北美的自然主义文学有着两大主题,一个是治愈,如特丽的《心灵的慰藉》,另一个则是意义重建,如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自然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可以治愈彼此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充实我们的精神。《万物安生》由宠物狗的短暂失踪引出女儿的抑郁症问题,作为母亲,这种遭遇会让人错愕,让人深感无力和无助。如今,庞大的抑郁症群体和由此生发出的社会问题,逼迫着人们正视它的存在。《目之所及》则是疾病的延伸形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宠物正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的病痛让与之亲近的人感同身受。接受它们的病灶以及离去,恰是新城市生活经验的内容。而被激发起来的人的内心的柔软,促发了米兰·昆德拉式的命题的普遍发生:这是一个流行离去的世界,但我们却不擅长告别!
施毅的《越过取景框》在主题把握和精神特质上与黄其龙的作品非常接近。以偶然的瞥见铺垫通过生活深处的道路,人的神色和行为动作不过是取景框的表象景观,其后面还内隐着不同个体与生活搏击的惊心内容。这一作品在专注度和开掘深度上稍微有一些欠缺,但这一写作路数值得肯定。符合罗曼·罗兰笔下英雄主义的理念设定。如前所述,梁晓阳的《布爹布奶》、宋先周的《追逐,向暗处》、连亭的《我的农民工父亲》、韦东柳的《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覃冰的《鞋》,这五篇作品有着共同的苦难底色。而且这五篇作品皆集中在父母辈生活的勾勒上,通过童年经验的重拾,苦难作为父母辈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其声音穿过时间的重重迷障,在不同的作家笔下被激活。《布爹布奶》涉及家族内部的裂隙,裂开的口子冷冷如刀锋。《追逐,向暗处》触及人与动物的争夺战,那是贫困时代里才有的疯狂和血腥。《鞋》虽然有着乐观明亮的结尾,但关于母亲的选择里,那些隐忍、自我牺牲的内容,依然可以被充分地捕捉。这篇散文还存在着为亲人讳的内容,留下了少许的遗憾。《我的农民工父亲》虽然是传统叙事的框架结构,但因为作者出色的笔力和结构能力,在感染力上,应该说居同类作品之首。
罗南的《下一个路口》放弃了叙事的锋利,是作者向内转的一种尝试。这篇作品将经验的内容加以压缩,作为背景色嵌入作品之中,这里有独身中年女性的欲说还休,有自我对于周遭世界的怀疑主义,有对不确定性的直面内省。琬琦的作品书写了身边易被人们忽视的卑微的生灵。对于它们来说,童年期的孩子就是天敌,似乎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曾使用过残忍的手段对付它们,那些死掉很久的小小的生灵,其存在意义或许在于提供忏悔的机遇,让理解生命、走向中年的我们,通过重审,通过自我的忏悔,以达成与往事的和解。因此,这一篇内蕴的散文生态意蕴也是较为突出的。林虹笔下的两则在主题开掘上匹配不够,第一则《像雪花覆盖着》以建筑工人这些城市的边缘群体为主体,将自我的世界加以远推,如同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边缘处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也隐藏着锋利和真实。罗晓玲的《密林,或另一种索引》,题目起得非常漂亮。这篇作品看上去是写疾病的,实则是写“未病”的,也就是源于疾病的个人想象所实际产生的心理波动,在这种波折里,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其拖曳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折转。人们一直盛赞想象力,在科学中,在文学艺术范畴内,而丰富的想象力对于个体而言,也有损伤的一面。廖献红《大田面的鸟儿们》直面偏远地区的村落,在急速变动的历史时期内,其踉跄的脚步,它的坚守和它的新变。马克思曾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理性认识和感性切入有细微的差别,在文学系统里,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栖息的具体形状。孟爱堂的两则作品中,《等风来》意味深长,满爷的形象立体而丰满,他对女性的爱怜和保护,乃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朴素美德。李会鑫的《修罗场的黄昏》触及爷奶辈对待疾病的态度,他们简约的生活观,他们豁达的生死观,可能在观念汲取上仅仅是来自一个小小的地方,然而又非常中国。岑叶明的《一个人热闹》较为特别,在这篇解剖自我的作品中,源于特殊的家庭氛围以及求学过程中被孤立备受挫折的过往,作品讲述了“我”是如何转身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借助虚构,补全世界的残缺。同时,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也使得“我”与文学写作结成亲缘关系。因此,这篇散文更像是一个青年作家的自画像。
当你无处可去的时候,当他们被暮霭吞没之际,当世界冷冷地转身,当生活的激流剥离岸边的土石之际,当时间暂缓,黑暗沿着四肢攀爬的时候,这样的时刻,恰是散文之心苏醒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