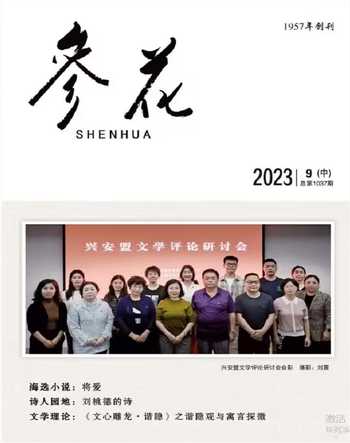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本色”论
2023-10-17吴秋璇
“本色”论如今被广泛认同为我国戏剧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理论概念,是对戏剧语言方面的要求,认为戏剧语言应通俗易懂。但纵观我国古代文学史,“本色”理论的起源甚至早于我国戏曲的起源,并且在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各个领域被广泛使用。在被作为文论使用时,本色也在其“原本的颜色”这一本意基础上生发出一系列含义。明朝之后,随着我国戏剧文学的发展成熟,本色论才被主要运用于戏剧理论批评之中,此后更是几乎成为戏剧领域的专用理论。
一、明朝以前,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本色”概念
起初,“本色”这一概念与文学批评并没有任何关系。“本色”最早记载于《晋书·天文志》:“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顺时应节。色变有类,凡青皆比参左肩,赤比心大星,黄比参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应其四时者,吉;色害其行,凶。”[1]在这里,“本色”指本来的颜色,与文学批评并无关系。
最早在文学批评领域使用“本色”一词的是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刘勰在他的文學批评著作《文心雕龙》的“通变”一节中提到:“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2]又在“诠赋”一节中提到:“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虽然提到了“本色”,但他并没有将“本色”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使用。而是保留了“本色”一词的本意:“原本的颜色”,将其作为喻体,以染色作比,对当时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略汉宗宋,重视相近时代的作品而忽视古文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提出创作者如果要纠正文章的不切实际和浅薄,就需要回到对古文经书的学习之中,就好像要提炼出蓝色和红色,需要蓝草和红草一样。而在《文心雕龙·诠赋》一节中,刘勰将“本色”拆分为“本”与“色”两个部分,指出撰写文章就像染布和绘画一样,染布和绘画时使用的颜色虽然混合在了一起,但是也有底色,而创作文章时虽可以使用各种巧妙华丽的词汇,但文章仍须有明确的主旨,有其根本。刘勰虽然没有为本色增加新的释义,但是他的比喻为之后“本色”理论的演变规定了基本的方向。
进入唐代后,“本色”的释义有所增加,可依据使用方式分为两类,但依旧没有被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使用。“本色”的第一类使用方式是将“本”与“色”拆开,作为两个含义不同的单字使用。这种情况下,本色一词便有了原本的颜色、原本的行业(色在唐代不仅有颜色,还有“角色、种类”之义)等意思。此义在崔令钦的《教坊记》中有所记载。第二类使用方式则是将本色视为一个词语,有“当行、内行”和“原本的功能”之义。“当行、内行”一义出自南卓的《羯鼓录》:“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动摇。”[3]此句意指汝南王十分擅长羯鼓演奏,连内行的技巧都能掌握。而“原本的功能”一义则在《唐大诏令集》等典籍中有所记载。
宋代时,各种文体逐渐完备,文学创作也极受欢迎,文学批评领域也迅速发展成熟。“本色”在宋代正式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并占有一定地位。评论文学作品需要一定的标准,而文学作品是否符合其文体的“本色”便是重要标准之一。作为文学批评概念,“本色”在宋朝时主要被用在诗词和作品语言评论方面,并且没有一个统一的释义。在曾将“本色”用在诗词批评领域的文论家中,比较著名的有陈师道、严羽和刘克庄。陈师道在他的诗论著作《后山诗话》中使用过“本色”概念:“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4]陈师道认同黄庭坚“诗文各有体”的观点。认为作者在创作时应该遵守各种文体固有的创作规则,即“本色”。韩愈“以文为诗”和苏轼“以诗为词”虽然也写出了好作品,但是却违背了诗和词原本的规范,受到了他的批评。严羽则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5]认为作诗之道在于妙悟,妙悟便是诗之本色。而刘克庄则提倡诗歌创作须符合“言志”“缘情”的原则,反对以议论作诗。词人张炎则将“本色”运用于词论之中,认为“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6]张炎认为词作要达到“本色”,就需要斟酌字句,不能用过于晦涩生硬的字词。宋朝对“本色”的诠释较为丰富,各种诠释都是基于“原本”一义的引申,对之后戏曲中的本色之论有着较深的影响。
元朝时,元杂剧作为一种全新的体裁出现于文坛,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正式成熟。但文学批评理论并无太大的发展。“本色”在元朝主要被运用于散曲文论。最早,胡紫山在《优伶赵文益诗序》中使用“本色”一词来赞扬民间戏曲演员的演出效果和教坊里的专业演员一样好。季坤山和顾瑛则将张炎的“本色语”引入曲论,亦是强调元曲用语应符合曲体规范。[7]元代文论典籍中提到本色的地方并不多,但有趣的是,后人点评元朝的散曲杂剧时,常以“本色”一词作为其鲜明特征,剧作家中又尤以关汉卿为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赞其“曲尽人情,字字本色”,[8]当代研究成果中也多认为他是元杂剧“本色派”的代表人物。元朝曲论并未对本色进行详细论证,但讲究“炼俗为雅,化雅为俗”[9]的元杂剧被评为了“本色当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后代文论家对“本色”的认知与定义。
综上可知,明朝之前,“本色”词义繁多,用于文学批评领域时多由原意引申,认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应符合文体规范,呈现出体裁应有的风格。在明朝以前,本色也未被用于戏剧批评,故也未形成有体系的成熟文论观点。及至明朝,“本色”方才逐渐被引入戏曲批评之中,作为戏曲文论领域的批评理论得到了一系列演化。
二、明清时期“本色”论的演化发展
明朝前期,風气严格,在一定程度上使包括戏曲在内的各种文学创作流于刻板说教,又严格限制了戏曲内容,统治阶层之后意识到戏曲的教化功能,试图通过戏曲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因此,明朝前期的戏曲理论多认为戏曲创作应以弘扬风化为主旨,少有对“本色”的论述。这一时期内的戏剧创作也充满说教意味。这便促成了明朝中期戏曲创作与理论批评对本色的回归。
明朝“本色”论专论戏曲语言方面,其第一次快速发展发生于嘉靖至隆庆年间。徐渭是第一个系统全面提出戏曲“本色论”的文论家,在他的戏曲理论著作《南词叙录》中,徐渭提出了自己的本色理论,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一、戏曲语言应自然不做作;二、剧情要取材于现实生活,描述真情;三、“贱相色,贵本色”,认为对人和事物的描写应符合其本来面目。[10]徐渭是唯一一个对戏曲剧情和人物塑造有所论述的曲论家,在徐渭之后的曲论家论及本色时,基本是围绕语言和格律进行讨论的。
除去徐渭之外,李开先与何良俊也曾在戏曲语言方面提倡过“本色”,李开先对本色的论述散落于各篇文论文章之中,而何良俊则是在其理论著作《曲论》中对“本色”进行论述,并没有像徐渭一样形成完整的理论。除去以上文论家,王世贞也是这段时期内颇有影响力的文论家,其在理论著作《曲藻》中对本色有所论述。及至万历年间,戏曲创作逐渐规范化,以汤显祖为首的文人们也逐渐追求起了戏剧语言的雅致化,文人和文论家逐渐分为吴江派与临川派两派。其中,吴江派的众位剧论家反对在戏剧创作中对雅致的片面追求,大力提倡本色论,这一派中的代表人物为沈璟和吕天成。沈璟提出的本色曲论主要分为语言和格律两个方面,认为戏剧应严守格律要求,戏剧语言应当贴近生活,不惮采用俗言俚语。吕天成则在曲论专著《曲品》中对“本色”和“当行”进行了专门的区分和论述。与沈璟一样,他也提出本色是指戏曲语言的质朴,但他同时也认为要达到本色,不应一味在创作中加入日常用语,而应进行提炼和加工,去掉粗鄙俚俗的部分。而“当行”则涉及戏曲的创作方法。此外,被后人公认为戏剧宗师的汤显祖虽是临川派代表人物,但与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在戏曲语言上有所论争,认为戏曲创作不应受到格律等形式的约束,且一生中并无有关“本色”的直接论述,但从其对《焚香记》的点评中可以看出,汤显祖在戏剧创作上也倡导“尚真色”,认为戏剧语言应包含真感情,与徐渭的本色论有共通之处。而他的作品也被之后的曲论家王骥德认为是本色创作的巅峰:“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11]
及至晚明,戏曲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本色论在前代曲论家各种观点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晚明戏曲家王骥德对前人的曲论观点进行了参考和总结,完成了曲论巨著《曲律》,书中对本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王骥德本是徐渭之徒,又常与沈璟去信讨论曲论,其本色理论便集采了二人观点之长处。王骥德认为,戏曲语言应既通俗又考究,不能过分俚俗,也不能过分雕琢;在创作时应根据戏曲体裁的不同来决定语言的风格,大曲可偏于文雅,而小曲则可多用本色语。一部戏曲中的不同部分也应分情况决定语言风格,如小曲的定场白应简单通俗,结尾则应使用富有文采的“俊语”收束。除王骥德之外,在晚明时期,还有徐复祚、祁彪佳等曲论家对本色论进行了讨论,主要还是对戏剧语言方面提出要求,认为戏剧语言应通俗易懂而不粗俗,反对过度雕琢。
明朝之后,本色论便未再引起大规模的讨论。明朝之后的曲论家普遍吸收了本色论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戏剧理论。清朝李渔便在吸收前朝曲论家的观点之后,建构了包含情节安排、文本用语,甚至是表演方法的,较为全面的戏剧创作观点体系。“本色”论在其中依旧是戏曲创作方面的理论。在《闲情偶寄》中,李渔曾指出,塑造角色时应注意角色的行当和身份,不能塑造得千人一面,使观众看不出分别。要达到这种效果,就需要在填词时下功夫,譬如花脸应塑造得更为粗俗,而生角、旦角等角色的台词应仔细斟酌,就算人物只是仆从丫鬟,语言也应考究,不能与净角或丑角雷同。
总的来说,我国戏剧领域中的本色论兴起并成熟于明朝,对明朝之后的戏剧理论有着深远影响。众剧论家对本色的诠释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提到了对语言风格的关注,认为戏剧语言应通俗家常,反对咬文嚼字和过度雅化戏剧语言。以徐渭为代表的文论家提出的本色论除了对语言风格有要求外,在剧情和角色塑造方面也有所要求,认为戏剧剧情应取材于现实生活,而人物塑造应符合人物身份。
三、结语
如今在包含“本色”的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戏剧领域中的“本色当行”,但“本色”这一理论概念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使用却并不局限于此。“本色”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经历了极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在我国古代文论的各个领域都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深入了解“本色”概念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提高研究者对不同文论中“本色”内涵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一册:卷一至卷一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唐]南卓,等.撰.羯鼓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郑孟津,吴平山.词源解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7]敬晓庆.明代戏曲本色说考论[D].西北师范大学,2004.
[8]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9]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0]杨琼.明代戏曲本色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
[11][明]王骥德,著.陈多,叶长海,注释.曲律注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吴秋璇,女,硕士研究生在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 王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