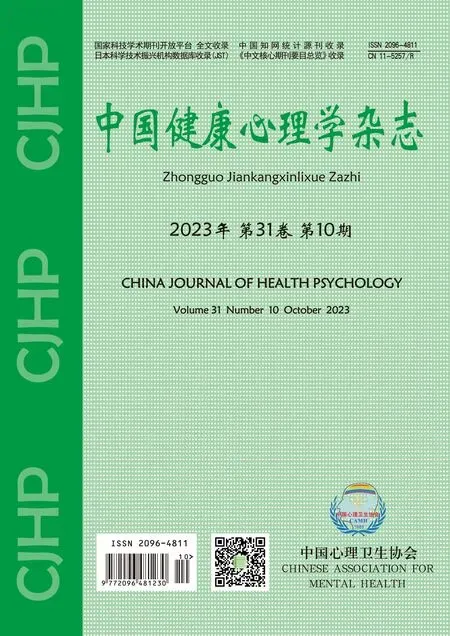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不孕不育夫妻正念与生育压力的关系*
2023-10-16王婕妤程静娴王春艳王吟霜庞晶晶吴炫烨王丹妮袁爱群罗桂英
王婕妤 程静娴 王春艳 王吟霜 庞晶晶 吴炫烨 王丹妮 袁爱群 罗桂英△
①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合肥) 230022 ②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教学中心 △通信作者 E-mail:luogyhsz@126.com
不孕症被定义为一种生殖系统疾病,其特征是在12个月或以上未避孕而未获得临床妊娠[1]。在世界范围内,不孕症的患病率为46.25%[2]。中国育龄夫妻不孕症患病率为25%[3]。不孕不育夫妻承受着巨大的生育压力,这包括生理问题、心理问题、夫妻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压力[4-5]。正念通常被定义为关注和意识到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状态,换而言之,就是通过身体和心理感知事物发展的状态,不抗拒也不逃避,接纳事物原本的样子[6]。有文献综述认为:正念干预可以减轻不孕女性的负性情绪[7-8]。正念作为积极的心理资源的一种,可能是缓解心理应激的方式[9-10]。有研究认为正念和生育压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1],但研究仅限不孕女性个体,并未涉及到男性,未从夫妻双方的角度出发,个体的正念对配偶的生育压力的交互作用尚且未知。
越来越多研究认为,处理辅助生殖中患者的问题,应注重夫妻之间的互动[12]。不孕不育是夫妻双方共同经历的重要事件,也应被称为“我们的疾病”。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证实了人的互动在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强调社会是一个动态实体,社会是人际间运用符号互动的产物,人和人之间通过互动,行成和发展自我,改变,处理和应对外界的变化[13]。夫妻之间也是通过语言,动作,表情,文字等符号进行交流。个体的心理状态可能会通过符号互动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配偶[13]。婚姻生活是夫妻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目前,不孕不育的心理研究已从个体层面转移到夫妻层面,探讨不孕不育夫妻正念与生育压力的关系及交互作用是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考虑到成对样本的非独立性,Kenny等提出了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也称为行动者-对象互倚模型[14]。该模型已用于夫妻互动研究。是一种多用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成对数据分析方法,可同时评估个体内部变量间,个体与配偶变量间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符号互动论和APIM模型,探讨不孕不育夫妻的正念与生育压力的主客体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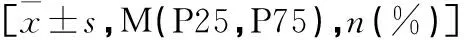
表1 607对不孕不育夫妻的一般资料和临床资料
1.2 方法
包括一般资料问卷、临床资料问卷、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和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ertiqol)。
1.2.1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 由Brown和Ryan编制,主要用来测量个体当前的觉知与注意的程度[16]。2012年,陈思佚等[17]对该量表进行汉化和修订,该量表仅1个维度,共15个条目。采用Likert 6级计分(1~6分),即“总是”到“绝不”分别计1~6分。总分15~90分,得分越高说明正念水平越高,低于40分为较差,41分~65分为中等,66~90分为较好。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本研究中男性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8,女性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8。
1.2.2 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PI) 由C R Newton等编制,主要应用于测量不孕不育患者的生育压力[4]。国内研究者Peng等[18]对此量表进行汉化。该量表有46个项目,5个维度来评价综合生育压力。采用Likert 6级计分(1~6分),即“完全不认同”到“完全认同”分别计1~6分,量表计分范围46~276,分数越高,生育压力越高,其中18个条目为反向计分。量表总Cronbach’s α系数为0.77~0.93[19]。本研究中男性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8,女性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5。
1.2.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法,取得安徽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号:20200961)。由课题组固定的3名成员向患者夫妻解释调查目的、意义及问卷填写方法,征得其同意后,请患者夫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发放问卷。调查时,对调查问卷进行登记与编码。双方同时填写,并在两间办公室进行,保证各自填写的保密性。完成问卷需15~25分钟,填写完成后当场检查,如有疑问由研究者再重新询问,最终采用双方共同认可的信息。如有双方任何一方资料填写规律作答则排除该对双方的资料。本研究共发放问卷619对,回收有效问卷607对(98.06%),排除的问卷中其中7名/对患者规律作答,5名/对患者拒绝作答。
1.3 统计处理
使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录入,SPSS 23.0和Mplus 8.3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中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使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非正态分布的数据使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数描述。采用卡方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丈夫和妻子的一般资料、正念和生育压力。用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APIM检验了一个因果变量对个体结果(也称为行动者影响)和对配偶结果(也称为伴侣影响)的影响。Kenny等认为夫妻属于可区分对子,APIM可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混合回归法和多水平模型等方法进行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是最简便的数据分析方法[17]。APIM中包括4个变量,个体A和B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个体自变量对自身因变量的影响称为主体效应,而个体自变量对对方因变量的影响称为客体效应。本研究使用APIM预测丈夫和妻子的正念与生育压力的关系。
2 结 果
2.1 609对不孕不育夫妻正念和生育压力的得分
不孕不育夫妻的正念和生育压力的得分差异不显著,见表2。

表2 不孕不育夫妻的正念和生育压力的得分比较
2.2 609对不孕不育夫妻正念和生育压力的相关性分析
妻子的正念与自身的生育压力和丈夫的生育压力均呈负相关,丈夫的正念与自身的生育压力呈负相关,夫妻双方的生育压力呈正相关,见表3。

表3 不孕不育夫妻的正念和生育压力的相关分析(r)
2.3 不孕症夫妻正念和生育压力的APIM分析
主体效应结果表明,主体效应:妻子和丈夫的正念对他们自身的生育压力有显著影响(β=-0.382,P<0.001;β=-0.295,P<0.001);客体效应:妻子的正念对丈夫的生育压力有显著的影响(β=-0.120,P<0.05),丈夫的正念的妻子的生育压力没有显著影响(β=-0.036,P=0.384)。根据Kenny等的可区分对子的APIM算法[19],通过卡方来比较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主体和/或客体效应的影响,使用平等约束检验来比较男女双方的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约束主体效应相等,模型没有变化:△χ2(1)=3.723,P=0.154,χ2/df=2.03,比较拟合指数(CFI)=0.994,非基准化适配度指数(TLI)=0.972,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041,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0.037。将客体效应限制,模型没有变化:△χ2(1)=2.030,P=0.184,CFI=0.991,TLI=0.957,RMSEA=0.051,SRMR=0.021。将主客体效应均限制,模型也没有恶化:△χ2(2)=2.578,P=0.155,CFI=0.991,TLI=0.977,RMSEA=0.038,SRMR=0.036。说明正念对生育压力的主客体效应对于丈夫和妻子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

表4 607对不孕不育夫妻正念对生育压力的影响
3 讨 论
3.1 不孕不育夫妻正念水平和生育压力水平
本研究中不孕不育夫妻中妻子的正念得分为53.93±11.97,丈夫的正念得分为55.24±12.45,正念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夫妻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林佳楠等的研究与本研究正念得分相近,均属于中等水平[20]。康晓菲的研究中,不孕症夫妻双方的正念属于高水平,夫妻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1]。不孕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治疗痛苦和周期结果的不确定性,亟需引导患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健康教育促进者与医务人员需要重视患者正念水平。正念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能够增加对消极事件的接受度,从痛苦的想法和感觉的认知中转移,改变一个人与压力源、情绪的关系,改变对自我、意识、现实的感知,并不是改变压力本身[22],有可能减少不孕所带来的痛苦。
本研究中不孕不育夫妻中妻子的生育压力得分为143.80±26.31,丈夫生育压力的得分为143.34±26.7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中生育压力水平比宋东红等的研究低,本研究样本中首次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患者较多,生育压力相对较小[23]。Sandra等[23]的研究中,男性生育压力得分:117.6±21.14,女性生育压力得分为125.23±25.98。与国外比,生育压力得分相对较高,可能是由于中国传统思想重视婚姻、家庭和生育,认为生育是人生要事之一,国外多数人注重自我,超越了人生的世代传承。Sandra等认为男性的生育压力比女性小[24],而Zhang等的研究中夫妻双方生育压力的分没有差异,与本研究相符[25],毋庸置疑,女性承担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在辅助生殖治疗的过程中,部分女性选择辞职,男性也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双方会经历性压力,这也与生育压力密切相关[23]。漫长的治疗周期,不确定的周期结果,不乐观的经济状况,多次往返医院的疲劳,面对社会及家庭其他人员的压力,最终使导致高水平的生育压力。
3.2 不孕不育夫妻正念和生育压力的二元交互作用
APIM分析结果表明:不孕不育夫妻正念和生育压力具有主客体效应。主体效应,即不孕不育夫妻的正念能预测自身的生育压力水平;客体效应,即不孕女性的正念能够预测丈夫的生育压力水平。妻子的正念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其自身的生育压力就会减少0.382个单位,丈夫的生育压力就会减少0.12个单位;丈夫的正念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丈夫自身的生育压力就会上升0.295个单位。这表明,夫妻双方的正念水平不仅关系自己,也与对方密切相关。因此不孕症是夫妻双方共同的事情,需要双方共同的参与。
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现象和行为是通过人际沟通和互动才能够得到解释,人与人之间要不断的动态互动[26]。符号是指语言、文字、记号等等。人们通过符号互动,改变自我概念,发展相互关系,处理和应对变化。他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号而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夫妻之间也是通过语言、行为、心理等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符号互动论中将自我分为“主我”和“客我”[27]。“主我”解释了妻子和丈夫的正念会影响各自的生育压力:正念程度高的患者对于不孕不育状态保持高度的关注水平,积极面对不孕症,会减轻自身的生育压力水平[28]。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患者中正念有助于缓解患者的抑郁水平[29]。正念还有助于调节睡眠质量[11],减轻疼痛的感知[30],也可能会间接减轻生育压力。正念可以使夫妻双方感知到自身的状态,学会自我关怀,管理情绪,承认和接纳真实的自己,让自己发挥出抗压力和抗挫折的心理弹性[20]。符号互动论中的“客我”在本研究中并不是指“客体”,而是指丈夫通过妻子的积极心理资源感受到的自我。“客我”是指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夫妻之间通过各种符号进行互动,使用符号理解对方的态度和行为,也以符号评估自己的行为对对方的影响[26]。不孕不育夫妻通过符号互动察觉到对方的反应,同时感知到自己的行为,并纠正自己的行为。夫妻双方的自我认识的正确形成和发展,不仅需要主我来支撑,更要依靠对方的反馈所形成的客我来进一步纠正。妻子的正念状态会通过语言行为等因素影响丈夫的生育压力,可能是女性患者往往倾向自我表露和共情[31],容易觉察到男性的心理状态,并使用积极的心理资源(如:正念)引导其丈夫重新认识自己的生育压力水平。正念倾听,正念回应,正念表达会促进和伴侣和谐的亲密关系[32],能缓解生育压力。
不孕不育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常被家庭需求和社会期望所重压,可能难以集中注意力和关注自我[33]。所以针对夫妻双方的正念训练亟待提上日程,如: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和接纳与承诺疗法等。目前对于不孕不育的干预大多针对个体,本研究为以夫妻为共同体的正念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正念影响生育压力的机制还不清楚,根据符号互动理论,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如患者自我表露程度,开放与沟通能力,人格特性等,后期可以探究这些中介变量。
本研究显示:不孕症夫妻的生育压力受主体和客体正念的影响。该结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这提示护理人员、健康教育人员和临床医生,应把不孕不育夫妻双方看做一个整体,本结果为后期以夫妻为共同体的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临床工作中更要关注女性的正念水平,提高女性正念水平,可能会对夫妻双方均有益。本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单中心研究,可能存在选择偏移,后期可进行多中心的研究。其次,研究设计属于横断面调查,限制了不孕不育夫妻正念和生育压力的因果关系的推断,以探究合理干预频率和干预最佳时间点。后期需要进行纵向研究,以更好地了解不孕不育夫妻正念和生育压力的变化轨迹。第三,本研究只探讨正念对生育压力的影响,后期可以针对生育压力的其他因素进行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