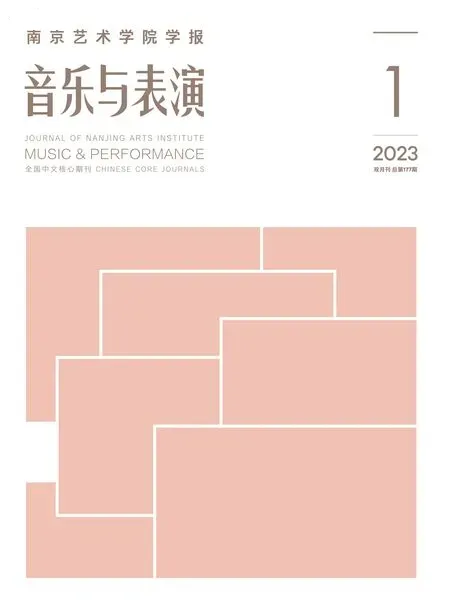从分庭抗礼走向融合①
——1950 年至1966 年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研究述评
2023-10-11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南京210038
张 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8)
冯效刚(安康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1949 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1949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华大地上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乱,进入一个以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解放区革命音乐工作者(其中的歌唱家以民间唱法居多)进城,一大批民间艺人也陆续成为专业文艺表演团体的职业歌唱家。当中国新社会步入20 世纪50 年代,虽然各行各业都处于重建之中,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艺术事业的复兴,在短短的三五年中,中国的新声乐表演艺术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一、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新中国建立初期,活跃在我国音乐舞台上的歌唱家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从海外留学归来或在国内随外国声乐家学习的美声歌唱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民间歌手中涌现出来的歌唱家;三是来自解放区的中国民族歌剧演唱家。
(一)美声唱法更趋成熟
20 世纪50 年代,以欧洲传统声乐方法演唱的艺术家纷纷登台歌唱“新社会”,除在新中国成立前便享有盛誉的中国声乐界著名的“四大名旦”黄友葵、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以出生年为序)和应尚能、蔡绍序、满谦子、葛朝祉、朱祟懋、李志曙、高芝兰、张权、周碧珍等仍相当活跃之外,又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且声部齐全的青年歌唱家,如女高音歌唱家邹德华、刘淑芳、张利娟、孙家馨(花腔)、郭淑珍、梁美珍、张越男、叶佩英、方初善、李晋玮;女中音歌唱家董爱琳、苏凤娟、罗天蝉、靳小才;男高音歌唱家沈湘、楼乾贵、李光曦;男中音歌唱家魏启贤、林俊卿、王凯平、刘秉义、胡宝善、寇家伦、黎信昌;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杨比德(杨彼得)、吴天球、李维渤;以及姚牧等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欧洲传统声乐方法演唱为主的歌唱家人数众多,他们大多接受了前辈美声歌唱家(或外国专家)的指导,对“美声唱法”的科学发声法的掌握更进了一步,同时在演唱中国艺术歌曲作品时,积累了一些表演经验。譬如:沈湘②沈湘(1921 年—1993 年10 月4 日),天津市人,中国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将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语言相结合,将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运用于演唱实践,形成了对正确演唱的独特认知,以事实证明了“洋为中用”在中国歌唱艺术中的可行性和正确性。他在一生的声乐教学中,培养出一大批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家[1];并且,他的学生继承了他的声乐理念,创造性地开发了被认为是“中国美声唱法”的声乐演唱体系——中国民族唱法(这是“后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注重歌唱艺术研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下,文化部组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声乐研究所——上海声乐研究所,由林俊卿①林俊卿(1904 年—2000 年7 月12 日),医生,歌唱家,1935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理学系医学选修科,1940 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建国后,任上海声乐研究所所长。出任所长。林俊卿对美声学派的歌唱训练方法深有领悟,他不仅是一位著名医生,还是歌唱家,创立了“咽音唱法”,成功地利用“咽音练声法”治疗、挽救了一大批“失声倒嗓”的歌唱家,尤其是由他培训出的一些歌唱家在该领域均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接受过西方正统“美声唱法”训练的歌唱家在中国歌剧舞台上十分活跃,如男高音歌唱家楼乾贵②楼乾贵(1923 年10 月—2014 年11 月21 日),浙江宁波人,男高音歌唱家。、李光曦③李光曦(1929 年—2022 年3 月13 日),出生于天津,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享有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女高音歌唱家张权④张权(1919 年—1993 年6 月16 日),江苏宜兴人,女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唱家。张权1947 年赴美国,先在纽约罗城纳萨瑞斯学院学习,1949 年入罗城大学伊斯曼音乐学校读研究生。、邹德华⑤邹德华(1926— ),江苏苏州人,女高音歌唱家。等,他们的演唱风格均各具特色。
20 世纪50 年代,美声唱法的歌唱家演唱中国民歌已经成为时尚。如郎毓秀在自己的音乐会保留曲目中增加了晋北民歌《绣荷包》、江苏民歌《小小针线包》、新疆哈萨克族民歌《明白了咱们的玛丽亚》、四川民歌《丰收》等[2]。郭淑珍演唱的曲目中也有《翻身道情》《王二嫂过年》等民族色彩浓郁的歌曲。以她们为代表的歌唱家在声乐表演艺术“民族化”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3]。作为我国系统研究美声唱法的歌唱家,他们为中国声乐表演艺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乡野之花”盛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特别关注蕴藏在民间的中国传统音乐舞蹈艺术,1953 年起连续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一大批优秀民间艺术家脱颖而出,如丁喜才⑥丁喜才(1920—1994),陕西府谷麻镇人,1953 年被贺绿汀特聘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民间音乐、榆林小曲,此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讲师、副教授。(陕北著名的二人台民间艺人)、朱仲禄⑦朱仲禄(1922 年2 月22 日—2007 年12 月22 日),出生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村。他一直潜心于“花儿”歌唱艺术的研究。他借鉴西洋歌唱艺术中有益的部分,使他的声音更加自然圆润、宏亮优美,真假声结合自然,声情并茂。他将青海“花儿”从江河源头传遍祖国大地,被誉为“花儿王”。(人称“花儿王”)和刘改鱼⑧刘改鱼(1939— ),出生于山西省左权县城南街的一户贫苦家庭,一生致力于演唱左权民歌。(“太行歌后”)就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在这些民间歌手的影响下,一批民歌演唱家迅速成长起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黄虹、郭颂、鞠秀芳、马子清等。
黄虹⑨黄虹(1928—1999),原名黄琼芝,著名云南民歌歌唱家。作为一个民歌演唱家,她对云南汉族民歌的介绍、传播以及演唱艺术的提高,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她演唱的《猜调》《小河淌水》《绣荷包》《耍山调》等云南民歌,赢得广泛赞誉。从小受到云南花灯、革命小调、抗日歌曲、滇剧音乐的熏陶。她读初一时,有幸遇上了“伯乐”赵沨,并接受了他的精心辅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虹演唱了《猜调》《小河淌水》《绣荷包》《耍山调》等云南民歌,成为著名的中国民歌演唱家,她对云南汉族民歌的介绍、传播以及演唱艺术的提高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演唱云南民歌最有成就的女歌唱家。
郭颂⑩郭颂(1931 年—2016 年5 月19 日),辽宁沈阳人,民歌演唱家。在民间艺术熏陶下长大,他演唱的东北民歌《丢戒指》等受到马可、李劫夫的首肯。郭颂以演唱东北民歌著称,他的代表作品《新货郎》《月牙五更》《乌苏里船歌》等把黑土地民歌艺术引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鞠秀芳⑪鞠秀芳(1934 年3 月— ),江苏人,原籍靖江,女高音歌唱家。1950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后,在贺绿汀院长、周小燕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下,随丁喜才先生刻苦学习,在民族声乐艺术道路上孜孜以求、努力开拓,终于以1954 年灌制的第一张榆林小曲《五哥放羊》,给了人们新颖的民歌艺术体验,得到广泛的称赞和肯定。
马子清⑫马子清(1935— ),女,陕西榆林绥德人,著名陕北民歌演唱艺术家,陕北民歌《三十里铺》的首唱,被誉为陕北民歌“歌后”。系陕北著名民歌艺人,她曾以一首《三十里铺》唱响大江南北,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被一度誉为陕北民歌“歌后”。
与此同时,一批少数民族的民歌手也走上舞台,展露出独特风采。如蒙古族最负盛名的长调民歌大师哈扎布、苗家“金嗓子”阿旺、“新疆百灵”帕夏·依香,以及被誉为“雪域金嗓子”的才旦卓玛等。
(三)民族歌剧演唱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民族化”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快速改观,展露出朝气蓬勃的风采。来自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8 年抗战、4 年解放战争的歌唱家,以《白毛女》第一代“喜儿”的表演者王昆为代表的民族歌剧演唱者“进城”后活跃在各种表演场合,她们自觉吸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滋润,继承了中国民歌和传统戏曲的演唱方法,以清晰的“吐字”、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进行表演,受到改变了社会面貌的中国工农大众的欢迎。这些来自“解放区”的歌唱家和郭兰英、管林、任桂珍等一起,形成了另一大阵营——中国民族歌剧演唱家。
郭兰英①郭兰英(1929 年12 月— )原名郭心爱,出生于山西平遥,中国女高音歌唱家,晋剧表演艺术家,歌剧表演艺术家,民族声乐教育家。原是山西梆子演员,投身革命文艺队伍后,她借鉴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精粹,因唱演俱佳而更具艺术感染力,“被公认为喜儿这一艺术形象的经典阐释者”。
任桂珍②任桂珍(1933 年—2020 年10 月10 日),女,山东临沂人,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来自山东解放区,她汲取了民族唱法在声音控制、行腔处理、吐字、音色变化等方面的特点,表演方面则大量吸收我国传统戏曲的方法。同时,她借鉴西洋发声法的优点,并融入自己的演唱。在上海实验歌剧院30 年的歌剧演唱中,“其嗓音纯净,歌唱富于表情,吐字清晰,表演自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当时的中国歌剧舞台上有“北郭(兰英)南任(桂珍)”[4]之称。
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歌剧领域活跃的歌唱家还有在歌剧《洪湖赤卫队》中扮演女主角韩英,并以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红海内外的王玉珍③王玉珍(1935— ),女,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因扮演中国民族歌剧“第一代江姐”而风靡大江南北,一曲“红梅赞”一直为一代代中国人所传唱的万馥香④万馥香(1941—1994),原名何宜珍,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在民族歌剧《江姐》中成功塑造了“第一代江姐”的艺术形象。;在歌剧《刘胡兰》中成功塑造了“胡兰子”的方晓天⑤方晓天(1925—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以清亮、甜润的歌喉和朴实细腻的表演,把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这一艺术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舞台上的乔佩娟⑥乔佩娟(1932—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以及首演歌剧《红霞》,成功塑造了“红霞”形象的蔡培莹⑦蔡培莹,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歌舞团”演员。;首演歌剧《红珊瑚》,成功塑造了“珊妹”人物形象的蒋晓军⑧蒋晓军,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文工团”演员。等。
由此可见,当时的民族歌剧演唱艺术是革命激情与民族风格的统一,中国民族歌剧演唱艺术从此逐步走向成熟。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我国民族歌剧舞台上,女性比男性形象更为突出,呈现出“女强男弱”的景象,一直到今天仍未根本改观。然而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声乐艺术领域,传统民间演唱艺术与“正统”声乐表演艺术基本上处于分庭抗礼的局面,它们各行其是,各自发展。
二、“土-洋唱法”之争
从20 世纪30 年代起,在我国声乐演唱和教学中,客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唱法,一种是学习运用欧洲“美声唱法”发声方法和演唱技巧的唱法,当时俗称“洋嗓子”;另一种是运用我国传统戏曲、民歌或曲艺等民间歌唱艺术发声方法和演唱技巧的唱法,当时俗称“土嗓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洋嗓子”主要活跃在大城市和专业音乐圈中,“土嗓子”属于民间艺术,其主要生存空间在农村。尽管一部分有远见卓识的声乐家,如应尚能、喻宜萱、黄友葵及周小燕等人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以美声唱法演唱中文歌曲时的一些问题,但从整体上说,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两家基本上处于相互隔阂、平行发展、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然而到了20 世纪50 年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美声唱法”的歌唱家与民族风格的歌唱家以及民间歌手常常同台演出,两种唱法固有的矛盾也就随之凸显出来,“洋嗓子”和“土嗓子”之间的所谓“土洋之争”变得难以回避,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史上最激烈的“土洋之争”随之展开。
“土洋之争”关注的焦点其实主要是演唱风格,在当时,西方美声唱法在“呼吸”“共鸣”等方面成熟的演唱方法(技术层面)已经得到大多数业内人士的肯定。
歌唱方法科学性一直是声乐教育者和实践者在追寻的真理,也是民族声乐向美声靠拢的主要依据之一。[5]
为了解决分歧、统一认识,当时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中国音协”)下属的“音乐问题通讯部”就“唱法”问题,在《新音乐》9 卷2 期至《人民音乐》1 卷4 期(1950 年6 月—12 月)上发动了一次“唱法问题讨论”,讨论为“笔谈”形式,以中央音乐学院教师为主,参加讨论的不仅有声乐家,也有一部分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工作者。
这场讨论大致可分为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强调民族民间传统唱法对于表现民族情感和语言的特殊优越性,并以此来贬低美声唱法,认为“洋唱法”是口里含橄榄,听起来像“打摆子”⑨时任中国音协主席的吕骥,在其《学习技术和学习西洋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便持有这种观点。[6];第二种意见则强调意大利美声唱法在歌唱方法上的科学性及其训练、教学的系统性,并以此来贬抑我国民族民间唱法,认为“土唱法”不科学,容易唱破嗓子。两种意见各执一端,互不相让。随着讨论向纵深发展,一种比较公允、客观的意见渐渐明晰起来。即:两种唱法既各有优长,又各有不足,不可能用一方取代另一方;唯有长期并存,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才能使两种唱法都得到发展和提高[7]。后由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师汤雪耕执笔总结。
这一争论虽然发生在声乐艺术领域内,而且触发媒介仅仅是所谓“唱法”问题,但其涉及的范围和性质,则远远超过了表演艺术的界限,而广及如何科学处理“中西关系”这样一个贯穿整个20 世纪且始终困扰中国音乐界的宏大命题,背后隐伏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具有长期而普遍的意义。发生在声乐表演艺术中的“土洋之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音乐界对于如何处理音乐中的中西关系问题的第一次观念大碰撞,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围绕声乐表演艺术在“唱法”层面为数极少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以民族民间唱法为主的歌手们对“美声唱法”在认识上有所提升。《人民音乐》1964 年第一期发表的一篇对李波、孟贵彬的访谈中就提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8]
李波在采访中谈到,由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训练民族唱法的完整方法,为了提高演唱技巧而向欧洲唱法学习是无可非议的,不承认其他唱法并不恰当,问题是吸收什么?怎样借鉴?孟贵彬谈到他在1955年曾到中央音乐学院去进修过三年,他的体会是:学习欧洲唱法作为手段使自己的表演技巧更加丰富是有用的,但是应该明确以民族的为基础,欧洲唱法只是作为借鉴。[8]
一些秉持“美声唱法”的歌唱家也对如何演唱中国歌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1953 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声乐比赛中获奖的上海女中音歌唱家董爱琳①董爱琳(1927— ),浙江宁波人,女中音歌唱家。1952 年成为上海乐团专业歌唱演员。获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声乐比赛三等奖。说:近几年来,我们学习欧洲唱法的同志在唱中国歌时,吐字已有很大的进步,但光吐字清楚还不行,语言还要唱得生动,令人听来亲切。语言要唱得生动,就得注意运腔问题。欧洲传统唱法的运腔,是按着旋律音、平平稳稳的,这个音唱完再接下一个,中间不能拐弯,如像上海郊区民歌中那种小颤音是没有的。这样来唱中国歌就会四平八稳,没有韵味,不生动。我们以前受欧洲唱法的这种影响很深,现在已经开始改变这种老办法。[9]
新的中国唱法应该“以中国人民的声乐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并且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各方面的营养来丰富自己,修正自己,科学化、系统化”。[10]张权认识到:“学习西洋歌唱艺术的,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或学习民族声乐的,向西洋学习,可以相得益彰,互为补充,是非常有益处的。”[11]这些事例表明,经过“土洋之争”的讨论,“两大阵营”的歌唱家都反思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认识上趋向统一,同时也是“土—洋唱法”融合这一发展道路上源与流的统一。
而“土洋之争”最直接的成果,是出现了一批注重吸收“土”“洋”唱法各自优势,既讲求“吐字清晰”基础上的“韵味”,又注意“发声”和“共鸣”的歌者,人们将其称之为“民族唱法”。1956 年,张越男②张越男(1934 年3 月15 日—2015 年),回族,女高音歌唱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副团长。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民族唱法的概念,指出:科学的发声,民族的吐字,在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的优点来丰富我们民族的声乐艺术。[12]
民族唱法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在国内,有人把“民族唱法”界定为:由中国各族人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爱好,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歌唱艺术的一种唱法,包括中国的戏曲唱法、说唱艺术的唱法、民歌唱法和民族新唱法等四种;还有人用意大利文“Nazionale cantanti”(直译:国民歌手)来界定“民族唱法”;中国著名音乐学者田青在“央视青歌赛”上提出,大赛上的所谓“民族唱法”只是注意到中国语言“吐字”“行腔”的“中国美声唱法”,真正的中国“民族唱法”是生存在民间的“原生态民歌”唱法。我们这里并不准备参与其概念的讨论,而是借用田青的观念以“中国美声唱法”来指代“民族唱法”。
自20 世纪50 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如何处理和把握中西关系这个焦点问题上,不断地围绕着技术技巧、民族风格与审美观念等主题展开讨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以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格为主无可争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唱法中的发声技巧。一种观点认为,技术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其本身并无中西之分,可以西洋唱法为基调,逐步将民族风格渗透其间。另一种观点认为,借鉴西洋唱法中的发声技巧就很难回避其演唱风格的影响,还是应当从中国传统唱法(民歌、戏曲、说唱)中汲取发声技巧,走纯粹的中国之路。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民歌、戏曲、说唱历经成百上千年的发展,一定有其成功的发声之道,如郭兰英有过多年唱山西梆子的经历,她将其中的一些经验融入新歌剧的演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见,中国传统唱法中有许多精华等待着我们去努力发掘、整理。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这些前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有些我们尚未进行整理(如民歌),有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如戏曲、说唱),其发声技巧与演唱风格融为一体,拆分整理起来相当困难。于是,在经历了几次颇为艰难的过渡和比较复杂的转换、变化之后,对于中西关系的认识已经有些发展和进步。如前所述,李波在20 世纪6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就曾谈到,民族唱法目前尚未形成自己的训练体系,需要从美声唱法中学习和借鉴成熟的演唱技巧[8]。最早的一批民族唱法的歌唱家往往也是有选择地接受美声唱法中的一些发声技巧,如“呼吸”“共鸣”等,加上自身良好的声音条件,形成风格迥异的演唱。这虽然是中国声乐艺术的创新,但还不成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三、民族唱法悄然兴起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演唱艺术中国化的重要形成阶段,一些从事声乐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把美声唱法与中国歌唱艺术结合起来,可以看作是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进一步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上海音乐学院在贺绿汀院长的倡导下,实行的一些举措非常有效。譬如,聘请有影响的民间歌手进入学院进行课堂教学,丁喜才(陕北)、朱仲禄(青海“花儿王”)等就是那时被聘请来的。鞠秀芳随丁喜才先生刻苦学习,成为我国高等音乐学府培养出来的首位演唱民歌的歌唱家。与此同时,从20 世纪50 年代起,得源于国家对少数民族歌手的培养,上海音乐学院开始进入了民族唱法的探索历程。王品素教授①王品素(1923 年4 月30 日—1998 年12 月11 日),女,声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可谓民族唱法教学的拓荒者之一。
1956 年,上海音乐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少数民族学生,并于1958 年正式成立了“民族班”,同时招收藏、维吾尔、苗、彝、蒙古、朝鲜、白、黎等8 个民族的民间歌手13 人,分别对不同民族歌手在保持其歌唱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化训练。在1958 年以前,王品素主要从事的是西洋美声唱法的教学与研究;1958 年底,藏族民歌手才旦卓玛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组织上安排王品素担任她的主科(声乐)教学老师。由此开始,王品素进行民族声乐教学的最初探索和研究。才旦卓玛后来回忆道:“我听着那些婉转如流水的花腔女高音,听得入迷,禁不住模仿起来,老师惊讶极了,因为她竟然在钢琴上找不到我的高音区。老师当即决定不让我走传统路数,让我尽量保留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指导我通过科学方法把自然状态发挥到极致。现在想来,老师做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丢失自己的嗓音特质。”[13]
从以上回忆中可以看出,王品素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保护学生原有嗓音特点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她借鉴“美声唱法”的演唱技巧,对不同民族学生进行细腻的艺术处理指导。经过她的悉心指导,学生们的音域得到扩展,西洋声乐的唱法与保留原有风格特点的嗓音相结合更加动听、灵活。此后,经王品素培养出的优秀歌唱家还有何纪光②何纪光(1939—2002),苗族,我国20 世纪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代表作品有《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等。、吕文科、胡松华、姜嘉锵、曹燕珍等,他们的演唱在更高的层次得到了提升和发展。
当时的民族班,在教学上特别注重对技能技巧的培养,将演唱过程中的民族性、专业性以及学生的个性密切结合。贵州籍苗族女青年阿旺③阿旺(1937 年12 月— ),苗族,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我国著名苗族女歌唱家。就是其中的一名学员。阿旺“在掌握苗族民歌的演唱风格方面,有着比较稳固的基础,但是歌唱时高音比较紧,下巴紧张,不会运用软口盖,气息的运用也有缺点。她的声乐老师(胡靖舫)学习、研究了她所演唱的民歌,了解了她的歌唱特点,在她原有演唱风格的基础上,帮助她克服缺点,巩固和提高她的发声能力和表现能力。经过将近一学期的教学,她的演唱能力有了显著进步”。[14]
上海音乐学院在实践中走的是一条融汇中西声乐文化的民族声乐教学之路,探索出了符合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规律的教学路线。
1964 年9 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亲自批示,在北京组建了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了以汤雪耕为系主任的民族声乐系,著名歌唱家张权、王玉珍等担任教学工作。中国音乐学院的建立,加速了中国民族声乐演唱艺术的教学与研究进程,推动着我国民族声乐艺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由于不可逆的原因,在此后十多年中未见长足的进步。
通过对以上事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天我国声乐艺术界对“民族唱法”的认知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在唱法上传承和借鉴一切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但一定是以本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符合中国人审美习惯的歌唱艺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民族唱法”(中国美声唱法)悄然兴起的年代,民族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于淑珍、邓玉华,男高音歌唱家吕文科、李双江、胡松华、何纪光、贾世骏、吴雁泽(以上按出生年为序)各领风骚,男中音歌唱家马国光的演唱深受大众青睐。
从以上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民族唱法歌唱家的成长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或多或少接受过美声唱法的训练,同时自觉注意吸收民族民间艺术的精华并融入其演唱中。在此基础上,许多歌唱家在演唱中吸取了中国传统歌唱艺术(民歌、戏曲和“说唱”)的优长,相互吸收使得他们在演唱中国作品时,十分注意咬字的清晰、语言声调的自然流畅、行腔的民族韵律和感情的真实表达。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最早的民族唱法歌唱家非常注意根据自身的“嗓音”特点去探索与中国语言字音、声调的结合,从而使得他们的演唱个人风格十分明显,一听就知道这是于淑珍,那是邓玉华。“千人千面”形成百花齐放,歌唱艺术展现中国风格成为声乐界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因此,民族唱法一出现便得到了广大中国民众的认可和欢迎,中国民族唱法由此登堂入室,成为具有独特风采的时代歌声。同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加速发展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当时在“洋为中用”口号的滥觞下,“美声唱法”曾受到了严重的“阉割”。首先,美声唱法作为外来的艺术形式,在文化背景、审美习惯上难以被当时的主流音乐群体普遍接受。由于对外来艺术不适应而产生的偏见和“左倾”意识的干扰,美声唱法被人为地贴上了诸如“声音虚、感情冷,与工农兵有距离”“资产阶级情调”等意识形态的标签。其次,美声唱法自身在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阶段性的问题和不足,尤其在与中国语言、风格的结合上暴露出了较多的问题。这些技术上的缺陷往往成为人们质疑乃至攻讦美声唱法的理由:“声音像牛叫,打摆子,含橄榄。”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对外交往上受到种种限制使得中国声乐艺术失去了正常的国际交流的机会,中国的美声唱法从曲目范围到声音概念、演唱技法、教学手段等各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制约,逐步与当时国际主流的西洋唱法拉大了差距。最后,政治形势的日渐严峻使得从事西洋唱法的人的基本权利和正常地位难以得到保证。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当时的西洋唱法被迫牺牲应有的规范和标准,在演唱吐字、行腔、审美趋向上迎合“左倾”意识形态的政治需求和审美趣味,“女声唱直唱尖,男声又压又紧”,从而严重降低了自身的艺术质量。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总体上是新音乐表演艺术的上升时期,国家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以“派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一方面选派优秀的青年音乐家赴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深造,另一方面邀请这些国家的专家来我国从事表演艺术教学。无论出国深造还是在国内随来华的外国专家学习,都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歌唱家。特别是在最初的十年中,政府不仅为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倾注了大量财力、物力,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自由学术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是由于氛围宽松,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歌唱家,以及外国专家将当时世界先进的音乐表演理念介绍进来,为国内的艺术家打开了一扇窗,从而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对反思自身以前的音乐表演艺术以及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良好的自由学术争鸣中,各家、各派的观点能够畅所欲言,通过反复讨论最终形成“共识”,这就使得新中国初期的声乐表演艺术观念凸显出“中西融合”的特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大批新中国优秀的音乐表演艺术人才茁壮成长,从而为20 世纪末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我国声乐领域的进展得益于中国政府对于音乐艺术事业的高度重视,凸显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新中国建立后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师资队伍越来越强大,声乐教育水平飞速提高,大批来自部队文工团的歌手(王昆就是其中之一)和民歌手被选送到高等音乐院校接受正规化和系统性的专业训练,经过声乐教育家的精心培养(如王品素对藏族歌手才旦卓码的培养),年轻的歌唱家成长起来。
其次是音乐界对声乐艺术民族化问题的关注,在“土洋关系”大讨论中增进了不同声乐演唱风格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在唱法民族化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歌唱艺术展现中国风格成为当时声乐界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总有一个作为文化秩序之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它始终垄断着文化意识中的权威性并以此来约束文化,要求整个文化来为之服务,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当然也并不例外。
诚然,艺术的“多元化”特性,不断催生着各类“新形态”艺术的诞生。概观中国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它在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的同时,无不体现出它的“历时性”。通过对以上事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天我国声乐艺术界对“民族唱法”的认知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在唱法上传承和借鉴一切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但一定是以本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符合中国人审美习惯的歌唱艺术。文化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便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