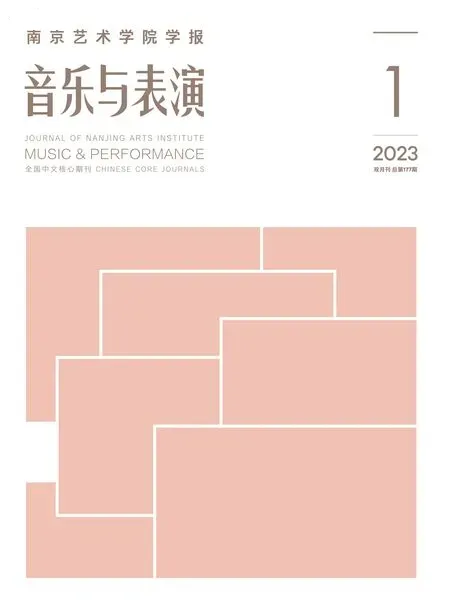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三个美学支点①
2023-10-11乔邦利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乔邦利(浙江师范大学 艺术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本文所谓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是指20 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背景下,中国歌剧表演艺术家在继承戏曲和民间歌舞表演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吸收并融合运用西方戏剧表演手段,在合理扬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清晰目标定位、鲜明民族特色、独特语言风格和稳定审美品格的音乐戏剧表演样式。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戏曲表演美学、民间歌舞表演美学和西方戏剧表演美学构成了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三个主要美学支点,在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观念、表演理论和表演实践中得到集中体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及其学派建设的发展和成熟。
一、中国戏曲表演美学
戏曲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瑰宝,也是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形成、发展并逐步成熟过程中取之不尽的文化、思想和技术宝库。毋庸置疑,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自成一体的舞台艺术形式,西方歌剧表演和中国戏曲表演虽然赖以生成的文化土壤、传播环境、受众群体等方面迥然有别,在舞台构思、表演观念、表现手段、舞台行动及语言风格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以歌舞演故事”这一功能定位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不管是西方歌剧还是中国戏曲,都将舞台表演艺术作为戏剧化呈现的重要手段和核心要素之一。以至于在西方歌剧传入中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一些人将戏曲和歌剧混为一谈。最初,人们将秧歌剧和《白毛女》等作品称作新歌剧,以与旧歌剧(即中国戏曲)相区别,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思维逻辑。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衬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辉煌历史和巨大发展成就。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些辉煌历史和巨大发展成就,才使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具备了与西方歌剧表演艺术进行比较的资本,也才能够让新文艺家们在错综复杂的中西关系之争中客观评价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比较优势和核心审美价值,进一步增强了歌剧表演艺术家的文化自觉和民族化追求。
传统戏曲表演是中国戏曲艺术的核心要素,在戏曲艺术发展成熟过程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成为推动中国传统戏曲流派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强大推动力。戏曲唱腔的流变、戏曲艺术流派的更迭等相关内容几乎贯穿整部戏曲发展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基于特定舞台观念和美学原则的戏曲表演实践与理论体系,成为足以与西方戏剧表演艺术相媲美的较为完善的表演话语系统,被誉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与此同时,一代代戏曲表演艺术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戏曲特有的舞台观念、美学范畴和发展传统。这种表演传统突出地表现为情景交融的写意表演风格定位和精益求精的唯美(泛美)表演追求两个方面。而这些表演传统中的优秀部分,既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不断发展的源头活水,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萌芽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基因。
(一)情景交融的写意表演风格定位
写意性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与西方艺术创作中重写实的审美取向和语言风格不同,中国传统艺术中更加注重写意性表达,对于“神似”的追求远胜于“形似”。在艺术语言和创作手法上强调亦虚亦实、虚中有实、以虚代实、虚实相生。中国传统美学注重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的“言外之意”“画外之音”,力求达到一种情景交融、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这种美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戏曲写意性表演美学及表演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具体而言,写意性表演美学及舞台观念在中国传统戏曲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程式化的舞台语言
程式化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也是最容易被观众所捕捉和感受的一种舞台语言表现手段。“动作的程式产生于生活动作的舞蹈化,即把普通的生活动作变成舞蹈、变成节奏化。”[1]
在人物塑造方面,中国戏曲将表演中的角色类别划分为生、旦、净、末、丑等不同的行当,分别代表不同的年龄、性别、社会身份及性格特征等。同样,戏曲唱腔也是这种程式化思维的结果,一曲多用是传统戏曲音乐展开的主要手段和结构特征。在舞台行动方面,演员在规定情境下的各种动作也具有某种程式性特征,比如开门关门、穿针引线、上马下轿、驾车使船、行军打仗等;在舞台布置方面,传统戏曲舞台上一般只有一桌两椅,十分简洁。但是,这一桌两椅在舞台上发挥的作用却十分广泛,既可以做道具,又可以做背景,随时根据剧情表现的需要而赋予其不同的功能,使用起来非常简便、灵活、自由。
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新歌剧表演艺术探索的秧歌剧表演在舞台布置方面从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传统戏曲,“演出没有布景,只挂一块天幕和摆一两张旧桌子和凳子之类的道具,一切演出条件是非常简陋的”[2]10。这种处理,一方面是为了克服实际困难,适应流动性演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主动向传统戏曲表演学习的结果。当时的艺术家们在充分尊重广大观众审美习惯,倾听观众意见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借鉴了戏曲表演中程式化的舞台语言技巧,让观众既有新鲜感,又有亲切感,易于理解和接受,获得“既熟悉又陌生”的独特审美感受。
注重工程施工技术的质量监管,对工程整体周期涉及到的技术方案、工序流程、组织结构等内容进行严格的把控。依照安全施工及规范化操作的标准,提升施工技术方案拟定质量,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工程施工效率。不仅如此,在施工技术质量管理过程中,也需提升施工技术交底工作的有效性,确保施工技术的先进性及适用性。
2.虚拟化的时空关系
在戏曲表演中,所谓虚拟化,就是演员利用事物之间的联系,以简单的道具或动作代替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或者利用舞台转换代表现实生活中的时空变化,以达到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以简喻繁的效果。比如,演员手握船桨代表划船,用马鞭代表坐骑,一刀一枪代表各种兵器,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等等。戏曲评论中“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江山;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的表述,就是对虚拟化表演手法最贴切的描绘。在著名京剧武戏《三岔口》中,演员通过虚拟化的表演,把剧中人物武艺高超、机智果敢的人物形象和在黑暗中摸爬滚打的打斗场面表现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刻画了侠肝义胆、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戏曲表演的虚拟性还表现在演员与剧情及角色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演员在表演中可以随剧情发展需要而跳进跳出,以剧中人、叙述者或旁观者等多重身份随时与观众进行交流。这种跳进跳出的人物关系,突破了舞台空间的局限,戏剧情节交代简洁明了,演员在台上自由转换角色,观众在舞台下看着真实可信,丝毫没有突兀和混乱之感。
在《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窦娥冤》《红珊瑚》等中国民族歌剧作品的表演中,虚拟化的手法可谓随处可见。比如,歌剧《白毛女》第三幕中,黄世仁与穆仁智在房间里密谋如何将喜儿卖到妓院里去,恰好被房门外的二婶听到。表面上看,二婶与另外二人之间好像处在同一个舞台空间之内,但是,表演者通过特定的舞台动作,将二婶安排在房门外的虚拟空间之中,手法简洁,效果逼真。再比如,在歌剧《红珊瑚》第二场中,老三驾船连夜到牛头岙给窦司令“送礼”,孙富贵手提灯笼押着珊妹在海上行进。整场戏的故事情节都发生在海上。在海政文工团的表演中,舞台上除了一张巨大的海浪景片之外,其他一无所有。台上所有人物的动作,如孙富贵手提渔灯、老三持橹摇浆、珊妹站立船头以及珊妹跳海等等舞台动作,基本都是在虚拟化的表演中完成的。同样的情节,在上海歌剧院排演的版本中,即便在舞台上增加了一个船的布置,但是任桂珍等人的表演中仍体现出较强的写意性和虚拟化特点。
3.象征性的构思手法
在艺术创作中,象征作为一种重要的构思手法,主要指艺术创作过程中某种抽象概念或复杂情感的具体化和对象化过程。象征性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鲜明特点之一,广泛应用于舞台动作、人物脸谱、服装道具、舞台布景、音响效果等方面。以人物脸谱为例,不同脸谱在选色定型、勾勒图案时都要考虑脸谱与人物性格、思想之间的相对稳定的指代关系。比如“红脸象征忠勇、正义,黑脸象征刚毅、正直,白脸象征多谋、狡诈,紫脸象征持重、稳练,蓝脸象征勇猛、骄横,绿脸象征倔强、残暴,等等”[3]。再比如,戏曲表演中,演员往往以某种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如做针线活时不小心扎破手指,弹琴时琴弦突然断裂等)预示着某种不幸的发生,等等。这些动作都是运用了象征性的表演构思手法。
对于传统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象征性构思手法,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采取了选择性吸收和批判性继承的态度,既合理扬弃了传统戏曲表演中的脸谱化做法,又把年龄、身材、声音甚至性格特征是否与剧中人物相符作为挑选演员的重要参考依据,以满足观众对演员与角色形象一致性的传统观剧习惯,保证形象设计与角色塑造、剧情发展和舞台行动之间的协调统一。这一点,从喜儿、刘胡兰、小芹、江姐、韩英、田玉梅等扮演者的身上都得到充分体现。
(二)精益求精的唯美(泛美)表演追求
中国戏曲将“四功”“五法”作为舞台表演的基本规范,在基本功训练和舞台呈现方面精益求精,着重体现古典艺术中的唯美(泛美)品格。从事传统戏曲表演,不但要具备优秀的嗓音条件和扎实的唱功基础,还需要在形体上加强训练,并具备运用舞蹈动作和表情塑造人物的能力,对演员的综合舞台表现提出了较高要求。
在戏曲演员的全面技术规范中,演唱能力(唱功)排在“四功”之首,足以看出戏曲表演对演员演唱能力的重视。总体而言,戏曲演员的演唱不但要声音明亮、气息贯通、字正腔圆,还要在演唱中配合各种舞蹈动作,并保证声音不走样、表情不变形;需要熟练掌握五音(喉、舌、齿、牙、唇)、四呼(开、齐、撮、合)、声调和润腔等各种技巧;音色运用符合行当和角色表现需要,声情并茂、风格浓郁。20 世纪以来,中国声乐工作者在民间唱法基础上逐步吸收美声唱法的科学发声方法和演唱技巧,经不断努力,逐步探索出一套基于科学发声原理,并且具有浓郁中国民族特色的“民族唱法”,成为民族歌剧表演在演唱方面具有标志性的表现手段之一。
除了演唱之外,戏曲表演同样对演员的舞蹈功底和舞台行动把握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演员在舞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不但要具有舞蹈美的品质,还要具有明确的戏剧表现功能。在发展过程中,对戏曲表演载歌载舞表演技术规范的继承和创新,构成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区别于西方歌剧表演艺术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窦娥冤》《红珊瑚》《江姐》等经典剧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综上所述,相较于西方戏剧写实化美学原则和表演传统,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表演美学通过程式化的舞台语言、虚拟化的时空关系和象征性的构思手法,弥补了戏曲舞台在客观生活表现上的固有局限和不足,有效解决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相协调统一的问题,舞台构思简便易行,舞台表演自由洒脱。在舞台表现方面,戏曲演员全面的表演技能,为载歌载舞的综合美感生成和唯美(泛美)表演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形神兼备的表演,让观众在听觉和视觉的综合体验中,获得全面、立体的审美感受。中国民族歌剧表演在借鉴西方歌剧表演美学原则和表现手段的基础上自觉吸收并大胆扬弃传统戏曲写意表演美学原则,综合运用程式化舞台动作、虚拟化时空关系和象征性表现手段,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特表演特色和审美品格的民族歌剧表演范式,丰富了中国歌剧表演艺术的内涵,成为在中国民族歌剧表演学派建设中的一大突出贡献。
当然,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对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的学习,并非简单照搬,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创新。比如,民族歌剧表演在演员和角色关系处理时,放弃了传统戏曲行当的脸谱化做法,却合理吸收了综合舞台美感呈现的表演理念,强调歌剧演员与角色外在形象的一致性,并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与西方歌剧表演的显著不同。
二、民间歌舞表演美学
民间歌舞是我国传统艺术中独具特色的综合表演艺术形式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间歌舞是在劳动人民日常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同样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舞与地方戏曲、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为它们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滋养。
载歌载舞是我们民间歌舞表演中的突出特点之一。多数民间歌舞表演都集演唱、舞蹈和器乐演奏于一体,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者大都是技术全面、既能唱又能奏、既能演又能跳、身兼数职的全能型演员,熟悉“四功”“五法”的各种技巧及相互协调配合。一般情况下,演员在表演中都是边歌、边舞、边演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民间歌舞表演中演唱的一般都是当地民歌,演唱方法不加修饰,音质纯真质朴,亲切自然,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舞蹈动作讲究与音乐所表达情绪的协调一致,并充分挖掘舞蹈语言的造型功能,结合化妆、舞美等手段,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表演中的动作多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加工提炼而来,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种高度概括化和典型化的肢体语言。
得益于民间歌舞表演的悠久传统和良好的受众基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发展过程中,歌舞剧表演得到快速发展。其中,城市歌舞剧表演以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社为代表,黎明晖、徐来、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和胡笳等人当时都在上海滩红极一时。其中,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和胡笳还被称为明月社的“四大天王”。她们表演的作品,如《小小画家》《三蝴蝶》《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等,装扮时尚,舞蹈动作简洁明快,情感真实自然,舞台形象纯真可爱,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艺术性品格,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风靡一时。
在广大农村地区,以工农革命时期苏区革命根据地文艺家创作的活报剧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当时编演的活报剧中,影响较大的有《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五一歌舞》《五卅歌舞》《粉碎敌人乌龟壳》等。表演时,“文艺战士身着蓝衫,另配三角形上襟(类似肚兜),里红外白,演出时翻出红襟代表革命人物,白色则代表反面人物,表演的动作简单明确。演员也可以代表机器牛马,还可以用队形变化和形体动作来象征某种事物”[4]。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活报剧表演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与中国戏曲和民间歌舞中模仿、象征等表演传统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内在联系。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活报剧在表现内容上更加突出了时代性的主题,舞台动作也更加简洁明快,通俗易懂。新的表现主题、时代性的表现内容与传统的舞台表现手段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
延安时期,新文艺家们对民间歌舞的改造和利用更加自觉和主动。特别是通过对陕北秧歌的改造,创作出一大批形式新颖、内容积极向上、格调清新的秧歌剧作品。在秧歌剧表演中,保留了大秧歌、小场子秧歌、腰鼓舞、花鼓、推小车、跑旱船等灵活自由的表现形式,载歌载舞,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种手法在后来的《白毛女》等新歌剧表演中得以保留,并构成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歌剧《白毛女》第一幕“扎红头绳”一段中,喜儿的舞蹈动作与演唱融为一体,产生强烈的造型性和戏剧性效果;在《小二黑结婚》中,婚礼中的假面娃娃舞及北方秧歌舞,也与剧情紧密结合,具有生活化的特质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而《窦娥冤》中“托梦”一场,端云(幼年窦娥)的形象则基本是在戏曲身段基础上加以舞蹈化处理的结果;《洪湖赤卫队》中的“三棒鼓”“手拿蝶儿敲起来”等唱段,也在表演中根据戏剧场面和情节推进中人物性格表现的需要,对身段造型加以舞蹈化的处理,等等。演员们在这些段落中的表演,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对民间歌舞的合理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及其学派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
三、西方戏剧表演美学
20 世纪初,在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虽然西方歌剧传入中国已有些时日,但是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对西方歌剧表演尚未形成概念,话剧和歌剧表演对新型舞台表演所产生的影响也相当微弱。即使在当时作为时尚文化代表的黎锦晖儿童歌舞剧表演,在舞台语言风格上也更多受中国传统歌舞的影响。一些名为歌剧的原创作品——如《扬子江暴风雨》,在表演形式上也大多以话剧加唱的形式在舞台上呈现,话剧表演的成分所占比重较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歌剧表演对西方演剧的学习并非针对单一的西方歌剧表演传统,而是同时对话剧和西方歌剧表演艺术学习、借鉴与融合运用的结果。从中国歌剧表演艺术中分离出来的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自然也不例外,是“二种民族形式(民间小型歌舞剧与传统戏曲)与两种外来形式(西洋歌剧与话剧)互相融汇的产物”[5]。西方戏剧表演美学也成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重要美学支点之一。
总体上说,西方戏剧表演对中国民族歌剧表演的影响,在舞台观念、演唱和舞台行动等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其中,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则在于演唱方面。历史地看,西方歌剧演唱中所普遍使用的美声唱法对中国民族歌剧的声音定位和唱法选择上一直都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歌剧《白毛女》创作和首演过程中,王昆、林白将自己学到的美声唱法技巧与民间唱法优秀传统相结合,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同样,中国民族歌剧表演在唱法探索方面的每一次进步,也都是在中国传统唱法与美声唱法相互争鸣与博弈过程中所逐步取得的。近年来,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声唱法演员(尤其是女中音、男中音、男高音等声部的演员),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民族歌剧表演的多元审美特征。
在表演方面,西方歌剧和话剧的写实表演美学和技术技巧对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产生的影响则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种影响在较早使用“新歌剧”概念的田汉和聂耳身上都有较突出的表现。他们二人在创作和表演上都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定位为“话剧加唱”的形式。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话剧表演手段在《扬子江暴风雨》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基于话剧写实表演美学观念、生活化舞台语言和雕塑化人物造型手法,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扬子江暴风雨》在表演上的主要特色,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延安时期,关于歌剧《白毛女》表演定位问题,大家在经过广泛讨论后,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即“我们完全应当以‘歌剧的’表演方法来处理它,我们的情绪应是诗的情绪,动作应是诗的动作——舞蹈,说话应是诗的歌唱,应该在充满诗意,在音乐和舞蹈的气氛和节奏中来进行。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2]45。毋庸置疑,西方歌剧和话剧中的表演观念及其表现手法同样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并成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与传统戏曲表演相区别的重要身份标识之一。
结语
作为伴随20世纪中国歌剧艺术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戏剧表演风格类型,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从歌剧《白毛女》开始奠基,经过《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歌剧作品的表演探索,一步步走向成熟,至今已走过近80 年的风雨历程。近80 年来,经过几代表演艺术家的接续努力,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紧跟时代主题和观众审美需要,扎根戏曲、民间歌舞等中国传统舞台表演艺术,同时合理借鉴西方戏剧表演的先进观念和技术手段,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国戏曲和民间歌舞中的虚拟化写意表演美学与西方戏剧中的生活化写实表演美学进行融会贯通、纵横捭阖,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具有独立审美品格的舞台表演范式和话语逻辑。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以宽阔的胸襟和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在不断探索中彰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不同发展阶段积累了数量可观且颇具典范意义的舞台表演成果,同时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民族歌剧表演艺术领军人物,学派建设成就斐然,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的可持续发展和体系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和人才基础。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也因此成为20 世纪以来中国舞台表演艺术领域最具生机和活力的类别之一,在国内外戏剧舞台上赢得了崇高的艺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