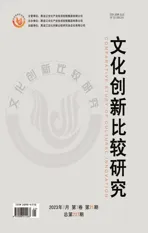从两版《小城之春》看中国两代电影导演的民族文化传承
2023-10-09蒋韵平吴熙
蒋韵平,吴熙
(深圳大学 艺术学部,广东深圳 518060)
民族文化的传承,就像文化加工厂的一道生产工序,随着人类自身的代代繁衍,推动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
抗战结束,残垣断壁的小城里住着一户人家。丈夫戴礼言身患肺病,妻子周玉纹不得不日日照顾他,家里还住着丈夫的妹妹戴秀和一个仆人老黄。直至一个春天,丈夫的昔日老友登门拜访,原来是妻子的初恋情人章志忱。朝气蓬勃的志忱吸引得戴秀对他暗生情愫,但他心中始终无法忘怀玉纹,而玉纹也因他的到来重新点燃了小城生活的希望。二人发乎情止乎礼,志忱终究离开戴家,玉纹终究在小城里继续生活下去……
这便是费穆导演的电影《小城之春》的故事。而这一段故事,通过另一位导演田壮壮的翻拍,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实现文化传承,意欲寻求中国电影发展之路的答案,不禁让人心生敬意。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1],很少出现时隔半个世纪拍摄同名电影的事情,同一个电影名字出现在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位知名导演的创作生涯中,这看似巧合的背后,贯穿的是相同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基因虽因表现载体的不同而变化,细观其中,我们仍能看到其“根”的存在。
1 两版长镜头语言“虚实”的破与立
中国的艺术创作自唐宋元时期,就探索出“以虚写实、虚实结合”的美学精神。被称为人文类别导演的费穆,曾在《中国旧剧的电影化问题》中提出,“中国画是意中之画,所谓 ‘迁想妙得,皆微于言象之外’,画不是写生的画,而印象确实真实……有时轻轻几笔,传出山水花鸟的神韵”[2]。
受中国文化美学精神影响的费穆,在作品《小城之春》中,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巧妙地将电影艺术的写实和中华美学的写意相融合,创作出画面流动感与东方古典美兼具的长镜头(见图1)。

图1 费穆《小城之春》(1948年)的电影画面1
1.1 卷轴式长镜头传递东方美学意境之美
电影开始3分钟左右的一段长镜头,让人印象深刻。仆人老黄拿着围巾,到花园里的废墟上去找少爷戴礼言。长镜头伊始右摇,画面中老黄走向围墙上残破的洞口,朝里唤了声“少爷”,随即走向右边另一个洞口与礼言对话,镜头小幅度从左向右摇,但并没有跟过去,而是巧妙地从左边的洞口慢慢推进,穿过围墙,进入园林,再接着深入推进坐在墙边上的戴礼言,老黄接着从右入画。由墙外的废墟潦草到墙内的别致园林,在与音乐的配合中,不断推动的镜头为观众带出了如此一位战后幸存的民国少爷。镜头在不断运动中呈现着不同的内涵,其视觉上呈现出流动的美感,恰似诗里所描绘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费穆版《小城之春》的另一段长镜头,也刻画了剧中四人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涌动。志忱来到戴家,妹妹戴秀给志忱唱歌,吸引着他的注意;而志忱虽坐着听歌,他的目光几乎一直落在玉纹身上;玉纹给丈夫礼言弄药,偶尔回看几次志忱。礼言在左边的床上歇息,玉纹在前景忙碌,占视觉的中心,右侧是戴秀和志忱。这段一分半钟的长镜头左右横摇6次,但玉纹、志忱、礼言三人从未同框,在这看似如此平和的午后,镜头悄然诉说着三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电影作为一种西方的舶来品,若要在中国发展壮大,必定离不开对中华传统艺术和中华传统思想的继承[3]。在“戏影观”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电影发展早期阶段,同时也是西方长镜头理论正式提出的20年前,这两段别出心裁的长镜头的出现极具艺术特色和美学价值,无疑象征着费穆导演在对电影语言的前瞻性探索和研究。费穆导演在《小城之春》中将两者相融,可见中国“第二代导演”在电影发展史上的创新与匠心[4]。
1.2 以静制动助力长镜头语言的虚实表达
费穆版《小城之春》的长镜头运用,很好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与韵味,是中国古典文化中虚实相生的最好运用案例。如何将这一精神传承下来,也成为田壮壮导演翻拍同名电影时特别注重的地方。在2002年版的《小城之春》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第五代导演”对前辈之创造性的文化传承[5]。
1948年《小城之春》中被后人反复推敲的传达四人微妙关系的一幕戏,在2002年的影片中被这样呈现:礼言与志忱在书房谈话,隔着玻璃窗,玉纹在走廊对面擦拭着门窗。礼言说着话,志忱却漫不经心地透过窗户看着玉纹,男女两人全程并无眼神交流,暧昧又谨慎的氛围却从中蔓延,镜头蕴含的情感张力呼之欲出(见图2)。

图2 田壮壮《小城之春》(2002年)电影画面
另一长镜头的妙用,则在众人为戴秀庆生的那场戏里。
长镜头开篇,礼言居中,背对镜头作为前景,餐桌上志忱和戴秀分别坐一左一右,志忱向戴秀敬酒庆生,老黄从桌子对面走来给二人倒酒,其乐融融。老黄倒酒后离开桌子,玉纹登场,镜头慢慢向右移动,将礼言和戴秀作为前景,光线昏暗。四人皆坐后,兄妹开始划拳,镜头将焦给至前景二人,占主要画幅的志忱和玉纹二人虚焦,但光线充足,志忱含情脉脉地看着玉纹给他倒酒。紧接着,志忱邀请戴秀与他划拳,两人游戏之时,摄影机将焦点给向志忱和玉纹二人,镜头却不移动。这样的构图持续了一分多钟,直至礼言起立坐在了二人中间。镜头左移,将四人如卷轴般铺在画卷上,此时四人面部光线一致充足,戴礼言居于画面的中心位置,看着志忱和妹妹划拳……
在2002年版的《小城之春》这场五人戏中,田壮壮导演并没有通过镜头切换进行“点面描写”,而是通过室内光线的强弱运用,以及轻微移动、趋于静止的长镜头,进行极为客观的呈现[6](见图3)。夜戏中温暖的金色烛光,借助黑色背景和女主人身上暗红色旗袍,勾勒出一幅流动的油画,别样的光线处理也使得这场戏在低色温处理下显得耐人寻味。如此一来,观众不仅能察觉到玉纹内心久违的愉悦和大胆,还能看见志忱的游离挣扎和自我麻痹,切身体会到戴礼言对生活热情的觉醒和对过去与现状的无奈,以及长久以往的孤独;也避免了创作者对剧中人物的主观评价以及对观众焦点的强制性,给予了观众更多的观赏空间和思考空间。

图3 田壮壮《小城之春》(2002年)生日宴场景的别样光线处理
1.3 两版镜头表达强化同一东方美学内涵
1948年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被誉为中国电影美学史上的一个高峰。2002年,田壮壮导演重新翻拍的 《小城之春》获得当年威尼斯国家电影节大奖。可以说,两版《小城之春》为所有爱好中国电影的观影者带来了穿越时空的精神享受,也为中华文化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写下了一首“成长诗”。
无论是1948年制作的黑白电影,还是2002年翻拍的彩色电影,都通过长镜头的镜语表达,构建了东方美学的恬淡隽永,让民族文化中“情景交融”的美学内涵,在不同年代镜头里均得以表现。这是对文明的传承,这是对东方美学的培育,这种在不同代际导演间,以无声之语、默契之心传承发扬的做法,笔者希望可以更多一些,因为文明的质量要靠不断地付出和创新,以及对文化的认同和珍惜来构建,只有这样,中华文明的根脉才能在电影艺术的银幕上,闪烁着芬芳优雅的光芒。
2 东方美学表演中“留白”的更与迭
在中国美学世界里,因国画中的“留白”而产生出独具特色的艺术智慧[7]。“留白”是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特色,广泛运用于音乐、诗词等创作中,创作者将主观情绪以“留白”的形式显现,传达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让观者进入无限想象空间,是中国文化艺术中含蓄且内敛美学的精华表达。中国电影人将“留白”运用到影像创作中,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审美体验一脉相承[8]。
如果说,两个版本的《小城之春》的电影语言中,皆有中国传统的古典韵味,故事里的人物塑造,也是留白美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两个版本的电影中,女主人翁玉纹一角,最能体现东方美学里典雅又俊俏的涵义[9]。
玉纹从小生长在南方。10年前,母亲不赞同她和志忱的感情,志忱离开小城,玉纹放弃爱情选择生活;10年后,其嫁的戴家家道中落,丈夫弱不胜衣,玉纹尽妻之责,日夜照顾,在枯燥无味的日子里继续生活。志忱的突然到访,让玉纹冷却已久的心底泛起涟漪。她让老黄代送一盆兰花,并亲自送去一壶热水,便是小心试探的痕迹……
玉纹和志忱在书房初次单独会面的场面,两个版本的《小城之春》均有演绎。虽然身处不同时代的演员和导演对同一角色的理解有差异,但两个版本中的玉纹,通过形象气质、性格作风、表演风格的表达,同样也塑造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女性形象。
2.1 演员塑造人物的表演留白尽显东方之美
费穆版 《小城之春》的玉纹在面对志忱的问询时,是这样解释的:“早忘了给你送来,怕你要喝。”玉纹将重音放在“忘”上,佯装镇静,她漫不经心的语气中透着傲娇,试图拉近和志忱的距离,展现了玉纹在志忱面前将此行来意与自身情感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暗示此番到访“名正言顺”的小心思。而当玉纹送来的热水和洗漱用品被志忱婉拒之后,玉纹仍微笑着对他说“你留着洗脸吧”“你留着用吧”,随即走向别处继续收拾布置。玉纹温柔的劝说,裹挟着愿在书房里侥幸久留的心思,尽显东方女人细腻和温婉的同时也凸显其十分可爱有趣。
玉纹要给志忱拿被单和毯子,志忱拒绝,玉纹坚持要去。玉纹笑着看着志忱,一步一回头,连说三句“我就来”。这句话明面意思是“我很快回来”,而玉纹面部洋溢着的笑容又像是在跟志忱打趣,如同年轻姑娘般俏皮任性,心中荡漾着久违的愉悦之情(见图4)。

图4 费穆 《小城之春》(1948年)的电影画面2
电影中,玉纹的举手投足和造型身段皆精准把握住了东方女性的优雅端庄和含蓄典雅,这归功于费穆导演对扮演者韦伟的启发。费穆建议韦伟借鉴梅兰芳的表演,将戏剧中的程式融入角色创造中去。韦伟并没有把玉纹塑造成一个循规蹈矩、恪守妇道的传统女人,而是在保持着东方韵味的人物造型中,通过对台词和行动的精妙处理,创造出富有魅力和生命力的女子。
2.2 留白艺术之美在当代电影表演中的延续
同样这场戏,在2002年田壮壮版《小城之春》中亦有呈现。从外形角度上看,新版《小城之春》中田壮壮导演对“玉纹”的选角是更加贴合的,演员单薄瘦小的体型和小巧精致的五官,迎合了玉纹作为南方姑娘的特点。
玉纹的扮演者胡靖钒双手拿着热水壶,幽幽地走进书房,转头回应道:“老黄忘记给你送开水了。”同样强调了“忘记”。当玉纹听到志忱说已有10年未见之时,玉纹顿了一下立刻走开,故作轻松地拿起洋蜡转移话题,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这样的表演 “留白”,仿佛说明玉纹不愿意触碰这个话题,寻求逃避。而后,玉纹幽幽流露出真情说道:“我不知道来的客人是你。”志忱听闻后正想上前敞开心扉,玉纹却再次佯装热情地指着别处聊。
如此一来一回中,新版“玉纹”的情感转换与旧版“玉纹”此景此情相比,倒少了几分可爱生机,多了层悲剧色彩了。正如我们所知,早期中国电影演员通常非科班出身,表演方法杂糅,而21世纪初的演员有条件接受专业电影学院的系统培养,拥有成体系的表演方法,相较过去更加自然化、影视化。
在2002年版的《小城之春》中,电影叙事更依赖于演员表演[10]。田壮壮导演以更加影视化的手段叙事,通过镜头语言和表演细节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将观众从玉纹的内心世界拉出,置于剧中人的暗流涌动之中,让观众在演员的表演中,深切体会到剧中三人的命运纠葛和复杂心境,正视多样化的伦理观念和道德选择,这或许也是田壮壮导演将画外音剔除的原因。
2.3 构建中国电影民族化表演美学势在必行
1948年版作品的演员们身处的环境更贴近于故事发生的年代,当时的社会环境、生活习性等信息唾手可得,这是2002版演员所不能及的。然而,抛开所有时代因素而谈,在对同一场戏的表演处理上,1948年版玉纹情感变化和行为逻辑受费穆导演的指导,借鉴了艺术大师梅兰芳的表演思想,将东方美学贯穿始终,人物分寸感拿捏到位,在全球影史上留下一个独具魅力的东方女性形象。这背后蕴含的是老一辈艺术家们对电影角色的日雕月琢和不懈探索,这恰恰是也当代青年演员需要传承和发扬的。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电影的表演品质和表演美学也在与时俱进地提升。表演艺术的审美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的关联和交互密不可分,中国电影表演者需要不断增强适应能力,提升表演准备性和审美度,在学习国际潮流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在展示表演的风格化和个性特色的同时,也需要对中国电影民族化表演美学的构建贡献力量。
综观新中国前30年电影表演思潮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双结合”表演,还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表演创作,均是中国电影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具有东方美学的中国电影的表演学理论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美学的语境中得到积极探索。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越走越实,中国电影民族化表演美学的学理建设、规律总结、未来开创等研究势在必行,这需要更多有志于提升中国电影美学、传承中国文化的年轻艺术从业者加入,对中国电影发展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 结束语
在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无始无终的循环中,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代艺术从业者,都是这个环链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哪一个环节的脱落,都将影响文化的再生产,而在代际传承环链中的脱节,会直接导致文化的断裂和中止。所以,民族文化的传承,绝不单是个人的自我行为,而是有着极强的群体性和整合性,最终实现民族群体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
在时间的长河中,《小城之春》已经成为代表中国电影艺术民族化的经典之作。无论是1948年诞生的版本,还是2002年翻拍的版本,都是中国电影民族文化探索进程的产物,其成果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以中国人的动作、中国式的表情去表现他们的内心活动……其次,剪辑手法和情节进展的速度,也必须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和趣味”,这才会形成真正的中华民族特色。
从两个版本的《小城之春》电影看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任何一个社会的传统都不会是静止的,艺术作品的价值上限大大取决于创作者的文化底蕴。我们从两位导演的作品中皆看到了不同时期的电影人将电影语言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不懈追求的精神,以及对中国电影创新发展的思考与期许,这或许是我们从这两个《小城之春》、两位电影导演身上所应学习和借鉴的,也是其时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