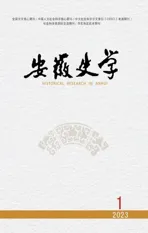宋代遗嘱征税的性质
——兼论析产与继承的区别
2023-10-07魏道明
魏道明
(青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开始要求遗嘱纳税:“凡民有遗嘱并嫁女承书,令输钱给印文凭”(1)《文献通考》卷14《征榷一》“重和元年”条,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但实行不久即废。南宋绍兴三十一年,王之望总领四川财赋,因军费过巨,重拾旧规:“凡嫁资、遗嘱及民间葬地,皆令投契纳税”,实行一年,共得钱467万余缗。(2)《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23页。王之望认为遗嘱纳税不仅可增加财政收入,也可免“亲族兄弟日后诉讼”,于公于私皆有益,故在次年上言高宗,建议向全国推广。因此,绍兴三十二年户部便制定法条,规定:“人户今后遗嘱与缌麻以上亲,至绝日合改立户及田宅与女折充嫁资,并估价赴官投契纳税。”(3)《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26,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342页。
遗嘱征税,实际上是对遗嘱中涉及的财产征税,很容易联想到这是遗产税。学界确实也有类似意见。如李淑媛就称之为遗嘱税或遗产税;(4)李淑媛:《争财竞产:唐宋的家产与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132页。乜小红也有类似看法,并积极评价其历史意义:“南宋实行遗嘱税……实际上是征收遗嘱继承遗产税,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5)乜小红:《秦汉至唐宋时期遗嘱制度的演化》,《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遗产税的征收有赖于强大的财产监管体系,是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征收难度很大的税种。20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曾开征遗产税,但效果差强人意,所预期的财政功能与社会功能皆未能实现。(6)参见刘巍:《民国时期遗产税制度的讨论、设计与实践》,《福建论坛》2018年第5期;雷家琼:《抗战前中国遗产税开征的多方推进》,《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今日虽屡有开征遗产税的计划与呼吁,但限于条件,仍未实现。(7)参见李华、王雁:《中国遗产税开征与否:基于遗产税存废之争的思考》,《财政研究》2015年第11期。那么,南宋时期,有能力和条件推行遗产税吗?即便抛开能力和条件不谈,在强调实行同居共财、禁止子孙别籍异财的古代社会,开征遗产税的法理依据又何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将宋代的遗嘱征税看作是遗嘱税或遗产税,或有不妥之处,称之为契税,可能更为合适。以下试详论之,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一
在中国古代,父祖尊长用遗嘱(书、令、命)处分财产的现象,较为常见。如果没有子孙等财产承分人,法律允许用遗嘱安排身后财产分配事宜:“在法: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官给公凭。”(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户婚门·违法交易》“鼓诱寡妇盗卖夫家业”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4页。如果有承分人,家产的承继,法律明文规定由诸子均分,原本无需尊长遗嘱安排,但土地有肥瘠,房屋有朝向,牲畜有老幼,很难做到均平划一,为防止纷争,父祖尊长往往会用遗嘱的形式预先定分家产。
以上两类遗嘱,性质各有不同。前一类遗嘱,是无财产承分人即“户绝”状态下所立,此时缺乏子孙等财产共有人,同居团体内无法形成财产共有关系,家庭财产事实上成为了个人财产,故遗嘱人可自由处分财产。唐代,对于指定继承人的资格及所能继承的财产份额均没有限定(9)唐代《丧葬令》规定:“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贷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宋刑统》卷12《户婚律》“户绝资产”门引唐令,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3页。,完全尊重遗嘱人的个人意愿;宋代开始有了限定,必须遗嘱给“缌麻以上亲者”,但对各继承人的份额仍然没有限定,遗嘱人可自行决定。此类遗嘱,性质等同于现今的遗嘱继承,可称之继承遗嘱。
后一类遗嘱,遗嘱人不过是为子孙等共有人平均分析家产,处置的是共有财产而非个人私财,遗嘱人的身份像是主持人。他既不能指定继承人,对于什么人分以及怎么分,也需要尊重法律的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也不能在继承人中对财产做不等额的分配:“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10)《宋刑统》卷12《户婚律》“卑幼私用财”门,第221页。在遗嘱中厚此薄彼,分产不均,属于违法行为,按规定是要受处罚的。此类遗嘱,是为了避免纠纷而借父祖权威进行分产,分配方式也是按法律规定进行均分,有遗嘱之名而无遗嘱之实(11)法律意义上的遗嘱,可以自由处分财产,但在中国古代,此类遗嘱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唐宋法律规定只能在无承分人的场合适用,“有承分人不合遗嘱也”。《名公书判清明集》卷5《户婚门·争业类下》“继母将养老田遗嘱于亲生女”条,第141—142页。有承分人时,父祖所立的遗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遗嘱,父祖只是借遗嘱之名——以遗嘱的形式按法律规定为子孙公平分产,而不能行遗嘱之实。,不妨称之为析产遗嘱。(12)在唐宋时期一些所谓的遗嘱中,立遗嘱人也参与财产的分配。如唐天复八年吴安君的口述分家遗嘱中,吴安君既是立遗嘱人,又是财产分配的参与人。可参见[日]山口正晃:《羽53〈吴安君分家契〉——围绕家产继承的一个事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257页。说明此类文书与将个人财产转移于他人的遗嘱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分割家庭共有财产的析产文书。
在中国古代,无子的家庭一般都要收养嗣子,“户绝”的情形较少发生,少有立继承遗嘱的机会,因此,我们所见绝大多数的古人遗嘱,都属于后一类。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出土的我国最早的遗嘱实物——《先令劵书》(13)参见王勤金、吴炜等:《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就是一件为共有人分割家产的析产遗嘱。汉代用遗嘱为子孙分配家产的行为较为常见,法律对析产遗嘱的效力还专门给予了肯定:“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叁辨劵书之,辄上如户籍。”(14)《二年律令·户律》,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唐宋时期,用遗嘱(书、令、命)为子孙分析家产的情形更为常见,宋人袁采就说:“父祖有虑子孙争讼者,常欲预为遗嘱之文。”(15)袁采:《袁氏世范》卷1《睦亲》“遗嘱之文宜预为”条,《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2页。敦煌写本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析产遗嘱及析产遗嘱样文(式)。
宋代的遗嘱征税,显然不是任何遗嘱都征税。从前引遗嘱征税的法条来看,“遗嘱与缌麻以上亲者”的遗嘱才征税,而“遗嘱与缌麻以上亲者”的前提条件是“财产无承分人”。由此可知,只有无财产承分人时所立的继承遗嘱才需要纳税,有承分人时所立的析产遗嘱并不征税。这可以从宋代遗嘱征税的配套措施中得到验证。
遗嘱只是财产的传承方式之一,若规定遗嘱征税,也需要对其他财产传承方式一并征税。故凡开征遗产税的国家,也同时开征财产赠与税。如果宋代给子孙等承分人的析产遗嘱需纳税,就应该同时规定父母生前就给子孙分产或者父母死后无遗嘱而子孙自行分产都需纳税,否则,谁也不会用遗嘱的形式为子孙分产,所谓遗嘱纳税无异于一纸空文。
但从本文开篇所引法条来看,宋代并没有生前给子孙分产或者父母离世后子孙自行分产需纳税的规定,与遗嘱同时配套征税的只是“嫁女承书”“嫁资”“田宅与女折充嫁资”一类,说明立法者原意是要对无财产承分人时所立的遗嘱征税。此时的遗嘱,遗产一般是给女儿,遂补充规定,生前以嫁资形式赠与女儿财产的,也要纳税。王之望建议在全国推广遗嘱纳税的理由之一是可免“亲族兄弟日后诉讼”(16)《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20,第5002页。,所谓“亲族兄弟”,应该是针对出嫁女而言。出嫁女夫家、娘家两边都有兄弟,“亲族兄弟”是特指娘家兄弟,这也可证明纳税的遗嘱是特指无承分人时给女儿的财产遗嘱。除去“户绝”时的遗嘱,其他遗嘱是不纳税的,所以敦煌写本中才有为数众多的析产遗嘱及样文(式),才有袁采所谓宋世父祖为子孙“常欲预为遗嘱之文”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父祖亡故后,家产由子孙承分。包括《宋刑统》在内的各朝法律一般规定为“兄弟均分”或“诸子均分”。(17)《宋刑统》卷12《户婚律》“卑幼私用财”门,第221页;《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户婚门·立继类》“命继与立继不同(再判)”条,第266页。按此,承继、分割家产的权利为子孙所享有,是当然的财产承分人。只要有子,即便是继子,包括女儿在内其他亲属都不能参加家产的分割。被兄弟或诸子均分的家产,我们无论将其全部或部分视为父祖的遗产,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遗产主要是在父子、祖孙等男性直系亲属之间传承。而他们之间的财产承继是不征税的。
总之,宋代的遗嘱征税,只有在“户绝”时或传承与儿孙等承分人以外的部分才征税。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遗嘱和遗产都是不征税的,称为遗嘱税或遗产税,并不十分妥当。
当然,现代遗产税属于富人税,只有达到一定数额才征税,相当一部分人的遗产不征税,实际上也是大部分遗产不征税。那么,宋代虽只有一少部分遗产才纳税,似乎称为遗产税也未尝不可。其实不然。严格来说,宋代遗嘱或遗产是否征税的依据,不是被继承人所留遗产数额而是继承人的身份,如果一份遗嘱中,同时给财产承分人及其他人分产,分给承分人以外的部分才征税。
或许还有这样的疑问:依照身份纳税,承分人以外的才纳税,或者说析产遗嘱不纳税而只有继承遗嘱纳税,不正好说明其性质是遗产税吗?
但宋代的遗嘱征税,按绍兴三十二年户部的规定,是在“合改立户”也即过户之时(18)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26,第6342页。,如果不过户,财产就是分给非承分人,也无须缴税。按唐宋时期的法律规定,父母双亡后的析产,在室女可按男子之半的标准分得生活费用,称为“女合得男之半”法。(19)在反映南宋时期司法判决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些案例允许女儿在非“户绝”时也参与家产分割,只是份额为男子的一半。如周丙死后,留有遗腹子及已婚女儿细乙娘,因分产发生纠纷,负责审理案件的刘克庄(后村)判曰:“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遗腹之男,亦男也。周丙身后财产合作三分,遗腹子得二分,细乙娘得一分,如此分析,方合法意。”《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户婚门·分析类》“女婿不应中分妻家之财”条,第277—278页。假如有人按此规定在遗嘱中给在室幼女财产,她可以使用这笔财产,但不需要纳税,只是长大出嫁以此财产作为嫁资时,才需要纳税。如果在出嫁前就已将财产变卖或者全部消费完毕,也不存在纳税的问题。在室女(包括归宗女)在命继场合所分得的财产,也与之类似。(20)古人立嗣有生前立嗣与死后立嗣之分:生前立嗣是父母俱在世时所立的嗣子;死后立嗣,可以分为“立继”与“命继”,“立继”指妻为亡夫立嗣,“命继”指夫妻俱亡,由近亲尊长立嗣。“命继”并非出于死者本意,由近亲尊长代立,目的多为争产。故法律规定命继子与女儿共同承袭家产,命继之子承袭家产的份额要受女儿身份不同(在室女、归宗女、出嫁女)的影响。即使没有女儿,命继子也不能承袭全部家产,国家也要从中分一杯羹。参见李淑媛:《争财竞产:唐宋的家产与法律》,第156—175页。如高五一死,仅有年仅一岁的幼女公孙,故立五一亲弟五二次子六四为五一命继子。公孙所分得的田产,无需纳税,田租作为生活费用,“候公孙出幼,赴官请给契照,以为招嫁之资”。(2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户婚门·女受分》“阿沈高五二争租米”条,第239页。可见,立契纳税是在过户之时。
因此,宋代的遗嘱征税,实际上就是过户税,也即产权转移税,称作契税更为合适。对此,史籍中也有明确记载。绍兴三十一年,王之望在四川对嫁资、遗嘱及民间葬地征税,史籍中称“皆令投契纳税”或“第括民质剂未税者”(22)参见《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卷372《王之望传》,第4223、11538页。,都是从契税的角度看待王之望的遗嘱征税行为。这在绍兴三十二年户部征税条令中说的更清楚:“人户今后遗嘱与缌麻以上亲,至绝日合改立户及田宅与女折充嫁资,并估价赴官投契纳税。其嫁资田产于契内分明声说,候人户赍到税钱,即日印契置历,当官给付契书。”(23)《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26,第6342页。
契税的本意是指对契约所征之税,通常是当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产权发生转移变动时,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或流转税。(24)刘勇:《契税征收与返还的解释论》,《法学》2018年第2期。契税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一般认为,契税虽创始于东晋,但直至五代,发展受限,宋代才成熟起来。(25)参见金亮、杨大春:《中国古代契税制度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魏天安:《宋代的契税》,《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宋代法令规定:买卖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26)《宋刑统》卷13《户婚律》“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第231页。,“凡典卖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27)《文献通考》卷14《征榷一》,第147页。按此,田宅、牲畜、舟车买卖在宋代属于要式行为,不仅要订立买卖契约,而且还要经官印押。(28)郭东旭:《宋代买卖契约制度的发展》,《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而经官印押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收手续费,也即契税。所以,在宋代,凡“人户典卖田宅、船、马、驴、骡,合纳牙契税钱”。(29)《宋会要辑稿》食货35之13,第5414页。可以看出,契税具有规费的性质,是以保障产权的名义征收的。
起初,契税的征收着眼于典卖交易行为,因赠与、继承而产生的产权变更,不征契税。随着国家财政拮据局面的加剧,北宋重和元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先后颁布法令,赠与女儿嫁田及遗嘱与女儿或内外缌麻亲属田宅,均需缴纳契税。(30)给予女儿的田产要上契税,至少延续到元代。元至正六年“徽州休宁县吴兰友为女陪嫁产业文书”中,给女儿益娘的陪嫁田产,“一听益娘婿偕甫自行闻官受税,收苗长养,永远为业”。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1页。但对赠与、继承行为征收契税,仅限于非承分人,子孙分析家产,以“分书”“阄书”一类前去官府办理过户手续,毋需缴纳契税。(31)南宋真德秀曾言:“人户分析,当从其便,访闻诸县乃有专置司局,勒令开户者,但知利其醋钱,不顾有伤风教。自今惟法应分析,经官陈请者,即与给印分书,不许辄有抑勒。”《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官吏门·申儆》“劝谕事件于后·禁苛扰”条,第15页。袁采也有言曰:“县道贪污,遇有析户印阄,则厚有所需,人户惮于所费,皆匿而不印,私自割析,经年既深,贫富不同,恩义顿疏,或至争讼。”《袁氏世范》卷3《治家》“析户宜早印阄书”条,第60页。按此,子孙析产时以“分书”“阄书”一类前去官府办理过户手续,也花费甚多,以至于“人户惮于所费,皆匿而不印。”但这并非契税,而是“醋钱”一类的杂费或是县道官贪污索贿。以上两条记载可以作为子孙析产过户不需要缴纳契税的旁证。
二
在宋代,给女儿财产,无论是用遗嘱还是生前赠与嫁资,都要征收契税。但是给儿子分析家产,无论是用遗嘱还是生分,都无契税可言。那么,子孙继产为何无契税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对子孙继产给予了免征契税的优待。免征是本应征收但因故免除。我国现行税法中,对于法定继承人继承土地、房屋权属,给予优待,免征契税。宋代也有免征之举,但因为契税税率较高,“人户投纳契税契钱,每交易一贯,纳正税钱一百文,并头子等钱二十一文二分”(32)《宋会要辑稿》食货35之15,第5415页。,是重要的财政收入项目,所以一般不会免除契税。按规定,宋代只有买卖耕牛可“蠲免投纳契税”。(33)《宋会要辑稿》食货35之10,第5413页。同时,按照古代礼俗,休妻要返还嫁资,因为嫁资已经征过契税,为避免重复,遂规定“田宅止于出母、嫁母,方合免税”(34)《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26,第6342页。,即被休或夫死改嫁之人从夫家随身带走的田产,不必再次纳税。可见,宋代免征契税的范围很有限,根本不包括子孙继产。这个“可能的解释”并不能成立。
绍兴三十二年,王之望在建议扩大契税征收范围时曾言:“契勘人户,将田宅遗嘱与人,及妇人随嫁物产与夫家管系。在法:‘田宅止于出母、生母(35)“生母”一作“嫁母”,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26,第6342页。,方合免税。’若与其余人,并合投税。今四川人户遗嘱、嫁资,其间有正行立契,或有止立要约,与女之类,亦合投税。缘得遗嘱及嫁资田产之人,依条估价投契,委可杜绝日后争端。若不估价立契,虽可幸免一时税钱而适,所以启亲族兄弟日后诉讼。”(36)《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20,第5002页。此举是试图将亲属间的不动产转移也纳入到契税的征收范围,虽然提到了继产的主体——“亲族兄弟”,但征税的着眼点,似乎都在子孙继产以外或者说是对外的产权转移——家庭财产转移给出母、生(嫁)母、出嫁女、近亲等,而家庭内部诸如父子、祖孙之间的财产传递,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说明作为立法倡议者的王之望根本就没考虑过子孙继产征收契税的问题。
没有免征待遇却又不征税,说明子孙继产本就不在契税的征收范围之内。从契税是产权转移之税的角度而言,不征契税,就意味着官方没有将子孙继产看作是产权转移行为。
但子孙继产产生新的产权单元、新的纳税户。析产的凭证——分书或阄书,是产权证书,与不动产买卖契约一样可以要求官府印押。南宋名臣真德秀就曾要求下属官员“自今惟法应分析,经官陈请者,即与给印分书,不许辄有抑勒。”(3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官吏门·申儆》“劝谕事件于后·禁苛扰”条,第15页。分书或阄书具有法律效力,遇有纠纷,以此为准。如在盛荣诉侄友能强占竹地、桑地一案中,官府就“照分书将上件竹地标钉界至,作两分管业”(3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户婚门·争屋业》“叔侄争·再判”条,第190—191页。,所以袁采告诫世人:“凡析户之家,宜即印阄书,以杜后患”。(39)袁采:《袁氏世范》卷3《治家》“析户宜早印阄书”条,第60—61页。
承认子孙继产产生新的产权单元,但又认定子孙继产不在契税征收范围之内,这或许与古代社会家庭财产制度的特性有关。现存的各朝律典,从唐律到清律都规定同居亲属实行共财制度,如《宋刑统》中就说:“同居,谓同财共居”,“称‘同居亲属’者,谓同居共财者。”(40)《宋刑统》卷6《名例》“有罪相容隐”门疏议、卷16《擅兴》“征人冒名相代”门疏议,第107、288页。同居共财团体内部,禁止拥有个人私产,所有收入皆要上缴作为共有财产,由家长统一调度、管理,成员隐匿收入或擅自处分财产要受法律制裁。同居共财实际上就是家族内的同居成员对家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大略相同于现代法律上的共同共有。
当然,现代共有制下,如果是夫妻共有,那么夫妻都是共有人,如果是家庭共有,那么家庭成员都是共有主体。而古代的同居共财,只有男性才可充当共有主体;女性在家庭中享有的财产权利,只是以使用表现出对生活必需品的占有权,事实上被排除在共有主体之外。(41)参见魏道明:《古代社会家庭财产关系略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7—48页。同居共有实际上是父宗血缘团体共有制,或者说是同居男性成员共有制。同姓共有、禁止财产外流是其主要特征。妻来自于外姓,女儿终究要嫁给外姓为妇,承认她们是共有主体,夫妻离婚、女儿外嫁,都会分割共有财产,财产外流便无法遏制。(42)魏道明:《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所以,古代同居共财关系不由婚姻产生,也不因离婚而终止,子孙成婚、女儿出嫁都不能作为分家析产的理由。(43)《宋刑统》规定,父母在及居丧,子孙皆不得擅自别籍异财,参见《宋刑统》卷12《户婚律》“父母在及居丧别籍异财”门,第216页。按此,子孙分割家庭财产,只能是奉父母之命或父母去世守丧期满,成婚自然不是分家析产的条件。但在此之前如汉代,可能并非一定如此。《二年律令·户律》载:“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78页。律文中似乎没有强调分家是父祖的特权、子孙不得擅自分家。相反,子孙成婚就可以提出分家析产。按简文规定,提出分家析产甚至都没有子孙必须成年的限制,而且只要提出分家析产,官府就会“皆许之,辄为定籍”。窃以为,这一规定过于宽松,或许是汉初特殊形势下的规定,不能代表先秦秦汉时期。结婚时妻子带来的嫁奁,不作为共有财产,分割家庭财产时,“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44)《宋刑统》卷12《户婚律》“卑幼私用财”门引《户令》,第221页。这看似是在维护妻的权益,实则是对同居共财稳定性的维护(45)瞿大静:《宋代析产制度研究》,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3页。,目的在于让同居共财免受婚姻关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妻在离婚时,自然就不能分割夫家财产。敦煌写本中,有不少反映唐宋时期夫妻“和离”的离婚协议书样文(式),称为“放妻书”或“放弃书”,涉及财产方面的内容极其有限。如编号S6537(背)的《放妻书格式》:“三年依(衣)粮,便献柔仪”(46)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萃编》上册,第410页。,编号P3730的《某乡百姓某专用放妻书一道》:“三年衣粮,便□柔仪”(4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97页。,俄藏编号Дx.11038《放妻书(样式)》“惣不耳三年衣粮”(48)《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这些均是夫家出于情义赠与妻子几年衣粮之资,而非夫妻分割家产。
女性非财产共有主体,她们承袭家产,就是继承他人具有所有权的财产,实现的是所有权主体的变更,自然要缴纳契税。同居团体中的男性属于共有主体,本就具备共有财产的所有权。但按“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的法律要求(49)《宋刑统》卷12《户婚律》“卑幼私用财”门疏议,第221页。,共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统一由家长行使,对其他成员来说,所有权与所有权权能是相互脱节的。共有人等份划分共有财产、自己行使所有权权能,等于将以前寄存在家长手里的所有权权能收回并由自己来行使,属于析产。从性质上看,析产所分割的是自己已经具有所有权的共有财产,不像继承那样是所有权的转移,而只是所有权权能的转移过程,所有权主体并没有变更(50)魏道明:《略论唐宋明清的析产制度》,《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自然无契税可言。
当然,如果较真的话,子孙承袭家产的行为,并不完全属于析产行为,也有继承的成分。按照古代社会的一般情形,家庭共有关系终止的起因往往是父祖尊长的死亡,所以分家析产多发生于尊长死亡后。(51)当然,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就分家析产的情形也并非罕见,据研究,《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此类案例不下十余件。参见邢铁:《家产继承史论》(修订本),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9页。这时待分割的家庭财产性质较为复杂,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部分是基于共财事实上的共有财产,一部分是基于财产权利人(父祖)死亡事实上的遗产。此时分割财产的行为既不是单纯的析产,也不是单纯的继承,而是两者的混合。(52)如果尊长生前就与诸子析分家产,则属于单纯的析产,与继承无关。但生前析产意味着父子之间的同财关系己经结束,形成“同居异财”关系;父母亡后,诸子再分割其财产,则又属于继承。
假如一个二子的家庭中,父亡,兄弟欲结束共财关系,核算家产共值150贯。兄弟和已故的父亲都是共有主体,按等份拥有的原则,每人平均50贯。每人一份的财产不管父亲是否亡故,所有权都是属于自己,是共财关系下已经拥有的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只有属于已故父亲的50贯才能看作是遗产。如果二子分割这150贯,每人合得75贯,其中50贯应是析产所得,25贯则是继承所得。
诸子承继家产,除非是独子,一般而言,析产的成分总是大于继承。而且,多数情况下,析产与继承是同步发生的,析产所得既然不必缴纳契税,继承部分也跟着受益。不妨这样认为,继承被析产吸收了。
中国古代的家产传承,属于析产还是继承,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古籍中“继承”一词虽已出现,但多表示事业或身份的传承;(53)如《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页):“朕以眇身,继承鸿业”。又《宋史》卷340《苏颂传》(第10859页):“无土无爵,则子孙无以继承宗祀”。古代用来表示财产分割、传承的通用词是“析产”。(54)如《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第4200页):“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明史》卷158《鲁穆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20—4321页):“漳民周允文无子,以侄为后……因析产与侄”。然而,时过境迁,近代以来,继承却成为财产传承的通用语汇。同时,由于古今财产制度的不同,析产对应的是共有体制下的家产传承,而继承反映的是单纯的个人所有权基础上的遗产转移,于是,中国古代的家产传承,应该沿袭传统称作“析产”,还是遵从现代称为“继承”,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55)可参见俞江:《继承领域内冲突格局的形成——近代中国的分家习惯与继承法移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卢静仪:《“分家析产”或“遗产继承”:以大理院民事判决为中心的考察(1912—1928)》,《私法》第8辑,2010年。
在笔者看来,完全以继承来指代中国古代的家产传承,肯定是不全面的;若沿用析产一词,虽然凸显中国古代社会与近现代社会的差别,却也淡化甚至是割裂了古今财产传承方面的有机联系,也是不合适的。应该认识到,古代中国的家产传承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其中既有继承的成分也有析产的成分。笔者曾撰文建议,以承袭人的身份将古代社会的家产传承区分为析产与继承两种不同的行为:家产共有人(男性成员)承袭家产的行为为析产,非共有人(女性成员)承袭家产的行为为继承。(56)参见魏道明:《略论唐宋明清的析产制度》,《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邢铁也以发生时间来区分这两种行为,父母在世时分割家产的行为属于“析分”,父母亡后的家产传承则为“继承”。(57)邢铁:《家产继承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唐宋分家制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14页。宋代对家产承继行为的契税征收制度,则进一步证明了以上区分的可行性与合理性。